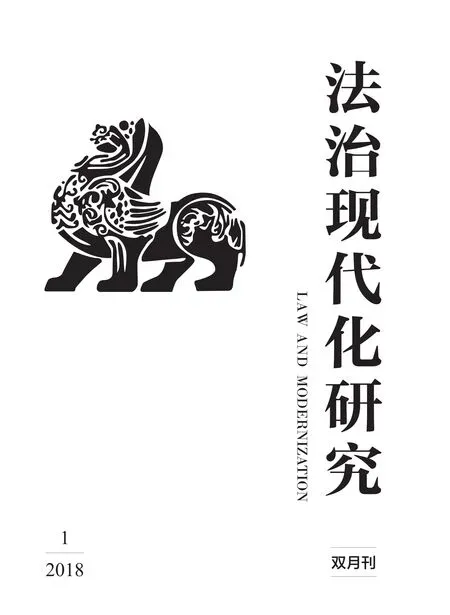财产权的进化史:事实与观念
[英]霍布豪斯 著 张凇纶 译
迄今为止,关于财产权演进的一般性论述,成功的作品仍付之阙如——或许以当下的知识储备,这样的作品实难写成。关于财产的资料隐晦不清且差强人意,类似局面从未见于其他制度的比较研究。法律理论与经济事实之间、成文法律与常见习惯之间以及权利的推定内容与实际享用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导致同一制度(在一定限度内)能被描绘的全然不同,且均诚意满满又言之凿凿。法律史学者关注规范或原则,但对真实的生活少有涉猎;反之经济史学者对制度细节毫无耐心,他们要求审视制度的实际功效,论断某些事件的转折引发了法律原则的觉醒,进而成为经济系统运行中重要(甚至是致命)的推动力。学者一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总能找到各种佐证,比如对事实进行撷取或隐略、援引行旅者(traveller)、民族学者、早期法典再或当代习惯之观点,等等。事实上,学者对制度的研究日复一日,而在自己的论证中又可以忽略其他观点,要是这样还找不到支持自己的论据,可谓奇哉怪也。不过,试想让我们的社会历史学家讲讲任一世纪中英国土地财产权之全貌,但却不能提及该财产的历史沿革,这会是多么困难。既然如此,我们就不难看出,原初住民的财产历史缺少书面文件,只有某些行旅者的陈述。尽管这些人的观察可能非常犀利,但若要重构此间财产权利的真实特性,科学的方法该是多么重要。
一个简单的说明就足够了。在某个处于粗放型农业经营的原始共同体中,某人告诉行旅者:“这块土地是我的,而那块土地是邻居的。”当我们看到这句话,大概会认为此间土地的个人所有权已经发展成型,而不会想到要考察是否存在保有(tenure)的条件。而其他观察者若认为该土地“属于”部落,于是得出迥异之观点,即认为这是原始共产主义存在的有力证据,似乎亦有正确之处,但之前的陈述中完全没有说明部落成员对土地的实际使用采取了何种形式。针对澳大利亚的某些部落,有人断言此处完全没有私人的土地财产权;[1]Walter Baldwin Spencer and F. J. Gillen, The Northern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 (London, 1904), p. 27, etc.而亦有学者肯定土地既不属于部落,也不属于不同家庭构成的集体,而是属于某一男性。[2]比如 Grey and Eyre, cited in Richard Hildebrand's Recht und Sitte auf den verschiedenen wirtschaftlichen Kuhurstufen (Jena, 1896), p. 4.这究竟是部落之间的差别,还是学者彼此的歧见?此处涉及的方法问题与困境,不仅让我们想起Howitt先生在经典作品中的一个片段:[3]Alfred William Howitt, The Native Tribes of South East Australia (London, 1904), p. 83.在新南威尔士的沿岸部落中,只要某个儿童出生在某块土地上,这块地就是“他的”,他可以在其上进行狩猎。甚至(该儿童的)父亲或母亲亦可据此“取得”此块土地,即便该地并非父母所属之地区。一位老人说道:“男人出生之地就是他的地区,他总可以在这里狩猎。所有在这里出生的其他人,也有权这么做。”不难看出,这种产权模式对文明人而言可谓天方夜谭。对每一位土著的访查,都会让人得出“土著享有自己出生之地”的结论。如果没有碰到同一个地区同时出生的数个人,仅凭之前的访查,我们就无法了解如下事实:此间土著将某块土地称为“属于自己”,他所指涉的财产模式和我们的认知完全不同——既不是个人的,亦不是共有的。
在事实难于确定之际,一般性的理论概括往往靠不住。此处仅设计了若干要点,希望据以此明确财产在社会系统中的不同功能,财产权概念所经历的嬗变以及财产权与社会的一般发展之间的关联方式。我们将简要考察:(1)财产权的一般观念;(2)财产权所依据的心理学条件;(3)财产权社会功能的特定要素;(4)财产权在社会发展过程之若干阶段的表现形式;(5)根据上述考虑,简要回顾并评论若干典型的财产权理论。
一、财产权的观念
根据社会理论之要旨,财产权被理解为人对物的管控。人需要食物来吃、工具来用、土地来劳作,而劳作自然需要“站立”与“搬入”——为了保障所需,该人至少要对使用的工具和劳作的地点保持暂时性的管控。但这种暂时性的管控或占有若要变成财产权,关键要进一步满足特定的条件。首先,该人的占有必须获得他人的认可,也就是说,必须具备权利的性质。其次,由于物品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其权利也须有持续性。该人对物的使用须可靠,且在一定的时限内,该人对物的权利不能仅限于物品在手之时,与物分离之际亦须得到认可。再次,该管控必须排他,如果与其他人共享对物的管控,则该物不属于其私人财产。但如果该人与其同伴共同管控某物并可对抗其他人,则该物属于他们连带共有(joint)或一般共有(common)之财产。不过,如果其他人亦可使用该物,则不存在财产权。财产权可分为私人型、共有型或共用型,但必须确定归属于某人或某些人,并得排除对抗其他人。
不过,所谓“排他性管控”,并不意味着“彻底性管控”。比如,甲为了某一目的,对某物进行排他性的管控,甲当然可以据此排除乙;但此时乙仍可为了另一目的,对该物进行排他性的管控,又可以反过来排除甲。“我”使用酒店中的某个房间过夜,当晚这个房间就是“我的”,可以排除任何人的使用。但房主对该房屋仍然拥有绝对权利,并可依此对抗“我”本人。或许会有人质疑,认为房主拥有的才是“财产权”,而这个例子中的“我”只拥有使用的权利。这一观点当然更符合习俗(usage),但我们会在最后对财产权的分析中指明,各种形式的管控与财产权实为种属。对物的管控可为全部或一部,但一部性的管控可逐步升级成为全部性的管控,因此二者之间并无泾渭之别。若说最为重要的区分,当属为使用和享用之对物管控,以及为了处分、出售、交换或遗赠而进行管控。后一种管控可在终极所有权(eminent ownership)的意义上被认定为财产权,但若将财产权仅限于此,会遗漏其中所蕴含的使用和享用之内涵。某人可能仅为某块地产的终生租户(life-tenant),对土地的处分会在该人死后,由法律、共有人或在先所有人的遗嘱所决定。但在该人在世之时,其对土地管理享有完整的管控,类似的条件可以通过代际不断重复。如果不考虑终生利益,就会造成财产概念与现实管控的主要条件之间的割裂。
这样我们便可看到,财产权是一项规则,在不同方向会衍生出不同的变体。财产权是一种管控,但与社会所认可和保障的管控多少会有龃龉。与现实的使用、占有或享用相比,财产权的内容可能更多,也可能更少;可能更可靠,也可能更不稳定。财产权可能归一个人,也可能归一群人。与某物之用途相比,财产权的内容可能更广,也可能更窄。但管控若欲被认定为财产权,则必须获得某种认可,必须展现某种独立且即时的物理性享用,且在某时刻须得排除他人的管控。在上述限制内,财产权在各个方向上都有变体,这些变体的种类和数量并不确定,且彼此之间无须互为支撑。
二、财产权的心理学
前述考量要素有助于我们探索财产权的心理学基础,对此则要论之即可。有些学者会提及财产权的本能,但这种说法太过简略了。当然,高级动物也会有财产权的基本观念:一条狗抓住的骨头就是“它的”骨头,如果谁敢把这根骨头抢走,这条狗就会非常愤怒——但如果拿走的是它并未抓住的那根骨头,此狗就不会那么激动了。笔者自己豢养了一只乌鸦,有一天,它偷了我的铅笔欲迅速逃走,就在此时,就像一切心虚的小偷一样(抑或是它正在用铅笔做游戏),它把笔扔在了地上,又迅速地捡起来。而当我想去把笔拿回来的时候,它冲着我的手指头就是一下子,就像在对我喊着“不要脸!”一样。上述实例显示,物品所激发的那种兴奋感——无论是食物,还是像(笔者的)铅笔那种特例,即霸占那些漂亮、精巧而又便携的物品——关键在于首次的占有行为,甚至是对特定物品的首次感知。因此一切伴随着(或附属于)对物品的感知与反应的训练,都会指向对特定物品(而非其他物品)的反应。这就构成了取得物品的心理认知:不仅适用于人类,同样适用于动物——狗与自己埋起来的骨头;鸟和自己的巢以及我的乌鸦和它的“贮藏”——取得的物品成了行为的长期基础,成了某种可以在需要之时依靠和回去找到的东西。不过,对人类而言,其财产必须是自己可以指望和依靠的物品,比如能永久居住的家、保障生存必需或享受的永久工具。因此,对有目的之行为所构成的有秩序生活而言,财产权是必备要素。正是基于相同的原因,财产权也是自由生活的必备要素。这就得以区分财产权与单纯的物质本身。如果一个人的餐食完全由权威专家定好并供应,这餐食可能非常丰盛而精致,而这个人也吃得营养均衡,但他对盘中的餐食不享有任何财产权,因其只有吃掉或者倒掉喂猫这两种选择,完全没有(为其他行为的)自由。如果一个人口袋里有一先令,他就可以用这些钱买点自己喜欢的吃的或喝的东西,也许买来的食品并不精美,但这个人是可以自行选择的,或做点其他事情。同样条件之下的两个人,一个人每周工资是钱,另一个人的报酬却是实物,那么前一个人就比后一个人更自由。类似地,在同样的条件下,一个人在自己土地上用自己的工具劳作,而另一个人却是(在他人土地上工作)领工资,那么前一个人就比后一个人更自由。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的生计越是能依靠适用在自己财产权上的劳作,那么就越能按照自己的品味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要言之,财产权的考量是自由必不可少的基础;反过来讲,自由的范围与所有权的如下要素正相关,即对所有权的保障与维持。
三、财产的社会因素:使用与权力
很不幸,一人之自由常是他人之不自由。在成型的社会中,一人的财产权固然意味着管控和享受,可以此作为自己劳动的基础和行为之规范,但更意味着对其他人的管控,以自己的财产权作为其他人劳动的基础,并规范其他人的行为。抽象的财产权概念当然会忽视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比如劳动者有权取得自己产品的理论,就完全忽视了如下事实:随着工业的发展,财产权最为明显的功能,就是确保某人的劳动产品能令他人获益。无论是历史还是财产权哲学,都在将上述两种关系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一方面,财产权以物质作为载体,指向永久化、秩序化、目的化和自我导引的行为。这些构成了财产权的整体内容,即当事人自己或与自己最贴近和最亲近之人得以直接使用或享用之权利。但从另一方面看,财产权也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它决定了劳动之人未必享有财产权,而享有财产权者未必劳动。正因如此,所有权人的掌控本质上也是对劳动力的掌控。所以,财产权就是“在牛眼窗里无所事事的庄园主”(Seigneur lounging in the Oeil-de-Boeuf)的法宝(alchemy):这令他能拿走采集者在田野里发现的第三个鸟巢,并将其称为“租金”。所有权不一定会包含对物质实体的掌控和使用,它可能和物毫无干系——正如阿根廷铁路的股东虽然名义上拥有一块“铁轨”,并且每六个月就会有红利进账,但其可能全然不知这条500英里长之铁轨的具体位置。
现在我们看到了财产权的两个功能:一是对物的管控,二是通过物品对人的管控。前者带来了自由和安全,而后者则赋予了所有者以权力,可见这两个功能迥然不同。尽管在某些因素中二者会针锋相对,但其性质终究彼此交缠,密不可分。关于这两个功能之间的关系,须到制度史中加以钩沉。接下来,我们要对财产权制度史的某些阶段加以说明。
四、财产权发展的某些阶段
在每个已知的社会形态中,我们都能看到一般意义上的财产权。男人的衣装、武器以及工具;女人的首饰;家庭的小屋或山洞,甚至前述居所中做了标记的部分,[4]比如,易洛魁族人以及其他北美印第安人的“长屋”(Long House)。Lothar Dargun在“Urspung und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s Eigentums” Zeitschreifi für Vergleschende Rechtswittenschaft [eds. Franz Bernhöft, Georg Cohn, and J. Kohler (Stungart,1884)] 坚持这一点。根据Seligmann博士的观点,Vedda一家在共有的山洞中有自己合适的位置。一俟获得他人的认知,便可归属于这个男人、女人以及这个家庭。Seligmann博士提供了Vedda一家所拥有的财产清单:
“一把斧子、一把弓和若干只箭、三个罐、一张鹿皮、一个燧石和一块铁器,以及一个火绒、一个用来装水的葫芦、一个草袋子(带有草做的盖子)、一些盒子形状的东西来装石灰以及一些备用的衣物。”[5]C. G. and Brenda Z. Seligmann, The Veddas (Cambridge, 1911), p. 117.
原初社会亦认可当事人这些个人物品享有权利。偷盗至少会引发个体的憎恨,而且当事人会根据习惯的形式提出补偿要求。一俟公共法院成型,其即开始管理此项权利,并开始针对两造适用相同的一般规则和类似的方法,以便确定不法行为。[6]考诸外人对原初住民的观察,难谓不够细致;但十中有九都意在说明原初住民无视白人的财产权。问题是,原初住民会如何描述白人的道德?他们又会如何看待文明人的财产观?(这些都付之阙如)的确,有的案例显示财产未经许可即被拿走,而且也没有受到谴责,但这肯定是特例。为了讨论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对权利的社会基础进行一般性的讨论(尽管这偏离了我们最初的论题)。对一切人而言,财产权从一开始就获得了认可,正如人之权利或婚姻权利一样。就这一点而论,所有案件都显示了相同的发展轨迹。我们需要考虑的重点在于,何种物品得成为财产权的客体;它们又是谁的财产权——用更加根本性的分析术语就是,(财产权)对物品包含哪些排他性的管控,且又是由谁来管控?
根据我们的了解,在最原初的部落中,即靠采摘水果、刨挖树根和打猎为生者,可成为财产权之客体的物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部落成员的个人财产(正如前述);另一类则是土地——未加清理和开垦的土地,当然亦是最重要的谋生之物。前一类构成了私人所有权,但很显然,这个小社会的生死存亡,主要取决于土地的所有权——因为后者决定了狩猎或采摘的自由与限度。既然如此,上述共同体对土地的所有权是何种形态?是共有还是个人所有?若能给出翔实而清晰的回答,我们就能解决原初财产权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村落共同体性质的争论亦可尘埃落定。很不幸,相关的资料缺乏且不清。在某些范例中,土地共同占有的定性当属无疑,前述澳洲中部的部落恰堪为证:首先,部落有自己的土地,部落里的人知道土地的坐落,且该土地与相邻部落的土地之间有明显的边界。部落内部有分组,分组之下又有再分组,最小的单元则是由若干家庭组成的“当地群”(local group)——在一个部落中,最大的群有40个人——这些单元作为一个整体,在确定的区域内游牧,而整个部落则在整块属于该部落的土地上游牧。在此区域内不存在个人财产权,资源对部落的所有成员都免费开放,但部落之外的人若想在此处狩猎,则必须获得许可。每个部落边界均依据习惯而定。更重要的是,这个区域里保留着生活在上古黄金时代(Alcheringa)的祖先之灵魂,而这些灵魂又会在部落成员的身上转世,故所有权与这一块土地的中心紧密相连。用我们的术语来讲,这块土地当然是部落的共有财产。否认此处猎人们(对土地)享有共有财产的学者,只能将其称为主权(sovereignty)而不是财产权。究其实质,此处的集体诚然构成了自治单元(autonomous unit),但唯一的推论是:政治性的管控(如果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概念)和财产权在此并非截然对立。对土地而言,主权和财产权的界分要等社会发展到相当晚近的阶段才会完全成型,且仍有人质疑,上述两者的彻底界分实为不可能,因其对社会将造成毁灭性的后果。不管怎样,(在上文讨论的澳洲部落中)对土地的控制属于群体,任何成员都不享有能对抗群体的排他性权利;而每个集体都可以排他性对抗其他集体,这一权利亦受到其他集体的认可。此种权利实在是太像共有所有权了:如果所有的狩猎族群都适用相同的财产系统,土地财产权体系之发展的起点就很明确了。
很遗憾,这个假设并不成立。由于狩猎和采集食物的必要性,土地权利会形成进一步细分的状况。我们发现了各种实例——既有澳大利亚的,也有其他地区的——证实土地可以由狩猎者及其家人私有。[7]找出10个适用共同所有权或5个适用家庭所有权的澳大利亚部落(团体)是很简单的。但有些学者,比如Gidoen Scott Lang、George Grey、Edward John Eyre以及Edward Micklethwaite Curr则指出,此间仍然存在个人所有权。不过,由于证据存在冲突,在某些案例中我们只能推断存在双重类型的所有权。因此J. Browne在Dr. Petermann于1856年编辑的《地理学》一书中,指出其间描述了其所熟知的四个西澳大利亚部落,其土地归家庭和个人所占有。但他也指出,由于部落在整个地区游荡,不分彼此;对外人入侵会加以反击甚至战斗,因此很难说这个“个人所有权”包含了哪些内容。他指出,或许所有权人唯一的特权(prerogative),就是在反抗入侵中担任头领。至于家庭所有权,我们必须记住澳大利亚当地的团体规模往往甚小,几乎只是一个家庭的扩大版。因此家庭所有权与团体的所有权可以互相转化。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对狩猎战利品的分配规则在澳大利亚很常见:在我所调查的20个案例中,10例是在整个部落中分配,6例是在亲属间分配(包括妻子的亲属),剩下的4例则规则不明。由于很多案例中的证据隐晦不明(前文已提及),本文以Vedda一家为例,因其相关的报告还算准确。Vedda一族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每个家庭规模很小,家族人员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每个家庭集体有自己确定的狩猎区域,但在每个区域之中,每个男人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这一块土地可以作为普通的遗产,也可能给予自己的某个儿子或某个孙子。该土地亦可转让。但无论是给自己的子嗣还是其他人,土地财产权的流转都必须取得家庭集体中每个成年男子的同意。[8]前引⑤,Seligmann书, pp. 107, 111。通过这个实例,不难看出即时性的所有权属于私人,但最终极的(eminent)所有权属于集体。集体(对所有权)的管控得以保障如下这一重要事实,即只有集体成员所生的子嗣才能保留对土地的进入和享用。在上述模式之下,土地既可能是共有财产,也可能是私有财产,还可能是两种模式的混合——但无论如何,对土地仅可使用而无(处分)权力。对土地的保有是占有性的(occupational),而且笔者认为,我们暂且可以推断这是原初之土地财产权的一般特性,也就是说,是在历史发展最低阶段中生产基础的本质属性之一。[9]
为了给母婴护理员提供实训机会,公司与有关妇产医院签订了实训合作协议,进行护理服务实操培训。同时,为了提升服务品质,采取了专家上门到家巡查方式,一对一沟通指导,对客户产后心理疏导、月子餐饮搭配提出合理建议。
农业的起源证实了上述推论。土地须被清偿一边种植庄稼,但其肥力就会很快衰竭(也许一次收割之后就不行了),这样小集体只好搬到另一个地方。由于某一时段同时进行垦殖的土地只占部落所有之未垦殖土地中很少的一部分,而且任一部落成员都可以进行狩猎,因此清场的权利不是个问题。但某人一旦清场(至少是到开始垦殖之时),该土地就归该人及其家人所有。在这个阶段,私人财产权只是占有的权利,一旦庄稼收割完毕,清场可能要比开垦还要麻烦无益。正所谓“年复一年,土地不变”(Arva per annos mutant et superest ager),仍有大量的未清场土地归部落共同体所有,每个成员都可以对其进行开发。[10][ Karl Friedrich Philipp] von Martius在 [Beitrage] Zur Ethnographie [und Sprachenkunde] Amerika's [Zumal Brasiliens (Leipzig, 18670)]一书中对巴西土地保有制度的评论可供比较。这一评论足够明晰,但仍然受到了Dragun的批评。(Entwicklungs-Geschichte, pp.51-54)这就出现了永久性的共有所有权和暂时性的私人占有并存的局面。但在这一节点上,一切皆有可能:农业可能变成集体性生产——田地的耕种和庄稼的收割都可能由集体完成(正如Karaya部落)[11][E.]Ehrenreich, Vervf [fentichangen aus dem], Königl [ichen] Museum [für Volkerkunde], Band I [(Berlin, 1889)].,而且会建立特别存粮以备所需[正如克里克人(Creeks)];但更普遍的情况是,由于耕种技术不断发展而日趋密集,占有开始由暂时性变为永久性。由于土地需要休耕,因此就出现了两田制(two-field)或三田制(three-field),而对同一土地的周期性占有就逐渐强化为永久性的所有权。不过,这种占有并非由个人所为,而是由家庭或亲属所持。由于亲属在长屋(Long House)中共同生活,存粮亦共有,因此其在集体中构成了整体性的共产(communism),规模虽小但联系亦更为坚固。[12]Iroquons的共有房屋中包含5到20个家庭,共同存储粮食,且由监管之母(superintending matron)在各个家庭之间分配义务。克里克人居住在簇集型房屋中,但基本模式类似。(Lewis Henry Morgan, Houses and House Life [of the American Aborigines(Washington, 1881)], pp. 64-68)但可能随着亲属关系的解体,抑或作为种植技术发展的直接结果,[13]目前的证据还不能为我们提供从亲属共有到个人所有这一转变的固定顺序。它更像是在不同群体中遵循了不同的发展轨迹。土地的清场者或耕耘者对土地拥有了私人财产,可以让渡、出售或遗赠。[14]因此根据 Anton Willem Nieuwenhuis的考察(Quer Durch Borneo [ (Leiden, 1904, 1907)]),在婆罗洲的Kayans,未分割的土地可为任意人所获取,但一旦加以耕种,则土地归于私人所有权,可以被出租或交易。根据[ Henry] Ling Roth的考察(The Natives of Sarawak [ and Britch North Borneo (London, 1896)]),在山地迪雅克人(Hill Dyaks)中,土地在部落界限内非常充裕,但个人所有权非常少,唯一的例外就是临近房屋的个人地块,后者可以进行交易。农场的位置一般会由部落议事会决定,因此一条路即够所有的人使用。而在海洋迪雅克人(Sea Dyaks)中,一个男人可通过对土地进行清理而取得对土地的产权。对已耕种地块的即时所有权可以让渡于亲属、家庭或个人,但集体仍然对该土地保留着特定的支配权利与管控权力,比如,不得将土地转让给非集体成员,除非获得集体成员的一致同意。[15]早期中世纪的德国即如此,Richard Karl Schröder, Lehrburh der deutschen Rechtsgeschichte (Leipzig, 1889), pp. 207-208.随着对集体或酋长基于清场而取得新土地之权利的认可度日益提高,这种权利的价值也逐渐增加。
集体可能仍然保持对耕种的一般性管控,并且针对其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共同生活的一切习俗性规范,集体都保有管辖权,并且是上诉的终极裁决者。这一传统演进成了欧洲中世纪的庄园法院。不过,仅仅对耕地进行耕种是不够的,随着农业的发展,还需要驼兽(beast of burden),而且在公共牧场的放牧权和对荒地的使用权对耕地的保护亦至关重要。但公共牧场和荒地仍然是集体共有的;对草地而言,集体需要根据每个持有人的需求来分派使用。最后,如果家庭持有不均,无法满足需要,则需要通过定期的再分配系统来维持集体的凝聚力[正如在俄国的米尔(Russian mir)那样],而这需要相当谨慎的努力。
尽管类似的系统一度与个人所有权之发展相伴,但其实在太过原始,因其将财产权与使用(而非权力)相连。[16]笔者曾考察过100多份针对原初文化中农业与放牧族群的描述,只发现了10例允许土地进行租赁(leasing)或租借(letting)。在财产权作为生存工具之前,每个男孩在成长为男人的过程中,都有赖于社会结构所保障的生活—经济基础。他会继受家庭土地的份额,有权使用牧场、草场和荒地,且权随地走;嗣后若家庭规模扩大导致个人土地份额减少,该人可以获得集体的同意,在荒地中进行额外的垦殖。如果出现人口压力,受到影响的会是邻居之族群,而不是家中无地之贫民。人口压力有可能带来部落的骚乱、迁移甚至争战。这或许是失序的一个可能之根源,但除此之外仍有其他原因。人生来即不平等,一家兴之同时可能另一家废。一俟承认了债务奴隶——尤其是因未支付赎罪赔偿金(wergild)[17]赎罪赔偿金(wergild):在古日耳曼和古英国法中,每人之“价值”取决于其社会阶层,一般是赔偿金;如果是自杀,则是罚金;如果是其他特定类型的犯罪,则可以通过进一步追究责任或惩罚使犯罪人得以开释。[英国牛津词典(OED)]而引发的债务——则当事人可能落入债权人之手,为后者开垦土地。这一劳役在战俘处亦有体现。[18]关于日耳曼人的此类农奴,参见Tacitus, Germania, [chap.] xxv; Schröder, pp. 46, 47.事实上,整个部落都可能沦为强者的附庸,[19]即便是狩猎部落亦可如此。比如,南美的Mbaya就将临近的部落Guanas制服为自己的农奴,命令后者为自己耕种。在集体中,首领的地位会随着军事组织的膨胀而有所提高,而其所信赖的追随者即成为贵族,高居于自由民大众之上。首领的提升对其他人则意味着相应的压迫;某人成为贵族,则意味着有人须为其服役。
但除了上述趋势之外,仍有另一经济之发展,而我们对此置墨甚少。在世界的某些地区——特别是东欧和亚洲的干草原(steppe)——牧地为从狩猎阶段发展到另一形态提供了机会。与耕种土地相比,集体对占有畜群的设限要少得多;牲畜虽说是家庭财产,但家父堪称真实的权利人,其权力比其他人大得多。更重要的是,畜群的财产权往往盛衰不居,因此在放牧型社会中,贫富之别往往一目了然。某些放牧型部落确实蓄奴,其他部落相对贫穷的成员则会成为奴隶而提供服务。[20]或者整个部落都为他人伐木和汲水。比照Herman Jeremias Nieboer发现,在放牧型群体中,有10例明显存在奴隶制,而有12例则不存在奴隶制。 Slavery as an Industrial System [( The Hague, 1900)].如果某个人看上去明显不是奴隶,但在共同生活资料中又没有自己能继承的份额,则该人会特别依赖于放牧的生活方式,(至少)在农业文明的社会中会极大地受到放牧状况的影响。最终,当某个城市的牧地和荒地被圈占,继而摧毁了残存的公共土地系统,进而导致了小型土地持有者的覆灭。[21]参见[R. H.] Tawney,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1912)]; 以及[ J. L. and Barbara] Hammond, The village Labourer [1760-1832( London, 1911)].
以上概述以西欧中世纪组织体的进化为例,向我们展示了经济的一般特性。关于在庄园以前之组织体的问题仍然争论不休,但对人类学数据的整体性考察证实了如下观点:在经济史的演进过程中,“村落型的集体共同对敞地进行耕种”是基础性的要素;“其余农村生活中的必要事务实为附属”。[22][Paul] Vinogradoff, [The] Growth of the Manor [(London, 1905)], p. 365.这里唯一的问题是,集体的私有财产究竟发展到了何种程度,以及最终极的管控是否得以保留?看起来,似乎最早对土地的持有只是为了使用,对土地特定部分的所有权人而言,该地块之价值会受到如下因素的约束,即该土地中当然属于共有部分的权利。但我们已经看到,首先此种体系容易导致不平等;而且上文已经指出了此间不平等会得以发展的若干方式。考诸中世纪的我国,国王权力的膨胀带动了将司法特权和财政义务许可于私人和教会,这些最终使得村落发展成了庄园。[23]比照[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 Doomsday Book and Beyond, [(Cambridge, 1897)].到了庄园时期,对土地的耕种既是为了领主,也是为了耕种者自己。领主持有的财产权是“为了权力”(for power)——严格地讲,领主所持有的是针对居民之法律权力,后者是经济性的贵族地位(economic appanage),实为保障财产权的权力。与此同时,传统体系中的一个良好特性得以保留,即正常出生的孩子仍然可以获得确保其劳作和生存的基础,他仍然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威格或半威格土地。[24]威格(virgate),是早期英国土地的度量衡。对范围说法不一,但一般而言是指30英亩(OED)。即便在最差的情况下,只要该人不是奴隶,[25](传统意义上的)奴隶制(Chattel slavery)在12世纪的英国已经消失。则其可作为佃农(cottar)[26]佃农(Cotter),是指拥有小屋(cot)或农舍(cottage),以及与之相连的地块(一般是5英亩),该人须负担劳役(抑或包含金钱或农产品的给付)(OED)。拥有数英亩的土地,并且基于惯例(practice)或严格习俗而对牧地和荒地享有权利。很遗憾,这些权利并不稳固,当时代发生变化,围圈牧场、自用地甚至暗侵荒地变得有利可图之时,只有土地的自由持有人(freeˉholder)才能提出抗议。[27]关于公簿持有人(copyholder)和习惯法的租户(customary tenant)的情况,参见I' awney.随着庄园系统崩坏,农奴虽然获取了自由,但却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这一叙事的轮廓如今已经明确,虽因太过冗长和复杂,此处无法加以总结,[28]参见Tawney先生和Hamnond夫妇之前引著作;亦可参见Gilber Slater, The English Peasantry and the Forclosure [of Common Fields]. London, 1905.但最终的结果人尽皆知:一方面,(领主的)私人所有权取代了传统的公共负担;另一方面,无地的劳动阶级(Proletariate)昔日可以无偿地作为集体成员——这亦是他们最主要的经济特权,而今则须背井离乡另寻良途。在二者之间的是农民,后者可以拥有产品,但须承租土地。
尽管如此,资本主义农民的表象只是财产权性质之剧变的一个微小表征,而这里所说的“财产权”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土地的私人所有权。在早期社会,我们实际是将土地作为生存的必需品,“土地的积累离不开私人占有”这一事实被认为是为了维护共同体的生存。但到了放牧阶段,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积累——畜群与兽群作为实在资本的最早形态,即刻引发了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界分。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总能引发这种界分,而后者对立法者来说永远是个难题——无论是雅典、罗马法还是我们这个时代。随着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当下文明社会的财富积累幅度明显提升,政治、宗教、民族、(有人还会加上)社会以及自由的边界都在拓宽,但财富的不平等也在增长。不过,这种不平等并非当下系统的基础性事实。问题的关键是大众对土地和资本存在需求,但这些土地和资本却属于其他人。笔者估计,在工业社会新出生的儿童中,每六个人就会有五个缺乏生活保障,没有维持自我生存的能力。他们有手有脚,但他们既没有土地来耕种,也没有进行耕种的设备。更重要的是,我们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进行农业生产,对于纺纱工、铁路工或挖煤工而言,讨论其作为个体拥有生产工具实属空谈。大工业的勃兴断送了个体对经济问题加以(任一形式的)自行解决的可能性。
由此看来,现代经济条件事实上废止大部分使用性财产权(除了家具、布料等少数物品),财产权成了为大多数人进行生产的手段。反讽的事实是,正是大多数人才使得财富大量积累,但财产权的权力却属于少数人。上述冲突在权力和使用之分化的影响下日益加剧。大地主还可以直接管控自己的地产,其所有权与职责并存,二者之间的关系甚至比土地保有与政治功能之间的明显联系还要牢固。在现代的早期阶段,资本家雇主与雇工刚刚开始分化,在工业革命的头两代人中,一个典型的特质是,资本家就是雇主,反之亦然,恰如其名。也就是说,他之所以能积极地参与经济活动而有所作为,恰恰是其拥有财产所致。但随着财富积累,更深一步的分化开始出现:对资产的占有和经营之界分愈发成型,而随着股份制的兴起,资本被划为股份和存单,而二者不过是所有权人的纸质证明或英格兰银行的出入凭证——更有甚者,持有人可能对英格兰银行从未谋面,其只关心一季度或半年之后的资产回报。但正是这些投资和资本,掌控着全世界成千上万人的生活。正是资本机制的指导和管控,才使得世人纷纷流动,劳动力得以维持。如今功能的分化已臻完成,而且更奇妙的是,资本的所有人对工人而言,就像是一个幻想,一个抽象、遥远且未知的真空泵,它将工业生产的成果按一定比例抽取,但却对劳作本身毫无任何贡献。
五、财产权的诸理论
以上之论述涉及财产权制度在社会演进中的各种形态,接下来我们要讨论思想家们关于财产权之基础与功能的不同理论,两相对比,颇有助益。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攻击私有财产、推崇共产主义的观点;随后是为私有财产制度提供一般性的理论证成,或基于经济价值,或基于伦理价值;最后,我们要看看基于财产权的不同类型和功能而提出不同解决方案的理论主张。
其一,财产权有时会受到攻击,可能基于哲学,也可能基于宗教。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的目标是尽量明晰地描绘出一个完全一体化之国度的样貌。所谓一体化,正如器官之于身体:某个成员的苦痛对国家而言,正如手指之疼痛对个人一样。柏拉图发现,家庭和财产权对个人对抗社会集体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因此他废除了二者:身居高位的守护者(guardian)过着最社会性、最哲学化的生活,不容得其顾及家庭或经济利益;共产主义所推崇的利益分配并非为了享乐,而是奉行简朴——正是在这一点上,柏拉图式的哲学家可能会被认为是修士集体的原型。柏拉图在这两方面的见解都招致了批评:过分强调集体化与统一化,会导致对个人人格的破坏;而“拒斥物质”这种论调本身就是自我毁弃的。人的生活不可能没有物质,只要其生存之必需品须有赖于他人的意愿,则其生活亦有赖于他人。一旦没有了生存之必需品,则人寸步难行,自然也就等于放弃了自我导引和自我否认,而后者正是赋予人以灵性之自由的关键,最终必然是完全放弃个人自主。
不过在古时,财产权规则亦曾受到自然法观点的批判。在那些赋予财产权概念以伦理色彩的思想家们看来,财产权无疑是一种人为的制度。自然的馈赠——包括土地及其产物——自始必须归所有人类共享;但财产权的取得是人的行为,而对取得的制度规则亦源自人定法。正因基于自然世人皆自由而平等,因此基于自然,人类皆享有如下权利:依各人目的对土地及其果实进行用益;自由劳作并依意愿享受产出。
上述观念彰显了实证法制度之下的自然共产主义(natural Communism),早期教会恰恰秉承这一点。但教会所提倡的基督—共产主义,并非基于柏拉图式的抽象统一体,而是基于理想中的兄弟之友爱与互助——包括共同信仰基督教者、同一圣父之儿子们以及一家人中的成员之间。这种理想只对小范围内的集体成员有用。当教会要谋求基督教伦理与国家法之间的和解之时,其不得不求诸斯多葛学派对自然法与政府的实证法之间的界分。尽管共产主义据称是教会法发端之时的自然法,但在社会结构中,对于那些决定财产权持有和财富分配之条件的国家机构而言,它既不能提供指导,也不能加以证成——除非是为了保障征收税款以便对教会和贫民提供服务。因此共产主义的理论在尊重既成机构的前提下,成了慈善的原则。
事实上,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共产主义更多是一种情绪,而不是一个体系。在小规模的集体中,共产主义尚有用武之地。比如对家庭而言,每个成员聚居,因此家庭的本质就是共产型集体。而且共产主义的成功运行,有赖于小集体中的有志者——一旦他们热情退却,则共产主义就难以为继。而一旦集体规模扩大,那么只有在享用物品却不需要履行相应义务之时,才能适用共有的原则。比如公共空间、游乐场、照明以及如下因素的某些方面——包括清洁、公共卫生、秩序以及良好政府——都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共有财产。每个人都可以享用,但无须付费——因为在上述物品中,有一些财产是只有每个人均可享用方得存在;而其他财产适用于部分人和适用于所有人的成本完全相同。但这些财产仅仅是生命中最外围的东西。
其二,大部分思想家都认为,为保证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必然存在关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成果的系统性分配方案。社会有机体功能很多,而每个功能都要求相应的激励和基础,因此最为流行的财产权理论,就是将劳动权和劳动之产出相结合。正是基于这一点,洛克为财产权提供了先于实证法的合法性证明。根据自然法,土地归所有人类共有,但自然法同样申明,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享有财产权,其中就包含了可劳作的双手。正因如此,“混合其劳动”之物便可归属该人,其中包括其通过占有和耕种所索取的部分土地。但洛克亦明确指出,这里的财产权受到使用范围的限制:“谁能在一件东西败坏之前尽量用它来供生活所需,谁就可以在那个限度内以他的劳动在这件东西上确定他的财产权;超出这个限度就不是他的分内所得,就归他人所有。”可见洛克的理论与“独占”(engrossing)并非不相容。但很不幸,洛克的理论仅适用于“美国人”,因为只有美国人的土地才仍然非常充裕甚至过剩。当洛克将财产权视为组织化社会中已经建立的制度之时,他就只能给出一些苍白且无奇的结论:“很明显,在社会和契约的边界之外,人们已经达成一致,占有的土地可以不相称且不平等——因为在法律所规范的政府之下,为了保证个人可以拥有多于自己所利用之物,又不会引发物品之败坏,人们已经共同探求了一种方式并获得了认同,这就是接受金银。”[29][30][英]洛克:《政府论》(下篇),第五章。这一段的一个更聪明的变体,参见《政府论》(下篇)第五章, ed. Peter Laslett,2nd edn (Cambridge, 1967).
的确,洛克所说的是一般情况,即法律和政府应当与自然法的原则相一致。如果我们将上述观念适用于财产权,就会发现洛克如果还活着,他亦可能得出非常激进的结论。洛克的观点固然可以作为财产权的合法性证成,但也可以视为对工业组织的批判。看起来,个人的权利包括如下:首先是有机会进行劳动;其次是拥有劳动产品;再次是对这些产品进行使用,除此无他。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用益性的财产权”。这一概念是个人主义的,但亦可做社会性的解读:首先,社会是一个集体,决定了经济制度的结构和运行;其次,在社会中人们为了交易而生产,而劳动本身作为一种社会机能,劳动的价值就是劳动的回报。也就是说,洛克的理论等同于承认,每个人的社会权利于经济秩序中各置一席,其中既有机会在社会服务中贡献自己的才能,也可以就其贡献部分的价值索取相应的回报。
其三,不过,亦有理论认为:集体只是社会的特性之一,真正的共有必然是诸多相异部分的汇总。这一个人主义理论远比洛克激进,而且历史同样悠久——亚里士多德学派对柏拉图的批评就源自此理论谱系。上述理论还认为,财产权针对外在物品,对人格(personlity)的全面表达意义重大。为了强调这一点,我们或许还可以提及亚里士多德,后者曾将共有原则阐释为单纯的宗教热诚。私人占有兼公共使用听起来很不错,不过说实话,也就只能听听而已。当事人利用自己的占有物,却要坚持如下格言的精神,即“友人之物皆共享”(the things of friends are common),社会根本无法依此制定成系统的法律。
这一理论谱系以认定财产权是人格实现之工具为核心,在现代社会得以复兴并扮演了重要角色。一般而论,以上所述足以预先证成该理论。我们应当承认,如果某物品可归自己所有,可以抛弃或找回,亦可依自己的意愿加以使用,这样的物品是有目标之生活的基础,自然也是人格之理性化与和谐发展的基础。但若将这一理论作为财产权制度的基础,后果往往会被忽视。一方面,它等于对社会进行了谴责,因社会系统中以供人格发展的财产之种类和数量有限,并非全体公民皆可取得——即便是并无过错而仍有资格者亦然。一个社会若奉行“财产—人格”理论,则会拒绝一切现存的财富分配机制,也不会承认任由少数人聚积财富而大多数人赤贫如洗(就维持其生存的现实目标而论)的财富积累方针。这样一来,作为一种保守主义理论,它内部就蕴含了激进革命的种子。而另一方面,如果这一理论要求财富分配的整体化且无例外,就会以灵魂之健康为标准而限制财产积累。其断然不会承认如下事实:财产权的占有从土地上得以释放,其不仅是为了自我保护,也是为了控制其他人。要言之,财产权的合法性变成了对富人的排挤,财产权的个人主义伦理轰塌了自己的堡垒。
其四,当然,对于区分了基于劳动而取得和基于生产资料而取得的财产权理论,我们亦可以一般性地将其称为社会主义式的财产权概念。但就理论层面而言(即不考虑实践应用),这一类学说的困难包括:首先,细分上述两类财产权几乎不可能;其次,考察个人获取生产资料的条件、回报的伦理基础以及范围都非常困难。不过,我们首先要区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后者而言,一切物品都要作为享用之对象而平均分配,完全不考虑支付的价款或提供的劳务。而对前者——以及一切适用社会主义理论的社会——来说,财产权并非归于一切人,而只是为一切人共同持有,财产权的分配或取得都取决于集体的规则。不履行社会所分配到己之相应功能者,不能享用财产。社会主义者面临的困难始终在于:集体规则如何与个人自主的创新性与进取心相协调?甚至有人会质疑,在纯粹的社会主义体制之下,上述难题实为无解。
这一难题在民主组织的心理困境之下愈发严重。公有财产与共同行业(common industry)都致力于共同善与秩序,而后者又是基于公意。当我们谈及这些,似乎自然而然。但公意所在何处?它是修辞学者的虚构,还是生活中活生生的现实?在实践中,公意是普通人皆有贡献的集体决定,因而每个人在一般意义上的人格皆得以表达?还是执政者和专家的指令,而普通人只能被动接受,只因自己无他处可去?如果是前者,那么集体财产与人格之间的有机关系,正如占有某块土地的农民与了解每一寸土地之生产力的所有权人之间的关系一样。而若为后者,则集体行业成了一种机制,每个人沦入其中,成了毫无思想的齿轮,终日转磨且毫无自由,一如资本家之工厂里的工人一样。每个人都像物品生产中照看机器的人一样,只能进行碎片化的工作,对其工作的社会价值毫无意识,而只关心产品能不能响、完不完整、到了陌生人手里能不能用,以及会不会造成损害——这些陌生人与自己从未谋面,也永远不会结识。上述问题触动了当下某些有识之士,后者开始寻求对财产权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希望重新复兴个人主义,而不是推进集体主义——近年来立法受到了集体主义的深刻影响。这些人的目标是建构有点类似中世纪的组织体,但去除了后者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他们所渴望的,是小型土地所有人与自主工人的历史时期。
财产权制度一旦关涉土地,则其适用必然受限。但首要的问题是,财产权制度受到经济发展之既定事实的阻碍,包括大规模生产以及世界市场中货物的繁杂交易。尽管如此,上述理论的意义,就在于认识到了财产权观念中不可磨灭的价值内核。我们必须看到,如果私有财产基于某些原因(且在上述局限内)有成就人性之效用,那么公有财产对人性的表达和社会生活亦有同样的价值。关于共有财产在现代经济组织的困境,我们需要发现一种方法,其能与新时代工业生产条件相适应,能保障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公民权利,即在工业体系中有一席之地,对公有产品能有所指靠,而无须依靠私人慈善或官员的自由裁决。
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就是保障国家对自然资源之财富和先辈积累之财富的终极所有权,并且对工业行为和劳动契约握有的最高掌控权。我们不能重建早期公社。我们也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有遗产、土地以及犁具。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关系,类似于传统社会中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但它能适应复杂的现代经济现实,能够融合旧制度中的安全与新制度中的灵活性与自由。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部分基于教育和培训,部分基于工业组织的监督。我们必须重建个人与劳动工具的契约,必须保证个人享用财产的持续性,必须保证个人免于意外事故与无助——前提是该人有合理之勤奋与节俭。为了实现上述构想,我们必须重建这个社会:其中包含对某些物品的直接型所有权,但对财富生产的关键物品,则适用终极所有权(eminent ownership),这样才能保证个人享有“使用之财产权”,保留民主国家的“管理之财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