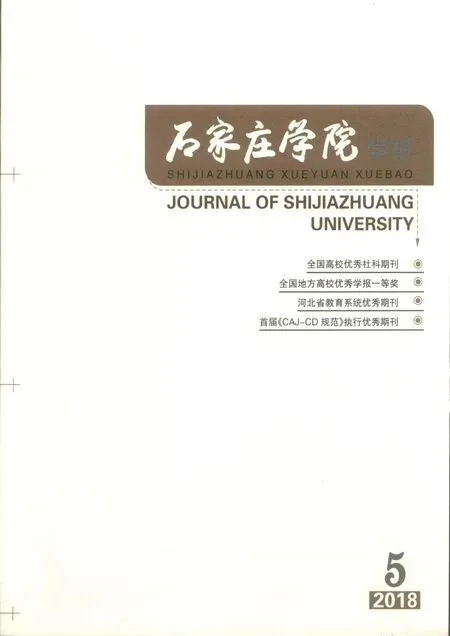民间文化逻辑嵌入乡村治理的思考
——基于河北张村的田野调查
张 爽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进程的深入发展,民众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要求日益增高。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新的执政理念——社会治理,并将其作为政府工作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联合国治理委员会界定,“治理”概念包涵四个特性:过程、调和、多元和互动。社会治理指在社会领域中,多元主体通过协调和互动而采取一致行动的过程,目标是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1]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治理逐渐延伸至传统乡村,并从中获得新的内涵。作为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乡村社会治理的成效直接影响着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从乡村“地方知识”出发,将传统文化逻辑引入现代乡村的社会治理,既是乡村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是对国家制度层面的地方回应;既落实了国家“从实求知”的发展要求,也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举措。因而,对地方文化逻辑研究既具有方法论意义,又兼具现实价值。
近年来,政府为改善农民生活采取的一系列农业措施,在缓解农民负担、强化国家认同的同时,也带来不可预料的治理危机,[2]例如,基层组织的权力弱化,即“悬浮型”政权[3]、“策略主义”[4]运作逻辑盛行等。这引发了中央宏观调控与地方实际需求之间的沟通失效,影响了国家资源在地方投放中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治理困境除了在政治经济层面外,在社会文化层面也存在,尤其是个体主义造成传统伦理社会的义务性逐渐被权利性所取代,致使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5]125。
鉴于事实层面的城乡二元体制,中国的乡村治理与其他国家存在着显著不同。这一概念自诞生之日起,就嵌入到“国家—社会”的关系理论中。从历史上看,中国民间社会有时与国家治理存在抗争,有时二者又存在着“共谋”。“乡村”这一概念既存在着客观视角中的行政边界,又存在主观视角上的文化界定。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指出,从“文化持有者内部眼光”出发才能把握文化研究的本真性,[6]32乡村治理的重要性和现实困境呼唤着学术界要进行“真实性”经验研究。因此,本文以民间内部的文化视角对乡村治理进行界定。
通过对近几年乡村治理的文献梳理发现,乡村治理主要沿着两个方向进行,即外部方向和内部方向。外部方向是指国家、社会或社会组织作为治理主体,直接对乡村进行资源输入式帮扶,通过控制资源形成乡村治理之实;内部方向是指国家、社会或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从乡村社区现实状况出发,对乡村进行针对性扶持。目前,内部路径逐渐占据主导,这是乡村治理本土化的必然结果。
学界对于内部治理路径的关注主要在乡村内部生活逻辑与现代社会治理的配合方面,其研究路径包括从微观乡贤个人到宏观基层组织,再到对乡规民约进行深层价值观研究等。在微观层面,陈秋强、吴雄梅、李晓斐等学者发现乡贤在参与乡村治理中发挥了重要功能,乡贤既包括社区中的政治、经济精英分子,也包括掌握文化权威的精英。①参见陈秋强《乡贤: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载《社会治理》2016年第2期;吴雄妹《乡贤文化与现代乡村治理——基于江西省乐平市乡村治理实践分析》,载《地方治理研究》2016年第3期;李晓斐《当代乡贤:地方精英抑或民间权威》,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在宏观层面,杨丽、闫臻、张康之等学者从乡村社会组织的角度探讨了乡村治理的模式。②参见杨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理论、问题与政策选择》,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闫臻《嵌入社会资本的乡村社会治理运转:以陕南乡村社区为例》,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张康之《论主体多元化条件下的社会治理》,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在价值观念层面,孙玉娟、王丽惠、陈华等学者以乡规民约切入来探讨乡村治理的深层本土逻辑。③参见孙玉娟《我国乡村治理中乡规民约的再造与重建》,载《行政论坛》2018年第2期;王丽惠《乡规民约与村治:研究范式的综述与反思》,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陈华、李荣《明清晋东南乡村规约与社会治理:以碑刻为中心的考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7年第4期。这些研究共同显示出学界对乡村社会内部治理中的“地方精英”自治路径探索,但缺少从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视角进行合理谋划的路径。而实际上,乡村生活逻辑源自地方精英和普通民众在生活诸层面的互动。因此,本文将重点关注普通大众的生活逻辑。
民众的生活逻辑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民间信仰,民间信仰为广大民众所共享、传承,是其日常生活赖以依存的核心和灵魂,在潜意识中支配着民众的观念与行动。建国后,民间信仰被斥为封建残余而遭极力打压,但其背后的文化网络和知识结构依旧存续。1982年,中央政府采取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宗教热在随后几年出现。同时,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呈现出从“迷信”到民间宗教、民间信仰再到民间文化的研究过程。
经验研究表明,文化形成过程是一个包容性过程,既具有历史感又具有现实性,是主体与文化网络互动的产物。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现代性导致传统因素不断被现代因素取代,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过程。[7]45-47而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现代化则呈现出相反的局面,传统文化因素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得到复兴。沐浴在乡村文化的熏陶下,沉浸在21世纪的社会变迁中,个人体悟的具身认知,形成了对这一现象的疑问:传统民间信仰复兴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本文旨在通过对河北张村民间信仰组织的分析,来探讨“地方知识”逻辑与社会治理的互动关系。
二、张村民间文化的现状
张村行政上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境内,在地理上位于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的冀北山地北部中段,地势呈现出南北高、东西低的特点。该村落形成于河流沿岸,国道112线穿村而过,村落大体呈条带状东西走向分布。村落的民间文化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公共领域,包括村庙文化、社火文化;二是私人领域,即“四大门”信仰(当地称为“保家仙”)。两部分信仰观念与活动相辅相成,共同勾划出村民的乡土情感和仪式行为。村庙和社火作为公共领域文化活动的两种形式,因其公共性与社区发展相互嵌入,表现出逻辑上的自洽,本文基于此展开讨论。
(一)村庙复建
张村后街北侧中心坐落着村民文化、民俗信仰的圣地——清净寺,村庙文化即是指清净寺的信仰与仪式。之所以称“村庙”,是因为村中人普遍称之为庙。清净寺分为前后两殿,前殿供奉的主神是关羽(当地人称关老爷、关帝爷),左右为其护法关平、周仓;在前殿的后门是韦陀护法神,也称韦陀护法菩萨。后殿由三个殿房组成,中间大殿供奉的是大势至菩萨、释迦牟尼佛、送子观音菩萨;东侧殿供奉的是药王佛;西侧殿是九神殿,九神是由雷公、电母、马王、虫王、阎王、龙王、苗王、土地爷、土地奶构成;门口东西两侧矗立着执笔判官、拿锁小鬼。该庙目前由“清净寺管理委员会”(简称庙管委会)负责。寺庙的始建年份已无从考证,据庙志记载该座寺庙始建于清代,村中老人也普遍认为这座庙应是清代建造,但副庙主描述这座庙始建于唐代。该寺庙在2003年被确立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农历每月初一、十五日,张村会开放村庙以便村民们前来祈福上香。农历四月十五日是举办庙会的日子,村民们会来上香、祈福平安,每年都会请县里的戏剧团前来唱戏,资金由村中富户捐助。
在对庙管委会成员的访谈中,他们均表示只是将寺庙作为文物古迹和文化遗址来进行保护、传承,且多次提到村庙作为一种民间文化习俗,具有教人行善、培养良心、孝敬父母等教化内容。村庙作为地方文化传统的“知识”载体,在传统乡村中,发挥着维持乡村和谐的功能,从治病、生育、养老、娱乐、传承文化等方面都是在行使社区整合的相应职责。
2015年4月,旧的村庙在新成立的庙管委会组织下开始破土翻修,资金来源主要是村中富户的资助、村民的捐款以及平时的香火钱。翻修本着节俭的原则,旧砖瓦清洗再用,村民自愿帮工。据庙管委会成员回忆,寺庙翻修从破损最为严重的后殿开始,由于后续资金充裕,才进行了全面翻修。同年11月底,翻修完毕,除钟、鼓二楼外,大体竣工,并塑了新的神像。目前,村子正在筹资修建钟、鼓二楼。
(二)社火盛行
社火是主要流传于北方地区民间的一种节日庆典仪式活动。“社”即土地神,“火”即火神,是北方地区人民千百年延续下来的一种民间信仰的遗脉。社火在张村也被称为“火神圣会”“花会”,是村庄集体性娱乐活动的重要形式,目前由村民自组织举办。据组织者回忆,“火神圣会”始办于清朝年间,距今有200多年历史。最初举办火神圣会主要是借助“火神”的巫术,帮助村民保证房屋不“走水”①“走水”在当地村民的话语中意为火灾。、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在演化过程中,活动逐渐祛除了巫术内容,而变为一种文化活动。
社火活动在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三至十六日这四天进行。接“火神”活动是全村过年的盛事,村民普遍认为正月十六日送完“火神”年才算过完。正月十三日是社火开始的日子。表演的村民们会穿戴服饰、装扮整齐到村庄北部田地迎接“火神”,将其迎接到村庙外搭建的棚子后,表演队伍绕村巡演一圈,期间不做停场表演,称之为“压街”,且晚上没有活动。正月十四日会应附近村庄邀请进行巡演;如果没有被邀请,则在村中进行巡演。这其中就会有人要求在自家商铺或者单位门口进行表演,称之为“打场”,同样晚上没有活动。正月十五日“火神圣会”是最为热闹的日子,白天晚上均会有表演活动,人们也会燃放烟花,要求“打场”的人也最多;晚上,灯会与“圣会”共同举行。正月十六日是火神圣会结束的一天,白天会进行“压街”,晚上举行送“地藏王”“火神”的巡境游神活动。在送二神时,先送“地藏王”,村民抬着火盆和有“地藏王”牌位的轿子,从村庙出发,至村最西侧折返,到前街东头。村庄道路两旁会燃放烟花,将“地藏王”送至村最东侧的田地中。人们将火盆中的灰烬倒出,村民下跪,会首要说“请地藏王将村中恶鬼、横鬼都带走,保村里平安”之类的话语,随后结束返回。人们再次回到火神棚子处,一起恭送“火神爷”,同样将火盆和牌位抬起,沿迎接时的原路返回至村庄北部,将“火神”送走。至此,社火“刹会”。
三、嵌入现代社会的民间文化
通过了解张村公共文化的现状,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社会特质在基层社会发展中仍保持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该村的民间文化能够得以保留、发展,与现代社会为其提供相应的生存土壤和发展空间密切相关。
(一)多元化主体
目前村庙管委会共由6人组成,全部是本村村民。该组织正式成立于2015年3月,设主任1人,主抓全面工作;安全员1人,负责防火等;会计1人,并配有出纳1人,均为女性;讲解1人;古建筑维修工程师1人。这些人均在县文物局登记备案,男女性别比为2∶1。虽然村庙有固定的管理人员,但在实际的活动中,仅靠管理人员是不够的,常常会有其他村民参与帮助维持寺庙的运行。早在该组织成立之前,就有一些固定的村民从事寺庙的维护、管理工作,1999年一些村民就开始筹建恢复村庙,而且该庙最初修建的人员也并非现在的庙管委会成员。当前村庙组织的成立是伴随着寺庙的翻修而成立的,据村主任介绍该组织是否换届由其自行决定。2015年村庙进行翻修的善款也是由村民共同捐得。由此可见,村庙管理的组织化程度正在逐步提高。在被问及为何要重修村庙时,庙管委会主任称:
这个是老辈子人留下来的传统,不能到我们这一辈就丢了啊!咱村就这么一个文物古迹,看着它塌了,心里难受。
社火活动的组织者称为会首,有正副之分,各1人,均为男性,负责整个社火的组织工作。其余表演队有各自的小会首1人,男女不限,负责组织各档人员。每年过了正月初五,会首开始联络小会首,由小会首各自联系自己档的人员,如有不愿或不能参与的告知大会首,由大会首再另想办法,找其他人参会。目前,正会首一直由聂姓老人担任,传自其同姓家兄,并有意让其孙辈后人接替。在会首人选上,原来的会首是由村中的大地主担任,需要有一定的财力来承办整个火神会的费用,而相应的副会首也要出资。比如,大会首出资1 000元,相应的副会首就要出资500元。据村民回忆,正会首一直是聂姓担任,副会首则不定期轮换。会首从小就参与到社火中担任某一角色,不用刻意去教导,在跟随长辈过程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而学会。如果家中后人不愿意担任则另找熟悉之人。此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小会首。解放后,会首则开始由村中有威望的人出任,并存在村委会主任担任会首的情况。现任会首就曾担任过村庄的生产大队队长、村委会主任等职。现在则是在村委会的名义之下进行组织,由村主任与会首共同承担举办火神会。圣会在兴盛时,总参与人数有200人左右,最低落时有120人左右。参与表演的人员以老年人居多,外村人参与到其中的人比例逐年上升,而本村青年人逐渐脱离。
(二)层级性组织
乡村社区的这种组织与村基层组织形成了一种层级性关系。庙管委会是在村委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村委会是清净寺的法人代表,但村委会不对庙管委会的具体事务进行管理。村委会代表庙管委会与县级文物部门交流,包括村庙文物手续的办理、宗教活动的申请等。这种关系得到了庙主的认同:
庙管理委员会也是在村委会的领导之下……但这是属于咱们村的,归他们领导,各管一边,村委会不抓这个。但是有情况了必须得向村里汇报……再一个,有事了去文物局办理,就是这么个结构。
与清净寺管委会一样,社火组织也是在村委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每年出会都要由村主任与会首共同向镇政府提出申请,得到镇政府批准后,由镇政府委派派出所民警进行全程的督导,防止出现任何打架斗殴、意外情况。在表演队伍赴各村表演过程中,要有村委会成员跟随。每年的花会所需费用都要由村委会出面进行筹款,特别是一些村中富裕户的资助。村主任介绍,只有他去才能筹得大额款项。在表演过程中,如果出现意外情况,如演出人员摔伤,则先用社火组织上的费用进行治疗,如果不够则由村委会负责赔偿。2015年,高跷上的某一男子,在表演中因摔倒导致手臂骨折,村委会赔偿4万元。村主任在访谈中提到:
以前都是土路,即使摔倒了,也摔不坏人。现在柏油路硬,出事了村里给补钱,那你给村出会,别人谁管。2014年把SYW①这里采用人类学匿名方法,将访谈人名字进行技术处理。(村民)他儿子胳膊给摔折了,赔他4万。全部都是村里出的钱。
2017年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村委会为高跷队买了部分保险。由此可见,张村村民在社区文化中,既扮演着组织者的角色,又充当着观众的角色。村民通过庙管委会、会首组织与村正式组织共同合作,采取协商合作的方式解决具体事务,形成了一种关键组织与弱势组织共同配合、多元性主体参与社区建设的局面。同时,组织者的现代生活逻辑正在与乡村生活方式相契合。为了保障村民参与社火的安全性,村委会购买商业保险。在现代生活中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常识行为,其实背后是市场逻辑与传统逻辑的相融。
(三)仪式性展演
仪式的特征之一是具有展演性,但在现代社会,其表演形式却占据了仪式的主导位置。在地方文化传统与现代因素交流中,仪式活动逐步走向现代化、去魅化。传统村庙仪式主要是发挥其宗教功能,村民寻得神明庇佑。近几年,虽然这种形式没有消失,但其娱乐功能强化,且教化功能分化。庙管委会会邀请县里的评剧团下乡演出以娱神娱民,而村民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愈发愿意为村庙复建、社火仪式捐钱、出力,“功德”箱中钱币的面额越来越大,以至于庙管委会要固定的会计和出纳管理资金。
社火表演的内涵体现着时代变迁。解放之前,“火神圣会”既表现出对火神巫术所带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祈盼,也表达着村民丰收的喜悦,并借此娱乐、放松。新中国成立后,表演的内容随之变为歌颂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在人民公社化时期,生产大队会为每个参与表演的人记工分,内容曾出现过样板戏,歌颂领袖、人民公社制度等。文化大革命时期,政府要求停止办会。但据会首说,在1969年中共“九大”时办了一届的花会,当时主要歌颂林彪同志,之后又被禁止。1982年,“火神圣会”重启,延续至今。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农村,农业渐衰,村民外出打工,参会热情降低。他们的祈求也从庄稼丰收转为多聚钱财、身体健康等。而更多的人将之视为娱乐性活动,出现较强的随意性。
在表演技艺上,许多独具特色的民间技艺节目随着表演人员的缺失而失传,文武场的表演音乐、韵律,表演所需的民间手工艺品也在随着年长人的离去而逐渐消失。传统的表演技能也降低了要求,增加了普通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传统的表演说辞随时代变化而不断更新,加入了歌曲表演等新形式。
从仪式逻辑看,传统生活中,村民是自愿参与社火活动以此来取悦“神明”,不获得实际利益。近几年,这种荣耀“神明”的行为没有改变,同时每年的参与者都会收到一定的金额,且面值越来越大,2015年是60元、2016年是80元、2017年是100元。
由此可见,现代生活的市场逻辑与传统社会逻辑正在紧密地融合。随着乡村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开展,乡土文化面临着消解与重生两种变迁之路。在一个社会和文化的重生过程中,文化活动的具体内容和实践方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迁,但仅表现为可见的内容与成分的变化,其文化的深层结构是不变的。[8]350实地观察的结果仅能描写一个社会结构的横剖面,而纵向的研究则有赖于对其历史的探讨,这一点则从结构式访谈中侧面了解。现实和历史两方面的总体调查表明,张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已走出传统社会的模式,正在向现代社会靠近。从最初的原生社会到现代的文明社会,从对神明的依赖到文化内涵转型,乡村文化根据不同阶段的时代环境与政策导向,基于自我生存的需要,不断调整以迎合新的社会需求,呈现出去魅化的文化模式。因而,张村民间文化的发展史,也是社会变迁与传统民间文化的互嵌重构史。
四、民间文化嵌入乡村治理的特征
乡土文化与乡村治理互嵌的形式多样,张村的民俗社会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这种互嵌治理模式的生存与繁荣得益于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生活的逻辑适切,且得到了地方基层组织的保障合作,这也是国家现代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的乡村发展之路。根据上述调查所得,总结互嵌模式的四大特点。
(一)“乡贤”身份的再现
“乡贤”在基层社会中基于才学、地位、声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治理职能,是乡村社会整合的关键力量,并表现出维系国家与个人关系的中介作用。“乡贤”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有变化,但其表征的群体却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在张村,村落的文化精英、经济精英是这一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对家乡具有强烈责任感,以回报家乡的情结参与着乡村建设,在村正式组织的领导下,履行其社区义务,参与组织并支持社区活动。尽管文革期间,他们一度被消解,但改革开放后,又重新崛起。“乡贤”生命力的延续性说明这一社会力量是传统乡土社会生存环境与文化结构的产物,若充分利用则有助于实现乡土社会的良性运转。李晓斐指出,当代“乡贤”的核心特质介于自身的客观支配力与当地人们的主观认定之间,即“乡贤”具有由当地特定文化观念体系塑造与建构的特质。[9]人类学家庄孔韶在研究华南农民工的组织方式时提出“类亲属组织”的概念作为农民工的组织形式,同乡领袖发挥保护和组织的功能,带领村民外出打工。[10]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研究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社会时,提出了保护型经纪和掠夺型经纪之分,其中保护型经纪即村庄保护人角色。[5]43-44
(二)文化结构与现代化契合
乡村社会的文化结构与现代化发展模式相契合。在不断接受现代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传统社会的文化特质逐渐与之相融合。乡村社会的文化特质包罗万象、内容丰富,在与外界不断地交流互动中,能够保持多种文化并存,当与现代文化交融时,会自发地契合。这种契合是基于对传统乡村文化的尊重和保护之上的,传统文化融入时代特色,既有利于保护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又有利于促进文化创新。同时也应看到,乡村文化也在不断融入中而被重构,表演内容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融入现代因素,成为文化传播的新窗口,这是村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智慧结晶。传统文化具有其自身的包容性,因之可以历经千年而不腐,在现代社会依然可以在时代的感召下发挥自身的功能。
(三)二元组织结构倾向
乡村社会组织与村级正式组织相结合,呈现出二元结构倾向。在张村,乡村自发组织在改革开放后之所以能够适应新时期的社会发展和文化环境,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是贴合村落对组织的功能性需求而形成的。村委会发挥服务职能,得到庙管委会和社火组织的一致认可,后两者在名义上归村正式机构管理,但在具体活动中与村委会共同出力,分工明确。在对外展现中,以村委会组织来定位自身,具体细节则是由民众自发组织实施,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乡村居民自治与政府职能的并存与互补。但也应意识到这一格局具有其自发性、主动性和脆弱性。
(四)乡村社会文化的功能性
乡村社会文化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和社区养老功能。随着乡村现代化进程,尤其是撤村并镇政策出现后,原村落村民远离家乡到镇里,在心理层面具有失落感,而且在新居住地最担忧的是被边缘化。现代居住格局又使得人们之间的相互沟通机会大大降低,接触减少不可避免地就会产生误解,甚至是矛盾。在参与村庙活动和社火活动中,活动组织为村民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场所,有助于村民之间的相互融合。在社火表演中,有不少参与者是从外乡而来的,他们与本乡人在表演中相互合作、相互沟通、相互交流,提高了社区的凝聚力。
随着外出就业、升学的人数增加,村庄老龄化进程急剧加快。而且近几年农业成本升高、收益降低的现实,使得村庄老年人逐渐脱离土地,其生活日益闲散。研究显示,目前居家养老仍是中国最主要的居民养老方式,但乡村社区养老机构并不健全。[11]因此,老年人将业余生活投入到社区事务中,这种社区养老模式无疑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在调查中发现,许多从事仪式活动的组织者均为老年人。究其原因,一是时间充裕;二是有强烈的参与意愿;三是组织能力在日积月累中得以提升。在参与组织活动中,他们与同辈人共同合作,并将其奉为一种事业,提升了自身的社会获得感。
五、总结与讨论
通过对民间信仰介入乡村治理的特征研究,可以发现,民间文化与社会治理的互嵌遵循着这样一条路径:在村正式组织的保障下,村庄精英发挥主导性作用,通过社区组织平台提供活动空间,吸引广大村民参与其中。这种互嵌使村民在参与社会文化生活的过程中实现了乡村社会的上下互动与内外整合,其历时性与延续性为文化复兴提供了逻辑前提,也是社会治理得以进行的土壤。同时也应看到,在多元文化地区,由于其文化特质丰富、文化包容性强,文化的深层结构更具韧性,即使面对剧烈的社会变迁,若现代性文化因素的嵌入路径适当,社会结构依旧能够自洽。当然,从社会治理角度来看,基层政府组织发挥其服务性职能,是与传统文化得以保持正向关系的重要前提。
基层社会所表现出来“自愈能力”,既有微观层面的乡贤参与,即乡村精英广泛承担家乡义务,积极组织群众性文化活动;又有宏观层面的组织性介入,村民自组织与基层组织之间的合力配合,解决实际生活的邻里纠纷;同时,在价值观念层面,村庙宣扬的“助人为善、孝悌道义”在思想层面教化着普通民众。对民俗文化参与社会治理的经验研究表明,乡村社区的共同体逻辑正在与现代性的文化因素不断整合而成一个复合体。
对张村“地方知识”参与乡村治理的经验研究分析,不仅是了解其文化与社会互嵌的模式,更是以这样一个案例为切入口,力图在方法论上验证乡村治理乃至社会发展需要借助其地方的传统文化结构。在乡村文化浓厚的地区,其发展要与本地的地方知识相契合,这是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新举措。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Alden Kuhn)在研究中指出,不同国家是可以经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12]168而这一方法取决于其自身的条件,乡贤阶层参与社会事务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要素。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末提出,“文化自觉”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前提,是保持中国发展走本土化道路的重要路径。因此,从学理上我们可以发现,所谓的现代性并非是“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关系,[13]35当下的乡村变迁也许恰是传统乡村发展的必经之路。从历史中走来的乡村社会,其治理也应借助“传统”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