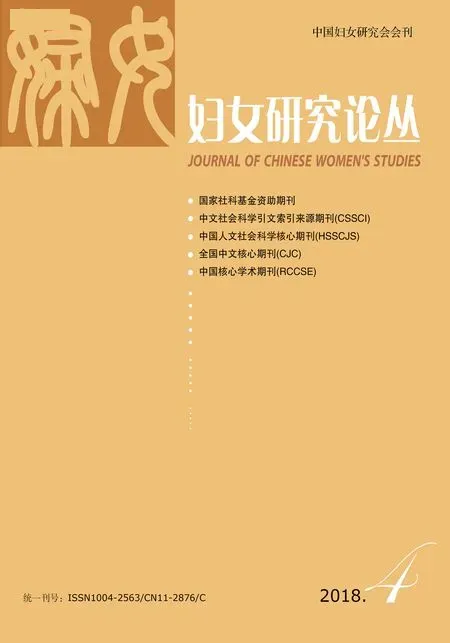犹太女性的大屠杀叙事书写*
——《大披巾》中的女性话语建构
孙鲁瑶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1](P 26)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揭示了犹太大屠杀书写的道德困境。文学语言的美学机制以及大屠杀概念运用的“泛化”“琐碎化”倾向时刻动摇着犹太大屠杀的历史严肃性,使文学书写陷入伦理争议。然而,对犹太女性作家来说,问题远不止于此,大屠杀书写中亦存在性别失衡的现象。不论是大屠杀回忆录还是第二、第三代美国犹太作家的后大屠杀创作,男性经验往往被置于暴力叙事的中心,女性的大屠杀体验则被弱化和边缘化,难以获得完整的文本表达。“女性性别意识、女性在大屠杀中所肩负的母亲与受难者的双重身份、女性的互助关系网以及女性因以存活的既合作又独立的生存方式,这些元素在男性的大屠杀作品中缺失了。”[2](P 241)面对大屠杀的表征困境及书写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越来越多的犹太女性作家独辟蹊径,将女性的大屠杀体验纳入文学视野,其中,辛西娅·欧芝克(Cynthia Ozick)的小说集《大披巾》(TheShawl)*欧芝克的小说集《大披巾》由短篇小说《大披巾》(“The Shawl”)和中篇小说《罗莎》(“Rosa”)组成,二者存在叙事逻辑上的承接关系。颇具代表性,小说以犹太女性的大屠杀经验为叙事核心,再现了女性在纳粹集中营及战后美国的受难、创伤和救赎的历程,建构并巩固了犹太女性的大屠杀权力话语。那么,欧芝克如何应对犹太大屠杀书写的道德质疑,又是如何通过文学叙事呈现并强化犹太女性的大屠杀体验的?其书写实践对大屠杀文学创作及历史书写意义何在?
对此,本文将以犹太大屠杀的书写现状为论述背景,通过审视《大披巾》中的女性叙事策略,管窥犹太大屠杀叙事书写中女性话语的建构及其意义。
一、大屠杀书写现状:伦理困境与性别话语失衡
要探讨《大披巾》中犹太女性的大屠杀叙事,就必须明确大屠杀书写的现实语境。一方面,文学的审美性与大屠杀事件本身的历史严肃性相悖,使书写遭受伦理质疑;另一方面,现存的众多犹太大屠杀文本仍呈现出男性本位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现象。其中,前者关涉大屠杀叙事的书写正义,后者则是女性文本旨在解构和颠覆的对象。
20世纪60年代至今,“语言表征历史是否可靠”引发了犹太文坛及批评界的持续探讨,这一有关大屠杀文学历史合理性及道德严肃性的思考使大屠杀文学书写陷入了“言说焦虑”。首先,有限的语言符码难以切近庞杂的大屠杀历史真相。“大屠杀幸存者往往将‘死亡集中营’视作语言难以触及的黑暗领域,因为我们的语言从未用来描述过这样一种精心规划的恐怖行为。”[3](P 2)其次,语言文字的美学机制干扰并弱化了大屠杀的历史严肃性和道德感。不论是关于大屠杀的日记、回忆录或是小说,其“艺术表达的形式都要臣服于创作的规则”[4](P 49),隐喻、拼贴、移置甚至叙述时序的调整都有可能将真实的创伤性历史经验转变为轻浮的“文字游戏”和“历史神话”。再次,由于语言的生产性,“大屠杀”(the Holocaust)概念逐渐被泛化和琐碎化,常常被随意地隐喻为一种与其无关的叙事,丧失了民族性和特定的历史指向*关于“大屠杀”概念的泛化和琐碎化,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曾言:“我不能再使用‘大屠杀’这个词,因为它变得如此琐碎,一旦有灾祸发生,人们就称其为‘大屠杀’,…一位评论员将赛事的惨败形容为‘大屠杀’,加利福尼亚的重要报纸上,6人遇难的凶杀案也被称作‘大屠杀’。所以我没什么可说了。”Elie Wiesel,“Some Questions That Remain Open”,Comprehending the Holocaust,Frankfurt:Peter Lang,1988,P13.。大屠杀概念的“解域”(de-territorialization)现象僭越了历史言说的底线,使严肃的历史灾难变为日常生活中肤浅的戏仿。基于以上因素,大屠杀书写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
不过,尽管陷入表征困局,犹太作家并未放弃书写大屠杀。随着奥斯维辛的远去、灾难亲历者的故亡和犹太同化现象的日益严重,不少犹太知识分子认识到追寻和唤醒民族记忆的必要性,大屠杀正作为一种记忆符号存续于犹太作家的书写之中。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的半自传体小说《夜》(LaNuit,1955)、杰西·科辛斯基(Jerzy Kosinski)的《漆鸟》(ThePaintedBird,1965)、杰拉德·格林(Gerald Green)的《大屠杀》(Holocaust,1978)、艾萨克·辛格(Issac Singer)的《仇敌:一个爱情故事》(Enemies:ALoveStory,1972)和塞恩·罗森鲍姆(Thane Rosenbaum)的《二手烟》(SecondHandSmoke,1999)等都是颇具代表性的文本。这些作品对大屠杀的表达和解读虽各有不同,但却共同反映了大屠杀暴力叙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视角及创伤经验。与之相较,女性则很少在大屠杀书写中表述自身,尽管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犹太大屠杀进行了记述和思考,但女性经验始终未能在大屠杀文本中获得持久而有力的呈现,这不仅因为传统的父权制偏见限制了犹太女性的表达自由,更缘于女性在犹太历史建构中的被动性。
作为对屠杀书写中男性中心主义的回应,犹太女性作家开始尝试书写独特的奥斯维辛记忆和后大屠杀经验。默娜·戈登堡(Myrna Goldenberg)指出,由于纳粹性别化的暴力机制和女性所特有的生理机能及社会分工,女性的大屠杀体验在以下几个方面明显异于犹太男性[5](PP 78-93)。首先,女性潜在的生育力往往使其成为纳粹的首要清洗对象,即便侥幸存活,也往往因性侵害造成身体及心理的长久伤害。其次,集中营中犹太母亲与幼子的特殊生存关系使女性的大屠杀经验更为复杂。一方面,幼子是母亲及周边女性的生存阻碍,“为了防止营房中的女性遭受报复,母亲不得不变为杀手,被迫弑杀刚出生的婴孩”[6](P 161)。另一方面,犹太母亲同其他女性以合作的方式隐藏和保护幼子,将营房变为母性的空间。这种“母性侵蚀”和“母子依存”的矛盾关系势必使女性因情感分裂而饱受创伤。再次,犹太女性的家庭经验和社会分工使其在集中营里形成了与男性迥然不同的生存智慧和互助关系。女性在生活上互相协助,缝补衣服,制作食物,不仅客观上增加了生存概率,更增进了自我认同,发展出患难与共的姐妹情谊。以上经验在犹太女性作家的大屠杀书写中不仅获得了充分的体现,更经由艺术化的文学手段加以表征、编排和重构,从而勾勒出消匿于男性大屠杀叙事模式之下的女性生存史。
在众多犹太女性作家的大屠杀叙事作品中,欧芝克的《大披巾》颇为典型。虽然欧芝克亦认为将大屠杀等同于文学想象的做法是一种抹灭真实历史的修正主义,还甚至因写作《大披巾》而颇为自责,但她同时指出书写大屠杀亦是历史和道德所需:“书写大屠杀,我不能自已……因为大屠杀冲击着历史,它不断回响,在破碎和空洞的颅骨中呼啸。”[7](P 393)正是这样的冲动促成了欧芝克颇具试验性的大屠杀书写实践。面对大屠杀的表征危机及大屠杀书写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欧芝克选择以直描的方式呈现犹太女性在集中营及后大屠杀时代的受难史,并采用多样的后现代叙事手段及女性书写逻辑,在匡扶犹太大屠杀书写伦理正义的同时开拓了女性的大屠杀叙事空间,建构并强化了犹太女性的大屠杀历史话语。
二、奥斯维辛“再述”:大屠杀叙事的女性经验建构
奥斯维辛幸存者伊莎贝拉·莱特内尔(Isabella Leitner)在自传中写道:“如果无姐无妹,就没有压力,就没有活着结束一天的绝对责任。”[8](P 44)伊莎贝拉的证词反映了犹太女性在集中营里“扶持”和“共生”的关系,然而,对携带幼子的犹太女性来说,其情感及道德状态则显得较为复杂和非常态化。通常情况下,犹太母亲与幼子处于既依存又对立的情感关系之中,这一独特的“母性声音”成为女性在大屠杀历史中独特的文化记忆形式和言说力量。在《大披巾》中,欧芝克通过塑造犹太母亲的战争话语和文学影像,勾勒出极端环境下犹太女性特殊的母性形态和灾难记忆。
主人公罗莎(Rosa)在集中营里艰难生存,与幼女玛格达(Magda)形成了既依存又对立的矛盾关系。罗莎辛勤地哺育和保护着幼儿,她是“行走的摇篮”*本文中,短篇小说《大披巾》的翻译均出自辛西娅·欧芝克著,陶洁译:《大披巾》,《外国文学》1994年第4期。[9](P 3),拥有玛格达渴望的“乳头”和“乳汁”,她还能用披巾为婴儿提供庇护,包裹和掩护玛格达躲避戕害。披巾是温暖的织物,象征着母性的柔情和爱护,也是哺育婴儿的“亚麻牛奶”[9](P 5),“玛格达抓住大披巾的一角,以它代替乳头吸吮起来,她啜了又啜,把毛线弄得湿漉漉的”[9](PP 4-5)。罗莎的母性通过披巾传递,赋予了婴儿以生命力,使玛格达几乎不眨眼睛,也不打瞌睡;罗莎把食物都留给了玛格达,自己忍饥挨饿,“她从玛格达那里学会把手指放在嘴里品尝滋味”[9](P 5);而玛格达也形成了与母亲之间特殊的生存默契,她从来不哭,只会安静地蜷缩在披巾之中,罗莎甚至觉得她是个哑巴。正因为玛格达的“安静”,罗莎格外小心,她害怕睡着时将玛格达碾压窒息,也担心玛格达会从披巾中掉出,就连玛格达走出襁褓即将遇难之时,罗莎依然本能地想要“去拿,去抱,去取”幼女赖以存活的披巾,“举起它,挥动它,拍打它,把它打开”[9](P 8),甚至想要冲入电网。在大屠杀背景下,女性这种抚育和保护幼子的冲动往往比男性强烈得多,波兰犹太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林格本(Emanuel Ringelblum)曾记述道,犹太女性即使被暴力押解,“她们的怀中仍抱着年龄不同的婴儿,用层层毛衣包裹着,唯恐孩子着凉”[10](P 195)。在大屠杀中,女性这种坚持哺育和照料婴儿的行为不仅是对纳粹种族清洗政策的反抗,也诠释了犹太母亲延续民族生命与希望的英雄主义形象。而犹太男性则不同,他们虽然“哀叹孩子死亡,表达父亲的悲伤,但并未将重点放在保护孩子上。…男性舍身救子的行为与女性相比亦不足为道”[11](P 18)。并且,当大屠杀到来时,男性“无法保护家人和自己免遭屈辱,这种无能为力……击碎了男性的自我认知,将他们阉割了。”[12](P 146)
但同时,极端环境下的罗莎又与玛格达构成了生存竞争,使母性表达出不同寻常的残酷和隐忍。玛格达几乎消耗了罗莎所有的生命力,罗莎怀抱玛格达轻飘飘地行走,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昏厥,她“没有月经”[9](P 5),“乳房枯裂,连一滴奶汁都没有,乳管消失,像一座死火山”[9](P 4),甚至丧失了对疲惫和饥饿的生理感受;同时,罗莎的母性也在消磨,她想“离开列队一分钟,把玛格达塞到路边任何一个女人的手里”[9](P 4),在预料到孩儿死亡的宿命后,她竟感到“一股令人恐惧的狂喜”[9](P 7),甚至在玛格达被投入电网时,罗莎能够抑制住以身涉险的冲动,选择自我保全,她“只是站在那里,因为,如果她跑的话,他们会开枪的,如果她去捡玛格达的柴火棍似的尸骨,他们会开枪的,如果她让沿着她骨架子升上来的狼般的痛苦的尖叫爆发出来的话,他们会开枪的”[9](P 10)。在非生即死的瞬间,母性走下神坛,表现出真实和现实的一面,这往往是集中营里犹太母子生存冲突的真实写照。默娜·戈登堡在《不同的恐惧》(“Different Horrors”)中提及,为了挽救母亲及同伴的性命,营房里的新生儿往往在张口呼吸的一刻被捏住鼻孔,给一剂毒药,或是被溺亡在水中[5](P 86),同样,在幼女生死存亡的关头,罗莎也只能压抑母性、保持缄默,“她搂住玛格达的披巾,用它堵住自己的嘴,…直到她咽下了狼的尖叫,尝到了玛格达口水的深深的肉桂和杏仁的香味;罗莎吮啜着披巾直到它干枯了”[9](P 10)。罗莎与玛格达之间既共融又对立的母女情感不仅反映了犹太女性在大屠杀中普遍面临的伦理困境,更凸显了犹太女性挣扎于“生存本能”和“母性本能”之间的复杂的生命经验,成为女性大屠杀话语的重要来源。
如果说《大披巾》以直描的方式再现了犹太女性的大屠杀历史,那么其续篇《罗莎》则是对犹太女性“后大屠杀”生存样貌及话语状态的持续关切。奥斯维辛使罗莎变成了孤独自闭的“疯女人”,一个精神的“拾荒者”[9](P 13)。母性伦理困境、性侵害及由此而来的生存恐惧在罗莎的精神意识里频繁闪回,导致其出现“后大屠杀”认知障碍。虽然玛格达的死终结了罗莎的母亲身份,却并未终止罗莎的母性回忆,这一创伤使罗莎沉浸在语无伦次和沉默封闭的精神状态中。萨拉·霍洛维兹(Sara Horowitz)指出,即便是数年之后,杀婴的痛苦记忆仍旧存在,当事人“很难提起或是将其整合成关于过去的意义清晰的叙事”,即使能够叙述,也会在期间出现无法自控的静默[12](P 137)。罗莎的言语错乱正是源于其潜意识无法消抹玛格达遇难时的记忆图景。这一心理建设的失败激发了罗莎近乎疯狂的母性意识,令其难以认可“母性圈子”之外的社会关系。罗莎呓语连绵、近乎疯癫地给玛格达写信,将文学语言作为言说创伤的路径,她幻想中的玛格达不仅幸存,还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有成,玛格达不再是集中营里的哑婴,而是医生或希腊哲学教授;并且,玛格达也不再是纳粹的后代,而是生于名誉之家,祖父哲学造诣丰厚,父亲“受人尊敬、彬彬有礼、教养极佳,是为人可靠、颇具声誉的人”[9](P 43)。罗莎通过重塑玛格达的出身及社会关系,不仅回避了幼女的出身及死亡的真相,更制造出富于能动性的母性想象空间,以修复大屠杀中被撕裂和剥夺的亲子伦理身份。同时,罗莎还将母性转移至玛格达的披巾,将其视为寄托母爱的圣物。犹太传统中,“披巾是高度性别化的仪式性物品”[13](P 10),象征着男性系统的宗教权威,犹太男性经常身着传统披肩参加晨间祝祷;但是另一方面,披巾的温度、手感和气味又与女性特质相关,同母性相连,它可以用来包裹和哺育婴儿,即使在玛格达死亡后,披巾依旧是罗莎母性存留的场所。披巾母性化的过程不仅意味着男性逻辑的退场,也使母性有了宗教的仪式性和神圣性。“装着披巾的盒子到最后才能动,…等一切完美无缺的时候再打开它”[9](P 34)。当罗莎抱住装有披巾的盒子时,“她感觉到琐碎和愚蠢,这里的一切,甚至连最深刻的‘存在’都轻飘飘的,她感觉好像有人将她的生命器官切下并令她握在手里”[9](P 56)。罗莎对幼女的幻想和对披巾的情感供奉正如源源不断的乳汁,持续支撑和强化着母亲身份,使其获得了创伤性的母性满足。
除了与母性相关的精神伤害,罗莎还受困于性侵害的创伤,两者共同作用,造成了罗莎“怪诞、傲慢、刻薄且不讨喜”的病态性格。小说中提到,罗莎因丢失内衣而局促不安。“内衣”代表着女性的隐私和性征(female sexuality),内衣的遗失不仅隐喻了大屠杀时期犹太女性被强制除去衣物、暴露私处甚至遭遇性侵犯的创伤,更意味着女性丧失掌控身体和维护性别尊严的能力,这使得罗莎感觉“可耻,丢脸,腰上隐隐作痛,如同火烧一般”[9](P 34)。同时,性侵犯还使罗莎无法开展正常的两性交流,她往往将男性视为危险的敌人,面对异性的追求,罗莎言语冷淡、刻意避让,甚至过度防卫、自我封闭,难以同男性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
由于母性和性心理方面的创伤,罗莎的生活被切割成三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之前的生活”“之后的生活”和“当下的生活”。“之前的生活”是为真实,“之后的生活”是玩笑,而“当下的生活”则是无尽的难耐[9](P 58)。尽管迈阿密是战后犹太人的理想家园,但由于长久未能逃离创伤,罗莎眼中的城市依然回荡着奥斯维辛的影像:“街似焚炉,阳光炙烤,每天都烈焰四起”[9](P 14),“整个佛罗里达半岛颓丧于后悔之中,每个人都生活在不真实的世界里,在这里他们什么也没有”[9](P 16)。当然,罗莎的这种创伤性的时空体验不仅源于创伤事件本身,还源于与“失女”和“失贞”有关的女性创伤话语难以获得充分的交流和认同。虽然帕斯基(Persky)企图理解罗莎的受难及创伤,但传统的男性语言无法与女性形成完整的经验共同体,这也是罗莎重复“你的华沙不是我的华沙”[9](P 22)的深层次原因。
实际上,犹太女性的大屠杀创伤并非仅限于意识层面的自闭和幻想,还表现为无意识领域的创伤性梦境。梦境是涌动的潜意识,其内收、碎片化及非逻辑的特质正如女性意识的涌流,成为女性话语表达的通道。欧芝克的另一部作品《陌生的身体》(ForeignBodies)中的莉莉(Lili)就是一位创伤梦境的制造者。莉莉经历了罗马尼亚的纳粹屠杀,因弹中手臂得以幸存,而家人却枪中要害而死,这使得她受困于“死一般的、创伤性的”[14](P 127)梦境,常常发出无意识的尖叫和抽泣。“罗莎式”和“莉莉式”的大屠杀创伤症候共同反映了犹太女性独特的灾难经历和情感体验。
那么,犹太女性在后大屠杀时代应如何走出历史伤害,重建女性主体?从罗莎的恢复过程来看,欧芝克显然认为犹太女性应当“肯定两性的手足关系”[15](P 827),在两性的扶持和尊重中建立和谐共生的话语关系。集中营里,侄女斯特拉(Stella)偷走玛格达披巾的行为隐喻了其与罗莎建立母性联系的冲动。在战后的美国,斯特拉试图以取代玛格达的方式给予罗莎母性上的宽慰,她不仅保留着大披巾,更赡养罗莎,鼓励罗莎清除虚幻的奥斯维辛记忆、踏入新生活。斯特拉最终将大披巾还给罗莎的行为象征着罗莎病态母性观念的消失和新母女认同的建立,罗莎由此获得了更为健全的女性人格。罗莎的男性朋友帕斯基激发了罗莎言说自我的冲动,他鼓励罗莎正确看待性别创伤并重塑正常的社会关系,建立了女性大屠杀经验在两性间的理解和认同,最后罗莎寻回内衣的情景意味着其女性性别心理的恢复和重整。与此同时,罗莎与玛格达的交流也脱离了疯狂的想象态,进入了历史的真实,她在写给玛格达的信中不仅清晰回忆了华沙隔都中的犹太生活,描绘了电车轨道上方阻挡犹太人的天桥,以及电车中波兰女人冷眼和鄙夷,还讲述了在美国无人理解的落寞,封存的历史就像“燃烧的飞流”,成为罗莎“大脑深处流淌的文字之光”[9](P 69)。这种母女交流不再是想象的和病态的,而是回归了真实和健康,罗莎的母性创伤也由此疗愈,“玛格达跑走了,蓝色的小裙子变成了罗莎眼中的小光点,她甚至不曾停留”[9](PP 69-70)。
总之,不论是《大披巾》对犹太母亲在战争年代生命体验的细致描画,还是《罗莎》对战后女性幸存者创伤的关注,犹太女性都是大屠杀叙事中至关重要的主体,女性对民族历史灾难的“重忆”和“再述”不仅是自我发现与肯定的过程,更是她们主动参与犹太大屠杀话语的权力争夺,实现了从“失语”到“发声”的质变;同时,超越性别对立的互助型创伤消解模式也体现出犹太女性包容共生的话语能量。
三、历史元小说与阴性书写:大屠杀叙事的女性话语策略
艺术手段亦是话语形式。小说集《大披巾》中,欧芝克除了书写女性主题,亦借鉴“历史元小说”与“女性书写”的叙事艺术,在揭示和呈现历史的建构性本质的基础上,采用微观聚焦、意识流、碎片化和去逻辑化的方式解构男性叙事框架,强化了犹太女性的大屠杀话语能动性。需要指出的是,大屠杀书写中,历史元小说和女性书写的手法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彼此融通,互为支撑,共同构建了女性大屠杀叙事的话语体系。
犹太大屠杀书写的伦理困境是欧芝克首要应对的问题。对此,《大披巾》不仅以直描大屠杀事件的方式避免因“泛化”所致的文本伦理危机,更通过呈现历史与文本之间的亲缘关系,弥合了“历史记述”和“虚构性小说”的鸿沟,实现了文学与历史话语的并置和交融。一方面,罗莎目睹玛格达被投入电网的场景取自《第三帝国的兴亡》(TheRiseandFalloftheThirdReich)中真实的历史纪实,这就使得小说文本具有了历史、社会和现实基础,同时,欧芝克还使用第三人称视角及零度叙事模式冷静地铺陈事实、讲述现象,甚至在玛格达被投入电网时,对罗莎的描写也仅限于客观动作的勾勒,呈现了传统历史书写的特质。而另一方面,欧芝克又毫不避讳小说文本的虚构性,在呈现文本生产手段的同时揭示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的建构本质。《大披巾》以“缺少特定时空坐标的童话故事式的叙述策略”[16](P 133)来体现文本的想象性,同时,和续篇《罗莎》呈现出分离却互有关联的模式,“一个故事总是包含并点评着另一个”[17](P 155),这一双向互文叙事不仅呼应了米德拉什(Midrash)*又称米德拉西,为犹太教阐释《希伯来圣经》的书卷。的“循环”释经传统,更打破了传统历史书写中时间正序的叙事模式,揭示了历史、文本和叙事的话语交织。由此,欧芝克呈现了“历史”与“文本”共有的“历史性”(historicity)、“文学性”(literariness)和“虚构性”(fictionality)[18](P 102)特征,从而弥合了文本与历史之间的断裂,为开展小说叙事、表达犹太女性大屠杀经验和历史话语奠定了基础。
面对犹太大屠杀书写中女性话语的边缘化现象,欧芝克在小说中采用“女性书写”手法对犹太大屠杀文学中的男性叙事权威予以回应,在巩固犹太女性大屠杀主题的同时重建犹太女性历史书写中的独特话语。欧芝克的“女性书写”不仅呼应了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所倡导的“批判父权文化的线性逻辑,用感性和诗性的语言言说身体的欲望”[19](P 86)的理念,更将其与犹太女性的历史体验和创伤经历相联系,生产出犹太女性独特的大屠杀叙事方式。
首先,欧芝克使用微观聚焦的方式书写“女性的战争叙事”。与男性大屠杀书写中的宏大视角不同,《大披巾》仅将叙事镜头聚焦于犹太母女的身体及情感的微观空间。小说始于对“死亡行走”中女性身体的照相式定格(photographical focus),“乳房”“母亲”“婴孩”“奶水”“摇篮”等女性化能指均紧扣女性的身体及母性经历,主体叙事中由“护女”到“失女”的情节推进也经由犹太母亲罗莎的心理刻画和创伤独白而自然衔接;《罗莎》的叙事亦聚焦于女性创伤个体而非宏观的后大屠杀世界,情节铺陈及场景转换多经由女性身体及心理的微观变动展开,这一紧扣女性的微观描写不仅是女性“书写自己”的简单冲动,而且是确立犹太女性在大屠杀文本中的主体意识的重要方式。
其次,欧芝克以阴性书写的方式表达犹太母亲感性和诗性的语言,从而恢复了女性情感在叙事中的肯定和表达。西苏指出,女性应当用白色的乳汁书写自身的母性特质,以反逻各斯的非理性书写创造女性特有的表达方式,“将自己放入文本”[20](P 875),这种肆意流淌的母性语言正体现为《大披巾》中罗莎涌动的母性和意识流式的心理叙事。例如,在死亡行走和幼女遇难时,罗莎瞬间的母性心理矛盾呈现为一种内视角的流动式的女性独白。“她可以离开队列一分钟,把玛格达塞到路边任何一个女人手里。但是,如果她走出队列,他们可能会开枪。还有,即使她躲开队列半秒钟,把披巾裹的包塞给一个陌生女人,她会接受吗?她也许会大吃一惊,会害怕起来;她也许会失手把围巾包掉了下来,玛格达会摔了出来,撞破脑袋而死去。那个小小的圆脑袋。她真是个好孩子。”[9](P 4)紧凑的句式、尖锐的矛盾碰撞和难以抑制的母性柔情不仅体现了女性特有的感性思维,也恰到好处地呈现了犹太母亲的大屠杀情感体验;这一意识流式的书写在玛格达遇难时达到了叙事的高潮,“她明白玛格达快要死去……如果她冲进点名区去抱玛格达,叫喊声不会停止,因为玛格达还是没有披巾;但是,如果她跑回营房去取披巾,如果她找到了,如果她拿着披巾并挥动着去追玛格达,她可以把玛格达抱回来,但是玛格达又会把披巾放进嘴里,又会变成哑巴”[9](P 8)。罗莎不敢去捡拾玛格达的尸骨,“如果她跑的话,他们会开枪的,…如果她让沿着她骨架子升上来的狼般的痛苦的尖叫爆发出来的话,他们会开枪的”[9](P 10)。整段意识流式的心理描画构成了小说的核心张力,延宕、铺展和非理性的叙事形式不仅在内容上清晰地呈现出主人公罗莎局促的母性意识,更在形式上表征了女性情感柔软和流动的特殊形态以及“如狂风暴雨般奔泻”[20](P 878)的身体力量。在《罗莎》中,这一诗性的母性语言表现为对玛格达难以克制的情感告白,“玛格达,我灵魂的祝祷”,“我黄色的小母狮”[9](P 39),“我的金子,我的财富,我的珍宝,我看不见的小芝麻,我的天堂,我的黄色小花,我的玛格达!绽放的花之王后!”[9](P 66)非理性、即时和松散的情感想象以明显区别于父权制书写逻辑的形式铺展开来,从而强化了女性自身的母性话语逻辑。
再次,欧芝克将女性书写理念与大屠杀创伤叙事相结合,以“非确定性叙事”“再现和闪回”“重复与断裂”的方式在事实与想象、理智与疯癫中游移,将女性碎片化的、非逻辑的情感体验及书写方式“带入历史”[20](P 875),这一疯癫型的女性创伤叙事集中体现在《罗莎》中。一方面,小说以“讲述和否定讲述”的方式破坏文本的确定性,呈现犹太女性的创伤型叙事特点。受创主体的讲述不断“打破现实与幻想、生命与死亡、记忆与遗忘、过去与现在的界限”[21](P 124),在形式上表现出女性在创伤之下的母性情感特质。小说中,玛格达的身份被不断地再想象——时而是医生,时而是教授——且文本中并无对此歧误的任何说明。小说在交代玛格达父亲身份及家族背景时亦前后矛盾,叙事不断以“蓝眼睛”“金棕发色”等体征确定玛格达纳粹后裔的身份,但之后却堂而皇之地将玛格达的出身改述为书香门第。这一虚实相间的书写方式不仅还原了女性创伤主体真实的心理状态,更颠覆了清晰、理性和条理化的叙事逻辑,呈现女性身体书写的离散性特质。另一方面,小说采用闪回、重复的叙事方式和断裂的句式呈现女性在母性和性别上的双重创伤。罗莎看到海滩上林立的电网时,叙事突然从和平年代的迈阿密沙滩闪回至奥斯维辛集中营,“她的手腕在颤抖。被锁在铁刺网里!没人知道她曾是谁,她遭了什么事;她从哪来。这里的大门,刺栅栏,男人和男人并排躺着……她害怕接近任何类似坟堆的东西。没人能帮她。这些迫害者们”[9](P 49)。文本叙事以“铁丝网”为时空媒介,将分属于不同时代的奥斯维辛意象关联并置,不仅呼应了玛格达电网遇难对罗莎造成的母性损伤,也“再叙”了罗莎在集中营里因隔离式关押而遭遇的心理侵害;同时,文本以不断重复“我的华沙不是你的华沙”的方式凸显和强调女性创伤的缠绕性和独特性,又以局促断裂的文字排列方式营造女性创伤文本,如罗莎思念幼女时的呓语:“玛格达的披巾!玛格达襁褓布!玛格达的寿衣。玛格达气味的记忆,逝去孩儿圣洁的芬芳。谋杀,被扔向围网,带刺的,尖利的,通电的;网格和筛子;焚化炉,火上的孩儿!”*原文为“Magda’s shawl!Magda’s swaddling cloth.Magda’s shroud.The memory of Magda’s smell,the holy fragrance of the lost babe.Murdered.Thrown against the fence,barbed,thorned,electrified; grid and griddle; a furnace,the child on fire!”[9](P 31)整段叙事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呈现断裂的特质,名词意象与动词的堆叠使用迅速勾勒出犹太母亲近似疯癫的创伤记忆,短促和不完整的句式结构“恢复了创伤经历原本的碎裂本质”[22](P 104)。
实际上,“非确定性叙事”“再现和闪回”“重复与断裂”的文本呈现既是犹太女性创伤表达的媒介,亦是创伤本身,它因“感性、碎裂、非线性和延宕”的特质与女性经验和女性书写紧密联系,形成了根植于犹太历史的女性创伤书写模式。欧芝克对大屠杀叙事的艺术把控不仅强化了犹太女性的文本权威,更体现了女性争夺和再造大屠杀权力话语的能动性。
四、结语
米莉莎·拉斐尔(Melissa Raphael)在《奥斯维辛中上帝的女性脸孔》(TheFemaleFaceofGodinAuschwitz)里说道:“很明显,纳粹的屠杀并没有忽视性别,……女性在大屠杀中饱含性别特质的受难、生存和死亡必须要获得知晓和述说。”[23](P 1)不论在主题还是叙事策略上,《大披巾》都传达出强烈的言说冲动。欧芝克突破大屠杀书写壁垒,以独特的性别视域讲述犹太女性的性别体验及历史创伤,并运用性别化的叙事技巧,将女性话语贯穿于整个文本的建构之中。这一书写实践一方面丰富了大屠杀文学的叙事表达和阐释维度,为犹太女性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书写经验及美学路径,更体现出犹太女性言说和建构民族历史的愿望和动能。女性立足自身的性别经验,与男性平等地述说历史、追问人性,这亦是“女性大屠杀书写”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