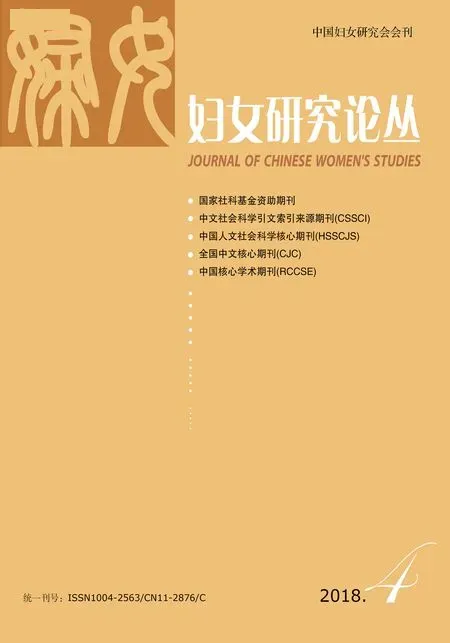历史无声却有痕*
——评魏爱莲教授《美人与书:19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
马勤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美国卫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魏爱莲(Ellen Widmer)教授是北美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方面的重要学者。20世纪70年代,她师从享誉世界的哈佛大学教授韩南(Patrick Hanan),专攻中国小说史。几年后,她在欧洲女性主义思想影响下,对中国古代闺秀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思考“女性如何被纳入中国文学图景”并做出自己的解答[1]。1989年,魏爱莲在《晚期帝制中国》(LateImperialChina)上发表了讨论传统闺秀问题的第一篇代表作《17世纪中国才女的书信世界》。当时,北美的明清女性文学研究刚刚起步,魏爱莲此文可谓开风气之先。更幸运的是,她还遇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于是,魏爱莲积极地组织座谈,与她们交流。这一学术共同体的研究引出了一种假设:“中国妇女文化在特定时期里经历了急剧的发展。仅就江南来看,就会发现有明末清初以及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这两个时期的发展。”[1]高彦颐(Dorothy Ko)即是在这一学术理路之下,做出了突破性的成果《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1992年,《晚期帝制中国》隆重推出了中华帝国晚期妇女文化主题专刊,其中即有魏爱莲的重头文章《小青的文学遗产与帝制中国后期的女作家》*收入魏爱莲《晚明以降才女的书写、阅读与旅行》(赵颖之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该书总计收录了魏爱莲自1989年至2015年研究明清女作家的14篇论文。。1993年,她与孙康宜在耶鲁大学召开了美国汉学性别研究方面的第一次大型学术会议——明清妇女文学国际研讨会,将相关研究引向深入。
20世纪90年代,北美中国传统闺秀研究的重心主要集中在诗词方面,魏爱莲却另辟蹊径,转而关注19世纪闺秀的小说阅读与评说。但她并非从理论出发,而是受韩南治学的影响,从扎实的资料工作入手[2](PP 111-114)。她曾说,“想实践韩南教授对我的训练,把它用在这个新方向里”[1]。2006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刊行的《美人与书:19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TheBeautyandtheBook:WomenandFictioninNineteenthCenturyChina,下文简称《美人与书》),是魏爱莲多年思考的集中呈现。2015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该书对中国古代女性与小说*此处的“小说”,指的是散体小说。魏爱莲曾将《美人与书》的要义精缩为一篇文章,并开门见山地指出:“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在1911年清朝覆灭前,中国女性与小说产生了怎样的互动联系?要回答这个问题,弹词不能不提,但我更关注的是,当时的女性是否阅读或参与了章回小说的写作。”(参见魏爱莲:《佳丽与书籍:19世纪中国女性与小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事实上,“弹词”这种文类无论是在古人的观念中还是在晚近学者或为诗、或为词的文体指认下,都与“小说”有着明晰的界限(参见马勤勤:《隐蔽的风景: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创作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页),只有将它们同时置于“通俗文学”或“叙事文学”这一大的概念之下,二者才会在一定程度上被统摄起来(参见谭帆:《稗戏相异论——古典小说戏曲“叙事性”与“通俗性”辨析》,《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因此,尽管魏爱莲也在《美人与书》中讨论到了弹词小说的问题,但这更多是作为一种参照出现的,而非全书的重点。之“结缘”的全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追踪与考察,为小说史和妇女史的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域。
一、历史叙述的“空白之页”
20世纪初,著名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曾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指出,在18世纪到19世纪的英国文学里,多数女作家以小说为主要的创作文类,女诗人则很少出现。她详细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指出女性受限于琐屑的家庭义务,难得有安静、完整的思考空间与创作时间,因此无法发展需要全心投入的诗才,而转向可以利用零碎时间“随写随放,随放随写”的小说。沃尔夫在这里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作者选择创作的文类,是否会受到性别的影响与牵制?而不同社会、文化与文学传统下的女性,在创作时是否会有不同的思考与选择?沃尔夫对英国文坛的分析是否得当是另外的问题,但是如果把视野放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则会看到一幅迥异的历史图景。中国女性文学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据传,《诗经》中即有若干女性作品。但是,中国古代女性的文学创作多为诗词。特别是到了清代,即使“妇人之集,超迈前代,数逾三千”[3](P 5),也基本都是诗集。正如顾廷龙所说:“观乎历代妇学,以现存著述论之,则诗文词为多,而文又远逊于诗词。”[4]对于这种现象,谭正璧在《中国女性文学史话》中给予了精当的总结:“中国文学是韵文的,说得时髦些是音乐的,这句话如移来专指女性文学,尤其来的切合。女性作家所专长的是诗、是词、是曲、是弹词,她们对于散文的小说几乎绝对无缘。”[5](P 17)
在中国古代,小说长期被看作一种品格趋俗的文体,历来不少小说作者的真实姓名和生平事迹往往不详,立言传世与小道末流的矛盾或许也是其原因之一。在女性身上,这种矛盾更加突出和复杂。除了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压力之外,女性还要承受儒家传统妇德和性别分工的道德规塑。无论是官方法令、社会舆论还是家规家训,中国古代的女性都是不被允许翻阅小说的,《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6]中即保存了大量与之相关的史料。女性阅读小说尚且如此严苛,更勿论去创作小说了。如此,我们似乎可以公开宣称,古代才媛与小说之间乃是一种完全“绝缘”的状态。事实上,目前主流的看法,也认定女性与小说发生关联是迟至清末民初甚至“五四”之后才有的事情。这种文学史观深入人心,已然成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历史事实。
17世纪之后,古代小说的创作进入一个繁荣期;几乎在同一时期,女性文学和才女文化也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于是,我们不免会发出疑问,在女性文学和小说创作如此欣欣向荣的明清两代,“女性”与“小说”这两个同处文化边缘的存在,是否真的如礼教所规范的那般“绝缘”?很多时候,所谓的法令、舆论和家规家训,反映的可能不是现实,而是一种“意识形态”诉求,越是严防死守,越是证明它是一个医生面对病入膏肓的病人企图力挽狂澜的方式。换句话说,种种对于女性道德的指摘、限制和博弈,所影射出来的是一整套的权力话语和规训体系,其实反映的恰好是它们所批评的现状。事实上,古代才女写作小说确实信而有征。清代的汪端曾作《元明佚史》,虽然被作者本人烧毁不传,但各种资料均显示这必然是说部一类的作品,以白话小说的可能性为最大。作品流传下来,并且可以确定作者为女性的白话小说,目前只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然而作者却只署“云槎外史”,未敢显露其女性身份。
毫无疑问,中国古代才女与小说之间曾发生过微妙的联系,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制约,这种联系若隐若现,最后淹没在社会对女性与小说关联的压抑性话语之中。那么,假如我们今天重新出发去探寻古代才女与小说的关系,则必须重返明清女性文学与文化的历史场域。近年来,与明清女性文学互动最大的,便是妇女史对17世纪以降中国女性生活的检讨。美国妇女史专家曼素恩(Susan Mann)曾明确提出,“在将妇女引入传统的历史框架时,我们并不是简单地改变了框架的内容,我们或许还会摧毁这个框架本身”[7](P 9)。如此,几乎所有的妇女史(妇女文学史)研究都是从这个信念出发,以“改写/重写文学史”为职志。于是,文学研究者努力挖掘并呈现女性作者活跃积极的文学工作,妇女史研究者则致力于对“五四”史观之下的中国女性受压迫又无能为力的卑微形象进行“翻案”,发现她们曾经鲜活多彩的生命形态。由于文学研究者必然要借重妇女史研究的成果以支撑文本分析,而明清女性的主体性往往通过文艺活动展现,所以妇女史研究者也必须从文学现象取材——至此,两个领域便形成了一种彼此依存的共荣生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然而,在历来的分析框架中,主要是以女性诗词为核心史料。高彦颐曾在《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中提到,“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最恰当的材料还是由闺秀自己写作的大量作品——大部分是诗歌”[8](P 11);曼素恩也在《缀珍录》中开章明义,“我利用的最重要的史料,均来自于女作家的作品,主要是诗作”[7](P 1)。另一方面,确如胡晓真的观察,由于“晚明以来女性诗词选集辈出”,“客观上也使得女性诗词成为女性文学研究的主体”[9]。尽管近年来,学界已经意识到了研究的取材不能过于窄化,并且努力拓展文类的范围——诸如戏曲、弹词、散文、书信、传记、档案甚至文本以外的物质文化资料(如绘画、刺绣),但很少谈及小说。
目前,稍微触及古代女性与小说关系的是小说史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降,海外学者何谷理(Robert E.Hegel)和马兰安(Anne McLaren)受到伊恩·瓦特(Ian P.Watt)《小说的兴起》对英国小说与新兴的女性读者群体之关系相关论述的影响,提出中国古代存在小说的女性阅读者,并分析了女性可以进行小说阅读的前提,如具备一定的识字、经济能力,还要有大量的空闲时间。此外,他们也列举了明初以来女性阅读通俗读物的一些事例*Robert E.Hegel,The Novel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Anne E.Mclaren,Chinese Popular Culture and Ming Chantefables,Leide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Press,1998.。随后,不少中国学者也注意到了女性读者的存在,如李舜华、潘建国、宋莉华、蔡亚平、蔺文锐等人*参见李舜华:《女性读者与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学术研究》2009年第10期;潘建国:《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3页;蔡亚平:《读者与明清通俗小说创作、传播的关系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3-92页;蔺文锐:《情色诱惑:明代通俗小说读者的题材选择》,《戏曲艺术》2007年第2期。。然而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中,女性还只是作为被动的接受者而非主动的生产者而存在,远远未能触摸中国女性与小说关联的问题核心。可以说,在目前主流的历史叙述中,这个话题还是一个停留在时空深处等待言说的“空白之页”。那么,在“女性”与“小说”看似“绝缘”的文化表层之下,有过怎样的暗流涌动?她们是在何时发现并走进小说领域?这种“结缘”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和动态过程?才女又是以何种方式“瞒天过海”,跨越传统观念和妇德规范与小说接近?凡此种种,魏爱莲的《美人与书》可谓适逢其时,为我们提供了部分问题的答案。
二、揭开一段“无声的历史”
《美人与书》总计八章,除去具有“绪论”性质的第一章之外,其余文字被分为上、下两编,主要着眼于19世纪早期作为小说读者、作者以及“形塑者”的女性,并追踪“她们”写作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女性参与小说(特别是章回小说)的全景图画。
魏爱莲的主要观点是,相较于17世纪,19 世纪的女性写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一部分才女开始大量阅读小说,进而自己付诸创作。促使这一系列变化发生的原因有很多,如出版市场与印刷文化的发展,男性文人袁枚、陈文述的鼓励与倡导,乃至邮驿制度的发展,均令19世纪书籍的流通与女性文学网络的扩张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速度。然而,促成所有变化发生的最为关键的节点是1796年《红楼梦》的出版,它对才女的影响可谓空前。
魏爱莲选取了几个个案来论述她的观点。
案例之一是李汝珍和他的《镜花缘》。魏爱莲认为这部小说的作者虽为男性,但主题却是写女性和有关她们的故事。通过对李汝珍交游圈的考察,魏爱莲发现他生活在一个支持才女的文人圈子中。更为有趣的是,《镜花缘》收录的“十四家”题词中,有四家出自女性之手,而这在中国章回小说史上还是首次。由此,魏爱莲认为,李汝珍的拟想读者不仅限于男性,很可能还包括了官宦家庭的闺秀;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女性读者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小说的情节与走向——因为《镜花缘》的故事呈现出了很强的“女性化”倾向。
个案之二是女作者侯芝。她的一生充分展示了高贵的闺秀出身与其作品通俗属性之间的张力。侯芝之父为进士侯学诗,其弟侯云松、其夫梅冲、其子梅曾亮均为举人。她幼承庭训,父亲一贯服膺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故而侯芝也在弹词中公开宣讲妇德,标榜女性应温柔敦厚。然而,有趣的是,侯芝在1811年由诗词转向弹词写作,却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凭借诗才成名遥遥无期,而弹词则拥有更为广泛的女性受众,无疑是一条“终南捷径”。同时,魏爱莲通过对弹词《再造天》的细读,发现其“公开宣言”与“潜在修辞”之间存在着诸多裂隙——恰好可以印证侯芝所谓的“温柔敦厚”与自我表现之间的疏离。凡此种种俱可证明,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侯芝早已练就与各类女德闺训周旋应对的能力,她可以在创作中一边发泄才女不切实际的无尽幻想,一边又大力鼓吹儒家传统的价值观,最后竟能做到两者之间互不关碍。这无疑是我们理解古代才女如何跨越传统观念与女德规范、进而走入小说领域的绝佳个案。
个案之三聚焦于19世纪初的三位杰出女作家——梁德绳、汪端和恽珠,进一步阐释了才女与小说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作为弹词《再生缘》续者的梁德绳和《元明逸史》的著者汪端二人,关系甚为亲密——汪端自幼丧母,是梁德绳将她抚养长大。梁德绳出身显赫,她在续写《再生缘》时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试图将自己置于优雅、谦卑的妇德语境。例如,她最后将女主人公孟丽君从朝堂“解救”归家,同时宣称此书是与丈夫一起“联合写作”,并刻意夸大自己的年龄。尽管梁德绳做了如此之多的牺牲与努力,但是当时所有为她的《古春轩诗钞》写序题词的人以及阮元为她撰写的小传中,都对《再生缘》只字未提。倘若不是陈文述的《西泠闺咏》,我们今天可能对梁德绳续写《再生缘》一事一无所知;同样的,也是因为陈文述的记述,才保留了第二位女性——汪端与小说关系的资料。可以说,在汪端的写作生涯中,最冒险的行为就是创作了小说《元明逸史》,但随后又自己销毁。幸运的是,小说的许多细节还保留在其《自然好学斋集》的《张吴纪史诗》和《元遗臣诗》中。魏爱莲指出,通过改变文类,汪端得以实现了自己与小说联系的切断,进而安全退居传统之地。第三位才女是北京的满族人恽珠,即著名的清代闺秀诗人总集《清闺秀正始集》的主持者。她在赞赏女性才学的同时,也强调要从属于“温柔敦厚”一类的女德。于是,小说便成为一种禁忌。然而吊诡的是,恽珠的《红香馆诗草》却透露了她不仅阅读小说,而且还曾与书中人物唱和。这一切,似乎昭示了恽珠在私人领域的生活与作为清代“教化工程”代表之间的巨大沟壑。
梁德绳、汪端和恽珠无疑是那个时代女作家中的佼佼者。她们都表现出了对章回小说的兴趣,并做出了对传统观念和妇德角色的某种僭越;同时努力隐藏自己与小说的联系,并让这种兴趣从属于自身写作生涯中的其他重点。连同侯芝的个案,这四位女性各自向我们展示了19世纪的闺秀对小说兴趣的一个侧面,透露了才女与小说“结缘”过程中的种种艰辛和复杂图景。
个案之四以小说《红楼梦》及其系列续书为核心。魏爱莲认为《红楼梦》是促成古代女性与小说关系所有变化的关键性节点,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现存唯一一部出自女性之手的小说《红楼梦影》,即属《红楼梦》续书之列;其二,清代不少才女感伤于《红楼梦》的女性悲剧,留下了大量诗文。可见,女性已经成为《红楼梦》读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此后风行一时的《红楼梦》续书,也是为了迎合女性的审美与趣味。可以看到,这些续书无一例外地修改了原作女性的悲惨结局,同时说教性大大增强,并表现出不少“女性特质”——这无疑是从精神层面上向闺秀世界的价值体系进一步靠拢。因此,当顾太清决定选择小说文类进行创作时,她去写作一部《红楼梦》的续作,也就显得合情合理,因为有不少先导可资借鉴。此外,魏爱莲还指出,顾太清与沈善宝等才媛的闺中友谊和“联络写作”,为其小说创作提供了很多支持与帮助;而《红楼梦影》的出版商北京聚珍堂,在刊印书籍时也考虑了大众需求,它的读者定位不仅针对男性,更顾及女性。
《美人与书》的学术价值是丰富的。首先,它论证了在19世纪女性不仅成为小说的重要读者,更重要的是她们还以相当的能动性参与到小说的写作中,并影响着故事的情节与走向。其次,它通过侯芝、梁德绳、汪端、恽珠这四组平行个案,揭示了才女与小说“结缘”过程之艰辛的诸多侧面。再次,它明确了《红楼梦》在激发女性读写方面的空前重要性,这既是《红楼梦》续书系列流行于女性市场的重要前提与内在驱力,也为最初的女性小说创作实绩提供了合理背景。可以说,从17世纪到19世纪,女性对小说文类的参与度不断提升,从阅读、感怀到续写、编辑、批评等呈现出多种样态,最终成为章回小说的重要生产与消费力量,揭示出19世纪为女性与小说关系的新阶段。
三、“想象历史”的可能与限度
尽管《美人与书》从多个向度初步呈现了中国古代女性与小说的关系,但不得不说,魏爱莲所能利用到的这些材料,其流传下来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倘若没有陈文述的记载,我们今天很可能无从得知梁德绳曾经续写了弹词《再生缘》,也不会知道汪端创作过小说《元明逸史》。然而,汪端是陈文述的儿媳,梁德绳又是汪端的姨母兼养母,亲缘关系让这种“记录传世”显得得天独厚。同样,学界之于顾太清对《红楼梦影》著作权的确定也颇有戏剧性。《红楼梦影》出版于1877年,当时只署“云槎外史”;直到1989年,赵伯陶才根据《天游阁集》日藏抄本,确定该书出自顾太清之手[10]。该书为《天游阁集》的早期抄本,很早即流入日本,中国本土早已失传。
无疑,在中国古代的文化象征中,“女性”与“小说”都处于非主流、边缘的存在,因此,一旦从属于“内闱”的女性与谓之为“小道”的小说相“结缘”,不仅文人士子对此视而不见,就连女作家本人也遮遮掩掩、欲说还休,只能长期深潜于历史的表层之下。于是,我们不免会发问,在漫长的历史运动中,是否还存在着诸如《红楼梦影》一样被冠以“雌雄莫辨”笔名的小说作品,实际是出自女作家之手?或者,是否还有其他才女像汪端一样写作了小说,但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致使作品未能传世,导致我们今天对其一无所知?
除了典籍的大量缺失,妇女史文献资料本身的性质与属性也大大制约了这项研究的展开。在以男性为主的历史记载中,女性一直被视为“空白之页”,因此,妇女史研究者一直致力于追寻女性的声音,揭示“她们”也曾是能动的、鲜活的、具有主体性的一群。于是,除了被认为是“她们自己的声音”的女性诗词,研究者致力于挖掘形式各异的文献资料,从多个向度重写中国女性的生命故事。其中,女性传记备受关注。然而,传记本身就具有程式化的倾向,而且还会时常出现为亲友讳的情形,为女性所做的传记尤其如此。很多时候,传记中的女性只是代表了“男性的凝视”下的对象要素。可以看到,尽管我们今天认为续写《再生缘》是梁德绳最主要的文学成就,然而在阮元为她撰写的小传中,却对此事绝口不提。事实上,阮元不仅与梁德绳的丈夫许宗彦进士同年,也是梁德绳婚后的老师;不仅如此,梁德绳之女还嫁给了阮元之子,两家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姻亲关系。从道理上讲,阮元对梁德绳续写《再生缘》之事绝无可能一无所知。那么,阮元在小传中对此事的回避,很明显是因为弹词的低俗属性无法彰显梁德绳的谨守闺仪,也无法成为其家族的荣耀。
站在今人的角度回顾历史会发现,由于诸多原因,本应呈现网状结构的历史图景,往往只剩下一个个孤零零的点,散落在过往的时空之中。换句话说,历史具有文本的局限性,后来者所知的历史都是文本的呈现,其本身是局限、断裂的;我们绝不能认为全部的历史真实都存在于今日可见的文献之中,否则就会有简化历史的风险。反过来说,文本也产生于一定的历史背景,不能脱离外在的体制、环境、世界而存在,也就是说,文本同样也具有历史的局限性。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应该如何利用现存的文献资料来诠释史实、连缀“空白”,重构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返回曾经的历史现场。
在《美人与书》中,魏爱莲使用的文献资料主要有三类:一为女性总集、诗集和文集,即“她们自己的声音”;二是小说作品,特别是《红楼梦》及其续书、《镜花缘》以及弹词《再造天》;三是胡文楷编著的《历代妇女著作考》。细读《美人与书》可以发现,作者恰到好处地解答了这一课题所面临的主要困惑——不仅需要去还原不同材料的作者想要传达给我们的“言内之意”,而且需要挖掘潜藏于文字之下的“意外之声”;更重要的是,作者还必须动用自己的史识与想象,去填充文献记录的空白与不足,以弥合历史的叙事线索。对此,《美人与书》别出心裁地采用了“传记式”的考察路径与“互文性”的分析策略*Hu Ying,“Review on The Beauty and the Book:Women and Fiction in Mineteenth Century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007,67(2);也可参见任诗琦:《在历史现场聆听红颜——以〈美人与书:19世纪中国的女性与虚构文学〉为中心看魏爱莲的明清女性文学研究》,潘世伟、黄仁伟、乔兆红编:《中国学(第五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04页。。可以看到,魏爱莲从女性诗词和小说作品中,根据自己的写作意图重新筛选了资料:一方面,关注人物生平与文学活动的交织;另一方面,将诗词、传记、小说、书信、笔记等多种文本涵括在一个大的对话场中。通过将不同类型的文献资料相互串联,魏爱莲提供了一个次序性的、有条理的解释与分析,同时在适当的时候加以历史“想象”,最终形成一个有内在发展逻辑的故事。这样,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正史资料与虚构文学就形成了一种互文、交流、协商的态势;一个个历史的散点也被串联起来,从而编织进入一个引人入胜的情节之网。至此,曾经孤立、破碎的“美人与书”的历史图景,也就得到了生动、有效的还原。
具体涉及书中的案例,最能体现魏爱莲这一学术理路的,莫过于第六章对《红楼梦影》“自传性”的分析以及第七章对《红楼梦》及其续书之于女性参与小说作用的勾勒,堪称全书最为浓墨重彩的两笔。在第六章中,魏爱莲严密搜寻、铺陈各类史料,将顾太清《红楼梦影》的写作置于“北京-杭州”“满-汉”的双轴心视角中,指出梁德绳、汪端、恽珠、沈善宝等人对她的重要影响。同时,魏爱莲还通过将小说内容与顾氏生平并置,辨析《红楼梦影》的“自传性”特征,如有关生产和育儿的细节、小说中的吟诗会(顾太清和沈善宝曾组织过“秋红吟社”)以及对骑马、箭术和北京城的兴趣。第七章将《红楼梦》的续书谱系与女性的相关诗词放入同一个对话场域,观照《红楼梦》及其续书在女性群体中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的反作用,为《红楼梦影》的诞生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背景。
除此之外,《美人与书》中还有不少精彩的阐发,例如对侯芝《再造天》“公开宣言”与“潜在修辞”之间巨大张力的辨析,对汪端《元明逸史》故事内容与作品文类的还原等。可以说,在《美人与书》中,魏爱莲将“想象历史”的方法运用得十分精彩,得出许多令人信服且深具启发性的结论。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该书最引人质疑的,恐怕也源于此。在魏爱莲向我们展示的“美人与书”的故事中,证据链条中的一些“想象”环节,还无法构成推论下一步的前提。例如,尽管魏爱莲发现不少才女互通书信的资料,但依然无法证明她们是否真正组成了写作团体、形成一个影响广泛的闺秀文学网络。再如,尽管《镜花缘》的四家女性题词在中国章回小说历史上首次出现、意义重大,但若就此认定她们塑造甚至参与了小说的写作,恐怕还为时过早。事实上,这种大胆的假设与文献的过度诠释,也是目前海外妇女史研究特别是美国学界普遍存在的问题——2015年翻译出版的《张门才女》,可视为这一学术理路推向极端化的表现*曼素恩的《张门才女》(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中译本于201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罗晓翔。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在直接利用关于张家的文献之外,还加入了作者自己的猜想和创作,并且在编纂方式上采用类似“太史公曰”(the historian says)的形式。本书引起不少学者的批评和怀疑,争论的焦点即是质疑通过推测和臆想的方式重构古人的生活情景,是否已经超越了历史学的界限。。好在魏爱莲自己对此也有相当的自觉,《美人与书》从不惮于剖白研究思路的局限与矛盾*例如第七章,魏爱莲先从《红楼梦影》和《再造天》中提取了所谓的“阴性特质”,并以此作为检视《红楼梦》几种续书是否出自女性之手的标准,但随后又推翻了这种做法,指出其局限性。——这既是作者自我补充与修正的结果,也是未来相关领域研究的前进方向。
魏爱莲的《美人与书》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其研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史料分散,需要长期积累与细致爬梳;话题也只有一个大致的方向性,把控失度,便会“汗漫掇拾,茫无所归”。但是,这项研究工作的典范价值恰恰提示了一个开放式的构架,可以不断生长。恰如《美人与书》的《中文版序》所言,“借此次中译本的翻译之际”,魏爱莲再次“对原书内容做了一些改动”:“调整了论述结构,修正了部分错误,同时删去言语枝蔓之处”。她甚至认为,“中译本比英文版更加完备”。然而,这仍然是未完成的状态,魏爱莲清醒地认识到,书中“还遗留了一些问题,等待进一步的研究”:“譬如,顾太清于1877年出版的《红楼梦影》,除了序者沈善宝(1808-1862),是否还存在其他读者?倘若没有的话,那么,为什么?是因为作者的满族身份,还是因为清王朝的行将就木?或者,是此时来自西方的新型小说影响渐增,让中国的传统小说举步维艰?那么,为何同为北京聚珍堂出版、1878年问世的《儿女英雄传》,同样采用了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同样出自满族人之手,却读者众多、影响甚大?”[11](PP 2-3)
《美人与书》当然不算完美,但仍称得上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魏爱莲不仅成功地将“女性”写入小说史,也将“小说”写进了妇女史,同时为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视域。同时,书中那些暧昧不明的罅隙不仅无损于它的价值,或许反而能够激起读者对魏爱莲下一阶段研究的期待,抑或召唤感兴趣的学者同力协契,推动中国古代女性与小说互动联系这一课题不断深化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