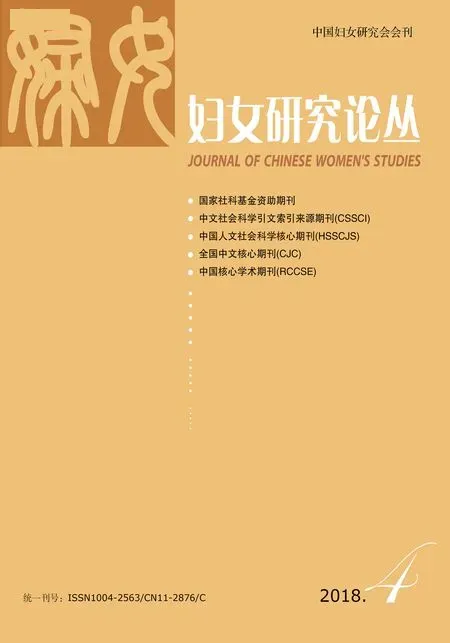满眼山河擎旧恨,谁将故国问青天①:明清之际的性别书写与自我呈现
——评李惠仪的《中华帝国晚期文学中的女性与国族创伤》
王晚名
(麦吉尔大学 东亚研究系,加拿大 魁北克省 蒙特利尔市H3A0G4)
2016年2月,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李惠仪(Li Wai-yee)教授的英文论著《中华帝国晚期文学中的女性与国族创伤》[1](WomenandNationalTraumainLateImperialChineseLiterature)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设立的约瑟夫·列文森图书奖(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该奖为英语学术界20世纪前与20世纪后的中国研究各设一个奖项,每年分别颁发给一部英语学术著作。李惠仪的研究因广泛检视并深入探索明清鼎革之际与女性有关的各种书写而获得“约瑟夫·列文森1900年前图书奖”(Joseph Levenson Pre-1900 Book Prize)*另一奖项“约瑟夫·列文森1900年后图书奖”(Joseph Levenson Post-1900 Book Prize)由意大利学者路易吉·通巴(Luigi Tomba)的《邻家政府:中国城市中的社区政治》(The Government Next Door:Neighborhood Politics in Urban China)获得。。
这部2014年出版的论著显示,明末清初的文学创作为后人留下了这一时期的种种记录——从国家和民族到家庭和个人,从无比残酷的现实到美妙绝伦的幻想,从锋芒毕露的批判与控诉到欲言又止的哀悼和申辩,虚实相间,悲欢难辨。这一时期大量身份各异的女性中,不仅有男性文人的关注、描写和想象的对象,也有与他们同仇敌忾、并肩创作的盟友与知己。
朝代更迭所造成的明末清初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特殊性,令这一时期成为北美学术研究的焦点之一。北美汉学界对中国女性写作尤其是明清时期女性写作的关注热度,也已持续三十年。李惠仪以女性的命运与抉择作为观察明末清初社会态势的重要视角,同时为这两个学术热点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杰出的范例。
一、该书的内容与结构
该书长达638页,其中前言、正文六章及结语共583页。各章长度分别为88页、101页、94页、96页、89页和99页,平均每章超过94页。在人文学科的英文学术论著中,这样的长度十分罕见。如此惊人的长度,容纳了丰富内容和坚实论据,进而支撑起了全书对多个主题的深入发掘和精彩论断。
第一章“借用女性化修辞的男性声音”,专注于男性文人在诗词中如何运用女性第一人称口吻或富于女性特质的修辞手段。在明末清初之际,男性文人采用这一传统手法曲折地哀悼明朝的覆灭,抗议清统治者建立的新秩序,自伤命途多舛、难以自决。其中,王士禛用这种所谓“女性化修辞”创作《秋柳》四章,表达尤为暧昧不明的政治内涵,推动了文人间以同样的手法遥相唱和,成为连接多个文学团体的桥梁。
第二章“借用男性化修辞的女性声音”侧重女性诗词创作。所谓借用“男性化修辞”,是指这一时期女诗人每每展现慷慨豪放的诗风,选择更能反映自己历史与政治关怀的怀古、咏史、咏怀等诗体和军事、武功等题材,刻画忠烈英武的人物形象,抒发自己的家国情怀、高远志向,表达对女性性别角色所承受的局限的不满。
第三章“英雄化的转型过程”,分析弹词、杂剧、小说等各类文本中的女性英雄形象。这些女性英雄形象或取材于现实,或属虚构,身份、性格、事迹各异,而她们的共同点是被赋予了为男性所不及的英雄气概和出众胆识。这些品质是对时代的需要与局限做出的回应。通过对女性英雄形象的塑造,这些文本的作者或伤悼男性无力挽回的一个朝代的陨落,或构想一种美好的新秩序。
第四章“欢愉与激情的命运”转向男性文人以诗歌、散文等文体对个人现实生活的记录,其中心内容是他们与自己的妾室或秦淮风尘女子(两类身份有时重合在同一女性身上)的共同经历与记忆。风尘女子所代表的情欲和爱恋,承载着男性文人对旧王朝花柳温柔之地的眷念,这种眷念和对故国的缅怀紧密纠缠,无法分割。而这些文人在对爱妾的记叙中把她们刻画成英雄,这些记录因此也成为男性自身品格的证明。
第五章“牺牲品身份和主观能动性”审视有关被乱兵劫掠的女性的诗词、话本小说等各类文学作品。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女性的悲惨命运往往与男性文人士大夫的遭际相通。而部分作品中女性对自身命运的把握,暗喻了男性在朝代兴替之时政治上的抉择。女性的贞与男性的忠对应,对女性节操上的白璧微瑕不忍苛责,便代表了对男性在乱世与新秩序下选择自保的宽恕和体谅。
第六章“评判与怀旧”对从明清鼎革之际直至康熙年间笔记、传奇等各种文本的分析,凸显了文人对女性的评判与对旧时代的怀念之间的矛盾张力。被评判的女性中既有“扬州十日”中或贞或淫面目各异的无名女子,也有陈圆圆、李香君这样的名妓。在文人笔下,她们的命运是明末道德危机与国难的缩影。对她们的赞美或谴责透露了男性文人对这一时代所抱有的种种复杂情绪与解读,如对明亡原因的痛苦反思,对时代洪流中个人际遇的偶然性的认识,或对美德与道德堕落共存的明末文化爱恨交织的矛盾态度。
二、该书的研究主旨
该书探讨书写中的两性关系与策略,试图重新评价明末清初文学。
早在2006年,李惠仪教授与同系的伊维德(Wilt L.Idema)教授、卫斯理学院的魏爱莲(Ellen Widmer)教授出版了合编的英文论文集——《清初文学中的创伤与超越》(TraumaandTranscendenceinEarlyQingLiterature)[2]。李惠仪为这一论文集撰写了一篇长达70页的英文绪论,概述该书致力解决的具体论题。蒋兴珍(Sing-chen Lydia Chiang)在为该论文集所作的书评中总结道:李惠仪的绪论显示,清初文学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作者的自我质疑和内在的道德判断。如若试图有效纠正以往政治和道德方面对于这一时期的偏见,则需重新评价内化的道德冲突对于清初文学复杂性和创造力做出了怎样的贡献。《清初文学中的创伤与超越》自觉承担起并且圆满完成了重新评价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的任务[3](P 439)。
这部论文集审视与分析了明末清初吴伟业、钱谦益、冒襄、丁耀亢等人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曲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作品出自男性作者之手,但大木康和吕立亭在他们的研究中已经采用了性别观照的角度来考察男性文人“复杂的政治和心理目的”(complex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purposes)[3](P 440)。二位学者敏锐地揭示,冒襄、丁耀亢等人在他们的散文和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身上投射了自身的渴望与焦虑。他们的男性气概(masculinity)体现在故国的性别、家庭、社会和政治秩序与关系中。他们痛悼和愤懑着这一切的毁灭并想象和期待对其的重建。而这一切,是通过他们笔下的女性所具备的美好特质和所经历的颠沛流离折射出来的[3](PP 440-441)。蒋兴珍在书评末尾进一步总结道:通过对群体性创伤(collective trauma)的文学反响(literary responses),这部论文集探索了书写、阅读、文本编辑、文学评论、戏剧表演、性别建构(gender construction)以及藉此对破裂的共同体(a fractured community)进行“(重新)构建”(re-construction)等一系列行为背后隐藏的复杂心理动力(complex psychological impetuses)[3](P 443)。
蒋兴珍的总结凸显了《清初文学中的创伤与超越》所反映的以李惠仪为代表的北美学者对明清易代之际文学写作的一个关注焦点,即这一特殊时期文人的道德、情感困境及其隐秘的外化和解决方式。而她未特别明确指出的一点是,北美学者选取的观察角度之一,是写作者如何借用异性身份和声音进行自我呈现和塑造。
蒋兴珍未指出这一点,大约缘于性别观照并非《清初文学中的创伤与超越》的主要研究角度。十年之后,这一角度在《中华帝国晚期文学中的女性与国族创伤》中被李惠仪重点运用。《清初文学中的创伤与超越》对明清鼎革之际文人学者的内在困境和写作策略的关注与探索,也在《中华帝国晚期文学中的女性与国族创伤》中得到延续。
《中华帝国晚期文学中的女性与国族创作》关注的时间段与《清初文学中的创伤与超越》相同,并同样以明清之际朝代更迭所造成的国家和民族的“创伤”(trauma)为重要主题。在《清初文学中的创伤与超越》提供的对男性写作广泛而坚实的研究基础上,《中华帝国晚期文学中的女性与国族创作》进一步探讨男性文人如何通过各种与女性有关的方式来书写创伤;与此同时,在近三十年明清女性写作研究热潮的基础上,该书关注女性在这一时期如何采用“男性化修辞”来书写创伤。在北美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包括明清时期女性写作领域,这种男性和女性写作并重的范例尚属凤毛麟角。孙康宜(Kang-i Sun Chang)教授在对此书的书评中将此书同时列为明清女性研究和性别研究两个领域的重要专著[4](P 223)。笔者认为,性别研究这一定位相对来说更为全面准确。
三、别具只眼的研究视角
(一)挑战和超越性别界限
古典文学的创作实践中,作者模糊性别界限或转换性别角色(gender role)的尝试所在多有。其中一类典型的例子,即是始自《楚辞》的“美人香草”寄托比兴传统。在这类作品中,男性作者凭借富于女性特质的修辞手段或采用女性第一人称口吻,通过描述对爱情曲折艰难的追求,隐晦委婉地表达政治志向与抱负。然而,此类书写往往局限于男女爱情主题,并且在角色和情节的设置中基本遵循儒家正统意识形态中的性别秩序及行为规范。如果用“挑战”与“超越”来定义这类实践,则易显得用词分量过重,过于拔高。而李惠仪在论著前两章中的分析显示,在明清之际政治失序(political disorder)的状态下,转换性别角色的书写呈现出比以往远为丰富的多样性、远为激烈的情绪及远为复杂的写作意图,体现了明末清初文人“挑战”与“超越”性别界限时出众的活力与勇气。
第一章检视的文本中即有一部分属于男性作者采用女性第一人称口吻的类型。吴兆骞以女子刘素素和王倩娘之名所作的两组诗歌是其中非常特殊的例子,与他创作的其他此类诗歌中遵循传统发出的薄命女子“绝无怨怼君上之意”的“悲苦之音”[1](P 24)形成鲜明对比。诗中,刘素素和王倩娘哀叹着女性的不幸命运与乱世中的颠沛流离。李惠仪清楚地知道,在这一动荡时期,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的意象在诗歌中无处不在。她的分析显示,这两组诗歌共同的独特性在于,刘素素和王倩娘的哀叹不仅暗合吴兆骞自身的坎坷遭际,而且很可能是吴兆骞借以悲悼明朝覆灭、抗议清朝政权的伪装(guise)手法[1](P 23)。
李惠仪更为深入而令人击节的论证,则在于根据二者不同的创作背景而对吴兆骞写作目的和手法的推测。1657年,吴兆骞被卷入株连极广、屡兴大狱的丁酉江南科场案,1658年被流放东北宁古塔,直到1681年才被允许返乡。而这两组诗歌分别写于1657年和吴兆骞北上的1659年。李惠仪敏锐地意识到,在前一组诗中,吴兆骞并未——像他自己惯常所做的那样——声明这是一位男性诗人以女性口吻吟咏的“代言”之作,任由他人误以为这是一组女性作品。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指出,这组诗只是游戏笔墨;吴兆骞作为作者,与自己虚构出的刘素素这一代表无数不幸女性的形象保持着距离。而所谓王倩娘所作的后一组诗本出自吴兆骞之手,这一点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吴兆骞的遭遇使王倩娘的故事显得异常真实,王倩娘的形象也令读者深刻体会到吴兆骞命运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在这两组诗歌的创作和流传的过程中,吴兆骞饰演了多重角色。他在作品中虚构了刘素素和王倩娘这类时代的牺牲品,同时,他自己本身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牺牲品。他将这两组诗歌以题壁诗的形式公布于多数女性通常难以涉足的公共领域,更以刘素素之口盛情相邀,“欲与吴下才人,共明妾意”,引致大量唱和;同时他自己又是被邀请的“吴下才人”之中的一员,并藉此建立与文坛的交流和联系。李惠仪猜测,吴兆骞应当是深知并利用了一个规律,即文学作品的流传和保存往往得益于其中女性形象的美丽与痛苦[1](P 25)。
李惠仪用吴兆骞一例让我们看到,明末清初文学创作中应用性别策略的丰富、微妙和精巧程度,居然可以一至于斯。此外,她在第一章中对大量诗文的分析进一步提醒我们,由于政治环境的严酷,明清易代之际对“美人香草”这一传统的应用达到一个高峰,对这类诗文中的隐喻与寄托的诠释也具有了远比以往丰富的可能性。
在明清时期女性写作研究中,对性别界限的挑战和超越始终是重要论题之一。不同于男性文人“美人香草”写作传统的历史悠久,女性作者在这一时期刚刚开始建立自己的这一新传统[1](P 5)。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儒家性别伦理为女性设置的界限严格而名目繁多,这些界限在制约女性的同时,也为女性的挑战和超越提供了比男性更多的目标和可能性。高彦颐(Dorothy Ko)1994年出版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TeachersoftheInnerChambers:WomenandCultureinSeventeenth-CenturyChina)中显示,明末清初女性的创作、结社、诗歌酬唱,无不是为争取更大活动空间而与儒家性别秩序所进行的协商(negotiation)[6]。高彦颐所关注的时间段和人物与李惠仪的论著虽然有重合之处,但她所取的例子主要出于时局相对稳定、经济繁荣的时期;而李惠仪所关注的特殊时期,促生了更为多姿多彩、锋芒锐利的尝试。正如她所指出的,明清之际的政治失序既提供了各种新行为的可能性,也孕育了可以想象新的社会角色的空间。对于女性来说,则体现为既参加抗清运动,也在写作中不再局限于以闺阁生活为主题、以精致婉约为典型语言风格、以男女情爱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女性化形式,而是自觉地塑造充满英雄气概的自我形象、探索性别界限的不确定性[1](P 100)。李惠仪在第二章数度援引同时代的男性文人对她们的赞语:“凡所叙述,慷慨激昂,绝不类闺房语。”[1](P 148)“意殊慷慨,不做儿女态也。”[1](P 153)“慷慨英俊,无闺帏脂粉态。”[1](P 154)“诗才清俊,作人萧散,不以世务经怀,傀俄有名士态。”[1](P 154)这些赞美证明,她们在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两方面对传统女性性别角色的背离,在当时已经得到充分的注意与承认。
女性在明末清初时期担任的新的历史角色,不仅通过参与政治与军事斗争,而且通过从事写作来实现。例如,女性原本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所以不必像男性一样面对降清或归隐的抉择。即使如此,一部分女性依旧选择生活在对前朝的忠贞和缅怀、对新政权的拒绝和反抗之中,这意味着她们和一些男性一同选择“遗民”这一自我定义(self-definition)。李惠仪指出,“女遗民”的身份超越了女性性别专属的美德范畴[1](P 101)。其中,以徐灿、朱中楣为代表的个别女性,甚至对自己丈夫仕清进行了含蓄的批判。王端淑在诗文创作中自觉地承担起了记录和评判历史的责任,包括对自己父亲未能及时自尽殉国表达一种近乎不近人情的惋惜,被李惠仪视为“诗史”。而诗史这一角色,同样并非儒家意识形态为女性提供的身份定位。李惠仪指出,在太平盛世时无须面临的忠君爱国的选择,成为极少数女性此时宣告自身独立性(independence)和坚持自我(self-assertion)的一种手段[1](P 101)。
这些女性作者在写作中发出的声音和塑造的形象,同样模糊甚至超越了性别局限,呈现出男性化的特质。李惠仪承认,女性写作中的男性化(masculine)特质其实定义并不明确;她选择将直抒胸臆、雄健有力视为男性化的艺术风格[1](P 112)。这一点也与当时男性文人频繁使用“慷慨”一词形容这类女性作者及其写作中的男性气质相吻合。第二章中检视的大量文本中被王端淑、李因、刘淑等女性作者加入了本属男性专利的政治、军事、武力因素。她们在诗文中慨叹时局国运,表达了对政治的关注和参与。她们反复描绘剑的意象,歌咏侠的形象,抒发自己的英雄抱负。她们甚至大量应用描述男性性别角色的词汇,进行对自己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义。例如,刘淑在诗歌创作中发展出的自我形象,不但有慷慨悲歌的剑侠、闲云野鹤的隐士这类男性专属的身份,甚至有跳出家庭和社会框架(framework)、求索超越凡人的种种局限与人类必死命运的可能性的“孤生”[1](P 144)。王端淑记录自己与一位男性的友谊,将自己定位为他的“诗酒交”[1](P 167)和他所属的遗民阵营中的一员。如果如魏爱莲所论,这位男性其实便是她的丈夫丁圣肇,那么她刻意将二人的夫妻关系隐去,从而尽可能地掩盖自身女性特质这一尝试,就显得更加有趣而意味深长。即使是在表达和描绘女性之间的友谊时,女性作者也因采用男性的标准和模式而使其显得更具分量。王端淑、周琼、吴琪等人在诗中突出她们交流中涉及哲学、历史、政治和军事内容的因素,甚至纷纷将闺友比拟为信陵君、范蠡、王羲之、黄庭坚等士、隐、侠一流人物。
女性对自身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义,源于她们对女性社会性别的不满(gender discontent)。女诗人如周琼、顾贞立都在诗中表达了对女性装束的厌弃,并避免使用与之有关的带有色情意味的词汇。她们这种不满,与对历史和政治关注、参与和失望又是紧密相关的。而这些例子的大量出现以及其中包含情绪之强烈、使用手法之多样,当拜明末清初的残酷现实所赐。
《中华帝国晚期文学中的女性与国族创作》前两章的对照反映了一个现象:明清之际男女作者都借由书写中性别的互换、对性别界限的超越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抒发对自身的期许、对遭际的不平、对现状的愤懑等种种情绪。鉴于女性写作迟至明末才开始繁荣,两性气质和心理在文学作品中互相依存并相互阐发的写作形式——尽管李惠仪并没有直接做出这一结论——应当是在明清之际才达到古典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
(二)隐晦的自我表达与自我描绘
孙康宜指出,各章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互动是该书最突出的特色。这种联系和互动的表现之一,就是含有“自我”(self-)这一前缀的词汇在各章中的频繁使用。据笔者粗略统计,该书中这样的词汇约有220余个,即在正文中平均不到三页就出现一个。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包括“自我定义”(self-definition)、“自我揭示”(self-revelation)、“自我质疑”(self-doubt)、“自我辩白”(self-justification)等。通过应用这些词汇,各章的分析论证相互印证、相互呼应,共同揭示了一个主题,即明清之际的男女作者通过各种有关性别的书写进行自我表达和呈现。前文所述及的超越性别界限、改换性别角色的手法,是其中一种方式。该书的后四章检视了男女作者在各种体裁的文本中描写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中既有虚构的艺术形象,也有历史人物,包括作者身边熟识的挚友或宠姬。李惠仪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深入挖掘了作者如何通过对这些形象的刻画透露自己的心态、情感和价值观。
第四章的研究重心是秦淮风月之地。李惠仪指出,明末清初的许多文人甚至包括1647年英勇牺牲时年仅16岁的夏完淳,都将政治上的悲叹和英雄抱负融于对这处温柔乡充满浪漫气息的缅怀中。而其中冒襄、周亮工、吴伟业、钱谦益对几位他们所爱敬的、多数出身于此的女子的回忆中,则隐含着更为复杂的心理。
李惠仪认为冒襄《影梅庵忆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为自己战乱中保持旧有的生活方式进行辩护,将正统的道德和社会秩序——有时通过将之唯美化的手段——加于混乱的时世[1](P 307)。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爱姬董白则在其中担任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冒襄对董白才华的赞美显示,董白所创造的充满女性柔美特质的空间,不仅为他提供了一处政治失序中的避难所,而且令欢乐、激情和正统道德在其中得到统一。而董白的贤淑、温顺、克制和自抑,对家庭毫无保留的付出,以及对关羽这样的道德楷模的崇敬,赋予了她道德上的模范性,这一模范性使得他们在乱世中尝试保持的浪漫唯美的生活特质也变得合理而正当起来。李惠仪对这一主题的探索充分展示,对于道德的正当性的关注是冒襄在《影梅庵忆语》中的自我呈现(self-presentation)的一个重要特点。他特别强调自己对孝道和家族荣誉毫不动摇的服从,对于他来说,这些远比他与董白和陈圆圆这些风尘女子的情谊更为神圣和重要。当他为这些责任而不得不将她们置于不顾时,他明确表示“负一女子无憾”,“如释重负”[1](P 311);当举家逃难时,他的双手搀挽的,一边是老母,一边是发妻,而无余力照顾董白。他对董白的艺术天赋的欣赏,包含着他作为董白的伯乐和良师的自我祝贺(self-congratulation);他在热情洋溢地慨叹董白“断断非人间凡女子”[1](P 312)的同时,也不忘提到董白敬慕他“慷慨多风义”[1](P 312),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无愧于董白的奉献的君子的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
比冒襄情况更为复杂的是由抗清而仕清的“贰臣”们,例如周亮工、吴伟业、钱谦益三人。为自责(self-reproach)和自辩(self-justification)的动机所激发,他们在对王荪、卞赛、柳如是三位女性的描写中投射了自我转化(self-transformation),将三位女性描写成充满勇气和忠贞的英雄。周亮工明末任山东潍县县令,曾于清军围城之际誓死抵抗。但李惠仪注意到,在入清后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周亮工对于这次守城抗敌的文字记录几乎从未被人提起,而且其中绝大部分都被他从自己的别集中删去[1](P 322)。李惠仪在第四章所分析的《海上昼梦亡姬成诗八章》,是周亮工仅剩的有关此次抗清的作品中对王荪的记录。在这组诗歌的自序中,周亮工仅用二十余字,简约地记述了王荪与自己相伴七年多的“共甘苦”[1](P 323),而其中涉及的唯一具体事件,即是王荪伴随自己抗清的义举。他同时也详尽记录了王荪对他充满深情的临终遗言并倾诉自己对她的思念之情。李惠仪则指出,王荪对周亮工的深情,是和他们共守潍县的记忆密切相关的[1](P 324)。在记录二人魂梦相会的诗作中,李惠仪同样通过只言片语发掘周亮工的隐秘心理。例如在二人梦中的交谈中,周亮工回顾自己从北到南的历程,暗示在自己由抗清至镇压反清起义的行为中,一以贯之的对合法政权的效忠。这一诠释方式既是清廷的惯用逻辑,也是“贰臣”们进行自我辩白的方式。周亮工还提到王荪提醒他宦途凶险,不如早日致仕。对照他后来的两次下狱,被劾论死,王荪的忠告显出惊人的先见之明。李惠仪指出,对于周亮工而言,王荪不但为他的人生选择提供了理解、接受和明智的劝告,更令他铭记当年抗清的英勇壮烈——这一切没有像他后来的人生那样,被变节所玷污[1](P 331)。
在对吴伟业《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和《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两首长诗的分析中,李惠仪将一些看似关联并不紧密的片段联系在一起,揭示吴伟业诗中暗含的深意。在《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中,卞赛叹息女性在昏庸无能的南明小朝廷和残暴的清廷统治下的悲惨命运。而在《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中,卞赛以薛涛所制的十色笺书写经文。她虔心向佛的选择,反而使她重现作为青楼名妓所具有的、体现着情欲和灵性的美。这样一个形象多面的卞赛,成为承载着种种历史见证、使一切免于被遗忘的流浪诗人和评论者。李惠仪将这两首诗对照阅读并进行诠释,论证吴伟业通过呈现卞赛个人的痛苦、以宗教为归宿的选择和决定自身命运的勇气,将她塑造为这样一位诗史。同时李惠仪指出,吴伟业笔下的卞赛在哀叹同时代女性的不幸命运时,其实被赋予了吴伟业的判断和感受。吴伟业通过这一方式确认了自己同样作为一位诗史的自我定义,并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历史时刻,完成了对自己过去的救赎,以及对卞赛代表的充满欢乐与激情的温柔乡的追忆[1](P 356)。
在对钱谦益和柳如是的例子的研究中,李惠仪检视的文本数量更多,内容更为丰富。她注意到,从17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在钱谦益的诗作中,他与柳如是之间的男女之情总是和他们作为抗清伙伴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1](P 357)。柳如是入清之后的诗作几乎全部湮没无存,她作为一个明遗民的形象完全是在钱谦益的诗作中建立起来的[1](P 360)。钱谦益盛赞柳如是的英勇、才智和忠贞,并将她描写为一位女侠,一位梁红玉式的英雄,一位拥有高洁志向却被人苛责不能保全贞节的不幸女子,一位真正能够理解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与情感、与他志同道合的前明忠臣,一位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中与他怀有同样的忧惧、文学追求和政治目的的伴侣。在这样的形象里,钱谦益隐含着他设计的韩世忠式的英雄人物和杰出军事家的自我形象(self-image),暗藏着一个被误解的、隐蔽的明遗民的自我身份认同[1](P 357)。通过这样的方式,钱谦益试图洗雪仕清为他带来的耻辱,向世人控诉他承受毁谤的不幸命运,呼吁柳如是和后人理解他的志向、苦闷和英雄行为,而不是仅仅依据他的屈膝投降来判断他的品行[1](P 369)。
在该书分析的各类文本中,论书写者和被书写者关系之熟悉与密切,无过于此类文人与风尘女子的例子。因此,以这种亲密关系为前提的书写下潜藏的自我呈现和塑造,应该是最为丰富细腻而多层次的。而各类书写者中,论心态矛盾复杂、迫切需要言说又难于启齿以及处境的微妙、尴尬与艰难,大约也无过于周亮工、吴伟业、钱谦益一类由抗清而仕清的“贰臣”。他们在此类文本中对自我形象的塑造,应该是极为隐蔽的。李惠仪在第四章中对这类文本的诠释以及讨论男性文人对这类被书写者所代表的温柔乡的记忆投射了对前朝缅怀的部分,笔者以为是该书最具深度、最强有力的论证之一。
在其他章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对男性文人的心理同样深刻的分析。例如她在第五章敏锐地指出,在对屠杀劫掠中的牺牲者的记录中,有关抗清的政治因素往往被冲淡,取而代之的是对牺牲者“孝贞”[1](P 423)的叹息和赞美。有关历史的记忆,就这样通过对新秩序的顺从和融入而流传下来[1](P 429)。这一章李渔笔下《巧团圆》中的主人公耿二娘在被掳之后,凭借自己的“权宜之术”[1](P 468)免于最终失身。而《奉先楼》中的舒娘子则用自己的贞节作为交换,保全了自己儿子的性命、夫家的香火。李惠仪指出,李渔对耿二娘和舒娘子的态度反映了他对道德的重新定义(redefinition),这一定义中容纳了妥协、实用主义和个人利益的成分,反映了乱世促生的种种困惑、矛盾和无助。在对这一切做出评判时,必须注重本意、行为和后果之间的关系和平衡[1](PP 475-476)。第六章中,在分析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时,李惠仪甚至偶尔放下一个学者应该保持的冷静,尖锐地批判王秀楚在怀孕的妻子为了保全他挺身而出阻挡清兵时的无所作为,以及他在痛斥一些女性不能守节全贞的同时,对自己的无能几乎全无自责(self-recrimination)和自省(self-reflection)的心安理得[1](PP 484-485)。这种个人情绪的一闪即逝,恰恰是一个学者尤其是一个女性学者才华和人性的闪光点所在。
四、“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方法
《清初文学中的创伤与超越》中检视的作者和作品,有不少出现在该书中。与此同时,李惠仪在该书中充分体现了北美华人学者精通双语的优势,秉持其一贯的大量占有第一手资料的特点,涉猎了更为广泛的研究对象。Yang Zhiyi在对该书的书评中指出,该书涉及了从晚明到民国初期的所有文学和历史类文体,其时间和文体上的广度是其长处[5](P 1)。孙康宜更为具体地指出,此书检视的文本体裁包括诗词、传奇、杂剧、文言和白话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弹词、回忆录、笔记、地方志、传记等。她盛赞此书与《柳如是别传》相近的“百科全书式”研究方法,称此书充分显示了作者的“博学”(erudition)[4](PP 222-223)。
李惠仪在该书中对大量资料的处理展示了她深厚的文本分析和考据功力,其中两个突出的例子分别是第三章对林四娘故事和第五章对自沉烈女事迹的分析。前者检视从清初蒲松龄、李澄中、王士禛、陈维崧、林云铭、安致远、陈奕禧七个版本到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林四娘形象从柔弱艳魄、飘渺剑仙发展成为尘世忠贞英武的复仇女将的过程,从而展示一个虚构的文学形象在逐步演变为似乎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的过程中如何被英雄化。后者比较关于自沉烈女传说及诗作的更为复杂多样的版本,逐一罗列谈迁、计六奇、施闰章、陈维崧、王端淑、黄周星、陈鼎、钮琇、恽珠、沈善宝等人的诗作、笔记、诗话、诗歌总集以及《姑妄言》《武冈州志》中烈女姓名、籍贯、故事情节以及所录诗作的异同。在此基础上,李惠仪进一步分析不同作者的自我认知(self-perception)、政治关怀(political concerns)和道德判断(moral judgment),论述文本中对贞节和孝道的强调可能如何冲淡政治抵抗的成分,以及烈女所忠诚的对象(明抑或清)可能如何被轻易掉换。这两部分内容可以与其他学者的研究互相对照参看。例如,台湾学者王佩琴曾有旧作《林四娘故事研究》[7];美国学者田菱(Wendy Swartz)的专著《阅读陶渊明》第二章中,有专门一节检视陶渊明的形象在历代作者所作的传记中如何发展和演变[8]*第二章这一节应该是在她2004年发表的文章的基础上改写而成,见“Rewriting a Recluse:The Early Biographers’ Construction of Tao Yuanming”,《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2004年第26期,第77-97页。。该书与这些研究的对比,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领域、不同背景的学者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异同。
尽管在该书中对女性写作的研究所占篇幅不多,仅有第二章以及第五章一部分等处,但该书所分析的文本绝大部分都是以女性为书写对象的。因此,“女性”是该书无可争议的重要主题。该书所涉及的文本数量庞大,题材多样,这就决定了其中女性形象的丰富多彩。这些女性来自社会不同阶层,性格迥异,经历各别。女性形象作为被研究对象在一部专门论著中所呈现出的这种多样性,无论在中文还是英文研究领域中都尚不多见。
正如前文所论及的,明末清初的文学作品大量描写社稷飘摇、山河破碎的时代中的女性,例如身世飘萍、无力主宰自身命运的刘素素、王倩娘,英勇壮烈、不让须眉的王荪、柳如是,避世绝俗的卞赛。除此之外,第四章中男性文人在诗文里追忆的还有力阻侯方域与阮大铖结交的“侠而慧”的李香[1](P 304),“日与文人骚客相往还”的特立独行的“女侠”寇湄[1](P 305)等。而在其他章节中,李惠仪的大量研究与分析显示,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和史料记载中的女性形象,其类型的多样远不止此。
在第三章中,弹词《天雨花》刻画了封建士大夫家庭的女儿左仪贞的形象。在明末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造成的政治失序的背景下,“才智节烈”[1](P 223)的左仪贞得以超越性别界限,进入公共活动领域,参与政治活动。同时她与妹妹左婉贞都对父权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抗议和反叛。吴伟业在杂剧《临春阁》一反“红颜祸水”的传统论调,将张丽华和冼夫人两个历史人物描写成手握大权、参与政治、才华出众的南陈朝廷“重臣”[1](P 244)。她们之间的关系实现了男性文人关于“君臣知遇,生死交情”[1](P 245)的理想,而她们的忠贞和才干则与“男儿误国”[1](P 251)的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五章中,孟称舜的传奇《张玉娘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所反映的贞节观与耿二娘和舒娘子“妥协下的贞洁”(compromised chastity)截然不同。主人公张玉娘以女性的“贞节自许”类比男性的“忠勇自期”[1](P 454),选择坚守婚约,不事二夫,终以身殉。
第六章中,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丁耀亢的《续金瓶梅》以及扬州、江都等地地方志等文本当中,记录了兵燹中遭受劫掠、凌辱和屠杀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她们有的为保全贞节而毅然赴死;也有的觍颜事敌,毫无廉耻。男性作者对她们在危难之际的不同选择表达了敬佩、同情或鄙视。这部论著汇集一个时代的史实与文学作品,为读者呈现出一个时代的女性群像,为作者的论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五、研究不足
Yang Zhiyi指出,该书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对称设置的[5](P 1)。仅从题目的对仗便可看出作者的意图十分明显。然而对于“女性化修辞”(feminine diction)和“男性化修辞”(masculine diction)这两个术语如何定义,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连李惠仪自己也在第二章中承认这是一个问题。孙康宜认为,“女性化修辞”这一说法容易误导读者,令读者以为第一章整章的研究对象都是突破性别界限的“香草美人”式的作品;其实其中不少作品只是风格属于婉约一派而已,而婉约风格从来并非女性作者的专利[4](PP 226-227)。严格说来,婉约与豪放风格之别出现在词这一领域;并且即使在词学领域,这种二分法也显得过于简单化。而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并无哪一种风格被认为是女性化的。男性作者在各种风格的创作中自由而毫无顾忌地大胆尝试,并且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后起的女性作者则和她们的男性前辈与同侪承继了同一套理论和修辞传统,并未发展出另外一套专属女性的系统。第一章中讨论的令王士禛诗名大噪的《秋柳》四章,寄托深远,和者如云。无论和者是男是女,都不曾因其诗风而被认为是女性化写作。第二章讨论的女诗人陈的《秋柳》和诗,也只是被评为“濯濯如新”[1](P 103),并无人专就其性别而对其诗作出特殊评价。因此,将男性文人的这类作品放在第一章这一题目下,或许反倒稍为有损于该书性别观照的理论深度。
明清女性写作热情和成就曾被世人长久忽略和遗忘。在明清女性写作研究的热潮已持续近三十年的今天,她们的声音仍旧值得进一步被发掘。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古典文学历史的长河中,女性写作的数量、质量和影响都远远无法与男性写作相比。如果在研究中仅仅聚焦女性,未能充分考虑女性写作与男性写作的关系以及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的位置,则得出的结论可能单薄孤立,甚至不堪一击。李惠仪的研究,建立在对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学创作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基础之上,并将女性写作放置在历史发展和文学传统的双重语境中,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范例和思路。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华帝国晚期文学中的女性与国族创伤》都完全无愧于孙康宜“里程碑式”(monumental)[4](P 222)作品这一评价。继叶嘉莹先生之后,北美汉学界文学、历史及女性研究领域,涌现了李惠仪、高彦颐、方秀洁等新一代华裔女性学者的代表。这些女性学者正处于学术高产期,她们更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