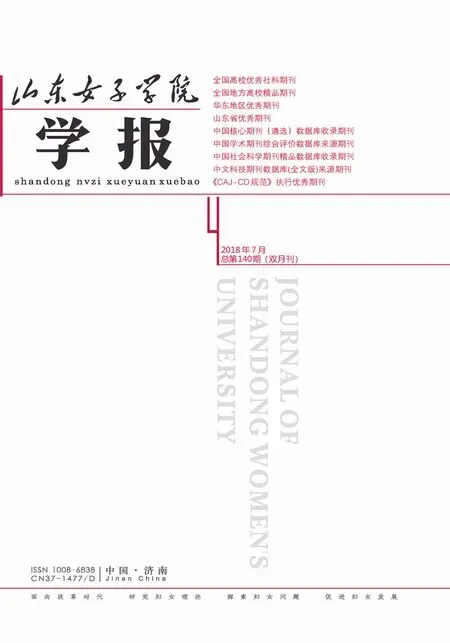女性在民族战争中的爱情悲歌
——读萧红《朦胧的期待》
周佳薇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 沈阳 110034)
萧红是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最有代表性的女作家。萧红始终坚持以女性的眼光观察世界,她用最真实的笔法写下了她的所感所想,唤醒了真正自觉的独立女性的声音,这与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权利有着巨大的冲突,对20世纪的文学创作有深远意义。从五四新文化思想启蒙开始,女性问题就突显出来,萧红作为觉醒的女性,她从性别的立场和女性的经验出发,描绘出女性在社会中遭受的苦难和命运,真正写出了中国广大妇女的生存面目与生活困境。萧红的文学创作中,有着对父权的批判,对被压抑的底层妇女的同情和对人性愚昧的讽刺,我们却很少看出她对爱情主题的诠释和表达。作为一个女人,萧红一生渴望爱情、憧憬爱情,甚至可以说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为了爱,她可以奋不顾身追随陆哲舜去北平,却忽视了封建势力的强大和男人的怯懦。为了爱,她可以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多次忍耐萧军的感情出轨,她忽视了爱情的平等性。对爱情,萧红充满着罗曼蒂克的幻想。遗憾的是,爱情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和伤害,因而,在她的创作里,极力表现了当时女性的爱情悲剧,为她们唱出了一首首悲歌。
一
小说《朦胧的期待》主要讲述了国民党高级官员家中的女佣李妈一厢情愿爱着卫兵金立之,在得知金立之要上战场后,她表现得既焦虑又恐慌。善良淳朴的李妈为情人买烟的功夫得到的却是他不告而别的消息,她最后只能将这种感情化作朦胧的期待。小说开头李妈唱着“一年之中三百六十日,日日在愁苦之中。还不如那山上的飞鸟,还不如那田上的蚱虫。”这是因为她得知金立之要去前线打仗,内心十分荒凉、愁苦,而唱了这首怨妇歌。小说结尾处也反复强调李妈心里的话“把我的工钱,都留着将来安排我们的家。”我们可以看出萧红对理想生活和理想爱情的向往,以及对家的归属感的强烈期盼。在创作这篇文章前期,萧红就和萧军感情破裂,又于1938年5月与端木蕻良结合,上一段感情以失败告终,萧红想再一次把对爱情希望寄托在与端木蕻良的感情中。所以,文章结尾处这段话不只是李妈对爱情和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的憧憬,更多的是萧红希望自己的爱情有一个完美的结局。这与萧红在童年时期心灵受到创伤有着很大的关系。萧红出生在没落的乡绅地主家庭,从小由于父母重男轻女的思想而受到心灵的伤害。她失去了家庭中的温暖和爱,饱受着封建社会带来的坎坷与痛苦。她在无可奈何而又义无反顾地舍弃原生家庭后,又满怀希望去探寻,她把这种家庭中爱的缺失寄托于对爱情的渴望中。不幸的是,她在感情道路上又历尽坎坷,初恋时喜欢了表兄陆哲舜,其由于家庭势力的威胁抛弃了萧红,后来遇到萧军意外结合,二人本来就缺乏感情基础,在战局骤变时,萧红希望有个稳定的居所去安心创作,不想忍受生活的各种折磨,可是萧军却一心要实现革命事业的抱负,结果二人因性格不合导致分手。至于第三次与端木蕻良的结合,也是一次错误的选择,萧红一生都在苦苦追寻爱情,她从心底里渴望两情相悦的爱情。
萧红笔下的李妈性格原本是开朗的、明亮的。“李妈才二十五岁,头发是黑的,皮肤是坚实的,心脏的跳动也和她的健康成和谐。”平日里,她拿着竹竿经过那葡萄藤的时候,总是要触碰着正生长的葡萄,并说着“要吃多啦……多快呀,长得多快呀……”但是得知金立之离去后,她变得沉寂、忧郁了,也不再看那葡萄藤,厨房里也不再有往日欢快的气氛,同时她的身形憔悴许多,脸色失去了以前的神采。李妈不知道怎么表达内心的情感与愿望,只能默默承担着伤痛。萧红以独特的女性的立场观察并审视社会和人生,她用细腻、柔和的语言来描述着李妈遭到的来自社会、家庭的心灵伤害。《朦胧的期待》看似是一篇叙述爱情的小说,实则作者想表达的是荒凉的人生感悟和对人生的无限悲悯。“李妈回头看一看那黑黑的院子,她不想再走进去,可是在她前面的黑黑的小巷子,招引着她更没有方向。”在这里萧红已超越了情爱叙事层面,她用深凝又诗意的目光深入到人的生命意识中,用自己的人生经验来挖掘在大时代背景下女性个体对爱情的认识及其人生的荒凉。
二
《朦胧的期待》是萧红于1938年10月创作的,创作在抗战高潮时期但却避开描写战争的场面和拒绝直接宣泄抗战的情绪,而是从侧面视角对广大劳苦人民给予关注,凝视着在战争中无奈而绝望的女性的命运。萧红的小说在特定的年代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然而她只是把战争处理为大时代背景,这与她缺乏自身经历而无法进行正面战场的描写有一定关系。但她更多的是着眼于战争中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以女性的艺术视角展示动荡时代的民族精神面貌。这样的小说特征,师承鲁迅的“改造国民性”[1]文学观影响。萧红和鲁迅虽是两代人,但是他们都关注民族命运和在旧中国黑暗统治下人民的精神状态。小说主人公李妈承受了情人的离去,承受着在战争的环境下的巨大痛苦和幻灭,与情人的分离让她变得恐慌、焦虑与绝望。这种悲剧的形成来自于严酷的战争,而战争所带来的灾难绝非仅是肉体的摧残,更是对心灵的伤害与折磨。文本中的一段描写“等她拿着纸烟,想起这最末的一句话的时候,她的背脊被凉风拍着,好像浸在凉水里一样,因为她站定了,她停止了,热度离开了她,跳跃和翻腾的情绪离开了她。徘徊,鼓荡着的要破裂的那一刻的人生,只是一刻把其余的人生都带走了。”随着情人金立之的离去,李妈对人生的热情已经消退了,似乎对这样的结局感到麻木,因为这是第二次送心爱的人去战场。虽说严酷的战争给李妈带来了心灵创伤,但是萧红没有把这种伤害演绎成对家国的仇恨。李妈的第一个情人投身红军也没有妨碍她给国民党官员当佣人,这样小说就淡化了战争中的阶级意识和民族属性等政治问题。
同年1月,萧红参加了《七月》杂志社以“抗战以来的文艺活动动态与展望”为主题的座谈会,表达出自己对抗战文学题材的见解,同时也反对战场高于一切的文学主张。有的作家为了迎合战时文化的需要,认为文学必须服从于政治的创作规范。他们要放弃自己的原有创作风格、创作习惯,然而萧红把文学创作作为心灵精神上的抒写,她没有像其他作家一样迎合革命化群体意识的潮流。在党派斗争的问题上,她更愿意做一名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关注同情失败的弱势者。萧红在小说里没有正面表现战争,而是从个体的悲剧命运出发,来展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威胁和伤害,家庭毁灭使得他们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大时代背景下,她站在个人生活的立场抒写自我情感的体验,忠实自己的情感表达,以同情的目光关注战争边缘的女性群体,给予她们深厚的关怀和怜悯。
三
在小说《朦胧的期待》里,金立之豪言壮语:“这次,我们打仗全是为了国家,连长,宁做站死鬼,勿做亡国奴,我们为了妻子,家庭,儿女,我们必须抗战到底。”作为有高昂的抗战斗志的男性对立形象的李妈,她显得极其焦虑和恐慌,金立之有好几次机会可以和李妈有独处的时间,可是他却毫无察觉也没有安慰的话语,毅然决然地上了战场,留下李妈在黑暗中独自等待。萧红把李妈安排在民族抗日的宏大的时代背景下,李妈小小的愿望在“不当亡国奴”的时代氛围下,显得如此渺小。没有人包括她爱的金立之也不会注意到这样一个普通女性的小小的愿望。她渴望与自己爱的人过着幸福、安稳的日子,也期盼着自己爱的人能早日平安归来。在战争年代,女性问题一直被男性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意识遮蔽,实则女性也同样关注着民族、整个国家的生存状态。小说结尾李妈梦见金立之从前线打仗回来,金立之的头发还和从前一样黑,暗示着李妈也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从小说文本和作者创作来看,“九一八”事变爆发使得萧红开始陷入民族危机和女性危机,在她流亡到青岛时亲眼目睹了房东将卖包子的老朱一家子赶出草亭,她看到了战争中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状态。战争使得萧红清楚地认识到人性最丑恶最残酷的那一面。同时期,萧红也体会到感情带给她的痛苦和伤害。实际上,小说里的情感情节与当时和萧军、端木蕻良的两段感情有着微妙的联系。萧军多次想投身革命事业、时刻准备驰骋沙场,而萧红以“爱人”和文学同志者的身份劝阻萧军坚守自己的岗位,适可而止。二人因此产生了激烈的争吵,最终以分手告终。萧红结束与萧军的恋情,与端木蕻良结合,可这也是新的问题的开始。如果说萧军和萧红的关系是类似父女的话,与端木蕻良的关系则像是姐弟。端木蕻良对萧红有着很强的依赖性,久而久之萧红也会感到情感带给她的疲累。再加上当时端木蕻良与萧军有着同样的问题,他们作为男性都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都想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前线支援。1938年7月2日,端木蕻良参加了全国文协,与大公报主编取得联系,想作为大公报特约记者去前线采访,正怀孕的萧红没有了依靠,感受到了些许凄凉。此后,端木蕻良先行去重庆找住处,萧红就去朋友那里,因住宿条件有限,萧红只好在走廊楼梯上铺着席子睡觉。如此艰苦的住宿条件,使得萧红深切地体会到在战争中,女性很难获得真正的幸福,爱情悲剧也必将是她们的结局和宿命。萧红来到重庆曾对接待她的张梅林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东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一个人走路似的……”[2]无论是战争还是男性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怀,都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加剧了女性的苦难。
从五四以来,个性主义、人道主义观念深入人心,在一定程度上受封建思想禁锢的部分女性接受了男女平等、人权的民主思想,一方面她们追求自由、人格的独立,另一方面她们深受男权社会的影响,对男性有潜移默化的依赖。萧红作为一个女人,她本身就是中国女性的矛盾统一体。作为被男权社会不断伤害、放逐的女性,性别是关系萧红生存立足的根本问题。从出生时被歧视、求学时的艰苦抗争和抗婚后的遭放逐,她一直在社会中力图寻求一条女性独立的道路。虽然萧红反对把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追求独立的人格,但她总是把这样的反对和追求建立在获得男性支持和庇护下的。她既努力寻求独立,又把自己视为弱者,需要男性的保护和同情。她把这种对恋人的情感依赖和自身情感命运的悲伤,更多转向作品对人生的探索和追求中。作为作家的她一生都处于漂泊中,在长时间的路途中所发生的人事变迁使得她在痛苦中思考人生、感受生命,从对自我的关注转向对社会民众的关注。李妈的悲伤、宿命和绝望凝聚着萧红本人痛苦的生命经验,具有深远的现实批判意义。
四
萧红笔下的女性都是中国社会最普通的女性,《朦胧的期待》中李妈的爱情悲剧是社会的历史的悲剧。李妈的忧伤和失落已经上升到对人生的深深失望和怀疑,有一种对现实失望的冰寒彻骨的伤感。但李妈对爱情仍还保留一丝希望,她渴望着早日与金立之团圆,渴望能有属于自己的家。萧红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女性情味来诉说着女性在民族战争中的宿命和无法逃脱的苦难。萧红曾感叹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啊,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3]这是萧红对爱的绝望的呼喊,爱情的反复落空使得她吐露出心灵的孤寂。在萧红眼里,中国女性的命运注定是悲惨的,她们无法避免世俗社会强加给她们的肉体苦难和心灵残害。萧红以女性的生命体验与身心感受写出了不同于同时代男性作家笔下女性的生存真相,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 鲍晶.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M].天津:天津出版社,1982:170.
[ 2 ] 梅林.忆萧红[M].黑龙江: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14.
[ 3 ] 章海宁,聂绀弩.在西安[M].黑龙江: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50.
——端木蕻良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