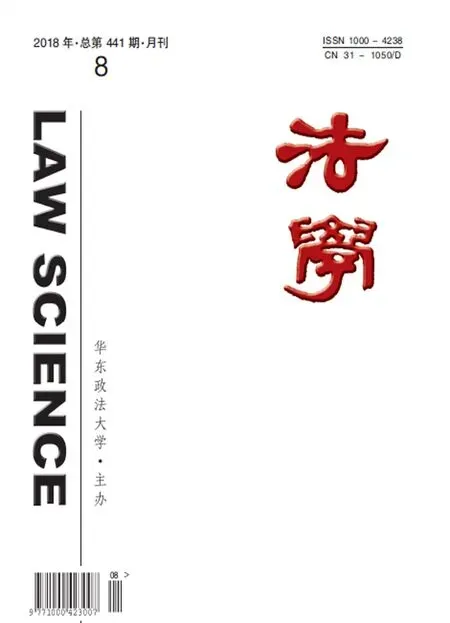大数据的竞争法属性及规制意义
●陈 兵
伴随数字全球化及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已成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深刻影响甚至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格局与方式。依托互联网的平台经济、大数据(big data)、云计算、算法以及进阶后的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业态等已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新的增长点,尤其是大数据已然从互联网经营者的商业技术核心进阶到了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新布局和新战略的顶层设计中。从2015年8月《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发〔2015〕50号)的发布到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都从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提出了我国大数据发展的顶层设计。〔1〕《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指出,大数据已经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新机遇,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可以预见,在大数据及以其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和共享经济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新动力的同时,围绕大数据及其相关的领域也可能会出现诸多问题。申言之,大数据不仅带来了商业竞争格局的改变,而且亦对现有的市场经营行为、商业模式及竞争秩序产生了冲击,加之平台经济对传统竞争法规制思路和框架的挑战,更加剧了大数据对传统竞争法规制理论的颠覆。在此背景下,如何在互联网时代革新竞争法实践进路,竞争法如何回应围绕大数据广泛运用产生的市场竞争问题,正成为摆在学者面前的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亟需作出理论深耕。
一、数据到大数据的法律属性素描
当前,围绕大数据所展开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法学界对大数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界定以及数据相关属性判断的层面,将大数据作为数据的下位概念展开递进式研究,将大数据作为一种独立现象和介质的法律属性的研究成果甚少,而将大数据置于竞争法层面的研究更是阙如。相对于理论研究的滞后,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与大数据相关的竞争法问题或者是纠纷,〔2〕例如,被称为我国“大数据不正当竞争第一案”的“脉脉非法抓取使用新浪微博用户信息案”最终二审法院认定脉脉经营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判决驳回其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法院主要围绕以协同过滤算法为代表的大数据手段是否能够通过计算自动精准匹配脉脉用户手机通讯录中联系人与新浪微博用户信息,认为在较短时间的数据积累下,脉脉用于协同过滤算法的数据原料若在数量、质量方面没有充分可靠的保证,难以计算出准确的用户信息和对应关系,最终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参见张璇:《大数据不正当竞争第一案的烧脑庭审》,《人民法院报》2017年4月10日第6版。)又如,2013年“百度诉360违反robots协议案”、 2016年“大众点评诉百度地图抓取用户点评信息案”、2017年“运满满诉货车帮盗取用户信息案”,以及淘宝屏蔽百度搜索,顺丰与菜鸟有关物流数据接口的争议,新浪与今日头条有关微博内容爬取的争议,华为在Magic手机中利用微信用户聊天记录进行AI服务推荐等。(参见田小军:《AI时代数据之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数据权”?》,https://mp.weixin.qq.com/s/5UijjDGov9pTKNpqLAb2bA,2018年3月4日访问。)相形之下,国外关于大数据于竞争法适用的案例则更多,譬如,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对Facebook 的调查,Microsoft收购LinkedIn,Facebook收购WhatsApp,TomTom 收购TeleAtlas等。2017年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竞争政策研究中心发布了《数据与竞争政策研究报告书》,标志着日本也开始对“数据垄断”行为施以竞争法规制。理论与实践的不相匹配要求法学界必须对大数据与竞争法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应的规范及实施路径作出有效探索,尽快形成体系化、系统化的研究成果和实用性、有效性的智库产品。
客观而言,大数据一词虽广被讨论,但对其具体内涵以及相关概念的特征仍缺乏共识。鉴于此,有必要先对数据、大数据概念及相关概念的特征属性加以阐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申出对大数据竞争法品性认知上存在的不足或盲区,并说明此一状况不利于全面准确地看待和分析大数据在实然与应然层面对市场竞争和竞争法的影响及意义。
(一)数据与大数据的界分
一般认为,数据是对于客观事物的逻辑归纳,是信息的表现载体与形式,是在计算机及网络上流通的在二进制基础上以0和1的组合而表现出来的比特形式。〔3〕参见[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页。数据通常与存储在计算机上的信息相结合,在线商业模式(online business pattern)中的数据通常是指个人数据。〔4〕See Bruno Lasserre, Andreas Mundt, Competition Law and Big Data: The Enforcers’ View, Italian Antitrust Review, (1), 2017,p.88.数据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它依赖载体而存在,即它只能依附于通信设备(包括服务器、终端和移动储存设备等),无上述载体,数据便无法存在(尽管云形式打破了传统数据的存储利用方式,但依然离不开相应的载体存储数据);二是它通过应用代码或程序自然显示出信息,但信息的生成、传输和储存均体现为通过原始的物理数据来完成。〔5〕参见梅夏英:《数据的法律属性及其民法定位》,《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实践中,人们经常将“数据(data)”与“信息(information)”混用,其实信息的外延要大于数据,数据只是信息表达的一种方式,除电子数据外,信息还可以通过传统媒体来表达,〔6〕参见陆小华:《信息财产权——民法视角中的新财富保护模式》,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页。亦即信息因其内容而具有意义,但这些具有特定意义的信息并不仅仅由电子数据来传播,数据作为信息技术媒介只为其首要特征。〔7〕参见化柏林、郑彦宁:《情报转化理论(上)——从数据到信息的转化》,《情报理论与实践》2012年第3期。互联网技术系统打破了传统的信息先于媒介存在的状态,而体现为网络具有通过数据产生信息的功能,如海量储存在cookie〔8〕Cookie指小型文本文件,是包括谷歌在内的部分网站为了辨别用户身份而存储在用户本地终端上的通常经过加密的数据,通常包含了用户名、电脑名、使用的浏览器、曾经访问的网站等敏感信息,极易受到盗窃、投毒等威胁。参见翟巍:《欧盟谷歌反垄断案》,《网络法律评论》2014年第1期。里的网络行为数据即体现为用户的网络行为信息,这种网络行为数据正是大数据的基础形式。〔9〕同前注〔5〕,梅夏英文。
何谓“大数据”,学界对其并无准确定义。国外对大数据的定性虽不统一,但对部分特征已有共识,即大数据不是大量数据的简单叠加,而是具有多个维度,一般可被概括为数量(volume)、速度(velocity)和多样性(variety),〔10〕See Xavier Boutin,Georg Clemens, Def ning “Big Data”in Antitrust,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Chronicle, (2),2017, p.3.甚至包括增加的价值(value-increase)。〔11〕See 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 Debunking the Myths Over Big Data and Antitrust,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Chronicle, (2), 2015, p.2.数量是大数据的最基本要素,单个数据并无过高的价值,称为大数据,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所依托的数据量庞大;速度是指数据生成的速度,还包括处理分析数据的速度,若数据不能被快速处理和分析,便会很快失去价值;多样是指信息数据种类的多样性和数据来源的多样性。〔12〕同前注〔10〕,Xavier Boutin、Georg Clemens文。在早期文献中,对大数据的核心在于预测的认识〔13〕同前注〔3〕,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书,第16页。更多地是从思维方式和商业模式层面来讨论大数据的功能和价值,尚未能系统地归纳出大数据的属性,尤其是其法律属性。现在有部分学者则认为,大数据是一种技术,与供给相关,而非与需求相关。〔14〕同前注〔10〕,Xavier Boutin、Georg Clemens文。我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对大数据的表述是:“大数据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正快速发展为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从中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
目前,大数据尚难以被视为一种类似于消费商品的存在,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定位仍需作进一步厘清。事实上,广义的大数据强调的是思维方式,强调使用大量多样且快速更新的数据来预测相应趋势,寻找各种现象之间的相关性,而狭义的大数据被视为技术,是一种挖掘分析数据的计算机技术,运用云计算、机器学习等计算机手段,对人们在互联网上留存的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再创造的计算机技术。笔者认为,在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阐释大数据的内涵与属性其实更有助于明晰大数据与市场竞争的关系,以及其在竞争法上的意义。
(二)数据的法律属性
大数据以数据为起点,学界对大数据的研究亦以数据为基础展开。目前学界对数据法律属性抑或法律品性的探索主要围绕数据的物权属性、人格权属性以及相应的刑法属性展开,关注的重点在于数据创造者与数据之间的权利归属问题,偏重于私法层面,以及对应的基于对私益的严重危害达致刑事违法程度而课以刑事责任,较少涉及大数据对市场竞争秩序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的分析,更缺乏在竞争法视阈下对大数据法律属性的讨论,以及大数据对促进竞争法革新意义的评价。
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数据型或者基于数据之大数据技术的运用导致的垄断现象,例如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行为、大数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力行为等,现有的竞争法实施理念和行为依据尚不能有效应对源自大数据运用产生的限制、排除竞争行为,也不可能对既存的或潜在的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予以适度且合理的事前规制。如此一来,极容易出现“管与不管”皆尴尬的局面,也容易混淆事前规制与过度规制(over regulation)的界限,也可能引发由于忌惮事前规制的滥用风险而出现规制不足(under regulation)的问题。加之大数据所依托的互联网平台有别于传统单边市场的双边市场特征,使其市场法律规制路径的构建更加复杂。故此,只有先梳理和比较数据在不同部门法视阈下的属性,通过描述其多元特征,才能进一步探讨在数据被大数据技术广泛适用后,衍生出的大数据于竞争法上的属性。
承前所述,数据的法律属性是多维的。关于数据的人格权属性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数据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载体,由此衍生出的公民个人信息权的定位、内涵以及相应救济机制的探索。尽管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明确了个人信息权益的侵权法保护定位,〔1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规定:“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公开自然人基因信息、病历资料、健康检查资料、犯罪记录、家庭住址、私人活动等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下列情形除外:(一)经自然人书面同意且在约定范围内公开;(二)为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且在必要范围内;(三)学校、科研机构等基于公共利益为学术研究或者统计的目的,经自然人书面同意,且公开的方式不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四)自然人自行在网络上公开的信息或者其他已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五)以合法渠道获取的个人信息;(六)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方式公开前款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个人信息,或者公开该信息侵害权利人值得保护的重大利益,权利人请求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国家机关行使职权公开个人信息的,不适用本条规定。”但在学理上,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法律属性及范畴始终界定不一。〔16〕对公民个人信息权的属性界定一般有宪法人权说、一般人格权说、隐私权说、财产权利说、新型权利说、独立人格权说,司法实务中,各级法院一般将个人信息权视为隐私权,在涉及他人社会评价时视为名誉权。参见张里安、韩旭至:《大数据时代下个人信息权的私法属性》,《法学论坛》2016年第3期。而在大数据时代下,不断扩充的公民个人信息已难以通过列举式实现全覆盖,加之公民较以往更加注重保护个人信息,〔17〕2013 年大规模开房记录泄露事件引起了人们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广泛关注,个人信息的内涵也由过去仅包括“身份证、电话、住址、家庭情况”等多属于个人隐私内容,到现在个人的信用评价、网页浏览记录、购买记录、消费信息、行程信息等,个人信息已成为一种兼具隐私属性和财产属性的权益。多重因素叠加下的个人信息若仍单纯地将其归为现有权利体系中的某一类已不能适应或符合时代之要求。〔18〕目前,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民法学者认为,个人信息权是一种独立人格权,张里安教授亦认为,纵观个人信息权属性的六大学说,唯有独立人格权符合个人信息权的内在属性,能够涵盖个人信息权的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属性,因此,个人信息权在法律属性上应视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参见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现代法学》2013年第4期;同前注〔16〕,张里安、韩旭至文。更关键的是,当前我国的权利救济体系尚未搭建起来,更多地是以侵害隐私权和名誉权为由请求侵权损害赔偿,缺乏单独以公民个人信息权受侵害为由主张侵权损害赔偿的机制。面对大数据时代下个人信息内涵的不断扩容,尽快确立作为独立人格权的个人信息权的存在,对各类个人信息实施在收集、处理、加工、存储、流转、交易上的全方面保障,是保护个人人格的必然要求。〔19〕同前注〔16〕,张里安、韩旭至文。
关于数据的物权属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数据是否具有传统民法的客体性和财产性。数据具有非特定性,且缺乏独立性,导致其难以与“物”类似作为民法的客体,但也有学者和司法裁判者力图在传统民法体系中为数据增加一席之地,以求理论与体系的完整。〔20〕只能通过控制服务器、手机、硬盘等固定载体的方式控制数据,不能与载体分离。同前注〔5〕,梅夏英文。同样,对于数据的财产性也是争议颇多,有学者认为,数据因其非客体性,不具有独立的经济价值,而不具财产性,〔21〕同前注〔5〕,梅夏英文。但是,随着以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为代表的数据交易市场的开启,可以预见,相关争议可能会成为过往,抑或会变得更加激烈,也就是说,数据的经济性是否可以证成其财产性仍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论证。
至于数据在私法领域的属性映射到刑法范畴,则主要聚焦在受刑法保护的公民信息的内涵范围该如何确定上。〔22〕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修正案(九)》扩大了该罪的适用范围。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成为定罪量刑的关键,是仅包括“身份证、电话、住址、家庭情况”等多属于个人隐私的内容,还是应当包括个人的信用评价、网页浏览记录、购买记录、消费信息、个人爱好等内容,大数据使得隐私与非隐私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而且大数据的技术特点使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显得更加隐蔽、复杂且难被发现。比如,百度旗下APP被曝监听用户电话,百度回应并无能力监听用户电话,也不会监听用户电话,刑法如何去规制如上类似行为,均构成大数据刑法意义上展开的重要话题。参见《两款手机APP被指监听用户电话,百度:没能力、不监听》,http://www.chinanews.com/sh/2018/01-08/8419113.shtml,2018年1月8日访问。尤其是针对通过大数据技术对看似简单无用的使用记录等数据分析出公民更多隐私信息的特点,如何界定公民隐私信息范围以及如何识别互联网环境下危害公民隐私信息的行为及其严重危害性等问题都因互联网环境而变得复杂且难以回答。
(三)数据法律属性的扩围
数据尤其是在数据依托计算机技术发展成为大数据后,已在诸多部门法上引起了激烈讨论。但是,前文对数据各个面向上法律属性的梳理与分析并不能阐明大数据在影响市场竞争秩序及消费者福利中所展现出的竞争法品性。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部门法的范畴和特征决定了其在观察维度和解释路径上的差异。大数据在当前市场经济运行中所展现出的正向和逆向激励已不能仅将其单纯地作为数据概念的下位概念来看待,在此前提下,对大数据所涵盖的法律属性进行独立讨论与深入研究成为必要。如果不能对大数据本身的法律属性进行阐释,那么围绕大数据所展开的一系列法律适用探索将会发生混乱。对竞争法而言,只有明确了大数据自身的竞争法品性,才能有助于围绕大数据展开一系列竞争法规制路径的探索。例如,大数据影响下的用户为获取相应服务而支付的数据“对价”〔23〕当用户注册使用互联网应用时需要同意《使用条款和隐私政策条款》,其中就包括应用开发商可以收集使用相关用户非隐私数据,此种授权可以视为用户获取免费服务所提供的“对价”。当然收集数据的方式并不只是通过应用渠道收集,还可通过网络爬虫获取用户浏览网页的记录等方式,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日臻成熟,数据收集方式将会更加的多样。是否公平,以及“对价”的质量能否得到保证,即质量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相对下降,或在质量无法得到保证时,基于数据的不可携带性或转移成本过高而引发对用户公平交易与自由选择的不公正限制,或是出现基于滥用大数据优势力扭曲或破坏市场公平自由竞争秩序的现象等问题,都需要更多地得到竞争法理念和技术的关照。
基于此,为了厘清基于数据而发展起来的大数据在竞争法上的意义,就需要先行分析大数据于市场竞争在正向与逆向激励上的显现状态及其行为逻辑,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探讨大数据在竞争法上的属性及对竞争法革新的价值,由此得出大数据之于竞争法的现实意义。
二、大数据于竞争法上的意义
(一)大数据对市场竞争的正向激励价值
大数据之于市场竞争的功能体现在多个方面,以微软(Microsoft)并购领英(LinkedIn)、Facebook收购WhatsApp、TomTom 收购TeleAtlas等为代表的跨市场经营者兼并案,集中展现了大数据强大的市场反馈预测循环加强效应和链接传导功能。具言之,相关商品市场的经营者在海量用户数据的支持下,积极推进现有产品服务的更新换代,促使了相关技术的进一步升级,加剧了市场竞争的程度,使得跨市场的融合导致了相关市场的竞争更加复杂多样。而且,在不相关市场〔24〕“不相关市场”是相对于“相关市场”而言的一个概念,传统竞争法根据损害理论界定相关市场,以相关性理论为基础,强调围绕受诉行为确定相关的市场,不相关市场恰好则是与受诉具体行为无关的市场,或者不具有显著相关性的市场,该市场与受诉行为缺乏相关性,与相关市场概念范围相对立。参见兰磊:《〈反垄断法〉上的“不相关”市场界定》,《中外法学》2017年第6期。上,经营者在兼并过程中所展现的链接传导功能同样对市场竞争产生了正向激励结果,推动了相关市场内的经营者通过多途径的寻求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促使了整个市场的自由竞争度得到极大提升。
1.大数据的市场反馈预测价值
以“微软(Microsoft)并购领英(LinkedIn)案”为例延伸展开的一系列产品(销售)经营者兼并社交软件案,〔25〕Case M.8124 – Microsoft / LinkedIn.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MERGER PROCEDURE.甚至可延伸到产品(制造)经营者兼并互联网平台的相关案例,都显示出一个共同的特点——两个不处于同一相关市场的经营者选择合并,凸显出与传统竞争市场兼(合)并的不同。在传统竞争法视阈下,对市场竞争秩序的评价通常聚焦于某一相关市场,并以相关市场界定为前提和基础。〔26〕参见王先林:《论反垄断法实施中的相关市场界定》,《法律科学》2008年第1期。然而,随着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发展,相关市场及其界定作为竞争规则中核心的基础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尤其是在经营者集中审查案件中“不相关市场”和“未来市场”〔27〕“未来市场”概念的提出较早出现在对数字型驱动合并审查案件之中,既是一个客观的时空概念,也是一个主观上用来表达对创新研发的对象未予清晰识别的认知概念,即在对基于平台性和网络性为特征的经营者合并或者合作中所涉及的产品无法归类为某种现有商品及其相关市场的一种描述,对于这类市场,包括时间上、地理上、商品或服务上的无法用现有相关市场概念予以解释。在未来市场上,可能出现相关的创新成果延迟产生或者根本就不再产生的情况,也可能存在在未来的某一时空内基于现在无法界说的表达,而出现新产品并影响市场的自由竞争。进一步的论述,可参见龙睿、李丽:《德国2017年〈创新:反垄断审查实践的新挑战〉调研报告摘要》,http://mp.weixin.qq.com/s/ERxdfeFeZVHuyE9kzSNudw,2018年3月26日访问。概念开始受到各界关注。其中,大数据作为技术和资源被广泛运用于市场,在为“不相关市场”和“未来市场”的竞争提供支持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在“微软(Microsoft)并购领英(LinkedIn)案”中,微软并购领英的动议及决策的作出与领英拥有丰富成熟的大数据资源关系密切,此举可视为是微软基于大数据强大的市场反馈和预测功能加强了对“不相关市场”和“未来市场”上竞争优势的争夺与整合。申言之,在大数据技术和资源的支持下,数据使用者从以往只能收集使用很少数据,到可以收集分析数以百兆或千兆计的数据量,并在高效能的数据分析处理能力的支持下,使得数据的价值飙升。过去缺乏能将需求反映到软件上的技术,而计算机算法的发展使得人类的现实需求能够更完整地反映到技术层面,配合持续的大数据反馈支撑,使得算法不断得到优化,更加贴合人类的使用需求,甚至引导使用者尝试新的体验产品。使用者在使用各种软件时会产生各种数据流,同时会不断探索软件的使用边界,并希望自身的需求能够反映在计算机技术上。作为经营者的微软通过借助大数据技术不断收集、分析这些数据,进一步优化其产品内容和体验服务;使用者与经营者则通过数据反馈预测功能开展对产品改进的互动。而大数据将这一反馈预测机制的作用加速放大,成为微软并购领英行动的一个重要支持。
2.大数据的市场链接价值
仍以“微软(Microsoft)并购领英案(LinkedIn)”为例作观察,微软的主要经营领域和主要产品及服务要想在互联网产业深度发展的今天继续保持其行业优势地位,就必须要不断优化既有产品,研发创造新产品,这些皆需依托对大量用户使用数据的研究与分析。于是,其经营者将目光转移到寻找大量用户的数据流上,而拥有大量数据流的社交软件的代表领英进入其视野。微软通过并购领英便可获取领英拥有的大量的用户数据流,而互联网平台型市场具有的用户粘性和锁定效应(即社交平台的转换成本较高〔28〕See Justus Haucap, Ulrich Heimeshof f, Google, Facebook, Amazon,eBay: Is the Internet Driving Competition or Market Monopolization? DICE Discussion Paper, No. 83, 2013, p.7.——用户的社交生活以社交软件为依托),使得用户难以在短时间内转向使用其他社交软件,〔29〕社交软件市场具有明显的使用惯性,一旦绝大多数人开始并习惯使用同一社交软件,只会导致更多人使用该软件,且产生使用惯性,短时间内难以转向其他平台。如此一来,微软便能持续、稳定且有效地获取大量用户的使用数据,这无疑为其进一步巩固在计算机软件市场的优势地位奠定了大数据设施基础。
微软与领英两公司本无经营业务交集,前者主打职场办公软件,后者是职场社交平台,但是两者的目标受众(都专注职场)具有相似性和融合性。通过大数据技术抓取领英用户的海量数据,可形成有效的市场反馈信息,再辅以云计算和数据的自主学习技术对使用者所需信息的分析、挖掘和预测,在更新优化原有产品的基础上,研发出新产品及服务,确保其在计算机系统及软件开发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在此过程中,作为互联网技术和资源的大数据将原本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的市场联系起来,成为原有产品市场上经营者附加的竞争优势,此时在原有的产品市场上,看似微软并没有兼并直接的竞争对手,也不存在明显的算法技术优势,但其背后依托领英平台亿级用户数据流的支持,通过大数据优化现有算法更好地收集和分析了数据,从而实现了自我优化和创新,凸显出“雪球效应”价值,〔30〕See Bruno Lasserre, Andreas Mundt, Competition Law and Big Data: The Enforcers’ View, Italian Antitrust Review, (1), 2017,p.91 .同时,在看似公平自由的产品市场上,微软已经建立起了巨大的技术优势和数据资源来进一步巩固其对用户的吸附力。虽然人们对于互联网创业低门槛这一误区始终坚信不疑,〔31〕See 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 Debunking the Myths Over Big Data and Antitrust.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Chronicle, (2), 2015, p.7.但“雪球效应”积累的巨大技术优势已远远甩开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并令准备进入的新经营者望而生畏,从客观上设置了难以跨越的新型市场壁垒。进一步言,虽然仍有不少的新进互联网初创经营者,但是这些经营者几乎最终都会被现存的互联网巨头所兼并。〔32〕See Johannes Laitenberger, EU Competition Law in Innovation and Digital Markets: Fairness and the Consumer Welfare Perspective, European Commission, Oct.10, 2017.虽然在互联网产业中高新技术引领创新,创造了巨大的竞争机会和竞争潜能,但在很大程度上用户资源才是决定价值的核心因素。在现存互联网经营者庞大的用户数据的支持下,初创公司虽然在初期通过创新可一时占得市场先机,但最终仍需要借助庞大的用户数据的支持才能获得发展,所以说,被拥有大量数据流的经营者收购就是这些经营者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终极选择。不可否认,大数据作为附加的竞争优势已对原有市场的竞争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大数据对市场竞争的逆向激励风险
承前所述,大数据之于市场竞争的功能展现是多维度的,在对经营者参与市场竞争起到正向激励作用的同时,亦给市场竞争利益及相关利益埋下了潜在风险,其中由大数据垄断引发的个人隐私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了广大用户和监管当局的关注。〔33〕关于消费者隐私安全保护是否应纳入竞争法框架,学界争议颇多,支持者认为,将消费者隐私安全视为非价格竞争维度,可以纳入竞争法执法框架;反对者则认为,消费者隐私保护有更加专门的法律保护、隐私保护难以量化,不适合纳入竞争法框架。但是,该问题已经引起了各国竞争法执法机构的重视。参见韩伟:《数据驱动型并购的反垄断审查——以欧盟微软收购领英案为例》,载王先林主编:《竞争法律与政策评论》第3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68~169页。大数据技术的逐步提升和广泛使用使得占据数据优势的经营者越来越强,进一步强化了“赢者通吃”的互联网市场竞争格局,导致独寡占市场结构的加速形成,而这很可能造成现存免费服务质量的相对下降,以及数据源封锁对相关市场内其他经营者的不利影响,并为市场潜在的进入者设置了不正当的进入壁垒。而且,大数据强大的预测功能会让现有的市场支配地位者伺机消灭市场新进竞争者所可能带来的投机性威胁,大数据对市场竞争的逆向激励会对市场竞争秩序及参与主体的正当利益产生严重损害。是故,有必要对大数据于市场竞争的逆向激励作用作出系统分析,并就由此引出的大数据市场的垄断问题展开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1.潜在的损害用户数据安全的风险
通常观点认为,个人隐私安全主要由侵权法保护,受竞争法的影响较小,甚至与竞争法无涉。当恶意使用他人的个人信息时,被侵害人往往诉诸民事法律来解决隐私保护问题,严重者甚至借助于刑事法律的保护。然而,随着互联网发展向大数据阶段的深度推进,数据驱动的商业战略和行为有时会引发隐私安全与竞争法适用的关联问题。数据驱动的合并,如Facebook收购WhatsApp,可能会减少提供给消费者的隐私安全保护上的非价格竞争。〔34〕同前注〔31〕,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文 , 第 5 页。
传统竞争法关注的重点是市场上自由公平竞争秩序的维护与消费者公平交易资格和自由选择机会的实现,在该维度上,隐私安全并不在竞争法适用的视阈之下。但是,通过仔细推演传统的消费者隐私安全法律保护逻辑展开的前提及实际发生的环境不难发现,传统市场上的消费者通常不会授权经营者采集其个人信息,即便是在某些交易服务环节提供了一些基本信息,如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邮箱、通讯地址等表面信息,但这种提交呈现为一次性,也就是说,信息不存在持续性更新,不存在对消费者行动轨迹(数据)的不间断记录,也不会使用大数据技术对消费者数据进行高效能分析和衍生利用。此际,当传统市场上的经营者侵犯消费者隐私安全时,通常较易锁定侵害主体及其行为,透射出的法律关系也较为明确,一般通过请求侵权损害赔偿即可实现权利救济,这些皆与竞争法实施无涉。
然而,大数据环境下的平台经营者获取数据是建立在消费者授权基础上的,是其为消费者提供基础性免费服务的对价。对于该对价的性质目前法律上尚未予以明确,仅是作为使用条款存在,未与平台提供的基础性免费服务构成对价关系,这无疑给平台场域下消费者隐私安全法律保护的实现设置了障碍。因为对价关系的缺失,所以很难认定为消费损害。具言之,当消费者授权平台经营者收集其个人数据后,消费者的每一次使用都会在平台上留下数据记录,这既给经营者掌握消费者的行动轨迹提供了充分机会,也让经营者使用消费者个人数据有了正当理由,正可谓“一次授权,始终有效”。在此基础上,平台经营者借助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机器学习自主挖掘数据,可进一步锁定消费者的更多信息(隐私),此际,一旦发生信息泄露或滥用事件,由此造成的危害往往难以评估。可以预见,可信又可靠的隐私安全服务将成为平台经营者未来参与市场竞争的一个重要的非价格因素,必须给予高度重视。事实上,一旦平台经营者的数据垄断地位形成,其很可能妨碍消费者在同等条件下选择更优质隐私安全服务权利的实现,阻碍消费者获得更多隐私安全保护上的选择,〔35〕同上注,第5页。这一结论完全可以从互联网平台用户锁定效应中推演出来。基于用户锁定效应,平台经营者一旦建立起市场垄断,即便有新经营者提供了更多隐私安全保护方面的选择,但因其市场力弱小,数据获取方面常常会受制于数据垄断者,最终会随垄断者的持续限制而消失,这实质上妨碍了消费者自由选择权的实现,属于明显的市场竞争逆向激励后果。
事实上,大数据技术能够做到量化传统数据收集技术所无法收集的一切事物,将现象转化为可制表分析的量化形式,尽量将一切予以数字化。〔36〕同前注〔3〕,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书,第98~126页。通过收集、分析各种用户在互联网上的留存信息,可归纳总结出用户的习惯偏好、行动轨迹等专属于用户个人的隐私数据,通过对隐私数据与非隐私数据界限的模糊处理,对用户隐私数据范围界定造成冲击。现有的隐私权保护范畴已无法明确涵盖大数据视阈下消费者数据利益范围的变化,以消费者数据安全保护扩容其范围,才更能体现出大数据时代竞争法实施与消费者利益保护协同发展的现实需求。以欧盟处理的Google收购DoubleClick案(以下简称“谷歌案”)为例,谷歌建立的用户数据库不仅包括了用户的IP地址,还包括了小型文本文件(cookie),而该种文件极易受到盗窃、计算机病毒等威胁。〔37〕同前注〔8〕,翟巍文。由于缺乏针对该数据库安全的外部措施,目前只能依靠经营者自身不断优化数据安全保护措施来提供一定的保障。“谷歌案”涉及的消费者数据安全问题是众多异议者反对Google收购DoubleClick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竞争当局并未就这一点否定该项收购,〔38〕See Statement of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Concerning Google/DoubleClick, FTC File No. 071-0170.但是消费者数据安全已经成为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审查中必须要考察的因素之一。调查显示,美国有不少的消费者担忧自身的数据安全,他们不知道谁有权访问他们的个人数据,以及经营者正在使用哪些数据,数据如何以及何时被使用等。〔39〕同前注〔31〕,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文,第 10页。又如,因Facebook滥用个人数据,德国反垄断当局考虑对其进行处罚。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局长认为,该机构对Facebook收集和使用个人数据的方式感到担忧,认为Facebook可能滥用了自己的市场力。〔40〕参见《德国反垄断当局考虑处罚Facebook因滥用个人信息》,http://tech.sina.com.cn/i/2018-01-03/doc-ifyqcwaq7288980.shtml?dv=2,1&source=cj,2018年1月3日访问。目前Facebook因泄露用户数据遭遇严重的信任危机,股价大幅下跌,并且面临多项潜在指控与调查。实际上,销售数据本身就是Facebook的商业模式,该公司的业务之一就是向第三方出售用户的各种数据。Facebook在用户数据市场上的优势地位给数据安全带来了极大隐患,存在着滥用数据及其市场力的可能。参见《德国等多国要求调查Facebook》,http://mp.weixin.qq.com/s/hfBfxcqQtXyryXHBTJOkRQ,2018年3月28日访问。
2. 存在设置过高进入壁垒损害潜在竞争者利益的风险
大数据于市场竞争的优势在于预测,当经营者(尤其是那些已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利用大数据资源与技术进行市场竞争预测时,通常会先于其他竞争者和竞争规制者发现影响其市场地位的未来挑战和潜在竞争者。申言之,在市场竞争中大数据的使用就好像经营者发明(或改进)了一个雷达系统以追踪竞争威胁,使之可在监管机构和其他机构发现竞争妨碍威胁之前便能够拦截或者击退威胁。〔41〕同前注〔31〕,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文,第 8页。也就是说,由于经营者与竞争规制者所处的立场不同,即便是竞争规制机构可以或者已经发现未来的竞争者构成潜在的(指投机性的)威胁,却苦于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市场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可能因此受到损害,故而也就无法提前规制现在看来不具有危害竞争秩序但未来可能存在极大竞争损害的行为。与竞争规制机构不同,经营者(特别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并不担心“提前击落或拦截可能影响其竞争地位的竞争者会给现行市场竞争的整体福利产生的不利影响。它只管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拦截或击毁他们。”〔42〕同上注,第8页。客观上言,对潜在或未来的市场进入者来说,大数据资源与技术已为它们进入相关市场设置了很高的隐形的进入壁垒。现行市场上占据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完全可以利用大数据资源与技术预测消灭潜在的或未来的威胁,这具体表现为以大数据资源和技术迫使新进入市场者接受不正当的交易条件,通过“雪球效应”在产品市场一侧建立起优势地位,阻碍潜在的或未来的竞争者自由公平地进入市场。于此情形,在当前竞争法规制理念和框架之下,竞争规制机构尚难以依法有效地介入相关的调查与审查,由此放任了对未来市场上自由公平竞争秩序的预期损害行为的发生。
实践中,经营者(尤其是已在平台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经营者)通过集中拥有大数据资源和技术的其他经营者,会给其他经营者带来难以预估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在涉及大数据市场上的经营者的集中交易都会产生竞争力聚集和竞争力传导效应,客观上较传统领域的经营者集中更易增高市场进入的壁垒,尤其是在以平台大数据为核心竞争力的经济领域更是如此。以互联网应用的开发与经营为例,由于开发十分依赖于平台的大数据优势,所以在其成功运行后反过来会支撑和巩固平台大数据的优势地位。然而,现实世界中的互联网应用的开发者与大数据平台的拥有者并不总相匹配,为了获取大量的数据流,其常会通过不正当的爬虫协议来抓取大量数据。〔43〕参见张平:《〈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及其适用——搜索引擎爬虫协议引发的思考》,《法律适用》2013年第3期。与此同时,由于开发需求不同,其他应用开发者二次加工的数据不具有替代性,应用开发者难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取大量的原始数据源,很大程度上只能转向专门从事原始数据收集的经营者寻求数据交易。在拥有大数据资源和技术的经营者尚未与市场上某一竞争者合并时,众多经营者可通过竞价的方式获取相应的数据,此时的交易机会对每个经营者而言都是平等的;一旦该经营者选择与某一竞争者合并,就容易出现所谓的大数据领域的核心基础设施使用问题,该经营者就有可能妨碍其他经营者获取相关的大数据资源,这无疑为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设置了畸高的进入壁垒。〔44〕美国西东大学法学院(Seton Hall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的讲席教授爱德华S.亨德里克森(Edward S. Hendrickson)也持相似的观点。See Marina Lao, Erring on the Side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 When in Doubt in Data-Driven Mergers, Douglas H. Ginsburg,An Antitrust Professor on the Bench- Liber Amicorum, Vol. I, Institute of Competition Law, (N. Charbit et al., eds., 2018), pp.497-530,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147223#, last visit on Apirl 6, 2018.尽管在形式上其他经营者也可以向这些拥有大数据资源的经营者申请API端口,但是在定价及运营模式上均无法做到真正的公平公正,因为此时其他的经营者尚欠缺谈判的筹码和实质上的对抗力,凸显出数据源的闭锁效应。数据源闭锁效应在“微软(Microsoft)并购领英(LinkedIn)案”中一度受到欧盟委员会的高度重视,在若干市场的竞争评估中欧盟委员会深入考虑了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数据收集的范围和规模要求以及数据的可替代性等问题。〔45〕同前注〔33〕,韩伟文,第 167 页。可见,数据源闭锁对市场上其他经营者而言具有十分危险和难以识别的潜在的反竞争限制。
三、大数据应具有竞争法属性
竞争法的核心在于保护市场自由竞争秩序和维护消费者利益。〔46〕有关自由竞争秩序与消费者利益作为竞争法实施的独立价值目标的论述,可参见陈兵:《反垄断法实施与消费者保护的协同发展》,《法学》2013年第9期。即消费者利益的保护非竞争法实施的反射利益,而是其实施的直接利益。竞争法视阈下的竞争是指经营者之间在商品经济活动中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而进行较量的行为,〔47〕参见杨紫烜:《国家协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9页。是在法治框架下对交易机会和资源的自由公平的争夺。虽然市场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经济效率,但是市场本身并不具有维持自由公平竞争秩序的能力和责任,故此,垄断及不正当竞争行为会伴随市场经济竞争的高度发展而不断涌现,这是市场经济无度展开的客观后果。
对垄断与不正当竞争的规制需要借助法律之手,竞争法即是规范市场自由公平竞争秩序的基本法律制度,该法是调整在规制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48〕同前注〔47〕,杨紫烜书,第220页。我国的竞争法以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为核心,其中反垄断法的核心在于保护自由竞争秩序,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核心侧重于保护公平竞争秩序。〔49〕参见王晓晔:《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宗旨》,《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综合两法之核心,竞争法的核心则在于保护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承前所述,大数据作为一种计算机技术和数据资源,是通过对海量用户行为轨迹的记录和快速分析来体现数据的多样性和增加值,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形式上与带有明显利益偏好的各类竞争行为截然有别,从严格意义上说,其是否能直接适用竞争法的正当性与妥适性尚不明晰。然而,基于大数据运行中对数据收集和算法的设计及使用,使得单纯的数据分析技术的运用正面临着价值层面的拷问,譬如,最近发生的Facebook滥用数据市场优势力事件透射出大数据的中立性在互联网经济的激烈竞争中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在前面分析了大数据对市场竞争秩序的各项激励功能后,大数据对于市场竞争活动的影响远比预期得要复杂,可能产生现行竞争法无法回应且难以恢复的不可逆反的竞争效果。是故,在以互联网为核心和平台构建经济生态已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下,竞争法理应对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主导的新经济作出积极回应,扩展和延伸竞争法的规制范畴和规制逻辑。
虽然大数据作为一种计算机技术和数据资源已被人们所广泛认可,并且认为对其的使用是技术革新的一种表现,有着巨大的创新潜能和市场价值,原则上应予鼓励和支持,但是若大数据的选择性甚至歧视性使用对广大用户和其他经营者产生了交易压迫,就会构成一个基于优势滥用而出现的妨碍自由公平交易之情势,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妨碍将长期存在并有逐渐强化之势。当很难甚至是穷尽前文所言的私法救济皆无力改观时,我们就应该考虑从竞争法维度对大数据市场结构及其运行过程予以规制。譬如,伴随大数据的普遍运用所带来的对整体产品或服务质量的把控极易形成“雪球效应”,逐渐显现为对竞争对手尤其是未来可能出现的潜在竞争者的压制,无限制地收集数据对个人数据安全的威胁甚至是操控,对用户服务质量的相对下降等,都已无法依靠单纯的私法逻辑予以解决,引入以第三方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实现为基本价值范式的市场竞争法制度及实践模式来进一步规范成为必然。〔50〕有关竞争法,尤其是反垄断法的基本价值诉求及其表达的论述,参见陈兵:《我国〈反垄断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适用问题辨识》,《法学》2011年第1期;同前注〔46〕,陈兵文。
此外,大数据作为计算机技术与数据资源共同支撑了当下互联网竞争中凸显商业价值的算法设计与算力评价。算法与算力在现实商业活动中已构成了经营者所掌握的一种商业秘密和竞争能力,而其他经营者通过对前述经营者所拥有的大量数据的爬取,甚至恶意窃取,已然实在地影响到了被侵害者的市场竞争基础,不正当地攻击了经营者的竞争能力,存在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之可能。事实上,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偷取和破坏数据和大数据被认定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并受到竞争法处罚的案件,〔51〕同前注〔43〕,张平文;同前注〔2〕,张璇文。说明竞争法已经扩展了现行竞争法规制的基本范畴,较竞争法理论已经有了实然的发展,也进一步拓展了对民法和刑法视阈下的大数据属性的辨识。
通常,我们对某一对象法律属性的判定,主要是从该对象是否具有该类法律之一般意义、是否符合该类法律之主要特征入手。具体到对大数据之竞争法属性的辨识,主要应该考察大数据是否具有经营者所从事市场竞争行为之特征,即关注大数据作为一种技术和资源,在互联网经济下其技术的中立性和客观性、资源的公开性与开放性是否已转变或正在转变为一种具有价值偏好的竞争力要素,且作为技术和资源的大数据的使用是否已然构成了经营者市场竞争行为的组成部分。诚如全球研究大数据和竞争政策的著名专家莫里斯和艾伦所言,数据寡头或数据垄断(data-opoly)本身并不违反反托拉斯法,但是如果数据寡头为了获得或维持其垄断地位,实施了排除其他经营者获取该大数据的行为——该获取行为构成了与数据寡头展开有效竞争的必要条件——那么该排除行为就可能违反反托拉斯法。〔52〕See 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 Big Data and Competition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277.其实,作为互联网进阶时代一个不争的事实,大数据已经成为了从事互联网经济的广大经营者——不论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抑或与之可能产生竞争关系的其他经营者——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竞争力。大数据作为技术与资源的集合,理应归入竞争法规制的范畴,并由此前展竞争法规制的基本逻辑。
不可否认,当围绕互联网构建经济运行新生态已是当下主流认知的背景下,以技术中立和资源开放审视大数据运用而不加干预的观念已经落后于实然。犹如前文对大数据于市场竞争的正向和逆向激励的分析所示,大数据已经对市场竞争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消费者利益的威胁亦始终存在,如果放任其对现实竞争利益与消费者利益的影响,着实有悖于竞争法制定与实施的基本价值目标。所以说,将大数据纳入竞争法视阈予以调整不仅符合大数据的基本特征,而且满足竞争法运行的现实价值,总体而言,大数据应该具有竞争法属性,并受到竞争法规制。
四、大数据对竞争法实施的挑战与机遇
在肯定大数据具有竞争法属性的基本判断后,接着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大数据如何影响竞争法的实施,换言之,大数据对竞争法的实施究竟带来了哪些现实挑战,与此同时亦可能基于大数据技术和资源广泛应用于法治生活而给竞争法实施带来了一定机遇,即大数据该如何促进竞争法实施的整体化系统革新?
(一)大数据对竞争法的规制理念提出了挑战,促进了竞争法规制逻辑的调整
如前所述,大数据强大的市场反馈与预测功能能够让拥有大数据优势的经营者伺机消灭投机性威胁,压制“不相关市场”和“未来市场”上出现的竞争对手,通过传导大数据优势力和巩固相关市场优势地位来实现对“不相关市场”和“未来市场”的延伸,让其竞争优势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得以建立并维持,由此形成“雪球效应”。
事实上,当大数据被广泛运用于市场竞争之际,传统竞争法注重事中、事后规制相结合的理念已经受到了挑战。申言之,被视为投机性威胁的新进入或潜在进入的市场经营者原本可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成长为保持市场一定时空范围内自由竞争度的重要力量,但因大数据技术和资源被已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经营者广泛使用和集中掌控,导致越来越多的市场新进入者或潜在进入者选择依附于现有市场上的寡头经营者,主要为那些具有大数据优势的平台经营者接力顺势进入相关或不相关市场,让原本就缺乏有效竞争力的互联网市场更加缺乏新鲜血液与活力。此正所谓大数据时代“挟用户以令天下”,超级平台正在上演“顺者昌,逆者亡”的“赢者通吃”传奇,只有靠近甚至进入占据大数据优势的平台经营者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53〕譬如,2018年4月2日,阿里巴巴集团、蚂蚁金服集团与饿了么联合宣布,阿里巴巴已经签订收购协议,将联合蚂蚁金服以95亿美元对饿了么完成全资收购。阿里巴巴新零售战略在向本地生活服务的纵深拓展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此次收购将为本地生活服务市场带来何种变量,阿里巴巴将如何应用自身的新零售全生态资源为饿了么加持,饿了么将在阿里巴巴新零售体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都是下阶段市场关注的焦点。(参见《加入阿里,饿了么的融入与“升维”》,http://tech.ifeng.com/a/20180402/44927387_0.shtml,2018年4月2日访问。)又如,2018年4月3日,美团全资收购摩拜再次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互联网科技巨头整合力量进军新零售业的期待和担忧。(参见《昨夜,摩拜“卖身”美团,CEO的最后感言意味深长》,http://www.sohu.com/a/227264134_617374,2018年4月4日访问。)可以预见,未来本地生活服务类市场上将会不断上演各大互联网科技巨头之间,主要表现为对各类生活服务类大数据技术与资源的抢占和跨界平台设施的链接共享下的混合竞争,资源会进一步向优势企业集中,滥用大数据优势的风险正在逐步逼近。然而,在业界主要是互联网经济和科技业界高度评价和期待这类并购交易的同时,却鲜有人关注此次并购将会对生活服务市场上的大数据资源整合和使用产生何种实质影响,由此进一步将会对未来各类生活服务市场上的竞争产生何种影响。两大平台所拥有的大数据技术与资源的融合与升级影响的不只是生活服务市场上的竞争,更涉及会对零售业市场竞争带来怎样的变革,会不会出现滥用大数据优势排除、限制其他零售业者从事自由公平竞争的可能等问题,而这些都需要从竞争法角度予以考察。针对这一现实,传统竞争法的规制理念及其行为模式已无法及时回应上述所言及的潜在的风险,只能在危害结果发生之后施以救济,更甚者,这种事后救济也可能无力改变已经完成的市场结构和商业模式。
若将大数据对竞争法规制理念的挑战置于整个互联网时代下互联网科技对法治理论与实践带来的根本性挑战与如何回应的维度观察,其实质上就是对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引发的各类科技风险应该适用何种法治原则和分析方法的拷问。当前成本效益论和预防原则是两种主流的辨识标准,且两者间存在明显的对立。支持成本效益论者认为,预防原则不仅付出的代价过高因而昂贵,而且不具事实可行性。但也有学者认为,由于成本效益分析的反事实论证属性、无法回应价值通约的问题以及科技风险的人为属性,所以预防原则应成为政府以法律手段因应科技风险的主要原则。〔54〕参见陈景辉:《捍卫预防原则:科技风险的法律姿态》,《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由是可见,如果将理论聚焦到竞争法对大数据所引发的规制风险的回应上,那么可以认为传统的事中、事后规制,尤其是事后规制方式则属于典型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而此处所主张的基于大数据的强大市场反馈与预测功能能够让拥有大数据优势的经营者伺机消灭投机性威胁的现实以及可能出现的对市场竞争产生的逆向激励风险,前移竞争规制的逻辑起点更加符合预防原则实施的基本要求。但与此同时,如何保证行使事前规制的实际效果,审慎克制事前规制权力的制度风险,避免滥用事前规制的危险,则是更加重要且无法回避的实践问题。
(二)大数据对竞争法的规则体系提出了挑战,促进了竞争法规则建设的完善
前已述及,基于大数据技术与资源的广泛运用,尤其是大数据优势被平台经营者所掌握,现实中出现的各类复杂的交互关系已经引起了不同法律部门的关注,目前主要集中在民事和刑事法律领域,对涉及竞争法律关系,或属于广义上的市场规制法律关系的讨论尚未进入研究者视野,相关理论研究匮乏,加之竞争执法机构和司法机关对大数据所涉及的竞争法律关系在多数情势下仍然保持着审慎的克制姿态,相关规则建设和司法解释尚付阙如,既有的规则系统亦缺乏对大数据竞争与垄断行为的体系化与一致性的文本表达,无法及时展现竞争法制的时代特征。
囿于规则体系的不健全,诸如大数据竞争法属性的辨识标准,滥用大数据技术与资源限制、排除竞争的违法认定基准及规制手段、责任承担方式,滥用大数据技术与资源侵害用户自由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的认定标准与表现形式,大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的审查要素,大数据企业和平台经营者或大数据企业间的纵向或横向协议或共谋行为的认定基准,大数据市场认定基准,大数据引发的用户数据安全风险的防范与救济等问题都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澄清。对此,建议在多部门密切合作之下,尽快出台有关大数据竞争法适用指南,或制定更为广泛的涉及数据行业的竞争法实施规范,将行业标准的执行纳入到竞争法统一适用的范畴之中,尽可能地协同行业发展与综合竞争执法之间的政策性与制度性冲突。在此过程中,应以竞争政策为基础,加强对新增的行业发展政策和行业部门立法的公平竞争审查,确保行业正当利益与竞争规范价值的协同并进。
(三)大数据对竞争法的规制方式提出了挑战,促进了竞争法规制方式的优化
大数据技术与资源得以广泛使用与我国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互联网平台经济的高速增长密不可分。尤其是平台经济的野蛮增长,几近疯狂的用户增长和无节制、无规则的数据抓取,造就了大数据在中国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经济业态中的优势地位和迅猛发展趋态,大数据技术与资源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参与世界竞争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而这种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与现行竞争法规制理念滞后和缺乏相应的竞争法规则体系不无关系,正可谓“无规无矩”则“无畏”的创新增长突破了交易壁垒和体制机制的巨大成本负担,或者说,这种负担相较于传统经济活动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然而,不可否认,风险也因此暗埋于下。在突破传统经济体制、创新商业模式的同时,也使得现行竞争法规制方式无法有效地应对随之而来的新型违法竞争行为和巨大的商业风险。譬如,现行竞争法规制中普遍采用的结构规制和行为规制在面对具有明显动态竞争(dynamic competition)特征〔55〕动态竞争是指所谓的竞争优势地位都只是一种短暂的态势,竞争优势的形成依靠竞争者不断地创新,而这种基于不断创新而形成的竞争优势本身又是固定成本和风险投资极高的。(See Christian Ahlborn, 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New Economy: Is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up to the Challenge?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Review, 22(5), 2001, pp.156-167.)故此,在这种情势下对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就不可能是静态的,不能仅考虑产品因素和市场份额,还应同时考虑时间维度和市场进入壁垒,以及其他经营者的对抗力等。的“大数据+互联网平台”经济活动时,经营者的市场行为类型及跨度变得更加复杂而难以预估,从相关市场到不相关市场,乃至未来市场上的市场地位也伴随大数据强大的市场预测与链接功能下不断增多的混合竞争和模糊竞争样式而变得难以被准确认定。
实践中单纯依靠对经营者单一行为或特定行为,以及经营者所具市场结构来判断经营者某一时段的市场行为和市场地位是否具有反竞争性的做法已然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也无法准确反映其市场创新与市场垄断之间的敏感界限。〔56〕以大数据技术与资源为基础和支撑的互联网新业态自带很强的科技性和创新性,大数据正在或已经模糊了合法创新与违法垄断的边界。事实上,在保护科技创新的合法垄断与滥用知识产权垄断之间本来就具有很强的模糊性,不易被实践所辨识,导致了当前对涉及大数据的违法竞争行为的规制效果总是有些不尽如人意,甚至竞争执法机构自身也觉得缺乏正当性和妥适性,亟待革新现有的竞争规制方式,引入综合性的系统规制方法。
在此方面不妨可参考韩国对“高通案”〔57〕See Bing Che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Qualcomm Case in Korea and China: Focusing on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Korean Competition Law Association Conference, Daejeon, Korea, June 23-24, 2017.的处理模式,重点关注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KFTC)对利用优势传导和交叉维持行为组合所结成的反竞争商业模式的规制经验。2016年12月KFTC在裁决“高通案”所作的处罚决定书中指出,“高通公司凭借其在专利许可市场和基带芯片市场上的支配地位,对竞争对手限制或拒绝标准必要专利(以下简称SEPs)授权,与手机制造商签订了各类不平等交易协议,巩固了高通的支配地位,增强了其在谈判中的影响力。更甚者,高通公司将以上三种行为演变成为一种反竞争的商业模式,这种商业模式形成了一种排他性的闭合系统,使得其能维持并利用在专利许可和基带芯片两个市场的支配地位。”〔58〕KFTC Imposes Sanctions Against Qualcomm’s Abuse of SEPs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December 28, 2016, p.8.事实上,对于处罚决定书,高通公司一直辩称其单个商业行为,如对SEPs的授权行为并不违反“公平、合理、非歧视”原则(即FRAND原则),是一种商业习惯和交易惯例,其所要求的手机制造商反向许可专利,强制接受专利打包等条款也可以解释为是出于维护自身知识产权的正当利益等。〔59〕同上注,第6~7页。在此,笔者无意于讨论高通公司答辩意见的正当性与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仅对比该答辩意见与KFTC的处罚意见。通过对比可以发现,KFTC对高通公司“三个单项行为有机组合成的商业模式”的反竞争性和反创新性的关注才是促使其在经过七次听证,包括两次同意命令(content decree)审查和一次案件深度评估(in-depth review),仍然不接受高通公司的承诺整改计划,最终作出严厉处罚的根本原因所在。而且,KFTC在处罚决定书中一直强调对高通公司的处罚措施具有开创性,首次对反竞争和反创新性的商业模式采取了矫正措施,关注经营者行为的一体化与有机化,力图建立一个开放性的促进竞争的生态系统。〔60〕同上注,第2页。
虽然韩国“高通案”与本文讨论的大数据对竞争法规制方式的挑战并不契合,甚至有些“风马牛不相及”,缺乏佐证力,但是若从该案所涉及的商业模式与单项行为之间的有机联系分析,案件折射出的对“一手托两家(基带芯片制造商和手机制造商)”式的具有市场优势力的平台型经营者的规制,绝不能仅就某单项行为或某单一市场结构而采取行为规制方法或结构规制方法,必须对经营者的诸多市场要素,如市场地位、经营行为、商业模式等采取系统规制,尤其是在大数据技术与资源的实际运用中往往关联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运行,传统的以市场结构和经营行为为主要分析对象的规制思路和方法亟待升级,整体的系统规制方法有待进一步明确化、精细化及专业化。
在面对挑战的同时,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由于大数据技术与资源被广泛使用的巨大影响和无限可能,其运用于当前和未来法治生活的客观现实和发展趋态,大数据之于竞争法实施的促进作用及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同样不容忽视,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扩展竞争法实施维度,凸显和肯认竞争法对消费者利益保护的直接价值。有关竞争法实施维度及其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问题,我国学界素有争论,其焦点在于竞争法实施对消费者利益能否构成直接保护,消费者利益是竞争法实施的“反射式”间接利益还是直接利益,进而争论消费者利益能否单独成为竞争法实施的直接诉求。〔61〕有关竞争法实施与消费者利益保护间的关系,笔者的立场很明确,即消费者利益理应成为竞争法实施的直接利益,可以作为单独诉求启动竞争法。(参见陈兵:《我国〈反垄断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适用问题辨识》,《法学》2011年第1期;同前注〔46〕,陈兵文;陈兵:《现代反垄断法语境中的消费者保护》,《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陈兵:《信息化背景下我国消费者保护法律模式的升级——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视角》,《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等。)对此,有批评的意见认为,过分强调消费者利益作为单一独立的竞争法实施诉求,容易混淆竞争法价值。(参见兰磊:《反垄断法上消费者利益的误用批判(上)》,《竞争政策研究》2016年第5期。)也有支持的观点认为,中国竞争法对消费者的保护不应局限于一种“反射式”的间接保护,而应当是直接保护甚至是侧重保护。(参见陈耿华:《互联网时代消费者在中国竞争法中的角色重塑与功能再造——兼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其他相关论文,还可参见马辉:《消费者选择标准在反垄断法中的应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这直接影响到竞争法实施的维度和现实效用。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技术和资源的广泛运用,平台经营者在互联网场域下的竞争活动已经具有了区别于传统线下市场竞争的特征,价格及其弹性作为一种基本且显著的竞争标尺和测量指标已经无法精准地描述竞争的真实境况和实际程度了。换言之,价格及其弹性对消费者利益的反应灵敏度在大数据竞争环境下不再是那么重要了。此时,消费者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已然发生了变化,消费者对非价格要素的竞争所引起的质量基准的高低提出了要求,并且对质量提供者的选择权利提出了合理期待。与之相关的解释已经在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360诉QQ”一案中得到述明。〔62〕参见陈兵:《网络经济下相关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探析——以“3Q”案为例》,《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年第9期。更有学者明确提出,消费者(用户)隐私利益与竞争法实施的交叉点(intersection)体现为将消费者隐私保护作为平台竞争中非价格质量竞争的主要形态和测试标准。〔63〕同前注〔52〕,Maurice E. Stucke & Allen P. Grunes书,第 260页。扩展言,对基于数据驱动而出现的各类市场行为的竞争法考察,必须关注到消费者(用户)对服务质量及其可选择的权利作为平台经营者市场行为之竞争合规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认知与期待,消费者利益保护不仅包括价格维度的利益保护,还包括非价格维度的利益保护,这一点在大数据竞争环境下表现得尤为明显。甚至可以认为,消费者对其隐私保护的质量及其选择接受何种服务提供者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数据驱动型市场竞争秩序的自由公平维持方得以实现。进而言之,在数据驱动型市场竞争环境下,欲提升对消费者隐私的保护,必须维护该相关市场上的自由公平竞争秩序,以此激励相关平台经营者不断警惕和提高对隐私(数据)的保护,如不能满足消费者对隐私保护的正当诉求,则消费者必须赋予选择转移于其他服务提供者的权利和负担公平合理转移成本的可能。此际,消费者利益已构成数据时代竞争法实施的直接目的,成为了竞争法实施的独立诉求,而非一种“反射式”的间接利益。
其二,增进竞争法实施信度,提升和巩固竞争法在维持互联网市场秩序上的基础地位。大数据技术与资源的广泛运用有助于打破“信息孤岛”困局,实现数据共享,在客观上影响到各类法律的实施。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保护原则的适用范围和可能得以扩展,强调了提前预防的必要与价值,〔64〕同前注〔54〕,陈景辉文。这具体到竞争法实施领域,则表现为有针对性地规制涉嫌滥用大数据优势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以及在算法运用领域出现的算法歧视、算法黑箱、算法共谋等侵害消费者利益、损害公平自由竞争秩序等新型反竞争和反消费者利益的行为。由此,对现行规制方式和规制技术的科技含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以科技手段规制科技滥用将有利于更好地推动竞争法的实施,助力竞争法实施的智能化建设。在扩展竞争法实施维度的同时,提高竞争法的实施精度,其直接效果则在于对竞争法在互联网领域市场竞争中基础地位的维护和巩固,只有清晰地认识到大数据对竞争法实施带来的深刻变化,才能准确地判断竞争法实施在当前和未来以数据为驱动的升级后的互联网产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增进竞争法实施的信度。此处提及的信度,一方面是指竞争法实施的可靠性(reliability)和稳定性(stability),另一方面则是强调竞争法实施的实效性(effectiveness)和信任度(conf dence)。前者源自“信度”在统计学上的意义,指测验结果的一致性、稳定性及可靠性,具体到大数据技术对竞争法实施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提高竞争法实施的可预测性和可信赖感,在扩展竞争法实施维度和延展竞争法规制环节的同时,利用大数据技术防止滥用竞争法的风险。后者对“信度”的理解更多地是站在对大数据于竞争法实施的美好愿景的维度上,希望通过大数据技术和资源的广泛使用提升竞争法实施的实际效果,增进社会各界对竞争法于市场经济尤其是互联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和信任程度。换言之,只有竞争法行之有效,才能提升民众对竞争法实施的依赖和信任,实现有效方有威、有威更有效的良性互动。〔65〕有关竞争法实用性和权威性之间关系的讨论,参见陈兵:《从继受到自主创新:19世纪下半叶美国法上垄断概念研究》,《中外法学》2010年第2期。
如前所述,虽然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大数据平台经济的快速增长给竞争法实施提出了挑战,但与此同时,当大数据技术和资源被广泛运用于法治生活之际,也为革新和升级现有的竞争法实施理念、范畴、方式、效果提供了现实机遇和无限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言,以科技手段回应由于科技之于法律实施的挑战所引发的外部性变化是可能的,在法律体系的构建完善和规则适用的调整改进中,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吸纳科技元素,释放科技力量。法律作为一种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外部性手段和方式,也应该且必须注意到纳入其他外部性要素对其自身更新的必要与意义。
五、结语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带动了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发展,给大数据技术的迅速成熟与大数据资源的巨量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实践场域,互联网时代已正式步入更高进阶的大数据时代。可以预见,以互联网技术和平台经济的广泛适用和普遍接受为基础,融合大数据技术与资源,将会为下一阶段市场经济竞争带来全新格局与视阈。大数据作为一个聚合概念将会无限扩展和无限可能地影响市场竞争。
透过对大数据于市场竞争的正向激励价值与逆向激励风险的分析可以发现,大数据具有强大的市场反馈与预测功能,能够通过数据优势传导有效链接“不相关市场”或“未来市场”,形成在纵向与横向市场上的跨时空竞争优势,并将这类优势持续传导和交叉维持下去。尤其是在大数据优势被平台企业掌握或通过协议、经营者集中等方式俘获后,极易出现滥用该优势限制、排除竞争的行为,不仅损害其他经营者的自由公平竞争利益,也对消费者利益产生压制风险。特别是当现有市场支配地位者利用大数据技术和资源消灭潜在的竞争威胁、构筑过高的市场进入壁垒时,更是以牺牲市场自由公平竞争秩序为代价来维持和巩固其市场支配地位,其动机和行为的反竞争性和封闭性显露无遗,其危害之巨、影响之深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故此,当前亟待从大数据自身特征及竞争法属性评价入手,在充分结合大数据于市场竞争的激励功能的基础上,聚焦大数据给竞争法规制理念、规则体系及规制方法等带来的挑战,适当扩展竞争法规制的逻辑链条,由强调事中、事后规制,前展至事前规制,并引入系统规制,建立具有预防性和整体性的规制系统。同时,还应充分重视大数据技术在竞争法规制实践中的运用,提升竞争法实施的科技含量和科技手段,〔66〕譬如,在前文提及的“脉脉非法抓取使用新浪微博用户信息案”中对大数据技术的把握成为了案件审理的关键。由于审判人员缺乏相应的技术知识,导致庭审的难点主要集中于技术问题而非法律问题上。可以预见,未来对科技的识别和运用在涉及互联网科技的竞争规制的案件中会越发凸显。事实上,可能由于专业科技知识及背景的缺乏导致法官的裁判容易出现问题,无论是过激的或过于谨慎的裁判,都可能延滞互联网技术的创新使用,以至于阻碍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有关此案的审理情况,可参见前注〔2〕,张璇文。达致规制科技滥用与激励科技创新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