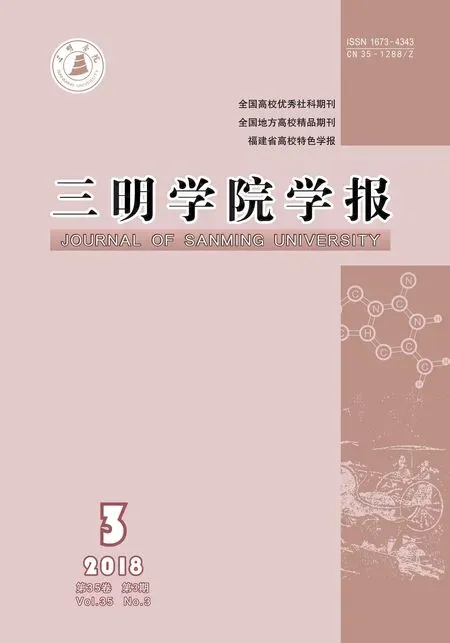福建文化视野中的闽中文化概念辨析
柳传堆
(三明学院 三明市地方文化研究中心,福建 三明 365004)
三明市在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诸多瞩目成绩,但也遇到了一些尴尬。其中之一是,我们有客家文化,但我们研究不如龙岩、梅州、赣州;三明尤溪是朱子故里,研究朱子文化,但我们研究不如建阳。三明大田有部分闽南文化,但我们研究不如泉州。主要原因是没有找到三明应有的文化定位,总是在周边的客家文化、福州文化(尤溪的部分)、闽南文化、闽北文化(沙县的部分)之间游移,漂浮不定,亦步亦趋跟随他人做文化。如三明的宁化、清流、明溪是由闽西原汀州府所辖8县中的3个县,确实有较为纯正的客家文化,客家祖地宁化石壁也已经获得世人的公认,但是有人硬说整个三明地区都是客家属地,于是乎尤溪大田的土堡碉楼变成了 “客家”建筑文化,市级博物馆成了客家专馆,连外形都设置成圆形土楼模样。2016年10月18日《人民论坛》上刊发文章《“闽学四贤”理学思想与闽西北客家文化特质》——断定“闽学四贤”都为客家人:“他们植根于闽西北客家土壤,以自己家乡作为理学思想主要传习地,其理学思想对该区域客家民性中的思想构建、价值取向、性格塑造和行为方式的养成起重要作用,直接影响了客家文化的发展。”这显然是犯了泛客家主义的错误,其结果是张冠李戴。“闽学四贤”均非客家人,但闽学对客家文化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很多三明人邯郸学步,跟着周边地区研究文化,倒把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的真实面目给忘了,甚至有文章认为,客家文化影响到沙县、尤溪、永安、大田,那些土堡、餐饮、祠堂等等都很有客家味。客观事实是沙县、尤溪为代表的闽中文化影响了客家文化。据林国平等主编的《福建移民史》,“从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汉人南迁入闽渠道主要有以下几条:“(1)由江西鄱阳、铅山经分水关入闽;(2)由江西临川、黎川越东兴岭经杉关入闽……(3)由闽浙边界山口入闽;(4)由海路入闽。”[1](P29)“由闽浙边界山口入闽”的通道没明指哪儿,但笔者认为应为这两个关口,即浦城与江山之间的仙霞关①、位于福鼎的分水关(福建有三个分水关)等。专家还指出:“入闽的北方汉人,从海陆来的主要居住在福州及沿海地带;大多数则从陆路经江西、浙江移居闽北,然后由闽江上游、中游而到达下游的侯官,再由侯官往南迁至木兰溪流域、晋江流域和九龙江流域;其中也可能有一部分从江西直接进入闽西,然后再到达闽西、闽南九龙江流域,但这部分数量较少。”[1](P30)可见,大规模由北南迁汉人是从东部、北部入闽的,当然,也有一部分移民从江西赣州之石城等地再迁徙到宁化石壁等地,然后开发闽西,因此主次要分清楚。三明虽然是由历史上的建州、延平府、汀州府、邵武军、永春州等辖境拼凑而成,但三明地域上正好地处闽中。从东晋义熙年间到明嘉靖十四年(1535),沙县、尤溪、永安、大田陆续建县,经过1130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三明本土存在着正宗、内涵丰富的“闽中文化”。
一、“闽中”的地理概念、历史概念、行政概念、文化概念辨析
“闽中”的地理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闽中即福建,唐朝中期前闽中即闽的名称,如称“闽中士子”,是说福建的知识精英。因闽处在吴越(浙江北部)和南越(广东大部、广西、越南中北部)中间,故称闽中。狭义指福建省中部,即以尤溪县为中心,介于闽东、闽南、闽西、闽北之间的尤溪县、大田县、沙县、梅列区、三元区、永安市以及德化、永春靠近戴云山脉那部分。
“闽中”的历史概念,有三说:第一指福州,如明代“闽中十才子”,说的是福州地区的林鸿、郑定、王褒、唐泰、高棅、王恭、陈亮、王偁、周玄、黄玄②等十人。第二种观点认为,“闽中”既可指处闽北与闽南之间的地区,如莆田、仙游。莆田市委党史研究室曾编写 《中共闽中地方史》(1999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书中的闽中,指莆田、仙游及其周边等地。也可指处闽东与闽西之间的地区,如福清、永泰、永春、惠安、大田、尤溪、沙县、德化、永安、梅列、三元等县区。第三种观点认为,“闽中”即指福建整个地区,出自闽地之中,包括台湾地区。
闽中的行政学概念。福建省最有资格从行政概念命名为闽中的地级市是三明市。但是又因为宁化、清流、明溪、建宁、泰宁等县划归三明市管辖,三明有时被一些人称为“闽西北地区”,实际并不准确。
“闽中”文化学概念是指,以尤溪县为核心,以沙县、大田、永安、三元、梅列为环状的文化圈所产生的文化为闽中文化。凡是在闽中文化圈内产生的任何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均属闽中文化。在闽中文化圈外围,分别是福州市为代表的闽东文化、以建阳为代表的闽北文化、以泉州为代表的闽南文化和以长汀为代表的闽西客家文化。
历史上,闽中文化的最高哲学、伦理学思想是闽学,亦即福建理学。福建理学,宋明以降,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高势位文化”,不仅仅影响了闽中区域,它还影响了福建东南西北的各个区域,即影响了闽东文化、莆仙文化、闽北文化、闽南文化、闽西客家文化。之所以下此论断,一是因为诞生于尤溪县城的朱熹是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正是他及其弟子的努力,完成了中华文化思想史上儒家、道家、释家以及《易》经智慧的大融合、大开拓、大发展。因此,理学思想是福建文化乃至全国文化的纲领;二是“闽学四贤”中,有“三贤”在“闽中”,占四分之三。狭义的“闽中”正是处在这个文化圈之内,其地理位置之独特,文化地位之显赫,文化影响力之大,全国哪个地方的文化能与之比肩?
二、“闽中”文化发展轨迹
闽中文化发展轨迹可以分为前奏、成熟、发展、命名几个阶段。
“闽中”文化的前奏有二:一是汉代建安元年(196)析分侯官县北乡置南平县,当时属会稽郡南部,辖境覆盖如今的“闽中”大部分;晋代太元四年(379)改延平县,属建安郡;南朝宋泰始间(465—471)复名南平县。现今沙县因毗邻南平,在建县之前,属南平县管辖。二是将乐建县,即三国吴景帝永安三年(260)。那时的将乐县,辖境包括如今的将乐、宁化、建宁、泰宁、邵武、沙县、永安等一大片。这个阶段福建大多数地方都是处于蛮荒之地,少受或未受中原文化影响,文化是以闽越族文化为主。考古学新发现,有人认为福建在闽越族之前的几千年,早有人类居住,他们不信蛇图腾,而是海上飘来的矮个子棕色人种,后来可能被同化或者灭绝。
“闽中”文化诞生的标志时间应当是沙县建县——即东晋义熙年间(405—418),这差不多对应着中国历史上“五胡乱华”——“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始入闽者八族”(《三山志》)时期。其中有林姓、黄姓、陈姓、郑姓、詹姓、邱姓、何姓、胡姓八姓,本系中原大族,入闽后先在闽北浦城、建阳及晋安(今福州)定居,而后渐向闽中和闽南沿海扩散。史称“衣冠南渡,八姓入闽”。这是中原地区人民第一次大规模南迁,也是北方汉人与闽人的第一次大融合。沙县建县之时,所辖范围非常广泛,唐之前,辖地南尽黄田岭,西及站岭,包括如今的沙县、尤溪县西北部、梅列区、三元区、永安市、明溪、清流、宁化,南部、西部外围分别与如今的龙岩黄田岭、江西石城(站岭)接壤的广袤区域。沙县历史上的繁荣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因沙溪河贯穿而过,航运发达,下联南平(唐宋时期,南平港已经很发达了,“舟车辐辏,物阜人彩,省门以北,无以为比”[2](P82))、福州,上接沙溪上游广袤区域(今梅列、三元、明溪、永安、宁化),支流在宁化段名翠江,在1960年前尚可航行4吨以下麻雀船。正是水运方便,造就了沙县历史上经济、文化的发达与繁荣,遂有“金沙县”之誉。
“闽中”文化成熟的标志是尤溪县的建立与朱子理学的诞生。尤溪始建县于唐开元二十九年(741)。笔者以为,一个地方文化成熟的标志并且得到命名,要符合如下几个条件:
一是地理位置相当契合,名至实归。如山西省有“晋中市”,位于山西省中部,东依太行,西临汾河,北与省会太原市毗邻,南与长治市、临汾市相交。尤溪、大田正好处于闽中,把这个地方及其周边附近区域产生的文化命名为 “闽中文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是人口足够多,可设州立府。有一定的自然区域与一定数量的人口,至少具有相当于“州”“府”的规模。尤溪县建县后,辖区幅员辽阔,尤溪流域,含尤溪上游文江流域都是它的辖境,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尤溪县全境、大田县大部分。“闽中”按今天地理区域算,包括沙县、尤溪、永安、三元、梅列五个县区,足够古时“州”“府”的规模,只不过因为南剑州(延平府)设立的时间早、闽中区域内戴云山脉阻隔等特殊原因,没有把沙县或者尤溪上升为 “州”“府”(沙县府或尤溪府),这不能说不是历史的遗憾。
三是文化名人足够多,人杰地灵。“闽学四贤”(杨时、罗从彦、李侗和朱熹)中有“三贤”在今三明市境内:将乐县分得“一贤”是闽学鼻祖杨时;沙县分得“一贤”罗从彦,他是朱熹父亲朱松和李侗的老师;尤溪分得“一贤”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尤溪县城是朱熹的诞生地。朱熹1至7岁都在尤溪度过,绍兴七年(1137)夏,8岁的朱熹随父母到建阳生活。但朱熹曾先后多次回尤溪,有据可考者九次,今有其流传下来的诸多诗、书法和典故为证。朱熹共著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西铭解》《太极图说解》《诗集传》《楚辞集注》等60部400多卷,皆为中华民族文明之经典文献,润惠福建,光耀中华,泽被后人。因此,我们把朱熹的诞生及其贡献,看成是闽中文化成熟的标志。
闽中文化名人还很多。理学家陈渊(1075?—1145),杨时的得意门生之一,今永安贡川人,一说沙县城关人,绍兴八年(1138)赐进士。《延平府志》将陈渊与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和廖德明并称“道学”六大代表人物,有《默堂集》22卷传世。陈山(1362—1434),沙县溪南九都溪口人,洪武二十七年(1394)进士,曾参与编修《永乐大典》,后擢升为吏部给事中。田顼(1496—1562),今大田县上京梅林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被称为晚明四大才子之一。还有宫廷画家边文进、音乐家杨表正等。
闽中自古以来出了不少能臣、忠臣、廉臣、循吏、名将,如:唐代能臣范子高(863—?),进士,大田县城关人;宋代廉臣张若谷(生卒年不详),沙县城关兴义坊人;宋廉臣邓肃(1091—1132),永安贡川人;宋忠臣陈瓘(1057—1124),沙县城西劝忠坊人;宋能臣陈偁(1015—1086),沙县城西人;清廉臣吴腾汉(1780—1851),大田梅山人。明嘉靖年间名将领詹荣(1500—1551),尤溪新阳镇高士村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曾任兵部左、右侍郎,两度主持兵部工作。清代,“闽中”出了两个武探花——沙县的罗英笏和大田的林宜春。
历代科甲名数,也是衡量地方文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闽中的沙县、尤溪、大田、永安四县表现不凡,宋代尤盛,明清时期有所衰落。“闽中”科甲胜地第一个当属现在的永安贡川。此地人杰地灵,自唐朝以降,曾出过2名探花,16名进士,13名举人,24名贡生,3名理学家,宋朝新科探花陈瓘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朱熹赠联曰:“一门双理学,九子十科名。”陈氏家族遂成为远近闻名的名门望族。第二个科甲胜地可能是古驿道上的明珠、有 “小福州”之美誉的——尤溪县洋中镇的桂峰村。北宋端明殿学士、书法家蔡襄之后裔九世孙蔡长肇基于此,至元代子孙繁衍渐成规模。明洪武初年(1368—1377),蔡氏子孙奉行“耕读传家,经史名世”的祖训,读书人中有多人先后考中秀才、贡生、举人。据记载,明清两代中进士3名,中举人12名,中秀才412名。第三个科甲胜地是大田上京镇的梅岭村,在明代出过一村三进士,号称“梅岭三田”(田顼、田琯、田一儁)。
据卢美松《福建历代状元》(附录《福建历代一甲进士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统计,福建历代状元总共46人,其中福州16人,莆田、泉州均为9人,南平6人,三明3人(沙县1人,其余两名在泰宁)、龙岩、宁德、漳州各1人。
据林荣发《三明科举文化》统计,元代三明境域有30名进士,占全省的40%(省志收录元代三明籍进士16名,占21.33%)。其中沙县10名,尤溪9名,即“闽中”19名,占三明的63.33%。在明代,三明境域共出过81名进士,仅占明代福建省进士总数的3.41%。其中大田12名,沙县10名,尤溪7名,永安5名,即“闽中”34名,占三明的41.97%。在清代,三明境域共出过96名进士,占全省的7%。其中沙县14名,大田12名,永安4名,尤溪3名,即“闽中”33名,占三明的35.10%。
四是书院林立,文化繁荣。沙县、尤溪、永安书院较多,大田较少。根据王晓暖《三明宋代书院考述》《三明辖境明清书院考述》:
据白新良统计,南宋三明辖境共有5所书院,分别是沙县凤冈书院(南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谏议(了斋)书院,尤溪南溪书院(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泰宁南谷书院,将乐龟山书院(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另据黄仲鑫统计,南宋三明辖境共有书院 8所,分别是将乐龟山书院,尤溪南溪书院,沙县谏议书院、凤冈书院、槟榈书院,泰宁翠云岩书院、南谷书院,建宁云岩书院。又据明代黄仲昭的《八闽通志》统计,南宋三明辖境共有 6所书院,分别是将乐的龟山书院,沙县的谏议书院、凤冈书院,尤溪的南溪书院,建宁的云谷书院,泰宁的翠云岩书院。[3](P73)
明代,永安县新建书院6所:豫章书院 ;先贤(四贤)书院(正德朝);槟榈书院(嘉靖朝);纹山书院(不知建于明代何朝);道南书院(隆庆朝);云龙书院(万历朝)。[4](73)沙县修复、重建书院 2所:豫章书院(址在沙县城关);谏议(了斋)书院。尤溪县修复、重建 1所:南溪书院 (景泰二朝);新建 1所:镇山书院。[4](296)
在清代,永安县新建书院 4所;沙县新建书院 1所,修复、重建书院 1所;尤溪县修复、重建 2所;大田县新建书院 2所。[4](P296)
三、闽中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在清末,福建各地的地域性文化概念尚未形成,那时的人们并无“闽东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闽北文化”这样政治学、旅游学、经济学、文化学上的概念,当然也无“闽中文化”概念。笔者以为,既然提出了“闽中文化”概念,而且 “闽中文化”确实是在福建历史上客观存在的,那就有必要有义务发掘它的内涵并概括它的特征。
闽中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大体包括:闽中理学文化(哲学、伦理学层面),尤溪朱子文化,闽中文学史,闽中方言,闽中戏剧文学与文化,闽中科举文化,闽中信仰文化(太保信仰、陈靖姑信仰、谢祐信仰等),闽中书院文化,闽中建筑文化,闽中沙溪、尤溪流域水运交通文化,闽中饮食文化等。笔者认为具有如下三大特点:
(一)主流性与指导性
客观上说,福建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在福州,从汉代的冶城、侯官到现在的省会,其文化的优势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闽东地区自古多豪杰,科名之盛,冠绝福建,文人学士如过江之鲫,但遗憾的是就没有出过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力的大哲学家、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反而地处福建腹地的闽中地区,宋代以来,哲人辈出。仅仅宋代,闽学“四贤”之中,有“三贤”属现在三明。闽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闽中”之学。
闽中文化的哲学思想与伦理学思想是闽学,其实就是福建理学。福建理学,最终成为全国性乃至成为东亚、东南亚文化圈的主流思想,这就是它的主流性。福建自古以来讲“理”之风很盛。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因在福建讲学,弟子多为福建人,形成了世称“闽学”的学派。闽学,或称朱子学,至元朝被采纳为官方哲学。朱子学在宋元之际传播到朝鲜、日本等国,17世纪欧洲人开始注意朱子学,18世纪初有人翻译了朱熹的某些作品。可见,朱子学的研究已超越了国界,朱子学已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哲学理论。
所谓的指导性,指的是闽中文化中的理学思想被确立为国家正统思想之后,成为纲领性的指导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周边文化乃至扩散至全国各地区。就以客家文化为例,目前很多学者撰文分析客家文化中的儒释道成分,特别是客家的建筑、民风民俗无不打上宋明理学的烙印。
(二)封闭性与独立性
闽中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处于戴云山脉与武夷山脉之间,跨越闽江水系二条支流——沙溪河水系与尤溪水系,水路交通方便,但陆路交通十分不便。地理意义上的“闽中”之大田县、永春县、德化县的部分,正好处在戴云山脉之中,山高水险、路隘林深,这就造成了闽中文化的相对封闭性。因为封闭,所以独立;因为独立,所以浑朴;因为浑朴,所以有个性;因为有个性,所以有韵味。这里的古老文化较少遭到破坏,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存保留较为完整。
1.宋杂剧的活态遗存——张大阔公戏
大田县的文江赤坂、永安市槐南乡至今尚存的大阔公戏,现在已经成功申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研究专家认为,该剧为宋代杂剧的活态遗存形式[5](P17-22),十分可贵。此外,明清时期从外省入闽的大腔戏、小腔戏、汉剧等古老剧种,目前仍然可以在沙县、尤溪、永安找到民间剧团。其中,古老戏剧剧种保留最多、最完善、最浑朴的,当属大田县。
2.防御性的土堡(碉楼)——明清遗存居多
古堡主要分布在尤溪、大田、永安等地。据《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专家统计,土堡数目最多的是大田,1 500平米以上的土堡有19座。土堡规模最大的是永安槐南乡西华村的安贞堡,总建筑面积5 800平方米,是福建省罕见的大型民居建筑。
大田土堡,是典型的防御性建筑堡垒,极具闽中特色。大田建县之前,其地域分别归属尤溪县、永春县、永安县、沙县管辖,山高林深路隘,土匪常出没,匪盗猖獗。明嘉靖十四年(1535),大田建县,隶属延平府,清雍正十二年(1734),永春县升为永春州,大田县隶属永春州。但是境内及其周边土匪仍然很猖獗,官府及老百姓不堪其扰,富人官宦之家独资或村民部分姓氏自愿集资在乡共建土堡,目前保存19座。大田代表性的土堡有:芳联堡(均溪)、琵琶堡(建设)、绍灰堡、光裕堡(广平)、安良堡(桃源)、潭城堡、凤阳堡和泰安堡(太华)等。
3.方言的独特性与独立性
闽中方言多而复杂,全国方言最复杂的区域在福建,福建方言最复杂的区域在闽中——区分为沙县话、尤溪话、大田话三大类。尤溪话是指通行于福建省尤溪县内大部分地区 (城关镇、西城镇、梅仙镇、联合镇、溪尾乡、坂面镇、台溪乡等)的方言。可分为7个小区和1个闽南方言岛。大田方言更为复杂,大体可分为前路话(本地话)、后路话、闽南话、桃源话、客家话等五种。沙县话是闽中语的一种方言,主要通行于三明市的沙县一带。历史上,沙县曾是闽中地区的行政中心,因此,沙县话曾一度被当作闽中语的代表方言。沙县话以城关凤岗镇的城关腔为标准方言,各地口音与城关腔大同小异,完全可以互通。在沙县与永安之间的梅列区与三元区,存在着一种三明本地话,介于沙县话与永安话之间。
闽中方言被语言学家誉为语言活化石。闽中方言至今保留唐宋古音、古韵的读法,有的在闽南话中已经消失的唐宋古音,在这里依然可以找到。如“燃”字,大田话声母念“L”,而非普通话“R”声母。 “陂”字,普通话都如(pō、pí、bēi),大田话念(bī)。这是古代一种拦水为坝引水灌溉的工程,常见木构的石笼做墩,墩与墩之间架木,用芦苇、芒草拦水,一年修一次,洪水冲毁后,来年再修,周而复始。“古无舌上、古无唇齿”的古汉字发音规律,在闽中方言中得到充分印证。全国各个大学与科研机构,招收汉语音韵学的硕士、博士,最理想的区域在福建,福建最理想的区域在“闽中”,闽中最理想的区域在大田,因为大田话复杂且原生态。
(三)混融性与包容性
闽中文化的混融性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居民成分的多元性,主要体现为土著人口与外来移民之间和平共处;不同来源的外来移民之间和平共处;不同时期来源的移民之间和平共处;不同民族之间居民和平共处——原闽越族、汉族、畲族、回族等和平共处。
外来的人口移民与土族人和平共处。根据《福建移民史》研究,闽中移民大体上可以分为:一为政治移民,即朝廷未解决粮食危机或财政危机,鼓励百姓移民。二为军事移民。唐高宗总章二年(669),为了平定福建,派大将陈政、陈元光率3 600多名府兵入闽平叛,事成之后陈元光上报朝廷申请设立漳州,获准后他任首任漳州刺史,陈元光因此被后人尊为“开漳圣王”。唐僖宗光启元年(885),黄巢起义,群雄割据。时任河南光州固始县佐王潮因父亲早逝,与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率兵响应黄巢起义,偕母徐氏(后封河涧夫人)参加黄巢起义军王绪的一支军队,由河南光州固始入闽,途经江西赣州到福建汀州(今长汀)后南下,开创了统一八闽的光辉业绩。乾宁四年(897)王潮去世,王审知继其位,朝廷任他为武威军节度使、福建观察使,累迁至检校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琅琊王。天祐四年(907),后梁太祖朱温升任王审知为中书令,封闽王。王审知的母亲徐氏梅花墓在今永安清水乡。三是灾荒、战乱移民。东晋八王之乱,衣冠南渡,八大姓入闽是也。四是海外移民。如宋代泉州港为当时世界最大港口,很多海外“番民”移入,其中就有阿拉伯人来华经商,后来定居下来,他们之中也有部分人移居闽中腹地。大田县前坪乡有一个村名为“山川回族村”。这个村的回族先祖是明代从同安县迁徙而来的。
宗教信仰的混融性。有学者指出,中国汉人无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但又有信仰,而且很杂乱。闽中的信仰也非常复杂,几乎什么神都信。最大的信仰当属道教信仰与佛教信仰。闽中的佛教信仰朝世俗化、功利化方向发展,而且很多地方佛道同奉、佛道不分。同一座庙中同时供奉道教与佛教神佛,如沙县的罗岩庙,本是供奉道教神仙太保公的,可是里面也供奉佛教的观音佛。大田、尤溪、永安等地也有此类现象。
沙溪河流域的太保信仰。玉封太保侯王,全称是玉封十极太保英烈侯王,是沙溪河流域信众信仰的一个地方道教神,主要信仰区域为沙县、尤溪、永安、明溪、大田及南平等地,在福州城区也有一些信众。传说太保侯王吞毒解救民众得以被信众敬奉而成神。目前在沙县境内有三个太保主庙,其中在高砂池沧的太保庙为祖庙,在南阳罗岩和高砂冲厚的为主庙。其中以南阳罗岩的知名度最高,其次是高砂池沧的,目前高砂冲厚的太保庙知道的人已经不多。其他各地玉封太保侯王的庙都是以上三个庙的子孙分衍庙。
临水夫人又称大奶夫人、顺懿夫人、顺天圣母、三山女神,是道教闾山派的重要女神。据传,神姓陈名靖姑,或名进姑。福州下渡人,赴闾山学法,师承许旌阳真人。其主要事迹《闽都别记》有载。临水夫人庙在沙县、永安、大田均有发现,如大田城关附近上太有娘嫲宫一座,香火很旺,供奉的就是临水夫人。
闽中道教信仰系列的人造神,还有三明列西正顺庙、贡川正顺庙中的谢佑信仰。此外,“闽,东南越,蛇种”,谓闽人是蛇图腾的种族。下尤溪县与南平交界的人,仍崇祀蛇神。闽中与福建其他地方一样,也有土地神(村级,洋主公最多)、树神、石神、山神、风神、雷神、谷神、花神、药神等神信仰。
闽中文化的包容性,指的是它的文化接纳性强,突出表现为全国各地的移民所带来的文化,都可以在这里扎根生长。就全国范围来说,可以接纳来自中原发达地区的文化习俗。如闽中这里的尤溪、大田、永安等地,办丧事的时候,先生称死去的女子为“老孺人”,这是先民南迁以前贵族生活的遗存。“孺人”,古时称大夫的妻子,明清时为七品官的母亲或妻子的封号。据《礼记·曲礼下》:“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后人称普通妇女为“孺人”,足见当年江左衣冠士族南渡后,中原办丧事的遗风留存——尽管他们已经是老百姓,早不是官老爷与官太太了。
与闽中文化的混融性不同,客家文化圈体现出较强的“排他性”。“客家”“客人”的自谓,即“以客人的身份”在这个地方安家;作为当地人来说,起初则是将他们当作“客籍”,然而久而久之,就不再有视他人为“客”之眼光与心态。但是奇怪的是“客家人”来到福建或者其他地方几百年之后,还把自己看作“客人”。有人说,他们认定自己是中原人,将自己祖宗的灵牌带到所迁徙的地方,并声称自己迟早要将自己祖宗的灵牌重新安放在中原。他们表现出与当地人的一种对立情绪,这恐怕可以视为客家文化的 “负面”价值。
从西晋开始,直到唐宋,中原地区民众因为战乱原因,其中有两次大规模入闽,他们逐渐构成了今天闽东文化、闽南文化、闽北文化、闽中文化圈的居民,所占人口比例,与本地土族相比,是99%以上。但是这些地区的居民从来不以“客人”自居,而是自觉与当地原住民互相融合,尤其是互相通婚。
四、闽中文化与四周文化之关联
闽中文化与福建其他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闽东文化与闽北文化,是孕育闽中文化的母体。闽南文化是闽中文化的兄弟姐妹,在福建大地上共同成长。客家文化,因其孕育的时间更迟,在文化主导思想上无法影响闽中文化,但是像餐饮、建筑、服饰、婚丧嫁娶等习俗,也会影响闽中文化,同理,闽中文化也会影响客家文化。
(一)与闽东文化(闽都福州文化)的关系
闽东文化对闽中影响最深的地区是下尤溪的汤川、洋中、西滨这一片,因为他们毗邻闽都福州。洋中的桂峰村,历史上是闽中通往福州地区的必经之地,著名的驿道路过那里,因此必然带来了那里经济文化的繁荣。汤川的尤溪话,也非常接近福州话,习俗也与福州更为相像。
(二)与闽北文化(南平、建阳)的关系
闽中的沙县及其后来成立的尤溪县、永安县、大田县,都曾隶属延平府管辖,因此受到闽北文化的影响是自然而然的。从文化上说,闽北文化开发早于福建其他地区,文化上居于“上势位”,下势位的地方以学习、仿效为主。朱熹在尤溪出生,但他8岁便随父母离开尤溪到建阳生活,拜南平的李侗为师。李侗,人们称他为“延平先生”,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朱熹最终成为理学大师,声名远在老师之上。
(三)与闽南文化的关系
闽中文化与闽南文化关系的连接点是大田县,清雍正十二年(1734),永春县升为永春州,大田县隶属永春州。清循元明旧制,县隶州。大田受永春州、泉州府管辖,在文化上,大田自然也向州府学习、仿效。现在大田县屏山、济阳两个乡说闽南话。大田的前路话与闽南话也很接近,受闽南话影响比较深。大田民居建筑,以学永春的居多,经济往来也与永春联系密切。
(四)与客家文化的关系
在“闽中文化”概念尚未建立之前,学界流行着一个错误观念:客家文化影响了沙县、尤溪、永安、大田等。然而,客观实际是闽中文化(特别是沙县)首先影响了客家文化。后来,由于时代的发展,人员的流动与交流,客家文化又反哺影响了闽中文化。譬如说,现如今的“沙县小吃”,不少菜肴产于闽西客家。
关于闽粤赣各地客家文化、客家民系的宣传与炒作,主要是近百年来的事情。经过众多人的努力,客家文化已经演变成一个很大的体系——客家源流、客家民间信仰与民俗、客家建筑与古村、客家宗族、客家妇女、客家教育、客家艺术、客家方言和客家与当代等,可谓洋洋大观。福建其他地域文化研究,远远不如客家文化,如闽东文化、闽南文化。
如有识之士指出,客家民系,尤其是福建客家,原来并非是福建文化的主流。因为福建客家人入闽时间较迟,沿海平原开阔之地已无缘拥有与开拓,只有闽西山区比较荒芜,人烟稀少,于是他们的先民就在那里定居下来,繁衍生息。因闽西多丘陵被称为“丘陵上的民族”。闽西土地较贫瘠,不如闽东、闽中肥沃,适合种水稻、小麦、玉米、小米等五谷杂粮,论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属于比较落后的地区。在20世纪以前,中国并无“客家学”概念。尽管有人说,客家意识萌芽于清咸丰年间广东土客之间大规模的械斗,真正意义上的客家学奠基人是罗香林(1906—1978),其《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客家史料汇篇》等开创性著作,为客家研究之学奠定基础。近代以来,粤中因其地域开放包容,民主革命有孙中山举大旗,得全国风气之先,应者云集。又因海外客家众多,革命资金筹集以同乡之宜入手更容易号召。政治人物中,孙中山、廖仲恺、邓演达、邹鲁、张发奎、陈铭枢、陈济棠等人,为客家学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历史学家陈寅恪、顾颉刚、朱希祖、洪煨莲,社会学家潘光旦,语言学家罗常培,考古学家李济等人的跟进研究,催生了客家学学科建设。
总之,三明市核心的文化概念不是客家文化,而是闽中文化。
注释:
① 据史载,唐高宗总章二年(669),为了平定福建南方“蛮獠啸乱”,陈政、陈元光父子以及陈政的老母魏氏夫人及其他子孙入闽,走的就是仙霞古道。
② 黄玄,字玄之,将乐县人。善诗,与周玄齐名,时称二玄,官泉州训导。初从林鸿学,后林鸿弃官归,乃移居侯官县,从之深造。
[1]林国平,邱季端.福建移民史[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
[2]福建省轮船总公司史志办.福建水运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7.
[3]王晓暖.三明宋代书院考述[J].教育与考试,2009(5).
[4]王晓暖.三明辖境明清书院考述[J].三明学院学报,2009(3).
[5]余达忠.宋代杂居的活态遗存——三明大田县新发现地方戏《张大阔公戏》研究之一[J].戏曲艺术,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