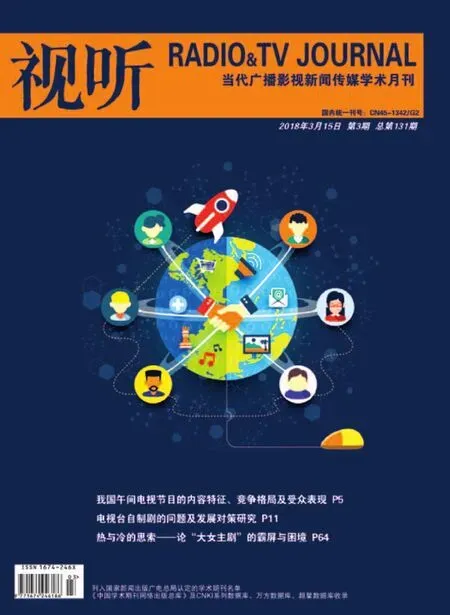人性善的呼唤与回归
——浅析电影《芳华》及其原著小说的人性书写
□ 邓雨青
“我的故事《芳华》对于多重、复杂的‘人性’的反映与揭露亦是深刻的。”①人性问题,是严歌苓小说及其改编影视作品一以贯之的创作主题。《芳华》以刘峰的“触摸事件”为核心展开故事,阐述了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人性状态,基于严歌苓对小说的“诚实写作”和在电影中担任的编剧身份,我们有理由相信二者在人性等主题观念的阐释上具有一致性,这两种媒介对故事的多形式表达为我们提供了更立体的参照。
一、刘峰:“善”的行使者
在“文革”题材中,严歌苓不仅生动刻画着人性的扭曲,也着重渲染人性的善。刘峰就是这样一个有雷锋特质的人物,书的开篇便细数他的付出:他帮小括弧挑水,担任女兵的毯子功教员……电影的处理更简洁典型:一句“欢迎全军的学雷锋标兵凯旋归来啊”奠定了刘峰的形象特征,伙伴都对他养成了习惯式的依赖:猪跑了、结婚买沙发、战友掉队时他们都会想到刘峰。就如电影所说:“那时候,我们歌颂默默无闻的英雄,歌颂平凡中的伟大,就是歌颂刘峰这种人。”
但“伟大”并不意味着没有需求与欲望,“童年啊,‘文革’看到父亲被折磨,那个十年……让我看到人性的各种各样的表演。”②学界对于人性的理解观点不一,从严歌苓的作品和观点中可看出:其人性观超越了“文革”时期“极左”思想下的“历史的”“具体的”“阶级的”相对的人性,也非是一元的“善的集合体”③,而是更接近王和《人类历史是人性展现的历史》的观点:“人性是人与生俱来的都有的特征,包括欲望、感情、理性、非理性,等等。”④刘峰的有血有肉集中表现在他对丁丁的情感中:他的迷恋从“卫生条”事件开始,他看林丁丁“是带荤腥的”,拥抱时他手下意识地伸进了衬衣……正如书中“他的欲求是很生物的,不高尚的。但他对那追求的压制……却是高尚的。……最终他对林丁丁发出的那记触摸,是灵魂驱动了肢体,肢体不过是完成了灵魂的一个动作。”⑤
人性是复杂的,那个时代激进的道德规范也遏制着本能需求的合理满足。这是刘峰苦难的来源,他扔弃了那象征褒奖的纪念品,代表着他看清了道理,但他依然会追寻阵亡士兵的陵墓、看望战友、帮助失足少女……这说明,刘峰曾经所做的奉献与付出不是对于集体的盲目跟从,更是基于他人性之善的自在抒发。刘峰对自己源于人性的那份善的坚守预示着人性的善在他意识中,在那个充斥着激进思想、人性压迫的故事语境里的回归。
二、何小萍(何小嫚):“善”的乞求者
刘艳在评析《芳华》时曾说:“何小嫚的成长史、成长叙事,反而蕴含了小说中极为繁富乃至诡异的人性书写,甚至超过了刘峰故事和叙事里人性书写的力道…”⑥电影的叙事调整为以刘何两人的故事为主线展开,可见,无论在电影还是在原著中何小萍(何小嫚)都是关键的人物。
小萍(小嫚)是个追寻爱而缺爱的人。“文革”拆散了她健全的家庭,电影中她想念着父亲,但终没有等到父亲。小说中她在继父家生活:藏食物、偷听、撒谎……“她母亲为维护那样一个家庭格局而必须行使的一套政治和心术伤害了她……是那一切使小曼渐渐变形了。”⑦身世和性格使她为战友所排挤。内衣事件中,电影版本有意隐去了内衣的归属,让集体对小嫚(小萍)的霸凌得到更鲜明的揭露。因为汗多被舞伴嫌弃,唯有刘峰同她伴舞时,“他把她搂抱起来,把她放置在肩膀上,这世界上,只有她的亲父亲那样扛过她。”⑧那个举动不含有缠绵的私心,却输入了同情与关怀,至此,善在小嫚的生活中复苏。
“一个从不被善待的人,最能识别善良,也最能珍惜善良。”唯她没有顺从集体批斗刘峰,没有心怀歹意地解读他对林丁丁的感情,所以她才用“抱”字来联系刘峰的触碰,这个字正是电影中刘峰对于自己行为的定义,它区别于“摸”字的猥亵意味。此时的她,对刘峰的善良唯有笼统的意识,尚无法理解刘峰扔弃奖品的缘由,也会因希图公众的关注而享受装病的演出。但当她经历了战争,被称为“战地天使”时,她恍然发现“标语上的何小曼似乎不是她”⑨,她的挣扎、打扮伪装都无用,“她不能变成任何人,她还要做她自己”⑩。经历着同刘峰一样的“否定”与“肯定”的转换后,她才感受到公众对于善的衡量与真实的人性间有多么荒谬的错位,这个角色也展现出一个缺乏他人关爱的人的性格将如何变异,被扭曲的人性之“善”又是如何地荒诞。
三、萧穗子、林丁丁、郝舒雯:盲从的旁观者
叙事上,小说呈现出多线索的抒情化、散文化特征,它更倾向于对历史中的小人物命运的感怀,在文工团集体中,萧、林、郝代表着主流的集体意识。在“触摸事件”里,她们站在自保的立场上,以集体的形式对自己的战友表示道德冷漠,他们的行为展现着人性的复杂:“所有人都暗暗地(也许在潜意识里)伺候他露出人性的马脚。一九七七年夏天,‘触摸事件’发生了,所有人其实都下意识松了一口气:它可发生了!原来刘峰也这么回事啊!”⑪“我们由于人性的局限,在心的黑暗潜流里,从来没有相信刘峰是真实的。”⑫这是人性对极端情景和道德过分政治泛化的自然反应,是对人性之善的漠视与质疑。
“现在让他用那只假手摸,人家都不愿意了。”电影里,萧穗子、郝淑雯同刘峰在海南偶遇,她们强调着刘峰对丁丁的举动是“摸”的意味的,认定刘峰仅是垂涎丁丁的美貌。她们不同于小萍(小嫚),对于刘峰的本性和他源自人性而散发的善,她们只有肤浅的认识。因为无论是在那个激进的年代还是新时期,她们蒸蒸日上的人生都没有能够反省人性的经历。
小说中相关情节发生的时间靠后,这时,三人的婚姻都以失败告终,她们面对了人性的挣扎与辜负后,才对当年“背叛即是正义”的错误有了痛彻的认识。书中萧穗子同郝淑雯对刘峰的寻找与关注,可以看作心灵对于人性善的召唤与思考,此时,她们基于丁丁的变化而对丁丁发出的嘲讽,更多的是对丁丁之流的人生的嘲笑,正如电影中所说的:
“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他们谈笑如故,但是不难看出岁月对于每个人的改变,和难掩的失落,倒是刘峰和何小萍(何小嫚),显得更知足,话虽不多,却待人温和。”
比起小说的悲剧结尾,电影中刘何有一个平和美好的结局,他们珍惜着人性中的那份善良,不在时代中迷失。小说中,萧穗子等旁观者未曾对“善”加以珍惜,忙忙碌碌后,生活几多失意。“好人”刘峰的早逝给她们带来的不仅是叹惋,更预示着人性之善在生活中的撤退。在惋惜、留念情绪的回忆中,我们对于人性善的呼唤与回归便有了更深的领悟。
注释:
①舒晋瑜.严歌苓:我们被“平凡即伟大”的价值观误导了[N].中华读书报,2017-07-26(18).
②严歌苓.写作每天都是在写向未知[A].严歌苓文集[C].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1.
③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性概念的阐释与考辨[J].外国文学研究,2015(6):16.
④王和.人类历史是人性展现的历史[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55.
⑤严歌苓.芳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33.
⑥刘艳.隐在历史褶皱处的青春记忆与人性书写一一从《芳华》看严歌苓小说叙事的新探索[J].文艺争鸣,2017(7):157.
⑦严歌苓.芳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66.
⑧严歌苓.芳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10.
⑨严歌苓.芳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30.
⑩严歌苓.芳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0.
⑪⑫严歌苓.芳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