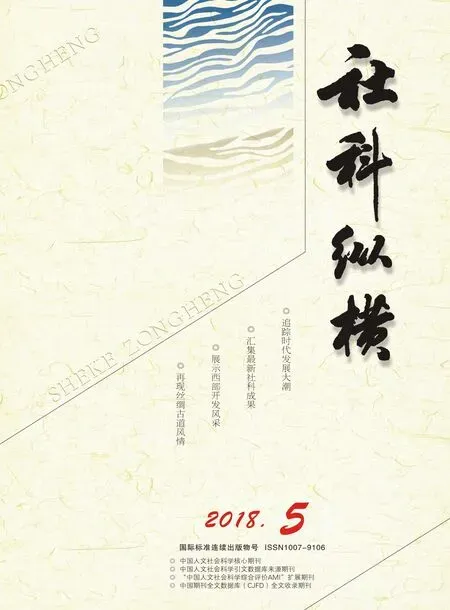会通汉宋
——郑珍、莫友芝学术渊源考
邹芳望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00)
郑珍(1806~1864)是清代贵州最杰出的学者和文人,在他还健在的时候,已被人誉为“西南儒宗”,甚而被称为“经师祭酒”,[1]与郑珍同学的莫友芝(1811~1871)同样高出侪辈,时人论西南学术,首推郑、莫。曾国藩即对二人推崇备至,咸丰九年致莫友芝函至谓:“侧闻阁下与郑君影息穷山,搜讨遗经,六合之奇,揽之于一掬;千秋之页,信之于寸心。每览尊著及子尹(郑珍字)兄所著书,窃幸并世幽人,已有绝学;西南儒宗,殆无他属,钦企不可言喻!”[2]此是私函,固不乏溢美成分,但郑、莫的学术声望,亦可窥见一斑。
郑珍、莫友芝生于嘉庆年间,但其成学都在道光以后。二人问学不主一家,均师出多门。其学术思想的渊源,从宏观上已多有学者论及,而二人学问之授受与思想之转变,细绎诸人文集,尚有诸多未发之覆,值得深入探究,今申论如下。
一、“道杨园而学孔孟”
郑珍十岁前由他的父亲授学,内容专在取士五经。郑珍曾自述:“珍幼不慧,而先人责望尤切,亲授诸经,课法尽善,能使所倍,久犹不忘记。”[3]他的父亲很严格,这使他早早打下了牢固的经学基础。
郑珍成学路上的第一次转折在他十六岁的时候到来,这年,他的舅父黎恂从桐乡知县任上奔丧归来。据说黎恂“归黔后以廉俸万金,购置书籍”,[4]继而有感于双亲俱逝,“引疾家居,尽发所藏书数十箧,环列仅通人,口吟手批,朱墨并下”,[5]他治学的标准是“经则以宋五子为准,参以汉魏诸儒;史则一折衷于《纲目》”,[6]可知其学得力于宋人处为多。郑珍从黎恂受学,得以“随发府君(黎恂)所藏书数千卷,纵观古今,殚心四部,日过目数万言”,[7]贵州由于环境的闭塞,书籍流传绝少,因此这一读书的机会非常宝贵。郑珍究竟读到了哪些书籍,史无明文,不能一一指出,但是并非全无线索。郑珍曾作《重刻〈杨园先生全书〉序》,回忆道:“余成童之年,舅氏雪楼黎公令桐乡归,从受业,乃始见《杨园先生全集》,读而爱之。后时举《见闻》《近古》二录中言行语,同辈率以不见是书为恨,余亦恨仅有手钞节本。”[8]可见郑珍曾读过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而且对他影响很大。黎恂在任桐乡知县时,“举杨园《愿学》、《备忘》诸篇谓邑士:士学程、朱必似此,真体实践,始免金溪、姚江高明之弊”。[9]由此可知,黎恂素来重视张履祥之学,郑珍能读到此书必非偶然,当是出于黎恂的有意教授。
莫与俦同样认为张履祥之学十分重要,他在为莫友芝讲述明清之际的理学谱系时说:“国朝两儒宗,曰潜庵、稼书。潜庵之学,承之新吾、苏门;稼书之学,开之蕺山、杨园。北方践履笃实,流弊绝少;东南曼衍空肆,极而为尽。三十三章见西来大意世界,得蕺山反之以实,杨园继之而更实,孔孟道乃复明。三鱼堂学术诸辨说,杨园尽已三致意焉,稼书特极力为善后策耳。顾诸先生绪论流传,天下翕宗,而杨园书极罕覯,知者亦鲜。然他日两庑俎豆,必不能少此一席也。”在这里莫与俦强调了张履祥在理学学风转为笃实的过程中所处的关键地位。他本人对张履祥十分推崇,认为张氏之书“陈事理近而旨远,辨大道疑似严而气和,其切于人,如布帛菽栗之于饥寒也,如鍼石药物之于疾病也”。因此,他要求莫友芝“留意求其本,自得师矣”。[10]父亲的教导无疑对莫友芝有很大影响,翻检莫友芝的文集,常可见到其引录杨园之语,甚而有“道杨园而学孔孟”的说法。[11]
莫与俦与黎恂不约而同地推重张杨园,绝非巧合。贵州的理学风气经过陈法的倡导,由陆王一派转而尊程朱。张履祥的学术思想正与处于学风递嬗之际的贵州士人的需求相契合,因而受到特别的重视。张履祥是刘宗周门下高弟,王汎森先生认为,刘宗周死后,蕺山学派一分为三,一派以张履祥、刘汋、吴蕃昌为代表,倾向程朱;第二派以陈确为代表,独树一帜;第三派以黄宗羲为代表,倾向陆王。[12]倾向程朱的一派以张履祥最有影响,他坚持刘宗周整齐严肃的理学作风,但对师说中和心学有关的倾向则采取回避甚至反对的态度。[13]《杨园全集》中载有其批评阳明之语,“姚江以异端害正道,正有朱紫、苗莠之别。其敝至于荡灭礼教”,[14]“姚江大罪,是逞一己之私心,涂生民之耳目,排毁儒先,阐扬异教。而世道人心之害,至深且烈也”,[15]可谓不遗余力。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莫友芝所谓“道杨园而学孔孟”中,杨园之道即理学脉络中学风由陆王转而为程朱的笃实之道,只有由此道出发,方可“学孔孟”而不悖。
但是郑珍习见杨园之书,态度却没有这么激烈。他说:“文成公之讲学,陈清澜、张武承、陆稼书诸先生详辨矣。此严别学术则尔。[16]至其操持践履之高,勋业文章之盛,即不谪龙场,吾侪犹将师之,矧肇我西南文教也。”可见他虽然“严别”阳明之学,但是对其“操持践履”、“勋业文章”仍然十分景仰,并且充分肯定王阳明在开创西南文教方面的功绩。这里可以看出郑珍与通常王学批评者的不同,他认为学术与道德不能混为一谈,阳明之谬只在学术取向,他的道德践履仍然不容置疑。
二、莫与俦:乾嘉汉学的引入与陶铸汉宋的学风
莫与俦在嘉庆四年成进士,这一科正是乾嘉学术极盛时的阵容,“座主则相国朱公珪、刘公权之、阮公元;又师事相国纪公昀、编修洪公亮吉;而同年友如编修张公惠言、主事郝公懿行、尚书姚公文田、王公引之,讲六书、明汉学者数十计”,因此莫与俦得以与闻“国朝大师家法渊源”,[17]“其称《易》惠氏,《书》阎氏,《诗》陈氏,《礼》江氏,《说文》诂释有段氏、王氏父子,盖未尝隔三宿不言”。[18]道光三年,莫氏任遵义府学教授,其后十九年没有变动,直至去世。他对遵义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据说“遵义之人,习闻君名,则争奏就而受业。学舍如蜂房,又不足,乃僦居半城市”。[19]郑珍在十八岁时从学于莫与俦,开始接触到清代汉学思想,他出色的表现引起莫与俦的爱重,“每与道乾嘉之际亲炙经师学问宗旨、高节轶事,以相劝勉,或中夜不休”。[20]郑珍至此开始有意于在学术上一展抱负,他的诗“我年十七八,逸气摩空盘。读书扫俗学,下笔如奔川。谓当立通籍,一快所欲宣”,[21]说的就是这一时期的情况。
莫与俦针对晚明以来心学的空疏之弊提出批评,他的救弊之方是切近笃实。他说:“论学必极穷神知化,令学者何处著手?吾辈只就日常行扩去,上半截境地,听其自然,高谈圣神何益?”[22]在他看来,“上半截境地”亦即所谓“性与天道”一类的问题,是可以存而不论的,合理的著手处是“就日常行扩去”。他认为清代考据之学比心学更高一筹,因为“三代教人不出六艺,本朝专门经生,书、数、礼、乐得圣人意者多,虽颇繁碎,而无过高之病、无证之谈,犹存圣人述信遗轨”。[23]“过高之论、无证之谈”是陆王心学所以致弊,也是清代汉学一派所以优胜的地方。但他绝不认为汉学是学问的止境,他已看出汉学“颇繁碎”的毛病,所以他教授生徒读书时说:“读书当求实用,程子谓学须就事上学,朱子谓须就自己分上体验。盖凡人之所为,六经子史皆有一定之则以处之,苟徒从事章句,虽读书,仍与未学等也。”[24]寻章摘句是汉学家之能事,但仅从事于此,就相当于“未学”,需要用程朱的笃实在弥补。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莫与俦治学的一套总体思路,即以汉学救心学之弊,以程朱补汉学之不足。
汉学与程朱理学是莫氏学术的两面,二则互相配合,形成其学术的整体。他教学“必举阎徵君‘六经宗伏郑,百行法程朱’之牓以树依归”,[25]换成他自己的话就是“学者立身行己,当法程、朱,辅以新吾、苏门、潜庵、稼书之笃近。若言著述,我朝大师相承超轶前代矣”。[26]这种融汇汉宋的学风,对他的弟子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后来莫友芝论学“不拘拘焉以门户相强”,[27]认为“门户在胸,虽大路椎轮,浸鲜有过而问焉者”。[28]郑珍论学说:“尊德性而不道问学,此元明以来程朱末流高谈性理,坐入空疏之弊,明于形下之器,而不明形上之道,此近世学者矜名考据,规规物事,险溺滞重之弊;其失一也。程朱未始不精许郑之学,许郑亦未始不明程朱之理。奈何岐视为殊途,偏执之害,后学所当深戒。”[29]所谓“行上之道”也就是莫氏所论“上半截境地”,“尊德性”、“道问学”就是汉宋学术的不同趋向,学者当兼容并蓄,不可“岐视为殊途”。观郑珍、莫友芝之言,都可看出莫与俦学术思想的影子。
莫与俦成进士后,师门濡染,精熟汉学,这是通常研究者都能看到的。但是他在遵义教授生徒,持论却在汉宋兼采,就少有人注意了。张舜徽先生看到了这一点,[30]但是并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事实上,莫与俦的这种学术主张,同样来自贵州本土的学术渊源。贵州自明代中叶起理学之风浓厚,明代专讲心学,自清代陈法以后一变而尚程朱。在这种风气笼罩下,读书人无不受其影响,因此莫与俦在中进士以前必定已有了相当深厚的理学基础。这不是猜测疑似之辞,我们能找到一些更切实的佐证。其中的关键人物是贵阳人谢庭薰,他曾经从学于陈法,是陈法的入室弟子。[31]他于乾隆十八年乡试中举后,两试进士不售,大调二等,被选为独山州训导。在独山时,“与麻哈艾茂,州人万邦英、蔡其发、黄琼、都其思等共任纂辑,成《独山州志》十卷”。[32]这些与谢庭薰相交游的士人,都是独山士人中的精英,尤其是其中的万邦英“于独山学术开拓最多”。[33]莫氏是独山望族,与万氏关系密切,“邦英从弟岁贡生邦仪娶于莫,为贞定(莫与俦私谥)姊”,而其子万全心“又学于贞定”。[34]可见两家在姻娅的基础上,复有学术的授受。谢庭薰官独山时,莫与俦尚年幼,但曾从万氏口中与闻谢庭薰所传陈法之学是完全有可能的。谢庭薰注意乡邦文献的蒐集整理,使“郑莫继起,得所取材”,[35]则又不光耳闻其教,并且进而钻研其著述了。可见莫与俦汉宋兼采的学风中确有本土理学渊源的一脉,而郑珍、莫友芝融会汉宋的主张也当在此萌芽。
三、程恩泽:学政对地方学风的影响
学政掌一省学校生员考课升降之事,对地方学术风气的影响很大,以学者而为学政,尤其能在地方掀动士风、造就人才。贵州学政中,除程恩泽而外,前有洪亮吉、后有严修,均能以学术相倡导。洪亮吉在任上“以古学教士,地僻无书籍,购经、史、《通典》、《文选》置各府书院,黔士始治经史”;[36]严修在任上开官书局,倡导汉宋兼采的学风,[37]尤与贵州士习相合。
程恩泽于道光三年莅任,郑珍即其所识拔的人才。道光五年,贵州共选拔贡士七十五人,郑珍在其中。程恩泽很欣赏郑珍文章,告诫他:“为学不先识字,何以读三代两汉之书。”[38]郑珍于是“大感服,益进求诸声音文字之源,与古宫室冠服之制”。[39]可以说郑珍的汉学由莫与俦启蒙,至程恩泽来黔才真正形成规模。程氏汉学功底深厚,在嘉道之世与阮元并驾齐驱,只是由于程恩泽死后遗稿散佚,后世难以窥见其学术的根底,使他声名不若阮元显著。程氏少从同乡前辈凌廷堪游,“约礼博文”,[40]及“居京师,益勤于学,天算、地志、六书、训诂皆精究之”,[41]其学是纯然汉学考据的路径。
郑珍在道光六年赴京师参加廷试不获选,还至湖南入程恩泽幕府,得以与程恩泽朝夕相处。程氏对郑珍“期许鸿博,为提倡国朝师儒家法,令服膺许郑”,郑珍“乃博综五礼,探索六书,得其纲领”。[42]后来同样担任过贵州学政的翁同书,“尝亲奉程侍郎之教”,认为“其能为侍郎之文者,遵义郑子尹一人而已”,[43]可见郑珍确得程恩泽的真传。我们看黎庶昌《郑征君墓表》所述郑珍后来的论小学“形、音、义”的文字,有源有流,“粲然一出于正”,[44]其渊源当以得于程恩泽者为多。
但是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汉学家法并非立即就与郑珍自幼习闻的理学思想水乳交融。汉宋两学在方法取径、价值追求上的巨大差别,绝非一时可以弥合的,这种两相歧异的思想给郑珍带来了极大的困扰。道光十四年,亦即郑珍离开程恩泽幕府的七年以后,郑珍致函程恩泽,从中可以看出他思想上的彷徨。文繁不录,具载郑珍《巢经巢文集》卷二之中。
信函中透露的内容令人感到惊异。道光十四年,郑珍已年近而立,但他自呈此时的思想状态是“狂惑跳叫,中无自主”,原因在于“冥冥无指导可恃”,所以急切需要他的业师开示“为学之方”。我们之所以认定他这种思想上的彷徨是由汉宋两学的冲突造成,是因为如前所述,郑珍自幼生长于理学风气极盛之乡,在受业程门以前又得到黎恂、莫与俦系统的程朱理学指导,他本人的思想已经打下了很深的理学根基;但是,在受业程门以后,他的思想逐渐趋向于汉学,以致于痛诋宋后学术为“凭臆拟度”、“歧出泛滥”,并自认从前所学为“剽窃涉猎”,这种前后的巨大差距“实原自先生”,亦即由于汉学思想对郑珍从前所习程朱理学的冲击造成的。他自己能清楚感受到这种思想上的冲击,所以想在二者中作一选择,“意寻一古人之路”,“别声音,辨文字”,“以字读经”又“以经读字”,但是又怕“行之已远,忽觉路非”,到时再欲改变,精力已有所不及,“岂非冤哉”![45]
虽然莫与俦以“会通汉宋”的治学方法教士,但这一法门显然不能在短时间内平息郑珍思想世界内的纷争。书缺有间,我们今天已很难找出郑珍弥合汉宋两学的具体学思历程。观其后郑珍的论学诗《招张子佩琚》可知,他这时的议论已趋于持平,程朱的格致“非冥悟”,而是“祖周实郊郑”,学程朱而“谈性命”,只是“俗士”所为,这一见解似乎已回到莫与俦以程朱之学为笃实的路上来了;同时,他也认为清代的“绝学”“谈经一何盛”,汉以前的典籍“字字经鞫证”,其成绩“直耸高密堂,上与日月并”。[46]
到郑珍晚年,程朱理学在他本人的学术话语中重又占据第一义的位置。他读《四书集注》和《近思录》,“二书道理,历历在目前滚过”,[47]其子郑知同说他“晚年于道益深”、“慎重道学,精益求精”,[48]可知他折中于义理的治学取向已完全确立,而他思想的归属已全在程朱理学了。
参考文献:
[1]翁同书:《巢经巢诗钞序》,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附录五,成都:巴蜀书社,1996:1507.
[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三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314.
[3]凌惕安:《郑子尹(珍)先生年谱》,香港:崇文书店,1975:25.
[4]张其昀主编:《民国遵义新志》,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成都:巴蜀书社,2006:168.
[5]郑珍:《巢经巢文集》卷第五,《郑珍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151.
[6]郑珍:《巢经巢文集》卷第五,《郑珍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151.
[7]郑知同:《敕授文林郎征君显考子尹府君行述》,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附录三,成都:巴蜀书社,1996:1475.
[8]郑珍:《巢经巢文集》卷第三,《郑珍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73.
[9]郑珍:《巢经巢文集》卷第五,《郑珍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151.
[10]莫友芝:《校刊〈张杨园先生集〉序》,张剑等编《莫友芝诗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570.
[11]莫友芝:《娱藼台记》,张剑等编《莫友芝诗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646.
[12]王汎森:《清初思想趋向与〈刘子节要〉——兼论清初蕺山学派的分裂》,氏著《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60—269.
[13]何俊、尹晓宁:《刘宗周与蕺山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22.
[14]张履祥:《答沈德孚》,《杨园先生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85.
[15]张履祥:《备忘》,《杨园先生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1138 页
[16]郑珍:《巢经巢文集》卷第二,《郑珍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63.
[17]莫友芝:《清故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县知县贵州遵义府教授显考莫共行状》,张剑等编《莫友芝诗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768-769.
[18]曾国藩:《翰林院庶吉士遵义府学教授莫君墓表》,《曾国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310.
[19]曾国藩:《翰林院庶吉士遵义府学教授莫君墓表》,《曾国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309-310.
[20]莫友芝:《清故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县知县贵州遵义府教授显考莫共行状》,张剑等编《莫友芝诗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768.
[21]凌惕安:《郑子尹(珍)先生年谱》,香港:崇文书店,1975:25.
[22]莫友芝:《清故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县知县贵州遵义府教授显考莫共行状》,张剑等编《莫友芝诗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768.
[23]莫友芝:《清故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县知县贵州遵义府教授显考莫共行状》,张剑等编《莫友芝诗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768.
[24]莫友芝:《清故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县知县贵州遵义府教授显考莫共行状》,张剑等编《莫友芝诗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767.
[25]莫友芝:《答万锦之全心书》,张剑等编《莫友芝诗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619.
[26]莫友芝:《清故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县知县贵州遵义府教授显考莫共行状》,张剑等编《莫友芝诗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769.
[27]莫祥芝:《清授文林郎先兄郘亭先生行述》,张剑等编《莫友芝诗文集》附录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1116.
[28]莫友芝:《校勘〈中庸集解〉序》,张剑等编《莫友芝诗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559.
[29]郑知同:《敕授文林郎征君显考子尹府君行述》,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附录三,成都:巴蜀书社,1996:1482.
[30]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97.
[31]凌惕安:《清代贵州名贤像传》,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202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37.
[32]凌惕安:《清代贵州名贤像传》,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202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37.
[33]万大章:《独山莫贞定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27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487页.
[34]万大章:《独山莫贞定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27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487页.
[35]凌惕安:《清代贵州名贤像传》,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202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37.
[36]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三五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11761.
[37]严修撰,高凌雯补,严仁曾增编:《严修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90:46-48.
[38]黎庶昌:《郑征君墓表》,《拙尊园文稿》卷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00页.
[39]黎庶昌:《郑征君墓表》,《拙尊园文稿》卷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00页.
[40]阮元:《诰授荣禄大夫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春海程公墓志铭》,《程侍郎遗集·墓志》,《粤雅堂丛书》丛书本,第1页.
[41]阮元:《诰授荣禄大夫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春海程公墓志铭》,《程侍郎遗集·墓志》,《粤雅堂丛书》丛书本,第5页.
[42]郑知同:《敕授文林郎征君显考子尹府君行述》,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附录三,成都:巴蜀书社,1996:1475.
[43]翁同书:《巢经巢诗钞序》,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附录五,成都:巴蜀书社,1996:1507.
[44]黎庶昌:《郑征君墓表》,《拙尊园文稿》卷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01页.
[45]郑珍:《巢经巢文集》卷第二,《郑珍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35-36.
[46]郑珍:《招张子佩琚》,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前集卷二,成都:巴蜀书社,1996:160-161.
[47]郑知同:《敕授文林郎征君显考子尹府君行述》,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附录三,成都:巴蜀书社,1996:1482.
[48]郑知同:《敕授文林郎征君显考子尹府君行述》,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附录三,成都:巴蜀书社,1996:1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