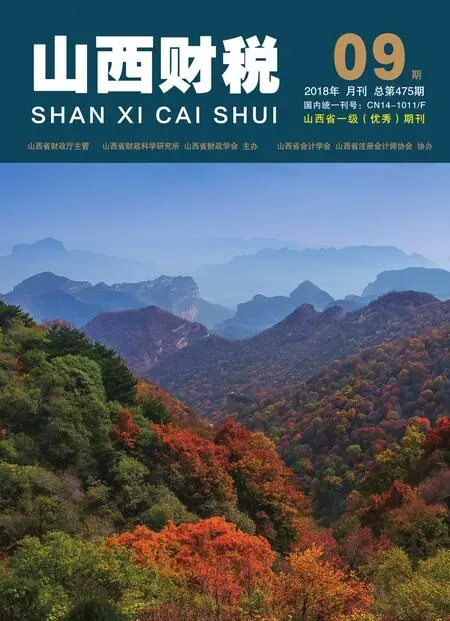山西省生态产品供给机制研究
□ 王晓东 郝兆裕
生态产品、工农业产品和文化产业产品被认为是人类三大产品。工业发展所产生的污染和生态环境的矛盾越来越严重,虽然公众依靠经济发展逐渐告别了物资短缺,但是生态产品的短缺已然成为了经济稳健发展的瓶颈。山西省经济一度以煤炭为主,粗放型经济模式导致了生态环境恶化,生态产品短缺,如何增加生态产品供给亟待解决。
一、生态产品的供给机制
生态产品和多个学科有关,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态学和经济学等,《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把生态产品界定为:“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宜人的气候”。从宏观角度来看,生态产品是为了保护生态安全,保持生态调节功能,它是良好的空气质量、清洁的水资源、高覆盖率的森林、适宜气候和与人类劳动看似没有关联的自然产品;从微观角度看,生态产品是清洁、低耗能、低污染、能循环利用的产品,如生态工业产品、绿色产品、有机农产品、生态材料等。
(一)供给主体
1.政府。政府主要通过财政进行生态补偿,如政府进行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治理、保护森林湿地,以增加生态产品产量。政府为生态产品提供制度供给,政府会出台相关的法律规定或政策,鼓励相关生态产品的生产。政府直接出资提供生态产品,以保证生态产品供给。
2.企业。企业利用生态产品的生态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例如,新煤炭企业通过清洁能源的生产和原煤的深加工,焦化和剩余化学产品的回收、煤炭气化、液化和发电等,能够从生态产品供给中获利,故而提供生态产品。另外则是环境领域的企业,如垃圾处理企业,通过垃圾处理,减少城市垃圾,变废为宝,以此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3.公共团体。公共团体包括环保组织,救援组织和扶贫组织,这些组织以公益为起点,在当地进行宣传,把“保护生态环境又致富”的思想进行传播,提倡供给生态产品便是发展。这些组织通过公益活动,投资生态产业,把盈利的一部分再次投入公益事业。
4.个人。个人提供生态产品主要是让其生产生态产品,如林区农业,让农户退耕还林还草。经营林区农业,一方面直接让农户生产生态产品,带来经济收入;另一方面也改善生态环境。或者鼓励农户植树造林,给予经济补助,能直接提供生态产品。
(二)供给机制
1.价格机制。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价格机制可以起到引领和反馈的功能。生态产品价格应由资源价格、生产成本、环境成本、赋税和社会平均利润构成。资源价格依据资源获得的难易程度、市场供求状况而定;生产成本即为生产生态产品过程中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之和,如净化水源,其中涉及到政府行政部门管理、监督成本;环境成本主要包括改善、修复、恢复生态环境所支付的各种费用,如矿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的覆土、绿化、回收再利用的费用、垃圾处理的费用等;赋税包括缴纳的各种税收;社会平均利润即一般企业经营过程中所获得的平均利润,若企业不能获得平均利润则不会从事生态产品的生产。
2.交易机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生态产品的交易机制应以市场经济的规律为基础,有形的生态产品能直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而无形的生态产品需要产权化、价值化和商品化,通过价格机制进行定价,以政府作为媒介,购买方应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供应方则是地方政府或县级政府。
3.政府财政补偿。政府的财政补偿主要是为了激励生产者提供生态产品,是市场的激励机制。政府的财政补偿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直接的财政补偿即政府向生产生态产品的企业和农民提供资金、技术指导,维护、恢复当地的生态自然环境;间接的财政补偿则是政府通过向社会大众募集资金,地方政府投入资金,给提供生态产品的企业和农户进行补偿。
二、山西省生态产品的供给现状
(一)山西省生态产品供给不足
山西省水土流失问题是困扰山西省生态化建设的一大问题,土地水土流失情况严重,约占山西省总面积的69.2%,占全省山地、丘陵总面积的88%,水蚀情况同样不可小视,面积为9.3万平方千米。从水资源环境来看,2016年全省地表水质中度污染,11个地级市生活饮用水水源,总体水质达标率为89.3%,阳泉、临汾水质不达标。空气质量方面,2017年12月份环境空气质量指数,太原8.25,吕梁9.36,临汾9.97,运城10.89,主要污染物是PM2.5,其他污染物还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等。植被覆盖方面,2015年造林面积达280.94千公顷,2016年植树造林266.69千公顷,同比减少5.07%。能源利用方面,2016年一次煤炭能源生产56480.85万吨标准煤,但是回收能源却仅为516.18万吨标准煤。
(二)生态产品定价困难
当前山西省生态产品市场化的困境主要体现在生态产品定价难这一点上。公共产品存在正向外部性,搭便车效应会使公共物品供给低于适当水平。由于生态产品的供应具有完整性、不可分割性,干净的空气、清洁的水源等无形生态产品的定价困难,生态产品的价值、成本、环境成本难以估算。虽然已经出现了市场价值法、条件价值法,但这些方法缺乏科学的观测和评价体系,在实际操作中行使困难。
(三)生态产品供给机制存在弊端
虽然政府是生态产品的主要供给者,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上级政府通常会把生态供给任务委托给下级政府,例如省级委托市级,市级委托县级,县级又委托乡镇级,层层委托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问题,例如政府补偿问题,造成对一些地区的重复补偿和对一些生态产品供给不足地区缺失补偿。层层传递过程中,会出现下级糊弄上级,骗取补偿金等问题,影响市场的资源配置。生态产品的正向外部性将导致企业或私人社会收入大于私人收入,如果没有办法对差额进行弥补,将会减弱私人和企业供给生态的积极性。
(四)缺少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制度
目前我国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颇多,而关于生态产品生产方面的法律仍不足,资源的整体性和综合性难以得到保障,缺少对生态产品生产的实体与程序的相关规定。《山西省环境保护条例》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要增加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并采取保护环境的经济技术和政策,辖区环境质量是其工作业绩的考核内容。但是采取何种方式投资,采取何种措施和政策,谁为供给主体,环境质量如何鉴定并没有具体的规定,缺少稳定的、持续的制度环境。
三、山西省生态产品的供给路径
(一)生态购买供给路径
当生态环境持续退化和环境破环严重到无法自然恢复时,只能人为调控,恢复和重建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生态购买即通过政府购买生态产品,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生态产品的供给,实现了政府主导与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机结合。政府作为需求方,集体、农户成为供给方,生态购买增加了供给主体的收益,使私人部门积极参与生态产品的生产,实现生态致富。
以山西省岚县购买式生态扶贫为例,2015年岚县将造林绿化和精准扶贫相结合,鼓励农户组织造林合作社,通过实施购买式造林生态扶贫工程,既帮助群众脱贫,也同时促进了绿化环境,改善了生态环境。购买式生态扶贫将造林资金和任务向农村贫困村、贫困户靠拢,引导有造林能力的贫困农户和造林合作社参与生产,验收合格后政府回购,通过购买社会化服务,让贫困户参与林地的培育和管理,雇佣贫困户,实现就业增收,稳定脱贫。首先,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要求民众到绿化,到民众主动绿化,让政府、企业和贫困农户共同获利,实现了有效的统一。其次,政府要求合作社在种植、管理林木时,使用有技术的贫困农户,使贫困的农户得到了收入。最后,促进了育苗产业的发展,由当地人决定苗木种类,理顺了育苗和造林的关系,推动了产业发展。生态购买在山西省实行的可行性,作为一种生态产品供应机制,同样适用于生态工业品等有形的生态产品。
(二)市场直接交易供给
在人口增多、经济增长和全球生态变化的今天,空气和水也被认为是经济活动的基本生产要素,但作为公共物品的水和空气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当其被视为基本生产要素时,它必须遵循产权规则。科斯定理中,如果商品能界定产权,那么就能转变为私人所有。产权化后,能够设立一些条件使用生态产品,如付费。
1.排污权交易。在污染物总量不超过规定排放量的前提下,通过某些地区的货币交换将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调整污染源,调节排放数量。交易市场的污染物,需要排污的企业根据自身利益自主确定排放标准,交易排污权限。这种交易排污量的方式可以看作是对无形生态产品的供给,比如干净的水源,清洁的空气。根据2018年2月份山西省排污权交易情况来看,山西省共完成了43宗排污权交易,成交金额1490万元,二氧化硫261吨,二氧化氮5吨,二氧化氮化合物428吨,烟尘43吨,工业粉尘87吨。
2.碳交易。工业发展产生了大量温室气体,发达国家无法完成《京都议定书》中对于降低碳排放的标准时,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支付费用,获得在发展中国家减少排放的额度,购买到的减排额度用以减缓温室气体所产生的效应,例如在植树造林、管理森林、恢复植被中达到减排目标。山西省应加快建设林业碳汇交易市场,开发林业碳汇项目。据计算,每亩林地可产生1吨/年碳汇量,碳汇交易价格30元/吨,山西林业资源丰富,开展碳汇交易,不仅可以改善生态环境,而且也提高了林业附加值,带来巨大经济价值,为修复生态环境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
(三)经营方式资本产业化
针对当前供给主体不明的问题,生态产品供给可以通过PPP即公私合营模式来实现。通过政府与民营企业合作在PPP模式下供应生态产品,将生态产品供应项目外包,由专门生产者管理生态产品或政府直接购买生态产品的方式,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激励生产者供给生态产品。PPP模式将生态产品部分或整体的生产转向市场,包含合同外包模式和特许经营模式。合同外包模式中,地方政府利用专项资金委托企业或者个人进行生态系统修复,如山西省孝义市采煤沉陷区的生态修复;特许经营模式中,政府以合同的形式,明确企业或个人从事指定生态产品的生产,特许经营者向政府支付费用,如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棚户区改造等。近几年山西省也在积极推进通过PPP增加生态产品供给,但是项目规模和数量都偏小,因此在撬动社会资本大力推进PPP项目时,财政补贴、投资补助、贷款补贴等金融优惠政策也要配套实施,实现多元化融资,合理配置资源。
(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制定完整的法律法规,使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把环境因素纳入决策领域,对提供生态产品的供应者进行价格补偿,鼓励其生产生态产品。要根据我国生态法律相关规定,实行一套合理合法,适合山西省的生态法律法规,增加对生态产品生产方面的实体和程序的相关规定,明确政府的监管内容。尤其要完善关于PPP项目实施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合同主体、权利和义务,确保生态产品的有效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