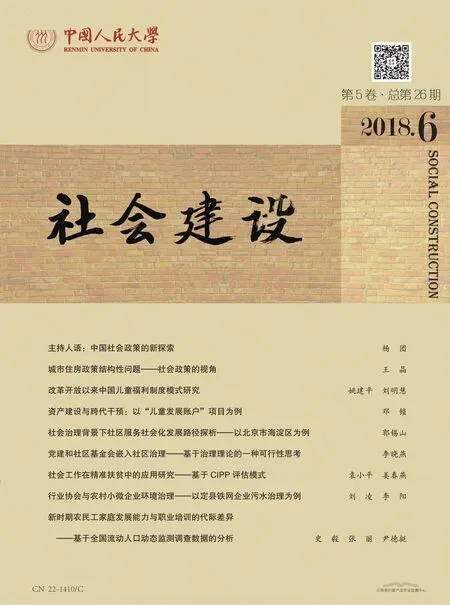主持人语:中国社会政策的新探索
杨 团
中国的社会政策尽管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从欧洲、日本引进并且进入了大学课程,但是在新中国建立后近30年随着社会学被取消而摒弃。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引起老百姓不满,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中断了几十年的社会政策才得以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和政府议程。
可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社会政策演变的轨迹是跟随性、被动性的,即跟随党和国家一段时期的政策倾向而变。改革开放早期,国家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时期的“社会政策”全部打上经济烙印,再分配统统向经济增长倾斜。而社会问题堆积到不得不解决时,政府只能采用临时性的行政手段应对。这种状况导致了社会政策的滞后,社会问题的加剧。社会政策作为国家针对社会发生的重大不公正问题提出的预防、解决方案或治理方略,它需要以科学的态度从实践经验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理论思路和操作方法,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应当同步进行,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应当兼顾推进。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局面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正在改变。
本专题的三篇文章,无论住房保障、儿童福利还是资产建设,均可在一定意义上证明,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发展史,同时也是政府面对大量社会不公问题,以行政干预、对策手段应对问题为起点,逐步走向基本价值、基本方式的科学化、系统化的一部中国社会政策成长史。这部成长史四十年来只能算是完成了萌芽期和成长前期的工作,更艰巨的事业还在后面。而现阶段中国社会政策凸显的独特性,是被融入党和政府的政策,以及被融入经济政策。
住房是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它与其他服务性质明显的民生保障例如养老、医疗、就业区别显著。受保障的主体即房屋居住者并非在消费过程的同时参与生产过程,并不同时具备消费者和部分生产者的双重身份,从而也与其他保障的受保主体拥有完整的自主决定权不一样,房屋居住者住房消费的功能与住房生产的功能是分立的,是由不同的主体完成的(就连农村住房现在也大都不是自己建造的了),这导致住房消费与住房生产形成性质完全不同的产业,是服务业和制造业。尤是社会走入现代化阶段,城镇化、工业化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大规模住房建设造就了房地产制造业这一高利润产业。这说明,住房这类具有跨界效应的物品,很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另外,住房的属性复杂,有自建自用的非商品,有他建商用的商品,有“居者有其屋”“寒士俱欢颜”的福利供给属性的准公共产品,还有供给中等收入以上人群不同层级需要和偏好的市场商品。住房的双重属性导致其政策定向比养老、医疗、就业、教育等政策的制定要难得多。在单纯市场的经济政策还是融入市场的社会政策的两种定向选择中,中国终于选定了社会政策定向,这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不过,社会政策定向并不排斥经济、排斥市场,并不是将住房视为单纯性质的产品,而是融入经济,融入社会投资,融入个人资产建设内涵,符合社会公平、公正价值观。中国的住房政策是市场商品和准公共产品分类实施的政策。
王晶的文章从住房的双重属性出发,进行了社会政策分析,并据此提出政府的社会政策的干预不可简单化,而要从双重属性出发,寻求理论上说得通,操作上可施行的第三条道路。她通过住房结构性问题的社会政策分析提出,住房供给上的利益诉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存在目标冲突,而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异和目标偏移的根源在于税制改革,中央政府取多付少,导致财政能力不足的地方政府,只能寻求其他途径弥补公共支出不足的缺口。有意义的是,她从住房双重属性的社会政策分析出发,提出住房政策要满足多目标,就要为涉及住房政策的多部门设置“放弃强力控制,为不同部门设立边界,给予政策支持”的“赋能”型特征的社会政策。这类社会政策不仅能容纳多主体而且兼顾市场功能和政府职能。而中国的住房社会政策要朝向“赋能型”的方向转型,关键是要解决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在住房问题的上权责不平衡的问题。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王晶提出的探索方向是进行土地制度改革 ,尽管她并没有明确提出如何改革,但暗含的方向可能是让乡村流动到城市的人口用自家废弃不用的宅基地和房产换取城市的住房及其他保障,这在地方政府对土地使用的实质的决策权之外,让城乡流动人口对自己在乡住房资产的决策权凸显了。尽管这个设想还需要兼顾多方利益的制度目标设计和具体的政策实施设计,以及运用试点的方法进行设计检验和不断试错,不过,它与某些研究提出的宅基地直接进入土地买卖市场目标和目的不同,所以,政策与制度的设计一定是不同的。
王晶给予我们的启迪是,住房政策的新的进路,可能是将传统政策延伸到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的领域,解决长期处于城市非正规就业地位而与正规社会保障无缘的农民工群体依照自己的意愿在城市落户的问题,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同时兼顾乡村新集体的资产建设和新集体经济兴旺发达的目标,从以个人收入和以政府补贴为本的政府直接干预型住房政策,走向以个人和集体资产建设和资本流通与收入、补贴并举,利用市场机制,干预手段前移的赋能型社会政策。
我国儿童福利政策的中国特征较之住房政策更为明显。计划经济时期,儿童福利无需专门提出,因为,城市人口全部进入国家直接举办的机关、事业、企业三大公共网络,儿童福利都由三大网隶属的各个单位直接操办,农村由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操办,从城市三大网漏下的极少数无人照看的孤残儿童,才送到城市举办的福利院养育。而改革开放以后,三大网突破了一个半,企业网算一个,事业网算半个,机关网也因改革不再自办托幼所,农村因包产到户,集体经济基本垮台,孤残儿童和孤寡老人都没人养了。再加上农村本来就大大过剩的劳动人口纷纷到城市打工,大批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谁来养育?事关近亿儿童的生活和教育的问题俨然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
姚建平、刘明慧的文章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重点讨论了了我国儿童福利政策和制度的变革。该文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儿童福利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从计划体制下的极少数孤残儿童的机构养育转变为适度普惠型政策,对更大范围的流浪儿童、留守儿童、贫困儿童贫困、残疾儿童实行面向家庭儿童福利供给的转变,形成了涵盖各类困境儿童的社会保护体系。而他们对儿童福利政策的讨论并不止于此,而是针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未能达到提升生育率的预期的实际情况,提出儿童福利政策需要从适度普惠型过渡到完全的普惠型,因为前者主要关注困境儿童,而没有面向所有的家庭。而缺乏普惠政策,导致家庭养育和教育成本过高,提升生育率是不可能的。于是,倡导普惠型儿童福利政策,成了实现国家提升生育率目标的手段。
而被视为社会政策传统领域的儿童福利政策,最近20多年以来,受到源于美国迈克尔·谢若登教授的试验而后波及全球的资产社会政策的影响,走向以儿童发展账户为工具的资产建设为本的新型社会政策。邓锁的文章就揭示了中国在这方面的创新试验。
传统社会政策是以收入为本,而资产社会政策利用个人发展账户这个工具,进行有限制条件的资产配额方式界定和管理资金,使之转化为一种可持续产生满足需求的实物、劳务或收入的资产,这样,就将需求—产品供给—收入提供的倒梯形非平衡结构转变为上下对称的平衡结构,它改变了社会政策的传统范式,对经济和社会都在产生着难以估量的长期影响力。
邓锁的文章通过陕西白水县和西安市的两个“儿童发展账户”项目案例研究,揭示了以资产建设为本的新型社会政策试验在中国儿童福利传统领域出现的新景象。它打破了我国扶贫政策将成人和儿童分立,成人用产业扶贫,儿童用福利收入和服务扶贫的传统做法,以设立儿童发展账户的方式鼓励家长对所补贴的现金进行储蓄,激励家长为孩子的未来进行持续性的资产建设,这让贫困家庭的脱贫有了更加切实的努力目标,同时也通过社会工作的辅导让家长学到了家庭康复的技能。家庭康复不再是传统的儿童福利消费,而是进入了家庭进行自主性资产积累和规划的生产性概念之中。两个“儿童发展账户”项目的实验还形成了家庭、社会组织与金融、民政、残联、扶贫办等政府部门之间相互配合的社会合作生产模式,以及医疗康复、护理、社会工作等不同专业主体相互连接的专业合作生产模式。
尽管这两个案例的规模小,实验时间一个过短,一个尚未结束,研究还很初步,不过,对于我们这些亲历资产社会政策在中国研发历程的学者而言,看到坚冰已经打破,路线已经开通,资产社会政策终于在中国的大地上长出了幼芽,仍然为之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