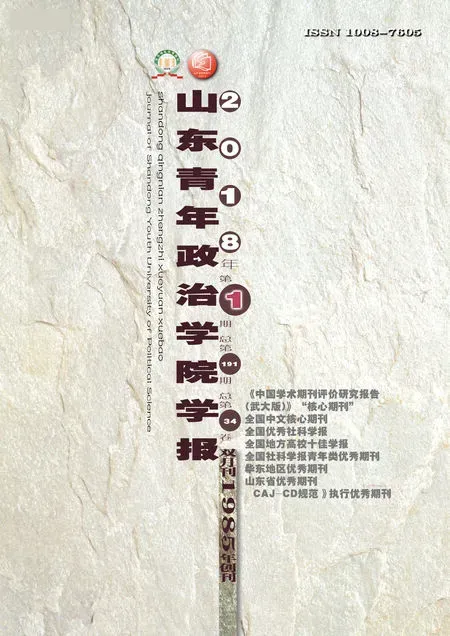从古典神话到现代隐喻
——论电影《西游伏妖篇》中的人物性格塑造
冯敬远
(山东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济南250014)
周星驰新作《西游伏妖篇》自上映之初便备受瞩目,并在大片如云的春节档斩获15亿票房。作为同期诸多喜剧电影中的一道独特风景,它既不同于成龙的“大团圆式的”喜剧电影《功夫瑜伽》,更不同于王宝强纯粹搞笑式的《大闹天竺》,它以对经典神话原型解构的后现代主义色彩浓重的喜剧创意实现了对“人性的真实再现与表现”[1],获得了低碳艺术①的审美品格。
众所周知,我国古典名著《西游记》是以着力弘扬典型形象孙悟空所彰显的不畏强暴、追求自由、征恶扬善等主流精神价值的神话故事。《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电影作品也基本上围绕着这一基本价值取向来进行现代影像编创的。然而,跟这些改编作品相比,电影《西游伏妖篇》的整体审美风貌则迥然不同。它完全解构了经典原作中主要人物形象的固有性格,并将其赋予了更具人性张力的现代新质。
首先,在电影中,唐僧一改经典的潜心修法的道德楷模形象,变成了一个优缺点俱在的世俗凡人。电影开场,梦中的唐僧在小人国受到众人的追捧并被加封“终生成就奖”。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分析,这正是自我需求在潜意识里的投射,追名逐利自我膨胀,一个与众不同的唐僧形象由此跃入眼帘。“人的主要的与基本的动机与动物的一样,是利己主义。亦即迫切要生存,而且要在最好的环境中生存的冲动。”[2]百战怪咔国一段,为了获得取经路上的活动经费,师徒四人沿街卖艺,为了两文钱出头表演。孙悟空一段表演,配以西游经典背景音乐,拉开了电影的戏谑之旅。为了显示自己为师的风范来,唐僧强行当众呼喊孙悟空为“臭猴子”,口中不断重复着“这孙子惯不得”,当后者暴走时唐僧立刻唱起儿歌来控制局面,这也为之后唐僧失声面临险境做了铺垫。作为西游取经的领导人,唐僧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各色妖魔鬼怪,还有团队内三个各怀鬼胎的徒儿:性情暴戾可怖的孙悟空,虚伪好色搬弄是非的猪八戒,高冷漠然的沙和尚。师徒四人之间经常是尔虞我诈,当孙悟空假意要了结唐僧,猪八戒和沙和尚却在一旁暗中较劲:咬啊,咬死他,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为了生存唐僧不得不谎称自己会如来神掌,怨恨时会念咒羞辱孙悟空为臭猴子。与原著中八戒取钵化斋的开场不同,盘丝洞一段的开场被置换成徐克经典作品《倩女幽魂》燕赤霞同款伏魔师在白骨精府邸降妖除魔的故事。此时山谷的另一侧,唐僧正手持曾束缚孙悟空百年的藤蔓鞭笞后者,进行团队管理。然而每当危险来临,唐僧仍旧第一时间求助孙悟空,伪善的赶走自己的徒儿让他们出去反省“想不明白不要回来”,蜘蛛精现原形时立刻原地改口“你们回来”,而当孙悟空杀死蜘蛛精时,他立马伪善现形为“除魔靠的是真诚,度妖向善是不一定要靠打打杀杀的”,“我还没表演你就买单了。”没来得及显摆的失落感跃然显现。失声后无法通过儿歌三百首控制孙悟空一段将唐僧作为团队管理者的狡黠体现的尤为淋漓——无意间听到徒弟三人打算了结自己,他佯装不知退居次位去悬崖祈求佛祖,在一系列巧合下被误认为会使用如来神掌侥幸逃脱厄运,在被八戒听到自己失声的事实后他威逼利诱,先谈感情再威胁之“师傅认识很多杀猪的”,同时假借悟空之手惩治了搬弄是非的二徒弟猪八戒,也将“祸从口出,沉默是金”的为人处世之道传达出来。影片通过塑造唐僧这个人物符号,将现实语境下的胆小怕事、利己虚妄的活生生的社会人形象生动的描绘出来,展现了真实具体的人性。艺术作品之所以着迷于展现人性本真,正是由于人性是复杂的多面体,神秘而富有魅力。在充满异域风情和童真童趣的背景音乐中,师徒四人一行来到了比丘国。行为举止如幼童的比丘国国王要求唐僧现场表演一段驱魔法术,被拒绝后恼羞成怒想要处置后者,唐僧无奈只得疾呼“谁都不要拦着我,我非得给国王露两手,我找个地方随便补个妆就来” ,使用听话符被孙悟空戏耍失手打了国王,在城门外师徒兜底一段完整全面的体现了唐僧管理团队的厚黑学。面对即将离开的孙悟空,他以退为进下跪认错收买人心,与孙悟空称兄道弟,成功化解了团队危机,将唐僧权谋一面表现的尽致淋漓。
“只要一种艺术作品让人们领略到了本真的人性力量,那么无论这种艺术所依托的爱情主题本身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是净化心灵的艺术、陶冶情操的艺术,启迪思想的艺术,也就是低碳的艺术。”[3]周星驰的《西游伏妖篇》对原著进行了解构,给凡人唐僧安排爱情桥段,使其情感经历更接近一个真实的凡人,更立体将唐僧形象呈现在银幕上。三打白骨精桥段的“白骨精”小善,在大殿上翩然起舞一段犹似惊鸿翩然,《一生所爱》响起,电影同时以回忆蒙太奇交叉着段小姐起舞的画面,唤起了唐僧对旧爱段小姐的情谊,一个推镜头特写将唐僧内心的波澜不定展现给观众。离开后的唐僧全副心神都在小善身上,途中折返一路奔向君王求赐予小善同行。而电影前作《西游降魔篇》的剧情也已经交代,作为心系唐僧的驱魔人段小姐被尚未归化的孙悟空活活打死,给两人亦敌亦友的师徒关系做了交代,因此在续集中当孙悟空要棒打小善时唐僧才会奋不顾身的冲上前去替小善受难并喊出那句“你又想杀死我心爱的人么?”唐僧拼死守护挚爱的行径,让爱情这一永恒主题恢弘起来。汤显祖曾在《牡丹亭》中为爱情高歌:“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4]将爱情赋予决绝而伟大的力量,危难时牺牲性命也要保护挚爱,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么一个有痛苦、有执着、有牵挂的修道之人。当最后小善身份昭然,唐僧也并未因为她的身份而有所嫌隙,仍旧替她超度,以期小善来世可以投胎为人。当小善问唐僧是否对自己有感情的时候,唐僧并没有出于同情而欺瞒她,将自己心中只有段小姐的实情和盘托出,“出家人不打诳语”的意象在此刻有了更为具体的现实指向,也将唐僧情有所终只取一人的痴情形象演绎开来。出家人情根未净,这样的剧情设置看似离经叛道,却也最符合一个凡人行径,令人信服。也正因此,当师徒重新上路,唐僧吟诵“有过痛苦,方知众生痛苦;有过执着,放下执着;有过牵挂,了无牵挂”时,那份历练后的澄明才更可贵。唐僧最终接纳了有缺憾的自己,走向了归途与克制。另外,影片用九宫真人对如来的一往情深与之做了横向对比,使得不同个体人性在面对爱情这一永恒元素时呈现真实的差异化。与唐僧最终克己复礼为仁的选择不同,九宫真人则信奉“随心随性大法”,九宫真人原是如来的坐骑九头金雕,为如来而生,脉脉深情遭如来冷遇后携带助手红孩儿潜入凡间比丘国,给西行的唐僧四人设障,企图以此让如来现真身。由姚晨饰演的这个角色有着广阔的社会外延,延宕不羁是她最大的性格特征,将比丘国的朝堂设置成大型游乐场正是她游戏人间的佐证。她所信奉的“随心随性大法”通俗讲就是“想干嘛就干嘛”,将人剥离开社会关系网,成为不受道德约束的“弄潮儿”。如同她不顾道义恋上如来一般,最终现出原形被如来收走,这也是电影向传统道德形式的皈依。她罔顾道义追寻吾爱的行为本就是一个执念,因为所爱牵涉他人,这样的爱本就疯狂,却也真实。这种真实与低碳艺术文本所要求的“与生活逻辑和历史逻辑相契合”[5]不谋而合。
<1),且各件产品是否为不合格品相互独立.
其次,作为影片的叙事重点之一,孙悟空的人物形象较之原著也发生了重大嬗变。影片开场,歪头跛足,口含木棍,暗黑色的服装造型与之所塑造的叛逆暴虐性格特征相辅相成,在规整的画面构图下,林更新着力将放荡不羁渴望被尊重的人物形象演绎得如鱼得水,被唐僧唬喊的不耐烦时,缓缓出场,言语激怒沙和尚表演换头法术飞沙走壁,脾气来了收不住把百战怪咔国这一个江湖草台班子毁于一旦。之后被唐僧用藤蔓殴打时也据理力争,需要得到尊重这个人之需求再次被提及。周星驰将这一人物形象的动物性进行抽离,加重了人性的描写,因此我们得以看到,在被喊作他最讨厌的“臭猴子”时,他会为了尊严与唐僧较劲“不要再喊我臭猴子”,虽然一直排斥被唐僧管束,也曾在夜黑风高夜杀他个措手不及,可是危险来临他却总是冲在最前面,替唐僧挡住那些血雨腥风。盘丝洞一役,他在已然识破蜘蛛精的真身仍然乐得与蒙在鼓里的唐僧演一出戏,让他在洋洋自得时出丑,在岌岌可危时护他周全。最后出手打死唐僧企图感化的蜘蛛精,让唐僧的虚荣心无处安放,体现了他睚眦必报的性格特点。比丘国朝堂之上借助听话符的契机,让唐僧当众出丑作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报复,当被唐僧的危机管理学折服时,他会心软与其称兄道弟,也是他一眼识破白骨精的真面目,将真相公诸于众企图得到大家的认可。当自我认知被否定时,他眼中噙着泪水,蹙眉神伤,口中的树枝也不似往昔有活力,那句“这世界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将真心遭遇践踏后的恼羞成怒表现的真实可感。转身离开,衣衫逐渐灰烬开来,爆裂石猴的真身逐渐走进画框中,他暴走将小善营造的幻象“河口村”夷为平地,被唐僧误解是滥杀无辜,也不辩解,继续一意孤行,逼迫小善说出真相。非黑即白,孙悟空这一认知与行为动机相契合,与刚正不阿的社会中二少年形象不谋而合。当最后的谜底被揭开,他化身超级英雄,腾云驾雾上天入海与三个假如来进行殊死抗争,召唤定海神针金箍棒在危机的时刻奋力保护唐僧的安全,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在师徒间展露无疑。最终师徒四人再次出发,孙悟空眼中的戾气皆化作师徒间友爱的戏谑,一路欢声笑语西去……受辱时渴望被尊重、危难时又不顾一切出手相助,所有的这些无不都是一个常人面对亲友时的常态吗?孙悟空这一人物形象在遇事时内心的焦灼与外在行为的暴虐亦与低碳艺术的本质特征“遵循真实的人性逻辑”[6]的客观真实不谋而合。影片借助孙悟空的人物形象展现了真实、丰盈的人性结构。凡人都有七情六欲和与生俱来的恶,修行便是要克制原欲达成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和解。
再次,作品对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等经典形象也进行了大胆解构,置换进更具低碳美学品格的现代人性内涵。“一切艺术创新都是为了让电影更好看、更生动、更有趣、更美。”[7]原著中猪八戒以“黑脸短毛,长喙大耳,穿一身青不青,蓝不蓝的梭布直裰,系一条花布手巾”[8]形象出场,到了电影中被置换成手绢掩面粉墨登场,借此隐喻猪八戒两面三刀、表里不一的性格特点。刚一开场,唐僧拉下帷幕,铁笼内忙于施粉的猪八戒第一次以侧脸引入观众眼帘,当被要求表演的孙悟空让他打自己的时候,猪八戒性格里的巧舌如簧的一面展露无遗,“不太好吧大师兄,打你还不是找死么,算了死就死吧。”面对如花妇女,猪八戒好女色的性格特点也被夸张的展现出来,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那位妇人,猪八戒立刻原形毕露扑上前去。蜘蛛精一战后,天色将晚时唐僧在后山的月色中祈求佛祖赐予如来神掌以牵制劣徒,猪八戒听闻后一边矢口否认听到了唐僧的祷告,一边附和唐僧的师徒情谊,信誓旦旦保证只想做自己,但转身离去立即将这个消息告知孙悟空挑起一番争端,最后唐僧侥幸逃脱,猪八戒被孙悟空一顿长拳暴打出猪头模样,正应了唐僧那句“祸从口出”,也由此猪八戒搬弄是非的形象立即鲜活起来。误入盘丝洞一役,猪八戒在与蜘蛛精缠斗中见色起意现出长嘴獠牙的原型。沙僧喊他去打水时,回应“水喝光了为什么要我去打呢?你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呢?”体现出他好吃懒做的性格特点。唐僧教训孙悟空一时失言要解散驱魔团队,刚刚还在一侧,坐山观虎斗的猪八戒误以为自己将会被咔嚓掉,于是掩耳不及惊雷霆之势出场,为唐僧送上汤药,并假意悔改,这无疑凸显了猪八戒见风使舵的行为特征。当沙僧被蜘蛛毒液误伤现出原形时,尽管百般嫌弃,甚至用巾布堵住了沙师弟的鼻孔。这一路上猪八戒却也不辞艰辛载着师弟前行取经,将猪八戒性格特征里憨厚宽容、重情重义的一面表现出来。比丘国国王为难唐僧让他当众表演法术的时候,猪八戒临危不惧直言自己可以化作唐僧的模样去大殿上表演,将一个有情有义的徒儿替师父着想的仁义孝悌铺陈开来。在真相大白后的交战中,他也拿起自己的九齿钉耙与孙悟空并肩作战保护唐僧的安危。在富有喜剧色彩的情节架构中告子与孟子辩论“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的论点得以被窥见,展现了真实复杂的本真人性。
作为取经团队中最为寡言慎行的成员,沙僧更多的时候扮演了沉默的大多数的角色,是西行取经的参与者更是拂袖旁观的见证者。影片对沙僧着墨不多,却处处经典。点破唐僧因段小姐与孙悟空生隔阂的是他,看穿唐僧危机管理学把戏的也是他。影片开场,面对唐僧呼吁积极表演的号召,他横眉冷对,只有当被喊做“扑街”时才被激怒挥拳打向孙悟空。现代社会生活中不正是有洞察生活真谛对他人的命运冷眼旁观的沉默的大多数吗?“正如我们在现实人生中所切身体验到的那样,真实的人性是变动不居的捉摸不定的,是善恶交织的统一体。”[9]
影片对白骨精这一角色的颠覆结构最为精彩传神。原著中的白骨精本是白虎岭内的企图借唐僧肉以长生的普通妖怪,与西行路上那些动机相仿的妖魔并无二致,但在电影中却被赋予了人性内涵,行为动机也在人性逻辑机制下得以展现。“人性只有通过具体而典型的行动才能彰显出来。”[10]白骨精小善在冤死后怨气不散,游离在人间,因为能瞒得过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被九宫真人选派在唐僧身边,以挑拨师徒感情。孤独的小善在唐僧的陪伴下,对其萌发了情感。所以当唐僧为了救她被孙悟空棒打时,她跪倒孙悟空身前眼含热泪蹙眉疾呼“不要再打了,我承认自己是妖怪,全村都是自己编造的幻像。”这一瞬间,观众体察到白骨精小善人性的光芒。将死之时,小善忍不住问唐僧,在他心中可有自己的印记留下来,唐僧给出否定回答后,小善孤独离世。百态善恶,皆为人性。
作为周星驰系列作品的传统,影片中不乏许多为人称道的配角,通过这些角色再次彰显出了一部优秀的低碳艺术作品所特有的德性价值——“对人性的精确再现与表现。”[11]开场,已经到达目的地天竺的唐僧,在梦中接受了自己师父“终生成就奖”的加封,原著中唐僧的师父实为金山寺长老法明和尚,他修身悟道,已然得到无生妙诀,在江边偶得婴儿,取名江流抚养成人。这江流正是唐僧的乳名。影片开场,唐僧的师父挥舞绳索钩挂至唐僧的鼻翼方至平衡稳妥,与清贫乐道的修道之人形象迥异,唐僧师父对目前身处天竺享乐的状态乐得其所,那句“你要的经书已经打包完毕,你要是喜欢可以带走”,成为最好的佐证。接着又为唐僧“加官进爵”颁发“终生成就奖”的获奖颈圈,将修道之人的天职本末倒置,一个固步自封、追名逐利的另类出家人形象演绎的尤为出神。“道德永远跟利益保持着暧昧的关系。”[12]
百战怪咔国一段的班主形象也令观众印象深刻,面对身侧人的挑唆他对凄惨的师徒四人出言粗鲁无礼,“有你们这么走江湖的么,砸我的招牌,给我走。”而当孙悟空三人小试身手,将众人唬住之后,袖珍班主立马改变态度,亲切熟络的对唐僧出言“大哥,你举手投足间真是光芒四射”,并试图以一串糖葫芦与唐僧称兄道弟。全副身家财产受到威胁时,果断使用苦肉计以退为进据理力争。将一个性格复杂多面的社会卑微底层小人物的境遇不失诙谐的呈现在镜像中。
正片伊始,大鹏饰演的驱魔人一行人来到蜘蛛精的府邸进行驱魔法事,对蜘蛛精两位长相老态毕至的干女儿诸多不满,对老妇进行照妖镜现原形无果后果断转向这两位并无美貌加身的干女儿,并出言“我忍你们很久了”,反复确认后才回身怀疑起样貌姣好的蜘蛛精本人,面对蜘蛛精现原形时的一句“大闸蟹”戏谑感全出。影片借助大鹏所饰演的驱魔人形象,将现实社会中以貌取人的现象展露在观众眼前。同时将以貌取人并不可取的价值观传达出来。
作为影片的绝对配角,饰演比丘国国王的包贝尔也留下了令人捧腹的表现。由红孩儿化身的比丘国国王,秉承了孩子的玩闹心性,将王室大殿变成大型游乐场,每日嬉闹玩耍不理朝政,将戏言当真强迫唐僧进行驱魔表演,将角色的孩子气推向极致,影片用这个孩童心性不作为的国王形象讽喻了现实语境下“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管理层人士。当红孩儿形象剥离,真正的比丘国国王出现时,面对一群并不美艳的后宫佳丽的无力感实则也在隐喻人在社会的身不由己言不由衷。唐僧为后宫佳丽求来特赦,可让她们离开后宫牢笼重获自由,后者不仅不感恩唐僧的善行反而怒目圆睁恶言相向,一时间“赶走唐僧,保卫爱情”的声音四起。影片借助这一群趋炎附势丧失独立人格的后宫佳丽这一意象,对社会中的坑老一族等依附他人生存的群体进行了鞭笞。
“与其虚假地、空洞地、娇柔地、人为地刻意制造某种貌似高尚的爱情、亲情、友情、某种英雄偶像、某种先进典型,不如老老实实得怀着人类痛苦的深切同情,将人性中的种种不幸、种种卑鄙、贪婪、阴险,种种不义、不公平、不自由、种种假恶丑相表现出来、再现出来,更有力量、更有价值、更为低碳。”[13]《西游伏妖篇》一系列人物性格对真实人性的表现和再现,直抵人心,堪称一部优秀的低碳艺术文本的典范。
注释:
①所谓低碳艺术就是在文本构成上以客观真实为主要特质,以直观真实、超现实真实或主观真实为基本辅助,在与审美主体互作中能够激发陶冶型自由情感,从而促进审美主体身心双重健康的艺术文本(参见马立新著《低碳人》,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版第136页)。
[1][7][10][11][12]马立新.奥斯卡艺术研究[M].济南:人民出版社,2014:330,67,17,396,111.
[2][德]叔本华.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21.
[3][5][6][9][13]马立新.低碳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70,135,135,67,63.
[4][明]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作者题词.
[8][明]吴承恩.西游记[M].北京:金盾出版社,2014: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