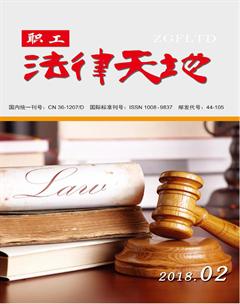浅论《刑法》第117条与第119条第一款之关系
张馨
摘要:“危险犯”这一概念一直以来都是刑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围绕这一概念所产生的问题也是困扰学者们的难题。其中,我国《刑法》分则第114条和第115条第一款的关系如何?第116条、第117条、第118条同第119条第一款之间为何关系?对此,学界观点不一。因此,以我国《刑法》第117条和第119条第一款的关系为例来进行探究,通过对危险犯的进一步了解,从立法者初衷思考,从总则的基本规定入手,具体分析犯罪的构成要件,力求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把握第117条和第119条第一款的具体内容,从而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危险犯;实害犯;基本犯;结果加重犯;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发展,危险犯成为各国刑法中一类重要的犯罪类型,成為了防范社会风险的有力武器。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国刑法学界就开始了对危险犯相关理论的研究。危险犯这一理论所带来的难题是众多的,由于其本身“危险”一词就无确定的概念,因其产生的其它概念理论自诞生便带着不确定性。在我国,这类犯罪主要规定在刑法典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实践中,在处理类似破坏交通设施罪等案件时,往往因危险犯的规定而存有诸多的疑问,例如该类犯罪的既未遂问题、“中止”问题等等。以破坏交通设施罪为例,《刑法》第117条和119条第一款均作出了规定,但在实践中如何具体处理是个难题。捋顺思路,便会发现首要解决的是《刑法》第117条和第119条第一款的关系问题,而关系问题的厘清还须弄清以下几点。
(一)危险犯之“危险”
一般认为,我国《刑法》第117条规定的是危险犯,但何为危险犯学界观点不一。危险犯之“危险”一词也是存有争议的。“危险”是否是一种结果,学界众说纷纭。刑法学界通常将这一概念理解为“行为人的危险”与“行为(广义)的危险”。而后者又有“行为的危险”与“作为结果的危险”之分。这两者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区分。通说认为,“结果”包括对法益的侵害也包括有侵害的危险。其中,“侵害的危险”是指作为结果的危险。按通说观点,危险犯中的“危险”是结果的一种。
(二)危险犯与买害犯
对于危险犯与实害犯这对概念,通说认为,前者的处罚根据是对法益有侵害的危险;后者的处罚依据是对法益的实际侵害。由此,认为《刑法》第117条系危险犯之规定,第119条第一款则是实害犯之规定。这一观点也是存在争议的,争议的源头来自于“危险”这一概念。上述通说认为“危险”系作为“结果”的危险。这里的“结果”与结果犯的“结果”不能等同理解。一般将结果犯与行为犯看作一对概念,并不是指具体的罪名而是犯罪的具体情形,主要解决犯罪成立与否的问题。因此,不能因为危险犯之“危险”属于结果而将危险犯也认定是结果犯。
二、我国《刑法》第117条与第119条第一款的关系之争
《刑法》将以具体公共危险状态为构成要件的破坏交通设施罪规定在第117条中,而将以造成严重伤亡结果为构成要件的破坏交通设施罪规定在第119条第一款中,并规定了不同的法定刑,将同一犯罪分别规定在两个法条中,这样一来,在正确认定破坏交通设施罪时,就不得不首先对两个法条之间的关系进行界定。我国刑法学界对此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是未遂犯与既遂犯关系说;二是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关系说。
(一)未遂犯与既遂犯关系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首先,这样理解在未遂犯的理论上没有障碍。《刑法》第117条所规定的破坏交通设施罪的构成要件是以出现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为构成要件,是刑法上的危险犯,而第119条第一款所规定的破坏交通设施罪是以“致人重伤、死亡,或者重大公私财产损失”作为构成要件实害犯,符合未遂犯的相关理论;其次,《刑法》分则条款并不一定是具体犯罪的未遂形态。认为破坏交通设施罪不仅具有财产犯罪和人身犯罪的一面,还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一面,所以刑法将破坏交通设施罪以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作为成立犯罪的基本形态加以规定,同时,又考虑到破坏交通设施罪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特征,危害性较普通刑事犯罪大,所以又将尚未造成严重损害的但已经危害到公共安全的行为也例外地作为犯罪处理;最后,该说认为将第117条理解为第119条第一款的犯罪的未遂犯,可以妥当地解决破坏交通设施罪的“中止”的问题。
(二)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关系
该观点认为,《刑法》第117条是基本犯的规定,第119条第一款系结果加重犯之规定。结果加重犯是指实施了基本犯罪,因发生严重结果而刑法加重其法定刑的犯罪。坚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该说的合理性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该说对两者关系的理解贴合理论,符合逻辑。破坏交通设施若造成“严重后果”则超出了《刑法》第117条规定的犯罪的构成要件的范围,不能将其评价在内。而第119条第一款规定的犯罪可以涵盖,而且后一条文规定了较前者加重的法定刑,显然符合我国刑法理论中对结果加重犯的定义;第二,将第117条规定之犯罪作为基本犯,将第119条第一款的犯罪作为结果加重犯,即在行为人故意造成具体公共危险状态,结果却过失造成致人重伤、死亡或者重大公私财产损失的严重后果,是典型的结果加重犯;第三,该说被各国刑法理论界所认同。日本刑法中对遗弃罪和保护责任者遗弃罪的相关法条规定存在类似问题,也是作为基本犯和结果加重犯来看待的。我国台湾地区刑法中的损坏交通设备罪和危害飞行安全罪的规定上也系此情形。我国《刑法》中第114条与第115条第一款,第116条、第117条、第118条与第119条第一款的关系都是类似情形,也可认定为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的关系;第四,该说对这两个法条关系的理解不仅可以合理地解决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处罚失衡的问题,还能更好地认定犯罪的未遂和中止问题,合理限制两个法条的适用范围。
三、对“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关系”之赞同
目前,对于我国《刑法》第117条和第119条第一款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两种主要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经不起推敲的地方,目前尚未有定论可依。
(一)未遂犯与既遂犯关系说之反对
对于《刑法》第117条和第119条第一款的关系问题上学界有不少的学者持“未遂犯与既遂犯关系”说。该观点在解释这两个法条的关系上的分析理由是顺畅的,但是在涉及犯罪未完成形态及处罚问题上还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一般认为我国《刑法》分则对犯罪的规定是以既遂为模式的。那么将第117条看作是未遂犯,就会冲撞这一立法模式,产生理解上的障碍和逻辑上的混乱。若为了将其解释为未遂犯进而再去解释质疑这一立法模式,就会使问题层出不穷。
其次,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鉴于像第117条这种危害性大于普通刑事犯罪的行为虽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已危及公共安全,因而将其作为例外加以规定。我国《刑法》分则是以处罚未遂为原则,不处罚未遂为例外。这样看来,这一说辞明显是有悖未遂犯的原则性规定的。
第三,将这两个法条理解为“未遂犯与既遂犯关系”不利于妥当解决这类犯罪中行为人主动消除危险状态的行为定性问题。例如,行为人将一巨石搬到铁轨上,意图颠覆火车,但在火车即将到达前,心生悔意,将巨石推开,避免了事故的发生。按照这种观点,行为人即构成第117条规定的破坏交通设施罪,按照该罪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如此对行为人来说,在危险结果尚未发生之前,行为人主动将巨石搬离铁轨的行为又消除了之前造成的危险状态的行为相当于作了无用功。在一般人的观念来看在此情形下对行为人科处第117条规定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显然有些不合情理。这种忽视行为人主观悔过的观点,不利于鼓励犯罪行为人及时中止犯罪。
第四,如果将第117条理解为未遂犯,而将第119条第一款看作是既遂犯,那么行为人对第119条所规定的致人重伤、死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结果只能是故意。显然,这一推论会被理论和现实所击溃。行为人犯《刑法》第117条规定的犯罪时,不需要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能致人重伤、死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这一严重后果,更不需要行为人对这一后果持追求、放任的态度,只要行为人有成就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的故意即可。在此,对于“结果”这一概念的理解也不能过于狭隘,在这两个法条中对结果的理解应当包含具体的危害结果和成就的危险状态这一结果。如此看来,这一关系说的解释略显狭隘了。
(二)对“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关系”之认同
“未遂犯与既遂犯关系”说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关系”一说是否就一定完美无缺?这一点不敢断言,任何理论可能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况且万事万物都在发展之中,理论也必当与时俱进,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就理论和现实层面来看,其确实存在优势。
首先,如上述学者们支持的理由之一,将《刑法》第117条与第119条第一款分别看作是基本犯和结果加重犯的关系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造成严重后果”超出了第117条犯罪构成的范围,不能评价在第117条之中,而被第119条第一款的规定囊括。第119条第一款的规定相比第117条加重了法定刑,显然符合结果加重犯的一般规定。
其次,将第117条认定为基本犯罪,将第119条第一款认定为结果加重犯符合理论和现实的要求。理论界中一般认为成立结果加重犯,对基本犯要有故意或者过失,对加重结果至少是过失。这使得行为人对第119条第一款规定的加重结果可以持故意的态度也可以是过失。这符合理论和实际中出现的具体案例,相较于“未遂犯与既遂犯关系”说能更好地联系理论结合实际来处理案件。
第三,将这两个法条看作是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的关系,能更好地解决犯罪的未完成形态的问题,均衡刑罚。一般认为,危险犯是与实害犯相对应的概念,行为犯是与结果犯相对应的概念,前者是解决犯罪成立条件的问题,后者是解决犯罪既未遂的问题的。第117条是危险犯也是行为犯,第119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实害犯也是结果犯。仍以上述的例子来说,行为人将巨石置于轨道上的时候危险成就之时,行为人即成立危险犯。在危害结果发生之前行为人主动消除危险状态的行为不能评价进行为人已经既遂的犯罪中也不能评价进未发生的结果加重犯的规定当中。虽然这一解释似乎不太清晰,其实结合犯罪既遂和中止的相关理论来看,逻辑上是通畅的,认为行为人成立危险犯的既遂。有学者指出,这样认定不就相当于“未遂犯与既遂犯关系”的处罚程度了吗?这种质疑是很有必要的,解释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联系实际,行为人主动消除危险状态的行为虽然不能认定为中止,但是结合刑事政策來看,行为人主观有悔过表现,也没有造成危害结果的出现,因此可以视为酌定从宽情节,在量刑中予以考虑。这样及鼓励了行为人及时停止犯罪,又不会使刑法对危险犯以及中止等制度设置的初衷落空。
四、结语
我国《刑法》第117条与第119条第一款的关系之争一直未能得出确切地答案。黎宏教授认为,“刑法上的危险判断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判断问题,而直接关系到刑法的规制范围;不仅仅与法律规范的逻辑分析有关,也与刑法规范的性质、刑法机能的认识有关。”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难题,如何理解关系到总则相关制度的设立初衷,关系到分则具体罪名的认定和处罚。对这一问题的厘清需要首先明确危险犯相关的基本概念。基于立法者在刑法中设立危险犯的初衷,不与刑法分则条文的基本立法模式相冲突的基础上,不违背立法者设立中止犯的立法原意以及结合实践中具体案件出现的情形,笔者认为应当认为这两个法条是“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的关系”。在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一章中,第114条与第115条第一款之间以及第116条、第118条与第119条第一款之间的关系是类似的,也应视为“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关系”。这一观点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但相较其他观点来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稳得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