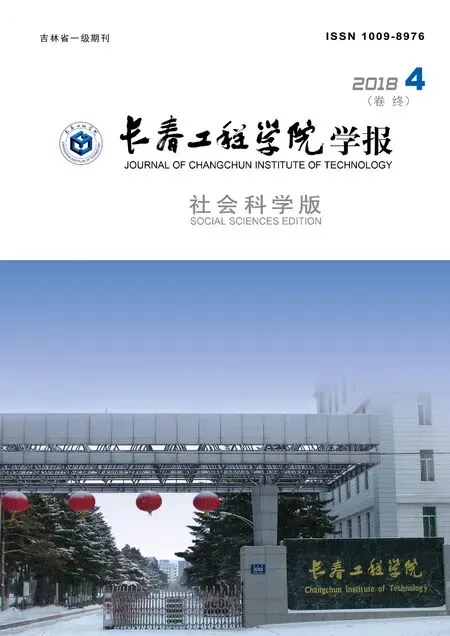“根的神话”
——多丽丝·莱辛笔下南非白人的帝国流散意识
刘玉环
(长春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长春 130012)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是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为南非英国殖民者的后代,莱辛在非洲[注]文中的“非洲”“南非”主要指“南部非洲”(southern Africa),即撒哈拉沙漠(the Sahara Desert)以南曾为英国所统治的地区,既包括现在的南非(South Africa),也包括现在的津巴布韦(Zambesia),后者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被称为“南罗德西亚”(Southern Rhodesia)。文中的“南非白人”指英裔南非白人殖民者。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二战”后回到英国,所以是流散作家。莱辛作品中塑造了很多南非白人殖民者形象,他们属于“帝国流散者”(imperial diasporas),即“为殖民离开故国来到居住国的流散群体”。[1]这些南非白人的流散意识体现为对故国英格兰这一“根的神话”的坚守、对居住国非洲的疏离。正因心怀这种流散意识,他们虽身在非洲,却不忘理想化英国,固守英国生活模式,心怀回归渴望。
一、莱辛笔下南非白人对英国的理想化
老一代南非白人对故国英格兰这一“根的神话”的坚守体现为对英国的理想化。从小到大,莱辛听惯了父母“关于美好富足天堂的谈论”。在父母眼中,英格兰是完美的人间天国;相比之下,非洲丑陋贫瘠,不值一提。
在莱辛父母的记忆中,英格兰是一座人间伊甸,缀满“青青的野草、春日的鲜花、猫一般温顺的奶牛”。[2]62对于当时的南非白人来说,“温顺的奶牛”几乎成为英格兰的象征,与非洲眼神野蛮、犄角尖尖的奶牛相对,提醒他们英格兰无可取代的家园地位。当时一位南非白人农场主特意花费巨资从苏格兰引入一头纯种牛犊。“这头牛之所以贵重,是因为性情温驯,温和如羊羔。”[3]温驯的英国奶牛象征着闲适、文明的英国生活画卷,这是南非白人借助距离的妙笔所描绘的理想化的英国生活场景。
莱辛的父母对英国奶牛的理想化体现了他们对完美的英国生活的向往。莱辛的父亲从小在英国跟农场主的孩子一起长大,一辈子就想当一名农场主。他无力在英国购买农场,所以来到非洲,想挣到钱后回英国买一座农场。对于莱辛的父亲来说,温驯的奶牛象征着他所梦想的英格兰农场生活。莱辛的母亲之所以怀念英格兰温顺的奶牛,主要是因为这种奶牛象征着英格兰生活的富足、优雅。在莱辛父母的记忆中,英国农场是一座闲适的庄园,奶牛在水草丰美的牧场上悠闲踱步。这一美好画卷深深印入莱辛的脑海,她晚年回忆道,“我仿佛看到一群群奶牛徜徉在肥美的英国草丛和苜蓿丛中,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4]194
与完美的英国奶牛相对的是瘦弱野蛮的非洲奶牛。莱辛提到:“在非洲农场,我们的奶牛是六七头瘦骨嶙峋的家伙。想要提供一家人食用的奶制品,这样的奶牛得六七头才够。而在英国,一头都绰绰有余。”[4]194此外,与温顺的英国奶牛相比,非洲奶牛野蛮得可怕。莱辛在自传中提及,“在非洲,我们的奶牛是牛角尖利、眼神野蛮的幸存者。要是走路时不小心碰到了,我会躲得远远的。”[4]194在小说《黄金之城埃尔多拉多》(“Eldorado”,2003)中,白人主妇玛吉(Maggie)也为非洲“只有成群犄角尖尖、目露凶光的牛”[5]而感到遗憾。总之,非洲没有足够的牛奶,没有友善的奶牛,这引发了南非白人无尽的感慨:“哎,要是在英国……”[4]194对英国生活的理想化体现了南非白人对故国英格兰这一“根的神话”的坚守。
二、莱辛笔下南非白人对英国生活模式的坚守
老一代南非白人对故国英格兰这一“根的神话”的坚守还体现为固守英国生活模式。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1961-)指出,英国“一直非常起劲地在白人统治的世界里复制着自己的形象”。[6]在南非,白人正是如此。南非城市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实际上是欧洲城市在非洲大地上的复制品,“其给人的感受、风情和习俗无一不令人想起英国。”[7]3
首先,当时南非白人努力在非洲复制类似英国的居住环境。有学者指出,“欧洲人不管到哪儿,都立刻开始改变当地住所的环境,其目的是把领地变成家乡的样子。”[8]南非白人正是如此。比如在小说《德威特夫妇来到峡谷山庄》(“The De Wets Come to Kloof Grange”,2003)中,在与世隔绝的非洲农场,在“被活埋在陌生土地上”的孤寂生活中,盖尔夫人(Mrs Gale)的应对办法是在非洲的红土地上打造一座英式花园。花团锦簇的非洲灌木掩映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英国草坪,一座金鱼游曳、睡莲盛开的水景园”。[9]在干旱的非洲高原,保持这样一座英式花园是一种奢侈,因为从河里抽水上来很费钱。这座非洲高原上的英式花园体现了盖尔夫人坚守英国生活模式的决心。
此外,南非白人还竭力保持在英国的饮食习惯。他们在南非打造了一块英国飞地,将英国传统饮食习惯保持下来。同其他南非白人家庭一样,即使在30年代经济萧条、食品短缺的情况下,莱辛一家仍保持着“爱德华时代大吃大喝的风气”,“仍屈从于每餐一百道菜的幻想。”[4]236直到莱辛1982年回非洲探亲时,南非白人仍保持着英国传统饮食习惯。莱辛告诉弟弟英国已不再固守传统的英国饮食习惯,而是“吃印度餐、中餐、比萨饼、意大利面食、还有美国汉堡包”[7]186,弟弟对此感到遗憾,将其视为文明的倒退。这种对英国生活模式的坚守体现了南非白人向往英国、疏离非洲的流散意识。
三、莱辛笔下南非白人的回归渴望
老一代南非白人对故国英格兰这一“根的神话”的坚守也体现为对英国怀有回归渴望。“‘回归神话’(myth of return)并不专属于犹太流散者。正像犹太流散者祈祷‘明年在耶路撒冷’一样,其他流散者也是如此。”[10]莱辛笔下的南非白人普遍对英国怀着归乡渴望,他们在非洲具有优越感,仅仅将其当做寄居之地。这种优越感可以追溯至古犹太流散者。正如有学者指出,古犹太流散者在居住国实际上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因为“与邻居相比,他们是‘选民’”。[11]南非白人也体现出选民意识,认为历史上“走失的以色列十支派”(Lost Tribe of Israel)实际上来到了英国,认为自己就是“英国以色列人”,“上帝选择我们以大英帝国的名义去统治全世界。”[2]190正因将自己看作传播上帝福音的选民,南非白人对英国怀着归乡渴望。
当时南非白人的寄居心态从他们居住的房子可以略见一斑。莱辛一家在南非山坡上的泥草房是作为临时过渡房建造的,本打算用第一年的收成翻建新房。然而,20年后,他们住的仍然是这座泥草房,“仍然是临时的”。之所以没有翻建,一是因为收成不好,农场难以为继,二是因为他们不打算在非洲扎根,始终期待着“明年回英格兰”。所以,虽然这所房子破败不堪,但他们并不为此感到羞耻,“为什么要为一个自己从不当作家的地方感到羞耻呢?”[12]与这种冷漠相对,是全家对英国的热情。莱辛提到:“母亲的继母去世后,母亲把那维多利亚式房屋里的家具保存起来,付钱存在那儿。年复一年,即使在没钱买食品杂货时也是这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考虑到“他们最后‘离开农场’来到英国时,最初可能没地方住,但至少还有一屋家具”。[13]这体现了他们对英国的回归渴望。
在当时的南非白人中,这种寄居心态非常普遍。比如在《高原牛儿的家》(“A Home for the Highland Cattle”,2003)中,刚来非洲的白人主妇玛丽娜(Marina)注意到白人并没有在非洲扎根,“没有人真正生活在这儿。”白人主妇庞德夫人(Mrs Pond)粉刷了房子的墙壁,修补了破损的东西,结果遭到其他白人的集体孤立。在南非白人看来,门把手之类的东西坏了一律不能修,因为“要是动手修理房子,就意味着一辈子都得待在这儿了”。[14]对南非房子的冷漠体现了他们对非洲的寄居者心态、对英国的回归渴望。
总之,作为帝国流散者,莱辛笔下南非白人的流散意识体现为对故国英格兰这一“根的神话”的坚守,也就是将非洲当作寄居之地,将英格兰当作真正的家。正因心怀这种流散意识,他们倾向于理想化英国,在非洲固守英国生活模式,对英国怀着回归渴望。实际上,南非白人对“根的神话”的坚守并不是特例,而是帝国流散者的普遍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