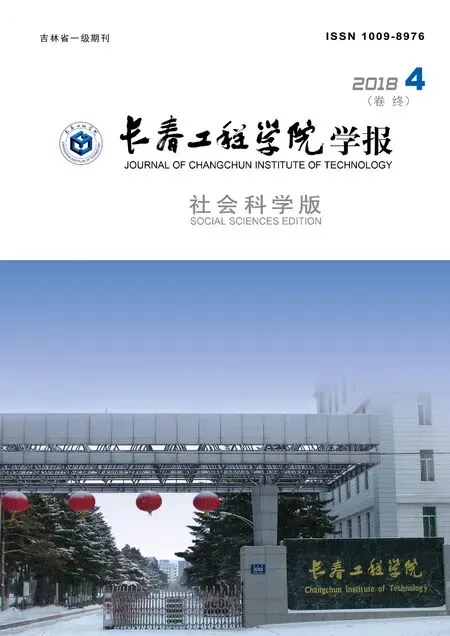中国参与联合国安理会事务的历程与省思
梁 琳,刘春吾,孙晓慧
(1.吉林省对外汉语教学培训中心,长春 130022;2.联合国信息与技术部,美国纽约 NY100172;3.山东省五莲中学,日照 276800)
引言
作为“二战”间无畏反抗日本入侵的国家,中国被赋予了与其他大国共同建立战后国际新关系的历史责任。1944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中美英俄拟定了“联合国宪章”草案,并在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定稿。然而中国虽然是该宪章的第一个签署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却直到1971年才被授予联合国合法代表席位,“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只有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的合法代表,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虽然中国从未停止对安理会工作的支持,但其缺席加剧了联合国安理会的职能问题。加入安理会后中国在国际和平和安全中的核心地位大大提升。
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在联合国维和的预算逐年增加、世界影响力扩大、区域和国际安全事务中的作用增强,以及在朝鲜、缅甸和苏丹等国家问题上的参与和建设工作已开始彰显作用,其希望在未来面对国际安全威胁的多样化、复杂化时,能够在协调和调动全球支持、维护和平与安全等工作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一、中国与联合国安理会新型关系
(一)新的时代,新的使命
苏联解体后两极化格局极速改变,新世纪后世界更是由多极化向一超多强方向发展。中国清醒认识到“和平与发展仍是主流趋势,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在加深”的情况。致力于通过澄清核心国利益,踏出全球战略第一步。2009年胡锦涛宣布中国的外交必须“保护主权、安全和发展的利益”。随后前国务委员戴秉国指明核心国家利益的三个方面,即中国的政治稳定,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中国可持续经济和社会发展[1]。
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要求建立“21世纪主要国家间的新型关系”。随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解释了“新型大国关系”:“基于相互尊重,旨在实现双赢合作。相互尊重意味着双方都愿意倾听对方的声音,相互理解,彼此尊重,找到适合的方式。双赢合作意味着双方应该放弃‘零和’策略,期待对方成功,并从对方的成功中寻找机遇。”
“十九大”报告也指出:“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这种新型双边关系是双方进行坦率沟通和及时磋商的关键问题,可以看到中国一直在参与国际社会活动的过程中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全球战略和明确的外交政策目标。
(二)低调参与,韬光养晦
中国全球战略的一个关键是其对自身力量和全球影响力的看法。David Shambaugh[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评价:“现在中国在世界各地和各个功能领域都很活跃,但不会影响或塑造世界各地的行动力量或事件。”[2]虽然可能夸大了中国“安静外交”的主张,但中国参与、促进苏丹和缅甸的国际社会合作就是两个例子。尽管经济总量为世界第二,但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远低于发达国家,这是坚持“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低调”原则的重要原因,也决定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反应和非领导作用,集中精力和资源优先发展国内经济,降低因为参与全球政治和安全事务造成的消耗。安理会1991年至2005年期间投票记录表明,中国在51项安理会决议中投了弃权,是这期间最容易产生弃权票的常任理事国,例证了中国的“原则性实用主义”:妥协的同时,使用弃权表达对某些具体决议的不满。这种行为模式一是为了保持安理会关注不受阻碍,二是清楚认识到中国依然缺乏必要的全球影响力,美国仍占据主体地位。
然而伴随近年国情改变、多极世界的出现,中国国内已出现激烈争论。例如出现“创意参与”理念,强调中国外交领导应具备主动性和建设性[3]。然而中国依旧十分审慎,“在某些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保持审慎低调的态度”,如在中东问题上,中国趋于风险规避,但若涉及周边或自身安危,中国愿意冒险投否决票。[4]
(三)开诚布公,共同发展
中国一直以来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深化周边国家关系,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安理会是推动中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机构。而随着全球化日益加深,安理会在处理相互关联依赖的挑战和威胁时将更为困难。为此中国希望安理会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现实,应对新挑战。而新兴大国的崛起和既定西方势力的相对弱化使世界更加分散、拥挤和多样化。这使得西方势力试图用西方概念和思想干扰联合国行为遇到了新兴大国的阻力,全球安全共识被削弱,需要更为公开和坦诚的对话和磋商才能在公平、公正和包容的基础上,达成新的全球共识。
中美及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间的互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让安理会依赖这种相互信任和相互包容的关系,能够提升其在全球和平与安全上发挥关键作用的能力。
二、中国参与联合国安理会事务的策略
(一)重申主权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
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以强凌弱。
冷战后各方不断怀疑和批评主权概念,国际人权和刑法重现产生更加剧了主权的衰落。欧盟的建立激发了对超国家组织力量和势头的期望,以及实现克服主权国家间边界和冲突最大文明的可能性。然而中国认为当代世界仍由主权国家主导,主权是国家的基本要素。中国对主权性质不断变化的观点重新解释了《联合国宪章》[注]《联合国宪章》是联合国的基本大法,它既确立了联合国的宗旨、原则和组织机构设置,又规定了成员国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以及处理国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第二条第七款,是否干涉基本隶属于国家内部管辖权,关键是对“本质在国内管辖范围”的理解。
通常说国家基本权利已经阐明了主权。随着“保护责任”概念的出现及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中从责任角度对“主权”的新解释,更好地理解主权的固有性质和范围,即国家的保护责任、国际援助能力建设,以及及时果断的反应。前两点支持了中国对“主权”的看法和理解,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主权基本保障了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的独立性,并提供了不理会外部干扰的权力。
中国认为必须加强国家主权和权威,特别是国家治理机构,以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这与第三个支柱中隐含的国际干预存在重大分歧。因此中国是第三支柱的主要批评者,因为它不仅会导致强国强制干预弱国,同时还超出了对国家责任、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法规的既定理解和解释。比如在2011年干预利比亚时,清楚反映出新兴大国对过度依赖和滥用第三支柱的担忧。因此中国支持俄罗斯关于任命将军或参谋团为安理会授权的、和平行动有关的指挥和控制机构的建议。但因国际社会对军事事务的深度不信任,这项提案很难推进。
(二)强调国家责任,重视国际干预
随着中国逐步适应新现实,评估国际问题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是: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人道主义危机的严重性、内部冲突的外溢效应,相关国家的条约或其他法律义务。而后冷战时期,安理会对“和平威胁”和“破坏和平”的解释十分广泛,极大扩大了《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范围,极可能催生内战和严重人道主义危机。于是相关区域组织就随着其机构和能力建设的加强逐渐展现出作用,成为审议和实施干预措施的关键行动者。例如非洲联盟在利比亚建立“禁飞区”的影响,使得中国对第1973号决议投弃权票。安理会和各区域组织决议和行动的先决条件应注重构建共识。干预利比亚的军事力量无视1973年决议中设置“禁飞区”是为保护平民和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的目的,用武装政权取代了保护平民的任务,造成了常任理事国间的不信任,叙利亚危机恰巧在这时出现。中国坚持认为,在无法判断实际情况时安理会不应仓促决定,还需考虑到对叙利亚的内部区域和平与稳定的影响。安理会应寻求得到广泛支持的政治和外交解决办法,而不是任意改变国家政府或国内政治进程,涉及保护平民的行动必须经理事会授权,并在联合国主持下有秩序进行。任何一方都不应任意解释安理会的决议,不应允许超越理事会任务的行动。基于以上中国否决了叙利亚的三权决议[注]分别为S/2011/612,S/2012/77和S/2012/538。。
相比之下,中国积极支持第2043和2059号决议的通过,该决议授权并延长联合国叙利亚监督团(联叙监督团)的任务期限。这明显反驳了称安理会因中国和俄罗斯的否决而在叙利亚问题上陷于瘫痪的指控。联叙监督团的最后撤离完全反映了中国对叙利亚内部冲突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的担忧。相反,联合国/阿拉伯联盟特使和叙利亚问题国际行动小组的活动表明,联合国和阿拉伯联盟的调解努力没有中断。中国一再努力促进解决分歧,派遣中东问题特使、接待叙利亚反对党的代表团,并向叙利亚难民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叙利亚政府提议加入《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并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监督和控制下移交叙利亚化学武器时,中国迅速提议有关各方应抓住机会,尽一切努力促进安理会第2118号决议的通过。中国倡导对叙利亚危机采取双轨方针,结合叙利亚化学武器处置的技术进程,就停火和民族和解进行政治谈判,争取达成最大化的妥协。
(三)提倡预防性外交,加强区域合作
“预防性外交”是:联合国应及时干预那些处于东西方阵营以外的争端和危险局势,以填补实力真空,防止东西任何一方插手,缓和紧张局势。其与“保护责任”的第一、二支柱中的预防措施的重点一致,这正与中国的不干涉原则相一致。
以往中国对预防性外交持负面看法,一是其可能转化为西方国家利用经济、政治和军事优势任意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二是其需要预防性干预以防止潜在冲突,这就需要提前评估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险和威胁。但预防性外交侧重于政治和外交措施,贴合中国倡导的和平和非强制策略。因此中国肯定联合国在预防性外交上日益突出的作用同时,也认识到预防措施应首先在区域、次区域一级建立共识。
中国已经在区域关系中发挥出作用,2012年上海合作组织北京首脑会议的《联合声明》强调:“如果存在对某个成员国或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的局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将采取有关规定的政治和外交措施,迅速、适当地处理危机”。另外,中国还积极推动亚洲和非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总的来说,中国认为安理会与各种区域组织间进行有效的协调与合作,有助于建立一个发展中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进而构建更加安全的世界。
(四)明确自身定位,不越权不越界
在政治干预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的问题上,《宪章》规定联合国的一个职能是促进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步发展,安理会作为联合国执行机构,一般被视为缺乏立法的能力,更不用说颁布新的国际法规则。
中国同意安理会决议一般都是基于这一信念。在某些情况下,安理会的一项决议可能意味着国际法在有关规则方面取得进展。这主要有两种方式:首先,安理会的某些决议需要成为世界各地广泛法律信念的一种证据。例如“9·11”后,通过了针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的第1373(2001)号决议;其次,由于安理会可以改变对《宪章》条款的解释和适用范围,这种情况包括安理会在内战或其权力范围内的冲突中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作用,其最近的一些决议还将条款视为逐步发展国际法,例如设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注]设在荷兰海牙,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附属机构之一。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R)[注]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庭址在坦桑尼亚阿鲁沙。。但应该对这类发展采取谨慎态度。
作为联合国的执行机构,安理会必须铭记可以国际立法的国际法律主体仍是国家,而国际组织的立法作用非常有限。因此,中国始终强调,安理会应继续被视为一个行政机构,而不是作为一个立法机构。
三、中国视角下的联合国安理会改革
(一)尽职履责:改革安理会集体安全体制
联合国需要进一步改革机构的体制框架和工作方法,以便适应更加多元化和迅速变化的世界。因此,中国支持安理会进行必要合理的改革,以加强安理会的权威和效率。
中国对改革的立场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应优先考虑增加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的代表性,使他们有更多机会参与安理会的审议,公平地域分配,特别是增加非洲国家的代表性,中国将永远不会支持无法赢得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支持的改革建议。2005年埃祖尔维尼共识中安理会改革的非洲立场,可能不完全符合中国的期望,但这并没有影响中国承认非洲国家在安理会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安理会的改革与联合国的未来作用及其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密切相关,需要包括所有成员国在内的广泛磋商进程,以达成尽可能广泛的共识。中国认为,应通过包容各方的协商解决改革议程上不同集团的分歧,急于投票只会加剧这种分歧。
(二)审慎用权:合理使用一票否决权
当前,安理会受世界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首先安理会审议否决权只用于非程序性事项。特定问题是否是程序性问题,需由安理会主席以所有成员的共识来决定,可见“双重否决权”明显被夸大。这种方式也逐渐成为安理会的惯例,常任理事国在行使否决权方面也变得更加谨慎,是对其他成员国行为的潜在约束,并非经常被正式使用。以此可以促使安理会成员国为通过非正式协商达成妥协和建立共识做出更大努力。这反映了《联合国宪章》设置否决权的意图:在各大国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和相互克制,以促进对话、协商和建立共识。
1990年代初,在冷战后国际体系结构调整中,常任理事国间的协商大大促进了安理会的团结。然而,当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单方面使用武力解决区域冲突时,安理会的重要职能再次陷入僵局,在解决中东和北非国家动乱和冲突方面也开始面临新困境。这种情况下,安理会必须考虑中小国家在倡议和概念创新方面越来越大的贡献。而根据《宪章》第二十七条规定的通过决议所需最低票数,如果有足够的志同道合的成员组成联盟,那么非常任理事国在阻挠决议草案方面也有一定影响力。
我们仍然生活在格罗坦世界,需要在“规则的力量”和“权力的规则”间取得平衡,国际机构反映的是其成员国意志,强大的国家意志使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制度化。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机构的加权投票和股权结构生动反映了这一现实,即国际事务的制度化和合法化使中小国家以及国际民间社会,可以通过援引国际法规则或使用国际制度的制度化结构,行使某种制约和平衡,有了更多的发言权。
(三)优化议程:倡议联合国工作方法改革
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近年来,安理会改革已转向重新设计其工作方法,这可能是在不久的将来推动改革议程的唯一可行方法。中国认为改革要透明,具备包容性和代表性,注意安理会的效力。理事会已积极推进改革进程,成员轮流每月主持简报会,向非理事会成员介绍工作方案,还可以召开更多的公开会议,有效地利用了各种形式,如非正式互动对话和阿里亚办法会议,以加强与相关成员国、和平建设委员会、民间社会和学术机构的国家配置的交流和互动。中国支持在“总统说明507”(S/2010/507)的指导下进行进一步讨论和行动,以及文件和其他程序问题非正式工作组(IWGD)的后续工作。
四、总结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对外的政策、在联合国事务中处理的态度都发生着改变,其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在国际中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中东和北非国家动荡近三年后,联合国安理会经历了好和坏的时代。它的权威大大加强,特别是五大常任理事国越来越依赖于依靠安理会在解决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合法作用。美国和英国政府在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方面的经验表明,没有安理会决议授权,政治家和人民不愿采取单方面行动。然而也看到了大国间的重大分裂,叙利亚危机暴露了安理会的局限。此分歧反映出了国家利益的影响,以及对基本原则和思想的看法,包括误解。[10]
中国之于安理会的作用主要在授权干预措施和处理干预的后果两个方面。西方列强放弃在国家保护责任[注]简称R2P或RtoP。简而言之,保护责任意指国家有保护其人民免受种族灭绝、战争罪等严重危害的义务,如果一国没有能力行使此义务,则国际社会必须随时准备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集体行动保护人民。第三支柱下的干预,使中国对西方列强推动安理会决议的意图更加警惕,对国际秩序可能的附带损害表示担忧。中国将本着实用主义精神,继续努力与其他常任理事国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与合作,促进安理会就争议问题达成共识。同时中国也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例如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方法的特点是渐进主义,明显倾向于稳定性和现状的逐渐变化。有时,它为西方的激进主义提供了必须的平衡。
除了为安理会提供更多物质支持外,中国也期望在未来可以在为理事会制定、解释和实施议程、议案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