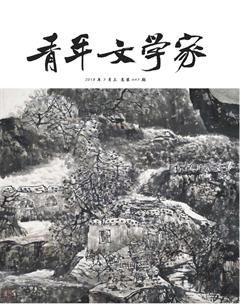杰克伦敦:人生与文学的互相成全
陈晓黎
娘胎里开始的苦难
1875年6月初,《旧金山纪事报》报道了一桩悲惨的新闻:一位孕妇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因为不愿意打掉自己腹中的胎儿,她被丈夫赶出了家门。这位自杀未遂的孕妇名叫弗洛拉·韦尔曼,来自俄亥俄州马西隆市富有的韦尔曼家族,此时距她离家出走已有5年。她可恨的丈夫钱尼教授,是一位酷爱航海、学识渊博、门徒众多且因出色的预言能力而受人尊敬的星象学家、作家和演讲家。如此耸人听闻的报道很快被全国各地的报纸转载。汹涌而来的民众发誓要把钱尼教授抓起来吊死,他很快从旧金山消失;备受同情的弗洛拉被接到好心人家里,靠给人占卜、上台演讲唯神论及民众的集资帮助过日子。1876年1月12日,弗洛拉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约翰·钱尼。8个月后,随着弗洛拉与约翰·伦敦结婚,这个还在娘胎里就饱受惊吓的孩子,改名为杰克·伦敦。
1896年,杰克终于打听到了钱尼教授的消息,他给钱尼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解开自己长久以来的疑惑。钱尼教授直到1899年6月4日才回信,他称杰克为“亲爱的先生”,并指责当时的报道严重失实。他强调自己与弗洛拉有同居无婚姻,声称胎儿不是自己的骨肉,抗议弗洛拉用假自杀逼他就范……在这封信寄出后不久,钱尼教授死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没有看到新世纪,没有看到杰克·伦敦的崛起。
虽然钱尼教授坚决不承认杰克与自己有血缘关系,但杰克简直就是钱尼的翻版。除了面容身材、走路姿势、说话腔调与钱尼极为相似之外,杰克的天性里还有着和钱尼一模一样的东西——热爱航海、喜欢冒险、嗜书如命、坚持写作,以及对贫穷的生活进行追根究底的拷问……
生父成谜,但杰克的生命中并不缺少父爱。约翰·伦敦,一个失去了妻子和儿子并独自带着两个女儿生活的老实人,在娶了弗洛拉之后,将杰克视如己出,还专门为他请了一个黑人保姆——珍妮妈妈。这名经历了南北战争的老兵,性格开朗,是属于土地的一把好手,不管是做蔬菜买卖还是办农场,他都做得有声有色。杰克在自家农场学会了骑马、养牲口、下地干活、酿酒、打野鸭、钓鱼……他跟着养父学会了敬畏土地,而养父那些打仗的故事,也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
大概在杰克10岁的时候,一场鸡瘟令家里的农场破产,约翰带着全家回到了奥克兰,靠借债租下了海边的一处村舍。杰克要靠自己赚钱才能维持上学的开支,他送报、到码头跑腿……在辛苦的日子里他有了一个伟大的发现——奥克兰公共图书馆是免费的。他一头扎了进去。和同龄孩子不同的是,他最爱看的是航海、探险、游记类的书。他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宏愿:世界那么大,要做一个马背上的水手,干一番事业。
从“蟊贼王子”到流浪少年
日子越来越艰难,13岁那年,杰克不得不辍学。他要把做工赚来的钱交给母亲,他自己能支配的钱则来自收集烟盒里的卡片、捡拾二手货。他养成了精明的生意人头脑,经他讨价还价,商品总能多卖出一些钱。他凑了些钱,买下了他的第一艘船,虽然破烂漏水,但他硬是靠这艘破船掌握了驾船技术。然后他又攒了一些钱,买了一艘稍好些的船,自己上漆、挂帆,只身驾驶小船穿过暴风雨中的旧金山湾。他开始加入当地的蟊贼帮派,袭击私人经营的牡蛎养殖场,把掠夺所得卖出,并以在帮派中年纪最小、胆子最大而开始小有名气。他急需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船,这样他一个晚上就可以挣200美元。后来他从一个老蟊贼手里买下了“狂欢”号单桅帆船,雇用了几个水手,成了蟊贼里最年轻的船长,被称为“蟊贼王子”。
在蟊贼帮里,酗酒、斗殴、抢地盘是家常便饭。杰克在15岁那年已经是一个屡经战斗、九死一生的首领,带着女朋友在几百千米的海路上自由浪荡,名声响亮。海湾巡警找到了他,劝说他加入渔场巡逻队,担任副队长,于是他又成為这一带蟊贼和海盗最怕的人。
1893年,刚过完17岁生日,杰克便决定去闯荡更广阔的世界。他加入了“索菲亚·苏德兰”号,奔赴白令海峡和日本海捕猎海豹。上船的第三天,正好是杰克掌舵,半夜里狂风暴雨、海浪滔天,他独自驾驶着这艘摇摇晃晃的近百吨重的帆船,毫无惧色。他出色的驾船技术和一往无前的勇气,令那些把他当毛孩子的老水手刮目相看。他们一起喝酒、打架,一起讲故事、说粗话。在白天经受了严寒、风暴、最沉重的苦役的锻炼之后,到了晚上,杰克便躲在铺位上举着油灯读书,他读的是托尔斯泰、福楼拜、莫泊桑等人的作品。
5个月后,“索菲亚·苏德兰”号回到旧金山,杰克用赚来的血汗钱替家里还清欠债,然后便一头扎进图书馆。他把海上的生活经历写成一篇散文《日本海口的台风》,参加了《呼声》杂志的写作竞赛。令杰克意外的是,他竟然获得了第一名,还得到20美元的奖金。更令他意外的是,排在他后面的都是大学生,而他仅仅是小学毕业。
眼看约翰的身体已无法负担家庭,杰克必须留在岸上担当家庭的顶梁柱。奥克兰电车公司录用了他,他每天在地下室铲煤13个小时,全年无休,月薪30美元。仅仅干了一个月,杰克就严重消瘦、筋疲力尽。他听说这原是两个人干的活儿,现在由他一个人干,工资却还不到原来的一半。没多久,一名被他顶替的工人,因为无力养活妻儿便自杀了。这燃起了杰克的怒火,他加入了全国性的失业工人请愿队伍,向着华盛顿进发。
从旧金山到华盛顿,横穿美国。因为记错了时间,杰克没能与大部队一起出发。他扒火车、搭货车,一路猛赶。他身上能换钱的东西都被用来冲抵路费,两手空空时他便徒步乞讨,风餐露宿。在沿路乞讨中,他发现自己还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即在对方开门的瞬间便判断出对方的心理,编出一个投其所好的故事。
当他在内华达州赶上大部队时,他的鞋子已经磨破,脚上满是水泡。从全国各地汇聚来的失业抗议大军浩浩荡荡,衣食住行都成了严重的问题,终于在行进到伊利诺伊州时,队伍分崩离析。杰克继续扒火车,无拘无束也没有目的地,到了芝加哥,又到了纽约。他面黄肌瘦,还被警察打破了头,成了一个十足的流浪汉。他被抓进监狱做了30天苦力,看见囚犯发狂的恐怖情形,又看到一个年轻、英俊的犯人因与狱长争辩而被丢到5层的石阶下面。他在日记中写道:“直到我亲眼看到,我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惨无人道的事。”那些罪犯的堕落并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错,有些人是自暴自弃,但有些人则仅仅是法律的牺牲品。出狱后他扒上西去的运煤列车到了加拿大西海岸,然后从温哥华做水手南下,回到旧金山。这一路,他看到了从未见过的可怕情景,听到了无数有趣的、可怕的、悲惨的故事,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最能怜惜穷人的其实是穷人。
别人淘金,他淘故事
回到奥克兰家中的杰克,决定上大学。他看够了人间的苦难,相信只有知识才能解开他无数的疑惑。他离开学校已经6年,必须把虚度的时间补回来。
他计划用两年时间补上高中课程,他戒了酒,每天读书到深夜。先是在奥克兰高中,后来又上夜校。他不再与昔日那些打架斗狠的伙伴联系,而是努力摆脱粗俗,学着优雅。他读了圣西门、傅立叶、普鲁东的作品,读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到1896年夏天,他自学了高中语文、历史、物理、数学等课程,顺利通过了考试,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虽然母亲竭力支持他上学,但家中已经没有能力为他支付学费了。仅仅上了一年,他便选择了退学。
在上学的这段时间,杰克的写作大有起色。他比同龄人见多识广,虽然因为衣着寒酸而被嘲笑,但他在校报、校刊上发表的文章,令他结交了不少真正的朋友。他加入由奥克兰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亨利·克莱学会,发现自己的经历、才智和思想在一次次讨论中有了意义;他在市政厅附近向工人们发表激烈的演说,并因此被捕。
白天他在一个洗衣作坊干活,晚上在租来的打字机前写作。这台打字机老旧不堪,只能打大写字母,而且时时发出巨大的噪音。辛勤的写作导致他的肩膀得了风湿,脊椎骨像烟斗柄般弯曲。长期严重缺乏睡眠,令他憔悴不堪。他寄出去的稿件不断被退回,尽管他一直在咬着牙坚持,但前途迷茫。
1897年,阿拉斯加州的克朗代克发现金矿的消息传来,这给他带来了希望。姐姐伊莉莎抵押了自己的房子,帮他添置了衣物行李。同年3月,杰克和姐夫搭伴,踏上了淘金之路。
他们从旧金山坐船到斯卡吉山谷,然后开始徒步进发。这一路异常艰辛,在齐尔库山,杰克身背68千克的重物攀登陡峭的山崖,上下一次要一整天。但更大的艰险还在后头,他们必须溯流而上。杰克和在路上结识的4个同伴砍伐木料,做了两艘小船。在穿越水流湍急的布克峡谷的时候,杰克用精湛的驾船技术拯救了很多束手无措的淘金者,赶在严冬到来之前将他们顺利带到拉博格湖。他靠驾船挣到了3000美元,在史都华河口修建木屋,开始淘金。然而他们千辛万苦淘出来的“金沙”不过是普通的云母石屑。整整5个月,外面冰天雪地,杰克就在木屋里和人聊天、读书,他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有弥尔顿的《失乐园》和布朗宁的诗,学习如何从人类痛苦的际遇中描绘精神的特质。
杰克的野外生存能力让他在淘金者中享有盛名,他能在暴风雨中点着火,做出可口的火腿煎饼,也能在森林里就地取材支起帐篷。他驾船通过峡谷天险如履平地的事迹口口相传,他的木屋也成为淘金者的“圣地”。他出手如此大方,分享食物毫不吝啬;他讲话又如此有趣、明智,让人忍不住对他掏心窝子。很快,杰克的冬季储备不够用了,食物短缺,他得了坏血病。这场病几乎使他瘫痪,他的关节肿胀得厉害,以致他走路时必须弓着腰。他的牙齿纷纷掉落,脸上长疮、出现水肿。好在终于熬到了5月,河面渐渐解冻,他决定启程回家。经过19天,他终于抵达了白令海峡。他卖掉自己的小船,搭上一艘货船当了锅炉手,来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市,再从温哥华搭船回到旧金山。他没有找到一块金子,而是带着听来的上百个故事结束了在克朗代克的淘金旅程。
贫穷在文学中得到了安放
回到奧克兰的杰克已是身无分文。此时约翰·伦敦已经去世,约翰的去世让杰克感觉自己失去了一个随时可以回来疗伤、哭泣的港湾,也让家里失去了顶梁柱。在没有稳定的收入之前,他不能再随便离家远行。他决定参加邮政局的录用考试,在等待补缺的日子里,踏踏实实地把自己一肚子的故事写出来。
杰克曾记录了他投稿的情形,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的80多篇稿子被退回400多次,只有15篇作品被录用,若将他的退稿便条堆积起来,有近两米高。他的压力很大,时常担心遭受失败,微薄的收入又常常使他为生计操心。
1899年对于杰克而言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份。1月16日,邮局通知他去上班,月薪65美元。这是一个可以维持一生的铁饭碗,他马上就可以摆脱贫苦的日子了,还可以获得女友父母的同意,娶妻生子,过上比普通劳动者好一些的稳定生活。但是杰克犹豫了,他已经从写作中获得了他最在意的快乐,正计划着把他20多年的人生故事一一写出来,他不相信那些来自蟊贼、水手、囚犯、流浪汉、淘金者、失业工人的故事没有价值,即便稿费寥寥,他也正走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但现实生活中又有一个困难:母亲会怎么想?
弗洛拉这时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这一刻,她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文学一边,她告诉儿子,只要还能从写作中获得快乐,她穷死都不怕,她坚信儿子一定能够成为伟大的作家。
这一年,杰克以极大的毅力笔耕不辍,他不在乎那些退稿信上对他的评价,不愿意写一些甜腻腻的平庸琐事来讨好读者。行过万里路的他已经被生活教导,他要把人世间的苦难提炼出来,把他体悟的人生真谛大声地喊出来。他疯狂地阅读,用自己的头脑接受、批判、思考,随手记下的卡片塞满了房间的每个角落。
第一笔稿费是这年1月份到的,数额是5美元。到了5月份,有4家杂志登了他的作品;6月份,他有5篇小说发表;曾经嘲笑他的奥克兰的报纸现在称他为“本市一颗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冬天的时候他完成了中篇小说《北方的奥德赛》,寄给了以高不可攀而闻名的《大西洋月刊》。这一次他没有接到预料中的退稿,随着录用通知一起寄来的,还有120美元的稿费支票,以及出版社出书的邀约。
杰克喜极而泣,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他才24岁,可他经历的颠沛流离和传奇冒险,却是大多数人一辈子都难以想象的。这些经历,将和他的名字一起,永远镌刻在世界文学的里程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