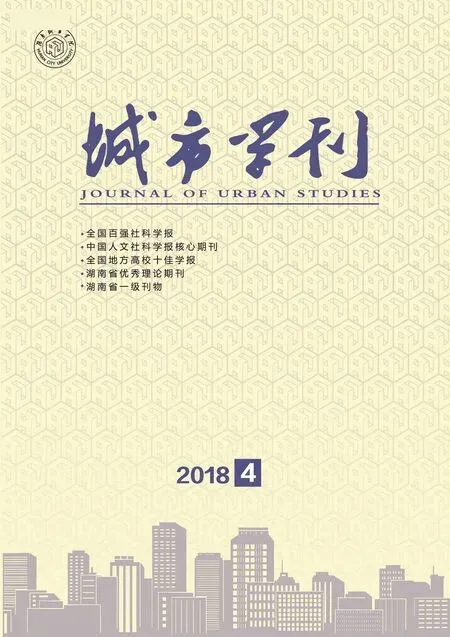恋城情结与心灵朝圣——鹤坪小说的执着与坚守
吕 健,王予霞
恋城情结与心灵朝圣——鹤坪小说的执着与坚守
吕 健,王予霞
(集美大学 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鹤坪是西安土生土长的作家,西安给予了他心灵的慰藉和创作的灵感。以这座古城作为题材,他创作了《说西安》《民乐园》《大窑门》等作品,集中体现了老西安的灵性。如果说,鹤坪前面的作品旨在揭开老西安的神秘面纱,那么,《俗门俗事》则让读者真正体味了老西安淳朴民风下的亲切与自然。可以说,《俗门俗事》是鹤坪继《民乐园》《大窑门》之后的又一力作,除了继续讲述老西安的民俗和那些被历史埋藏的记忆之外,更多的是鹤坪对这座城的心灵朝圣。
鹤坪;《俗门俗事》;老西安;心灵朝圣
鹤坪小说中都是老东西,是一些逐渐被现代所遗忘的老东西,恰如冯骥才所说:“鹤坪写的这些老东西有股子味道:历史的味道、民间的味道、陕西的味道,似乎还有点鹤坪的味道。”的确,鹤坪的小说有一种老西安独特的韵味,他只会写老西安,也只能写老西安,因为这座城对于鹤坪来说不只是生存培育他的土壤,更多的是给予他心灵的慰藉,使他在灵魂与心理表征上自愿向这座城致敬。因为自身与老西安的内核已经达到了整合的状态,所以鹤坪所讲述的老西安,不论是故事、传说、历史还是各种人物与风俗显得格外真实,并且对于那些不了解西安内蕴文化的人来说,也能察觉到这种立体感,并从中油然而生出想要去一探究竟的新奇感。这便是鹤坪小说的魅力。
《俗门俗事》并不是鹤坪第一部描写老西安的小说,之前《说西安》《民乐园》《大窑门》中,他已开始了陕西方言小说的写作。在以普通话和北京话为主流话语的中国文坛,地方方言小说的发展成为一股清流,无疑为当代中国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新思路。《俗门俗事》中,作者全景式地展现了老西安各类行业、各种风俗,带有史诗性质的书写,描写出了一个地方,抑或一个城市的味道,而对这种琐碎零散生活与俗事的建构,使作品传达出一种难以名状的诗意,由此,老西安城的独特魅力与心灵震撼力也就凸显出来。
《俗门俗事》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通览全书内容,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民俗民风下的人文景观;二是略带诙谐幽默的文风与方言特征;三是对手艺人的缅怀与致敬;笔者将从这三个方面来阐发鹤坪对于老西安这座城的心灵朝圣,揭示其自身在现实状态下的恋城情结。
一、民风民俗浸润的人文景观
从《俗门俗事》的书名便可窥见这部小说的中心离不开“俗”。鹤坪在《俗门俗事》的自序中这样解释道:“俗就是了,没有文野之争、雅郑之辩,俗是私事。切入了大众生活和社会生活,你才能切身感到:惟有俗是真正‘关心’与‘写生’的人生艺术。”也就是说,鹤坪有意使《俗门俗事》充满质感,因为“俗”贴近生活,也是将大众生活展现的最好方式。
随着大众文化日益深入,发掘民众日常生活、取材民间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民俗和民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地域中广大民众所创造的、享有和传承的文化特质。在现代中国文坛,乡土化、民俗化的小说创作势头从未发生断裂,如鲁迅笔下的江南鲁镇,贾平凹、陈忠实所代表的陕军,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等等,文学寻根也从未间断,这是民族文化自觉性的展现,同时也是对拥有旺盛生命力的地域文化的一种救赎。鹤坪便是这样的卫士,从被民风民俗包裹着的《俗门俗事》中就可以观照出,鹤坪不仅要写出自身对于老西安的朝圣和追忆,更希望能够将这些文化留在人们心中,绵延不绝。
《俗门俗事》分上下两部:上部主要涉及底层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俗事,有关于民间习俗的《庄户人进城》《撞干大》等,也有描写下层穷苦劳动人民的《拾娃婆和她的糙爷们儿》《媒婆红喜儿》等;下部则主要写老西安行业轿杠铺的兴衰、奶妈故事以及为建设西安呕心沥血的老辈夯班的故事等。整部小说不仅塑造了老西安人民的生动形象,而且从侧面表现出老西安这座风水宝地的独特人文气质,使得这藏在人们记忆中的老城给与读者特有的景观感受。众所周知,民俗主要分为物质民俗和社会民俗,前者满足人们基本的生存需求,包括衣食住行;后者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社会关系需求,如婚丧嫁娶、节庆、家族、家庭、行业习俗等;此外还有精神习俗,它满足了人类的情感需求,如道德礼仪、宗教信仰、民间文化等。这三个方面就构成了一个地域或地区主要的文化架构。《俗门俗事》便集中体现了老西安关于这三个方面的民俗。
在《庄户人进城》中,“农历四月初八是西安城祭祀城祖“稷王爷”的日子,古称“忙农会”,也称“忙笼会”。四乡庄户人有在城会期间“逛城”的讲究。”庄户人逛城就是为了迎合老西安的精神习俗。而在《春女》中,主要讲述了老西安古老行业轿杠铺的一系列习俗,“城里的轿杠夫都叫杠头,抬轿时前面的是“弁杠”,“弁杠”也叫“龙杠”,负责给后面的杠头“报路”,唱杠花子。”鹤坪笔下的民俗充满亲切感,类同于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观点:
从历史和现实看,对一个人的生活经验和价值信仰起关键作用的因素之一就是那些民风民俗和日常生活习惯,而不同地区所表现出的民俗和习惯有时千差万别。一个人从出生开始,他所身处的环境和风俗就会持续不断地塑造他的一切。
这样的评价用于鹤坪的创作心态与创作动机,也是恰如其分的。鹤坪由于对这座城的心灵诚服,而要将它的珍贵画面尽力描绘出来,他不单单是文化上的寻根,更多的是寻找这座城的灵性,是心灵上的体悟,他执着地要去打开老西安封闭的门。
除了彰显老西安的民俗质态,鹤坪更加关注它的人文景观,这是《俗门俗事》更为深刻的内涵。所谓景观是作者自身的主观体验,主要侧重于对人地关系的理解与感知,鹤坪在他的作品中有意将老西安作为一种地域景观呈现出来。在《俗门俗事》中,他并未对老西安的城建、环境做过多描述,而使景观成为一种抽象、被赋予一定意义和价值的元素。人文主义地理学强调,“地方”是一个稳定且有序的意蕴世界,“地方”不仅是空间或是场所,更是以“人的观念为特征”的意蕴载体。因此景观在《俗门俗事》中作为一种地理要素的同时,也是主观体验的一种表述方式。
小说中所塑造的老西安便是这样一个稳定且有序的空间。在这里,城里的土著们按照从上传下来的习俗、规约而生活着,人们对于这块土地的理解上升为老西安的秩序,一种印在脑海里不会被磨灭的信念,在老西安的诸多礼俗里,“摆供桌”这种路祭形式是最富人情味的。对穷汉来说,“摆供桌”是对富户的由衷感恩,对富户来说,“供桌”的多少则显然是本门本家贤良乐善程度的一个标记。
在老西安,穷汉对富汉的这种习俗已超越了贫富阶层的界限,富汉对穷汉帮衬、穷汉在富汉死后摆供桌,这些都成为老西安城民众心照不宣的秩序,也是老西安人民人性中善的集中表达,鹤坪通过这些故事不仅要展现老西安这些文化,更多的是作家自身的主观体验,他用文字如实地再现了老西安的人文镜像,但更多的是传达其中“微妙的人文特质”,揭示老西安潜在的人性价值,老西安的水土养育了一批生性善良、朴实的人群,它用自身孕育的风气滋养了这些文化,使这种文化上升为精神图腾,这是鹤坪最为感同身受之处,也是《俗门俗事》所要表现的中心议题。
鹤坪的小说是对老西安独特人文景观的细致描绘,但却不能将其归为普通的乡土小说行列,从书中字里行间可以觉察出,鹤坪对这座城的敬仰和热爱程度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乡土依恋”,更多的是一种“敬城情结”。鹤坪是受老西安的滋润和熏陶成长的,他也将老西安作为文学形象传达给世人,除了有对老西安人文景观特质的详尽呈现,同时也包含自身的文化寻根,探寻老西安孕育这些文化、发生这些故事的根因。
从地缘上看,西安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成为多民族融汇的聚集区。陕西是连接关内与关外的重要隘口,西安作为陕西秦地古都自然聚集了来自关外的少数民族,其中数量最多的要数回族人民。西安至今还保留着一大片回民区、回民街。鹤坪在《回坊,庚子年的那一道曙光》中,讲述了庚子年慈溪太后“西狩”时,与回民之间的传说。回民善良质朴,为老西安做着自己的贡献,得到了慈溪太后的尊重。老西安不仅庇佑了汉族土生土长的民众,同时也包容了这些来自外乡的“回回”,这些都凸显了老西安独特的文化包容性,这也是鹤坪所赞颂的。其次,关中地区地大物博、土地平旷,因此也就诞生了粗犷的民风,关中多义士侠客,这些人赤胆忠心,劫富济贫。《俗门俗事》中对于关中著名侠客“黑脊背”也有所描述:“黑脊背游走在东、西二府,以刀客自居,以打家劫舍为营生,打着劫富济贫、除霸安良的招牌。”连慈禧太后都赞叹:“西安城风罡土厚!想不到这一方人物竟如此尚武!”在肯定关中出英雄的同时,对老西安水土养育下的人民,慈禧太后也很称道。《俗门俗事》便是从这几种故事类型中,展现了老西安文化产生的根因,同时也是作家鹤坪的内心认同。
民俗民风下的老西安,是鹤坪的内心向往,也是他虔诚的归属。鹤坪通过这些俗人、俗事,表现了这块土地的地域特征、文化表现力、人文景观,加之自身对老西安的“恋城情结”与情感认同,展现了鹤坪笔下独特的老西安。
二、地域生态承载的劳动人群
与其说鹤坪在《俗门俗事》中描绘了一座城、一座沉淀了诸多文化积土的老城,不如说他表现的是这座城里的人和事,旧人和旧事缠绕在一起,就组成了老西安的特有韵味。《俗门俗事》展现了生活在这座城里、与老西安融为一体的原生态居民,老西安城庇佑了这些劳动人群,使他们安居乐业、老有所依;而这些人同样也在守卫着老西安的一切,使它经久不衰。人物可以通过事情展现出来,事情可以经由人物描述出去,鹤坪便是在《俗门俗事》中让人物与事情,互照互鉴,相映成趣,透过事情,体现出老西安“人物”的精神韵致和形神美仪,而人物衬托的事情则反映出老西安的文化内在底蕴,更加鲜活。
在小说中,鹤坪采用了传统“说话人”或者“说书人”的方式,不仅交待了人物关系和故事的掏腾,还将西安人身上独特的“味气”掺杂在人和事情中挥发出来。细细品读,在字里行间便能感受到老西安的真实民性:坚韧自信、朴实厚道,带有某种愚钝顽冥。同时,也可以嗅触到一股既矗立着贵族的深宅大院又弥漫着乡村泥土气味的古城氛围。《俗门俗事》中的故事充满生活艰辛和平民温情,其中也有传奇性的故事,但是,更多的是展现平民生活。在鹤坪的笔下,富人和平民没有等级界限之分,他们平等地被归为劳动人群和手艺人的行列,在老西安城互相扶持,营造了和谐融洽的城民关系。鹤坪对这些民间手艺人是敬仰的,不论是拧绳的、捏笼的、挑担的、吆车的,还是做生意的有钱人,这些代表老西安地域生态的民间手艺人,都是鹤坪所要致敬的对象,他极力挖掘这些人群的事情,加以描述和叙说,一方面展示老西安的文化氛围,更为重要的便是表现对传统的留恋和缅怀。
作家在《俗门俗事》中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有进城赶集的庄户人、接生的拾娃婆、说亲的媒婆、自食其力的寡妇、老西安的王傻子、站门汉等下层劳苦人群,也有关于老西安城大家贵族勤俭节约、善待穷人的故事;其中还穿插了各类各样的传说,还有关于刀客的、神医的这类富有传奇性的人物等等。小说的上部以简短的小故事、传说和野史为主要成分,在这些故事中以《手艺人的饭碗》和《食客与袖狗》最能反映作者对老西安传统手艺人智慧的赞叹,同时也包含着对这些文化逝去的苍凉之感。传统手艺和现代工业似乎本身就存在着矛盾与对立,现代工业机器的产生挤压了传统手工,手艺人的局部反抗换不来全面的胜利。在《手艺人的饭碗》中,老西安的泥瓦匠靠着自身的智慧暂时获得了“新派”人物的尊重,但是短暂的退让没能改变手艺人的境况。在《食客和袖狗》中,作为清朝统治时期带入老西安的食客行业与袖狗文化随着清朝的灭亡,也逐渐消失,老西安的特色再也无迹可寻,连作者也不禁感慨:“一个朝代灭亡了,必然有许多寄生于这个时代的东西与它同时灭亡。”
小说的下部以三则较长的故事构成,老西安传统轿杠铺的兴衰,为老西安城哺育一代又一代人的奶妈行业,以及解放时期为西安建设付出辛劳的夯班。鹤坪既对这些老西安传统随时光流失而遗失破产感到惋惜,同时又对这些能够展现老西安地域生态的土著人民感到由衷的敬意。这些人没有很高的文化程度,没有先进的思想,但是他们维持着老西安的秩序,他们骨子里带有老西安的味气,以最为本真的形象或状态印证了老西安的地域生态。
在未来的某一天早上,我们可能会惊异地发现:除了使用的钞票是机器时代的“制式”产品之外,生活当中的其他需要已经完全托付给了手艺人。手艺再一次回到了“手艺人”的身子上,使他们的身子像充满气体一样的“气鼓昂扬”,使他们迈出的每一步都豪迈豪壮。
这是作者的愿景,也是手艺人的归宿。在他看来,生活在老西安的劳动人群都是值得敬佩与追忆的手艺人,他们对于老西安的意义是难以磨灭的,老西安庇佑这些生灵,而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维护这里的秩序与规约,老西安的历史文化积淀靠这些生民坚定地传承下去。《俗门俗事》不讲老西安的前世今生、辉煌时刻,也不讲老西安的杰出人物,反而定笔于这些旧事、旧人,老西安的氛围诞生这些人物、事情,而这些人物、事情又构成了淳朴的老西安,最终凝聚成《俗门俗事》的中心旨归:向这座老城致敬,同时也是向城里生生不息的劳动人民和文化传统致敬。
三、质朴韵味的方言叙述
《俗门俗事》的第三大特征便是融入在小说中的方言叙述。鹤坪不是第一次使用西安方言来创作,早在他的《说西安》《民乐园》和《大窑门》中,就奠定了这样的创作基调,《俗门俗事》则是对这种方式的升华。毫无疑问,鹤坪是运用方言写作的高手,他能将老西安的俚语、俗语、民谣等方言形式以最为通俗的方式展现,陈忠实就曾经说过:“地方方言,最好是给人读懂,也不用全懂,百分之七十的人能懂就行。”鹤坪对于方言在小说的运用就是这样,他是可以用文字将这些土话表述出来,给予读者最为形象的表达,民俗加上方言的结合,使得《俗门俗事》更加充满质感,形成幽默谐趣的文风。
语言是一个国家、民族甚至地域历史文化特征最为直观的展现,它的文化甚至是文明承载力是不可限量的,它对于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传承与传递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可磨灭的。方言是对一个地方、地区生民形态的指涉,因此,方言对于一方水土文化的重要性决定了它不应被遗忘,也不应被消灭,从这样的层面上去看,鹤坪用老西安方言撰写的《俗门俗事》十分入味儿,如此地道的方言,不仅仅表现了西安语言的沉浊、鈋钝、质直等特征,更是表现了小说所要展示的历史感、现场感和鲜活感,老西安便是在这样的语言中被鹤坪写活了,充满立体感,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以方言取胜,也是鹤坪写作的特点。
评论家伍立杨曾将鹤坪评价为:“语言艺术的孤臣孽子。”只有鹤坪这样的鬼才,才能将民俗文化与方言特质相互杂糅、包容结合,这种创作态势下写出来的文章,对读者最容易产生的便是带入感,对于读者接受来说,没有什么比得上身临其境更加引人。《俗门俗事》开篇《庄户人进城》就这么写道:
天麻麻亮,吆车的和逛城的四乡庄户就早早赶到了城门楼子下。城门还没“放闸”,庄户人借着天光刚刚能辨识出老槐树上栖落的是黑老鸹(乌鸦)还是“花大姐”(喜鹊)。吆车把式搂着鞭杆子窝在车辕上打瞌睡,车上坐满了逛城的庄户人和他们的孩子。男孩子都在额顶蓄一绺头发,俗称“金盖瓦”,后脑勺上再蓄一根小辫子,俗称“富贵根”;女孩子都用红丝线扎“帽盖儿”……庄户人搂着鞭杆子坐在车辕上,咂吧着牙花子嘟囔:“这就算进城了。城里可都是比咱乡下人高一头、大一膀的裂倔人物。——你瞅,一个个看着牛气蜈蚣,日踏谁的江山呀!”
这段简短的描述,就将庄户人进城的体验表现得淋淋尽致,使老西安倍感亲切,丝毫没有陌生感。西安方言惯用叠词,比如,“天麻麻亮”,骡马大车哗啷哗啷地往城里面走”以及西安方言里面也多把字句,“这边‘天香村’门前的二掌柜也跟车把式搭上了话:‘捎二斤桂花糖,把娃甜一回!’”
《俗门俗事》里充满了老西安的俚语、俗语,但是,鹤坪将老西安的顺口溜和民谣也纳入其中,平添了许多诙谐意味。在下部《春女》中,老西安传统行业轿杠铺并不单单承载运送的业务,杠房还有承接婚礼和丧事的业务,而唱杠花子、吆喝也是杠房所要具备的把式,在丧事中,杠房掌柜唱道:“告知天王和城隍,苦主锣锣奔仙乡。平生没与人争嘴,为人没有胡日鬼。一路消停悠悠走,安顿早早报周祥。”而在喜事中,杠房的执事头唱道:“花轿到门前宾主站两边,鼓乐接淑女礼炮迎新亲,鸾凤鸣双喜蓝天种美玉,聚乐生祥瑞佳女配佳婿……一撒金,二撒银,三撒新人进了门,缓缓走,悠悠站,模样丑俊新房里见,过了牌楼朝前看,牛家的老辈子门前站,要得好,话说巧,要得有,跟着婆婆尻子走……”《俗门俗事》所有故事都是用这些简单却细密的民间语言来叙述和描绘,“老西安人说话就这味,保持着鲜见的城市文明与农业村社文明的紧密联系,其语言特点不吃涩、不滑别,形神皆备。”鹤坪凭借着自身对老西安的熟知,抓住了老西安方言特质,从容、灵动、逼真,用俗而得雅,不仅再现老西安的历史和风情民俗风物,同时也复刻了老西安的灵性。
“往直白里说,小说的根在民间俗世那里,写出的只能是平易简淡的俗浮世事、浮沉浪事、油盐琐事……小说就是熔铸传奇、杂学与语言的‘手艺活’。”在鹤坪看来,小说不是一定要背负时代任务和政治使命,同时小说也不是功利性的存在,小说只是挖掘民间素材,展示民间文化的手段,小说不一定要展现宏伟的事件,反而民间俗事更加贴近人群,这样《俗门俗事》的故事扎根于老西安街头巷尾、巷里巷外,用带有质朴韵味的西安方言代为叙述,讲述陈年老酒般悠远的故事就显得别有风味了,质朴逼真的方言盘活了整部作品,同时也揭示了老西安的纯正生态。
文学不仅仅是“人学”,同时它更是“情学”,因为情最贴近人类生命本原,直接源自于人类本能和原始欲望状态,也最能反映潜藏在人们潜意识中的能量和能力,激发人们的想象和创造力。鹤坪从初期创造的《民乐园》《说西安》和《大窑门》到现在的《俗门俗事》都是在将作品的文学形态转化为“情学”,通过情感的真切,而提升艺术的感染力。
鹤坪以老西安为主题的乡土小说创作基本都以老西安的人文景观、土生土长的民众和质朴的地域方言为主要框架来支撑自己的作品,而这三种特征之间也存在内在的关联,老西安的人文景观孕育了淳朴厚直的民风,滋养了这些朴实的劳动人民;而后者也成为老西安人文景观的象征,地域方言则穿插其中,既反映老西安的文化气息,同时也激活了劳动人民的鲜明形象,实现了城与人的对接。围绕着这三个基本框架,鹤坪的乡土小说在丰富饱满的同时,更多揭示了人性的回归。读者可以从中体味出诸多特征和情感,但是唯一不变的,是他心中对老西安的坚守与执着,《俗门俗事》是对老西安的朝圣与致敬,老西安的传统、历史,潜藏的人性价值与文化底蕴是鹤坪持续的关注点,老西安的神髓韵致在他的笔下美好呈现。
[1] 鹤坪. 俗门俗事[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17-193.
[2] 冯骥才. 鹤坪笔下的老东西[N]. 文艺报, 2017-5-12(08).
[3] 贾平凹. 我说鹤坪[N]. 文艺报, 2017-5-12(08).
[4] 鹤坪. 说西安[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268-270.
[5] 郑佳. 《日诞之地》中的地理景观:人文主义地理学视角[J]. 外国文学评论, 2016(3): 155-157.
[6] 宋欢. 民俗与小说的邂逅[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7] 李霁宇. 语言艺术的孤臣孽子[N]. 文艺报, 2011-9-23(06).
[8] 殷国明. 论“文学是情学”[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3): 1-3 .
Loving Knot and Spiritual Pilgrimage of Xi’ an: Persistence and Perseverance in He Ping’ s Novels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China)
He Ping is a native born writer in Xi’an. Xi’an has given him consolation and creative inspiration. Taking this ancient city as a subject matter he created works like Xi’an, People’s paradise and Dayao gate, which embodies the spirit of old Xi’an. If the work in front of the crane is aimed at uncovering the mysterious veil of the old Xi’an, the Vulgar folk custom makes the readers truly to appreciate the kindness and nature of old Xi’an’s simple.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Vulgar folk custom is another effort of He Ping after the People’s paradise and Dayao gate. In addition to continuing to tell the folklore of old Xi’an and those memories that have been buried in history, more it is the pilgrimage to the city.
He Ping; Vulgar folk Custom; old Xi’an; pilgrimage
2018-06-21
吕健(1993-),男,安徽芜湖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王予霞(1963-),女,河北邯郸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I 206.7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8.04.019
2096-059X(2018)04–0104–04
(责任编校:彭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