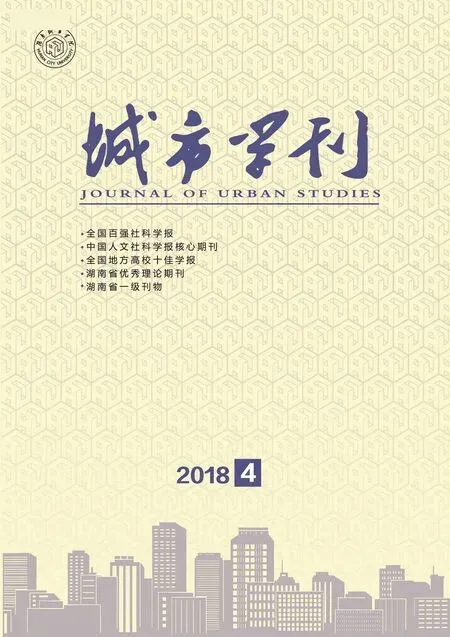论陈仓近年中篇小说的城乡书写
温江斌
论陈仓近年中篇小说的城乡书写
温江斌1,2
(1.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2. 南昌社会科学院 南昌 330038)
陈仓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创作20余部中篇小说,显示出深厚的创作潜力,得到了文坛和学界不小反响。纵观这些小说,作家以他独有的诗性叙事美学,游走于乡村与城市,在进城者的命运变迁和精神漂泊中,叩问转型时代的生存本相和精神依归,呈现出作家深切的现实关怀,为新世纪文学创作增添了一抹亮丽风景。
陈仓;城乡;精神;诗性
新世纪以来,在文学受到市场经济和媒体操作多重冲击下,作为具有独特文体规范的中篇小说创作持续稳健,保持文学基本品格,得到众多文学读者和文学批评家认可,体现了坚守纯文学的热情和勇气。自2012年以来,作家陈仓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以其丰沛的创作精力先后在《钟山》《小说月报》等当代重要文学刊物发表《父亲进城》等20余部中篇小说,题旨之鲜明、题材之切近、风格之清新,一时为文坛和学界所瞩目。纵观这些中篇小说,作家以他丰富的生命质感,独有的诗性叙事,游走于乡村与城市,在展现人物的命运变迁和精神裂变中,叩问着转型时代进城者的生存本相和精神依归,呈现出作家深切的现实关怀,为新世纪文学创作增添了一抹亮丽风景。
一、游走于城与乡之间
城市与乡村是陈仓中篇小说的重要空间,他的小说大多有一个城乡的背景,一边是偏僻贫寒的山村,一边是霓虹灯闪烁的城市,如果说乡村是“老土地”的指向,那么都市则是“新生活”表征。“老土地”的沉重情感与“新生活”的强大冲击,诸多故事就在二者的碰撞中渐次而来,形成一个个富有张力的文本。处女作《父亲进城》就从城乡背景迤逦展开,小说叙写了一个从未离开大山的古稀老人,在儿子劝导下,来到城市体验新的生活。无论是乘坐飞机、上街观景,还是居住入厕、吃喝洗澡等等,生发出诸多忍俊不禁的细节。这种看似喜剧的背后实际是农耕文化与城市文明之间异质经验的“断裂”。在转型之际的城乡二元结构中,《父亲的晚年生活》直陈当下农村的凋敝,这个叫塔尔坪的山村是中国成千上万农村的代表,它荒芜和凋敝是那么触目惊心,传统的手艺、民俗、烧窑、说唱、打卦、看相一切都烟消云散,甚至那赖以为生的农业收成都渐趋凋零,“连萤火虫都绝种了”。小说还以隐喻的手法复现传统文化的“失语”和陷落——曾经会唱戏的表叔成了哑巴、曾经会说书的先生成了瞎子。农村的凋零残破在《空麻雀》中有了进一步叙述:这个农村没有孩子出生,只有一个个老人死掉,因为人口稀少,抬棺材由八个人变成了六个人,坍塌荒芜的农村浮现出一幕幕幻影幢幢、歧路丛生的痛楚。
作家书写农村又不止于农村的破碎秩序,而且将农民置放到城市大空间中去,以此返照出农村的失落与茫然,这些人物生活于城市,不过城市仅仅是他们活动的场景。这些来自农村的底层人们,如奶妈、妓女、和尚、建筑工人、民间艺人等等,对于城市来说,他们是一群“他者”。这些底层人群进城后孤独无依、备受磨难,经历着经验世界的碎裂,《墓园里的春天》的陈元从杂志社编辑放逐为墓园的销售人员;在《羊知音》里,民间艺人的“我”为了生活、为了姐夫医药费和拯救那只羊,无奈卖血并屈服为被利用的“杨绵绵”;《从前有座庙》里的打工妹小月,被理发店老板强暴后怀有身孕,为了活下去,只得卖身和乞讨;这些人物在现实中的无奈困顿,让人备感辛酸。就连《猪的眼泪》《羊知音》里的那些进城动物,都难逃异化的渊薮,成为“人”的生存寓言式表征。作家谛视着这些底层人和进城动物,他们的生命创痛和沉重命运正是现代性冲击下农村陷落的症状,作家以自觉的意识对抗遮蔽于城市潜在秩序,对记忆中的乡村进行不间断地回眸和追认,希冀在逝去的陷落中重新突围。
如果说塔尔坪是小说反复指认的乡村,那上海则是小说不断确证的城市。相比不断给予乡村美好回忆和无尽伤感,作家对都市上海似乎持守着一种审视和批判的目光。在这些中篇小说中,他将人性中负面、庸俗给予了城市,如《墓园里的春天》里庸俗势利的都市准岳父岳母;《山里有座庙》里只知道追逐物欲、没有信仰的熙来攘往的城市人;《猪的眼泪》里嫌弃农村父亲汗味的岳母以及挑剔的邻居;《女儿进城》里罚款、租车、游玩、进公园,城市的一切充斥赤裸的金钱交易;《麦子进城》的城市在给孩子提供新奇和先进同时,更带来各种令人不安的担忧和隐患:找女学生的老板,猥亵小贩女儿的保安,都可以让人嗅到暗藏在城市繁华背后的各种危险;甚至《木马记》里城市人林太太的奶水都是干瘪的。当然,作家对城市的态度是复杂的,他说,“我对城市的感情,其实与一些夫妻之间的感情有些类似。说爱吧,谈不上,说恨吧,也没有,但是想要分手,太复杂了,牵扯的东西太多了。关键是分手后,你还有更好的选择吗?”[1]然而,面对一个僵硬冷漠和格式化的城市,作家似乎有着诸多的不满情绪,《上海不是滩》里农民小孩就说,他的理想长大后要成为一名电工,希望有一天把电闸给拉了,灭灭城里人的威风,男孩的偏激与其说是发泄对城市的不满,不如说是作家将批判态度指向了现实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秩序。《木马记》是书写城乡二元对立最为集中和宏阔的一篇,所涉及了职业歧视、农民工子女城市上学等问题发人深省,小说讲述一个失去新生儿的农村母亲张小泉为城市林小宽夫妇小孩哺乳的故事,城里人林太太对喂养小孩的苛责挑剔、对他人颐指气使以及高人一等形象在当代城市有着某种典型意义。小说中张小泉女儿天真活泼,对城市生活充满向往,但是却难以入学,失落无望绝食自杀。为了实现女儿入学愿望,作为母亲张小泉无奈中不得不委身于林太太的弟弟——幼儿园做饭的师傅,为此,小说将城乡二元结构给予人的压抑悲呛上升到一场有着深度意义的社会反思和批判。
小说在对农村荒芜颓败和人们困窘命运的书写中,凸显着变革之际进城一代的命运异变和无奈悲凉,展示出转型时代下都市与乡村的变幻莫测,深刻地反思和拷问造成诸多矛盾和异变的城乡二元结构制度,那种刻骨铭心的书写蕴含着作家苦苦探寻的现实命题:在城与乡分裂对立中,乡村何去何从,进城的乡村一代又行将何处?
二、进城人们的精神漂泊
城乡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一个主要问题,陈仓敏锐地把握到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民进城现象,同时又不流于简单描述而是深入其中捕捉“阵痛”时代的进城人物的精神症候。因此,他的中篇小说不但描写了诸多人们进城中命运变异,而且展示出他们精神漂泊与裂变——城市生活中的怀疑不安与焦灼疏离——作家将时代转圜过程中压抑、彷徨和渴望等复杂心理予以了多元重现。《小妹进城》叙写了一对陌生男女因为回家途中的大雪,把他们神奇地安排在了一起。然而一系列的事件一次次把两人带入猜忌与怀疑之中。最后,一只猫轻易地破坏这桩浪漫的邂逅。小说写出了相互设防、彼此怀疑的时代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似乎在一个充满怀疑的时代里,没有浪漫奇迹的出现。《羊知音》叙写了作为艺人的“我”在城市拉二胡,却难寻觅知音,最后只有一头来自山村的羊倾听了并随之舞蹈。而那些城市观(听)众在选秀节目对“我”的力挺支持,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热爱艺术,而是为了观赏奇异的表演和满足自己扭曲的心态。《兔子皮》以寻找雷管为线索,讲述了都市人内心的恐慌与不安,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颗雷管,都在忐忑的担心何时爆炸。不安和怀疑成为城市人的常态,“因为在这个大变迁的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太多了,人们太没有安全感了,每个人都需要伪装自己,也需要防备别人的伪装,只有充满怀疑我们才能减少伤害。”[2]168《上海不是滩》小说中那个“流水落花”的女人究竟真是一个疯子还是职场设置的桃色陷阱,连“我”自己似乎都没有明白,一切显得那么不确定,每个人在城市的身份显得非常可疑,“城市是一个不断膨胀的气球,是变幻着的,是漂浮着的,你不知道她的根在哪里,不明白她想干什么,她来这里与你有什么关系。”[3]120城市里这种惶惑不安甚至在人死后都难以得到调和,在《墓园里的春天》中一个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游子离世后,城市的岳父岳母和农村的父亲母亲为能将他安葬在身边,最后只得分别在城市与乡村安葬两个墓,某种程度寓意着身体与灵魂的割裂,这种疼痛正如小说的诗歌所写,“我漂泊的一生/可能需要两个坟墓……请不要让我自己和自己分开,分开/在那块金色的麦地里无名的小河边/为我的肉体与灵魂再安排一次重逢”[2]213,小说在看似荒谬中流露出浓浓的焦灼。
进城的男女难以融入城市,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那种压抑孤寂、飘浮无根的茫然又迫使他们寻找精神的突围。《麦子进城》里的记者陈元与按摩小姐“小四川”的畸形亲密,实际意味着疏离于城市的人们难得的撞身取暖。虽然他们只是固定的嫖客与妓女关系,但是因为相同的农村出身与居住城市的漂泊感,使他们在思乡的倾诉中相互温暖与慰藉。最后陈元带着麦子和“小四川”、余发财从城市撤离,或多或少有着城市挣扎幻灭过后精神归乡。然而,曾经的个人记忆早已颓败,荒废的故乡与无名的大都市已经阻断了他们还乡的归家之路,也阻断了可见的历史绵延。《空麻雀》在故事结尾处通过叔叔的返乡希冀重建乡村、皈依乡村,可是无论从叙述底气还是已有结构的对接,小说似乎显得有些苍白,乡村已然破败,人们的灵魂却难于皈依。对于精神突围和皈依,作家反而用死亡这个话题作了具体演绎和初步解答。在作家的中篇小说中,有4篇是讲述死亡或跟死亡有着紧密关联的,如《父亲的棺材树》《美丽而亡》《墓园里的春天》《影子进城》等。《父亲的棺材树》讲述的是喜欢栽树的父亲,无论什么时候,他总留下最好的树,为自己打棺材,随时准备把自己埋掉。父亲把人生归宿寄托在那棺材上,深刻表达了农村父亲对生活有着质朴的信念。《影子进城》以对话方式叙写了在父亲病逝离开后,儿子恪尽孝道背着父亲的遗体周游上海,完成了一次复归人性本真的精神旅程,发出了对生与死的终极叩问。《美丽而亡》写了秀花精心照顾叶老太太,对老人的黑白颠倒、喜欢在深夜里唱戏、从不愿将身体示人等这些怪癖,她都想尽办法解决。在叶老太太临终时,她精心地为老人化妆,让其“美丽而亡”。死亡是人类生活中的自然现象,但人们对死亡讳莫如深。在作家笔下,死亡是可以直面、追问和可以美丽的,皆缘由自身对精神的丰满自信。在某些意义上,作家叙写这些就是要直面精神皈依——善待了死亡和理解了死亡,活着就不会那么焦灼和彷徨,灵魂亦将安渡裂谷、怡然此岸。
一个作家在拥有自己艺术世界的同时,还必须对这个世界的精神有崭新的认识,小说写作的使命不仅是要讲故事,它还需要探寻人物精神和灵魂。陈仓小说展现了跌跌撞撞进城人们的思想情感波澜,也一直以在场者的目光苦苦探寻进城人们无根无家的精神恐惧。在创痛迷茫和不安惶恐的今天,在都市迷宫与危险丛林的现实,情归何处、心归何处——这或许是作家希冀在小说中所能表达的深刻能指和文化诉求。
三、浸润情感的诗性叙事
陈仓是一位不断实践着文体和语言创新的作家,他在艺术上进行了多向度的美学探寻,如《空麻雀》中的书信体、《上海十日谈》的日记体、《影子进城》中的第二人称叙事、《我想去西安》的倒叙手法和儿童视角、《墓园里的春天》的荒诞色彩等等,都是作家探索叙事艺术的重要表征。在二十余部中篇小说中,最为引人瞩目是他的诗性写作。贾平凹说,“如今他写起了小说,依然具有诗人视角。”“以诗人式的思维,诗意地写作了一系列作品。”[4]他自己也曾说,小说要成为经典,诗性成分是非常重要的。陈仓最早是从事诗歌创作,当转向小说创作时,写诗的精神自然汩汩地流淌其间,诗性叙事成为他小说文本的特殊文化修辞。
诗性叙事是指小说叙事的诗化倾向,是叙事话语系统所表现的对普遍叙事语法的逻辑背离。陈仓小说的诗性叙事首先体现在他小说内容中诗歌文本的植入。如《美丽而亡》屡屡重现“玉蜻蜓”评弹,《墓园里的春天》的“双碑记”诗歌,《上海十日谈》里“我”为米昔写诗,“进城”系列的十四首诗歌题记,等等。这些诗歌嵌入增加小说文本情感维度,并以在场的、显现的方式凸现出与日常话语相疏离的诗意空间。如果说将诗歌直接置入小说文本还是某种表面的诗性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些中篇小说大都充溢着作家情感的抒发——故事总是随着情感而波动,情感的变动成为结构小说的主要力量。《空麻雀》里的少女陈雨心以写信的方式倾诉对远在上海做建筑工父亲的思念,写出农村留守青少年那个孤寂的心灵。《影子进城》以絮语方式和悲悯的态度展现父子之间一场悲呛的隔世对话。《上海十日谈》在“我”与天使交往的十天时间里,他们时而睡在一张床上,时而游荡于山水之间,两个人在爱与不爱的对话间,缠绵悱恻又感人泪下。这些书信、独语、絮语和对话是作家在小说叙事中的重要方式,散发着作家的主体感受,“心灵化”叙述也使得故事张力得到丰富的延拓。
陈仓小说诗性叙事还显示在他的话语系统和语言运用上,他的语言简单明晰,多用短句、少用长句,叙事语调不紧不慢,从容安详,表现为节奏性的重复,有着明晰和清新的语境,隐藏着传统审美的趣味。如《木马记》在写到来自农村奶妈张小泉下楼后一个人在小区里踟蹰行走,当来到埋葬儿子花圃时,“我看四下再没有一个人了,于是像奶孩子一般弯下腰,解开自己胸脯上的两颗扣子,掏出了自己有些胀痛的乳房,轻轻地捏着。我充盈的白色的乳汁,一股股地流了下来,洒在了几株有些蔫巴的花上。这些乳汁一股股渗入泥土,泥土上有一条条裂缝,像是埋在根下的一张张小嘴巴,在轻轻地吮吸着。那几株花,被我用乳汁浇灌过后,就随着微弱的风轻轻地摇晃起来。”[3]135这些语言融叙事、描写、抒情等表达元素于一体,处处充满了对物像的感悟式描绘,映现的物像传递着淡淡的悲情,激起了人们对这位痛失儿子又无私哺育他人儿子的母亲的深切同情。这些诗性的话语不断地衍生和增殖,唤起无限诗意,同时强化了文本的喻示功能,充溢着丰沛的主体情志。陈仓小说正是以他的诗性话语实践,以他浓厚的浪漫气息、生命体悟和情感评价,在对时代转变的逼视与剖析、对城乡巨变中人性的考察中,展现出文学介入现实的强力和叩问人类生存本相的魅力。
丰富的生活现实使文学丰厚沉着,深切的生命体验提升文学的精神意义。陈仓的中篇小说,在某些地方还存在叙述琐碎、情节类型化、表达过于柔婉等问题,然而作家以他的苦难经验和人生体悟,写现实、写当下,诚恳地进行有温度的写作,为新世纪的文学创作增添亮丽的风采,一如学者王干在对包括陈仓等一批作家评论时所说,“70后作家尤其是男性作家在经历了成家立业、社会打拼之后,销蚀了身上的青涩和浪漫,他们开始正视生活的严峻,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因而他们的写作洗脱了早期先锋派的形式主义意味,沉浸到对生活、对人生、对人性的感悟和思考中,在创作上开始呈现出新的审美意向和文学态度。”[5]我们注意到,陈仓的《墓园里的春天》《从前有座庙》《喜鹊回到屋顶上》《如果没有鬼》等几篇小说已经显露出超越生活经验、探寻新的写作方向的端倪,为此,有理由相信作家在未来的创作中,将带来更丰富和更成熟的风格。
[1] 王湛, 裘雪琼. 进城的人,为什么总惦记返乡[Z]. 钱江晚报, 2015-05-10(05)
[2] 陈仓. 充满怀疑的社会没有浪漫[M]// 小妹进城, 北京: 红旗出版社, 2015.
[3] 陈仓. 如何界定一株秧苗的身份[M]// 小妹进城, 北京: 红旗出版社, 2015.
[4] 孙欢, 黎婧萱.贾平凹为家乡作家助阵[Z]. 西安晚报, 2015-08-09(07).
[5] 王干. 在夹缝中缓缓地成熟——谈70后作家的创作格局[Z].光明日报, 2013-06-25(14).
On the Urban and Rural Writing of Chen Cang’ s Novel in Past Few Years
WEN Jiangbin1,2
(1. S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2. Nanch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chang 330038, China;)
Chen Cang has created more than 20 novels in a short span of three years of time. He showed the profound creative potential, obtained the literary and academic quite a reaction. Throughout novellas, Chen Cang asks transformation era lives living nature and spirit of the city, with his unique poetic narrative, roaming the countryside and city, in the fate of the characters change and spiritual fission, it presented the author deep realistic care, added with a bright scenery for literary creation in the new century.
ChenCa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spirit; poetic
2018-06-18
温江斌(1980-),男,江西赣州人,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 206.7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8.04.018
2096-059X(2018)04–0100–04
(责任编校:彭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