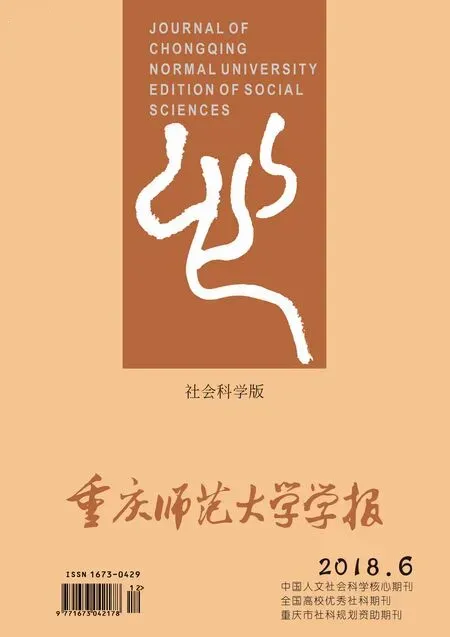张竹坡评点《金瓶梅》动因论析
曾志松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缘由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揭示《金瓶梅》中的文法。张竹坡盛赞《金瓶梅》的文法“针线缜密”“千针万线,同出一丝”“曲曲折折不露一线”,而“圣叹既殁,世鲜知者,吾将拈而出之”[1]212。另外一种说法是寄托说。张竹坡族人张省斋提出:“道深……曾批《金瓶梅》小说,隐寓讥刺”。[2]88隐寓内容,则语焉不详。至于是否含有寄托,张竹坡的表述则前后抵牾,《第一奇书凡例》:“作《金瓶梅》者,或有所指,予则并无寓讽。”[3]1476《竹坡闲话》说:“然而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也哉。”[3]1482评点的动因会对评点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鉴于“知人论世”的批评传统,学界对这一问题涉及较多,但多泛泛而谈。笔者仅见杨杨的硕士论文“从具体的客观条件和事实来分析张竹坡评点背后的心理结构”[4]12,对这问题给予了较多关注,但可继续深入的空间还有不少。
一、 家世巨变,借评点遣闷怀
张竹坡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伯父张胆、张铎入清后都做过高官。其父一生不仕,在家奉养母亲,正因为这一点,张竹坡家受到伯父们的资助,少年时代张竹坡家境宽裕。张竹坡自己在诗作也说“少年结客不知悔,黄金散去如流水”[5]261(《拨闷三首》),表明日子过得非常殷实。据吴敢先生的考证[2]64-89,与他们家族有交游的文化界的名人有:陈贞慧、李渔、尤侗、侯方域、张玉书、戴名世、张潮等等。如此盛大的交游圈也是张竹坡家族鼎盛的一个旁证。
十五岁是张竹坡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张竹坡父亲去世,他的生活走向贫困。张竹坡在他二十六岁那年评点《金瓶梅》。在评点的过程中,他写了一首《乙亥元夜戏作》,有句云:“归来虽复旧时贫,儿女在抱忘愁苦。”[5]260其间“旧时贫”表明他的境况已经很久了,他说“忘愁苦”,实际上却表明他忘不了。《金瓶梅》的评点使他“才名日振”[1]212,但名声的扩大并没有使他摆脱贫困。张竹坡在二十七岁秋冬之际参与了《幽梦影》的评点。《金瓶梅》和《幽梦影》的评点在时间上接近,可以大致认为《幽梦影》的一些评语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他内心的状况。在《幽梦影》评点中,张竹坡不止一次提到贫病的窘困。《幽梦影》第23则原文是:“境有言之极雅而实难堪者,贫病也……”张竹坡评曰:“我幸得极雅之境。”[6]40第69则谈及著新书注古书均是千秋伟业。张竹坡评云:“注书无难,天使人得安居无累,有可以注书之时与地为难耳。”[6]84他在第122则评曰:“无益之心思,莫过于忧贫;无益之学问,莫过于务名。”[6]129他虽然认为“忧贫”“务名”是最“无益”的,但是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他“忧贫”“务名”的深层心理。
少年富足与失怙之后生活上的落差,使张竹坡较早感受到人情的冷暖。他十九岁时作《乌思记》感慨:“至于人情反复,世事沧桑,若黄河之波,变幻莫测;如青天之云,起灭无常。噫,予小子久如出林松杉,孤立于人世矣。”[7]129张竹坡的伯父张胆、张铎功名显赫,张竹坡却处于“久如出林松杉,孤立于人世矣”的境况。“孤立”心理的产生,应该与来自伯父一支的“人情反复”相关联。张竹坡在《幽梦影》第93则的评语也指向此:“求知己于兄弟亦难。”[6]103张竹坡有亲弟弟张道渊,从张道渊为张竹坡立传及传中赞语的情况来看,他们兄弟是知己。据王汝梅先生考证,张道渊在张竹坡死后曾经主持过张评本的复刻修订[8]106。因此,张竹坡的这则评语不是针对他的胞弟张道渊而言的。考虑到他在《乌思记》所说的“人情反复”“白眼穷途”之语,他这句话所指是他父辈的兄弟或者他的堂兄弟。
张竹坡在《金瓶梅》的评点中表现出对兄弟伦理的呼唤,《竹坡闲话》:“天下最真者,莫若伦常;最假者,莫若财色……若夫父子、兄弟,如水同源,如木同本,流分枝引,莫不天成。”[3]1480-1481张竹坡视父子兄弟等“伦常”为“天下最真者”。相应的对“假父假子、假兄假弟”予以批评,并指出其根源在于富贵金钱对伦常的冲击作用:“将富贵,假者可真;贫贱,而真者亦假。……贫贱,冷也,冷则无不假。”[3]1481联系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前后的相关文字——上文提到的《乌思记》和《幽梦影》中的评语——我们认为,张竹坡这段针对财富颠倒伦常的议论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如果说这里的议论是在借议论小说《金瓶梅》而隐藏自己的锋芒,那么在《竹坡闲话》的结尾则跳出评论,直指现实:“迩来为穷愁所迫,炎凉所激,于难消遣时,恨不自撰一部世情书,以排遣闷怀。”[3]1482由此看来张竹坡有借《金瓶梅》这一部“世情书”来感慨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直接诉求。
正是因为张竹坡在《金瓶梅》的评点中隐藏了对族兄的不满,才会导致张省斋指出张竹坡“批《金瓶梅》小说,隐寓讥刺”却又语焉不详。张道渊则避而不谈。张竹坡既想挑明,又想掩饰,从而前后矛盾。
二 、久困棘围,借评点畅心志
张竹坡早慧,六岁时即能即兴对出“河上观音柳,园外大夫松”[9]73的佳句。据张道渊《仲兄竹坡传》记载,张竹坡有“读竟复诵,只字不讹”[2]246的过目不忘的神奇智慧。
张竹坡的父亲虽然自己不愿出仕清朝,但寄希望于早慧的张竹坡,希望他早日取得功名。张竹坡自己也极度自信,有“壮志凌宵志拂云”[5]261的抱负。但现实人生却是非常不幸:“五困棘围,而不能博一第。”[2]247十五岁的张竹坡首次参加乡试落第。十八岁再次落第。他性格中盼望出人头地的一面开始以凄厉的形式出现,作于十九岁的《乌思记》云:“矧予以须眉男子,当失怙之后,乃不能一奋鹏飞,奉扬先烈,槁颜色,困行役,尚有何面目舒两臂系五色续命丝哉。”[7]129他认为不能在功名场上扬眉吐气,便连“舒两臂系五色续命丝”的面目都没有。二十四岁,张竹坡第四次落第。那年冬天,张竹坡特意北游京师,访长安诗社,“登上座,竟病分拈,长短章句,赋成百余首。众皆压倒,一时都下皆称竹坡才子云。”[1]211张竹坡此举意在表现他文学方面的才华。他的愿望得到了实现:“一时都下皆称竹坡才子云”。但是名声的获得没有帮助张竹坡摆脱贫困,也没有帮助他获取功名。他在《乙亥元夜戏作》称“归来虽复旧时贫,儿女在抱忘愁苦”,“归来”指的是长安诗社夺魁归来,其生存状况依然是“旧时贫”。
二十七岁,也就是评点《金瓶梅》的那年秋天,张竹坡第五次落第。他对科举、君主乃至天命都开始怀疑,但对自己才华的自信仍在,在《幽梦影》的两则评语反应了这一心态。《幽梦影》第63则原文:“十岁为神童,二十三十为才子,四十五十为名臣,六十为神仙,可谓全人矣。”[6]79-80对于这一全人的人生模式,张竹坡云:“神童才子,由于自己,可能也;臣由于君,仙由于天,可不必也。”[6]80这一评语中表现出了对“君”“天”的不信任。第180则原文:“宁为小人所骂,毋为君子所鄙;宁为盲主所摒弃,毋为诸名宿之所不知。”[6]184张竹坡评道:“后二句少足平吾恨。”[6]184张竹坡将那批掌管科举路径的“主”斥为“盲主”,对自己才华信心满满的言外之意便相当明显了。
即便五次落第,张竹坡依然寻找着建立功名的机会,“眼前未得志,岂足尽平生”[5]261。在张竹坡人生的最后两年中,先是贫病客居于苏州,之后北上,效力于“永定河工次”。清廷甚是重视治水,借此获得富贵者不计其数,仅张竹坡一族就有道源、道溥、道汧等取誉于此。同族兄弟的成功之道必定给张竹坡巨大刺激与希望。在久困棘围之后,张竹坡为自己找到了一条通向“男儿富贵”的道路。在“永定河工次”,张竹坡“虽立有羸形,而精神独异乎众,能数十昼夜目不交睫,不以为疲惫”[1]212,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不幸的是在永定河工程竣工的时候,“呕血数升”而亡,所留遗物“惟有四子书一部,文稿一束,古砚一枚而已”[1]212。 “四子书”即四书。从张竹坡的遗物来看,张竹坡在永定河工程上依然在准备科举考试,表明他对科考获取功名并没有完全绝望。
张竹坡把自己对科考既失望又保持希望的复杂心态带到了评点中。《金瓶梅》中西门大宅里是“一片淫欲世界”[3]1512,众多妇人中唯有孟玉楼有较好结果:再嫁给李衙内,夫妻敬爱有加。张竹坡把孟玉楼的好结果归因为“宽心忍耐,安于数命”[3]1500。孟玉楼因“宽心忍耐”而独有结果,恰好符合张竹坡久困棘围而依然盼望成功的心境。所以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时特别重视孟玉楼,认为作者写玉楼是“自喻”:“至其写孟玉楼一人,则又作者经济学问,色色自喻皆到。”[3]1486《金瓶梅》作者是否有意识地在孟玉楼身上投注了自己的寄托,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张竹坡在孟玉楼身上投注了寄托则是毫无疑问的,他主张将《金瓶梅》的题目更换为“奇酸记”:
……故作《金瓶梅》者,一曰“含酸”,再曰“抱阮”,结曰“幻化”,且必曰幻化孝哥儿,作者之心,其有余痛乎!则《金瓶梅》当名之曰《奇酸志》《苦孝说》。[3]1488
张竹坡“含酸”“抱阮”云云,是对“高才被屈,满腹牢骚”[3]1495的孟玉楼的内外处境的一种总结。他在《竹坡闲话》中说得更清楚:“夫终不能一畅吾志,是其言愈毒,而心愈悲,所谓‘含酸抱阮’,以此固知玉楼一人,作者之自喻也。”[3]1480以“奇酸记”来命名小说就相当于将孟玉楼设置为全书的中心人物,将西门庆、潘金莲等设置为背景元素。张竹坡将一个相对次要的人物看成是最重要的人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孟玉楼最后有了一个好的结果。《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最后一则亦云:“以玉楼弹阮起,爱姐抱阮结,乃是作者满肚皮倡狂之泪没处洒落,故以《金瓶梅》为大哭地也。”[3]1513我们也可以说张竹坡的“满肚皮倡狂之泪没处洒落”,所以借《金瓶梅》中的玉楼来抒发他内心对待功名既失望又有希望的复杂心理。
文章开始时说过,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缘由之一是揭示小说中的文法。这是事实。《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开列了108则“读法”,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金圣叹给《水浒传》开出的15则。需要指出的是张竹坡从整体结构和细部伏线等方面开列出108则读法,其目的不仅仅是“喜其文之整密,偶为当世同笔墨者闲中解颐”[3]1476,其性质与诗社夺魁一样,是表明自己在文章方面才华出众,当下功名未就仅仅是时运不到而已,这也是他对自己功名尚保持希望的一种证明。
三、 奉扬先烈,借评点推崇孝悌
张竹坡家族笃守孝道,张竹坡的父亲就以奉养母亲而不出仕。张竹坡的家庭重孝道最为突出的例子是胞妹张文娴“算取花剪割股”[2]72偷偷地放在药鼎之内,以求父亲病愈。两年后,张竹坡十五岁时,张父去世,张竹坡“哀毁致病”[1]211。尽孝,奉扬先烈,甚至成为张竹坡追求功名的内在动力之一:
偶见阶前海榴映日,艾叶凌风,乃忆为屈大夫矢忠、曹娥尽孝之日也。嗟乎,三闾大夫不必复论。彼曹娥,一女子也。乃能逝长波,逐巨浪,贞魂不没,终抱父尸以出。矧予以须眉男子,当失怙之后,乃不能一奋鹏飞,奉扬先烈,槁颜色,困行役,尚有何面目舒两臂,系五色续命丝哉![7]129
曹娥是东汉有名的孝女,《后汉书》有传。十九岁的张竹坡将曹娥与屈原并举,可见曹娥所代表的孝在张竹坡心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张竹坡认为“当失怙之后”,就应当“一奋鹏飞,奉扬先烈”,即获取功名光耀祖宗。
二十六岁,已是四次落第的张竹坡,在《乙亥元夜戏作》称:“男儿富贵当有时,且以平安娱老母”,[5]260“娱老母”依然是他重要的职责。张竹坡做过一篇《治道》[2]243-245,写作年份不可考,但可以看作是他为“帝王师”的人生理想而撰写的一份施政纲领。在这篇纲领性的短章中,他认为“三代以上为政易,三代以下为政难”[7]127,其原因在于“人心不正,风俗以颓”[7]127。正人心淳风俗的关键在于“古人生而孩提之时,即教以父母之当孝也,兄长之当敬也”[7]127。孝悌俨然成为张竹坡“治道”中最为根本的一环。
在生活中,张竹坡笃守孝道。在《金瓶梅》的评点中,张竹坡也特别重视挖掘小说中“孝”的因素。首先,他认定《金瓶梅》的作者就是一个孝子。《竹坡闲话》中云:“《金瓶梅》,何为而有此书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呜唈,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3]1480这样就把《金瓶梅》理解为“孝子悌弟”的发愤之作。其次,张竹坡认为《金瓶梅》写作的动机是表达作者作为孝子的苦楚。他专门写了一个专论叫《苦孝说》:
故作《金瓶梅》者,一曰“含酸”,再曰“抱阮”,结曰“幻化”,且必曰幻化孝哥儿,作者之心,其有馀痛乎?则《金瓶梅》当名之曰《奇酸志》、《苦孝说》。呜呼!孝子,孝子,有苦如是![3]1488
张竹坡从他认定的作者是孝子出发,认为《金瓶梅》应当命名为《苦孝说》,其目的也在于突出孝。张竹坡对“孝”的重视在《第一奇书目》[3]1477-1479中表现得相当突出。张竹坡认为,《金瓶梅》中有一种重要的文法叫“两对章法”[3]1493,所谓“两对”即每一回中主要叙述两件事。具体参见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第8则。张竹坡将每一回目的两个关键词抽出,组成了《第一奇书目》,这实际上可以看做是整个小说的大纲。张竹坡对这大纲式的“目”,一共添加了9条批语。为了论述方便,笔者将其按顺序摘录如下,并添加序号:
1, 一 回 热结 冷遇 〇弟字起。
2, 十 回 充配 玩赏 〇金、瓶、梅三字至此全起。
3, 廿一回 扫雪 簪花 〇金、瓶、梅三人至此畅聚。
4, 廿九回 冰鉴 兰汤 〇全部结束
5, 四十六回 走雨 卜龟 〇两番结束
6, 五十八回 打狗 磨镜 〇孝子著书之意在此,教人以孝之意亦在此。此回以一个“孝”字照应一百回孝哥的“孝”字。
7, 七十五回 含酸 撒泼 〇是作者一腔愤恨无可发泄处。
8, 九十七回 假续 真偕 〇一部真假总结,照转冷热二字。
9, 一百回 路遇 幻化 〇孝字结。
这9条评语中,第2、3两条是指人物的出场、会聚、及其活动,第4、5两条是预述人物命运,即为书中人物“遥断结果”[3]399,这四条评语的关注点在于书中的人物。明清之际的小说批评家都重视人物,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与本题无关,此从略。“人情冷暖”的感慨和“高才被屈”的窘境分别由第7、8条来承担。强调孝则有第1、6、9条,占三分之一强,可见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时对孝的重视[10]。
张竹坡在生活中笃守孝,在治国理念中强调孝,在小说评点中突出孝。张竹坡于孝,真正做到了知和行的统一。对于自视甚高却又终未释褐的张竹坡来说,孝不仅仅是儒家的一种道德规范,还是一种人格上的精神支柱。
评点《金瓶梅》是张竹坡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小说批评史上的一件大事。评点《金瓶梅》让他名垂千古,但他志不在此。张竹坡写过三首题咏古人的诗,分别题咏“留侯”“酂候”“淮阴侯”[5]263,诗歌中对张良“终得骋其志,功成鬓未丝”、萧何“授汉以王业,卓哉人之雄”的成功人生表示了无比的艳羡,其间也有着自比张良、萧何的成分,在他内心有着“作帝王师”(《留侯》)的人生理想。对于武功赫赫最终被诛的韩信,则颇有微词:“既然用武善,为甚识机迟”(《淮阴侯》)。他写过《治道》一文谈论如何治理天下。但他最终没有成为“帝王师”,反而贫困交加,饱受人情冷暖。张竹坡评点《金瓶梅》属于“发愤著书”,与李贽、金圣叹评点《水浒》一样都是有所寄托的,他在《金瓶梅》评点中所蕴含的寄托不仅仅是张省斋所说的“隐寓讥刺”,还包含了更为广阔的生活态度以及人生追求。吴敢先生指出:“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把自己的家世遭遇情绪感触摆进去”,[11]17洵为的论。但是,张竹坡评点时主观情绪过于强烈,以至于他所阐释的主旨多与此相关,这就要求我们在接受张竹坡留下的这份珍贵遗产时需要冷静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