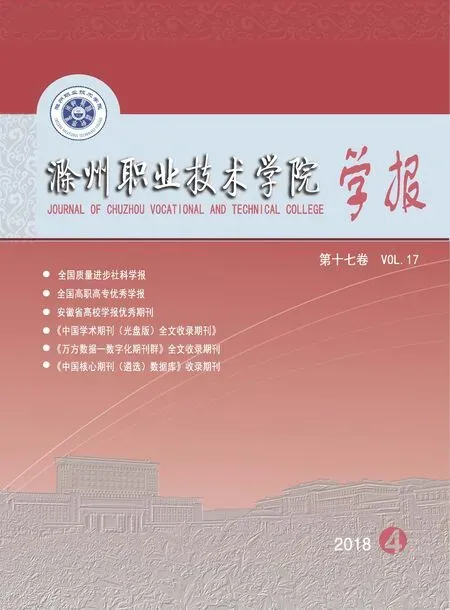“春华终不谢,一洗穷愁声”
——论晚清樊增祥“娱情”诗学观
薛超睿
(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0)
樊增祥(1846-1931),湖北恩施人,自进士而入翰林,从县令渐陟督抚,于清末地方司法及力推新政方面贡献颇多,是体制内官僚由保守转向开明的典型人物[1];同时他又是一位文才卓荦,喜好吟咏的诗坛巨擘,生前即有“诗豪”之誉。其创作之巨,今已难确数,章士钊《论近代诗家绝句》云“郁律蛟蛇四万篇”[2],钱基博估计有三万余首,陈衍称万余篇;樊增祥去世后不久,好友欲整理其遗著,结果感叹“多至二万首,无法整理,可为太息”[3],现存诗文词著作,除光绪三十二年付梓、后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的《樊山集》《樊山续集》各二十八卷外,尚有《闲乐集》一卷(1906)、《二家咏古诗》《二家试帖诗》各一卷(1901)、《二家词钞》一卷(1902)、《瞻园》五集(1911)、《集外》八卷(1912-1914),另有《樊山滑稽诗文集》(1913)、《樊山集七言艳诗钞》(1916)、《近著樊山诗词文稿》(1926)等;还有不少散见于民国报章,晚年无暇蒐集,笔者据此估计,樊氏一生作诗当逾两万多首。
(一)前人有关樊增祥诗歌的论述
樊氏好为艳体,同辈和后学对此各有轩轾,如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谓之“细写朝云,篇篇绮密,多应秀师呵叱。诗尚侧艳,自少至老,不变其体”[2];陈锐讽曰“其诗如六十美女,盖自少至老,搔首弄姿,矜其敏秀,为一时诸名士所不能及”[4],以致有“樊美人”之讥,樊氏生前即有耳闻,但并不以为意;从知人论世角度看,现实中他“无歌舞酒色之娱”、“疑为若何翩翩年少,岂知其清癯一叟,旁无姬侍,且素不作狎斜游者”[5],发妻亡故后十余年竟未续弦,连小妾都不曾娶,诚见诗如其人也并非绝对和唯一[6],故王闿运曰“大要为小旦作,故无深致。邪思亦有品限[7]”,由云龙亦道“盖因物兴感,偶奇闲情,正不必实有其事,要无害其人格耳”[8]。
樊增祥生平以诗为茶饭,无日不作,无地不作,陈衍谓“尝见其案头诗稿,用薄竹纸订一厚本,百余叶,细字密圈,极少点窜;不数月又易一本矣”,由云龙比之“如百战健儿,不愧萨都剌”,都指其创作多且速;他也沾沾自喜于此“才人落笔气豪健,倚马速成累百纸”,并以“多读多做多商量,庐陵诗法尽于此”为不二法门,而瞧不起苦吟派“”见人三日不成一字,或积学半生,箸书不盈寸许者,辄目笑之以为钝士”。这种能速不能迟的才人一病,被陈三立揶揄为“造诗机器”,大量作品面目雷同、形同套语,难免匠气有余而情旨不足“惟刻画工而性情少,采藻富而真意漓,千章一律,为世诟病”[2],晚年之作更“益庸滥,大都属文字游戏,诗道至此,可称一厄[9]”,正如陈子展所言“其长处在才气奔溢,短处在卖弄天才,贪多贪巧”[10]。
(二)樊增祥诗作的游戏化倾向
笔者认为,樊增祥的艳体诗作,多出于有意的游戏目的,创作不抱严肃态度,如其吟咏艳事最力的《十忆》诗二百首,不避内閫隐私,公开直露“惟有温韬鞳膝金”、“布指偷量小凤鞋”等不足为外人道的夫妻秘辛,尽管结尾以“愿度鸳鸯”作广大教化,表现齐家之道下有节制的欲望,主旨并无诲淫,但用最俗艳的笔,写最正当的事,缺乏隐喻寄托,仍不脱流于表象的玩赏意趣。至于他“最负盛名”的前后《彩云曲》,其事乃得知于耳食,辗转相传已有多处失实,历史细节更无从考证[11],连他自己都坦承“游戏笔墨,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窥其意,似不欲人再说,大有后悔之意”[12],所以只是一部暗含作家情色想象的戏说之作。
樊增祥的艳体诗中还有一大类咏物题材,所咏之物与诗人情感之间是相对独立的,具有显著的体物倾向;而将咏物又着一层艳感,则是樊增祥对宫体诗及韩偓《香奁集》的继承,如《咏灯》:
岭南佳制玉莲新,金盏兰膏故未贫。有味青编如昨日,相思红豆是前身。萧寒夜雨
宜闲话,隐约秋星替写真。愿得长明依绣佛,垂花双照玉台人。
所咏器物或是女性肢体的延伸,或为女性身体的装饰,都是借着联想得到性感的满足,诗中句句切合物体特征,又处处关涉女性色彩,达到物的艳化与人的物化合二为一,形成“丽而不淫,新而不纤”的风格。这种咏物诗“就题言之,则赋也”[13],即专意敷陈设色,随物赋形,强调“巧言切状,曲写毫芥”;重在“不黏不脱”,句句不现所咏之物,尽相又不致刻露,以形似之物比拟,围绕主题正反烘托,而无论“借物言志”的命意,这种无寄托的咏物,袁枚谓之儿童猜谜,朱光潜亦称“大半根据隐语原则”[14],带有游戏的意味。
除了艳体诗,樊增祥集中最多的就是郡斋诗,辗转州县,事简人闲,于是在官舍内精心布置,自得其乐,这种生活态度“使仕宦生活中的一切——风景、官署、斋室等都与吏隐之名联系起来,甚至还要绘成图画,属人赋诗,标榜自己超脱于宦劳俗累的心迹”[15],如其早年所作《拟桃花源诗三首叙》:
仆亲为负米,觍颜折腰,既蹀躞于风尘,更屏营于嫠纬。嗟乎!隙驹百年,单门八口,何虑不给而就微官。昔人不能降志于督邮,而顾手版倒持,为兹仆仆哉!苟有一廛,如渊明所记,稻田鳞比,花竹蝉嫣,所不即归,有如江水,因拟是题,寓息壤之意,若以吾意在避秦,则失之远矣。
意图已很显豁,既要获得风尘俗吏的现实利益,又希望超越俗务,居官如隐。樊增祥“不甘阁束方求外,雅好楼居为学仙”,时常在官廨和书斋中佛道双修“睡起闲寻道藏书”、“转珠惟诵藕花经”,以致“忘是儒生忘是吏”,超脱得一塌糊涂。
樊增祥对郡斋吏隐与繁忙公务分得很清:
或疑君勤求民隐,综覈精严,何能分题赌韵,如其在公车时;余之于诗如陆羽之茶,刘伶之饮,义取自娱,事无妨废,居常服膺宋儒玩物之诚,公事未毕,不得读书观画,及退食萧然,绿茗一杯,石叶数片,清吟抱膝,入兴成章。
工作中娴于事务,雷厉风行,退食后没有理由不可以逸乐,于是郡斋诗充当了消遣宦情的工具,从中很少读出忧国忧民的淑世情怀“扫除天下非吾事,只办萧斋对短檠”,而多是“官闲玩物华”的闲情逸致;这类作品常被评价为“格调降低、平淡琐细”,却忽略了生活中应有的园林之趣、诗酒之乐,在形塑文人中的重要意义,所以换个角度审视这些流连光景的小诗,其中不乏个性化、自然态色彩,流露着知足保和的情绪;而郡斋作为诗人的私人领域,属于一个独立于社会整体之外的个人主体,这一领域里的紧张总是被小心翼翼的加以调理,从而呈现一种游戏的面貌“在游戏的领域里,一般没有价值的地方可以创造出价值,原本微不足道的事物可以加倍增值”[16],这就是郡斋诗的价值所在。
入民国后,旧人物所仰赖的政教体制逐渐被边缘化,遗民成为一个尴尬的群体,樊增祥先是在沪上与诸老结超社,后应袁世凯之邀进京作了伴食参政,帝制失败后以鬻字自活。晚年的进退失据,是他对义利之辨的解构,对士林道德的弃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传统文学的载道观念也随之荡然;诗中充斥叹贫嗟老之语“黄金散尽还北走,坐使笼鸟惭冥鸿。大夫七十当致仕,我犹乞食颜为红”,时人也多由此抨击其文人无行[17]。樊增祥晚年所为益庸滥,如和易顺鼎“凌乱放恣、拉杂鄙俚”的《数斗血歌为诸女伶作》而作的《后数斗血歌》,用意变本加厉,语辞离经叛道,荒诞如“西京妖姬南国丽人之天癸”,粗鄙如“牛溲马勃败鼓皮”,颓唐已极,无以复加,论者无不扼腕“诗道至此,可称一厄”[9]。但樊增祥将其收入《樊山滑稽诗文集》,表明实有意而为之,以产生反讽与挖苦效果,达到犀利尖锐的责骂目的;世俗化甚至粗鄙化的书写,是语言的游戏与狂欢的另一侧面,是对崇高的消解,对传统的颠覆,具有黑色幽默的意味。
最后谈谈樊增祥用典中的游戏化倾向,他喜摭拾僻典,前人多言之,批评者如周达谓之“只做到生典熟用,有时且不免生典生用,其于熟典生用,不肯为,亦不能为”[4],欣赏者如陈衍调之“安石、碎金、樊榭、冬心诸家视之,当羡其沉沉夥颐矣”[18]。用典贵在常典反用、熟典生用、僻典偶用,要之隶事须无不达意,善达曲折之意,在此基础上可出其不意,产生陌生化的效果;而樊增祥用典,不过尽其对偶工巧之能,意在炫博矜才,晚年尤好诗钟,犹如科举之试帖,以典实工丽为鹄的,正合他腹笥鸿富、炫技逞才,故时常技痒而借此排遣。
(三)樊增祥的娱情诗学观探析
纵观樊增祥留下的两万余首诗,除了在重大事件、历史关头发表一些大声疾呼、关注现实之作外,绝大多数都比较清新博丽,弥漫着一种欢愉之情,这是对传统“诗可以怨”论调的反拨,有人称其诗“春华终不谢,一洗穷愁声”,他亦夫子自道:
文字多悲哀,岂有康乐理。扬云反离骚,吾恰与之似。将诗代丝竹,正赖陶写耳。操缦必和平,具食贵甘旨。五色选绯绿,七情专爱喜。
人皆谓余身居乐观,文无苦语。且夫殷忧屯险之遭,人生所不能免也,淡泊宁静之致,人生所不能无也。故宣圣以贫而乐为难,而广成以修厥身为寿。大抵乐府之遗,多以怨抑为工,曲屈其思,而婉微其旨,凄艳其质,而幽哀其音。小雅骚经,由来旧矣。仆百忧缠骨,六凿腐心,顾其为诗,了无苦语,良以终岁焦劳,惟此一事。是孔颜乐处,犹复虎贲屈子,优孟杜陵,哀乐乐哀,亦何自苦。明知愁语易工,欢悰难述,抑亦反离骚,蜀道易之遗意耳[19]。
钱钟书曾以中西两种理论对举,解释诗何以怨:
钟嶸的“诗可以怨”,目的是“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是把诗当做活人的止痛药和安神剂,强调了作品在作者生时起的作用,能使诗人和艰辛冷落的生涯妥协相安,借“可以怨”获得排遣、慰藉或补偿。
弗洛伊德认为“在实际生活里不能满足欲望的人,死了心退一步想,创造出文艺来,起一种替代品的功用,借幻想来过瘾”[20]。
樊增祥更接近弗氏之说,现实已经够累了,何必再于诗中写悲,徒增烦恼?故在诗中力求淡静之心,不作苦语。其次,陈衍指出樊山“欢娱能工,不为愁苦之易好”,一反韩愈“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之道而行,笔者认为,此大概受益于袁枚“富贵诗有绝妙者,谁谓欢愉之言难工”的说法,只要写我性情,不必强为悲喜,尝谓“昌黎云‘可怜无益费精神’,然作诗能娱我情,则非无益;吟不觉苦,自然成章,亦于精神无损。若如昌黎则真掷金虚牝,吾不为也”,于是走向了“要以敷鬯为宗,不以苦僻为尚”的诗学另一端。
吉川幸次郎曾总结过宋诗的一个特征,即开始认为人的生命不能仅仅被描绘为痛苦,而应超越痛苦,故宋诗中有一类与以往诗歌只能述怨的传统断裂,并有所修正,西昆体首当其冲,对乐的主题加以肯定,对无病呻吟似的哀苦之词则不以为然;欧阳修则主张,即使有理由感到沮丧和缘分,也应该保持一种雅然而乐的姿态。胡晓明也提出,在中国诗史上,有一条浅宋型路向“如公安派、性灵派,他们主张个人主义的,更多表现一种现实人生的情感化、情绪化和生活化倾向,其骨子里是一种世俗化的‘小人’文学”[21]。笔者以为这是一股隐伏于“唐型诗”与“宋型诗”之间的潜流,中唐元白、南宋四家、清代性灵是其源脉,樊增祥则处于殿军。这条路可能是中国文学向现代性转型的一个早期兆头,它的俗化倾向的确与新兴都市的某些口味契合;而樊增祥对自我情感化、情绪化和生活化的摹写,回归到世俗化和非功利的文学价值观,某种程度上带有“为艺术而艺术”的旨趣,所以他的作品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被屡次翻印或为证明。
但樊增祥诗学观的弊端也很明显,诗对于他而言,与其说是目的,毋宁说是手段,常为作诗而作诗,难免为文造情之病;文学创作文学创作得之于才识胆力,是一种感性的思维活动,而樊氏客观、精明,又有几分淡漠的天性,使他时常站在情外写诗,从而表现出过于节制的把持;且欢愉之辞,多浮于其表,易散漫而一发无余,所以比较淡薄而难以深入人心。从文化精神看,晚清民初国势日疲,士人呼唤阳刚,诗文多为载道“托命国运,回应危机,书写时代情怀,记录诗人心史”[21],雅正与淑世是主流的诗学特征与文化品格;从诗学路径讲,近代诗歌正是以矫正性灵末流,回归杜韩传统而发端;樊增祥却与此正道迥异其趣,耽于美感主义与辞章技巧,难免不合时宜,给正统主义者留下缺失士人担当的儇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