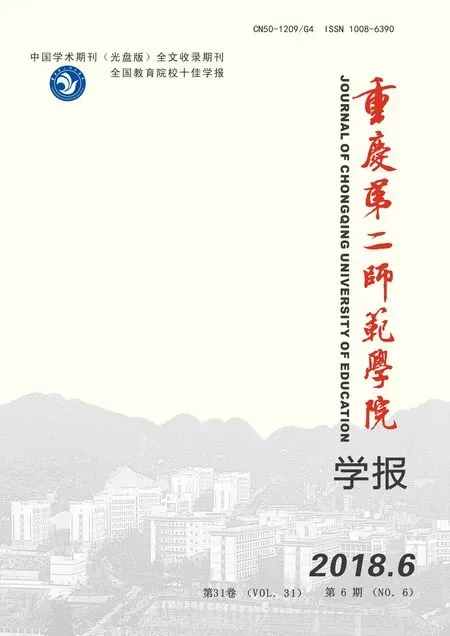对斯蒂芬·金作品《宠物公墓》的“恐惧和怜悯”研究
杨 烁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外语学院, 重庆 400067)
斯蒂芬·金是美国知名作家、剧作家、导演、制片人,其文学作品先后获得欧·亨利奖(1996年)、美国国家图书“终身成就奖”(2003年)、世界奇幻文学“终生成就奖”(2004年)、爱伦·坡“大师奖”(2007年)、史铎克奖(2008年)。他被誉为美国畅销书作家中的“常青树”。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评价“他的作品继承了美国文学注重情节和气氛的伟大传统,体现出人类灵魂深处种种美丽和悲惨的道德真相”。《星期日泰晤士报》更是赞美斯蒂芬·金“是美国当代的狄更斯,一位杰出的作家”。与同时代的其他恐怖文学小说家相比,斯蒂芬·金的小说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秘诀在于他在小说中制造出的恐怖触及了“恐惧压力点”——真正的恐惧触碰的是最原始的生活,恐怖作品撕碎了所有的粉饰只为找出真相,而这个真相先于艺术、超越艺术。[1]由于触碰到“恐惧压力点”,读者的时间通道被打开,接着被带回了童年,亲眼看到旧时的伤口被揭开,如同被催眠的人一样瞬间感受到恐惧、害怕和无助。
《宠物公墓》是斯蒂芬·金作品里极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在1986年获世界奇幻奖最佳小说提名,并于1989年改编为同名电影,该作品的成功绝大部分应该归因于它对于古典悲剧元素的继承。Douglas Winter[2]136认为《宠物公墓》表达了“恐怖是一种文学形式,它的真谛,如果借用哈姆雷特的话讲,就是所有活着的都会死去”,暗示斯蒂芬·金的恐怖文学和古希腊悲剧有某种联系。确实,斯蒂芬·金经常让读者感受到生活中的悲剧,比如令人瘫软的恐惧、无法忍耐的痛苦和死亡、万念俱灰的不幸,而看到这些小说中无辜的主人公在遭受厄运时的体会,人们心中产生了诸如“恐惧与怜悯”这样的情感,正好与伟大的悲剧带给人的心理感受类似。
一、《宠物公墓》中的悲剧元素
悲剧诞生于古希腊,是一种经久不衰的艺术形式,随着时代的变迁,它的表现形式有了相应的变化。在古希腊悲剧中,性格缺陷和命运是致使一个地位崇高的人物不幸的主要原因;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中,贵族人物受难或者死亡的原因虽然不是命运,但却是内部或外部的人为因素。总而言之,悲剧是由主人公性格缺陷或者坏人的恶意行为导致而成。无论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还是在18世纪的英国,以及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普通人代替了早期悲剧中的贵族或者历史人物,悲剧的原因也主要表现为性格的冲突和恶劣的环境。
悲剧人物在每个社会中的定位有所不同。定义《宠物公墓》为一部悲剧作品,主要是因为读者在阅读时发现一个受人敬仰的人因为过失酿下大错并因此饱受痛苦折磨时所流露出的感情——亚里士多德[3]75将此定义为“恐惧和怜悯”,“恐惧来自观看一个与我们相似的人遭受不幸,怜悯是由于我们认识到他/她遭受了如此巨大的不幸而引起的”。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关于悲剧作用的描述在学术界被广泛采纳并适用于多个悲剧艺术形式。
因此,当用“恐惧和怜悯”来衡量斯蒂芬·金的作品《宠物公墓》时,会发现小说主人公(一个受人爱戴和敬仰的人)确实遭受了巨大的不幸。斯蒂芬·金在谈到恐怖文学的角色定位时就提到:“(小说中)必须涉及爱,因为你越有爱……恐惧才越有可能产生,如果没有爱和感情,就没有恐惧。”[2]47虽然在此处斯蒂芬·金使用了“恐惧”而不是“悲剧”,但他却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即恐惧和怜悯来自爱。当作品中一个受人憎恶的角色遭受不幸时,观众们会认为是因果报应,然而悲剧作用的产生不是仅仅依靠积极正面的情绪,当一个可怜的人遭受不幸时,观众们仅会认为他可悲,而不能称其为悲剧人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中必须有选择和挣扎,换言之,一个真正的悲剧人物是深陷其无法控制的困境中,在与强大势力或对手交锋时做出了道德选择,并且会因为对手过于强大和自己错误的判断或者性格缺陷而遭受不幸。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以及米勒的“威利·洛曼”都败给了强大的势力,分别是命运、人类对手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同时,这些人物的性格缺陷和选择无疑也加速了其毁灭。《宠物公墓》的主人公路易斯·克里兹起初同样也是受人爱戴敬仰的人,他没有主动选择邪恶而是被邪恶选择,同时他的性格缺陷和错误判断导致了他及家庭的毁灭,这个悲伤的情节设计唤起了读者内心的亚里士多德似的“恐惧和怜悯”情感。
二、从“恐惧和怜悯”角度分析《宠物公墓》
斯蒂芬·金将故事分为三部分:“宠物公墓”“米克马克族古葬场”“伟大而恐怖的欧兹魔法师”。虽然这部小说被评论界公认为斯蒂芬·金最恐怖的作品,但在全书接近一半篇幅的第一部分“宠物公墓”中,却极少有恐怖场景出现。这是因为斯蒂芬·金模仿古希腊悲剧惯用的铺垫手法,营造了一个能够激发读者对路易斯·克里兹产生同情的故事背景,他在娓娓道来的描述中将读者带入一个典型美国小镇的普通家庭生活,在没有涉及维克多·帕斯托(一个因车祸意外丧生的人)和复活的猫丘吉尔时,本部分完全谈不上恐怖。主人公路易斯·克里兹博士是一个35岁左右的外科医生,性格温和,为人正直,不仅深爱家人,也关心朋友,如同每一位悲剧作家对主人公的必然设定一样,斯蒂芬·金让路易斯·克里兹成为一个与我们类似的普通人。在这一点上,他的作品更趋向于普通人的悲剧而不是古希腊或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公贵族的悲剧,主人公从幸福到悲惨的命运转变是悲剧的一个要素。虽然路易斯所从事的医学工作非常体面,但与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与“李尔王”这样的贵族相较而言,他与读者间的地位悬殊并不大。路易斯是谦谦君子,为人和蔼可亲,为了照顾家人,他选择在一个大学的医务室工作,而不是在大城市的私人医院谋职,在他的心中,妻子和孩子比他的前程和财富更重要。路易斯满足了读者对这样一个理想人物的期待。
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私人生活中,路易斯展现了从事专业研究的人所具备的理智客观、冷静自持,以及对事物的科学探究精神。在第一部分“宠物公墓”中,有一个场景是路易斯带着女儿埃莉第一次造访宠物公墓后和女儿之间的对话,埃莉询问父亲什么是死亡,尤其是这些宠物死了之后会怎么样,路易斯知道女儿的问题反映出她想关心自己的猫丘吉尔,但又没法在五岁的年龄正确地表达出自己的疑问。他秉持了科学诚实的态度回应女儿:“看,有种东西叫代谢,代谢的工作就是规定好时间……狗的代谢比较快,人的代谢比较慢”,但是理性的答案没办法安抚女儿,她开始大声哭泣,女儿的泪水让这个父亲动容,片刻间他突然认识到女儿无比真实的恐怖逻辑:如果所有的动物死后都会被埋葬,丘吉尔也会死去……也会被埋葬;如果这会发生在丘吉尔身上,也会发生在她的妈妈、爸爸、弟弟身上。对于她而言,死亡虽然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但宠物公墓却是真实的,墓碑粗糙的纹理就是一个孩子的手可以感知的真理。一贯的理性思维和尽力想表现的人性化只能让他说出:“宝贝,死亡会发生,它是生活的一部分。”虽然这个回答显得苍白无力,但却展现了一个父亲对孩子的深爱。这个场景本身没有展现激烈的冲突,正好相反,叙事上显得相当平淡——一个普通父亲试图去处理孩子成长中的“死亡意识”问题。斯蒂芬·金在第一部分中没有涉及任何他惯用的现实性或者超自然的描写,却通过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父亲形象为后续的悲剧情节做好了铺垫。
悲剧情节的开端发生在第二部分“米克马克族古葬场”,这部分见证了路易斯从一个慈爱的父亲、能干的医生到疯子的转变。拉开序幕的是作者在前言中的描述,即关于什么是“恐惧”——“认为人可以承受的恐怖值是有限的这一观点可能是错误的,当黑暗逐渐逼近,人会越来越恐惧,虽然恐怖值上升得比较缓慢,难以察觉,但梦魇开始后,恐惧滋生恐惧,噩梦催生噩梦,直至黑暗吞噬一切,其中最可怕的问题可能是一个人能够承受多大的恐怖,并且还能保持清醒、冷静的理智”。显然,斯蒂芬·金在文中所提到的“恐怖”与文学体裁中的“恐怖”并不同义,仅指痛失亲人(路易斯的小儿子盖吉)的恐惧。当斯蒂芬·金详细地描绘了克里兹一家,并描述这家人所遭受的不幸时,读者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宠物公墓》中克里兹一家的不幸即斯蒂芬·金所说的“恐怖”,也恰恰是悲剧中主人公所遭受的不幸,并非所有人对此都能够幸免。
由于斯蒂芬·金在第一部分成功的情感铺垫,随着第二部分情节的展开,读者看到了路易斯痛苦的内心挣扎,感受到了“恐惧与怜悯”:怜悯是因为看到好人遭受了如此撕心裂肺的痛苦,恐惧是预感到路易斯一定会抛去所有理智复活他的儿子。斯蒂芬·金使用了古典悲剧中惯用的铺垫手法,让死去的丘吉尔回归,也让维克多·帕斯托反复在梦中告诫他不要跨过墓园的栅栏,否则将迎来可怕的后果。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缓慢的叙事形成了强烈对比,叙事节奏加快,先以盖吉的葬礼作为开端,再在路易斯疯狂地挖出儿子尸体的时候达到高潮。读者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还来不及喘息,就被斯蒂芬·金带入路易斯的万劫不复的疯狂行动:葬礼前他担心盖吉的头不见了,下葬时终于看到儿子,却发现儿子小小的身躯被束缚在一件正式的小西装里,他悲恸不已;儿子的死让他感到越来越愤怒,在一个夜晚他挖开了盖吉的坟墓,抱出了儿子,他为儿子轻轻地擦去了脸上的苔藓,把丧葬工作人员塞在盖吉嘴里的棉花拿出来,然后抱着儿子倾诉爸爸有多爱他;虽然从成为一名医护工作者起,他一直致力于对科学和真理的探寻,但他还是轻轻地摇晃着怀里的儿子,一遍又一遍地述说着:“盖吉,会好的……我发誓,盖吉,会好的,会结束的……就是今天晚上,神灵啊!盖吉,我爱你,爸爸爱你……”他安慰埃莉是因为爱,所以不忍心欺骗她,现在却欺骗起自己和死去的盖吉,路易斯知道所有的这一切都不会好,但是谎言让他感觉到自己的变化。正如Bernadette Bosky的简评所言:“《宠物公墓》的悲剧在于当路易斯·克里兹本该怀疑直觉时,却跟随了直觉。”[4]
在这一点上,对于悲剧展开讨论的核心问题出现了:在哪种程度上,悲剧的主人公应该对其所遭受的厄运负责?或者说,路易斯的错误选择是导致他悲剧的主要原因吗?许多评论在解读这个话题时口吻相当含糊,Natalie Schroeder[5]认为“斯蒂芬·金在设置路易斯行为的终极原因时比较含混,有可能是因为路易斯完全受控于墓园的超自然力量,也有可能因为他失去爱子极度痛苦,导致他要抓住所有可能的机会让儿子回来——哪怕是做出亵渎神灵的行为(扮演上帝)也要让盖吉复生”。同样,Tony Magistrale[6]62也认为“斯蒂芬·金笔下的大多数角色也如同路易斯一样:他们选择了自己的行为”。然而Tony Magistrale在将斯蒂芬·金的《宠物公墓》与霍桑的许多小说对比时,他又不得不承认路易斯与霍桑小说中的年轻理想主义者一样,发现邪恶力量不再是一个陌生可怕的抽象物,“相反地,他(路易斯)发现邪恶力量对他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如同霍桑作品中的伊森布兰德和古德曼布朗一样,他屈服于邪恶所带来的混乱与堕落”[6]17。Tim Underwood[7]暗示因为缺乏情绪疏导和理性安抚,路易斯被痛苦折磨得几近疯狂,“他对所遭受的厄运负有责任,但这个角色却又让人同情怜悯:一个处于糟糕环境中的好人”。Douglas Winter还指出路易斯·克里兹的名字“Louis Creed”暗示着他的命运:“creed表示信条、理性的意思,这恰恰是将他一步一步推向毁灭的个性缺陷。”[2]134
评论家们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路易斯是否主动选择了邪恶?如果是这样,这个选择行为是否反映了其个性缺陷?古希腊悲剧中将此缺陷称作“hamartia”,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个缺陷主要表现为主人公性格的小弱点或小问题,而不是阻碍我们继续崇拜他的大问题,如恶习或堕落。[3]76这个缺陷不会导致处境立即逆转或者灾难发生,它只会和故事中的反派势力勾结一起发挥作用。例如,俄狄浦斯冲动易怒的性格弱点不会给他带来直接厄运,但会加速戏剧性的悲剧发生。“hamartia”在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中,正是因为主人公的个性缺陷,偶然事件和命运才能在悲剧事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即使在当代悲剧剧目如米勒的《推销员之死》中,主人公刚愎自用、自吹自擂的性格也让他在虚幻的美国商业文化中逐渐迷失自我,最后走向毁灭。
虽然《宠物公墓》中描绘的现代情感使它更接近当代悲剧类型,但它的决定论和命运论等要素又来自古希腊悲剧。古希腊悲剧受到一种契约观的强烈影响,即上帝、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三者形成一种牵制与平衡,如果这个“契约”被打破,那么这个失衡的天平就会反向运动自行修复,这个行为被称作“天谴”,正是它让悲剧的发生不可避免。“契约观”是一种道德观,但发生在悲剧主人公身上的特定行为并不依赖其道德水平。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悲剧“hamartia”,通常被翻译为“个性缺陷”,对主人公至关重要,个性缺陷并不必然是一种道德缺陷,但它往往是悲剧的导火索,导致天谴的发生[8]。
路易斯和俄狄浦斯一样,没有犯下任何会导致悲剧发生的罪行,只是爱子盖吉的死这件事情启动了悲剧发生的按钮。Douglas Winter认为路易斯的“理性”导致了他的自我毁灭,路易斯过度的理性确实让他在盖吉死后犯下过错,但和俄狄浦斯相似,这种个性缺陷也不会直接导致后期悲剧的发生,而仅仅是悲剧发生的导火索。小说中另一个角色维克多·帕斯托在故事前期几次暗示邪恶不会等着路易斯自主选择,而是会主动选择路易斯,并且当邪恶降临时,路易斯无法抗拒。虽然维克多·帕斯托多次恳求路易斯不要越过宠物公墓的栅栏,但也深知警告和路易斯的自我意志都不能阻碍其最终进入墓园,天谴终将来临,悲剧必然发生,所以他发出悲伤的预言“你的毁灭和所有你爱的人的毁灭之日临近了”。
《宠物公墓》中路易斯为了使盖吉复活而跨过墓园栅栏的行为打破了上帝、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相互牵制与平衡的契约,并且他的个性缺陷确实在悲剧故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路易斯跨过墓园的栅栏?Douglas Winter指出是非理性的爱。Vernon Hyles[9]认为“爱在现代哥特小说中被扭曲……企图从混乱中创造秩序,从软弱中获得力量,但它却制造出了怪物”。在《宠物公墓》中,路易斯早期表现出的对孩子的关爱变成了不惜一切也要让盖吉复活的执着,对朋友贾德·克兰德尔的爱变成了疯狂的怀疑,对妻子的爱也要屈服于他可怕的使命。整部小说最让人不安的时刻发生在路易斯坐在盖吉的坟墓前,对怀里的儿子尸体倾诉“爸爸爱你”。但是这种“爱”不会让读者感到父爱伟大,而是感到可怕,更会联想到故事结尾妻子瑞秋从坟墓里爬出来对路易斯诡异地呼唤“亲爱的”。
三、结语
虽然《宠物公墓》最后部分展现了恐怖小说中常见的血淋淋的场景——复活的杀人小孩确实惊悚得让人战栗,这一点倒是印证了许多评论家的对斯蒂芬·金小说的抨击,如John Podhoretz[10]认为“金先生的小说最大的能耐就是让人读的时候饶有兴趣,丢弃的时候又毫无遗憾”。然而不能毫无遗憾地丢弃的,在血腥场景褪去后,仍然长久萦绕于读者心头的是人类面对死亡时表现出的彻底迷茫与混乱。这部作品作为惊悚小说之所以能在文学界获得肯定,原因在于斯蒂芬·金通过故事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从非哲学、非科学和非理性的支离破碎甚至混乱不堪的视角来探讨死亡问题。
当看到路易斯科学的、理性的世界崩塌,爱的能力转变成疯狂的坚持,理智慢慢消失时,读者就对这个曾经尊敬爱戴的人产生了怜悯,也产生了恐惧,既为他也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路易斯如同其他悲剧主人公一样,代表了所有人,虽然读者试图从他所处的环境和行为上抽离,但终归无法完全做到——到底理性的生活是否真的完全安全?当面对死亡的残酷之时,是否不会因悲伤而疯狂?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真相存在于《宠物公墓》的悲剧恐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