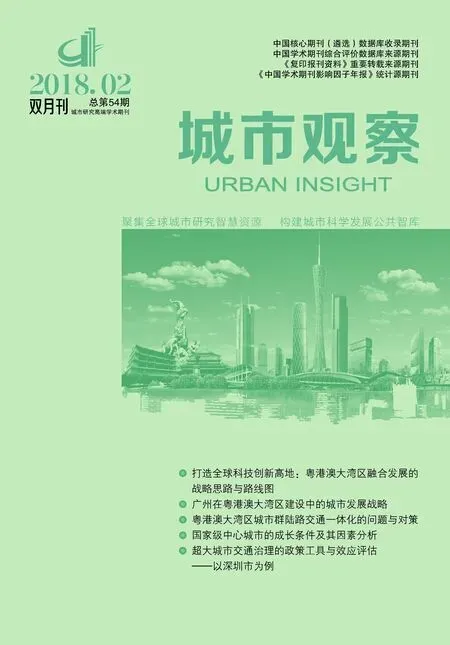城市区域发展的梯度性假设
——世界视野中的城市文明走向
◎ 余志乔 陆伟芳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中心所在,城市文明是人类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向。虽然城市与文明并不完全同义,但城市显然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文明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城市文明的扩展,从城区到城外,从近郊到远郊,从中心城市到边缘城市,就是城市文明向外梯度扩展的表现。城市文明超出城市本身的发展范畴,成为了区域社会发展的引擎或动力,带动着社会的全面发展。随着城市文明的不断向外梯度性扩展,非城市地区融入城市文明,整个人类社会都将生活在城市区域文明中。
一、城市文明梯度性推进的假设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从词语来说,在拉丁语系中,civil 和civilized基本上由civis演变而来,而civis的含义就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因此,城市与文明紧密相连。美国城市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人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说过“城市是文明人的天然居所”(the city,1916);沃思(Louis Wirth)则称“正如西方文明的开始是以早期的游牧的永久定居为标志一样,现代文明则显然是以大城市的增长作为最显著的特征”(The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1938)。而德国的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Spengler)虽然认为城市文明最终也会消亡,但也同意“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世界历史都是城市史。民族、国家、政治、宗教、艺术,以及科学都依赖于同一个现象——城镇。”(《西方的没落》)芒福德(Lewis Mumford)也认为城市是“文明的最重要的发明”。 “城市文化归根到底是人类文化的高级体现……人类所有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城市发展史》)
城市是区域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也是区域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区域强调的是空间概念。城市在时间中发展,在空间里展开。城市在空间上显然是“点”,是区域社会的中心点,网络枢纽的交叉点,资源利用的密集点,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高发点,经济高效的增长点,为构成区域空间的一个部分。城市在时间中展开,因此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城市也是经济密集的社会有机体,它的经济要素在一定的地域内高度密集, 这些密集要素之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城市成为区域发展的中心。区域是一个空间概念,是由一个经济发达的中心同周围地区形成信息、物质、能量的交换而构成的,是依赖于组织、计划、协调、控制经济活动,并从整体上加以考虑的一定的空间范围。区域发展是区域内中心城市(群)与其腹地联系的不断深化,也是区域内一种乡村景观向城市景观的转变。
城市化推进区域的城市发展进程。对任何区域或城市而言,城市化推进正如其经济社会发展一样,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城市化推进不仅仅是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城市建设质量的提高和城市运转的现代化,更主要的是作为区域中心功能作用充分和完美的发挥;区域城市化推进,其内容既包括让更多农民转变成市民,还包括区域的城乡化,包括区域城市(镇)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
城市和区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区域对城市具有养育、支持的作用;城市对区域具有引导和带领的作用,是区域发展的向导和动力。任何一个城市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地域范围,城市的发展都有它辐射的经济区域,城市与区域正在形成相互融合的地域生产综合体,这种综合体其实就是城市文明扩散的必然结果。
人类历史上有着丰富的城市发展理论,从各个角度来解释城市社会发展的现象,寻找城市发展的规律或模式。早期的圈层理论、中心地理论和增长极理论,最多考虑了城市对周围区域可能产生的影响,认可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发展梯度,即从城市向区域发展的一种梯度。但这些理论是站在城市的立场上来研究城市的,几乎没有涉及城市文明的向外扩展的使命,只把城市文明本身作为研究的重点,而广阔的区域大多只是为研究提供的一种参照物,是城市文明得以对照的一个背景。
从20世纪中叶起,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进程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化出现了一种以大城市为中心,连同周边受其辐射的邻接地区所组成的巨型城市区域集合体现象。于是,出现了大都市带理论、城乡融合及城市态(Citistate)理论等,试图解答新时代出现的新现象,探讨城市未来的发展模式。还有,弗里德曼提出了空间一体化四个阶段理论:第一阶段不存在等级的独立地方中心阶段,即前工业化社会特有的典型空间结构。第二阶段为单一强中心城市阶段,即工业化初期所具有的典型空间结构。第三阶段是全国中心城市与实力强的边缘次级中心城市共存阶段。第四阶段是功能相互依存的城市体系形成阶段,边缘性基本上消失,区域体系最终演变为良好的综合体。不过,这些研究似乎仍然更看重城市本身,没有研究指出城市文明发展的未来走向。
用世界视野来考察城市文明的发展历程,探索其未来的发展空间,那么邻域(Adjacence)、近域(Surrounding)、广域(Macrozone)和全域(Universal)四个梯度的理论(ASMU)假设,可能有助于更好地对应人类历史上的城市与区域社会的不同的梯度发展阶段,解释城市文明向更为广阔的区域扩展的现象。
第一个梯度是城市与区域的邻域发展阶段,是城市文明发展形成时期,在城市空间发展上是从城到城市的发展阶段。在农业文明的初级阶段,城主要是筑有围墙的设防单元,主要起着军事防御的作用,并兼有政治、军事或宗教的功能。这时的区域范围是比较狭小的,主要是在城墙外的有限的邻近地域,我们称之为邻域。随着区域社会的发展,在城墙外出现了市,充当市场功能,为城提供生活的需求,随后,城与市逐渐合流,变身为城市,邻域变成城市的组成部分。这时的城市既具有政治军事功能,也具有经济社会职能。这属于城市文明的邻域推进阶段,可以说,人类文明历史上的古代城市大多属于这类邻域发展模式。
第二个梯度是近域推进阶段,是城市文明向区域有限扩展时期。工业文明以来的城市从核心城市向外扩展,发展出文明富裕的郊区。这是城市文明的星火从城市从郊外区域的扩展。这时的区域范围逐渐扩大,城市越大,其相应的区域范围也越大。于是,我们有了包括郊区、远郊、卫星城、新城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开发区或工业园区、新城、第二城建设,也属于这一类。从人类发展史来看,城市对区域的影响范围明显扩大,也许可以说是成倍的扩大,区域发展有时呈现跳跃性的扩展。
第三个梯度为广域推进阶段,是城市文明更发散的时期,它大致对应信息革命以来的城市大扩展。这个时候,传统意义上的城市与区域界限逐渐消失,出现了城市群、城市带、都市区、都市区连绵带。最终分化为都市区与非都市区。这个阶段与近域推进阶段有两方面的差异:一是研究视角的差异。近域推进阶段,我们主要站在城市的角度,研究郊区、远郊、新城、边缘城市等等。而研究广域推进,则更多的是站在空中俯瞰地球,不是研究城市空间如何扩展到周围地域,更多地考察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的全方位推进,研究城市文明的质的飞跃。二是量与质的差异,如果说在近域推进阶段向郊区不断扩展,研究的是一种历时性进程,是一种量的研究,那么,广域推进阶段是质的变化,研究郊区、边缘城市等的全面发展,从而使郊变成市,是广阔区域社会的全面城市化,是一种质的考察。
第四个梯度是全域推进阶段,是城市文明遍及全社会的时期,是未来的城市与区域社会发展模式。随着世界的都市区与非都市区的形成与发展,整个都市区成为我们研究意义上的“城市”,而整个非都市区成为该意义上的“区域”,都市区将影响非都市区,带动非都市区最终向都市区发展;与此同时,都市区内部的发展也会带上更多非都市区的色彩。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由于信息革命的深入,生产与生活越来越信息化,分散化,集中的工作与生活成为一种选择,而不是必需。在这个阶段,城市与区域的界限将逐渐消失,城市与区域完全融为一体。这是全域推进阶段。这个阶段不仅有城市与区域在物质外观上的接近,更有生产生活方式、精神风貌等的全面接轨。
二、城市文明梯度性扩展的历史考察
城市与区域的融合是通过城市化来逐步实现的。城市化就是从近域向广域推进的发展,是城市文明向区域大扩展的历史进程。
从人类聚居方式来看,人类文明经历了游牧民的帐篷文明、农耕社会的村镇文明和工业社会的都市文明。在游牧状态下,只有广阔的游牧区域,还没有相对集中的文明点。到农耕时代,形成了村、镇、市的人类聚居方式,城镇成为广阔的农村腹地的商业中心。这时候已经基本形成了城市与区域的某种关系,两者犹如岛屿与海洋的关系。一般而言,城市只是区域海洋中的一个个孤岛,它再辉煌再繁华,也只能像一把火炬,能照亮一定的区域,但亮光的范围毕竟有限。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起初“城”与“市”并不相同。城指具有防卫作用的城池,周围的城墙是主要的防御形式,也即城主要是具有军事意义。
随着人类聚居方式的发展,出现了“城”与“市”的合一。有些“城”周边兴起了“市场”,形成城市,这种类型的城市多见于战略要地和边疆城市,如吴王夫差在古蜀岗之上筑邗城,邗城外兴起市,随后成为扬州城;天津也起源于天津卫;再如在罗马时期不列颠的重要北方军事堡垒约克城外,兴起了服务性的市场,随后发展成约克城。也有先有“市”发展形成的城市,也就是先有市场然后发展为城市,这类城市往往位于交通交汇之处,市场的发展吸引更多的人定居,从而形成城市。
城市最初主要诞生在人类文明发达的所在,是广袤的人类大地上的极为分散的一个个孤点。从公元前5000年起,在两河流域就出现了一批城市,如幼发拉底河畔的乌尔(Ur)城邦;在巴格达南90公里横跨幼发拉底河的长方形古城巴比伦;从公元前3200年到332年,在尼罗河流域的著名城市,如“白城”孟菲斯、带有城市规划的卡洪城、底比斯(Thebes)、法雍等。稍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500之间,在印度河流域,出现了著名的古城摩亨卓达罗城,它布局合理,人口众多,建筑规范,拥有良好的排水系统。在中国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也同样出现了最早的城市文明,距今约5500年的长江、巢湖流域的安徽含山凌家滩原始部落遗址,据信是中国最早的城市,稍后有山东日照五莲县的丹土村城市遗址。
农耕时代的城市有所增多。它们大多具有了一定工商业活动,是消费中心,需要依赖周围乡村供应生活物资。“在商业路线之前,一座城市居住地的规模大小直接取决于周围土地的耕种容量和最近的渔场的产量,”①因此规模较小,相对封闭。
这种城市的发展特点,可以从中外古代城市发展窥见一斑。公元前21世纪到前17世纪的夏朝,修建了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而分封的诸侯也修筑城池, 形成中国史的第一个建城高潮。到春秋战国,中国已经有了100多座城市,苏州、成都就是在这个阶段诞生。《史记》载,当时的齐国都城临淄人口超过了20万。农耕文明十分发达的中华大地,则在秦汉郡县制下,建立起了具有行政色彩的城市,促进了城市等级体系的发育和成长。隋唐大运河沟通南北后,又促进了运河沿线及南方城市的发展,如淮安、扬州、苏州、杭州的经济地位日益重要,形成了以首都长安为中心,东至汴梁、商丘,西到岐州、成都,南到广州,北到范阳(今北京)的城市网络。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农耕文明城市体系发展到顶峰,全国城市100多个,还有2000多个小城镇。明清之际,已发展出一批专业的商业性城镇,如陶瓷城镇景德镇已有10万多人,丝织业城镇苏州等。
欧洲城市发展也不例外。在地中海世界,古希腊和古罗马就先后建立了许多城市国家(城邦),虽然古希腊城市大多是小国寡民,规模不大,但公元前5世纪时,雅典也有了30万人口。随后的罗马继承了希腊城市的格局。在美洲玛雅文明的蒂卡尔城是中美洲已知最古老的城市。虽然著名史学家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1892-1957)称其为“城市革命”,但这些依然是广袤地球上的星星之火。中古欧洲城市虽然有兴有衰,但却走向了由“城”到“市”的转变,即由防御到商业色彩的演变,甚至形成了不同专业分工特色的城市。虽然大多数城市规模不大,伦敦在13世纪不到4万人,但水城威尼斯人口超过20万。
古代世界的城市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大城市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据Chander研究,公元前2000年,世界上最大城市的数量为7座,公元前1000年有13座,公元前600年有20座。②不同时代世界最大城市的人口数量也基本呈现日益增长的态势。公元前2000年,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苏美尔的乌尔有6.5万人,公元前1000年的底比斯有6万人,公元100年罗马有45万人,公元500年君士坦丁堡有40万人,公元1000年西班牙城市哥多华(Cordova)有45万人,公元1500年北京有67万人。③
工业化之后,从城市到都市的发展,意味着聚居方式的更高级形式,而且成为人类主要的聚居方式。不仅城市数量空前增加,而且城市的规模空前扩大,开始了从城区向邻域和近域的扩展。“在人类文化中,都市吸引力的范围变成了最重要的地理事实,因为都市的中心往往集中了经过该区域的能源、人员和物资的流动,对它们进行分散、转移或重新派送。”④这时,城市和都市使文明向前发展,高密度聚居文明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并且以城市为中心点,不断向区域扩展。城市的规模向百万、千万发展。
1851年,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人口比重超过50%的国家,基本实现城市化。但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1850年,世界城镇人口比重仅为6.3%,1900年增加到13.6%,1950年为30%。1900年伦敦就有648万人,1988年东京有2870万人。⑤2015年,东京仍以3800万人口雄居世界首位。城市正在向广域扩展。
在中国,据民政部2011年发布的《2010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截至2010年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设市城市数量增加到657个。⑥此后部分城市撤销、部分城市新增。截至2016年末,全国共有663个设市城市。
从城市与区域社会发展角度来看,郊区化及其蔓延显然是城市聚居方式向区域的扩展,是城市文明从点状向块状的发展。如果我们带着这种视野,那么,二战后西方世界的卫星城和新城建设也就有了全新的意义。它们是运用政府规划和建设的力量,促进城市文明向区域扩散,促使密集的聚居方式在更广大的区域占据上风。当代中国的新城新区建设,也是运用政府力量促进城市文明向区域的扩展。都市向大都市、大都市区、大型大都市区、大都市连绵带的演变,则显然是城市向区域扩展的梯级发展,而小都市区则意味着城市文明发展达到的深度。大都市连绵带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密集聚居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意味着区域社会获得了空前发展。到这个时候,城市不再是广阔区域中的一个文明孤岛,而是文明海洋中的灿烂的群星,这些群星与广阔的区域同辉,如同夜空中的银河一样光彩夺目。只有到这个时候,城市与区域才有机地融合到了一起。马克思说古代的历史是“城市乡村化”,而“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其实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可见,从城市文明扩展的角度来看,从游牧到农耕,从城镇到大都市连绵带的演变,正是城市文明向区域社会不断扩展的过程。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点到块,从块到带到区域,高密度的聚居方式越来越占据优势地位,城市对区域从外围影响到整体包容,城市对区域具有越来越大的作用。或者说,城市这种人类生活方式必将替代其他生活方式,成为人类共同的生活方式。
从空间角度看,就如置身于外空间,用俯瞰世界的方法来考察城市文明进程,是一种更为宏观的考察方法。在这种视野下,大都市区化恰恰是城市文明的扩展和深化。再进一步,那么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都将会在都市的精神之下。换言之,都市生产和生活方式,会扩展到整个区域,以至于城市与区域不再清晰可辨,两者融为一体。
三、城市区域扩展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西方发达国家从城市的邻域发展,走过近域发展历程,最后达到了广域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它们已经走到了城市与区域社会的高级和成熟阶段。整体而言,城市与区域社会是基本协调的。
若城市发展仅仅停留在这个邻域发展层面上,无法扩展到近域和广域,那么再繁荣的城市,也无法在时间的长河中保持永远的辉煌。阿拉伯帝国时代建立的繁华的商业都市,固然曾经拥有过耀眼的财富,犹如阿里巴巴“芝麻开门”般呼唤出空前的稀世珍宝,但终究只是过眼烟云,无法带动广阔区域社会的发展和繁华。城市与区域分离着,也没有发展到近域发展阶段,更不要说广域和全域发展了。
现代拉丁美洲国家也是如此。它们片面地发展大城市,使现代文明局限在个别特大城市上,区域社会成为落后的腹地,城市文明的星火始终只停留在邻域的初始阶段,没有能向近域扩展开去,陷入“拉美陷阱”。城市不像文明的火炬,倒犹如巨大的“黑洞”,蚕食着区域的资源、人力、财产和智力等等,留下一个极度贫穷落后的广阔的区域。从城市文明发展角度看,反映了区域的块状发展之不足,这些区域仍然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永远充当腹地的角色之中。从文明发展的形态来讲,似乎仍然是农耕文明阶段的状态,还没有进入城市文明阶段。
总之,从城市文明发展的历史与未来推测,城市文明的发展模式是:城市与区域社会分离到城市与区域社会发展融合的四个梯度——邻域、近域、广域到全域,最终实现城市文明扩及全社会。欧美发达国家的相对均衡发展之路,拉丁美洲国家的过度城市化所导致的城市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脱节现象,为我们的城市与区域社会发展提供了经验与教训。这种现象提醒我们,中国当代城市发展的未来,似乎应该摆脱邻域式蔓延,走向城市文明的发散化,使城市与区域的发展融合的新阶段。
注释:
①[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李翔宁,周鸣浩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354.
②[美]克里斯多夫·蔡司·邓恩,苏珊·曼宁著.包路林译.城市体系与世界体系形成路径探析——基于4000年的城市兴衰史.中国名城,2015,10:10.
③数据来源:http://irows.ucr.edu/research/citemp/ccr02/citypop5.xls。
④[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李翔宁,周鸣浩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354.
⑤数据来源:http://irows.ucr.edu/research/citemp/ccr02/citypop5.xls.
⑥我国设市城市数量增加到657.http://news.sina.com.cn/c/2011-06-16/20472265400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