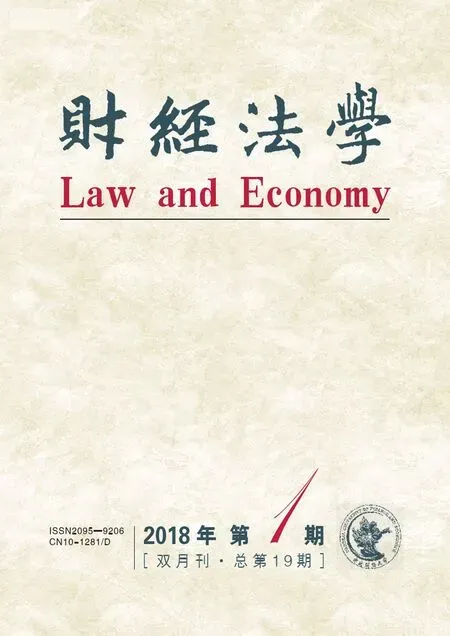德国审级制度原理探析:以历史为视角
卢 佩
一、德意志王国上诉制度产生之前的法院结构体系
在早期的日耳曼各原始部落中,民众大会是其最高权力机关,一切可服兵役的贵族及自由人的男子均可参加。它有权决定部落中的一切重大事务(如战争、和平、缔结条约等),同时兼具审判的功能。到会的人以敲击武器的声音来维护他们所同意的提案,以杂乱的喊声来表示他们的反对。早期的部落审判大会即是从民众大会延续发展而来。[注]Erler/Stammler/Cordes,Handwörterbuch zur deutschen Rechtsgeschichte (HRG) V,Berlin 1998,S.1022.这种大会共同体式的民主审判模式与现代意义上的法院审级建构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审判大会中的裁判者所进行的司法判决(Rechtsspruch)和法官所实施的司法强制(Rechtszwang)在组织与功能上处于分离状态。[注]Jürgen Weitzel,Die Bedeutung der Dinggenossenschaft für die Herrschaftsordnung,in: Leges-Gentes-Regna,Gerhard Dilcher (Hrsg.),Berlin 2006,S.351.法官并不参与案件的实质审判过程,只是通过发布命令的形式对诉讼实施形式上的程序指导,从而保障法院的审理过程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而判决的最终审判结果则由有资格参与审判大会的贵族和自由人的男子共同决定。在当事人双方针对案件事实陈述完本方观点后,法官就其案件如何判决向法院大会成员提出询问。由于参与审判大会的人员知识水平以及身份上的差异,并非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提出判决建议,因此通常由法官或其中的贵族成员提出一个较为具体的判决建议,其他成员既可以对该“判决建议”表示赞同,也可以对其提出异议,同时应相应地提出新的判决建议。最终由法官将所有成员一致通过的判决建议公布,进而成为案件的正式判决,从而结束审判程序。[注]Sigrid Widmaier,Das Recht im “Reinhart Fuchs”,Berlin,New York 1993,S.167.该判决一经公布,不得撤销。当审判大会的成员之间针对判决结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法官只能就此问题向咨询机构(Oberhof)进行咨询,[注]Oberhof实质上兼具审判机构和上级咨询机关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承担本辖区内争议案件的审判职能,也可以基于私人之间的协议承担仲裁调解的功能;另一方面作为下级审判机构的咨询机关,为其疑难案件提供法律咨询。该机构在中世纪时期非常普遍,几乎每一个法院都有其所隶属的上级咨询机关。但随着罗马法的复兴以及法院审级系统的不断完善,该机构在16世纪到18世纪间逐渐消亡。由其判断到底哪一种判决建议更为合理。对于该咨询机构所认可的判决建议,下级法院必须接受,并将其作为案件的最终的判决处理结果而对外公布。[注]Hans Müller,Oberhof und neuzeitlicher Territorialstaat,Berlin 1978,S.145~146.
在法院形成统一性判决建议之后,正式公布判决结果之前,包括案件当事人在内的审判大会到场的任何成员都可以向上级法官(höherer Richter)提出对该判决正确性的质疑,从而保障未来即将公布发生法律效力判决的正确性。由此可见,这种判决责问(Die Urteilsschelte)是建立于责问者与原判决建议的做出者之间对案件认识发生分歧的基础之上,从而对该“判决建议”是否正确进行审查的制度。既然将判决责问制度定位于“对原始判决建议的正确性”进行审查,那么将其审查范围局限于原有事实材料之内,而不能另行提出新的案件事实与证据,则成为其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只有建立在相同事实材料的基础上才能对其正确性做出审查。[注]Siegfried Broß,Untersuchungen zu den Appellationsbestimmungen der Reichskammergerichtsordnung von 1495,Berlin 1973,S.39.该制度也为后来的德国上诉程序中有限审查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上级法官对其正确性审查完毕之后,应将其处理意见返回原下级法院,由其以自己的名义正式对外公布。
综上所述,在德国1495年上诉制度产生之前,司法判决的形成过程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下级法院自身无能力形成统一性判决建议时所寻求的“事前咨询”途径,以及已产生统一性判决建议后为保障其正确性所寻求的“事后救济”途径。[注]Jürgen Weitzel,Über Oberhöfe,Recht und Rechtszug,S.4.尽管在这两种途径中都涉及上下两级法院之间的互动关系,或为咨询,或为正确性审查,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不能算是现代法院审级(Gerichtsinstanz)意义上的“上诉法院”,因为“上诉法院”的主要任务在于对下级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对其做出的错误判决进行纠正,并以自己的名义重新发布新的判决。而上面所述及的所谓“上级法院”,无论是“上级咨询机构”,还是“上级法官”,都是在下级法院正式判决做出之前,即对“判决建议”的具体内容存在争议的前提之下,应下级法院请求而介入判决的形成过程。但机构本身无论如何并没有权利以自己的名义发布判决,自始至终在其上下级法院的穿梭过程中形成的只有唯一的一份第一审判决。因此现代意义上的“上诉制度”在中世纪的初期和中期还并未产生。[注]下面我们可以通过一组12世纪到15世纪由领主地方法院上诉到王室法院(Königsgericht)的案件数据情况分析得出“上诉制度”在当时的实践情况。在王室法院审理的2 000多件案件中,12世纪只有4个案件,13世纪只有9个案件,其在进入王室法院之前已经经过了另一个法院的审理(即已经具备一定现代意义上的审级概念)。虽然14世纪进入王室法院审理的案件急剧上涨到7 400件,但是仍然只有30件在进入王室法院之前已经经过了另一个法院的审理。而在这30件案件中更多的是涉及案件的管辖权的争议(即是属于王室法院管辖还是属于封建领主范围内的法院管辖),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我们前面所谈论的第二审级的审理。由此可见在15世纪中期以前现代意义上的“审级”概念并没有出现在德意志王国的司法实践中。其仅出现的几个特例也主要集中在德意志王国的南部和西部,而这些区域明显地受到了更为先进的法国和意大利法律观念的影响。参见Bernhard Diestelkamp,Die Durchsetzung des Rechtsmittels der Appellation im weltlichen Prozessrecht Deutschlands,Stuttgart 1998,S.12~16。追根溯源,这主要由以下两个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所导致:
其一,“实体法”体系的不健全。上诉制度建立的最大功能在于,通过上诉法院的复查和监督,使得下级法院做出的可能错误的判决、裁定能够得到纠正,从而增加纠纷解决机制程序上的正当性,吸收当事人的不满,达到消弭纠纷的目的。但其审查必须遵循既定的标准,其前提是审查的对象必须具备可审查性。在现代上诉制度框架下,其已形成完备的法律规则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已形成一整套逻辑严密的法律适用规则,因此上诉法院以该规则体系为基准对下级法院的判决进行审查,其审查过程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原审法院是否正确解读法律规则,案件事实是否正确归入到法律规则的适用前提中,其法律结论的逻辑推理过程是否正确等等。其目的在于通过上诉法院的审查,判断原审法院的结论是否存在瑕疵,通过上诉法院的纠错程序而达到改进原判决结果的目的。但是由于在德意志王国早期根本不存在既定的法律规则体系,其原审判法院只能依据当时社会所共同认可的一些道德准则和个人的生活经验对案件进行处理。而事前咨询及事后审查两种途径则是为保证案件处理的准确性所设置的防护措施。换句话说,现代审级制度的建立前提是“客观”的判断标准,上级法院得以运用这个标准来对原审法院的判决过程进行审查和监督。而当时德意志王国的不同机构的审查程序的建立,目的在于通过上级权威咨询机构的审查,给出一个关于“法律规则的具体内容”的确定性结论,其发生争议的并不是判决结果本身,而是导致判决结果产生的法律规则的具体内容。不同的法院机构追求同一目的,即齐心全力地发展出一套完备的法律规则体系,其根本不具备“不同的法院机构对同一事项进行逐级式的审查”的特点,上诉制度的产生在当时也就无从谈起。
尽管当时并未产生现代意义上的“上诉制度”,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已经孕育出审级制度的结构性因子:司法权威及其贯穿辖区的辐射力。“事前咨询”途径中的上级咨询机构与下级法院之间,虽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隶属关系,但两者依然存在一定的附属关系。通常这种附属关系基于两种情形而产生:其一,在日耳曼城市法(Stadtrecht)的发展与传播过程中产生。在母城的法律规范向新形成的周围卫星城或子城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疑难争议问题,母城的审判机构理所当然地成为卫星城或子城审判机构的上级咨询机构。其二,因封建邦国中的领主管辖而产生。因德意志封建领主掌控其所辖领地内的统一司法权,因此领主在其核心徭役庄园(Hauptfronhof)内设立的审判机构则成为本领地其他区域审判机构的上级咨询机构。[注]Müller,a.a.O.,S.40~41.无独有偶,在“事后救济”途径中所出现的“上级法官”与下级法院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附属关系。其既可以依据下级法院审判权力的来源方式而确定,如可以向国王请求纠正所有下级法院错误的判决建议,或诸侯封地内的封臣向领主请求纠正等;也可以依据下级法院的行政隶属关系而确定,如依据母城而新建的子城法院成员向母城法官请求纠正等。[注]Johann Julius Wilhelm von Planck,Das deutsche Gerichtsverfahren im Mittelalter,Teil I,Braunschweig 1879,S.282~285.“上级咨询机构”与“上级法官”无论依其审判权力的来源上,还是从其审判知识与实践经验的掌握上,都具有较高的司法权威。这种司法权威,使得核心区域(即辖区权力中心的顶层)的法律可以顺利沿着这样一种司法等级的脉络辐射至整个辖区。而正是这种辐射作用,构成“司法统一”的原始驱动力,促进现代审级结构的最终形成。作为裁判依据的实体法律体系的缺失,构成审级架构形成的制度性障碍,但同时又在法律规则逐渐完备的过程中,产生“在整个辖区范围内实现公平和司法统一”的内在需求,构成审级制度形成的原始驱动力,在这种外在制度性障碍和内在驱动力的历史交替年轮中最终导致德国上诉制度的产生。
二、上诉制度的产生
随着罗马法的逐步复兴以及1495年德意志帝国法院的设立,建立在“一审终审制”基础之上的判决责问制度的运用在司法实践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直至15世纪走向消亡并逐渐被上诉制度(Appellation)所取代。在现代意义上的审级制度产生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其一,法院内部层级结构的转变。[注]Weitzel,a.a.O.,S.14~19.
首先,“判决责问”制度不断走向消亡。在文章的第一部分笔者已经对德意志王国早期判决产生的两种方式(“事先咨询”途径和“事后救济”途径)进行了详细介绍。在“事后救济”途径中,如果原审判大会所做出的判决建议,事后被上级法官确认为错误的,[注]如原判决建议的做出者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存在着徇私枉法(Rechtsbeugung)的情况。原判决建议的做出者将会受到制裁(Sanktion)。由于原判决建议的做出者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存在着“责问追究”的风险,为避免日后可能受到的制裁,他越来越倾向于在正式的判决建议产生之前,就该问题咨询上级机构(即便对于该纠纷原审判大会的参与者之间对此问题已经达成了一致性建议),并将其做出的咨询意见转化为正式的判决建议,这就保证了该建议即便后来受到他人的责问,其自身也不存在着受制裁的风险。久而久之,判决产生的“事后救济”途径逐渐被“事先咨询”途径所取代。
其次,法院的角色定位发生转变。随着法律规则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国家权力意识(或领主权力意识)的强化,法院“法律咨询者”的身份逐渐向“解决私人纠纷的中立裁判者”的身份转化。随着法官与判决建议做出者两者身份上走向统一,法官与当事人之前所建立的同等地位被打破,法官不再承担与各方主体共同探求法律规则内容的任务,而成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纠纷解决的超然裁决者。法院内部的这种地位分层扩展至外部,即在原法院与上级咨询机关之间也逐渐出现权力分层,这也就是现代审级架构的雏形。
其二,1495年帝国最高法院的设立及罗马法的复兴。
帝国最高法院的设立最初是为了受理各地领主之间的诉讼,调解帝国等级之间的冲突。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并不仅仅是一个解决纠纷的审判机关,它以“维系帝国领域内的共同和平”的名义,不断地通过司法程序创制在德意志王国内统一适用的“共同法”(jus camerale),[注]Adlof Laufs,Die Reichskammergerichtsordnung von 1555,Köln 1976,S.9.并担负着全面推进德意志法律转型的历史使命。这也正是德国学界将1495年视为德国“继受”罗马法的开始标志的原因。[注]Franz Wieacker,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2.Aufl.,Göttingen 1967,S.176~189;Gerhard Wesenberg,Neuere deutsche Privatrechtsgeschichte,2.Aufl.,Lahr 1969,S.8,S.75;Broß,a.a.O.,S.9.当然这种法律传统的转变也与当时的文艺复兴和人文思潮的发展趋势相符合。事实证明,帝国最高法院作为各邦国地方法院的上诉法院,对于维护帝国的内在稳定性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帝国最高法院可以直接受理臣民诉状,这就为邦国内普通下层居民对抗封建领主在其领土范围内至高无上的权力提供了一个平台,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领主滥用司法权的行为,并为封建邦国内建立更为公正的司法系统提供了契机。[注]Laufs,a.a.O.,S.4.
四是“订单式”培训模式。“订单式”培训可以根据地区特有的产业特色,将农民生产中的需求与就业、培训建立了对应关系,进而生成高效的衔接机制。该模式可以重点用于对农民实用技术和增收致富技能等的培育,例如教会农民养殖技术、种植实用技术等。
三、帝国皇家法院(Rechtskammergericht)的设立
(一)设立背景
史学家通常将中古英国、法国视为王权从微弱走向强大,国家从割据走向统一的典型,而将德意志作为割据分裂长期延续的典型。[注]参见侯树栋:“德意志封建王权的历史道路”,《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因为西欧封建主义将国王置于封建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其封建法制并不包含会导致权力分散化的固有发展趋势。[注]Otto Kimminich,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2.Aufl.,Baden-Baden 1987,S.84.但是德意志封建王权却遵循着与英法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即伴随封建主义的发展不断走向衰弱。随着13世纪封建等级制度的形成,各地的封建领主逐渐登上权力的顶峰,在自己的领地中拥有铸币权、贸易权、关税权、矿山权、森林权,并逐渐形成一整套行政机构和完整的疆域,还有自己的政治中心城堡。[注]参见孙炳辉、郑寅达、赵星铁:《德国史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这一切都为15世纪德国邦国制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但是在整个德意志王国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德意志皇权与各封建领主之间却呈现出不同的力量对比状况,其在司法领域则表现为德意志皇帝的统一司法管辖权与各封建领地的司法管辖权及其领主的司法豁免权之间的平衡与制约关系。当皇权占据优势时,封建领主享受的司法豁免权的范围则日趋缩小;反之,当皇权日渐衰弱时,封建领主的司法特权的种类与范围则不断地扩大。
随着1356年帝国皇帝查理四世《黄金诏书》(Die Goldne Bulle)的颁布,[注]1356年,帝国皇帝查理四世颁布一项《黄金诏书》(因诏书上盖有黄金印玺而得名)从法律上承认选帝侯(Kurfürster)的政治特权地位。1356年颁布的“黄金诏书”是神圣德意志罗马帝国时期最为重要的基本法,规定了选帝侯的选举国王制度以及选帝侯享有的种种司法特权。诏书确认了选帝侯有选举皇帝的权力,诸侯在自己的邦国内有绝对的君主权力,各邦国内的市民和自由民都隶属于他们的邦君。选帝侯对于皇帝拥立与废黜大权的掌握,正式宣布了从萨克森王朝开始的、旨在建立以继承法则为依据的统一王权斗争的失败,皇帝的存在仅成为各大封建领主自检相互监督与制约的工具,从而从法律上确认了诸侯邦国分立的体制,加剧了德意志的分裂。——1356年的《黄金诏书》中规定了贵族对于国王廷审权的司法豁免权,但是在实践中该制度并没有得到真正实行。而且在实践材料中“appellare”这个词经常混用,有时候用于审级意义上的上诉权,有时候仅在国王将原本属于封建领主管辖范围内的案件提审至王室法院来进行审理这个范围内使用,其实质依然是第一审审级的审理。封建领主的法律地位得到确认,这就等于正式宣示,在德意志皇帝与封建领主的力量角逐中,封建领主的势力战胜了皇权。在随后1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皇权日益走向衰弱。15世纪以来法兰西王国的向东扩张以及东方土耳其人的崛起使德意志帝国的外部环境日益严峻。而在其帝国内部,各地领主之间的战争纷起,私斗复仇不断。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纷繁复杂的德意志各邦国地区性法律规则满足不了与德意志工商业急速增长相适应的快速统一化的要求,面对着内忧外患,德意志皇帝和封建领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意图建立统一的法律秩序,为帝国创造和平、安全的环境,进而恢复帝国的地位。而1495年帝国皇家法院的设立则是改革在司法领域的一个具体体现。之前在帝国领域内虽然设有统一的皇家法院(Königliche Hofgericht 和Kammergericht),但因封建领主过多的豁免特权并没有在司法实践中达到统一帝国内部法律规则的效果,[注]如在《黄金诏书》中规定的选帝侯享有的特权主要有:选帝侯对其封地享有的领主主权由其长子继承;对国王廷审权的豁免权(Privilegium de non evocando);对于异地司法管辖权的豁免(Privilegium de non appellando),即赋予其排除属人管辖地法院之外的其他法院的管辖的权力。前者设立的目的是对于相互冲突的法定管辖权的排除,后者设立的目的是排除不法管辖权的侵犯。就其法理而言,德意志国王依然是封建关系的最高代表,因此其理所当然地享有着国家的最高司法权。国王的廷审权(Evokationsrecht)就是其中的一种,即国王对于任何一个还未审结的案件,都有权将其提审至王室法庭审理。《黄金诏书》赋予7个选帝侯对于国王廷审权的司法豁免权,即国王对享有特权的选帝侯并不享有司法管辖权。因此1495年神圣罗马帝国颁布《帝国最高法院规则》(Die Rechtskammergerichtsordnung,简称《1495年规则》),宣布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成立帝国皇家法院。它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最高司法机关。
(二)《1495年规则》[注] Die Reichskammergerichtsordnung vom 7.August 1495,Aus dem Frühneuhochdeutschen übertragen von Ralph Glücksmann.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1.帝国皇家法院的人员设置
《1495年规则》第1条规定:帝国皇家法院由一名法官(Richter)和16名裁判官(Beisitzern)组成。法官必须具有贵族身份,即必须是教会的主教或世俗的侯爵(geistlicher oder weltlicher Fürst)、伯爵(Graf)或者男爵(Freiherr),他并不参与审判过程,只是确保法院的运作依正常流程进行,这与前面谈到的中世纪德意志法律实践相符合。在16名裁判官中,一半必须是受过法学系统训练的法律专业人士(Rechtsgelehrte),[注]这里有待商榷,很多人翻译为法学博士,该法律条文的德文文本表述为Rechtsgelehrte,拉丁文文本表述为der Recht gelert und gewirdiget。另一半至少拥有骑士的贵族身份。这样的人员设置客观反映了当时处于法律传统转型期的社会状况,即基于贵族的权威身份而获得判决合法性基础的德意志日耳曼法律传统与基于受过法律学术系统训练的法律专业人士的理性推理论证而获得判决合法性基础的罗马法律传统两者之间的较量。由于法律专业人士都经过罗马法诉讼程序规则和实体法渊源的职业训练,其教育背景和思维方式上的同质性逐渐形成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注]参见林海:“帝国枢密法院——德意志地区法制近代化的推动者”,《司法》2009年第4辑,第260页。而其他的贵族裁判官来自于帝国各地方邦国,适用纷繁复杂的地方性民事诉讼规则,无法形成内部统一的主导型法律意见,在两方力量人数平等的情况下其失败的命运也就在所难免。事实证明,1495年所建立的平衡状态很快就被打破,1521年修订后的《帝国皇家法院组织法》进一步规定,拥有骑士以上身份的裁判官如未受过大学法学教育,也至少应对法院判例有所研究。这一规定使得裁判官变成清一色通达罗马法的专家和贵族,[注]参见戴东雄:《中世纪意大利法学与德国的继受罗马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页。同时随着这一规定的大范围的推行,德意志地区的全面罗马法化也就成为必然。
2.审级体系的构建
在德意志王国“一审终审”时期,由于国王力量的日趋衰微,封建领主权力的扩张,王室法院在与领主地方法院争夺案件管辖权的斗争中处于劣势。随着1495年帝国皇家法院作为上诉法院地位的确立,王室法院赢得了第二审法院的管辖权。《1495年规则》第13条规定:帝国最高法院禁止接受跨审级的上诉。换句话说,上诉到帝国最高法院的案件必须逐级提出,即必须经过地方高等法院的审理。该法律规定不仅促成在帝国范围内形成地方和中央互相分工的上诉裁判体系,同时也促使在各地方邦国内依照该模式建立地方的自治分级裁判体系,因为上诉案件必须逐级提出的前提是在地方邦国内已经设置有本邦的高等法院及其诉讼程序。层级制的、上下级存在分工的审级裁判体系初见雏形。帝国皇家法院通过对帝国领域内上诉案件的审理,对各地方封建领地内的案件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进行监督,从而达到限制地方封建领主权力的目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过高地估计《1495年规则》的历史意义。为了平衡德意志皇帝和地方封建领主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为了减少规则施行的阻力,《1495年规则》也做出了一定的妥协,如赋予封建领主上诉豁免权(sog.Privilegia de non appellando),对上诉制度规定了诸多限制,使得领地内案件的最终裁决权留在自己所管辖邦国内等等。
《1495年规则》的颁布及帝国皇家法院的设立,仅是日耳曼诉讼法律传统中诉讼过程单级制(Einstufigkeit des Verfahrens)向罗马法诉讼审级多级制转化的起点。在认识到这一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1495年规则》仅具有32个法律条文,其篇幅的简短决定了其只能描绘出审级制度的大概轮廓,而不可能针对上诉程序中的具体问题,如审理范围和适用程序,当事人是否能够提交新证据等问题做出详细的规定,[注]《1495年规则》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是否能够在上诉审程序中提交新的案件事实和证据。但有学者认为,结合规则中的内容可以大概推测出,《1495年规则》是允许在当事人在上诉程序中提交新的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因为第14条规定,当事人在二审程序开始时必须提交书面材料,该学者认为这条规定实际上向当事人开启了一条可以提交新证据和新事实的路,否则除此之外,在上诉审法官已经拥有了下级法院所有案件庭审材料的情况下,让当事人提交书面材料没有任何意义。参见Broß,a.a.O.,S.38.但是笔者对此观点并不赞同,《1495年规则》第14条明确指出,要求当事人提交书面材料的目的是确保正确理解当事人的主张,避免误解等问题的发生,与当事人是否能够提供新事实和新证据并无关联。这就决定了它在“规则统一性”上只能发挥非常有限的作用。随着1555年《帝国皇家法院规则》(以下简称《1555年规则》)的颁布,上诉程序规则逐渐走向成熟。1600年前后,法院受理案件的绝对数量达到了顶峰,这些案件都是关于领主互相之间权利的冲突——刑事审判权、税收、狩猎权等等。正是通过对这些领主间纠纷的处理,帝国皇家法院树立起了自己在政治领域内的权威,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注]Filippo Ranieri,Versuch einer quantitativen Strukturanalyse des deutschen Rechtslebens im 16.-18.Jahrhundert anhand einer statistischen Untersuchung der Judikatur des Reichskammergerichts,in Rechtsgeschichte und quantitative Geschichte,Frankfurt am Main 1977,S.1~22.
四、1555年《帝国皇家法院规则》(简称《1555年规则》)
(一)规则颁布的背景
《1495年规则》与其称之为帝国皇家法院的审判程序性规则,还不如将之理解为宪法层面上的规则更恰当些。帝国皇帝在1495年陷入了严重的内外困境,因此希望得到德国各阶层的支持,暂停私斗并给予援助。而德国各阶层希望进行帝国改革,获得更多的自治权。在此前提下,《1495年规则》出台,建立帝国皇家法院。两者之间的活动犹如一场租赁交易活动:作为出租人的帝国皇帝为了获得短期的利益,出租了自己的帝国皇家法院,而作为承租人的帝国改革者利用这个机会,来消解帝国皇家法院的皇权特征。[注]Ingrid Scheurmann,Die Organisation des Reichskammergerichtes und der Verfahrensgang,in: Frieden durch Reicht,Das Reichskammergericht von 1495 bis 1806,hrsg.v.Ingrid Scheurmann,Mainz 1994,S.119.转引自前注〔26〕,林海文,第226页。帝国皇家法院的建立和《1495年规则》的颁布,是不同阶层之间寻求政治上的妥协而导致帝国宪法结构上的变革。但成立后的帝国皇家法院力求远离政治漩涡的中心,通过专业化的司法流程以及逻辑严密的法律论证体系来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治权威,并将其工作重点逐渐从“阻止各封建邦国之间的争斗,维持帝国范围的永久和平”转移到“建立并推广统一的民事诉讼规则体系,形成服务于大众的帝国范围内统一的独立司法体系”的任务上来。[注]Laufs,a.a.O.,S.16~17.与此同时,《奥格斯堡和约》的签订为国内带来了短暂的和平,[注]查理五世(1519—1556在位)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激烈反对者,实行长期镇压新教的政策,于1546年与帝国境内德意志新教诸侯爆发了施马尔卡尔登战争(Schmalkaldischen Krieg),战争以皇帝的失败而告终。和约结束了天主教在德意志的一统局面,是路德宗新教同天主教在德意志平等存在的法律根据。暂时稳定的政治宗教格局也为《1555年规则》的制定提供了可能。
(二)《1555年规则》的主要内容
《1555年规则》主要由人员设置(Personen)、司法权(iurisdiction)以及诉讼程序(proceß)三个部分构成。这与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中所提出的人法、物法和诉讼法的三分法体例结构有异曲同工之妙,成为德意志法律体系进一步罗马法化的又一有力佐证。在第一部分“人员设置”中,规定了法官(Kammerrichter)、陪审员(Assessor)、助审员[注]这里的“助审员”其实有点类似于大陆法系中“专家证人”,是由法院雇佣的,利用其自身拥有的知识或特定方面的经验为法院提供咨询的人员(Redner),应公正地处理案件,其不能私下与当事人达成任何从案件获取私意的协议。助审员的报酬由法院根据具体的法律规定来确定。参见《1495年规则》第6条的规定。(Prokurator)以及律师(Advokaten)等各类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在第二部分“司法权”中,主要规定了帝国皇家法院受理第一审案件和上诉案件的范围和权限。在最后一部分“诉讼程序”中,主要规定了帝国皇家法院审理第一审案件和上诉案件的程序规则。下面将重点分析帝国最高法院作为各封建邦国的上诉法院的性质及其受理的上诉案件的范围。
1.上诉程序中诉讼标的额的限制[注]Ulrich Eisenhardt,Die kaiserlichen Privilegia de non Appellando,Köln 1980,S.22~23.
随着涌入帝国皇家法院的上诉案件逐渐增多,繁冗的诉讼程序严重影响着法院审理案件的效率,为减轻压力,帝国皇家法院一再提高进入上诉程序的案件标的限额。《1555年规则》中规定的上诉案件诉讼标的额最低限为50个古尔登(Gulden,德国古代货币计量单位),[注]Kammergerichtsordnung von 1555 Teil 2 Titel XXVIII § 4.1570年提高到150个古尔登,[注]Rechtsabschied zu Speyer von 1570 § 66.至1600年已达到300个古尔登。[注]Abschied des Deputationstages zu Speyer von 1600 § 14.诉讼标的额的逐年提高,诉讼经济上的考量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帝国皇家法院越来越倾向于将诉讼争议额较小、案情比较简单的以及其他必须尽快做出判决的案件排除在上诉法院的审查范围之外。[注]如当时一般将商事案件、房屋修建等案件排除在上诉法院的审理范围之外,因为该类案件争议如果持续时间过长,将会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需要法院尽快对案件做出确定的判决。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案件的诉讼标的额以及案件的性质已经成为上下级法院功能分层的一个标尺。
2.第一审程序的影响
其一,书面审判以及卷宗主义(Aktenprozeß)的影响。[注]Franz Wieacker,Privatrectsgeschichte der Neuzeit,2.Aufl.,Göttingen 1967,S.184~185.依照日耳曼古老的法律传统,法院的审判活动采取言辞的方式进行。但后来受到来自教会法的书面审判程序的冲击,在15世纪左右逐渐瓦解。帝国皇家法院采取书面审判程序,并且严格规定,所有未记载入卷宗的事实,不能作为法官采证的根据(quod non est in actis,non est in mundo)。由于采取书面审理程序,法官无法直接接触案件当事人,从而给审判活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实践中法官遇到疑难问题的时候,往往倾向于将案卷移送(Aktenversendung)给附近大学的法学院,由法学院的专业教授对其进行答复。为了便于教授有针对性地对其中的疑难法律问题进行解答,法官一般已经针对案件中出现的纷繁复杂的各类事实按照法律关系的归属进行了提炼,教授解答的重点将不再是具体案件事实的判别,而侧重于运用其专业的学术背景对涉及的法律关系做出判断。[注]以帝国最高法院1792年受理的Bruchsal市Witwe Bellon 药店诉Speyer 主教候地方政府曾为宫廷所属的药店颁发了一份附加许可证,未获得此类附加许可的原告Witwe Bellon药店认为这不公平,可能会影响自己的生意,诉至法院。卷宗就可以将其提炼为“独占特权案:是否会影响自由贸易和经营权利”的法律关系。见Rita Sailor,Untertanenprozesse vor dem Reichskammergericht: Rechtsschutz gegen die Obrigkeit in der zweiten Hölfte des 18.Jahrhunderts,in: Quellen und Forschungen zur hächsten Gerichtsbarkeit im Alten Reich,Bd.33 (Böhlau,Köln-Weimar-Wien 1999),S.334~335.转引自前注〔26〕,林海文,第244页。这一书面审理的过程实际上已经是“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相互剥离的第一步,为后来的上诉程序的审查及其区分提供了便利,因为所有第一审的审判材料将构成上诉法院的审查范围。
其二,“区分分明”(artikuliert)的“争点程序”(Positionalverfahren)。在这个程序中,当事人法律上的陈述被划分为多个独立的“争点”——每个争点都采取独立的诉讼方式进行攻击或者防卫,诉讼程序采取攻击(Angriff)、防卫(Verteidigung)和反击(Gegenangriff)的顺序进行。法院应按照不同的法律关系将案件的自然事实进行提炼,区分出诉讼请求权(Klagansprüche)、对请求权的异议(Einwendungen)以及相对应的其他请求权(Gegenrechte)。[注]如为对抗其债权人,借贷人必须采用以下复杂的形式来表示:我不对你富有任何债务,根本未曾从你那儿得到任何东西;无论如何,即使有取得任何东西,亦已返还;此外,我对你还享有相反的请求权。由此法院将其债权债务关系分割为:否认(没有债务)、抗辩(虽然负有债务,但已返还)以及反击(对方也欠其相同类型的债务)。前注〔26〕,林海文,第245页。每个诉讼阶段伴随着相应的独立的证据调查活动,并产生阶段性的证据判决结果。随着案件审理过程的逐渐推进,案件本来的自然事实提炼为法律规则中一个个抽象化的符号,而最后法官判决的做出则成为逻辑推理在法律论证领域的一个自然结果,其前提条件当然是受过系统法律训练的法官职业团体的形成。当然这一程序的运用,将会导致诉讼程序冗长(因为每个争点都要经过当事人双方的反复论辩),使法官无法从整体层面来把握案情。争点程序的出现,进一步分离了事实和法律之间的联系,使得法院的审判过程由“发现法律规则”转化为“适用法律规则”。
虽然在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中,并不存在促使“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区分技术产生的现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寄希望于在第三审“法律审”中凭空产生完备的区分理论和可操作性制度规则,这无异于“空中楼阁”,只可远观。这里无意花过多的笔墨来进行“争点程序”的具体细节及其优劣性分析,至少应该得到一个信号:法院对于当事人之间对于案件自然事实的争议,应该从第一审程序开始逐级分离出实质的法律关系争议,而这一逐级分解的过程也为发展法律规则提供了契机,无疑在当今的中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同时第一审法院和第二审法院承担辨析分解案件自然事实的功能,为第三审法院专职审查法律纠纷节约了时间和精力,上下级法院之间存在明确职能分工的审级裁判体系也就更加明晰化。
3.救济途径
在《1555年规则》中,对帝国皇家法院做出的终审判决禁止再行上诉(appelliren)或者另行向国王提起申诉(supplicirn)。但是在特殊的法定情形下,如果当事人对于终审判决不服,可以依法提起第三审(revision)或者向法官要求损害赔偿(syndicat)。[注]《1555年规则》第三部分第53章第1条。这也是第一次在法律条文中正式出现“revision”这个词,因此有学者认为第三审最早于《1555年规则》中产生[注]Johann Heinrich Christian von Selchow,Einleitung in den Reichshofrathsprozeß aus einer Handschrift des Franz Winand von Bertram,3 Bände,Lemgo 1778~1781,S.910.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虽然1532年颁布的《帝国决议》(Reichsabschied von 1532)中使用的是“suppliciren”这个词,但是却与“revision”具有相同的内涵。见Wolfgang Sellert,Prozeßgrundsätze und Stilus Curiae am Reichshofrat,im Vergleich mit den gesetzlichen Grundlagen des reichskammergerichtlichen Verfahrens,Ebersberg 1973,S.375.在其后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Westfälischen Friedensvertrag)和1654年《帝国皇室法院规则》(Reichshofratsordnung von 1654)中都是使用“suppliciren”这个词来表示第三审(revision)的概念。这是由于“suppliciren”这个词本意具有“个人向皇帝提起申诉请求”的意味,而帝国最高法院在其成立之初,就尽力塑造“完全独立于皇权”的中立司法机构的角色,因此在其组织规则中便极力切断国王对于帝国最高法院做出的判决可能造成的干预,也就不可能使用具有皇权色彩的“suppliciren”来表达再审的含义。相反,帝国皇室法院的成立就是以向皇帝提供政治咨询为目的,与皇帝本人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因此法律文本使用“suppliciren”也就在情理之中。。对于终审判决,《1555年规则》规定了三种救济途径,即无效之诉(Nichtigkeitsklage)、损害赔偿之诉(Syndikatsklage)[注]Reichskammergerichtsordnung von 1555 Teil 3 Titel LIII § 6.以及再审之诉(Restitutionsklage)[注]Reichskammergerichtsordnung von 1555 Teil 3 Titel LII.。再审之诉在功能上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审判监督程序”,是基于终审判决做出后新情况或新证据的出现,导致原判决内容错误而需要重新进行审判,与第三审程序存在较大的区别。损害赔偿之诉是当事人针对做出不公正或者无效判决的法官而提起的要求损害赔偿的诉讼,并不是针对原判决效力本身,本质上并不属于一种上诉手段,而只是对于法官公正执法的一种担保,因此也不属于这里所论及的第三审的范畴。[注]也有学者对此持相反意见,即认为两者都属于上诉手段。见Benjamin Ferdinand Mohl,Historisch-politische Vergleichung der beyden höchsten Reichsgerichte in ihren wichtigsten Verhältnissen,Ulm 1789,S.375;Selchow,a.a.O.,S.885。下面将重点分析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第三审源头的“无效之诉”。
导致判决无效的情形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判决的无效并不是基于欺诈或者恶意(auß betrug oder argelist),而是由法官或者助审员的疏忽(ubersehen)、不勤勉(unfleiß)、无知(unwissenheyt)或者误解(irrsall)导致。[注]Reichskammergerichtsordnung von 1555 Teil 3 Titel LIII § 5.其二是判决的无效是由于法官或者助审员出于他人的馈赠(geschenck,gab)、请求(bitt)、友谊(Freundtschaft)、怨恨(feindtschaft)或者类似的理由而导致。[注]Reichskammergerichtsordnung von 1555 Teil 3 Titel LIII § 6.在第二种情形下,当事人除了可以提出“无效之诉”外,还保留有对判决做出者要求损害赔偿的诉求。如果出现以上所列举的判决无效的法定情形,当事人可以向帝国皇家法院的监督委员会(Visitation)提出申请,要求宣布该判决为无效判决或者不公正判决。
监督委员会[注]监督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508年末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举行,其主要成员是美因茨和拜仁选帝侯派出的咨询员(Räte),国王代表由于特殊原因当时并没有出席。见Klaus Mencke,Die Visitationen am Reichskammergericht im 16.Jahrhundert,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Rechtsmittels der Revision,Köln 1984,S.13。最初主要由选帝侯(Kurfürsten)代表和罗马帝国皇帝代表(kaiserlichen Kommissare)组成,后来人员也逐渐扩大至其他帝国等级。监督委员会的活动可以分为例行会议和特殊会议(ordentliche und außerordnentliche Visitation)。例行会议定期于法律规定的时间内根据固定的会议议程举行,而特殊会议则根据帝国议会颁布的特殊决议举行。[注]Mencke,a.a.O.,S.11.最初设立的监督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在于处理帝国最高法院的财务问题、法院组织成员(Gerichtsmitglieder)的业务考核(Personalexamen)以及对现行适用规则的修改建议。具体而言,财务处理问题主要是指由监督委员会每年根据以往法院的财务收支情况结合日常活动的具体需求,确认法院当年应该上缴的税费;[注]Mencke,a.a.O.,S.21.业务考核主要是通过由监督委员会制定的问卷形式对成员的业务能力和品格进行评定(具体的标准如:是否能够严格遵守法律、是否能够勤勉灵活地处理案件等等),[注]Mencke,a.a.O.,S.42~43.监督委员会可以根据评定结果建议罢黜不合格的法院成员(到了1529年监督委员会已经拥有了独立的罢免法院成员包括陪审员的权力,[注]Mencke,a.a.O.,S.40.而无须事先取得帝国皇帝或者帝国议会的批准)。修改建议主要是指监督委员会针对以《帝国法院适用规则》为主导的程序性审理规则在实践中的运行情况,对其不合时宜的内容提出新的修改建议。[注]Mencke,a.a.O.,S.39.随着《1555年规则》第三审程序的确立,受理并审查当事人提出的“无效之诉”成为监督委员会越来越重要的任务。
监督委员会定期于每年的五月一日开庭审理案件(一般为期15~20天),因此当事人最迟应该在开庭前两个月统一将书面申请材料提交至美因茨大主教(Mainze Erzkanzler),由其转交监督委员会。如果案件判决于三月一日以后公布(即公布时间距离监督委员会开会时间已不足两个月),则对该案件的“无效”申请应推迟至来年提交。[注]Mencke,a.a.O.,S.85.当事人只能针对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出现的违法现象提出责问,不允许提交超出原审法院案卷的新的诉讼请求和证据。[注]Reichskammergerichtsordnung von 1555 Teil 3 Titel LIII § 3.原判决的效力随着当事人申请的提出而暂时中止(Suspensiveffekt der Revision)。因此为了防止当事人恶意提交无效判决的申请,在提交申请的同时应交纳保证金,如果最终监督委员会判定驳回当事人的申请,保证金则上交国库。但是保证金的交纳并没有起到实际的效果。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当事人为了推迟原终审判决的执行恶意提交无效判决申请,而监督委员会也因越来越多的案件涌入而不堪重负。[注]因此在帝国最高法院监督委员会积压的案件数量呈直线上升趋势。1595年只有11件,1600年上升到36件,1607年150件,1613年300件,1644年1 000件,而到1653年竟然已经急速增加到2 000件。Mencke,a.a.O.,S.58~59。尽管无效之诉制度在实践中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该制度的设立带来的积极意义。无效之诉建立的初始动机,是为了保障终审判决的正当性,因此监督委员会侧重于审查在做出终审判决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着违法行为(Rechtsverletzung),即当事人挑战的是原审判决在其做出过程中的形式合法性问题,而不涉及实质合理性论证,因此新的诉讼请求和证据不在其审查范围之列,为现代意义上的“第三审”的功能设计指明了方向。
(三)评价
总体而言,《1555年规则》的实行状况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虽然《1555年规则》对于第一审程序规则规定得相对比较完备,但是当时德意志帝国权力羸弱,而封建诸侯权力过分强大导致法院判决的执行力大打折扣。帝国最高法院作为上诉法院的角色也因封建诸侯“上诉豁免权”的存在而名存实亡,即便偶尔做出有效的终审判决,其效力往往也因当事人随性提交的无效之诉申请而自动中止。而第三审程序在实践中也面临着重大的困境,一方面,帝国最高法院的监督委员会每年一次的开庭无法应对日益增多的案件量,案件积压情况严重;另一方面“原审判决效力随着当事人递交申请而自动中止”这一规定也使得帝国最高法院受到众多非议,甚至一度有建议废止第三审,最终因“对帝国宪法结构改变过大不具有现实性”而被暂时搁置。[注]Johann Gottfried v.Meiern,Acta Comitialia Ratisbonensia publica oder Regensburgische Reichstagshandlungen und Geschichte,2 Bände,Leipzig/Göttingen 1738/1740,S.399.针对实践中出现的种种困境,帝国议会自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期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并在此基础上最终于1654年5月17日颁布《帝国最新决议》(Der Jüngste Reichsabschied)。其中涉及第三审的改革措施主要侧重于解决前面所论及的“当事人提交无效申请后原终审判决的效力问题”。决议中规定,如果原审判决的胜诉方在判决执行前提供足够的担保(具体的担保数额由法院在相应的程序中来确定),则原审判决的效力并不因当事人提交的无效之诉申请而自动中止,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帝国最高法院的压力。[注]但是实践中依然存在着如担保额规定得过高、胜诉方基于担心第三审积案时间过长短时间内无法收回担保额而拒绝缴纳担保金等等问题。见Heide-Marie Götte,Der Jüngste Reichsabschied und die Reform des Reichskammergerichts,München 1998,S.173~174。《1555年规则》中无效之诉建立的初始动机,是为了保障终审判决的正当性,因此监督委员会侧重于审查法官在做出终审判决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着违法行为。在德意志法律传统的发展过程中,无效之诉是当事人抵抗法官恣意裁判的最后一道屏障,因此在最高审级的制度设计中当事人对公平裁判的诉讼利益处于第一位。
五、结语
在德国1495年上诉制度产生之前,司法判决的形成过程主要采取“事前咨询”和“事后救济”两种途径,但由于当时社会上并不存在既定的法律规则体系,以及司法判决和司法强制在组织和功能上处于分离状态,因此现代意义上的“上诉制度”在中世纪的初期和中期还并未产生。尽管如此,却已经在其发展过程中孕育出审级制度的结构性因子(即司法权威及其贯穿辖区的辐射力),正是这种“在整个辖区范围内实现公平和司法统一”的内在需求,构成审级制度形成的原始驱动力,在这种外在制度性障碍和内在驱动力的历史交替年轮中最终导致德国上诉制度的产生。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纷繁复杂的德意志各邦国地区性法律规则满足不了与德意志工商业急速增长相适应的快速统一化的要求,因此“建立统一法律秩序”的强烈社会需求催生了1495年帝国皇家法院的设立,同时帝国皇家法院作为上诉法院地位的确立,反过来促进了职能分明的上下级审级裁判体系的建立,加速了全国范围内法律秩序的统一进程。
尽管帝国皇家法院的成立,是不同阶层之间寻求政治上的妥协而导致帝国宪法结构上的变革,但成立后的帝国皇家法院力求远离政治漩涡的中心,将其工作重点逐渐从“阻止各封建邦国之间的争斗”转移到“建立并推广统一的民事诉讼规则体系”的任务上来。《1555年规则》中所涉及的书面审判程序以及区分分明的争点程序的规定,加速了实质的法律关系争议从第一审程序中进行分离的过程,上下级法院之间存在明确职能分工的审级裁判体系进一步明晰化。第三审程序中“无效之诉”建立的初始动机,是为了保障终审判决的正当性,这一原始动机注定了在最高审级的制度设计中,当事人对公平裁判的诉讼利益不能也不应该被忽略。
从德意志审级框架产生、发展至最终形成的发展轨迹来看,司法统一理念的引入对于审级架构的最终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的追求固然可以作为国家构建梯级审理框架的合理性依据,但并不构成唯一主导性依据,因为国家提供唯一的、使得事件得以有效审查的审级即符合了“公正”的司法理念。而司法统一的需求必须借助于审级框架这个媒介,将各地的法律适用信息由下至上反馈至国家最高司法机关,然后再将其统一适用标准由上至下涵盖至国家的整个领域,这种司法上乃至政治上的向心力是构建审级体系的最终动力,而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则是其连锁司法反应的导火索。国家司法统一理念与当事人的诉求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决定着审级制度的最终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