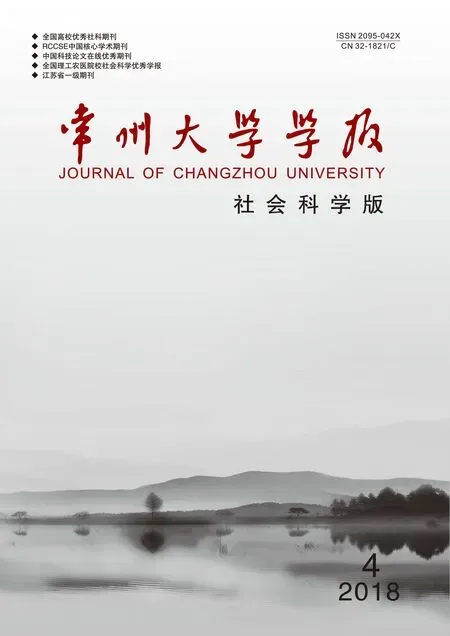《红楼梦》人物命名中真假系统的文化阐释
孙 娟,陈良中
姓名作为以性为根、以姓为本的特殊文化符号,有其独特的结构、礼仪和制度,可以体现出兼“同一”与“独特”于一体的身份认同。身份是一种出身或社会位置的符号标识,而认同旨在表达与他人相同或区异的观念行为[1]。即使“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也难以磨灭姓名系统中潜藏的神话传说烙印,以及时政、经济、信仰、风俗等因素的深刻影响[2]。从姓名中往往可以窥探命名者的心理过程和学识素养,从而反映传统习俗和文化认同。学界[3-6]对《红楼梦》中人名的命定原则及其隐喻性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仍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今以命名艺术可奉为“枕中鸿宝”的《红楼梦》为例,剖析以甄、贾(即真、假)对举为基础的命名系统。本文所讨论的“真名”,指可在官方文书中使用的唯一真实姓名,其它皆为“假名”,一个人可对应字、号等多个假名。探讨《红楼梦》人物命名中的真假系统,可以展现其丰富的思想资源、成熟的艺术技巧与潜在的文化认同,从而管窥经典作品对民族精神世界的传承与反思。
在文化认同视野下,从真假两极对举的角度切入,人们可以窥探曹雪芹作为满洲正白旗人对汉族文化的认同与融通,可以发掘其面对时代与道德困境时的焦虑与回应。
一、“真”名之伦理认同
姓名是名主标示自我的价值符号,拥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体现着对宗法中国重人伦这一传统的价值认同。
(一)别男女
名字能反映男女的特质、身份及社会分工的不同。相较之下,男性名强调自我核心,显现更多的自我认同;而女性名则注重社会属性,呈现更强的社会认同。
《红楼梦》中的男性名大多或抒发志向,如李“德”、贾代“儒”、戴“权”、赵“国基”、贾“政”等;或渴慕美德,如邢“德全”、林之“孝”、卜世“仁”、 余“信”、夏秉“忠”等;或企盼荣兴,如北静王“世荣”、牛“继宗”、蒋“子宁”、王“子胜”、张“若锦”等。而较为典型的女性名或表现妇功,如李“纨”(字宫裁),名、字皆与纺织、刺绣、缝纫有关;或蕴含雅趣,如贾府四春的丫鬟,分别名作抱“琴”、司“棋”、侍“书”、入“画”,合之为“琴棋书画”,暗合社会所认同的大家闺秀形象。
姓名大多蕴含美好的寓意和希冀,也能显露出长辈(甚至社会)对男女的不同规范要求和审美倾向。男子多以符合“三达德”*三达德:出自《中庸》,即智、仁、勇三种德行。或“十义”*十义:出自《礼记·礼运》,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为美,如包“勇”、王“仁”、余“信”、乌进“孝”、戴“良”、詹“惠”、邢“忠”等;女子则多以表现雅趣、花鸟或珠宝为美,如薛宝“琴”、翠“墨”、“莲花”、夏“金桂”、偕“鸾”、绣“鸳”、“鸳鸯”、“琥珀”、“玻璃”、“翡翠”等。观察谢“鲸”、薛“蟠”、紫“鹃”、春“燕”、“莺”儿等名,可以发现男性名所用的动物多硕大凶猛,女性名所用动物则温和可爱,即男子以高大威猛为美,女子以娇俏可人为美。男子名字所强调的美德都具有能动性和社会性,内在地涉及一种与他人的动态关系,而类似纯洁或天真无邪那样静态的或内在的美德,则较多地附丽于女子姓名之上。
少女之名,可反映出曹雪芹对永恒之美的追求,即对纯真少女的赞叹,但也隐射出其美好却脆弱的本质,潜藏女子依附于男子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中已婚妇人不在“水做的女儿”之列,更不是美好纯真的化身,已然从少女时代“无价的宝珠”变作了“死珠”或“鱼眼睛”了,曹雪芹这一态度也清晰地体现在姓名上。其姓名大多以“夫姓+称谓语”为固定模式,缺乏独立性与自主性。如贾“母”、王“夫人”、赵“姨娘”、张“奶妈”、李“嬷嬷”、来旺“媳妇”、祝“妈”等,不仅有出嫁从夫之意,也显示出女性为男性之附庸的低下地位。
若根据“社会”和“个体”这样两极性的模式来加以阐释,则男名强调“个体”(自我)和第一性,而女名倾向于“社会”和第二性[7]82。明尊卑、别男女是宗法等级观念在姓氏制度中的反映,也是被曹雪芹所认可的社会基本原则及行为规范。但对于由此衍生出的某些现象和观念,曹雪芹表现出的认可度则不一。
(二)体宗族
古代的姓氏与宗法等级关系紧密。《红楼梦》中“钟鸣鼎食”“翰墨诗书”之贾氏族人是上层的代表,不仅巨富,而且显贵,是“世卿世禄”的“百年望族”,所以命名颇为讲究地运用“范字”。与主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贾府的下人,可作为中下层的代表,其名多为随意地取自相关人、事。仆役之名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有名无姓,或只称名不道姓:如宝玉的小厮,名如“焙茗(茗烟)”“引泉”“扫红”“锄药”“墨雨”等,分别指向泡茶、浇水、扫花、伺药、笔墨等职责;黛玉的丫鬟“紫鹃”和“雪雁”之名与黛玉的情感和多病啼血有关。另一类是有姓无名,或干脆以职务之谐音为姓:如看花草的叶妈之“叶”,看竹子的祝妈谐“竹”,看荷塘的何妈谐“荷”,看树木的柳妈之“柳”,大观园种菜的田妈之“田”。底层以穷苦大众为代表,其取名侧重反映生活:或反映悲苦,如夏金桂的小丫头由于自幼父母双亡,故名“小舍儿”;或源于生活,如“卍儿”;或反映愿望,如张才谐“涨财”;或以贱命名,如“狗儿”,寓好养之意;或示意排行,如(醉金刚)倪“二”、赖“二”、何“三”。
姓氏既与宗族相关,不被曹公认同的“认宗”观念亦随之而来,小说中贾雨村“寅缘”复旧职,辛辣地讽刺了这种封建时代的丑恶心态。认宗思想“率由旧章”。明确身份、维系血统的家谱和大、小宗制度(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令宗族历久弥续。尽管“世爵世禄”制于秦汉后被取消,“宗子”之标准也由血缘脉络变而为地主官僚,但宗法家族的姓氏、门第仍是高贵显达的标志[8]。故而,有人以“认宗”来攀附权势,从而演变出姓氏制度中所谓“通谱”“认宗”的现象,如曹操出于政治需要“三易其祖”便是其中典型。
(三)序行辈
封建社会时,起名常用“范字”,即以“姓+族辈+名”为主的家族式起名方式。小说中贾家子女取名即按祖上已排好的行辈次序。第一代为“水”,长子贾演,次子贾源,他们的名中带共同的偏旁*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同辈关系,如宋代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再如《红楼梦》中贾家第一、三、四、五代皆用共同偏旁表示同辈关系。“氵”,象征贾府“荣”“宁”兴盛之源,教后世子孙明辨世系,尊宗敬祖。第二代是“代”,如贾代化、代善、代儒、代修。“代”意为更,更乃化、善、儒、修也,意为寻根留本,教人敦亲睦族、修身齐家第三代是“攴”字,“攴”意为小击,如贾“敷”、贾“政”、贾“敬”、贾“赦”、贾“敏”。“攴”本为承前启后,教人教化子孙,但由于从“攴”,又潜含讽刺意味,身不修何以齐其家。第四代是“玉”,标示三代人的权、财、势累积下的家族底蕴及脂粉、声色气息,“玉”在左旁(贾宝玉为特例)。“玉”本为石之美,有五德,反其道而用之,如贾“珍”、贾“琏”、贾“瑞”、贾“珠”、贾“环”、贾“璜”等人,更衬出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本质。第五代是“草”,都是“头上草”,如贾“蔷”、贾“蓉”、贾“芸”、贾“芹”等人。第四代之“玉”和第五代之“草”前后相承形成鲜明对比,是“宝”和“草”即“贵”和“贱”的代名词。这象征着从极盛到极衰的显著落差,亦符合“反者道之动”即“物极必反”的规律,正所谓“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五服”。
此外,小说《红楼梦》中的赖“二”、何“三”,再如贾府四春之名,以元、迎、探、惜法春之时序及用事之先后来序齿*《白虎通·姓名》有载:“法四时用事先后,长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时长幼号曰伯仲叔季也。伯者,长也。伯者,子最长迫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男女异长,各自有伯仲,法阴阳各自有终始也。”参见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第416页。,皆源自重人伦的命名思想。这种序长幼之法,其目的是维护宗法家族的纲常伦理,且男女皆适用,如《春秋》之伯禽与伯姬。“伦”,意为同族之人的条理、顺序。宗法伦理有兼自然(血缘)与文明(等级)的双重特征,其视五伦为基本,其中最核心、最根本的是父子关系,加之祖先崇拜的文化基因,使论资排辈成为人伦日用之中转相增益的礼仪节文。因此,行辈乃农耕文明下文化认同中祖先崇拜基因的产物。时至今日,由于姓名越发彰显个性,又融入了现代和西化的元素,导致按家族辈分起名法渐渐淡出视野,重名现象也愈发普遍。
姓氏制度从产生之初就携有严肃而神圣的伦理意涵。之所以有姓,是为了“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使生相爱,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参见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第401页。。郑樵《通志·氏族略序》曰:“女生为姓,故姓字多从女,如姬、姜、嬴、姒、妫、姞、妘、婤、嫪之类是也。”如果说姓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则氏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如轩辕氏、神农氏、燧人氏等。《说文解字注》载曰:“姓者,统于上者也;氏者,别于下者也。”[9]原初时期姓、氏有别,且以姓称女、以氏称男*袁庭栋认为,“最初的‘氏’,大体上应当是各个父系氏族的称呼或标识,也可以是该氏族的男性首领的称呼”。参见暴希明:《从甲骨文“姓”、“氏”二字看中华姓氏的由来》,《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第245-249页。。秦汉以后,姓、氏合一。不仅如此,还发展为姓以男性为核心,氏以女性为核心。姓与氏的嬗变中,可以管窥权力的性别转移,即由女权转向男权。姓最重要的功用是别婚姻,令同姓不得相娶。《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有载:“男女同姓,其生不蕃。”[10]因而,这一制度发展到后世,对以传宗接代为主要任务的女性来说,为防止同姓通婚,姓比名更为重要,如出嫁后的妇人“邢氏”和“尤氏”等,名已不存,仅留姓以相区别。氏可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而贱者无。可见,姓、氏可以反映出身份地位,甚至权力和心理倾向上的区别。“名”的功能是“吐情自纪,尊事人者”,先“正名”再借名之正以“正体”是圣贤的处世策略。由于人类的聚生群处,身份虽源于个体性,但最终仍要归于社会性。
姓名兼认同与区异于一身,是对身份、利益和归属的一致性体验。《红楼梦》中的姓名体现了在社会类化和社会比较基础上的别男女、体宗族、序行辈等宗法等级观念。
二、“假”名之行业认同
体现宗法等级观念的真名由长辈取定,而假名可以自己拟定。若说真名具有稳定性,则假名具有随意性,且后者可以凸显名主在不同文化群体间集体身份的选择与认同。由于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名主须从中选择一种作为集体文化自我,而将其他视为他者。《红楼梦》中的人物除了有“梦”中的真名以外,还普遍有用以“行走江湖”的假名。这些假名按行业之别可分为三类,即笔名、艺名、法名,体现了职业认同与身份选择。
(一)笔名群体
相对于姓名而言,字、号可自己选定,比如笔名。它能较为自由地反映名主的文化意涵与个性气质,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表现其人生追求和处世哲学。
笔名群体多展现文人的雅趣。《红楼梦》中最特别的笔名当属“颦颦”。这是宝黛初会时宝玉赠给林黛玉的字,理由颇多。其一,取“颦颦”有相关之义。西方有石名黛,可作画眉之墨,而林妹妹眉尖若蹙,“颦”乃皱眉之义,符合黛玉多愁善感的病美人形象。其二,晏几道《采桑子》词中有“颦入遥山翠黛中”,此取其典。再如甄士隐,名费,字士隐,出自《中庸》“君子之道费而隐”,即君子之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可谓费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则隐而莫之见也”[11],又与《庄子》所谓“无用之用”[12]相合,表明甄士隐名虽谐“废”,但并非完全无用,有提示读者“真事隐”之功,也可见曹雪芹辛苦十年的《红楼梦》如“君子之道”般“致广大而尽精微”。
《红楼梦》人物取字者虽不多,但所取字多较为典型,富有浓厚的艺术情趣。例如贾宝玉,其别号有许多:其一,“怡红公子”,取自他“悦红”(喜欢女孩儿)的秉性及住地“怡红院”之名;其二,“绛洞花主”,不仅缘自其屋里贴的“绛芸轩”,还标示出“绛珠仙草”的感情归属,绛珠即“泪血”,表明林黛玉爱哭的性格和还泪神瑛的使命,此外还符合“字字看来皆是血”的《红楼梦》主人公气场;其三,宝钗所送的“富贵闲人”,符合宝玉身为世俗贵族,心却游走于功名利禄之外的特点;其四,“无事忙”,亦宝钗赠予,和“富贵闲人”一样暗责宝玉不务仕途之正业,而整日“护花”。
再如李纨别号“稻香老农”,字宫裁,名字、别号皆引人深思。其一,“宫”可通“官”,暗示其出身于名宦之家,恪守“无才便是德”的礼法,终日营于女红;其二,“宫”为五刑之一,“淫刑也。男子割势,女子幽闭”,暗合李纨的青春守寡;其三,“宫”又可通“躬”,与别号“稻香老农”一道反映出农耕文明下耕读传家的传统家风。
此外,史湘云别号“枕霞旧友”,这不仅与史家之“枕霞阁”相关,且霞与云关系紧密,喻示湘云居无定所的境况和乐观明朗的性格。迎春的别号“菱洲”与其住所“紫菱洲”之名也别有深意。菱有角,暗示其性格类木,处世不圆滑;菱根基浅,暗合其庶出的身份和因无人护佑而“零落成泥”的悲剧命运。惜春的别号“藕榭”与其住所名“藕香榭”一样,皆值得仔细探索体味:其一,暗示她的愁思如藕丝般难断,结局如藕根般苦涩;其二,莲藕因并蒂同心、其叶偶生的特性而衍生出嫁娶祝福的意蕴,与惜春孤身一人的凄凉结局构成反衬;其三,莲的文化意蕴与佛教密不可分,莲根为藕,是其遁入空门的伏笔。再如黛玉之别号“潇湘妃子”,与多竹的“潇湘馆”一样意蕴丰富,不仅有娥皇、女英哭舜而投水的典故,还可借竹的修长外形喻示黛玉的纤弱之姿,借竹的神韵喻指黛玉之“还泪”任务等。
笔名,主要分字、号两类。尊对卑称“名”,下对上称“字”*“名者,己之所以事尊,尊者所以命己;字则己之所以接卑,卑者所以称己。”参见李昉:《太平御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6页。。取字是有讲究的。首先,男女成年后才可取字。男子满二十岁行冠礼时才能取字,所谓“幼名,冠字”[13]207。孔颖达注:“冠字者,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13]1412-1413正所谓“敬其名也”[14],“成人之道也”[13]1413。因为“成为成人才可以为人,可以为人才可以为治人,取得‘治人’的贵族特权”[15]。男子冠字,女子笄字*《白虎通·姓名》有载:女子“十五通乎织纴纺绩之事,思虑定,故许嫁,笄而字。”参见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第416页。。“冠”“笄”分别指“冠礼”和“笄礼”,是男子和女子的成年礼。“笄”是发簪,指结发而用簪子贯之。女子许嫁,“笄而醴之”,称“字”。“字”,其义为“乳”,而人及鸟生子为“乳”。可知,男女取“字”,是表示已成年可成家生子,这时需要得到社会的尊重,因而他人不便直呼其名,故择一与其本名涵义相关的别名,以表其德。其次,表字与名之间要有形对、音对、义对等对应关系,改名就要改字。
(二)其他群体
行业作为身份的象征,可标示出其行业烙印、阶层归属以及职业声望。与被曹雪芹视为集体自我*曹雪芹视知识分子群体为集体自我,该群体多以笔名为文化身份符号。的知识分子群体不同,《红楼梦》中的其他群体是他者。前者多肯定,而后者多否定。以最为典型的艺名和法名道号为例,分别展现枷锁难脱、真假难辨的特征。
1.艺名:枷锁难脱
《红楼梦》中有一类特殊人物,即优伶(包括家伎、职业优伶、串客),其名为“艺名”。如“十二家伎”,又称“十二官”,她们依“官”起名,而多从“艸”,即多以植物意象为名,暗示她们像依附于他者的蔓生植物,表明出色的才貌与卑下的地位兼而有之。这些窈窕淑女所具有的美好品质、高超技艺与独立人格为曹雪芹所肯定。但令人惋惜的是,高贵性情与微贱身份对比产生的强烈反差使她们或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与抗争精神,或因怜受宠而恃宠生骄,最后招致祸患。
艺名的使用可以追溯至上古时期,诸如“弈秋”“庖丁”“匠石”“伶伦”“医和”“优孟”“屠蒯”等,往往以职业在前,姓名在后。《红楼梦》中不仅有预示“十二金钗”命运的“十二家伎”,还有职业优伶琪官(本名蒋玉菡)及半侠半优的串客柳湘莲。这些优伶的取名形式有两种:有姓者,如蒋玉菡、柳湘莲等;无姓者,如“十二女伶”即是纯艺名。他们以艺名相称,有些甚至无真实名姓。在封建社会,艺名大多暗含对人格的侮辱,因为无名无姓即意味着来路不明、无依无靠可任人欺侮,这是他们社会身份的枷锁。
2.法名道号:真假难辨
僧尼道士是《红楼梦》中的另一类特殊群体,或已出家入寺门,或未出家但已皈依三宝,他们通常使用法名道号。法名如同剃度一样,目的是表示“寸草不留,六根清净”,脱离凡俗。但作者借法名道号形成了真、善、神与假、恶、俗的鲜明对照。
《红楼梦》中的僧尼道士之名表现了宗教的异化,展现出独特的美丑观念与二元对立。一类表面看来邋遢疯癫,却济世度人,如“癞头”和尚、“跛足”道人、“龙钟”老僧;一类脱俗如世外高人,却庸俗卑劣,如“水月庵”净虚、“清虚观”张道士、“天齐庙”王道士。通过真假、善恶、神俗等对比体系来凸显真善美与假恶丑。
《红楼梦》中还有空空道人、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警幻仙姑、梦痴仙姑等杜撰的神仙,其名暗示了世上的富贵荣华、生死荣辱不过黄粱一梦,反映了佛教“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色空观与道家“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有无思想,表达了曹公对现实社会奢侈淫靡景象的清醒认识,并且预示了封建社会“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终将消亡的历史命运。生死、盛衰、真假、虚实、善恶、有无、祸福等两极性概念的对举,更深刻地凸显出“空”“无”的永恒性。以“空”“无”来导向人生的最终归宿,意在警醒世人,使人返璞归真,“因空见色,自色悟空”。
虽然曹雪芹以笔名群体作为集体自我,视其他群体为他者,但在集体身份选择时,也有身份认同上的嬗变。笔名群体是在肯定的基础上否定,而其他群体是在否定的基础上寻求可资借鉴的积极意义。
三、“真”“假”之期望认同
真名体现别男女、体宗族、序行辈等宗法伦理认同,假名昭示行业认同与集体身份的选择,合之可以窥见曹雪芹的期望认同。面对美好理想与残酷现实间的巨大落差时,曹雪芹表现出对社会矛盾与家国危机深深的忧虑。于真名、假名的扑朔迷离中,人们可以得窥意义更为深广的认同。它包括时间脉络上的传统、当下与未来认同,主体层面上的个体、集体与社会认同,思想内涵上的价值、行业和期望认同等形态。它的独特之处在于认同主体在主流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以及由此发生的强烈思想震荡和巨大精神磨难,即一种痛苦与欣悦并存的心理体验。《红楼梦》是中国人命名艺术的集大成者,能体现作家独特的文化认同状态。
(一)讽名不副实
小说中的人物命名可谓“封建末世”的讽刺画卷[16],通过理想与现实、美好与丑恶的事实对照讥讽名不副实的社会现象。《论语》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而,君子应该“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17],为天下树立典范。《墨子》也认为:“诸圣人所先为,人效名实,实不必名。”[18]名副其实不仅是圣经贤传的要求,也是曹雪芹认同的前人遗教。因此,讽刺“名”“实”相悖是作者命名的意图之一。他通过对腐朽的官僚主义、被扭曲的封建礼教和炎凉的世态人情的讽刺,警策人们应回归健全的欲望,即立志追求“名副其实”。
1.官场腐坏
小说通过对一系列官员的命名,浅显直白地表达了对腐朽官僚的讽嘲。第一,作者通过“四王”之名*“四王”分别为东平王、南安王、西宁王、北静王,意指“东南西北,平安宁静”。讽刺当朝者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第二,小说借宦官之名抒发愤慨和鄙夷之意。如大明宫专管买官卖官的掌宫内监戴权,谐“贷权”;夏秉忠谐“瞎秉忠”;裘世安谐“求世安”。第三,贾姓人物之名,反映了贾府中人的道德沦陷、外强中干。如贾敬为“假静”,贾政为“假正”,贾赦为“假设”,贾琏为“假廉”“假脸”或“寡廉”,贾珍为“假真”,贾蓉为“假容”,贾蔷为“假强”。第四,贾府中清客的姓名亦极具讽刺意味。如卜世仁谐“不是人”,单聘仁谐“擅骗人”,詹光谐“沾光”,程日兴谐“趁日兴”,卜固修谐“不顾羞”……其名暗讽了这些清客相公沾光骗人、趋炎附势、奉承取悦、胡作非为的丑行。
2.礼教扭曲
贾家四春之名,可谐“细探因缘”,以诠明在礼教思想的消极影响下酿造的悲剧。元春得春光之先,故有椒房之贵,被选为贵妃。但韶光易逝,盛景难再!元春丫鬟抱琴之名谐音为“暴寝”,既预示着元春个人之命运,又暗喻家族之败落。迎春乃当春花木,其性类木,故又谓这贾府二小姐为“二木头”。迎春的侍女司棋之名谐音“死棋”,隐喻那些墨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制度的女子,一旦所遇非人(如孙绍祖),便会惨遭凌虐,此乃无解的“棋局”。探春的婢女侍书之名,谐“势输”,暗示贾府乃至封建制度势必一败涂地;又谐“事殊”,正所谓“一帆风雨路三千”,隐喻和亲制度下骨肉分离远嫁他乡的悲惨局面。惜春谓辜负春光与韶华,青灯古佛伴其一生。惜春的女婢名入画,谐音“入化”,隐喻“勘破三春”,即看破红尘投身空门。合此四春之名,则成“原应叹息”这一“名”谶*命名中的人物“名”谶,作为一种特殊的姓名文化现象,不仅预示着死生穷达与福祸寿夭,也潜含对未知世界的认知态度和对生命的关切与焦虑。它受天命论的思想、阴阳五行学说、天人感应思想、“微言大义”的笔法、因果报应(灾异)观念、名字巫术与语言禁忌等信仰的共同影响。。
3.世风炎凉
贾雨村谐“假语存”;名化,谐“假话”;胡州人,谐“胡诌”。此命名意在讽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世道人心。花袭人是贾母赠予宝玉的首席大丫鬟,旧名“珍珠”。侍宝玉后,“珠”已破而不“珍”,故改为“袭人”,点明其为人处世含攻击性的本质,也喻示她是优伶蒋玉菡的人。作者旨在讽刺那些以她为代表的,毫无反抗精神并甘做鲁迅所谓“万劫不复的奴才”的人。再如甄士隐,名费,谐“真废”,连自己女儿也保护不了,作者亦借此讽刺这类无能之人。甄士隐女儿原名甄英莲,谐“真应怜”,曾用名秋菱谐“求怜”,后改“香菱”谐“相怜”。甄士隐的岳丈姓封名肃,可谐为“风俗”,曹雪芹借此讥刺封建末世凉薄的人心世相及见风使舵等恶俗。
曹雪芹破而未立,没有通过人物的命名来塑造一个“名副其实”的使人趋之若鹜的典范,这反映了他对当时现状的批判、讽刺和对未来的茫然无助。他见惯了昏君与权臣,以及仅在名分、出身或权力地位上高贵的人,而不常见到真正的圣贤君子,故只知道批判而无法给出真正的典范人格[7]133。回溯自身亲历的那些令人失望的种种过往,曹雪芹无处寻找可资借鉴的典范。
正所谓“克己复礼为仁”。《红楼梦》对于“名副其实”的追求,其根本导向是自我的克制和社会秩序的重建,即意在教导人们要“克己复礼”。因为衡量身份的主要标准,不是出身,也不是社会形式上的职务,而是品行。而“个体的自我或私我”则是“妄想和痛苦、挫折和束缚的根源与渊薮”[7]106,是导致人品行不端的重要因素。唯有立志做君子,并始终保持君子的德行,不将意志系缚、执着于自我或私我,才能规避这些因素的影响。同时,这要求其“摒弃对于个人利益、个人名声、或者个人官能满足的追求”[7]112-113,即破除执念、价值内求。曹雪芹所追求的典范人格,不外如是。
(二)警世人破执
《红楼梦》是以甄(真)起——“甄士隐梦幻识通灵”,以贾(假)结——“贾雨村归结红楼梦”的一部“百科全书”,“真事隐”而 “假语存”。小说人物的命名也以两极对举的方式而形成真假两个系统。以甄、贾统摄全书,实质上提出了对历史真实性的质疑,即删去“真事”而存“假语”。如四大家族贾、史、王、薛可谐“假事枉雪”。
真、假所昭示的受佛、道思想浸染的“空”“无”观,是对世俗社会权势利禄的全面攻击,是对当下人情世风的无限失望,是对社会人生的清醒认识,更是对大团圆结局的认真反思。这给人们麻痹了的心灵带来的也许不仅仅是持久的刺激,还有及时的抚慰。历代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大团圆结局令人腻味疲乏,且容易与严酷的现实对比而引发幻灭感。“红楼梦”之名,体现出强烈的“宇宙意识”,即“从美的暂促性中认识到‘永恒’”——“无”,它最虚无,却又最真实,使人惊喜却又“震怖”,一切都变得渺小[19]。当然曹雪芹仍旧有对美好的追寻,但在玄妙的永恒面前,余下的多是错愕与怅惘,极少憧憬和悲伤。
这部“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记录了大量的命名思想,展示了成熟的艺术技巧,反映了时代潜涵的文化认同,揭示了如梦似幻、喜少悲多的人生常态,明示了“色即是空”——破除私我执念从而返璞归真的人生真谛。
四、结语
《红楼梦》中的姓名艺术集中体现于甄、贾,即真、假两个人名之上,其中潜涵着文化认同。姓名中蕴含有丰富的思想资源,其中由历史文化所展现出的价值认同、由职业属性所体现出的行业认同和由发展前景所呈现出的期望认同是其焦点。《红楼梦》中的“真”名不仅体现出对传统美德及花鸟珠宝等珍贵事物的认同,更表现了对别男女、体宗族、序行辈等宗法伦理的认同。《红楼梦》中的“假”名则反映了集体的身份选择。作者以笔名群体为集体自我,向其他群体借鉴,最终导向虚无的这一嬗变过程,揭示了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与能动性。小说人物命名所指向的“名”“实”之辨,要求克制自我并重建社会秩序,以实现“名”副其“实”。它以“真”与“假”、“善”与“恶”、“有”与“无”等二元对立的架构来警示世人破除私我的执念,观色悟空。
曹雪芹作为“内务府正白旗汉人(包衣)”[20],其《红楼梦》却融入了以儒之“礼”、佛之“空”、道之“无”为代表的汉族文化,剖析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反思,人们可以窥探出文化认同过程中清代汉化政策的推动轨迹,以及华夏文明的包容性与内在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