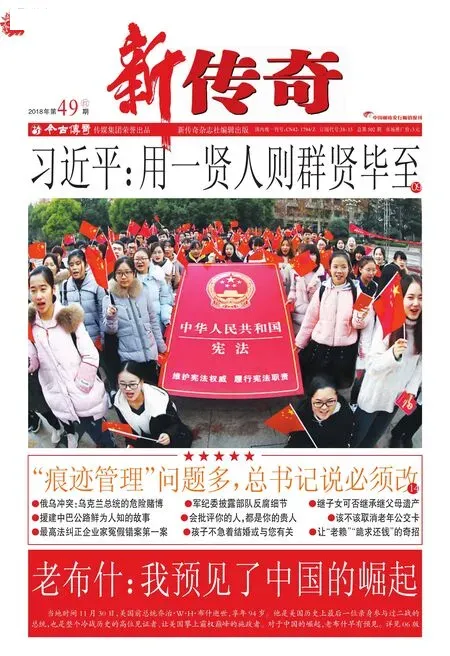被释日本战犯如何赎罪
“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作为实行者当然应由自己负责,同时要彻底追究罪行的命令者,还有制造这种局势的当权者的责任。”——1982年,在一封给友人的书信中,“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会长富永正如是说。

“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作为实行者当然应由自己负责,同时要彻底追究罪行的命令者,还有制造这种局势的当权者的责任。”“中归联”会长富永正三如是说。图为2014年7月11日,一位讲解员在介绍抚顺战犯管理所曾关押过的日本战犯
日本战犯出任“中归联”首任会长
新中国成立初期,位于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所关押了一批日本侵华战犯。中国政府对这些战犯给予人道主义的待遇,敦促他们自觉地认识自己的罪行,进行反省。辽宁作家刘家常曾长期关注抚顺战犯管理所及其关押的战犯。如今这位75岁的老者还记得,正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日本战犯藤田茂,出任了“中归联”首任会长。
1938年8月,49岁的藤田茂参加侵华战争,于1945年3月成为第43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侵华战争期间,他曾命令“俘虏尽量在战场杀害”。1945年6月在济南,超过600名俘虏被用于“教育刺杀”。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上,他承认,自己曾经常训诫部下:士兵如果不刺杀活人,“胆子是壮不起来的”。
藤田茂的继任者富永正三也有类似经历。1941年,日军见习士官富永正三在华培训最后一天的科目是“勇敢测验”,内容是“斩杀俘虏”。20多名蒙着眼睛、捆住双手的中国人,被带到长约5米、宽约3米的深坑周围。示范者拔出军刀,然后走到中国人身后,高举军刀,由上而下斜劈下去,尸体掉下深坑。第一次亲眼看到残酷的杀人情景,富永正三的呼吸都要停止了。不过,轮到自己时,他还是“横下心来,砍掉一个俘虏的头颅”。
这些经历不断被“中归联”老兵通过展览、演讲等形式揭露出来。还在抚顺管理所接受改造的时候,战犯们就有了“成立一个组织”的计划。1956年,关押在管理所的日本战犯被释放回国。次年,拥有1014名成员的“中归联”宣告成立。
致力于中日友好一直是“中归联”的目标。例如,1957年该会发起了欢迎中国访日代表团活动,1963年发起了恢复中日邦交的3000万人署名活动,1972年发起了祝贺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活动。
1959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争论激烈。“中归联”以《致岸信介公开信》的形式向日本国民发布公开信,产生巨大影响。时任日本首相岸信介是远东军事法庭认定的甲级战犯。在3000万人签名活动中,藤田茂在街头演讲中强调:“一定要把漏网的甲级战犯岸信介拉下马!”
藤田茂于1965年、1972年两次率领“中归联”代表团访华,都受到了周恩来接见。临终一刻,这名前日本陆军中将让家属把周恩来送给他的中山装穿在身上。
“中国政府教育我认识了真理,给了我新的生命”
成立“中归联”这个想法源于战犯们在中国的际遇。90岁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医务人员温久达记得,战犯们当时“身体都很好”,“我们的医疗制度很健全”。
1950年,富永正三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陷入了绝望:“我们这些战犯,哪有一个人的手上没沾过中国人的鲜血呀!”不久,重病的他被送入医院治疗。“腰椎疼得厉害,体温连续高达40℃,要靠注射安眠药才能睡觉。”富永正三突然想到,那些被自己用军刀杀死的中国人所遭受的痛苦,比这不知高多少倍。当年他用的药,是从国外进口、十分贵重的链霉素。死里逃生的他觉得,一度丧失的人性又回到了身上。
当年,上级要求一定要做好管理所的医疗工作,刘家常说:“不准跑一个,不准死一个。”
这背后是来自中国各地医务人员的努力。85岁的赵毓英清楚地记得,1950年自己根据东北卫生部转东北公安部通知,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被收押的战犯们“恐惧、精神不安定、血压特别不稳定”。普查的结果是,高血压占50%以上。
于是“一三五日本人、二四六汉奸”的医疗诊查工作制度迅速建立并严格执行。战犯病号的药,必须由医护人员亲手送到他们手中,看着他们服药完毕——60余年后,赵毓英用“革命的人道主义”概括战犯们当年受到的对待。那几年,管理所没出过医疗事故。可温久达记得,很多人对战犯们受到的待遇表示“气愤、反感、恨”,“上级让认真做工作”。
藤田茂在赵毓英印象中“学习积极”。到1956年6月日本战犯审判时,他被最高人民法院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判处18年徒刑。宣判后,审判长问他“有什么话要说”。藤田茂痛哭:“若论我的罪,判几个死刑,也不能赎罪于万一,我在中国人民的法庭面前低头认罪。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把我变成了吃人的野兽,使我的前半生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政府教育我认识了真理,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在庄严的中国人民正义法庭上宣誓,坚决把我的余生献给反战和平事业。”
回到祖国后,“中归联”成员们在日本各地宣传,“讲他们在中国受到的待遇,感谢中国,反战,要和平”。温久达说。可是他们的境况举步维艰。日本右翼势力将他们作为对手,时常阻扰。一些日本媒体认为,这些曾经在中国关押的军人们已经被洗脑。成员们被政府要求,交代他们在中国的言行。在备受歧视的境况下,很多人不得不合伙租房,靠打短工维持生计。
“想向中国人汇报一下回国后的状况”
“谢罪”则始终在进行。
1990年,“中归联”成员土屋芳雄在中国进行了自己的“谢罪之旅”,关于这次行动的纪录片《人、鬼、人》,在当年日本举办的亚洲电视节上被评为“优秀电视纪录片一等奖”。1931年参加侵华战争的主人公土屋芳雄,曾因屠杀和破坏抗日人员和组织有功,多次被日军授予勋章。
当年随团出访日本的赵毓英记得,抵日后,“中归联”成员们扶老携幼前来诉说衷肠,“回国后有很多斗争,要转业,要生活,一切安定后,想向中国人汇报一下回国后的状况”。
赵毓英等人被轮番请到“中归联”成员家里,聊天、照相。劫后余生的囚徒们说,没有中国放他们回去,就没有他们的命,没有他们的幸福生活。
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伴随他们终生。
多年后,中国媒体工作者赵冬苓曾见到一名参与当年“731”细菌战的日军士官,他“机械地坐在对面,机械地重复着谢罪的字眼”“两眼空洞,身体枯朽,像一具没有血肉和情感的尸体”。
时光流逝,随着大部分成员逐渐去世,2002年,“人数少、无力量”的“中归联”最终宣告解散。同年,“中归联”的使命,被一个叫“抚顺奇迹继承会”的组织承袭下来。当时不到30岁的熊武伸一郎,成为“继承会”的负责人。
每年都要来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熊武伸一郎觉得,日本战犯们从这里走出去,获得新生,堪称世界奇迹——“抚顺奇迹继承会”的名字由此而来。
熊武伸一郎的队伍参差不齐,其会员年龄最大的90多岁、小的18岁。很多“中归联”成员的后代成为“继承会”的成员。赵毓英记得,该会会长野津加代子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8月3日,“继承会”访中团在野津加代子率领下来到抚顺。访中团一位患脑血栓行动不便的老者,冒着雨,一点一点蹭到平顶山惨案纪念碑前,鞠躬默哀。
而今,“继承会”仍在积极搜集整理“中归联”的证言、资料、文献,举办讲座,并发行一些“中归联”的季刊。很多来到抚顺的会员,了解战争历史后,在惨案纪念碑前鞠躬默哀,“设想自己是当年的老兵,痛哭流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