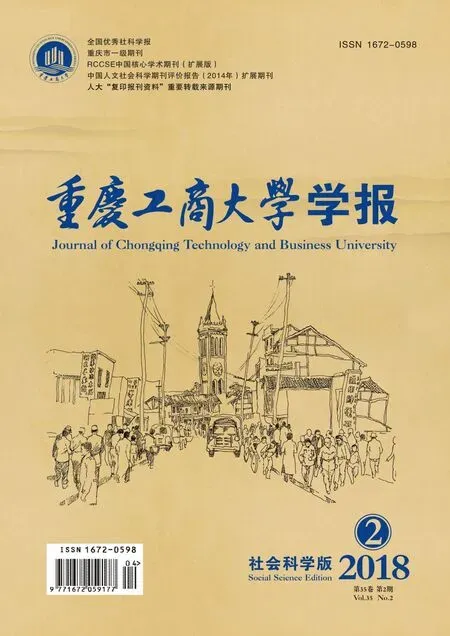“动”的精神与艾青诗歌的审美开拓
丁晓妮
(1.重庆工商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067;2.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艾青是现代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他的诗作饱含激情、生命体验和雄强的力量,给现代新诗带来了新的面貌。关于艾青诗歌的“自由的形式”[1]“完美的意境”[2]“土地、波浪、太阳等构成的意象系统”[3]“特定民族文化意识与时代精神内蕴的融合”[4]等,学界已经有充分的论述。艾青的独特性在于,他并没有像同时代的左翼作家一样,用革命理论来规约自己的创作,而是从燃烧的生命体验出发,创造出富有“动”的精神的诗歌,这一特质对中国现代新诗在审美范式上的开拓,是非常值得探讨的。
一、“动”的精神之表征
阅读艾青的诗歌,几乎一开始就会被强大的情感能量抓住,被强有力的动感推动、激动和鼓动着,心神都要兴奋和跳跃起来。如《透明的夜》《巴黎》《叫喊》《太阳》《生命》《黎明》等,无不沸腾着热力,跳跃着激情,颤动着生命。在诗歌中,动感首先表现为大量的动作描写,如《巴黎》的拟人化描写,短短十余行句中就有十四个动作,令人目不暇接,一个歇斯底里的姑娘,带着勃勃的生命力展示在读者的眼前:
你,无止息的
用手捶着自己的心肝
捶!捶!
或者伸着颈,直向高空
嘶喊!
或者垂头丧气,锁上了眼帘
沉于阴邃的思索,
也或者散乱着金丝的长发
彻声歌唱,
也或者
解散了绯红的衣裤
赤裸着一片鲜美的肉
任性的淫荡……你![5]
动感还来自同类词的堆叠,如“黎明的,黄昏的/中午的,深宵的”,似乎巴黎的日升日落正迅速闪过,简单的四个时间语词造成了时空旋转的动感。再比如大都市中运动变换的场景,用短句、声音、速度、动能……营造出非常强烈的驱动力,城市的巨大洪流带着无限的裹挟力量袭来,冲荡着所有:
看一排排的电车
往长道的顶间
逝去……
却又一排排地来了!
听,电铃
叮叮叮叮叮地飞过……
群众的洪流
从大街流来
分向各个小弄,
又从各个小弄,折回
成为洪流,
聚集在
大街上
广场上
一刻也不停的
冲荡!
冲荡![6]
此外,在原本属于静谧时空的乡村夜晚和黎明,艾青也发现了其独特的“动”的特质。黎明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开始,有着丰富的声音和动态的步伐,像奔跑的少女带来活泼新鲜的动力:
听见了鸟鸣
听见了车声的隆隆
听见了汽笛的嘶叫
我知道
你又叩开白日的门扉了……
黎明
为了你的到来
我愿站在山坡上
像欢迎
从田野那边疾奔而来的少女[7]
艾青也描写苦难大地上的人们,但不是从抽象理论出发,解读人民的革命性或落后特征,也不需要达成“对社会现象全部的(非片面的)认识”,[8]而是从具体而微的真切体验出发,去呈现一个场景,一个震撼的瞬间,从中开掘受苦受难群体的骇人之力。灾难土地上的农民,在被天灾、征粮的、讨债的逼入绝境后,在经历了“千载的痛苦”和目睹了亲人的死亡后,活着的人们爆发了,他们聚在一起,像黑色旋风,流光旋转,有着难掩的狂野力量:
那些活着的
他们聚拢了——
像黑色的旋风
从古以来没有比这更大的旋风
卷起了黑色的沙土
在流着光之溶液的天幕下
他们旋舞着愤怒
旋舞着疯狂……[9]
艾青诗中的典型意象,如太阳、火焰、风、人群等都具有强烈的“动”的特征。尤其是“太阳”这一核心意象,诗人用了大量笔墨,来描写太阳的“飞旋”“滚来”“震惊”。太阳复苏和唤醒了土地上的河流,高树,群众,冬蛰的虫蛹,一切都因为太阳的难遮掩的光芒而生机勃发,强力跃动。“火焰”是“太阳”的延伸意象,是黑夜的精灵,是欢乐的生命,火焰是跳动的、飞扬的、狂欢的:
在这些黑夜里燃烧起来
更高些!更高些!
让你的欢乐的形体
从地面升向高空
使我们这困倦的世界
因了你的火光的鼓舞
苏醒起来!喧腾起来![10]
此外,动感也来自于充沛的诗情和高能量的情绪。充满阳刚之力的激情流荡,它如此奔腾磅礴,一泻千里,不做停顿。仍以《巴黎》为例,诗中的情绪都是高能量的有冲击力的,如“愤怒,欢乐/悲痛,嬉戏和激昂”,多种情绪迅速转换,让着读者的意绪跟着动荡不已。极端情感体验的混融纠缠,“爱你吻你,或者恨你到透骨”“恨你像爱你似的坚强”“直叫人勇于生活,像勇于死亡一样的鲁莽”……,爱和恨,生和死,惊人地交织在一起,汇成震撼的冲击力量。
二、“动”的精神之形式
与内容的动感相契合的是诗歌的形式。不同于早期白话诗“给散文的思想穿上韵文的衣裳”[11],艾青主张诗的散文美,采用自由的诗体。诗的内质是第一位的,形式是第二位的,“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假如不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12]。虽然这一主张不无偏颇,但结合作品,我们不能不承认,自由诗体是最适合艾青的形式。
诗句的长短不定,较多使用短句,造成节奏的紧迫感和动感。在艾青的全部诗作中,只有《监房的夜》《ADIEU》《荒凉》等少数诗歌是整饬的,每行字数相同,这类作品的占比非常低。其他绝大部分都是自由的诗体,字数、句数、分节非常自由。有通篇都用较长句子的诗,如《大堰河——我的保姆》《献给乡村的诗》,最多的一句有22字,用以配合沉重绵长的思恋之情。更多的是使用短句,像《巴黎》这样的长诗,共197行,三字以内的有43行,5字以内的有89行,占到了全诗的一半。正如闻一多对田间的评价,“简短而坚实的句子,就是一声声的‘鼓点’”[13]。短句造成了节奏的急迫和紧凑,像迅疾的鼓点催促着阅读的速度。
省略标点,形成大量的跨行,使得诗情连贯畅达,有种不停顿感。标点作为构建诗歌节奏的重要形式,因为能够“使得语音节奏、语意节奏、视觉节奏的划分更为精细,调控生理节奏和情绪节奏时的方向感更强”[14],一度受到早期新诗作者们的重视。俞平伯的《冬夜》就特别依赖于标点来表示情绪和创造节奏。坚持新诗格律化的闻一多,强调标点的作用:“不用标点,不敢赞同。诗不能没有节奏。标点的用处,不但界划句读,并且能标明节奏(在中国文字里尤其如此),要标点的理由如此,不要它的理由我却想不出。”[15]
而艾青的诗歌,则反其道而行,大量省略标点,《马赛》一共135行,其中有标点符号的只有63行,不到一半。《生命》23行,只有5行有标点,《他起来了》《浪》《城市人》《黎明的通知》等,通篇只有一个句末破折号,而《手推车》《乞丐》《太阳》《月光》《荒凉》等,则通篇完全没有标点,这在其他新诗中是很少见的。不用标点造成的跨行,是一种非常有力的表现形式,就像奔流的江河,一往无前,不可遏制。
大量使用的排比句子,使得诗情获得一次一次地重复和加强。《铁窗里》用了12个“看见”,铺叙窗外的光明和美好,强调诗人在身陷囹圄的时刻,对自由和外面世界的渴望。再如描写太阳的诗句,就运用排比,强调和反复书写,使“太阳”更具动感的冲击力:
它以难遮掩的光芒
使生命呼吸
使高树繁枝向它舞蹈
使河流带着狂歌奔向它去[16]
没有严格的押韵。押韵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必要形式,在白话新诗的实践中,韵律也成为诗体建设的方向之一,新月派就是致力于诗歌韵律的。押韵带来一种音乐节奏感,重复出现的韵脚造成了阅读期待,形成稳定的节奏和形式上的封闭感,成为一种有必然性的约束,就如闻一多所说的“带着镣铐跳舞”。而艾青的诗歌,却几乎很少有押韵,呈现一种开放、自由的特征。“没有句式的均齐和尾韵的统一,但恰恰就是这样一种错落参差的形式,传达了诗人冲决激荡的现代情绪。”[17]
总之,艾青诗歌中的动词使用、动感画面、极致情绪与情感,和长短不一、省略标点、不严格押韵的形式,让内在情绪的节奏主宰诗行,让诗情获得充分自由,这些都构成了“动”的精神的表征。
三、“动”的审美体验
“动”的精神带来的审美体验不是沉静,不是深思,而是如同雄浑奔腾的交响乐,强劲有力地搅动着读者的身心,让读者跟随着心神震荡。艾略特认为:诗人……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对他和以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18]艾青诗歌的这种对“动”的审美开掘,也只有置于古典诗歌的大传统背景下才能凸显出其意义。
典型的中国古代诗歌,少有动态审美,更多的是静态刻画。如“皎皎空中孤月轮”“海上生明月”“大漠孤烟直”,无不通过静态的画面来营造意境,注重人与自然的交融。陶渊明和王维的田园诗,追求“无我之境”的和谐悠远,是这一审美理想的极致典型。宋元时期成熟的山水画,意境平和超脱,与古典田园诗歌的美学追求殊途同归。这种美学特征,与中国传统的庄老哲学及禅宗不无关系。李大钊认为:东方文明之根本精神在静,西方文明之根本精神在动,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用这一论点并表示赞同[19]。“静”的气质深深贯穿在艺术传统中,故诗人静观外在世界,一直到晚清,甚至是在感慨民族兴废的诗文中,也保有这种静止超然的心态,陈三立的著名诗句“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体现。
古典诗歌所达成的审美体验深厚而坚实。婉约、豪放、雄浑、典雅……《二十四诗品》所提炼出来的,都是古典诗歌中非常成熟的审美范式,每种审美范式都有大量的经典作品和知名诗人,以至于让读者产生了审美的惯性,只欣赏这样的诗歌。如郁达夫所言,“到了将来,只教中国的文字不改变,着洋装的少年,也必定要哼哼唧唧地唱些个五个字或七个字的诗句来消遣”[20]。即使在当下,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在农耕文明时代产生出来的诗歌理想和审美形式,并没有随着农耕文明的消失而结束”,“传统诗教也在继续影响我们,往往不自觉地还会欣赏古代的诗歌”,这构成了新诗“突围”的“艰难”[21]。这也是现代白话新诗自胡适的尝试开始一直饱受争议的原因之一。不仅仅是读者,哪怕是作者本人,也会感觉到白话新诗不够有诗味,不够美。这背后隐藏的是古典诗歌的阅读体验的参照系。可见,建立白话诗的新的审美范式,是比运用白话和自由诗体更大的挑战。
当然,古典诗歌传统的博大丰富,并非一个“静”字所能说完,也有瑰丽奇崛的屈骚传统,也有青春奔放的李白诗文,哪怕是陶渊明,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22]但是自宋以下,至元明清,伴随着诗歌的渐入颓势,豪迈奔放、青春洋溢的诗文是越来越少见了。
这一切到了郭沫若才有了新的面貌,他开创了新诗的动感审美。最有代表性的如《笔立山头展望》:
大都会的脉搏呀!
生的鼓动呀!
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
喷着在,飞着在,跳着在,……[23]
沸腾的都市有着沸腾的生命力,狂奔的天狗更是上天入地,强烈的能量的驱使: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24]
所以闻一多称赞郭沫若的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是个动的世纪。这种的精神映射于《女神》中最为明显。”[25]“动”作为时代精神,成为现代艺术与古典艺术区分的典型特征,也成为现代新诗冲出古典重围的突破点。
突破是如何产生的呢?艾青之所以能够自然而轻易地创造出异于古典诗歌审美体验的新诗,得益于他对古典诗歌传统接触不多。但是,当他把自身的悲欢深深地融入北方那悲哀的土地的时候,从“土地”意象的深沉的历史感和忧患中,又能够感觉到艾青的“传统”特质。从整体气质上看,艾青的诗歌与古典豪放派诗歌,也有着似曾相识感。阳刚、雄浑、豪迈、阔大等,所有适用于豪放派的评价,也似乎都适合于艾青的诗。这也是艾青的动感审美相比郭沫若,更容易被接受的原因。郭沫若作为天才诗人,他的诗裹挟着性格的亢奋,像发高烧一般的热力,就如天狗,不知何来,不知何终。也正因为此,郭沫若最有代表性的诗《天狗》《站在地球边上放号》《笔立山头展望》等始终伴随着批评和质疑。而艾青诗中的动感,和郭沫若有明显区别。由于深深地和土地、生命相结合,则更像北方时而缓时而急的大河,在涌动的波涛节奏底下,藏着大地的深沉的律动。“太阳”这一被艾青赋予全新特质的意象,也始终腾跃飞旋在“土地”“旷野”等厚重的意象之上。因此,这种审美体验,既是新的、异质的,又是亲切的、可接受的。
但是,在与豪放派诗歌的表面类似背后,实质性的差异是更应该被重视和探讨的。差异又在哪里呢?主要在于抒情主体和世界的关系。边塞诗是历史上豪放派诗歌的主要存在形式,“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或者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背后隐藏的是效忠君王、建功立业的“士”的精神。在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奔腾的气势,激越的声调,开阔的历史感,最终还是无奈低回,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收梢。而在艾青的最富动感的诗歌中,则雄强地树立起来一个独立的“大我”,这是真正的现代意识,是新的超拔的知识分子主体。抒情主体与世界的关系,是并立的,他燃烧自己,并因此而发现世界。
所以,“动”的审美体验带给读者的,不再是天人合一的和谐完满,物我两忘的顿悟澄明,欣然会心地拈花微笑,不寻求“忘我”和“无我”。甚至有的诗歌,其阅读感受是骚乱的、诧异的、绝望的、惊恐的、可怖的。这是现代社会的现代体验。当读到“忧郁的流散的弃妇之披发般的黑色的煤烟”,“飓风所煽起的砂石,向我这不安的心头/不可抗地飞来”[26],“手推车/以唯一的轮子/发出使阴暗的天穹痉挛的尖音”[27],那种复杂的体验,使得诗歌绝对不可能成为“赏玩”“吟味”“把弄”的对象。而是如鲁迅所言,“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氐鸟的真的恶声”[28],让读者带着被深深搅动起来的激动、焦灼、渴望和强力,想起“我”,发现“我”,将“我”投身其中,与诗人一起震颤冲荡。
四、“动”的精神内核
动感的审美,其激发的根源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民国时期社会格局的巨大变动。上文引的李大钊和梁漱溟对中国文明的“静”的判断。“静”的根底,在于中国社会的稳定,数千年保持着农耕社会、家族结构和帝王政体,“以一贯的民族传统和国家传统绵延着”[29],绝少发生变化。即使是王朝更迭,也不过是一种循环相因,如“久分必合,久合必分”就揭示了中国历史的封闭循环的结构特征。这种恒常性和稳定性构成了文学艺术的静态审美的基础。而晚清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中国不再是位居世界中心的“中”国,而是被外来侵略者瓜分蚕食的半殖民地。与政治结构崩塌同步的是,中国小农经济受到全面冲击,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商品涌入中国,深刻改变着从上层阶级到底层民众的每个人的生活,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观念。剧烈变动的社会,奇特地呈现为“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四面八方都是二三重以致多重的事物”,“一切人都在这矛盾中间”[30]。恒常被打破,变动成为常态,静态审美的社会根基被根本性地动摇了。西学东渐,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异域的新的思想和观念,更促成了思想观念的大变革。而某种程度上,五四的时代精神,就是狂飙突进,就是“动”的精神。
其次是异域和都市生活的体验。中国古典诗歌的本质是基于农耕文明的。“陆地物象是相对静止的,它的任何动态都是在静态的背景上产生的,都是以静态物象为存在的基础、为基本参照物而呈现出来的状态。沉静的理性将一切打出了明确的节拍”,而海洋的博大、起伏、动荡、变化莫测则促成郭沫若“新的审美境界”的开启。[31]现代都市为诗人们开启了全新的生活空间和无穷的可能性。艾青,“一个热情而忧郁的少年,离开了他的小小的村庄”[32],来到异国他乡,投身到一个陌生的文明世界,这个世界更繁华、更快速、更拥挤、更物质,充斥着大商场、码头、堆货栈、厂房、烟囱,穿梭着公共汽车、电车、马车,拥挤着野心家、白痴、淫棍、酒徒,也灿烂着凯旋门、博物馆、歌剧院。都市生活的一大特征就是“快”,是速度。现代都市文明大大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速度和空间同时获得扩展,带来无与伦比的生命体验,并激发出澎湃的诗情。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生命本体和生命自在价值的发现和尊重。中国传统观念对生命价值的度量,是在一个庞大的价值体系之中呈现的,所以才有“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的说法。看重的是群体和人伦关系,对具体的个体的生命存在从来都缺乏尊重,“家族意识阻碍了个人主义的发现”[33]。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重新发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生命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不需要依赖任何其他的事物,不需要在服从、奉献、遵循、牺牲中求取价值。“生命”是艾青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生与死,是诗人反复言说的主题,他一次又一次地赞颂和讴歌生命,甚至以《生命》为题,写下了“赤裸的臂”,“赭黄的健康”,血管就像“青色的河流”,这是生命,可以欢腾、颓然、鼓舞和烦恼:
青色的河流鼓动在土地里
蓝色的静脉鼓动在我的臂膀里
五个手指
是五支新鲜的红色
里面旋流着
土地耕植者的血液[34]
而生命的本质是动,血液的搏动,呼吸的开合,肌肉的张弛,有着自然的律动和美感。充满“动”的精神的诗歌,也更符合生命的运动本质。
生命的内在发现,与生存环境变动带来的全新体验,与剧烈震荡的国家民族局势,是同步完成的。“自我主体的确立才赋予了他们一双‘发现’风景的眼睛,并造成了物我关系的根本改变。”[35]这种关系根本上有别于古时“占有者与自然之间的闲散、休息、消极静观的关系”[36],它也不是一种必然的征服关系。艾青的诗歌,大都是描写一个对象,生命、旷野、太阳、火把、手推车、桥……对每一个自己所书写的热爱的对象,用燃烧的热情去逼近这个对象,去透视这个对象。对其本质的逼近和发现,敞亮地获得、对话、对视、坦陈,抛开既定的约束、概念、定义、制度、规则,抛开功利的价值的体系,从“存在”的意义上去逼近和发现它。
当然,并不是社会局势和生存环境的变动就必然能够造成自我主体的发现和更新,每个个体有着自身生存的特殊的微环境,有着先天的气质、禀赋差异,也有着自我的主动选择和取舍。从学衡派的吴宓,包括新诗人胡适、郭沫若、闻一多等现代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变动深刻的差异和复杂性。
五、结语
中国现代新诗自诞生以来,一直伴随着质疑和批判。直至20世纪末,诗人郑敏还在审视提问,为什么新诗没有产生出世界知名的大诗人,并将根源归咎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完全弃绝和因之造成的“语言的断裂”[37]。而回到新诗文本,我们可以看到新诗在短短数十年的实践期内所达到的成就,也看到新诗发展历程所受到政治话语的强大规约;更看到由于传统审美体验的坚实深厚造成的审美惯性,对读者接受新诗所产生的障碍;普通读者的阅读评判又进而影响到诗论家甚至诗人自身对新诗的评价,这样一种复杂胶着的关系。廓清这一历程,以开放的心态和历史的眼光来面对新诗文本,并真正从诗歌阅读体验中升腾起新诗研究和诗学建设的突围,在当下是有必要和有价值的。
[1] 杨匡汉,杨匡满.艾青诗歌艺术风格散论[J].文学评论,2015(04).
[2] 陆耀东.论艾青诗的审美特征[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04).
[3] 骆寒超.论艾青诗的意象世界及其结构系统[J].文艺研究,1992(01).
[4] 王泽龙.走向融合与开放:艾青诗歌意象艺术的探索[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01).
[5][6] 艾青.巴黎[M]//艾青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9-26.
[7] 艾青.黎明[M]//艾青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77-80.
[8] 茅盾.《地泉》读后感[M]//茅盾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331.
[9] 艾青.死地[M]//艾青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84.
[10] 艾青.野火[M]//艾青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259.
[11] 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J].创造月刊,1926(01).
[12] 艾青.诗论[M]//艾青全集:第3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1:23.
[13] 闻一多.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J].生活导报,1943(11):28.
[14] 王雪松.论标点符号与中国现代诗歌节奏的关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03).
[15] 闻一多.论《悔与回》[J].新月,1931:5-6.
[16] 艾青.太阳[M]//艾青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65.
[17] 李怡.百年艾青与中国新诗的精神传统[N].文艺报,2010-4-2(02).
[18]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M]//杨匡汉,刘福春.西方现代诗论.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74.
[19] 李大钊.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M]//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16.
[20] 郁达夫.谈诗[M]//郁达夫文集:第6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224.
[21] 李怡.“传统”与中国新诗的艰难性[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1).
[22] 鲁迅.“题未定”草(六至九)[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36.
[23] 郭沫若.笔立山头展望[M]//郭沫若诗选.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58.
[24] 郭沫若.天狗[M]//郭沫若诗选.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45.
[25]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N].创造周报,1923-6-3(4).
[26] 艾青.马赛[M]//艾青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29.
[27] 艾青.手推车[M]//艾青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94.
[28] 鲁迅.音乐[M]//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6.
[29]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上海:三联书店,1988:11.
[30] 鲁迅.随感录五十四[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60-361.
[31] 王富仁.他开辟了一个新的审美境界——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C].“郭沫若在日本”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8(05).
[32] 艾青.少年行[M]//艾青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53.
[33]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广州: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16.
[34] 艾青.生命[M]//艾青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71.
[35] 李怡.骚动的“松”与“梅”———留日郭沫若的自然视野[J].兰州学刊,2015(08).
[36] 李泽厚.美的历程[M].上海:三联书店,2009:172.
[37]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J].文学评论,199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