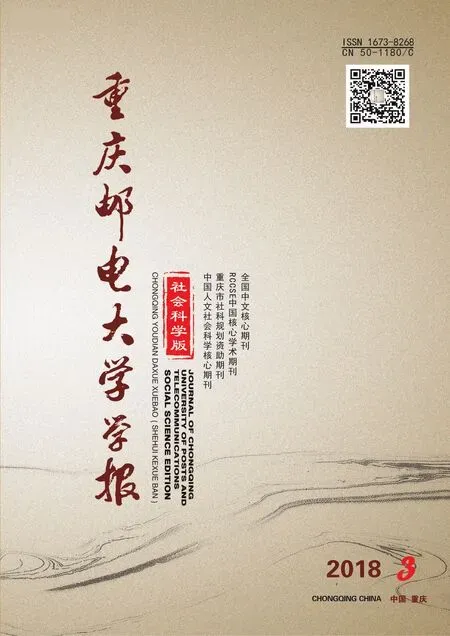肖江虹小说的民俗叙事*
杨 波
(贵州师范学院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来自贵州的青年作家肖江虹,因为执着于“底层叙事”“乡土叙事”“乡土焦虑”[1-2]等创作路向活跃于文学界并屡获学界好评,被认为是一位“以数量不多却令人悄然动人的小说叩人心扉并为读者所关注的作家”[3]。“出手不凡,颇见功力,有着超越一般青年作家的厚重。”[2]近些年,肖江虹携带《百鸟朝凤》《家谱》《悬棺》《蛊镇》《傩面》等作品先后荣登《人民文学》《当代》《天涯》等国内重要文学刊物,部分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选载,《蛊镇》还获得了2013年度人民文学奖。发表于《人民文学》2016年第9期的《傩面》在卷首语中更是被称赞为“活气弥润”,“人物语调、情景语感和叙述语韵臻于完美融合的小说范本”。综观肖江虹的小说创作,民俗是其一直以来最为偏爱的书写主题,著名评论家、原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陵在肖江虹小说集《百鸟朝凤》的序言中指出:肖江虹“对自己家乡的民俗民风情有独钟,写起来得心应手,并知道怎样把这些文化融入到人物的精神气质里”[4]序3-4。民俗文化已然成为肖江虹小说世界的核心元素,原本粗糙、拙朴的民间习俗焕发出了诗意的光辉,为传统与现代、守望与陷落、乡村与城市的文学命题赋予了新的意义。在目前国内的小说创作中,如此醉心于民俗书写的小说家实不多见,加之别样的观照视角以及具有超越意识的价值再造,让其在当下的民俗书写中确立了属于自己的写作姿态与艺术个性,彰显出一名作家独特的抒写色彩与文学纹理。
一、别样的书写模式:工匠精神与叙事再造
在一次访谈中,肖江虹曾提道:“在这个速度决定一切的时代里边,需要慢下来的一种工匠精神。”[5]20的确,肖江虹现在的写作并不疾速,初出茅庐时他曾有过在文学期刊看不到自己名字就十分恐慌的量的追求,后来这样的写作方式逐渐改变,《傩面》的创作就写了两年多,为了将傩戏这一民俗写得更加逼近真实,他到过贵州多地亲身体验。在写作《天堂口》时,肖江虹还亲自到火葬场去观看亡人火葬的场景。作为一名以笔为刀的文学“匠人”,肖江虹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刨根问底、近乎苛刻的写作态度,完成了一系列民俗小说的创作,如同乡间匠人的娴熟手艺,手起刀落之间淋漓的满是生活的碎屑,留下的是一尊尊民俗的精致雕像。
和众多作家一样,肖江虹的文学世界也主要依赖边地乡土进行构建,他自己曾言:“我小说的场景和人物,几乎都和那片土地有关,只要一想到他们,我就特别来劲。”[6]322一直以来,肖江虹家乡贵州因为交通、地理等原因,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汉孰与我大?”“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一州主,不知汉广大”[7]的历史描述,到后来鲁迅谈到贵州著名作家蹇先艾时的“老远的贵州”“贵州很远”[8]的文学评价,远离中心的地理与文化就成为外界对于贵州的前置印象和预设标识。据此,出于封闭保守和审美猎奇的双重效应,关于此域的文学书写也就更容易博得阅读和阐释的兴趣。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贵州早期的蹇先艾、寿申,亦或新时期的何士光、李宽定、石定,还是近年活跃于文坛的肖江虹、冉正万、王华、肖勤等,其文学世界的建构均不仅仅是关于贵州的古旧、僻远或者落后的文学自虐,他们对于一方乡土的内质把握,更是其创作价值的要义所在。美国著名学者凯文·林奇在其名著《城市意象》中指出:“一处独特、可读的环境不但能带来安全感,而且也扩展了人类经验的潜在深度和强度。”[9]于肖江虹而言,童年时期完全属于放养状态,“没日没夜的遍地乱跑”,“和那片土地建立了朴素而深厚的感情”[6]322。这种扎根乡野的童年视界作为一种内在规定性,反转形成作家故土依恋与精神回乡的艺术抉择,让作家在创作中不断进行审美咀嚼和精神吸取,并外化为无双镇、蛊镇、傩村、燕子峡等凝聚了僻远、神秘、古旧元素的文学地理空间。《百鸟朝凤》《当大事》《家谱》等的故事地点均被设置在无双镇,这是一个拥有金、木、水、火、土五个村庄的大镇,无双镇上的人们纷纷向城市集聚,城市不断对农村进行物质与文化的双重抽取,所以“按理这个镇子应该叫五行镇,可它却叫无双镇”[4]3。负载有传统价值的“五行道义”与“现实无双”的矛盾纠葛显露无疑。蛊镇“四面环山,进进出出就靠一个豁口”[6]12,蛊镇往西的二十里的古驿道上是“傩村”,但驿道早已被废弃,“驿道穿过半山,山高风急,路就被撩成一条折叠的飘带。弯弯绕绕无数回,折过一堆零碎乱石,就能看见傩村了”[10]。《悬棺》的故事生发地“燕子峡”也属于蛊镇,因为“山高谷深,陆路运送极其不便”,所以村人在蛊镇打制的棺材均靠猫跳河顺水而来[11]87。不难看出,“无双镇”“蛊镇”“傩村”“燕子峡”等均涵盖了高远的地理形势以及边缘话语的价值能指。同时,小说把叙事地域划定为“无双”“蛊”“傩”等,不仅昭示了文本的叙事主体,而且携带了与民俗紧密相关的隐喻意义。因此,肖江虹是在边地世界中把涉及民间艺术、民居、宗族组织、岁时节日、民俗信仰等多个门类的唢呐、悬棺、丧葬、傩戏、七月半、家谱、喊魂等民俗事象与生民的生活、生命、精神融合互渗,将乡土、城市、历史、现实诸因素汇聚而入,形塑起繁复多彩的文学时空体,依此开启自己独特的文学创造之途。
肖江虹小说的民俗叙事主要采取两种模式。一是将民俗作为叙事主体,民俗的仪式规程浸润于小说的全部篇幅,将民俗作为叙述的主体话语,一个文本驻足一种民俗,这是肖江虹与其他民俗叙事所不同的言说方式之一。这样的叙事组织不仅收获了“奇观效应”引发的审美餍足,还让小说更加逼近生活本相,因为在乡村世界尤其在较为僻远的山村,民俗本身即是乡民生活的重要组成,并逐渐演化为居于底层的一种族群心理,从民俗可以洞见整个底层世界。同时,这样的文学处理方式也可以有效回避身居城市对乡土的“遥望”姿态,实现“身即山川而取之”的美学效果。如《悬棺》开篇即呈现来辛苦和儿子爬下刀劈崖,迎接从蛊镇顺流而下的“老家”(即棺材),在族人的帮助下将“老家”放入悬棺崖,后来的故事讲述无不有悬棺、攀岩这两项贵州民俗的参与。尽管小说将旅游、移民搬迁等现实性因素纳入进来,但又都处在悬棺、攀岩等民俗的叙事场景中,民俗对于小说文本的支撑性作用无法挪移。《蛊镇》则是关于我国古老的民间方术“蛊”的文学描述,早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已经有了关于“蛊”的记载,如“‘有疾齿,唯蛊虐。’‘(有)疾,不(唯)蛊’之类的卜辞”[12]。而制蛊、放蛊的民俗一直弥漫于《蛊镇》的故事现场。同样,《百鸟朝凤》中游天鸣苦学唢呐、受传名曲、唢呐艺术衰败等成为文本的主体线索,唢呐这一民俗作为故事推演的主要凭借贯穿小说始终。《傩面》中的傩师秦安顺作为叙事的主要承担者,制作傩面、唱傩戏等具有地域风味的事象被作家进行细笔勾勒,和青年女孩颜素容回乡的种种表现互为表里,展现傩戏对乡民的行为砥砺和精神支持。《家谱》则着笔于民俗节日——七月半到来之际,我为家族中逝去的老人写包,为了追寻家谱中“许东生”的空白原因而多方查寻均无结果,最后竟然在别人的家谱中发现爷爷许东生实为村中祸患。纵观整个小说文本,家谱中人物的记载方式潜伏于叙事主线之下,但是民俗仍为叙事的主要话语。
肖江虹民俗书写的另一模式是在具体的社会事件中植入民俗事象,民俗成为叙事推进不可或缺的参与性力量。在这类小说中,虽有社会性事件来支撑叙事的主要场域,但民俗的踪影仍是无法消弭,作家总是在故事阐述的关键节点让民俗出场,力图通过民俗的道德、死生观念等来对历史、时代、社会进行意义评估和价值协调,以化解民间规约与现实社会之间相互抵牾的尴尬状态。这方面的小说主要有《一撇一捺》《喊魂》《当大事》等。《一撇一捺》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中篇,小人物谭麻子拒绝将顽劣作恶的父亲塑造为英雄,自己却因救落水小孩成为了真正的英雄。小说将丧葬民俗与谭麻子的命运进行合构,丧葬习俗的道德规训与扭曲的现实人性相互挤压,达致一种强烈的反思效果。《喊魂》虽将“喊魂”这一民俗作为文本标题,但是小说的叙述主线却是农村青年蚂蚁在城市拆迁中被打成植物人,回乡后蚂蚁家人为其喊魂最终未果的悲凉故事,喊魂民俗作为外延性补充,为思考城乡冲突、揭示农村青年命运提供道德参照系。
二、精神衰败与文化焦虑:乡间民俗的异化与陷落
著名学者钱穆亦曾有言:“全世界各民族,各体系的文化,都逃不掉‘冲突’与‘调和’之两面。”[13]作为民族与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民俗自当陷落于“冲突”与“调和”之中,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演进道路上左突右进,成为作家文学阐释与艺术思考的重要资源。1924年,周作人在刘大白诗集《旧梦》的序言中指出:“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14]。若想在中国建设国民文学,表现大多数民众的性情生活,本国的民俗研究也是必要,这虽是人类学范围内的学问,却于文学有极重要的关系[15]。在此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中,鲁迅、彭家煌、台静农、蹇先艾、沈从文、废名等人将自己家乡的民风民俗不断纳入书写场域,经过对乡村世界模式化的文化生活与生活文化的文学沉淀,逐渐抽绎出落后、麻木、恣睢或者眷恋、田园、诗意的话语表述,并延展为批判与讴歌的审美路向,成为五四时期精神启蒙、纾解人性的叙事装置。在此后的中国文学发展中,民俗叙事的传统一直得以赓续,并以解放文学、寻根文学等不同面相呈现不一样的历史逻辑和文学精神,在乡土中国的文学建构中占据要津。与上述前辈相比,肖江虹面对的时代语境已历经变化,作为一名“匠心独运”的文学“匠人”,肖江虹的民俗书写的独特性不仅在于他开启了别具意义的书写模式,拭去了蒙在民俗表面的拂尘,而且在于他以一种沉潜沉稳的写作姿态,对于民俗的内在纹理、肌质的独特把握,更在于他对乡间民俗异化、陷落的敏锐洞察,并据其推向文化焦虑、精神守望的纵深维度的思考力。这正如青年作家张楚所言:“他一直以一双旁观者的清澈眼神注视着消失中的风物,缅怀那些被时光抛弃的秘密和人心,同时将这些独特的叙事资源赋予一种美学意义上的审视、哲学意义上的反思。”[16]
著名学者朱光潜在讨论歌谣的异地传承时指出:“个人意识愈发达,社会愈分化,民众艺术也就愈趋衰落。”[17]这亦即是说,民俗所承载的地域风情、文化哲学的价值属性并非铁板一块,现代文明与乡土传统、技术统辖与自然秩序之间依然横亘着巨大的价值鸿沟,因为在中国现代文明的征途上,“个人意识与社会的分化”与现代性启蒙相伴相随,与之相应的是,民歌、民间艺术、民俗等话语体系一再被赋予落后、边缘等文化描述,也一再遭到批判、消解甚至抹除。在肖江虹的文学叙事中,民俗也是围困连连,从民俗的仪式本身到内在的情感、价值承载均遭到不同程度的异化。《百鸟朝凤》中唢呐的吹奏本是一项极为庄重的仪式,但是游天鸣的发小毛长生把接师礼、吹奏遍数都一一予以轻鄙和敷衍,唢呐的吹奏成为了名符其实的没有任何内在承担的“仪式”。而游天鸣一直苦苦坚守的唢呐艺术,却因城市巨大的吸附力,最终还是免不了“游家班”解散的命运。《傩面》中村长儿子梁兴富将傩面变为生财之道,并对秦安顺的傩戏嗤之以鼻。《悬棺》中燕子峡的攀岩技艺因为旅游而成为赚钱的营生。
在肖江虹的民俗叙事中,他总是将民俗与死亡融通互渗,形成叙事勾连。《当大事》中就将孟子的“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唯送死可以当大事”置于小说开篇,悬棺、蛊镇、傩面等均与死亡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联……其民俗与死亡的叙事勾连可谓不胜枚举。但是,他的小说文本中,死亡的庄重性遭到瓦解的现实一再发生,《当大事》中松柏爹的死显得极其零落,棺材、举灵幡、坟地选择、道士班子等在民俗中被认为是极为严肃的仪式均遭到拆解,死亡民俗的庄重性不复存在。《一撇一捺》中,谭麻子的父亲死后被村长出于虚假的荣誉奉为英雄,民俗的固有价被扭曲变形,原有的道德规训作用顿然失去。
总之,肖江虹小说的情节布置和叙事推进中,民俗无一不在城市以及现代性的文化演进中屡屡迷失、节节败退,现代性的技术伦理不断向乡村蔓延,民俗完全沦陷为空洞的躯壳,其天然携带的情感调适和心灵塑造的内在本质遭到悬置。因此,盛极一时的民俗文化,有的被人们遗弃,如唢呐的吹奏;有的被置于完全物化的地步,如傩村的傩面具;有的则在城镇化工业化大潮中走向消亡,如悬棺在水位的不断上升中缓缓飘走,传统乡土的精神版图正在被割据和复写。更进一步言,除了人们抛弃了民俗的既有形式之外,民俗具有的内在凝聚力量被消解,乡村社会民俗传统所负载的德性价值在现代文明的撞击下显得焦虑而迷惘。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残存的模糊地带慢慢遭到消解,两种文明相互驱离的悲壮现实与文化坚守的价值立场叠加互动,让小说文本形成了悲怆性、反思性的召唤本质,也凸显出作家心灵深处的焦虑与复杂的文化心理。
三、回到出发的地方:民俗叙事的重构与突围
陷落与困境固然充满焦虑与失望,但是守望与突围亦是欣慰而可喜的。为何总是葆有对民俗的审美趣味,这实则可以映照出肖江虹关于民俗叙事的审美超越与精神反思。要达致这样的书写境界,肖江虹的回答是——回到出发的地方,通过对民俗的本来状貌的“复原”“复魅”,烛照出其根部的文化智慧与精神审思,从而开启民俗文化的救赎之途。
要回到出发的地方,首先就要回归生活的细流,抚摸民俗文化的细部纹理。在民俗叙事的文本展示中,肖江虹亦从来不吝笔墨对具有浓郁地域韵味的民俗进行工匠般的细笔书写,这与前述将民俗作为叙事主体架构的形式相互融合,又形成了肖江虹民俗书写与乡土世界之间的平行视角,作家满怀情感沉潜于乡土之中,省去了凌空虚蹈的道德审判。《傩面》中秦安顺为颜素容唱解结傩和延寿傩,两场傩戏中的唱词、傩面具的使用以及人物在傩戏中的种种表现都得到了细微的呈现。又如《喊魂》,小说用了整整一节来叙写喊魂这一民俗,喊魂坑的选择、喊魂前的准备以及喊魂过程中种种繁复的仪式等均被作家全然呈现。其他如《悬棺》《百鸟朝凤》《当大事》等作品中,肖江虹也都将悬棺、唢呐、丧葬等民俗进行浓墨涂抹和直观呈现。如此精细雕琢的叙事处理,一方面让传统民俗的实施过程得到了艺术化释放,因为民俗仪式本身即具有魔幻、超验性质,与乡民的物性生活存在距离,作家将民俗的仪式化表演从生活常态中“剥离”开来,升华为乡民的精神生活空间。另一方面经过精神提升的仪式过后又回落到现实领域,凸显出民俗在乡村社会中的规范效应与调和价值。这正如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所言:“从外表来看,仪式的繁文缛节可能显得毫无意思,其实它们可用一种对人们或许可称作‘微调’的东西的关切加以解释:不使任何一个生灵、物品或特征遗漏掉,要使它们在某个类别系统中都占有各自的位置。”[18]历时和共时形态下的民俗传统,最终和乡村世界的道德法则相互作用,缔结为底层社会共有的秩序规约和文化心理,左右着乡民的行为边界和价值追求。《百鸟朝凤》中唢呐匠在无双镇的传统中极具声望,唢呐艺术传承人不仅具有崇高的品德,还必须是“一个把唢呐吹进了骨头缝的人”[4]28。作为唢呐名曲的《百鸟朝凤》只在白事上用,受用的人要有极好的口碑,否则不配享用。家谱的撰写成为《家谱》中一个人言行的最好征候,又逐渐聚合成申善弃恶的民间力量。《蛊镇》中王四维因为在外面背弃妻子与人相好,虽死于城市工地却被认为是王昌林为其制的情蛊所致,民间方术的魔幻力量某种意义上发挥了道德纠偏的作用,而赵锦绣与王木匠之间若隐若现的情意亦又最终发乎情而止于礼义。因此,肖江虹如此醉心于各类民俗的“细节复原”,实则是在唤起一种回到乡村伦理源点的文化启示。
除了在小说文本中展开民俗的文学返魅之外,肖江虹还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以坚挺的身姿坚守民俗文化的乡间人物,游天鸣、秦安顺、王昌林、来辛苦等人依然饱含敬畏,在困境中执着于民俗的精神持存,肖江虹将这种精神赋予了曾经畅行于乡土的民间艺人,他在每一种民俗背后必定安排了一类艺人的存在,唢呐匠、蛊师、傩师、攀岩者、木匠等乡间艺人无不具有匠的特质,意志坚韧、甘于寂寞、坚守民俗等品质始终盘旋于他们内心。游天鸣虽然天赋不高,却被焦师傅认为是“一个把唢呐吹进骨头缝的人”;蛊师王昌林、傩师秦安顺、攀岩者来辛苦等人也都能够把遭到弃绝或被戏为表演的民俗技艺看作胜过生命的“手艺”。他们的默不作声、默默坚守均源于深入骨髓的精神守望,因为“手艺人需要的是匠心而非匠气”[5]21。肖江虹也曾谈到自己的二叔——一个农村木匠,在村人流行去城里购买漂亮的组合家具的时候,依然“我行我素”牢牢把握最扎实的材料和做工,结果大家发现组合家具不耐用又都返回照顾二叔的生意,可他仍是“不紧不慢,按照自己的节奏种庄稼,农闲时才给大家做家具”[5]20。可以说,肖江虹的文心、二叔的匠心以及游天鸣、秦安顺、王昌林、来辛苦等人对民俗的捍卫具有精神上的同构关系,正如肖江虹所说的“匠心主要是一种精神,而非形式”[5]20。同时这也映照出乡村文明的深层定力。
纵观当下的民俗叙事,部分文本总是沉溺于种种“奇观”“展览”的书写意向,少了形而上的价值追寻,这亦是让此般书写难以实现内蕴升腾的原因之一,因为民俗叙事,“不应该流连于琐屑经验的镜像呈示,应以建立深阔的话语时空,和清洁的超越精神为参照”[19]。这也告诉我们,要回到出发的地方,还需要在日常的叙事之上达致现实生活的穿透性和精神时空的超越性。据此,肖江虹关于民俗异化、陷落的理性反思,决不能仅仅是叙事的表面滑行。
其实,在面对民俗文化遭遇现代性挤压的困境下,是逃避还是救赎?近些年不少作家都不断进行回应。贾平凹“商州系列”中关于换亲、冥婚、守孝、生子、乡会等民俗的艺术描绘,莫言“高密东北乡”建构中的戏曲、剪纸、婚配等民俗元素的参与,以及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图绘的鄂温克族的文化习俗,阿来《蘑菇圈》《三只虫草》中关于虫草社会的叙事展布,均对地方民俗的现代性境遇进行文学审视,以寻求乡土社会历经焦虑之后的救赎之道。不过,肖江虹与之不同的是,他在小说文本中给予读者更为深层的文化启示,那就是在遭遇到现代文明的剜心之痛后,青年一代踏上了民俗的回归之途,就像美国民俗学者理查德·多耳逊所言:“民俗使人脱开他所处的狭隘界限的另一种方式在于冲破有力的社会戒律。”[20]肖江虹正是通过对王昌林、秦安顺、游天鸣、颜素容等人的命运观照,揭橥民俗作为一种边缘文化在社会断裂地带的支撑作用,以及在历史普遍逻辑之外的价值能指。《蛊镇》中,因为王四维和儿子相继去世,蛊镇开始翻新蛊神祠,蛊蹈节那天,王昌林恍惚地看见“密麻的青年男女,顺着古旧的石板路,逶迤而来”[6]72。《傩面》中的颜素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戴上伏羲傩面安然离去,《人民文学》编者在卷首语中给予《傩面》如此评价:“‘常’之固守和‘变’之瓦解已经不能概括作品诸层面。”这亦即是说,肖江虹在民俗的固守之“常”和时代瓦解之“变”惯常逻辑之外,辟出了另一条蕴含了行为复归、精神回乡的救赎之路。因此,来高粱、颜素容、游天鸣等人对于乡土的归途,并不等同于所谓的“趾高气昂的Q爷”“灵魂的统治者”“精神的富足者”[21]的叙事设置。作家在民俗的传统价值和现代境遇之间,试图架设沟通与互溯之道。在面对纷繁的世界时,坚信民俗的传统力量仍然可以作为回到自我、返回原点的路标。在面对生命的困厄时,民俗仍是心灵的庇护所,这是民俗中固有的护卫人类内在心性的价值回溯。所以,将民俗所具有的文化之常和文化之根衹,用作人心唤回的呼告和灵魂救赎的凭借,这样的审美诉求使得肖江虹的民俗书写与民俗启蒙叙事,与民俗融汇国家话语的书写经验判然有别,实现了民俗叙事的重构,开启了民俗文化的精神突围之路。
肖江虹实现民俗文化突围与重构的另一路径是民俗与死亡的价值互渗,他仍是发挥作为文学“匠人”严谨、细腻的“刀客”功夫,游刃有余地出入于种种繁琐的丧葬程序中,为读者绘制了多种多样的死亡现场,同时将英雄死亡、革命死亡等传统表述悬置起来,通过死亡的仪式描述、在场或预演,加速死亡与自然、自由以及天地世界的融入,彰显一种本体性、尊重生命、抵达灵魂的死亡架构,将民俗的诗意光辉引向了生命的最初领地。另外,肖江虹在死亡民俗展演中还特别注意生与死的“跨界”言说,《傩面》中秦安顺不仅在傩戏中看见了父母相亲、结婚以及怀孕生子的过程,在为德平老祖“引路”、唱离别傩的时候也是幻游一般经历了人间与神界的穿越。《蛊镇》中蛊蹈节的热闹景象以及年轻男女返回蛊镇的场景被叙述成蛊师王昌林的眼中幻境。《悬棺》中来畏难几次登上祖祠崖,均在洞内看见具有魔幻性质的人物活动场面,而这种场景又是基于燕子峡人去世后亡灵的种种表现。无论是秦安顺,还是王昌林、来畏难,他们都经历了死亡的幻境,但又都“回到了生活的原地”,这种生死的魔幻经历强化了作家对于生命终极意义的拷问。值得一提的是《悬棺》中的来高粱,因为攀岩摔成残疾而无法进入悬棺,为了完成这一夙愿做出多样举动始终未果,在燕子峡人将要到异乡生存的时候,来高粱并没有同行,而是“背着翅膀的剪影从朝阳里踯躅着走了出来。在山顶立了片刻,那片剪影双臂展开,鹰燕般从高处飞了下去”[11]116。来高粱最后奔向的还是自己的悬棺,以极为悲壮的形式诠释了生与死的意义所在,具有强烈的殉道性质,而他所希望到达和奔向的悬棺,实则是精神和灵魂的归宿。可以说,来高粱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回到了生命出发的地方,也藉此完成了对民俗文化的捍卫。
四、结 语
苏联语言文学博士A·博恰洛夫说过:“艺术中的新东西并不永远都是生活里的新东西,但永远都是对生活的新认识。”[22]民俗叙事的历程可谓历经长久又波澜壮阔,肖江虹文学世界并非是在发掘一个全新的领域。但是,在一种关注底层、善意而温暖的写作情怀中,肖江虹将自己的文心与匠心相互融合,在小说文本中对民俗进行新的话语呈现,图绘了独特的民俗景观;同时通过民俗的细部勾勒,雕刻了民俗的独特纹理,一步步逼近了生活、生命的本相,重构了民俗叙事的审美期待,也升华了民俗小说的精神品质和意义空间。
参考文献:
[1] 杜国景.肖江虹的底层叙事与突破[J].小说评论,2015(1):159-164;高红梅.异化下的多重焦虑——“70后”作家陈集益、杨遥和肖江虹的乡村底层叙事[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4):120-125.
[2] 邓榕.文化语境变迁下的乡土叙事——肖江虹小说论[J].当代文坛,2014(2):157.
[3] 李海音.被抛弃者和被侮辱者——肖江虹小说论[J].当代作家评论,2014(2):128.
[4] 肖江虹.百鸟朝凤[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5] 舒炜.乡间早没人能吹百鸟朝凤了——对话作家肖江虹[J].廉政瞭望,2016(6).
[6] 肖江虹.蛊镇[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4.
[7]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671.
[8]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序3.
[9] 凯文·林奇.城市意象[M].方益萍,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3.
[10] 肖江虹.傩面[J].人民文学,2016(9):4.
[11] 肖江虹.悬棺[J].人民文学,2014(9).
[12] 袁定基.论放蛊和防蛊治蛊习俗[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1.
[13] 钱穆.中国文化精神[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51.
[14]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M].长沙:岳麓书社,1987:177.
[15] 周作人.永日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8:605.
[16] 张楚.俗世的温暖亮色与诗性的朴实穆静——肖江虹其人其文[N].贵州日报,2017- 05- 05(12).
[17] 朱光潜.诗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7.
[18] 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4.
[19] 滕斌.近二十年日常叙事困境突围的理论审思[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131.
[20] 理查德·多尔逊.民俗学[M]//王汝澜.域外民俗学鉴要.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14.
[21] 丁帆.“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关于文明冲突中乡土描写的转型[J].文学评论,2005(4):33.
[22]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