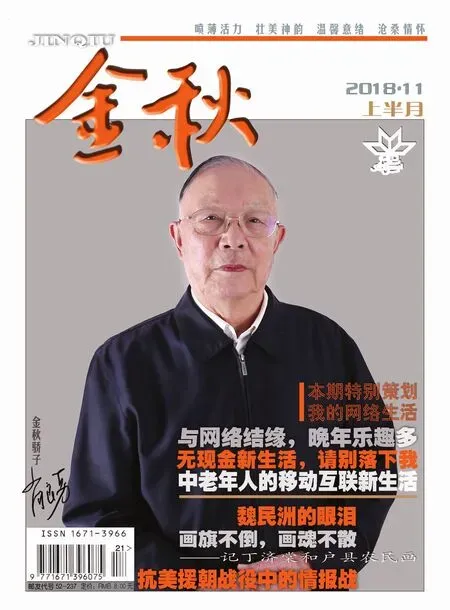狼口余生的记忆
文/冯长春

1950年8月初的一天下午,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觅子乡姚北村的十来个孩童,来到村外东北处的棉花田抓蛐蛐。这群孩子中最大的15岁,最小的只有3岁多。那时的棉花田是引流石川河雨后的黄泥水来灌溉的,水蒸发后泥巴就结成了1至3厘米的泥板并形成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裂口,蛐蛐们就藏在这些裂口之中。这时,年龄大点的孩儿们都进入棉花地里开始抓蛐蛐,我和3岁多的长兴等年龄小的孩子则站在田边,手里拿着火柴盒等待着大孩子们抓住蛐蛐后装进盒里。8岁多的长庆和9岁的江江一人守住一条裂口的一头,将一只蛐蛐包围了起来,他俩或用咪咪毛草堵截蛐蛐或朝裂口使劲吹气驱赶蛐蛐,眼看着那只蛐蛐将在劫难逃。
上世纪50年代初,富平一带还有狼患。8月的棉花枝繁叶茂,高约70厘米,含苞待放的花蕾密密麻麻,里面藏一两只狼,人很难发现。所以当江江专心用力朝着裂口吹气时,一只耳短尖直、尾巴粗直而不打卷的饿狼悄悄地将前爪刺入了江江的口沿下,立时鲜血直流,江江使劲地打掉了狼爪,用手捂着下巴上的伤口跑出了棉田。我当时也看见了那只狼,一直连声大喊着狼——狼——狼,由于恐惧,说话从不结巴的我竟然也结巴了起来。
孩子们闻声马上都跑出了棉花地,3岁多的长兴因年幼不懂事,不但不跑,还愣愣地站在田边一动不动。那头恶狼首次攻击没有得逞后,就向着离它最近的小长兴扑了过来,用两只前爪搭在长兴的两肩上,一口咬住长兴的左脸眼下颊部,长兴被狼咬住后一直站立着,既没有哭,也没有被狼拖倒在地,只是血流满面。当时40岁左右的本村人七娃他大,刚给包谷地上完了一担粪,正挑着两个空筐子往回走,听到我和其他孩子“打狼、打狼……”的喊声后就赶了过来。但是他身体单薄,眼神还较差,就将扁担两头的筐子放下,一边使劲摇晃扁担让扁担两头的铁钩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一边大喊:“打死你、打死你……”有了大人之后,孩子们似乎也有了主心骨,立刻捡起土块、破砖、炭渣块,向着狼所在的地方猛打起来。那只狼虽然穷凶极恶,但在众人的呼喊、拍打、围攻压力下,硬着头皮与众人对峙了一会儿,就不得不松开血口,耷拉着尾巴,向棉田深处逃窜而去。
闻讯赶来的大人们抱起小长兴赶快去找医生。当时乡村医疗条件太差,本地无法处理,听说庄里镇有个名叫余大川的西医,医术精湛且乐于助人,大家便连忙赶到了那里。余大夫给小长兴清洗了伤口,缝合了十几针并注射了盘尼西林。当时的盘尼西林是比较昂贵且稀缺的药品,一支20万单位的盘尼西林价值一斗麦子(当时人民币约2元钱,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34.5元左右),而且是钾盐,打起来比较疼,亦不能静脉点滴,更不能口服,但是治疗效果却特佳。过了一月左右,长兴的伤口便基本痊愈,但是面部的左侧却留下了一个V字型的伤痕,不过余大夫的缝合技术还算不错,若不注意看,那伤痕并不显眼。
如今,这两位狼口余生者都成了生活幸福的老人,正应验了民间那句老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长兴已经71岁,有3个儿子,一个女儿,可谓子孙满堂。江江在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兰州某军工单位,现已78岁,享受着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至于狼患则是自动消除的。上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关中平原生态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狼基本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