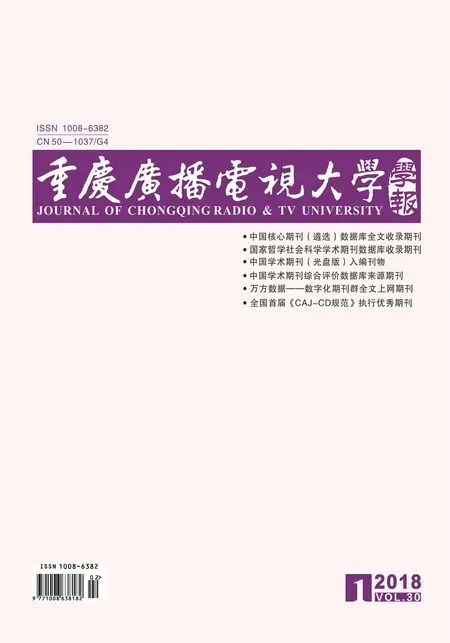谋杀的道德侧面:《洞穴奇案》中的生与死
封 韬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一、引言
五名洞穴探险人受困于山洞中,水尽粮绝,无法在短期内获救。为了维生以待救援,大家约定抽签吃掉其中一人,牺牲他以救活其余四人。威特摩尔是这一方案的最初提议人,但在抽签前又收回了意见。其他四人仍执意抽签,并恰好选中了威特摩尔做牺牲者。这四名探险者最终杀死了威特摩尔并靠着他的尸体活了下来。获救后,这四人以杀人罪被起诉,并被初审法庭判处绞刑……
这是美国20世纪著名法理学家富勒1949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的假想公案。尽管是虚构的案例,但这是以两个令人痛心的真实案例为基础的:1842年的霍尔姆斯案(U.S. v. Holmes)和1884年的杜德利与斯蒂芬案(Regina v. Dudley & Stephens)。①这两个案件均是海难发生后,在海上漂流期间发生的杀人事件,且这两起案件中的杀人者均被判为有罪。富勒以此为基础虚构了更加富有封闭性、冲突性的洞穴奇案,并进一步虚构了最高法院上诉法庭五位大法官对此案的判决书。1998年,随着法学与哲学理论的不断发展推陈,法学家萨伯延续了富勒的案例,增加了九名大法官的判决意见。这14份实际代表了近现代不同法哲学流派观点碰撞的判决书,构成了《洞穴奇案》这部法哲学著作。笔者选取了部分法官的陈词,以剖析这一法哲学的经典命题。
二、联邦法律的空间射程
洞穴奇案引出的第一个争点在于案发时的法律适用问题,亦即探险者们作为一个封闭空间内的灾难共同体,当时的(联邦)法律能否涵盖到这样一个空间?这背后涉及的是对法律适用的法理基础之一——领土原则的解读,以及对自然法的内涵与适用规则等的解读。
1. 福斯特法官陈词——“自然状态”下生存与否的抉择
福斯特法官主张被告无罪,但是他判决的角度可能有些奇特。他首先排除了所有现代法律规范与行政命令的适用问题,因为尽管法律的管辖范围是以领土为基础的,但这是假定当一群人共同生活于地球上同一特定区域时才是有效的,亦即领土原则是以假定人们应该在一个群体内共存为基础的。他认为,如果我们注意法律和政府的目的,注意实定法赖以存在的前提,就会发现本案被告在做出他们性命攸关的决定时,是远离我们的法律秩序的,就像他们远离我们的领土上千千米一样。坚固的岩石把他们的地下牢狱与我们的法庭和执行人员隔离开来,要移开这些岩石也需付出非同寻常的时间和努力。因此,福斯特法官进一步认为,当威特摩尔被杀死时,他们作为一个共同体,并非处在文明社会的状态中,而是处在“自然状态”中,这导致了现代法律对其不适用。他们只“适用源自与当时处境相适应的原则的法律”[1]22。
福斯特法官正是基于此提出了“自然状态”的观点,而那些“与当时处境相适应的原则”亦不言自明,丛林法则、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是我们无论厌恶与否都无法否认的自然规则。福斯特法官显然认为在当时的状态下牺牲是应被允许的。在他看来,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牺牲是十分虚伪的,因为我们的许多现代设施,如铁路、公路、隧道等,它们在被建之初就已经考虑到可能牺牲生命这一因素。尽管大家都心照不宣,但这正是现代文明正常运转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在这样的“自然状态”下,福斯特法官认为,探险者们当时选择一种相对公平的抽签方式来决定生死,而不是选择杀死最虚弱的那一个人,是合理的,甚至是值得被赞许的。
2. 唐丁法官陈词——以自然法为依据何其荒谬
唐丁法官反驳了福斯特法官关于“自然状态”导致法律不能适用的理论。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导出这种“自然状态”的理由是什么?“如果说这些人超出了我们的法律约束到达了自然法的管辖范围,那这种超越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当洞口被封住的时候?”只是坚固的岩石构成一个封闭的空间,这样就推理成完全脱离了现代社会的状态,似乎有些欠妥。虽然被困在洞中且没有食物,但不能简单地将本来的理性人直接视为原始的自然人。因为探险者们即使身处封闭的空间中,仍然能够以文明人的语言与方式沟通,而且还选择了抽签的方式。因此,很难说洞穴是一种完全的“自然状态”。那么,在相对的自然状态下,探险者们的选择与行为是否应被判为有罪,从不同角度来看也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唐丁法官的第二层争点在于,即使承认“自然状态”的存在,那么根据“自然状态”就理应导出这种抽签杀人的残酷方法吗?尽管福斯特法官在陈词中没有明示这点,但从他主张无罪的结论来看,这一点无疑是暗含其中的。而关于得出这种推论的理由,福斯特法官的论证其实是模糊的,但唐丁法官却正是基于这一点提出了猛烈的批评。他认为,福斯特法官所谓的自然规则“颠倒是非”,“令人难以理解”。在这样的规则下,合同法比刑法具有更高的效力:在这一规则下,个人可以订立有效的协定授权他的同伴把自己的身体当作食物;在这一规则下,当一方撤回合意时,其他方竟可以诉诸暴力强制完成。这实在是荒谬的。
三、“一命换多命”与“生命的绝对价值”
洞穴奇案最大的争议点,或者说永远值得被讨论的焦点在于,它最后的结果是以杀死一人为代价换取了本来极有可能死亡的另外四人的存活。它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牺牲少数人以拯救多数人究竟是否具有法理正当性,是否应考虑诸如基本权利、正当且公平的程序,以及征得同意等因素。这背后涉及的是结果主义与过程主义、功利主义与道德绝对主义的对立。
1. 塔利法官的陈词——古典功利主义的延续
塔利法官主张无罪,他在判词中这样写道:预防性杀人与自我防卫杀人成立的理由,就是让对方死去比让更多人死去更合理一些,也就是说这种方式可以将对社会和他人的危害降到最低。通过抽签将死亡的可能平摊,是公平的,是一项“划算的交易”。虽然要达到这样的结果,必须以杀人为手段,但是很明显的是,用一个将死的人使得四个人都存活下来,好过五个人都可能死去,没有人会不承认这一点[1]94,即杀人好过等待自然死亡。他进一步论述道,如果有人觉得杀一人使四人存活还是无法接受,那么如果牺牲一个人能够使一百人、一千人,甚至一百万人存活,除了“极端的宗教分子”,恐怕不会有人不愿意。我们不必“羞于承认”这一点。塔利法官的观点与很大一部分理性人在看到这个案例后的第一反应相似,也就是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来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件值得且应当做的事。这是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哲学的观点。
说到功利主义,自然不得不提边沁,他是功利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利”(utilitarianism)这个现在看来可能有些贬义的词语,正是他在两百多年前提出的。边沁的核心观点非常简单,即“正确的选择、公正的选择,就是最大化功利”。他的著作《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详细地阐述了其哲学主张,边沁通过观察得出,所有人类均受两大至高无上的因素支配——痛苦与快乐。“乐”可以最大地增加幸福的总量,并且引起最少的痛楚;“苦”则反之。而这种快乐和痛楚,边沁将它们同时定义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边沁认为,自然将人置于“乐”和“苦”两大主宰之下,由此决定我们应当做什么、将会做什么。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的。他认为功利等于快乐减去痛苦,幸福减去苦难,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功利最大化的原则。所以,我们应以道德为基准,不管是在考虑个人行为时,还是作为立法者或普通公民,于公于私,最正确的选择都该是全方位最大化地提升幸福[2]。边沁和他的功利主义常常被总结成一句话: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的幸福。这句话充满了直观上的道德感染力,其所蕴含的正义感如春风般扑面而来,让人沉醉。但在这之后,若细细回想,会发现如果只是看中结果的最优化而不问过程,似乎总觉得有所不妥,因为在美好结果的表象下,往往存在着一个个真实个体的牺牲,极端时甚至出现同该案中类似的杀人、吃人现象。当实现优化的结果后再回望这些血淋淋的过程,不免有些恍然。事实上,边沁的理论自诞生伊始,尽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但是质疑的声音也从未停止过。譬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到,正义着重强调差别原则,即符合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3]。从这一点来看,即使是杀死同伴中最虚脱的一个,也是非正义的。
若说功利主义全然只是一种直觉主义的假象,似乎又有些过了。但是,若以功利主义的核心观点为中心,为其加上各种各样的桎梏,却不失为一种出色的方法。以该案来论,尽管塔利法官在判词中饱含情感地写道:“我们是如此珍视生命,以至于我们总是倾向于更多的人而不是更少的人从悲剧事件中存活下来。”但是,大多数人存活下来这一结果,却是以杀人、吃人为手段,我想即使是最坚定的功利主义哲学的拥护者,在想到这个过程时,内心亦不免颤动。于是,善良、理性的人们不由得想到,在实现功利的最大化时,我们是否要有必须遵循的底线?譬如生命,以及那些我们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真的应当允许被牺牲吗?在做出这些选择时,是否要有必须进行的程序?又或者,即使结果是为了大多数人的福祉,但我们是否需要征求那些被牺牲的少数人的同意呢?综上,我们发现若单纯地以功利主义为这些探险者脱罪,显然不是这么简单。那么,以一种截然相反的哲学观点来处死他们又是否合适呢?
2. 特朗派特法官的陈词——强硬的道德绝对主义
在面对这个案件时,会有相当数量的人持这样的观点:杀人就是杀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即使是为了自己的生命,杀人都是一种恶。这正是特朗派特法官判词的核心观点,他主张有罪。他这样说道:“在法律看来,每一个生命都是极其崇高和无限珍贵的,这让每个生命具有平等的价值。没有哪一个生命可以超过其他生命。任何牺牲都必须是自愿的,否则就是侵犯了法律所确认的生命平等和神圣尊严。”[1]118
这是一种绝对主义的道德推理,而它的代言人正是康德。他的三大批判详细阐释了他的哲学观点。在康德看来,道德的来源首先是与真正的自由密切相关的。根据康德的思想,自由的行动就是自律的行动,自律的行动就是根据自我给自己所订立的法则行动,而不是听从本性或社会传统的指令。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并不是由随之而来的结果所构成,而是由完成这一行为的意图所构成。重要的是动机,而这种动机必须是特定种类的,即应是善的、好的,而非隐晦的、难以启齿的。我们应当为了“正当的理由而做正当之事”。康德否定意志受外因支配的说法,认为意志应为自己立法,人类辨别是非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从后天获得的。这套自然法则是无上命令,适用于所有情况,是普遍性的道德准则。康德认为,真正的道德行为是纯粹基于义务而做的行为,而为实现某一个个人功利目的而做的事情就不能被认为是道德的行为。因此,康德认为,一个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并不取决于行为的后果,而是采取该行为的动机。康德还认为,只有当我们遵守道德法则时,我们才是自由的,因为我们遵守的是我们自己制定的道德准则,而如果只是因为自己想做而做,则没有自由可言,因为你只是各种事物的奴隶。这一动机被康德称为“义务的动机”。但如果我们是出于某种利益或欲望的动机而行动,那便产生了义务的动机的对比,这被康德称为“偏向的动机”[4]。从绝对主义来看,即使面临非常绝望的困境,世上也没有任何情况允许人类来主宰别人的命运或决断他人的生死,我们没有那样的权力。
特朗派特法官否认了塔利法官的“划算的交易”的论点。他首先巧妙地反驳了塔利法官“一对一百万”的假设,认为如果杀一人以拯救一百万人是“无须犹豫”的,那么如果是杀四人以拯救五人,杀九十九万人以拯救一百万人呢?“面对这些数字,连他(塔利法官)那无情的直觉都会踌躇起来。”然后,他进一步说道:“如果每一个生命都有无限的价值,那么一个生命与两个生命就是同样珍贵的,与一百万个生命相比亦是如此。一个生命与无限的生命都是一样珍贵的。在预防性杀人中永远没有划算的交易,有的只是手上带着鲜血的幸存者。”
道德绝对主义,简而言之,即是否道德,取决于特定的绝对道德准则,取决于明确的义务与权利,而不管后果如何。这种观点当然是高尚的、正直的,我们甚至无法质疑它,因为它实在太正确了。但是,当善良的公民们习惯于站在高处指责冷血的杀人者时,是否至少应当首先在心中拷问自己,如果身临其境,自己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四、紧急避难的成立与否
本案除了上述哲学理论的争论,还有刑法理论中关于紧急避难(险)的适用与否,对此,法官之间也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个阵营。
1. 本案不能适用紧急避难
如果饥饿不能成为盗窃的理由,那又怎么能成为杀人并以之为食物的正当理由呢?唐丁法官举出先前有一名被告因处于饥饿状态盗窃面包,被法院认定有罪的判例。那么,举轻以明重,饥饿当然不能成为杀人的理由。且法律规定的“谋杀者”一词的威慑效果在于,他们(其他探险者)在执行杀人计划之前若再多等待几天,救援行动说不定会成功。此外,威特摩尔并没有威胁到被告的生命。基恩法官认为,自我防卫的例外*富勒所处的时代刑法理论尚未发展出紧急避险制度。仅适用于当事人抵抗威胁自己生命的攻击时。
而萨伯笔下的伯那姆法官同样认为不应滥用紧急避险。紧急避险的适用条件,首先是行为人主观上对于这种确信是真切而笃诚的,除此之外,还必须能够说明行为人当时除此之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伯那姆法官认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探险者们仍有力气决定抽签的程序且能在完成后顺利地杀死被害人,说明这种所谓的饥饿其实很难说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在他看来,探险者们完全可以再多等一段时间。此外,减轻饥饿也并非只有杀人一种选择,伯那姆法官认为在当时的情境下至少有四种可以备选的考虑:(1)等待最虚弱者自然死亡;(2)吃掉不太重要的身体末梢;(3)尝试重新恢复无线电联络;(4)再等几天。据此,伯那姆法官显然认为紧急避难的抗辩不成立[1]64。
2. 本案适用紧急避难抗辩
斯普林汉姆法官并不同意伯那姆法官的意见,在他看来,紧急避难的法理内核是:由于紧急避难实施犯罪的行为人没有犯罪意图,所以不应该受到惩罚。这其实是以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或者社会危害性为立足点,基于刑罚的目的而进行的考量。亦即,当那些探险者们只是为了存活下去而杀人时,这可以视为是一种“深深根植”于人性的自我保存的本能,并不能说行为人具有邪恶的意图,处罚他们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没有在实质意义上故意杀人[1]73。
塔利法官同样认为紧急避难抗辩适用,他认为紧急避难应是一种正当理由,其实并不用考虑行为人是否故意。紧急避难的理由在于,即使被告人的行为是有害的且是为立法所禁止的,被告人也是无可指责的。被告人要么为善,要么为了较小的恶,都应当免除其罪责。
五、自我代入与契约精神
1. 弗兰克法官的判词——设身处地的自我代入
“如果在场的话,我会加入抽签。如果我赢了,我会出力杀掉那个输掉的人,并且也会吃掉属于我的那一份。我无法谴责,更不要说处死,一个作了我也会做的事情的人。假如法官发现自己在惩罚一个不比自己坏的人,他应该辞职,如果惩罚被告的法官都是在惩罚不比自己坏的人,那无疑是法律的耻辱。”[1]142
朱熹在《礼记中庸》中注:“体谓设以身处其地而察其心也。”孔子的那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加广为流传。许多合理的哲学理念,中西方的先贤们无须互通也能得出一致的观点。这也是上述中特朗派特法官陈词的一个问题,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牺牲,是否合理?诚然,那些在生死攸关的时刻选择舍己救人的人当然是高尚的,但是如果法律要求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达到这样的道德标准,是否有些强人所难,沦为恶法呢?这种自我代入在法学领域有时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譬如安乐死,或许在一般人,甚至是一些法学家看来都是一种人道的、减少患者临终痛苦,使其有尊严地死去的措施。但是,日本刑法学家平野龙一教授在论述安乐死问题时说道,在日本,大部分法学家赞同安乐死,而大部分医生则不赞同。这是由于所处立场的不同,在这种场合下,成为规范的,不仅有法律,还有伦理、宗教、习俗等众多条条框框,更有他的良心[5]。一旦置身于这种立场,即便是法学家,也会对安乐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问题感到非常迷茫。也就是说,即使安乐死在理论上多么的人道、有益,只有当真正地站在那个为患者注射致死药物的医生的立场时,才能体会这种亲手结束一条生命的艰难与纠结。
但是,如弗兰克法官所说,如果是自己,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由此得出无法判决的结论,似乎也有些问题。因为法官审理判决案件,如果仅遵从自己内心的意思,那么法律条文就一文不值了。如果要求法官在审理每一个案件时都拷问一遍自己是否有可能会做出一样的事情,显然也并不妥当。
2. 戈德法官陈词——契约与认可
《洞穴奇案》特意设置了抽签的方式、同意的撤回这些情节,以增强案件的纠结与冲突,而这些问题在戈德法官处得到一个结论。戈德法官认为,我们所遵循的法律的义务并非建立在某种神秘的道德义务之上,也绝不是奠立于主权者的某种神圣权利之上,而是建立在我们遵守它的承诺上面,尽管这种承诺可能是默示的[1]127。
戈德法官的陈词基本总结了这个案件的另一大争议问题,也就是探险者们做出的“抽签食人”的约定的效力。在这个问题上,尽管戈德法官的最终结论与前述塔利法官以功利主义哲学为依据所得出的结论相一致,即认同这一约定的效力,但是其论证的过程却完全不同。
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了充满直观感染力的契约精神。今天我们认为契约精神本体上存在四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契约自由精神、契约平等精神、契约信守精神、契约救济精神。契约自由精神是契约精神的核心内容[6]。在此之前,主张有罪的法官如特朗派特强调生命的绝对价值,那么任何情况下生命都不能被承诺和牺牲,因此抽签与同意之类在他看来本就不应存在。而主张无罪的法官如塔利,他认为既然已经选择抽签这种平等地承担死亡的方式,那么威特摩尔同意与否已经无关紧要了。但是,戈德法官则认为威特摩尔撤回同意的行为是不容忽视的,契约之精神、自由之原则,且不论是否以生命为标的,任何一项契约若是一旦达成就不可撤销,或者即使提出撤销,也将以诸如暴力的方式来强行实现,这是可怕的。更不用说实现的结果是杀死一个生命。因此,即使威特摩尔是最初提议抽签的人,他也理应有撤回同意的权利。当其他探险者不顾威特摩尔的撤回将其杀死并分食时,契约精神已经不能为他们提供任何抗辩了。尽管以私法的精神来解读一起刑事审判可能有些欠妥,但是举轻以明重,即使认可生命可承诺并交易,也不能得出无罪的结论。以否定生命的可承诺性为基础的论证,显然也不能得出无罪的结论。
六、结语
《洞穴奇案》由富勒以真实案件为基础创作出来,50年后由萨伯加以完善成书。至今,许多哲学家、法学家仍热衷于探讨这个问题。富勒在他给出的五份判决中,三份主张有罪,两份主张无罪。杀人者最终被判处绞刑。而50年后,萨伯在他给出的九份判决中,五份主张有罪,四份主张无罪。杀人者还是被判处死刑。两位法学家以这种方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但是,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现代法律究竟能否适用于封闭空间的灾难共同体;法律判决应依据功利主义还是道德绝对主义;紧急避难抗辩成立与否;自我代入与契约精神的效力如何等。这些都是洞穴奇案的讨论之所以能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原因。笔者不由得想到孟子在几千年前曾讲过的一个故事。齐宣王见到大殿前有一头用来献祭的待宰的牛,他不忍心,说:“不要杀它吧。”下人就问:“那就不祭祀了吗?”然后齐宣王说:“怎么能不祭祀呢?用羊来代替牛吧。”孟子知道后问他:“既然是可怜牛无辜而被杀,那么杀一只同样无辜的羊又有何区别呢?”齐宣王回答不出来。孟子说:“没有关系,大王的不忍心,正是仁慈的表现,这样就可以了。因为您当时只是亲眼见到了牛而没有见到羊,君子正是这样,见其生而不忍见其死,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该典故出自《孟子》的《梁惠王章句上》,“君子远庖厨”常常被人误解,孟子的意思其实是“见其(活物)生而不忍见其死”。孟子的故事与富勒的案例其实有许多微妙的相似之处,当我们在讨论诸如“杀一人拯救一百人”“杀九十九人拯救一百人”,或者抽签杀人的效力、“自然状态”等问题时,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在道德上其实是没有答案的。在这个案例中也一样,无论是出于对威特摩尔无辜被杀的同情而主张惩治杀人者,抑或是出于对杀人者走投无路下做出选择的理解而主张宽恕,其实都是可以的。重要的是,无论怎样,我们都表达了对生命和法律的尊重与敬畏。
参考文献:
[1]萨伯.洞穴奇案[M].陈福勇,张世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2]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7.
[3]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56.
[4]迈克尔·桑德尔.公正[M].朱慧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20.
[5]平野龙一.刑法的基础[M].黎宏,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126.
[6]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