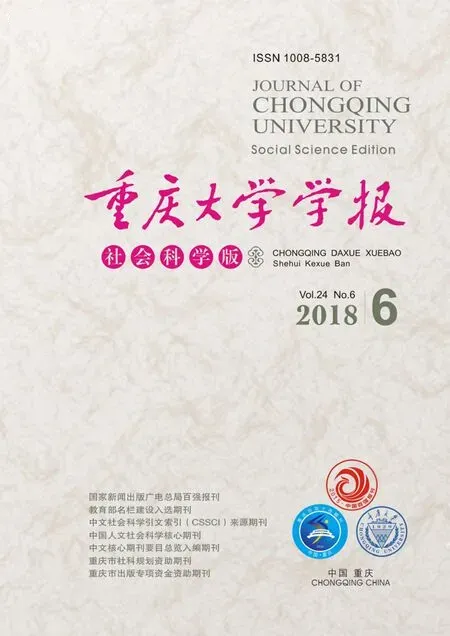任选性冲突法理论研究
殷 骏
(上海海事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1306)
一、问题意向:须认真对待任选性冲突法理论
当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遭遇涉外民商事法律纠纷且将之诉诸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时,司法机关及仲裁机构首先会根据现行的冲突规范来确定准据法,然后通过对该准据法的具体适用作出最终判决。2011年4月,中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该法是中国第一部国际私法的单行法,足堪中国国际私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然而,我们也应看到,虽然在生活中,涉外民商事活动愈发司空见惯,但当我们遭遇涉外民商事纠纷,需确定案件审理中应采用哪国的法律时,很少会意识到,涉案的其他国家的法律也存在被适用的可能。某些基层法院在法律适用法施行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所受理的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尚未适用外国法。在很多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审理中,不论是法院抑或当事人,都基本没有提及将外国法作为准据法的可能性;而是当然地将中国的法律作为准据法予以适用[注]殷駿《中国における新国際私法の適用――契約と不法行為に関する裁判例を中心に》(《日本国際私法年報》,2014,16:133 )。据统计,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2年度审结的409起涉外民事案件中无一适用外国法。。针对这种在涉外案件的审理中不主张适用外国法,乃至积极地主张适用国内法(即法院地法)的立场,传统的国际私法理论界和实践界还是认为必须先经过国际私法相关规定的判断后才能考虑准据法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学者弗雷斯纳(A.Flessner)于20世纪70年代就已主张:在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审理中,只有当双方当事人希望通过援引国际私法的相关规定来指定外国法为准据法并适用时,国际私法才是必须适用的。此即为“任选性冲突法”理论(Lehre vom fakultatives Kollisionsrecht)[1]。针对该理论,以欧陆诸国为主的各国理论界虽不乏对此理论的支持和发展者[2-3],但仍以针锋相对者居多,有学者甚至将其归为国际私法否定论的范畴[4-11],[注]比如诺伊豪斯就认为该理论本身即在否定国际私法。。迄今为止,国内理论界对于该理论的研究较少,有鉴于上述涉外民商事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直接适用法院地法的作法较为普遍,因而,在中国研究这一理论显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以下,笔者将尝试对这一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当前涉外民商事案件司法实践现状进行探讨,以期对完善和丰富中国涉外民商事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二、各国关于适用冲突法规定及外国法的概况
对于上述问题,除了上述中国的情况外,其他各国的情况也有采取和中国一样的做法,即司法机关应根据职权适用相关的冲突法及外国法的规定。如德国虽无明文规定,但通说及判例大都持相关立场[5]43,[6]1 ,[注]参见Soergel-Kegel, in: Kommentar zum BGB, Bd. 10, 12. Aufl. (1996)Rz. 166, 174 Vor Art. 3 EGBGB;Sonnenberger,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 Bd. 10, 3. Aufl. (1998) Rz. 564 ff..570 ff. Einl. EGBGB.。此外,奥地利国际私法第3条、第4条,瑞士国际私法第16条,意大利国际私法第14条,西班牙民法第12条第6款,土耳其国际私法第2条等立法例及日本的判例法[注]詳しくは、東京都地方裁判所平成4年9月30日判決·判例タイムズ825号193頁(判例タイムズ社.東京都地方裁判所平成4年9月30日判決·判例タイムズ825号[N]. 判例タイムズ,1992-09-30:193);また東京都高等裁判所平成8年6月26日判決·判例時報573号33頁など参照(判例時報社.東京都高等裁判所平成8年6月26日判決·判例時報573号[N]. 判例時報,1996-06-26:33)。也持相同立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普通法系诸国,外国的法律一般被视为须由当事人主张且举证的事实。如戴西、莫里斯主编的英国权威冲突法教材就认为,在依据规则18,其一,在外国法应被适用的场合下,为了满足法官的要求,外国法须通过专家对相关证据或事实采取特定的其他方法予以主张并证明之;其二,外国法并未得到充分证明的,法官得对该案适用英国法[12-13],[注]当然,并不是说在普通法系国家,外国法完全被视为事实,英国的法官根据其成文法(British Law Ascertainment Act 1859)也承认了职权探知的权利。在英国的庭审中,针对外国法的证明不但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外国法虽一般被认为是事实,但属于特殊的事实问题。此外,在美国,虽然外国法在传统上被视为事实,但根据成文法(Uniform Judicial Notice of Foreign Law Act(1936))、(Uniform Interstate and International Procedure Act (1962))及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44.1条的规定,职权探知(judicial notice)的权利被予以认可,且该原则已被半数以上的州所采用。。这一做法意味着,即使法院可依职权适用冲突法规定,但最终是否适用外国法将是一个由双方当事人决定的问题。换言之,即使法官依职权适用冲突法的相关规定,并据此指定外国法为准据法,只要当事人不举证该外国法相关法条的内容,法院仍然无法将该外国法作为准据法予以适用,最终只能适用法院地法。因此,普通法系诸国具有后文将论及的任选性准据法理论的一些特征。除了上述两种类型之外,法国的立场介乎两者之间。自破弃院(Cour de Cassation)于1959年审理的著名的比斯巴尔案(l’arrêt Bisbal)[注]参见Cass. Civ. lre, 12 mai 1959, Rev. crit. 1960. 62, note Batiffol, Clunet 1960. 810, note Sialelli, Dalloz 1960. 610, note Malaurie, J. C. P. 1960.Ⅱ11733, note Mptulshy.以降,不论当事人的态度如何,事实审法院具有适用外国法的权限,但无适用的义务。亦即是说,在当事人未主张适用外国法时,法院也无义务依据职权适用冲突法规定。反言之,即使当事人未主张适用外国法,法院依然有权依据职权将该问题作为法律冲突问题处理,并最终将外国法作为准据法适用之。此后,到了破弃法院于1990年审理的萨尔吉斯案(l’arrêt Sarkis)[注]参见Cass. Civ. lre, 10 décembre 1991, Rev. crit. 1992, 314 (2e espèce), note Muir-Watt.时基本确立了在如下两种情况之外,法院没有义务依职权适用冲突法:一是系争的法律关系依据的是法国已签署生效的冲突法条约;二是当事人不得依据自己的权利自由处分的法律关系成为争议焦点[7]。
此外,瑞士国际私法虽在第16条规定了法院依职权探知外国法内容的义务,但同条也规定了在财产权的请求中,外国法内容的查明是当事人的义务,当事人无法查明外国法内容的,法院将适用瑞士联邦法[注]瑞士国际私法第16条:法官负责查明外国法的内容。法官可以要求当事人予以合作。涉及继承问题的,由当事人负责查明。外国法内容无法查明的,则适用瑞士法律。。而匈牙利国际私法则规定了双方当事人共同提出不适用外国法时,可以适用匈牙利法或者在当事人得自由选择准据法时可适用当事人自由选择的法律,该规定的适用范围不限于财产法领域[注]从中可知,该条规定甚至将冲突法视为了任意法。。在荷兰,为了使离婚更加容易,在涉外离婚案件中任何当事人的合意选择或一方未到庭时另一方单方面选择适用荷兰法的请求都被认可。
三、任选性冲突法理论辨析
(一)弗雷斯纳的观点
弗雷斯纳于1970年发表的“任选性冲突法”理论的论文大致有如下核心主张:根据迄今为止的国际私法理论,在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审理中,在依据相关的冲突规则指定外国法时,法院理所当然地必须以该冲突规范所指定的外国法为准据法并作出判决。此时,关于“当事人双方是否真的希望适用该外国法”这一问题,则根本不在法院考量的范围。然而,上述传统做法不能保证给予当事人最合理的解决之道。一般而言,由于法官或律师对外国法并不如其对内国法那般精通,根据冲突规范适用外国法审理的涉外案件较之适用内国法审理的内国案件,其裁判质量要低劣很多。而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当事人享受优质裁判的正当权利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而遭到明显的侵害。因此,只有在当事人自己提出适用外国法时,法院适用冲突规范才具有正当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必须将冲突规范看作是非强制的,可以任选使用的任意法的一种[15]。弗雷斯纳的这一论断是建立在法院适用外国法审理涉外案件的裁判的质量远低于适用内国法审理内国案件的裁判的质量这一前提之下的,可以说该论断是基于现实主义所作出的。该观点的特色在于,它不是将视线聚焦于法院在适用外国法审理涉外案件时遭遇的困境及法院的负担乃至诉讼经济学等角度上[注]聚焦这些角度的论著可参考三ヵ月章《外国法の適用と裁判所」澤木敬郎=青山善充『国際民事訴訟法の理論》(《有斐閣》,1987年版,250-255页)。,而是置于当事人对法官在审理涉外案件时也能通过适用自己熟知的内国法来审理,使案件的裁判保持较高的质量(qualitativ hochwertige Justiz)一事所抱有的期待上。对此,弗雷斯纳作出了如下结论:“从相关各方看来,仅仅是任意地援用指定规则的做法,不论如何,都可以说是最好的做法。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在这样的场合中,将他们对于可以信赖的裁判所享有的利益,与支持适用作为根本标准的法秩序的其他的观点进行比较的,正是他们自己。”[1]
对于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出发将冲突规范定性为任意法规的范围,弗雷斯纳认为不应仅限于财产法领域,而应将之扩展到婚姻家庭法。具体而言,例如因继承事宜而产生的财产法上的请求,如继承份额、必留份额等。而在有关夫妻财产制的案件的审理中,考虑到当事人有权放弃自己所做出的请求,也应当将是否适用冲突规范的决定权交由当事人[1]。而当该财产法上的请求侵害第三人的利益时,当事人合意选择适用法院地法的请求将不被准许。此外,对于当事人不得自由处分的事项(例如身份法上的事项等),则不允许将冲突规范任意化[1]。即是说,虽然离婚及离婚时亲权人的指定等问题仍被列入任选性冲突法的适用范围[1],且“处分可能性”也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概念,但在弗雷斯纳看来,当事人自由处分的可能性及第三人利益的保护确是划定任选性冲突法理论适用范围时需要重点考量的事项。
弗雷斯纳所主张的不适用任选性准据法理论的另一个例外是,当事人没有申请适用外国法的行为可能造成规避法律的后果的场合[1]。弗雷斯纳认为,任选性冲突法理论是为了确保当事人享受高质量的裁判服务而提出的,不是为了方便当事人规避某一特定法律或者获得某一特定的判决而存在的。对于这种情况,即使双方当事人合意选择适用德国法,法院也应拒绝这一请求。
(二)对弗雷斯纳观点的批判
对于弗雷斯纳的上述观点,虽也有茨瓦盖尔特及休特厄姆等学者表示支持[2],[3]334,但更多的则是从传统国际私法理论出发对其作出的严厉批判。如前述诺伊豪斯教授就将该理论归入国际私法否定论的范畴。库洛弗拉则通过详细的分析论证出任选性冲突法理论将法院地法置于优先地位的做法不具备合理、正当的理由[16]45。克格尔也作出了批判[17]。上述批判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弗雷斯纳所倡导的当事人应具有享受优质裁判的权利的主张受到了下列质疑:在涉外民商事案件中,适用外国法时遭遇困难并不当然地意味着法官无法合理妥当地审理案件。此外,根据弗雷斯纳的理论,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司法实践中过分强调适用外国法审理涉外案件的裁判质量问题,很有可能会出现法官好逸,为了避免低质量的裁判,大量适用法院地法的情况。第二,对于弗雷斯纳非常重视的“当事人对高质量裁判的期待”,即对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上的利益”的重视,也有观点质疑这种做法反而有可能导致当事人丧失本来有可能享受到的实体法上的利益。亦即是说,质疑者认为,任选性冲突法的该做法不仅忽视了对冲突法上的正义的保护,甚至也并不具有完全正当的判断实体法层面利益的正当性,它剥夺了当事人通过适用外国法本来可以享受到的实体法上的利益。具体而言,比如关于居住在德国的外籍劳动者的身份问题,仅仅因该劳动者并未主张适用该外国劳动者的国籍国法,法院就理所当然地适用德国法的做法,对于并未完全放弃回国定居的意愿的该外籍人而言,其将丧失通过适用其国籍国法(本国法)而可能享受到的实体法上的利益。库洛弗拉也认为,较之冲突法上的正义及判决结果的国际调和,该理论过分强调了当事人基于对享受高质量裁判的期待所产生的程序上的利益[16]45。第三,根据任选性冲突法理论的观点,事实上默认了法院地法的优先地位。对于这一点,从内外国法平等的原则出发而观之,显然是与之相矛盾的。对于内外国法平等的原则的内涵,弗雷斯纳的看法是,该原则是指法官不应有意识抑或无意识地从内国法优先适用的前提出发裁判涉外民商事案件。与之相对的是,任选性冲突法理论所提倡的法院地法的适用,并不是将法院地法本身置于相较于外国法优先的地位,而是在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审理中,通过法院地法的适用,保护当事人享受对于质量至少等同于审理纯内国案件时的裁判的正当的期待。而且这看来是唯一的方法[1]。因此弗雷斯纳明确表示自己的理论与横行美国的法院地法主义是截然不同的[1]。第四,弗雷斯纳为任选性冲突法理论设定了一些不适用的例外情形。而该理论在划定适用范围时有一个重要的判断要件,即“当事人的处分可能性”。针对这一要件,在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当事人就某一法律事项是否具有自由处分权的问题本身即为应依据某一准据法所属国内法秩序所确定的先决问题;因此,从逻辑的角度而言是不可能在确定先决问题的准据法之前即对这一问题作出判断[15]。况且,弗雷斯纳在任选性冲突法理论中不得已设定这些例外的做法本身就说明了,不论保护当事人诉讼中的利益有多重要,当事人的这些诉讼中的利益也只能向当事人的冲突法上的利益乃至冲突法固有的正义让步[15]。对此,诺伊豪斯也认为,该理论无法真正划定边界,因此显然是不足以付诸实践的[4]。而这一批判也已经触及任选性冲突法理论的适用对象究竟是什么这一根本的问题。
(三)德·波尔教授的观点
虽然弗雷斯纳提出的任选性冲突法理论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和质疑,但该理论仍不乏支持者,如德·波尔就是支持者之一。德·波尔不但支持该理论,而且还对该理论做了更为系统的构建。在德·波尔教授看来,任选性冲突法理论的优势在于关于弗雷斯纳所提倡的审理程序上的问题。对此,德·波尔的态度较之弗雷斯纳更为慎重。他承认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中适用外国法是否将危及裁判的质量的问题只能通过个案来判断[7]。在此基础上,德·波尔阐述道:“当事人拥有请求经过充分、严格地训练且具有权威性的法官为其解决法律纠纷的权利,该权利是谁都不能否定的。然而,我们不认为法官在适用其之前从未适用过的外国法时同样具有权威性;在此情况下,法官的权威性将由于其自身对于法律调查结果准确程度的不自信及其对外国法查明专家的依赖而被显著降低。因此,明白无疑的是,除了案情极其简单的案件外,只要某一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外国法,无论法官如何谨慎小心,都将处于危险的状态。”[7]值得注意的是,德·波尔并未仅凭上述论据直接将任选性冲突法理论予以正当化,而是更重视该理论的另一个优势,即促进诉讼程序上的效率性(procedural efficiency)[7]。
对任选性冲突法理论所具有的促进诉讼程序上的效率性的优势,德·波尔认为涉外民事诉讼由依据冲突法规确定准据法及对所指定的准据法予以适用两个阶段构成。因此,涉外民事案件的审理要求法官付出其在审理内国案件时所不必要的努力。尤其对于诸如反致及定性等国际私法特有的专业问题,对于司法实务工作者而言,将比对于国际私法(冲突法)学者所能想象到的复杂得多。而如果采用任选性冲突法理论,则可在当事人没有提出关于法律选择的争议时将之予以省去[7]。而在法官负有依职权适用冲突法规的义务,当事人又并未意识到法律选择的问题时,为了避免当事人的利益意外地蒙受损失,法院应就本案将适用外国法一事向当事人作出告知。但这样的告知程序将会增加当事人及法院的负担[7]。与此相对的是,如果采用任选性理论,由于当事人并未预想到有关法律选择的争议点,即使在已经提交了有关实质性争议焦点的所有证据,但就涉外性问题的事实而言,在其证据存在不足的情况下,法院将不再要求当事人追加证据,而是立即作出实体法上的判决[7]。从上述论证可以看出,德·波尔显然较之弗雷斯纳更为重视诉讼法上的问题。
那么德·波尔所认为的任选性冲突法理论的根据究竟包括哪些呢?德·波尔是这样阐述任选性冲突法理论与当事人意思自治之间的关系的:任选性冲突法理论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就由当事人选择准据法并适用之这点而言,毫无疑问,两者是密切关联的。因此在理论上,在允许冲突法上法律选择自由的领域里,是没有理由拒绝任选性冲突法理论的[7]。然而,在另一方面,将任选性冲突法理论视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一种类型的观点,从冲突法上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法律这点而言,是将该理论不当地狭隘化。况且,从依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可以选择适用法院地法以外的法作为准据法这点来看,将两者视为相同的观点也是不合理的[7]。亦即是说,德·波尔所主张的任选性冲突法理论的基础是“程序上的处分自由(procedural freedom of disposition)”。对此,德·波尔进一步阐述道:“任选性法律选择去除了他们的争议焦点中的国际性侧面,且允许当事人回避并未成为争议焦点的棘手的法律选择及适用外国法等问题。如果当事人得以只需陈述有关他们所考虑的事实,而法院自发性地不允许将其他事实作为证据予以提出,则也应该同时容忍省略有关法律选择问题的事实的判断。而且,基于确定诉讼范围是当事人的特权这一理由,如果允许无视该事实,就很难理解为何法院会根据当事人省略的或完全因其他目的作为证据提出的事实、所提出的法律选择的争议点,主张应该解决它了。”[7]换言之,这里所说的程序上的处分自由,从广义而言,即是指民事诉讼上的辩论主义。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知道,在德·波尔教授的眼中,任选性法律选择更类似于诉讼程序上的问题。
面对上述质疑,德·波尔对任选性冲突法理论作了进一步阐述。第一个问题是该理论的适用范围问题。面对任选性冲突法理论的结论究竟是依据法院地实体法确定抑或依准据法确定这一难题,德·波尔认为,关于法律选择的规定是否属于自由处分的对象的问题,不应由该冲突规范所对应的实体法的基本目的及该冲突规范所指定的实体法来确定,而应由该冲突规范自己的基本目的所确定。亦即是说,法律选择规范的自由处分可能性也是由冲突规范自体所确定的。此外,从这一立场出发来看,国际私法比诸任何法律都更为主要面向当事人的因私的利益,其自身特点决定了其不可能是保护公共利益的。因此,国际私法已经失去了被界定为绝对强行(imperative)法的资格。这也意味着,当事人的程序上的处分自由与系争事项无关,都无须就法律选择的争议点受到任何限制。基于此,我们可以说,德·波尔所思考的任选性冲突法理论,比诸弗雷斯纳所表现出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给予了冲突规范更为广泛的任意法属性。
牛皮糖站在小卖部柜台前,指手划脚要一包简装红菊烟,忽听到后面的餐馆里吵吵闹闹。蹑手蹑脚过去,看到了村长,他陪着一帮人在那里喝酒。村长看到了牛皮糖,目光没有停留就闪过去,脸红脖子粗的和旁边的人划拳。好像他牛皮糖是个讨饭的。
第二个问题是,即使认可了法律选择的任意选择性,其是否须得到双方当事人的合意选择仍然是一个未解的问题。如果将任选性冲突法理论视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一部分,则双方当事人的合意的必要性确实是亟需解决的问题。然而,德·波尔将缺席审理作为典型事例,认为当事人的合意选择并不是任选性冲突法理论的成立要件。亦即是说,假设法院认为有应当要求当事人对有关法律选择的争议焦点予以释明,在缺席审理的情况下,即存在出现只对原告有利的判决的可能性。
第三是有关在该理论下保护消费者及保护被扶养人利益等构成冲突法根基的基本的法政策将受到动摇的质疑。面对该质疑,德·波尔认为,实际上,该质疑并不具有实际意义。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对于上述政策,在冲突法规定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的场合下,在确定诉讼管辖权时法院同样会予以考虑。而适用法院地法也通常与通过冲突法指定准据法这一做法得出的结论一致。例如,关于消费者,各国的国际民事诉讼法大都尝试并准许给予其住所地管辖权,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法院地与消费者的住所地是一致的[注]如布鲁塞尔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公约(1968年)第14条:在一缔约国有住所的售货人或出借人,得在该缔约国法院或在买方或租借人住所地的缔约国法院被诉。卖方对买方、出借人对租借人的诉讼,只能在被告住所地的缔约国法院提起。此项规定不得影响按本节规定在进行原诉讼的法院提起反诉的权利。。此外,保护一方当事人的政策是否真的对该方当事人有利,以及是否应主张实施该保护等问题,也应由该方当事人自己权衡决定。
值得一提的是,德·波尔的上述论断是基于其以法院地法适用为原则的国际私法(冲突法)认识论的。换言之,克里也认为,德·波尔所思考的民事诉讼法,其出发点也是法院地法的原则性适用(prima facie applicability)[7,18],[注]De Boer,Facultative choice of law, p.338. See,B. Currie, Selected Essays on the Conflict od Laws, p. 9.。在此基础上,为了适用外国法,进而解决法律选择的问题,须存在必须置换法院地法而适用该外国法的理由。德·波尔说道:“我自己是不相信通过法律选择可以达成判决的调和及国际体系的调整,抑或冲突法上的正义的。因此,对于这些理想的追求,在我看来,在成为足以置换掉法院地法的理由上根本不值一提。此外,也并不存在可以断言通过适用外国法可以较之适用法院地法更能促进实体法上正义理念的实现的先验性的理由,因此也不能据此得出不得不置换法院地法而得适用的理由。硕果仅存的理由无非是在诉由上适用外国法对他们有利,适用外国法可以促进判决的承认、执行,以及他们进入法律关系是由于相互之间对某一法律会形成依赖等,并以此为根据认为适用外国法将对双方当事人或者一方当事人有利。而且,如果这就是唯一的必须适用外国法的理由,为了适用冲突法规定,期待为了得到上述利益的当事人提出该主张的做法,似乎也不是不合理的。”[7]
四、借鉴任选性冲突法理论的依据与支撑
上述德·波尔教授的见解显然是以法院地法的适用作为系属原则的。就此而言,比诸弗雷斯纳,前者的理论具有一些更令我们难以接受的特质和内容。当然,从各国国际私法理论研究的最新动向以及长期以来涉外民商事司法实践中有关法律选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来看,包括德·波尔的主张在内的任选性冲突法理论仍有它的参考价值。
(一)任选性冲突法与当事人的利益
从弗雷斯纳的主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审理中非常重视当事人的利益是任选性冲突法理论的一大特点。德·波尔也在强调案件审理的效率性的同时,认为将法院地法置换外国法的唯一正当性是可以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当然这种主张的前提是否定冲突规范的绝对强行法的性质,且把是否适用冲突规范的选择权交由当事人行使。对前述任选性冲突法理论背后蕴含着法院地法优先的价值判断的批判,笔者认为有待商榷。虽然从结果看,采用该理论的实际结果很有可能是法院地法被适用的几率大增。但从该理论本身而言,只要当事人要求适用外国法或主张适用冲突规范,法院就必须适用冲突规范。因此,并不能一概认为任选性冲突法理论自身即属于国际私法否定论的范畴。
此外,任选性冲突法理论所重视的“当事人的利益”关乎当事人的“程序上的处分自由”,实际上是“诉讼程序上的利益”。对此,库洛弗拉就作出了较之冲突法上的正义及判决结果的国际调和理论,该理论过分强调了当事人基于对享受高质量裁判的期待所产生的程序上的利益的批判。该主张确实会由于过分强调当事人的诉讼程序上的利益而忽略了冲突法上的正义及判决的调和,也最终会损害当事人实体法上的利益。诚然,对于该理论所言之“诉讼程序上的利益”[注]例如冲突法上的当事人的利益、交易的安全、公序良俗的维持等。是否可与冲突法上的或其他利益并列考虑的问题,国际私法理论界长期以来争论不断,未有定论[19],[注]请参考A.Flessner, Interessenjurispundenz im internationalen Privatrecht (1990).。然而,考虑到本文开头就介绍过的目前国内涉外民商事案件审理中当事人未考虑适用外国法的情况非常普遍,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固守冲突法上的利益,认为法院必须适用冲突规范的做法确实存在需要反思之处。而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允许当事人请求将适用法院地法作为解决纠纷的方法,其得以正当化的根据则是任选性冲突法理论所言之“诉讼程序上的利益”。
(二)任选性冲突法与“当事人的处分可能性”
前文已提到,即使采用该理论,仍然存在着适用范围的问题。对此,弗雷斯纳作了种种例外性限制,德·波尔则主张在诉讼中应承认冲突规范的一般任意性[7]。这些主张成立的前提就是“当事人的处分可能性”。“当事人的处分可能性”的标准不是由这些冲突规范所对应的实体法的立法目的及这些冲突规范所指定的实体法所决定的,而是由这些冲突规范自己的立法目的所决定。关于这点,从冲突法各自具有独特的立法目的这点来看,也具有一定的价值。而冲突法规定是面向私人利益的,并非牵涉到公序规定,因此也就不具有强行规定的性质。然而,仅凭“冲突规范是面向私人利益的”这点就一概认为冲突规范具有一般任意性的观点,显然欠缺说服力。在考虑这一问题时,也应该像上述“诉讼程序上的利益”那样,与支持适用依据冲突规范所确定的准据法的冲突法上的利益进行比较分析。
另外,对于本文开头就已提到的国内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当事人自身是否意识到案件的涉外性以及其是否意识到存在适用外国法的可能性等问题,如当事人并不具有此敏感,站在任选性冲突法理论的立场,则对于如通过冲突规范适用外国法可能得到的实体法上的利益对当事人而言,其实际上将会因适用法院地法而蒙受实体法上的不利。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蒙受上述不利的当事人正好是经济实力上处于弱势的场合。亦即是说,任选性冲突法理论似乎更加有利于(或者说是保护)能够取得更多相关信息的财力雄厚的当事人。为了应对此一问题,在适用法院地法之前要求双方当事人取得意见一致是一种解决方法。前述匈牙利国际私法即是一例。然而,诚如德·波尔所言,考虑到缺席审理等情况,该保护性要件是否能够正常运作实属疑问。对于保护经济上的弱势方的问题,德·波尔回应道:“概言之,我并不相信任选性法律选择会将“弱者”置于不利的境地。完全相反,不论是富裕还是贫困,任选性法律选择将依靠法院地法抑或外国法的选择权交予当事人。两位当事人可以通过‘贫困的’当事人也应该熟知的法院地法来从程序方面评价自己的胜算。如果‘贫困的’当事人的律师得出了适用法院地法几乎不可能胜诉的结论,他随时可以将法律选择作为争议焦点而提出。”[7]
(三)任选性冲突法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此外,从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法院地法这点来看,其与国际私法上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一个问题。对此,德·波尔再三强调任选性冲突法理论与当事人意思自治之间的差异性,即任选性冲突法的正当化的根据是当事人的“诉讼程序上的利益”。对此,诚如库洛弗拉所言,过分强调法院地法的优先性的特征最终将会使该理论阻碍国际私法上当事人的意思自治[17]。不仅如此,在以欧洲为主的世界各国国际私法中,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以各种形式承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已经是大势所趋。在这样的背景下,片面地主张乃至强调认可当事人对于冲突规范的任意选择性似乎无此必要。当然,反过来看,如果我们已经在愈加广泛的范围内承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实际上也就愈加失去了从根本上否定冲突规范的任选性的理由了。就此而言,在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在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仍然受到一定限制的国家,任选性冲突法理论有其存在的意义。
(四)任选性冲突法与法院地法
从传统国际私法理论看,任选性冲突法理论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其否定内外法平等这一国际私法的根本原则,而给予法院地法优先的位置。对此,有学者尖锐地指出,该理论不啻是披着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伪装的法院地法主义[20]。而且,德·波尔自己也承认,其在诠释和发展任选性冲突法理论的过程中深受美国克里的影响。德·波尔所提出所谓法院地法的原则适用本身正是以克里的主张为基础的。因此,从以保护外国法被适用的可能性为大前提的国际私法规定看,在整个涉外民商事领域都以法院地法的适用作为原则来考虑德·波尔的立场和观点,显然是难以接受的。与此相对的是,弗雷斯纳所采取的,在决定适用法院地法抑或适用冲突规范时考虑当事人的利益的立场,似乎并不应该仅仅因为其优先适用法院地法而一概否定之,而是应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分析。可以说,将通过适用法院地法来解决涉外民商事纠纷时所隐含的当事人的“诉讼程序上的利益”与既有的冲突法上的各个利益放在一起比较衡量的做法十分必要。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所谓“法院地法”实际上往往并不是作为纯粹的法院地法而存在的,它经常同时也是被告或者原告的住所地法,或者是侵权行为地法[1]。传统上认为,各国的国内法院是作为超国家性质的法院来裁判涉外民商事案件的。但就现状而言,这些法院都是基于一定的合理的国际诉讼管辖规则而对相关的涉外民商事案件进行审理。因此,在国际诉讼管辖规则日臻完善的今天,给予法院地法一定的优先地位,也并非完全不当。
(五)任选性冲突法与“最密切联系地”
采用任选性冲突法理论时还可能面临如下的质疑,即当事人所选择适用的法院地法可能排除了与案件具有最密切联系地之法的适用,而最密切联系地法的适用正是冲突法正义的核心要素。传统的国际私法理论赋予冲突规范绝对强行性特性的主要根据是其最终必将指定与案件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域的法律而适用之,而该案件也只有通过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才能获得最为理想的解决。换言之,因为国际私法是从国际私法沟通的顺畅与安全的角度考虑,从相关的内国法及外国法中选择最为合适的法作为准据法的法律,所以其具有公法的性质,属于关涉公共秩序的调和的法律门类,也即属于强行法的范畴[10]。以此考虑,似乎就不存在适用最密切联系地以外的法域的法律的必要了。然而,纵观近来各国国际私法的动向,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准据法的判断标准已不再仅限于“最密切联系性”,而是同时会考虑其他的冲突法上的,乃至实体法上的利益。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大势中如何重构“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位置,乃是关涉到国际私法学者对于国际私法的根本的认识论的问题。无论如何,笔者认为不能一概批判乃至否定。在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审理中,重视当事人的“诉讼程序上的利益”,以此为判断标准之一并确定准据法,甚至秉持将法院地法作为准据法来适用的立场和观点。
五、结语
本文以弗雷斯纳和德·波尔两位教授的观点为主,探讨了国际私法上的任选性冲突法理论。理论上,只要法官对于外国法的调查、了解和研究足够充分,则当事人的“诉讼程序上的利益”将会得到充分的保护,也就不存在适用法院地法的必要了。然而,从各国的现状,尤其是中国的涉外民商事司法实践的现状来看,在外国法的查明、理解和适用方面,仍然存在整体水平不高,地区差异、个体差异明显等问题。因此,在如此特殊背景下来思考向来被传统国际私法理论的支持者批判的任选性冲突法理论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在国际私法理论研究、立法司法实践如火如荼的当下,作为传统国际私法理论支持者之一的笔者[21],也不得不面临重新审视传统国际私法理论,或者说重新探寻再次令传统国际私法理论屹立不倒的雄辩论据。
当然,任选性冲突法的范围、任选性冲突法理论与未来中国必将引入的民事诉讼法中的辩论主义之间的异同,以及任选性冲突法理论与冲突规则的行为规范性之间的关系等都是本文研究中的未尽之课题,对这些问题的探明直接关乎对于任选性冲突法理论的终局评判,此将留待笔者今后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