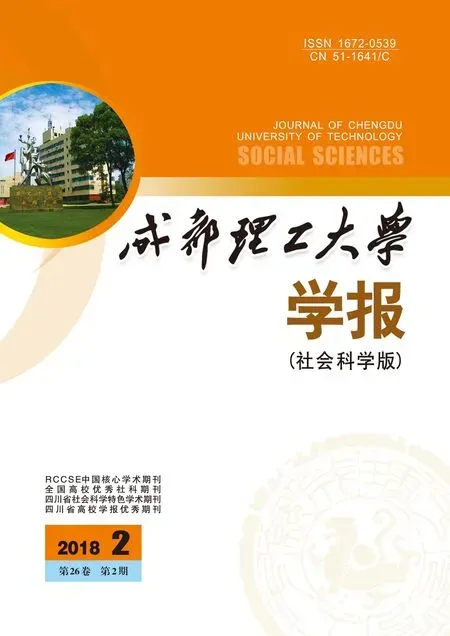竞争主管机构评估研究
郝俊淇
(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0088)
一、为什么要进行竞争主管机构评估
(一)背景:政府部门绩效评估的兴起
现代政府管理的核心问题是提高绩效,要提高绩效首先要了解和评估现有的绩效水平。绩效评估具有计划辅助、预测判断、监控支持、激励约束、资源优化、政治合法化等诸多功能,它的基本理念是顾客至上、公民参与、外部消费、结果导向、公共责任,它的精髓在于促成政府部门持续性的改进[1]。
政府部门的绩效评估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自尼克松政府以降,美国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政府部门的绩效管理和评估。1993年颁布的《政府绩效和结果法案》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政府绩效改革立法,是克林顿政府重要的政府绩效改革基石。该法案要求所有联邦机构制定五年战略规划,明确各自的使命和长期工作目标;制订年度绩效计划,明确为实现长期目标采取的重大措施和绩效测量标准;提出年度绩效报告,评估各自的绩效状况并向国会和公众公开。与此同时,克林顿政府还成立了国家绩效审查委员会(NPC),致力于政府部门评估的专门化、制度化、长期化。2003年,布什政府推出部门绩效“报告卡”制度,设立绩效基准和等级评估标准(绿色代表良好,黄色代表一般,红色代表不佳),以一种类似危机管理的方式展示公共责任。此外,布什政府还推出新预算格式,强调部门绩效与其管理自主权和预算经费的紧密关联,打破了传统管理中“奖励失败”的做法[1]。在美国的示范和带动下,政府部门绩效评估在其他国家广泛推广。撒切尔夫人主政期间,英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对政府部门绩效调查、评估和改进的“雷纳评审”,1982年英国财政部颁布的《财务管理新方案》标志着政府部门绩效评估正式推行。此外,荷兰的《市政管理法》、澳大利亚的《公共服务法案》、日本的《政府政策评价法》等都以正式制度的形式要求政府部门进行绩效评估。
(二)意义:竞争主管机构评估的必要性
卓越的竞争主管机构始终寻求累积性和持续性的改进[2]。竞争主管机构作为政府部门之一,是竞争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主导机构[3]。如果从其最基础、最狭窄、最通约的职能出发——执行反垄断法(竞争法律制度),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作反垄断执法机构(竞争执法机构),比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美国司法部(DOJ)、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CMA)、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JFTC),以及中国的三家反垄断执法机构:国家发改委(NDRC)、工商总局(SAIC)、商务部(MOFCOM)。实际上,但凡推行竞争法制的国家,就不可能没有竞争主管机构。这些竞争主管机构虽然处于不同的政府框架,依附于不同的政治体制,面临着大相径庭的经济社会环境,但是它们往往默契地宣称竞争法的实施会带来好处,并承诺保护市场竞争、促进经济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是它们的天职。然而,在强调顾客至上、公民参与、外部消费、结果导向、公共责任的“评估国”的境域里,保护市场竞争、促进经济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不应是纯粹的“语法规则”,与其先验地假定这些价值,不如系统地将其验证落实。须知,价值理性的存在、发展和兑现必须依赖工具理性。此际,竞争主管机构评估呼之欲出。
竞争主管机构评估之所以必要,从机构内部视角看,评估结果有助于机构持续性的改进,包括帮助机构了解并优化战略规划、设置优先事项、合理分配资源、促进制度变革,以此提升竞争政策的有效性[4]3。从外部视角看,机构持续性进步及其良好声誉是一个品牌,卓越的品牌构成价值高昂的无形资产[5]。首先,高品质的竞争主管机构会赢得更多的政治支持,潜移默化地影响立法决策,进而与机构管理权限、准立法权、经费预算、员额编制等产生关联;其次,高品质的竞争主管机构直接影响到法院对机构立场、观点、方法的司法遵从(judicial deference);再次,竞争主管机构品质的高低直接与企业行为和政府行为的竞争合规意愿挂钩;最后,高品质的竞争主管机构能够激发机构职员的使命感和获得感,有助于吸引和涵养人才,为机构发展注入长程动力。此外,竞争政策及其实践所呈现的以下特点,使得竞争主管机构评估的必要性更加凸显。
1.竞争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机构职能运作的试验性
反垄断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是能力有限的竞争主管机构如何处理复杂的市场信息[6]。竞争政策(反垄断政策)的形塑通常需要竞争主管机构对镶嵌在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又具有特异性的商业行为的竞争意义、经济效果进行艰难的权衡,这种挑战在创新产业、高科技领域、管制行业会进一步放大,因此竞争政策形成的不确定性,使得竞争主管机构的职能运作被赋予了试验性的特征。执法宽大政策(leniency program)实际上就是一场经由试验而获得的成功,美国司法部(DOJ)在1993年对其进行首试,虽然起初饱受质疑,但最终证明宽大政策对助推卡特尔瓦解效果显著,因此被其他同行机构竞相采纳;此外,具体案件中对垄断行为所采取的救济措施,结构性救济抑或行为性救济,行为性救济中对行为限制的程度等,无不凸显试验性特征[7]。竞争政策形成的不确定性以及竞争主管机构职能运作的试验性,从根本上决定了竞争主管机构评估的必要性,如果不进行事后评估和经验反思,我们无法确证支撑机构做出决定的假定条件和有关理论的真实性,无助于机构知识、能力积累和机构持续性改进,当然也无益于竞争政策的长期均衡。
2.产业组织理论与竞争政策的互动演进
竞争政策不是一成不变,它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这部分源于反垄断法原则性的立法特点,反垄断法本身是一个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并呈现哈特意义上的开放结构(opening texture)的弹性文本,是一个有待解释的不完备文本。这样的文本特点使各种创造性解释竞相填充规范罅隙,进而使反垄断法教义呈现出不同面相。竞争政策动态发展的更根本原因在于其交叉学科的底色。“反垄断”首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然后才是法律的议题。产业组织理论塑造了反垄断的方式方法,同时也塑造了反垄断法的原则。为了准确理解复杂的商业现象,产业组织理论实际上处于开放的变迁状态,这种变迁离不开实证依据的砥砺,而对既往执法案件、政策措施的评估有助于提炼经验证据,为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提供动力,进而促进竞争政策的优化和演变。
3.软化执法的流行及其有限透明
现代反垄断法的实施机制具有自足、多元和软化的特征[8],其最明显的表现是执法和解的广泛运用。比如美国反托拉斯法实施中大量运用的同意裁决(consent decree),它有助于解决被告法律责任的不确定性,节省实施成本和资源,使那些具有政治或经济重要性但法律上模糊的问题得到妥善处置[9]。我国反垄断法中的经营者承诺制度具有类似功效。但是,执法和解会伴随信息不透明或有限透明的弊端,从而造成对外部相关主体利益保护的弱减性,削弱了和解处分的公共可接受性[7]。解决该难题的一种途径是寻求竞争主管机构更加自觉和全面的信息披露机制;另一种途径,也是本文所强调的,即通过事后评估来揭露、检验和解协议的利弊得失,弥补信息亏欠,形成监控支持和激励约束,进而改进执法和解的运作。
4.竞争政策多域并行下的标杆管理
目前有超过一百多个国家建立了竞争法律制度,竞争政策正逐步成为国际准则。尽管各法域之间竞争政策趋同、融合的程度近年来明显增强,但是竞争政策的分疏仍根植于各法域的情境差异,寻求统一国际竞争政策无疑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10]。竞争政策的多域并行及其差异为同行机构之间的比较、借鉴提供了可能,域外同行机构富有教益的做法可以成为对本土机构进行评估的标杆或基准,有助于推动本土机构战略设置、资源分配、质量管控等方面的优化。进一步而言,在全球体系下,在竞争政策趋同与分化并存的世界结构中,竞争主管机构评估或许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自愿,而是受到结构性力量支配的“必然”,因为重视机构评估、寻求机构改进,是巩固机构自身话语输出以及国际竞争政策治理能力的必由之路。
二、竞争主管机构评估的标准
竞争主管机构评估尽管是一种国际通行实践,但是就如何评估竞争主管机构至今仍未形成共识性的标准[4]1。在国际竞争网络(ICN)发布的调研报告《竞争主管机构评估》中,成员机构普遍反映评估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在于,很难找到有意义的展开比较的客观手段或基准,缺乏准确和一致的衡量绩效的成熟标准。事实上,评估标准的确立关涉到什么是卓越的竞争主管机构的判断,本文认为,可以从实体结果产出和组织管理过程两方面进行考察。
(一)结果产出标准
新公共管理“最核心的观点是为结果而管理(managing for the results)”,结果导向是政府部门绩效评估的重要理念,能否让社会公众满意成为关键[11]。竞争主管机构绩效评估的重心应当是对执法干预或倡导措施的实际效果进行衡量。衡量的主要方面是经济效果的福利量化,此外也应关注案件教义价值的追踪。
1.经济效果的福利量化
对竞争主管机构执法干预、倡导措施的效果进行评估的最佳方式是通过数据量化以呈现消费者福利或社会福利的改善状况,以及商品或服务在质量选择、成本节省、创新激励等方面的福利改进。在2005年OECD的圆桌论坛报告《竞争主管机构行动和资源的评估》中,韩国举例说明了如何运用事后评估来量化测算有关卡特尔执法案件所改善的消费者福利[12]139-142。ICN的调研报告《竞争主管机构评估》中,大约有一半的竞争主管机构反馈,它们从事或尝试以某种形式来衡量其行动带来的直接消费者福利,其范围包括从对一些特定案例的分析、特定领域或类型的案例(例如合并)到一段时间内的所有机构的执法事项[4]3。
尽管经济效果的福利量化是对机构活动有效性的最佳衡量,但对于“要么相信上帝,否则拿出数据”的观点,本文只能予以弱势承认。福利量化涉及复杂的模型和公式,通常侧重于某些价格效应的衡量或假设,但根本上,真实世界中的某一福利效果受到多种市场因素的影响,在无法控制相关变量的情况下,福利量化的准确性存疑。正如加拿大在上述圆桌论坛报告中所强调的:也许迄今为止最大的困难是设计分析模型,制定健全的分析模型、收集和分析数据的过程是耗时的,涉及不平凡的成本。此外,尽管我们普遍认识到竞争倡导的深远影响,但是相较于执法活动的福利量化,竞争倡导的福利量化存在更大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因为与机构行动直接相关的“案件胜利(case win)”比“倡导胜利(advocacy win)”更容易识别和更易于呈现,后者依赖于外部多方主体采取行动的方式,因而难以测度其影响,同时难以确凿地在倡导措施与影响之间建立联系。尽管存在方法上的困难,一些竞争主管机构已经做出了有意义的尝试,比如将具体倡导措施与经济环境变化联系起来。例如,爱尔兰和美国在圆桌论坛上介绍了在竞争主管机构倡导动议下追踪行业实践和绩效调整的可能性。再如,有评估表明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对法律的竞争影响审查显著促进了经济发展,仅2011年因此带来的经济收益就高达300亿美元[13]。
2.案件教义价值的追踪
结果产出标准不仅体现在对经济效果的福利量化,同时也蕴含在执法案件所附带的教义价值(doctrinal significance)中。个案执法中的教义价值主要包括政策的可持续性、推动理论发展、提炼法律标准、优化分析范式、生成经典概念等。这些教义价值通常不是当下评估所能立马展现的,而需经过时间的淘洗,由“未来知识”予以追认。自此而言,结果产出标准实际上具有暂时标准和长远标准之分。例如,在1969年美国评论普遍认为当年最重要的反托拉斯案件是IBM垄断案,而Otter Tail Power案这样的小案件在评论界显得无足轻重,但是多年后人们恍然发现,正是该案打开了反托拉斯法适用于管制产业的豁口,并为20世纪七十年代旷日持久的AT&T垄断案铺平了道路。Otter Tail Power案的教义影响对于AT&T垄断案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正是所谓的“小案件造就大法律(small case that make big law)”[5]。
在可能存在福利量化难以精确、个案教义价值尚未揭示的情况下,我们尤其要对结果产出标准下的某些“替代性中介指标”保持警惕。一种典型的做法和认识是将执法案件数量、案件罚没款数额或执法案件“影响力”等同于机构成就。ICN的调研报告显示,机构绩效评估似乎对执法案件数据统计有一种天然的偏爱,追踪执法活动有助于简单量化,便于理解和呈现[4]3。美国FTC前主席罗伯特·皮托夫斯基在2008年的一次会议上声称,“布什政府的FTC虽然也调查了《谢尔曼法》第2条之下的一些案件,但是这些案件却无法与Microsoft案、Intel案、AT&T案、Xerox案、Kodak案相提并论。”在这一论断中,案件“影响力”成为核心关注,即能否占据媒体头条,能否成为公众舆论焦点,能否让机构的公共责任得到醒目彰显。奥巴马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更是宣称,“当下竞争主管机构(FTC和DOJ)的反垄断执法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最脆弱的(weakest)”,并声称要“重振(reinvigorate)反垄断执法”[5]。事实上,无论是将执法案件数量、罚没款数额等中介量化数据等同于机构成就,还是“重振反垄断执法”的意识形态,都是对竞争主管机构真实绩效的扭曲。其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会造成机构功能麻痹,忽视对竞争倡导等非执法活动的职能担当;二是未给予那些富于教义价值的小案件充分的权重;三是会扭曲机构及其领导人的激励,过分追逐案件数量和案件轰动效应,滋生短期行为,遮蔽机构的长程视野。
(二)管理过程标准
尽管重视外部消费、结果导向、公共责任是政府部门绩效评估的核心,但不能就此全然将内部控制、过程导向的评估标准对立起来。“为结果而管理”的理念实际上是实体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结合,优化实体结果离不开对组织结构和业务程序的质量管控,因而除了评估实体结果外,评估的另一重点是竞争主管机构内部运作的质量控制,该评估标准将管理和组织视作机构持续性改进和竞争政策实施的必不可少的投入。卓越的竞争主管机构会寻求精益求精的管理技艺来不断扩大和优化结果产出,并促进竞争政策目标的实现。
在组织和管理的评估视角下,竞争主管机构为保障执法效能和倡导效能而做的全部努力成为焦点。这里尤其强调竞争主管机构及其现任领导对未来的投资,即对机构能力、机构建设以及机构长程生命力的投资。根本上,卓越的竞争主管机构和有效的竞争政策是一个累积增量过程。“厚积薄发”对于竞争主管机构及其领导人而言,并不意味着平庸;相反,如果机构每一任领导人都惦记着“重振反垄断执法”,那么沉潜反复的探索可能前功尽弃,机构的长程生命力岌岌可危。道理很简单,就好比在集体球类比赛中,不可能每个队员都只顾得分,只想成为“终结者”,而罔顾助攻,没有助攻的得分是艰难的,没有集体意识、助攻意识的球队不可能赢得胜利、获得存续。因此,机构评估的组织管理标准实际上就是“助攻标准”或“投资标准”,主要可以从组织机构建设、效能工具拓展、知识基础投资三个维度予以考察。
1.组织机构建设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竞争主管机构的具体设计和运营选择将深刻影响实质性干预的质量。竞争政策的实施具有强烈的技术理性和专业化底色,表面上诸多看似法律的判断实质是经济学的判断,产业组织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反垄断的方式和方法。交叉问题、复杂问题、高层次问题的应对,内在地需要功能分化的操控方式,竞争主管机构不应当是一个职能混沌的综合体,而应根据竞争政策实践的需要,做出相应的职能分化。例如,美国FTC不仅设置了竞争局、消费者保护局以及作为技术支撑的经济局——“一个涵盖世界上最卓越的产业组织经济学家的团队”[14],此外还设置了行政法官办公室、政策规划办公室、国会关系办公室、国际事务办公室、公共事务办公室、平等就业和工作条件办公室、普遍咨询办公室、秘书处等机构(1)[15]。再如,自2001年以来,欧盟启动了合并控制的改革进程,并相应增设了首席经济学家办公室和异议小组(devil’s advocate panels),以此强化竞争主管机构的质量内控机制[12]9。实际上,组织机构建设不仅体现在科室分化,实质更在于人力资源的涵养。仅在2005年,美国DOJ反托拉斯局的工作人员就达到770名,其中559名是法学、经济学方面的专业人员;而FTC在2005年有工作人员1022名,其中600多名是法学和经济学家[16]。充沛的人力资源是组织机构建设的根本保障,也是推动竞争政策事业繁荣发展的生力军。
2.效能工具拓展
反垄断执法效果和竞争倡导实效的获取离不开竞争主管机构对相关效能工具的掌握和运用。FTC前主席蒂莫西·穆里斯声称,FTC拥有无与伦比的政策工具组合,使其具备直面和处理任何复杂竞争政策问题的能力[7]。事实上,如果没有充分有效的效能工具作为支持,那么竞争主管机构的职能运作就缺乏基本的“路径依赖”,一方面它难以找到解构复杂垄断案件的进路,另一方面也无法建立与公众、其他政府部门之间沟通的渠道。就目前国际竞争政策实践的先进经验看,涉及执法的效能工具大致包括分析工具和辅助工具,前者涵盖假定垄断者测试(SSNIP/SSNDQ)、市场集中度测试(HHI指数)、垄断势力测试(Lerner index)、同等效率竞争者测试、盈利模式测试、销售方式测试等经济学分析工具,后者涵盖诸如宽大政策、执法和解、安全港、快速审查等辅助性制度措置或适法安排。涉及竞争倡导的效能工具大致包括竞争评估、立法优先咨询、推动企业合规计划、法庭之友、构筑聪明消费者等。其中,反垄断指南作为一种“跨界效能工具”,不仅是“反垄断法实施中最具有影响力的部分”[9],同时也是促导企业竞争合规和政府行为竞争合规的重要倡导工具[3]。
3.知识基础投资
良好的知识基础(knowledge base)是竞争主管机构树立市场信念、理解商业样态、识别反竞争行为、有效开展执法与非执法活动的前提。管理过程标准的核心是竞争主管机构对知识基础进行投资的数量、范围和质量。卓越的竞争主管机构始终致力于竞争政策的研究和开发(competition policy R&D)[14]。根本上,知识不仅具有描述、控制的功能,同时还具有正当化赋予的力量。诚如福柯所言:知识就是权力。因此,如果说知识关系就是权力关系,那么竞争主管机构没有任何理由不加强知识基础的投资,没有任何理由不努力进行竞争政策的研究开发,这些投资和努力实际上是推动机构自身权力发展的引擎,也是助力竞争政策话语攀爬的阶梯。FTC历来重视对竞争政策的研究和开发,其探知领域相当广泛,包括对经济学理论的实证检验,对医药行业、石油行业、互联网行业的研究,也包括对合并领域、知识产权与竞争交叉领域的研究。FTC在2002年完成的研究报告《专利到期前的仿制药进入:一个FTC的研究》实际上重塑了医药行业的政策环境,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接受了其中主要的政策建议,并改变了自己以往的规则[14]。FTC在2003年发布的另一份研究报告《促进创新:竞争和专利的法律政策平衡》,更是引起了全球范围的热烈反响,推动了诸多法域的政策变革[4]。这些自主的知识探索和竞争政策研发,增强了FTC的公信力,成为了机构珍贵的“符号资本”和“声誉资本”,塑造了其竞争政策智识领袖的形象。
三、竞争主管机构评估的路径和方法
设计良好的评估标准如果不能顺畅落实,那么评估的意义和价值将大打折扣。以下主要对竞争主管机构评估的路径和方法展开论述。
(一)竞争主管机构评估的路径
竞争主管机构评估的基本路径可分为外部评估和内部评估。前者是机构外主体所进行的评估,后者是机构的自我评估。两种评估路径各有优劣,理应协同互补,共同推动机构持续性改进和竞争政策稳健发展。
1.外部评估
在ICN的调研报告中,85%的成员机构反馈存在外部评估的实践,这些评估通常是为多元目的或为不同受众而进行的外部评审,并且70%成员机构反映这是立法的明确要求,其中最常见的外部评估主体是具有监督职责的政府部门或中央审计机构,其他例子包括财务检查机构、立法机构等。也有一些成员机构会先进行初步自评,然后再提交给外部评估者[4]7。由此可见,竞争主管机构外部评估的重要支点是“政治体系内的纠偏”,着重财务、审计等方面的监督问责。这种类型的外部评估可能消极防范有余,但在突出重点和促导引领上不足。拓展外部评估更广阔的空间,可以寻求私人研究团队、学术研究中心、专业咨询公司、区域组织或国际组织中同行机构等多元灵活的外部评估。
这里必须强调本土反垄断律师作为一个独立群体对推进外部评估的重要作用。本土反垄断律师是竞争主管当局执法案件、倡导措施、政策制度最大的“消费者”,他们对整体的竞争政策质量具有丰富的体验和细致的感受,深谙“地方性知识”又不乏比较性视野,因此本土反垄断律师不失为一支推动机构改进的难得的“批判性力量”[17]。但是,包括本土反垄断律师群体在内的外部主体所主导的评估难免以下局限:第一,外部评估可能缺乏统一的标准,也可能缺乏连续性,进而影响评估的有效性。第二,外部评估受制于获取信息的全面性、真实性和有效性。第三,外部评估很可能被俘获,评估的独立性、中立性、客观性难以保障。不难想象,竞争主管机构一般不会与尖锐的学者合作,也不会待见“自以为是”的律师。第四,过分依赖外部评估会使竞争主管机构丧失自我评估的积极性,泯灭其起码的反思理性。
2.内部评估
ICN的调研报告显示,大多数成员机构会进行自我评估,这种评估可以是机构范围的,也可以集中于特定的执法领域、科室,甚至在个别职员层面进行。竞争主管机构是竞争政策的实践者,是执法决定、倡导措施、政策安排的当事方,因而是评估中最具信息优势的主体,竞争主管机构经常性的自我评估有利于自身反思性调整。即便如此,自我评估仍面临两大路障,一是评估意愿问题,二是评估耗费问题。
将自我评估视同“作茧自缚”,这是可以理解的。竞争主管机构如果坦诚披露政策实践的缺陷、失误,很可能危及机构以及领导人的声誉,因而会削弱自我评估的意愿。竞争主管机构也是“经济人”,具有自身利益考量,但作为公共部门,其最重要的利益是合法性的最大化,是权威的建立[18]。接受自我评估、自我批判这种危机管理的方式,也就习得了合法化的能力,开启了通往权威的路径。这里所强调的其实是竞争主管机构反而诉诸自身的批判理性,即反思理性,它是指机构自我规制的调控,强调由其主导的竞争政策系统在与市场环境、社会环境交互作用和信息反馈过程中能动地进行调适和变迁。
评估的耗费是机构自我评估的另一难题。ICN的调研报告中,成员机构普遍反映,相较于实施评估的需求,以及数据收集和解析的需求,投入到评估中的财力和人力资源是有限的。在机构总体预算和人力资源给定的情况下,这一难题实质指向资源分配。以上反馈暗含这样的逻辑:自我评估与政策实践是替代关系,二者是非此即彼的存在,有限的资源应当优先运用到政策实践。这其实是对自我评估极大的误解,根本上,机构自我评估与政策实践是互补关系,是相生相成的,竞争政策实践不能全凭热情、激情甚或直觉,若走错了方向,不仅是对资源更大的耗费,同时还会导致难以量计的错误成本(error cost)[19]。在此意义上,自我评估是对竞争政策实践的校准和引航,隐藏着巨大的资源节约和成本节约。因此,竞争主管机构应当追求一种有管理的自治,将机构评估纳入战略规划和经常性预算,合理平衡机构评估与政策实践之间的资源分配。
(二)竞争主管机构评估的方法
在学术研究中,对政府部门绩效评估较为推崇的方法是“3D模式”,即诊断、发展和设计(diagnosis, development and design)[11]。这种方法也适用于竞争主管机构评估。但是,该方法可能使得评估过于静态化和简单化,绩效评估的一个完整过程应当由基本战略设定阶段、指标创建阶段、绩效采集阶段、绩效评估阶段、绩效反馈阶段、绩效激励阶段构成[20]。OECD普遍推荐适用于竞争主管机构评估的“组织发展法”(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methodology)实际上就是以上方法的变体[12]9。“组织发展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1)明确机构的核心目标。明确核心目标的实质是对竞争主管机构的职责进行定位,职责定位可以是机构全范围的,也可以针对具体科室甚至落实到个体职员,明确了职责范围也就圈定了评估的对象。这一阶段类似于英国1979年“雷纳评审”的第一步“选择评审对象”,即每一个科室的负责人向部长提交一份工作陈述,包括工作内容、所用人员、工作程序、工作所要达到的目标等。
(2)将目标转化为实质性指标。该步骤首先需要对机构目标予以整合,进而确立相应的评估指标。葡萄牙竞争主管机构(Autoridade da Concorrência,AdC)在2004年运用“组织管理法”的试点项目中,确立了领导、组织、经营管理流程、人力资源利用、与政府机构关系、与有关公众关系等评估指标。实际上,评估指标往往是具有弹性的个性化设计,ICN调研报告中,普遍运用的评估指标包括执法行动或决定、施加的制裁、发起的调查、结束的调查、处理的投诉、类型化的调查或执法行动、施加的救济、倡导行动、涉及的诉讼、中间调查步骤(例如,突袭或搜查)、直面立法机构/管制机构/法院并与其交涉、发布的政策声明和指南、发布的新闻报道等[4]11-12。此外,信息披露、竞争政策的研发投资、参与机构之间网络建设等也可纳入评估指标体系[7]。
(3)创建指标运作的评估机制。绩效评估可以采取外部评估和内部评估的机制,也可以是两种机制的协同互补。具体评估可以采取定量的方式,也可以采取定性的方式,后者着重于对竞争主管机构及其行动的声誉反馈。声誉反馈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得,例如,通过与外部利益相关方的非正式接触或更为正式的调查方法。它可以由机构本身或外部主体进行,例如雇佣外部顾问。定性评估的实践发现,良好的声誉可能并不总是意味着数量更多的机构行动,而是更优质的机构行动[4]13-14。
(4)将评估结果用于机构行动计划的改进。一如前文所述,竞争主管机构评估的精髓在于促成机构持续性的改进。葡萄牙AdC开展的组织评估和发展项目表明,竞争主管机构可以从其管理和业务定期全面的评估中获得重大优势,它能让机构内部人员和外部人员确定衡量机构运作质量的标准,为机构建立一个改进基准,并可随时间推移反复校准[12]155-172。
(5)定期反复进行评估,使评估成为机构治理的常规要素。竞争主管机构评估不是机构声誉危机的临时应对方案,它是一种经常性措施,是一个动态管理、不断改进的过程。每一绩效管理周期的开始都是建立在上一次绩效管理的运作基础上,并吸收了上一次绩效管理周期的经验与优势,同时剔除了不足之处,是继承与否定相统一的周而复始、螺旋上升的管理运行体系。
竞争主管机构评估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法,结果的透明都是其共通方面。评估结果最常见的呈现方式是机构行动报告或机构年度报告,它们是用于编录竞争主管机构工作结果并向公众阐明其绩效的普遍使用的工具。鉴于构成评估事项范围的广泛性,实践中并不是所有结果都是透明的,有些仅供内部消费(internal agency consumption),但是卓越的竞争主管机构往往自觉寻求信息披露的全面性,这样的报告能够激发社会公众更全面的参与、更有效的反馈和批评,进而为机构的反思性整合和持续性改进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四、余论:我国竞争主管机构评估的展望
就目前来看,我国竞争主管机构的构造可概括为“双层次—多机构”,作为议事协调机构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以及国家发改委、国家工商总局、商务部分享了竞争政策的不同权能,但却共同担负着推动竞争政策发展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自2008年实施以来,我国竞争政策实践稳步推进,《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4号)的发布不仅标志着我国业已搭建了公平竞争审查的制度框架,同时也意味着我国竞争政策体系的初步形成[22]。这对于我国竞争主管机构来说既是成就更是挑战,在竞争政策实践多维并行、纵深发展的情境下,热情、激情甚或直觉固然重要,但绝不是机构职能运作的根本保障。我国竞争主管机构在大力推行对产业政策等政府政策措施竞争评估(公平竞争审查)的同时,也应当具备对自我的批判理性和反思理性。事实上,对竞争主管机构的评估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竞争政策的评估和校准,说到底“打铁还需自身硬”。因此,竞争主管机构评估是推行竞争政策最起码的工具理性,如果没有经由评估所形成的判断标准和方向导引,那么我国竞争主管机构不可能获得持续性改进,我国竞争政策实践很可能陷于盲目、混沌的无序状态。
回归现实,我国基本上没有政府部门绩效评估的沿革,更遑论竞争主管机构评估的勃兴。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部门绩效评估没有形成正式制度,评估往往处于自发或半自发状态;评估缺乏理论指导,实践中具有盲目性;重视政府部门对他者(比如企业、事业单位)的评估和控制而忽视自我审视;评估从内容到形式都缺乏规范性,主观随意性强,甚至流于形式;很多部门不是把评估作为改进手段,而是作为危机处置、消极防御的措施;评估还往往具有封闭性和神秘性[21]。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竞争主管机构评估实际上面临着“从零开始的设计”,艰涩在所难免,但这或许蕴藏了引领和带动我国政府部门绩效评估规范化、系统化、经常化的契机。无论如何,我国竞争主管机构评估的有效开展离不开诸方面的环境建设和保障措施,列要如下:
第一是政治支持。竞争主管机构评估的重要意义如果不能在政治上得到启蒙,那么相关评估活动必将处于无组织的蒙昧状态,其价值和意义跌宕而难有依归。开展竞争主管机构评估必须具备强有力的政治支持。
第二是制度保障。竞争主管机构评估不应是随意的、可有可无的选择,而应当通过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指南定格为正式的制度安排,形成长效机制和系统措置。
第三是规范建设。尽管对于竞争主管机构评估的诸多规范认识目前还存在较大分歧,但是在经验积累和比较借鉴的基础上,我们应当在评估的内容、标准、路径、方法、程序、结果利用等方面逐步凝练规范共识。
第四是评估组织专门化。专门化的组织有助于评估的中立、专业和有效,这种专门化的组织既可以是外部评估场合下的独立实体,例如美国的绩效评审委员会(NPC)、政府责任办公室(GAO),也可以是竞争主管机构内部承担政策分析职能的分化科室。
第五是预算规划。竞争主管机构评估与竞争政策实践是互补促进关系,评估的必要支出隐藏着巨大的资源节省和错误成本节省,因此应当将绩效评估纳入机构战略规划和经常性预算。
第六是信息开放。信息是竞争主管机构评估的基础质料,信息的充分性和可获得性是开展评估的前提。加大竞争主管机构的信息公开力度,强化执法案件、倡导动议以及其他政策措施的信息透明,最有助于激发社会公众参与评估,以及对竞争主管机构公共责任的监督。
注释:
(1)FTC在性质上不是行政机关,而是属于“第四部门”的独立管制委员会,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准司法的制度构造,即通过类似法庭审理和裁决的方式处理涉嫌垄断案件的活动,它是一种将行政与司法两大要素之特质完美融合的统一体。
参考文献:
[1]周志忍.政府绩效管理研究:问题、责任与方向[J].中国行政管理,2006,(12):15.
[2]William E. Kovacic. The Modern Evaluation of U.S. Competition Policy Enforcement Norms[J]. Antitrust Law Journal, 2003, 71(02): 377.
[3]郝俊淇,谭冰玉.竞争政策视域下反垄断指南的定位研究——兼及竞争主管机构的塑造[J].经济体制改革,2017,(5):197.
[4]ICN Agency Effectiveness Working Group. Competition Agency Evaluation [EB/OL].(2016-04-01)[2017-06-17]http://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uploads/library/doc1072.pdf.
[5]William E. Kovacic. Rating the Competition Policy: What Constitutes Good Performance [J]. George Mason Law Review, 2009, 16(04):913, 903-904, 912.
[6][美]赫伯特·霍温坎普.反垄断事业:原理与执行[M]吴绪亮,等,译.辽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11.
[7]William E. Kovacic. Using Ex Post Evaluations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Competition Policy Authorities [J].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2006, 31(2):509.
[8]焦海涛.论现代反垄断法的程序依赖性[J].现代法学,2008,(1):51.
[9]李剑.反垄断私人诉讼困境与反垄断执法的管制化发展[J].法学研究,2011,(5):78.
[10]David S. Evans. Why Different Jurisdictions Do Not (and Should Not) Adopt the Same Antitrust Rules[J].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9, 10(1):161.
[11]周志忍.公共组织绩效评估:中国实践的回顾与反思[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4.
[12]OECD. Evaluation of the Actions and Resources of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EB/OL].(2005-12-16)[2017-06-14]http://www.oecd.org/daf/competition/prosecutionandlawenforcement/35910995.pdf.
[13]张占江.中国法律竞争评估制度的建构[J].法学,2015,(4):68.
[14]Timothy J. Muris. Looking Forwar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U.S. Competition Policy [J]. Columbia Business Law Review, 2003, (2):403-406.
[15]时建中,陈鸣.反垄断法中的准司法制度构造[J].东方法学,2008,(3):53.
[16]王晓晔.我国最新反垄断法草案中的若干问题[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14.
[17]D. Daniel Sokol. Designing Antitrust Agencies for More Effective Outcomes: What Antitrust Can Learn from Restaurant Guides[J].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Law Journal, 2010, 41(3):575-576.
[18]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5.
[19]丁茂中.反垄断法实施中的“积极失误”与“消极失误”比较研究[J].法学评论, 2017,(3):75.
[20]陈通,王伟.关于公共组织绩效评估发展趋势的思考[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109.
[21]周志忍.公共组织绩效评估——英国的实践及其对我们的启示[J].新视野,1995,(5):41.
[22]郝俊淇.公平竞争审查法制化的逻辑[J].南海法学,2018,(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