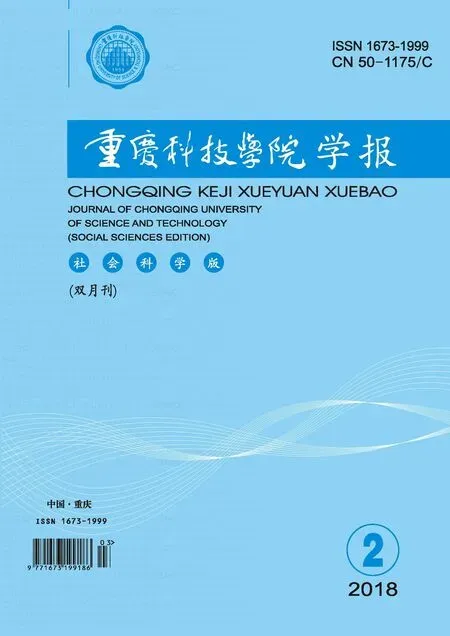论民国时期皖籍油画家艺术风格的多元化选择
刘 连
近代以来,安徽虽然输出了陈独秀、胡适、宗白华、朱光潜等一批思想大家,但是,由于相对分散的文化艺术研究走向,就地域性文化而言,其集体发声力量并不突出。而民国初期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散落各地的安徽籍油画家对艺术多元性的探索却体现了独特的文化旨趣与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
一、面向社会实际需要而存在的现实主义艺术探索
所谓“名人字画”,体现的是对画家身份及影响力的肯定,而画家的身份与价值取得也必然包含在社会影响、专业能力认可等诸多方面。清末民初是一个充满变革与动荡的时期,中国社会正逐步向现代转型。这一时期的画家群体,他们或是依靠良好的家族背景趁势而为,如蔡元培之女蔡威廉、晚清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诗人陈三立之子陈师曾;或是借助政治优势地位声名远播,如高剑父、于右任、梁鼎铭、张道藩、徐悲鸿等。作为这一时期的女性艺术家特别是女画家尤为特殊和不易。在屈指可数的几位女油画家中,就有来自安徽寿县的孙多慈和安徽桐城的潘玉良。
民国时期,在对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艺术采取开放与包容的态度下,各种美学探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社会文化人士比较中外艺术、吸收借鉴不同文化艺术思想、努力推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当时美术界关于“中国艺术道路前途”的争鸣主要分为3种不同观点:第一,守护传统本位,力争使其在时代背景下有所创新;第二,完全接受西方并全面深入地学习;第三,融合传统与西方,走兼收并蓄的道路。
在孙多慈开始接触油画的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西文化,中国思想文化界逐渐达成共识,以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颜文樑、方人定等为代表的画家不约而同地主张“中西合璧”“中西综合”。徐悲鸿主张用写实主义改造中国绘画的停滞现状,认为应跨越中西绘画的界限,走出一条新型的融合之路。徐悲鸿在主持20世纪30年代中央大学艺术科教学时,把他倡导的写实主义绘画理念运用到了西画组的整体教学中。这可以看作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改革中国绘画现状的具体实践。孙多慈因晚清新学推动者、其祖父孙家鼐的荫护,凭借父亲政治方面广泛的人脉资源辅助,以及安徽同乡宗白华的引荐,结识了民国时代绘画潮流的代表性人物徐悲鸿,开启了她的艺术道路。孙多慈在艺术界的初露锋芒及其绘画风格的选择,无不具有徐悲鸿的影子。
国立中央大学对艺术人才培养的要求是旨在“提高社会之艺术风尚”“陶铸优美雄厚之民族性”,这从孙多慈素描的造型方法上可见一斑。她创作的《背纤》《锄地男人体》其结构力求结实厚重,表现手段讲究客观内敛而无夸张变形;《自画像》《瓶汲》突出轮廓线条的韵律美感又兼容传统绘画线条的独特表现性,显现出徐悲鸿折中法国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风格之后的写实特点,体现了她在表述语言上的唯美倾向。在油画色彩处理上,以她参加南京第二届全国美展的《石子工》为例,她偏重对象的固有色,遵循形体与色彩的有机贴合,但在趣味上更偏爱温情与温暖。她的作品在遵循现实主义的主题下,又带有明显的生活气息。画面前景中,在对几个劳动女性头巾的处理上,她以女性的细腻视角区别各个人物之间的层次关系,凸现画家对装饰意味的兴趣,使作品更多地包含了现代因素。1935年,在她学业结束之际,因徐悲鸿的提携,中华书局为她印行了《孙多慈素描集》。宗白华作序称之“落笔有韵,取象不惑,好像生前与造化有约,一经晤面,即能会心于体态意趣之间,不惟观察精确,更能表现有味,是真能以艺术为生命为灵魂者。”又说她“观察敏锐,笔法坚实,清新之气,扑人眉宇。”此时孙多慈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应该可以算作具有雏形的中国学院体系范畴的成功案例的代表。一方面,这让西方油画中国化的改造努力得到了延续,给写实性风格在中国绘画领域的形成打下基础,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徐悲鸿绘画教育观念的普及。
波伏娃认为,女性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前提条件是做一个自由的人,她说:“艺术文学和哲学的宗旨都是让人自由地发现个人创造的新世界。”要享有这一权利,首先必须得到存在的自由。天资聪慧而又婉约可人的秉性气质,使得孙多慈的艺术道路相对平坦顺利。她在专业上的初露锋芒与徐悲鸿情感上的关照不无关系,当孙多慈的家庭生活与物质保障等多方面条件趋于稳定时,她对绘画追求有了逐步走向自我发展的可能。通过更多地亲身接触西方油画原作,她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自己及绘画的本质意义。在油画风格的选择上,她越发地注重自我内心的感受,这种从反映社会现实到注重自我表达的转变过程体现了她由传统文化的附属定位转向了开放式自我选择的思想回归,从对外部世界被动接受转向了主动担当。她到台湾从事绘画教育后,自觉地转向对西方形式主义的关注。而宗白华在对绘画趣味的定位上表现出与她近似的观点,认为“美与美术的特点是在形式、在节奏,而它所表现的是生命的内核,是生命内部最深的动,是至动而有条理的生命情调”[1]98。在 1932年的《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一文中,宗白华将中国绘画的形式与精神总结为:“不但须恢复我国传统运笔线纹之美及其伟大的表现力,尤当倾向注目于彩色流韵的真景,创造浓丽清新的色相世界,更须在现实生活的体验中表达出时代的精神节奏”[1]112。孙多慈独立寻找艺术方向,契合宗白华对艺术的这种价值判断,与同一时期的潘玉良在绘画观念上异曲同工。无论是孙多慈在后期引入印象主义抒情性描绘,还是潘玉良对野兽主义色彩与线条的执着,体现的都是安徽早期油画家对绘画形式的追求。
二、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的现代形式主义追求
艺术的价值在于能够合适地附着人性的情感需要,它的发展与个人存在、社会自由程度密切相关。西方现代主义的萌发与普及是建立在日益成熟的现代社会多元化的基础之上,这种对个体意识尊重与包容的社会形态很自然地催生出与之匹配的多元化艺术生态。当它们与世纪变革中追逐现代思潮的民国知识分子不期而遇,这种内在的需求冲动很自然地触发了对西方文化采取大规模的“拿来主义”现象。而潘玉良作为“新女性”,无论是社会身份地位还是成长环境,都使其少了背负传统的压力和沉重的历史责任。这给她在绘画上追求自由提供了便利条件。她用一生的艺术探索实践了民国时代女性追逐思想自由的梦想。而这种西方现代精神能在民国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依赖于当时相对开放、多样的教育。这种环境的生成,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对西方教育体制采取包容、开放态度,以借鉴、发展本国现代教育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是由于国民政府始终未形成长期、有效的教育管制制度。“五四”运动以来,美术教育中,西方教育观念逐渐占据主流,大量新式美术学校应运而生。它们的设立结束了“一宗一师一派”的历史局面,对社会资源进行了有效整合。新式美术学校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先进教育模式和新思想,使众多有识之士找到了发挥才能的场所,也成为后来众多艺术思潮、流派和风格的策源地和传播中心”[2]117。具有各类文化背景的画家围绕这些院校自发地形成了较为集中的艺术群体,一改传统绘画在一个比较自闭且自足的独立体系里繁衍。这种相对宽松的学术氛围营造出相对自由的思想空间,使艺术创作者既可以摆脱政治的束缚,又少了市场商业的侵扰,形成了民国时期短暂而难得的艺术自由之风。
相较孙多慈注重绘画的含蓄与优雅,潘玉良寄予绘画的感受则是热烈而直接。从潘玉良探索艺术的道路来看,她的身上恰恰展现出民国时期中国社会转型中普通女性在追逐自由与理想所经受的世俗阻力。与同时期产生社会影响的几位女画家的身份进行对照,潘玉良既可算另类,但又显得普通。她长得不算美丽,缺乏如“美女画家”关紫兰那样受人关注的外在容貌,以及陆小曼那样的风华绝代;缺乏显赫家世,甚至是身份低微,她先为雏妓,后当人外室,有别于蔡威廉、孙多慈等拥有良好的家族背景之人。但20世纪初,西方文化的涌入,“中国文化的内部,很自然地滋生出一种新的、力图使思想及学问面向生活并解决实际问题的因素。而这一因素又与西方文化大潮的冲击相结合,共同构成了中国文人思考各种问题的前提”[2]116。 时代给了潘玉良艺术尝试的可能,她捕捉的是个人存在的独立价值,追求的是现代社会非依附关系下个体选择空间的限度,这是“开启一条朝向完全崭新的世界的道路方式”[3],是现代西方文化观念在中国的延伸。潘玉良主动将自身定位与她所追求的现代主义艺术建立起内在的合理联系。但是,只有对不同个体价值的肯定与尊重,才是现代社会及现代艺术存在的根本。作为新旧文化思潮笼罩下的民国女性,对诸多道德束缚与文化观念的反抗却成为她现实的遭遇。独特的民国文化环境如同虚构的童话,顽固盘踞的传统不断与无法阻挡的西方现代思潮交替更迭。她的理想与艺术追求无法找到其生存的土壤,同时得不到包容的还有她无法改变的身份与经历,最终她与她的艺术只能被放逐,远离故土。
从艺术的发展规律来看,潘玉良对现代艺术的探索是符合艺术演变趋势的。她遵循的是绘画的自身规律,希望通过“展示西方艺术风格和时代精神,力争使中国现代艺术成为世界先锋艺术浪潮的一部分”[4]。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她与同时代致力传播西方艺术思潮的决澜社、中华独立美术协会、艺风社以及中国留法艺术学会等绘画组织沦为乌托邦式的先驱,无论是决澜社追求精神的自由和解放,还是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倡导的“超现实主义”,最终得到的是中国尚缺乏接受现代思想土壤的现实结果。但他们的努力与鼓动也确实给“在落后颓废的中国艺术界播下了希望的种子”[2]117,由此也更加显现出潘玉良等人在对近代中国现代艺术拓荒性的开创价值。
作为皖籍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邓以蛰、宗白华等大多主张以中西文化合为一体,以超越文化界限的姿态,开拓了学科新领域。不难发现,民国时期的这些为数不多从事油画的皖籍画家也普遍具有开放性眼光,形成了全身心投入融合中西的绘画实践探索的一种群体意识状态。尽管他们主要的学术活动与艺术探索不是直接产生于安徽,但安徽历史文化中的贯穿南北、兼容东西的区域性特性,给民国时期的安徽文化实践者们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城市新商业图像文化再造的中西融合
南宋开始,历经元、明、清三代,逐渐发达的江南经济催生出繁荣的商业绘画业态。富甲一方的商贾带动了巨大的书画市场,全国各地的落魄文人、民间画家纷纷云集于此。书画家要确立自己的艺术风格和发展方向,需要审时度势,既要符合时代的艺术潮流和游戏规则,又要具有一定的突破性和创造性,这样才能给人以新鲜感,获得社会的关注。从徽州走出来的郑曼陀用“月份牌”这种绘画形式创造出一种新颖的城市图像形式。郑曼陀如同那些自小走出家门,闯荡大江南北,成就富甲一方的徽商一样敢想敢闯,面对商业市场及新材料、新观念,他敏锐地捕捉到现代中国城市的图像雏形,创造性地把西方油画技巧嫁接到现代中国新兴城市文化氛围下的绘画作品中,并使之流行于大街小巷。如今,大众回顾民国时期上海都市风情时,“月份牌”上面的图像符号仍能唤起大众的集体记忆,并且“月份牌”画家营造的“时髦生活”正转化为当代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人们触手可及的现实生活的一种样式。无论是在图像内容的表现,还是绘画语言的选择上,郑曼陀敏锐地捕捉到西方绘画里中国传统绘画所欠缺的元素。他从油画中抽取古典技法,并使之与水彩透明罩染相结合,首创了表现肌肤丰润明净质感的人物擦笔画法,形成了一种合乎近代中国都市时尚人物的造型范本。
自民国以来,郑曼陀的绘画形式及趣味不断受到非议,但在当下,郑曼陀的作品正以精致、甜美的中国古典主义风格受到中国新富阶层的热捧,甚至成为大众认知中国油画的重要元素。在当时西画材料有限的条件下,郑曼陀实现了将传统的精英文化融入新兴的底层文化,是一次平民视角下的文化移植尝试。他在借助西方传统人物肖像原则的基础上,在表现人物形体动态与环境关系上创造出符合国人认可的形式,减弱了油画人物的西式趣味特点;从作品的格调来说,虽然在中西样式嫁接上面存在着一定的生搬硬套现象,甚至显得牵强做作,但在当时社会对西画知识体系尚未普及的情况下,像郑曼陀这样摸索出适宜中国文化现实土壤的西画变体,起到了填充中国人物绘画历史新阶段空白的作用。这些图像得以作为历史记忆与时代特征定格在近代文化体系里,不能不说是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5]。
在对民国时期美术界的诸多有关“中国艺术道路前途”的争论里,主导的认知趋向是以守护传统,兼收并蓄,或者全盘接受西方绘画理念并全面深入学习的道路为主要代表。在民国初期探索的浪潮里,安徽油画家坚持理性、务实的钻研态度,基于解决建设新文化生态体系为使命的担当,从绘画语言方面进行多层面中西文化可行性融合的尝试,相较于各类喧嚣的艺术主张,力量单薄且又相对独立的安徽油画家秉持自身的文化属性,依照各自的艺术诉求,为中国近代多元文化构建的形成增添了有生力量。用对中国现代美术发展作用的眼光来看,这种东西文化融合延展在艺术家一生的过程的讨论,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被不断思考和检视的历史过程,也是对中国美术现代化议题扩展和深化的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1]宗白华.宗白华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2]张剑.新世代的开启:浅析20世纪的“美术革命”思潮[J].铜仁学院学报,2012(3).
[3]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严蓓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34.
[4]石晶.民国时期艺术道路趋向[J].文艺争鸣,2012(3).
[5]刘连.浅析“西画东进”中徽州文化群体的贡献[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潘玉良的艺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