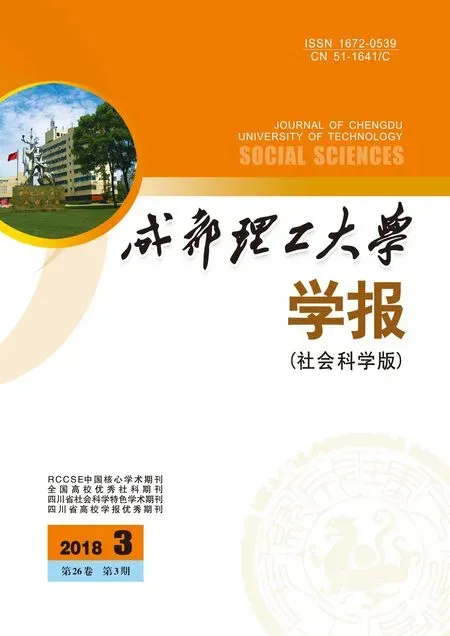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认同研究
梁 珊(西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主义学院,西安 710072)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和革命根据地(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总后方,在边区中共重视农民问题,不断争取农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中共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稳定的大后方。中国共产党争取农民的政治认同,与满足农民生存、安全、情感、尊重、自我实现的需求密不可分。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的需要主要是生存需要,中国共产党减轻农民负担,关注农民生计问题,保障农民安全需要;更加宣传农民为自己“阶级的一分子”,争取农民情感上的归属;并且尊重农民政治机会,逐渐取得农民的政治认同,获得领导合法性,为现代农村中国共产党提升农民政治认同提供经验。
一、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认同概貌
政治认同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产生的情感认同,与政治合法性息息相关。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1]692。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看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力量,关注农民生活的贫苦,逐步把没有政治意识的农民争取到自己阵营,并且拥护和支持自己,为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的政治认同表现为阶级认同、政党认同、政策认同,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凝聚成一股力量,支撑着中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取得胜利,赢得执政合法性。
(一)政治认同
关于政治认同的内涵,《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对其解释为: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人们在一定社会中生活,总要在一定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并自觉地以组织及过程的要求来规范自己政治行为[2]501。从中可以看出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产生的情感认知,这种情感认知可以支配和约束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生活。这种情感认知对于执政者产生的影响有利有弊,符合执政者利益要求的政治认同会促进社会稳定,反之,会引发社会动乱,造成政府合法性资源流失。在学术界,一般认为政治认同最早是由美国政治学家罗森堡姆在其《政治文化》一书中提出来的,他指出“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这些认同包括哪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3]6
谈到政治认同不得不提到政治合法性的问题,李普赛特认为政治认同和政治合法性具有相似性。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最适宜制度之信仰”[4]55,从中可以看出政治认同本质上是人们对政治体系的信任、信仰,是政治统治的坚实基础,是社会成员从心理认知层面对当前政府的支持。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指出,“意识形态能够赋予政治权力以合法性,并把政治权力转换为政治权威,而这种政治权威不仅比赤裸裸的暴力和强制来得可靠和持久,而且还能够使统治阶级用最少的政治资源进行统治。”[5]78政治认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正功能体现在凝结公民的共识,使社会成员从心理上认可执政者,对政治组织或当政者的政治理念表现出忠诚。政治统治者会不断赋予自己统治权威以合法性,从绩效、制度到意识形态提升统治的基础,增进民众的政治认同。
(二)中共到达延安前陕甘宁边区农民生活状况与政治心理
中国农民在数量上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1]642,而贫农和雇农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但其属于当时中国最为贫瘠的地区之一,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经济落后,人烟稀少。陕甘宁人口大约只有140万,富农和地主占人口的大约 12%,在土地占有上却拥有46%,大多数人极端贫困,由于气候原因,降雨量变化莫测,一段时间雨量稀少,但大暴雨也会倏然而至,冲走庄稼,农业生产不稳定,生长期短,并把解冻的黄土坡冲刷成一条沟壑[6]723-725。恶劣的自然环境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而同时地主豪绅有比较大的势力,土地大量集中于地主手中,“在陕西农村中,每户有地 10 亩以下的自耕贫农占全村户数的百分之三十”[7]368,而地租非常高,大都在五五之上,农民交租后,生活异常贫困。
由于地租重,陕甘宁各地农民多数入不敷出,不得不走上借贷之路,高利贷越来越活跃,而农民也越来越穷。另外,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军阀割据造成战乱不断,国民党政治统治的腐败,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当地农民长期遭受繁重兵役、差役、苛捐杂税。“10 年前 300余种,扩到 3609 种”[9]240,增长10 余倍。延安时期前陕甘宁边区农民受到地主阶级、封建阶级、官僚资本主义的多重压迫,受到的压迫最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希望得到解放的意识最强烈。这时期的农民生活状况凄惨,生存利益已经受到了威胁,根本无暇关注政治,但内心渴望政府能够关注自己的生存权益,改变朝不保夕的生存情况。
(三)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认同的实践表征
政治认同主要表现在体制认同、政策认同、阶级认同、政党认同、宗教认同,延安时期农民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政治认同主要体现在政策认同、阶级认同、政党认同三个方面。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到达陕甘宁边区后,制定的革命纲领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关注农民生计,制定的大政、方针也满足了农民的利益需求,逐渐取得了农民的政策认同。同时,农民对中国共产党政治认同表现为阶级认同,发展和提拔了大批农村干部,不断从制度上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将农民看作最可靠的同盟军。另外,农民即使在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实际生活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仍然全力忠诚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是政党认同的直接展现。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中共获得农民的政策认同、阶级认同和政党认同,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提供了人力、物力支撑。
在延安时期,农民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认同,有助于农民对当时的政治体制产生普遍认同感,有助于农民树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激发他们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和信心。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认同,让农民从心理上认可和情感上支持中国共产党,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取得夯实基础。边区农民的政策认同体现在其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决议,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这种政治认同让农民支持和参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的执行,使中共的各项方针政策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提升了当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并且有力地巩固了中共对乡村基层政权的统治。
二、延安时期中共取得农民政治认同的路径分析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政策认同、政党认同、阶级认同上取得农民政治认同,与中共考虑农民的道德传统、保障农民生存、尊重农民的自我实现是密不可分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上采用“双减双交”政策,减轻农民的负担,处理好农民“给”和“要”的问题;推行基层民主制度,让农民参与到国家政权中来,使农民直接体验到政治权利;发展贴近农民的社会教育,为农民参与政治提供一定的政治素养,充实农民的知识和技能,使社会风气更加良好,坚定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赢得农民情感上的认同和归属。
(一)关注农民生计,为农民政策认同提供支撑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和他们的利益有关[9]82。农民最关心的是关系到他们根本利益的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维持生计最基本的物质资料,能否保障他们的生存利益是农民对执政者的评价标准。中国共产党从经济上满足农民需要,为自己的政权提供经济来源和群众基础。“动员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那何愁没有人上前线,何愁没有钱抗战。”[10]77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上争取农民的政治认同,主要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和处理好“给”和“要”的关系。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中日矛盾,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减租减息政策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经过减租减息,取缔苛捐杂税,打击高利贷,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大大动员了农民的政治积极性。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中国共产党的经费主要依靠国民政府拨款和华侨援助,陕甘宁边区农民的负担还不是很沉重。1939年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边区包围,爱国人士响应抗战赶赴边区,脱产人士增加,边区财政不断吃紧,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外援中断,人民负担更趋严重,“鱼大水小”的矛盾十分突出。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号召军人和群众一起生产,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减轻农民负担。毛泽东提出“我们不但要组织农民生产,而且要组织部队和机关一齐生产。由于是农村,部队和机关就必须生产。”[11]1017同时进行大刀阔斧的“精兵简政”,精简人员充实基层,或转入生产第一线。中国共产党以身作则,积极参加生产实践,大大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让农民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站在农民利益上,关心农民生计,为民执政的党,使农民从心里认可中共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不断关注农民生计问题,减轻农民负担,处理好了“给”和“要”的矛盾,使农民在经济上获得利益,为取得农民的政治认同打下物质基础。
(二)推行乡村基层民主,提供政党认同的直接路径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实现人民的民主,保障农民政治权利,归根结底是实现广大基层农民的民主。“新民主主义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1]692乡村政权是边区民主政权的基本行政单位,它直接与农民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是农民日常生活中打交道最多的政府机关,乡村政府的选举直接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然而,选举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因为“千百年来,中国下层民众的生活深受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这四条代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绳索束缚”[12]31,根本没有民主的条件和土壤,没有机会参与政治,享受民主的权利,久而久之,形成对现状政治“认命”、漠不关心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不断动员农民主动参与到选举中来,打破农民的被动参与和政治冷漠,为动员农民做了大量宣传工作,让农民意识到选举一个好乡村政府的作用,用投豆子、画圈的方式让农民选举自己的当家人,选举身边“好人”,把不称职的、损害农民利益的基层干部撤换,使乡村政府真正为农民做主。
中国共产党给予农民选举当家人的权利,在选举过程中,农村基层政权“一是人民直接来议,不必经过代表。二是人民直接来管,直接参加政府工作”[13]420-421。当基层民众在选举过程中认识到手中的民主权利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时候,他们的参政议政热情和政治觉悟就得到极大提高。“边区的一千二百五十个最下级行政单位中的二千个官员,在以前全是农民。二百一十区的一千个职员中,大部分都是从最下级行政单位升上来的。其中很多已经提升到更高职位,在各县政府,专员公署,甚至边区政府尽高大的任务了。”[14]36农民切实地参与边区的政治生活,边区干部代表农民的利益,也正因为如此,扭转了农民对政治的漠视。边区农民意识到自己有和统治阶级一样的地位、权利,可以为自己的命运做主,这大大激发了当地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将其变为其阶级的一部分,使政权顺利在乡村立足并扎根发展,从政权的阶级性层面得到广大基层民众特别是农民的政党认同。
(三)开展贴近农民的社会教育,奠定政治认同的智力支持
文化利益为政治认同提供精神动力,同时影响政治认同的效果。参与政治需要一定的文化素养,列宁讲过:“文盲是在政治之外的”[15]300,一个不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的人,根本就不会了解自己享有的权益,更别提去维护自己的权益。“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再如华池等县,则两百人中仅有一人。”[16]4大量文盲的存在,必然影响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和贯彻,不利于农民参与政治维护自己的权利,调动农民参加抗战保卫国家的热情。然而,在旧中国教育从来都是统治阶级的特权,农民只是受到压迫的劳苦大众,更别提读书识字。
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将农民纳入自身领导体系,必须开展社会教育让农民理解自己的方针、政策,让农民从思想上建立中共是为农民当家做主的政党的观念。中国共产党看到对农民社会教育的必要性,大力发展农村社会教育,提高农民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为取得农民政治认同奠定智力基础。在对农民进行社会教育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深切认识到,向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必须了解和尊重农民的文化传统,满足农民利益,才能赢得农民对共产党的拥护和信仰。”[17]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大力发展社会教育,不仅推行冬学、夜校、新文字运动等社会教育,而且实施了革命戏剧、标语口号、识字画、模范、纪念活动、展览会等贴近农民的教化方式,使边区农民能够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目标,从意识形态上支持党的领导。贴近农民的社会教育使农民的教育权利得到维护,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为农民政治参与奠定智力基础。
三、延安时期中共取得农民政治认同的现代启示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当前,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即所谓“三农”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热点、难点问题。“三农”问题的实质或核心其实就是农民问题。当代新农村建设正在推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但农村与城市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同时,农民对基层民主的政治认同最弱,甚至表现出政治冷漠,对基层政治参与热情很低。另外,农民的素质为农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智力支撑,但目前农民受教育程度低于城市市民,农民子女获得教育资源远低于城市,在一定程度上甚至造成了农村的阶层固化和阶层分化,农民子女改变自身命运的渠道受阻。这些都造成了农民政治认同的弱化,对社会稳定存在威胁。这时有必要借鉴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认同的经验,为巩固当代农村政治认同提供建设性意见。
(一)促进农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奠定农民政治认同的民生基础
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土地大量以廉价或强制的方式被征用,许多农民丧失土地,失去了生存根基,只能通过出卖廉价劳动力为生。同时,农产品价格低廉,农民能从土地上获得收益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大量农民离开土地,外出打工来谋求生计。农民到城市谋生中,因为没有技能、学历,只能从事最底层工作,收入却很微薄,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正如亨廷顿指出,现代化通常给农民带来两个方面的冲击:一是使农民劳动和福利的客观条件恶化,二是导致了农民渴望上升[18]244-245。城市生活为农民带来了新思想和需求,然而因为城乡户籍和经济能力不足,城市留不下,农村回不去。农民的生活漂泊不定,归属感不强,对国家的认同感自然弱化。
党的十九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19]我国现阶段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大力提高农民经济收入是实现农村政治稳定的直接路径,但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必须使农村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政府大力推动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将地理和生态优势结合,发展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农产品产业链,推行生态农业、根据地缘优势、历史文化推进本地的服务业。当地政府和基层政府应对本地进行精准定位分析,把握当地区位、资源优势,多角度、全方面地挖掘当地资源,并进行合理创新,打造特色品牌产业链,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态势。
(二)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完善和规范农民政治参与
农民参加基层政权,是其参政的主要途径,也是获得农民政治认同的重要途径。农民直接打交道的就是乡村基层政权,它是农村最基本的管理者,与农民最基本的政治诉求息息相关。当前农民对中央到乡镇政府的认同感在逐级减弱,对乡村政府的认同感最低,甚至不满。乡村政府存在不作为,权力滥用,造成农民政治冷漠,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出现越级上访和干群冲突问题。然而正如阿尔蒙德说:“没有文化的农民对国家政治可能一无所知,而对本村的决策却可能积极参与。”[20]41但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保障农民政治权益,为农民政治认同提供规范,使乡村政治参与在制度下规范进行,保证乡村中的恶黑势力无法干扰乡村自治,使农民在基层政权中的政治权利得到最大程度的行使。
对农村基层政治制度的建设,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从制度上规范乡村社会权力运行,保障乡村权力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另一方面,保障农民选择基层政府的权利,选举出农民最满意的当家人,将村委会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实现从领导向中介的转变。在建立与乡村社会权力运作相适应的制度机制上,中国共产党需要强化村务公开制度,提高村民对村委会的监督,同时也能使村民有知情权,从而参与村务决策,以制度化的方式实现农民和基层村委会的沟通,实现乡村的民主自治。村干部选举是农民最重要的民主权利之一,面对受贿和拉票选举的,就要改变基层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支部成员的产生方式,公开选拔村党支部成员,打击贿选、拉票以及乡村恶霸势力,加强对基层民主选举过程的监督,才能真正选出农村基层政府的领导人。
(三)提高农民个人素质与促进农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结合
目前城乡之间存在教育资源不均,这影响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的提高,特别是农民子女的教育提升。城乡教育资源不均,一是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无法满足农村义务教育的需求;二是教学设施破旧;三是师资力量薄弱。而由于城市教师的物质条件与农村相差较大,教育质量差距带来进入高等学府的机会不均,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的阶层固化和社会阶层分化。习近平同志在进行十九大报告的时候指出:“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19]可见,国家在加大对农村的基础设施投资,改善教学环境和设施,让农村孩子拥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提高乡村教师的薪资水平,同时引进高学历、有经验的教师,优化乡村教师结构,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使得农村孩子从小有学上、上好学,缩小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质量差距,使农村青少年从“娃娃起”逐步提升知识阶层,减缓城乡之间的阶层固化、分化。
农民作为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只有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才能提高农民参政议政能力,整个国家的素质才能得到提高。农民的素质提高,辨别是非能力也会相应提高,才不会轻易遭到其他意识形态的蛊惑。另外,农民的个人素质提高,适应社会的进程和能力也会加快,对整个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自然更强,对国家的统治也会更加认可。现代化的发展带来一个文化多元化的社会,农民的文化水平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在提高农民素质的基础上,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当然在对农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中,采取的方法和途径一定要接地气,兼顾农民的文化传统,结合大众传媒以简单易懂的方式,方可有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中共在开展文化教育中逐步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增强农民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升农民政治认同的心理基础。
四、结语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政治认同的强弱影响政权的稳定性。在现代化进程中需要不断加强农民对政府的肯定、信赖,以及对当下政治制度的支持,同时不断完善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将农民纳入领导权阶层,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最终取得政权稳定。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注民生,推行乡村民主,发展符合农民的社会教育对强化当代农民政治认同有借鉴意义。目前农民政治认同存在弱化现象,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政策认同、政党认同、阶级认同来提升政治认同,在绩效、制度、意识形态基础上奠基政治合法性,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争取农民的政治认同、巩固政治合法性提供了借鉴:当代中国已经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二元差距,关注民生,奠定农民政治认同的经济基础;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保障农民政治权益,完善农民政治认同的制度规范;促进教育配置,提高农民素质,加强思想文化教育,促进农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来夯实农民的政治认同,有效地保障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1992.
[3][美]威尔特·A.罗森堡姆.政治文化[M].陈鸿瑜译.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84.
[4][美]西摩·马丁·李普赛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08.
[5][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王沪宁,陈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6]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7]乌廷玉.中国租佃关系通史[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8]乌廷玉.现代中国农村经济的演变[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谢觉哉.谢觉哉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4][美]G.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M].李风鸣,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
[15]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6]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册[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
[17]秦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与中国近代乡村社会变迁[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4):5-10.
[18][美]塞谬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01).
[20][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郑世平,公婷,陈峰,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