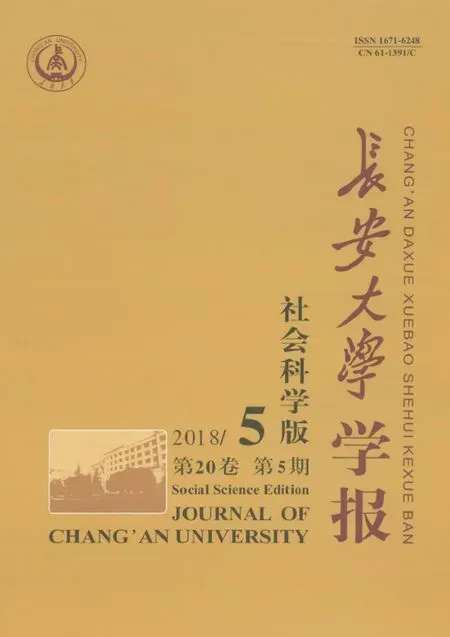清代民间舆论对洋银流通的认知与因应
熊昌锟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16世纪,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后,开始将此地丰富的白银运往欧洲,但巨额的白银数量导致物价飞涨,最终引发价格革命。西班牙商人无奈,只得将白银运往欧洲以外的地区。此时中国正值赋役革新以及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阶段,对白银的需求旺盛,因而成为美洲白银的重要运销地。此前运入中国的白银以银条为主,在各地熔铸成各式各样的银锭后投放市场,不过因其需要一定的检验费用,导致交易成本高昂,因此形制统一、检验方便,节省了一定交易成本的机制银元逐步流入中国。但各地长久使用银锭、制钱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导致银元最初在中国市场的流通经历了诸多波折。另一方面,从政府到民间对洋银的认知有一逐步加深和接纳的过程[注]学界此前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主要有:侯厚吉、张家骧按照时间序列,对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以及赵兰坪、杨端六、马寅初等人的货币思想和主张进行了评述。参见侯厚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想史(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叶世昌细致梳理了中国历代的货币理论,详尽阐述了魏源、周腾虎、钟天纬、张之洞、郑观应等人的铸银钱思想和废两改元前的思想主张。参见叶世昌等:《中国货币理论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林满红将当时士大夫、学者对于白银流入所持态度分为“干预派”与“放任派”,并将持两种不同态度的思想背景追溯至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差异,从而阐发两种思想流派的不同主张。参见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因而对其认知和因应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几个层面,首先是从流通传播层面介绍洋银的形制及其在不同区域的使用情形,其次从认知接受层面展现时人对洋银流通的看法,最后是从应对行动层面来看洋银流通对中国财富的“暗耗”以及各省自铸银元的实践和清廷币制改革的过程。
一、认知层面:对洋银流入情形及鉴别真伪的介绍
洋银自明中后期开始进入中国,因而最初舆论对其的认知和介绍是国人了解这一新式货币的重要途径。早先进入中国的洋银种类繁多,名称各异,《一斑录》提到,“今闽、广外洋诸国,最西者大西洋,峡以内小西洋。若商贩所能及者,为亚齐、为彭亨、为柔佛、噶喇叭、柬埔塞,以及南洋之吕宋、苏禄。凡来中国贸易者,并用洋钱。其四工、反衣形较小而厚者,曰小吉,其余不一。荷兰者为大头,则较次;三花七星则又次;英吉利者为鬼头,已不用;佛头而外有双柱、马剑,今俱不至”[1]。其中小吉指西班牙查理四世银元,佛头、双柱指西班牙银元。三花七星,是指早期的美洲银元,因每面俱有七星。鬼头为英国银元,而马剑为荷兰银元[2]。可见,各国银元流入中国后,民众根据其形制或图案创造了新的称谓。
道光年间以后,墨西哥银元、香港银元等渐次进入中国,“中国定制,官库出纳,向用足色宝纹,通商后,始有大吕宋佛头银洋。咸丰初年,又有墨西哥鹰洋来华,银色、轻重、光洁与本洋相等,惟花样不同,近已通行。……同治五年、十一年,香港银局新造银洋;十二年八月,香港到有美国新洋;十月到日本新洋,轻重、成色、圆净与本洋、鹰洋相等,而洋面花样则异,沪市及江、浙、皖、鄂尚未广行”[3]。随着西班牙银元在中国的广泛流通,清中期以后流入中国的鹰洋、美国贸易银元、日本银元等实际都是仿造本洋的形制,重量、成色相差无几,不过流通程度不及本洋、鹰洋。
而洋银的流入过程及在各地区的流通情形也成为第一阶段舆论认知的重要内容,洋银的流入以及在中国各地的流通,最早要追溯至明中后期,一定数量的外国机制银元流入东南沿海一带,在漳州、厦门以及广州等地流通。闽、粤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很早已与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有着直接的商业往来,明中期以来更为密切。《闽书》记载:“昔患苦倭奴,近患苦红夷,而又土狭人稠,谷食不赡。今且不忧卉服,而忧赤子。番钱内艳,粟货外流。”[4]倭奴是指日本海盗,红夷则是荷兰等国商贩,字里行间流露出番钱(洋银)充斥,货物外流的忧虑。当时漳州等地使用洋银已较普遍,“漳例纳番钱,岁计百万”[4]。“岁计百万”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当时漳州每年已有数万到十数万的洋银进入,福州、厦门的情形也大抵如此。张燮在《东西洋考》中提到:“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5]明隆庆(1566~1572)年间海上开禁,外商云集闽地,白银大量流入,使得福建逐渐成为明清政府的财赋重地。
另外,福建商人不惧风险,前往南海贸易获取银钱,“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东洋。大西洋则暹罗、柬埔寨、顺化、理摩诸国道,其国产苏木、胡椒、犀角、象齿、沈檀、片脑诸货物,是皆我中国所需。东洋则吕宋,其夷佛郎机也。其国有银山出银,夷人铸作银钱独盛。我中国人若往贩大西洋,则以其所产物相抵,若贩吕宋,则单是得其银钱而已”[6]。受认知条件约束,何乔远并不清楚菲律宾本身产银有限,其银钱多来自于美洲。顾炎武也存在同样的认知问题,其称:“东洋中有吕宋,其地无生产,番人率用银钱,钱用银铸造,字用番文,九六成色,漳人今多用之易货。”[7]其实,菲律宾所用银钱,正是大帆船贸易从美洲运来,进而流入中国。
洋银亦很早就进入广东地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提到:“闽粤银多从番舶而来。番有吕宋者,在闽海南,产银,其行银如中国行钱。西洋诸番银多转输其中,以通商故。闽粤人多贾吕宋银,至广州揽头者就舶取之,分散于百工之肆。”[8]屈大均生活在明末清初,因此所记均为此前或当时的情景,“分散于百工之肆”,说明洋银已有广泛使用。不过,吕宋并不产银。“西洋诸番银转输其中”则符合实际情形,其中番银多从美洲运来。且洋银在日常交易、输关纳税时皆有行用,以致时人评论道:“闽广两省所用皆番钱,民自幼至老,有不见纹色等银者,自正供杂税以及关盐等课,俱用番钱输纳。”[9]可见,洋银在闽、粤两省的使用范围十分广泛。江苏、浙江一带的洋银从广东、福建输入,并很快为市场所接受。慕天颜在《请开海禁疏》中称顺治六、七年间,当时禁令未设,市井贸易均有外国货物,民间行使多以外国银钱,各省流行[10]。此处所指各省,主要是指东南沿海粤、闽、浙、江几省,而洋银的流通范围也逐渐向北扩张。
洋银最初是在沿海、沿江商埠流通,在内陆地区的使用则有一定的滞后性。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记载自己曾应盐商邀请,在安徽绩溪一处寺院游玩,“临行以番银二圆为酬,山僧不识,推不受。告以一枚可易青钱七百余文,僧以近无易处,仍不受。乃攒凑青蚨六百文付之,始欣然作谢”[11]。沈复生于乾隆癸未年,即乾隆二十八年(1763)。二十五年后,为乾隆五十三年(1788)。此时番银在徽州等地已有流通,但绩溪等偏远之地不甚通行,故山僧拒绝。相比闽粤、江浙沿海地区,即使是在乾隆后期,洋银在内陆的农村地区仍不甚流行。
此外,时人对银元的种类和识别方法的描述也极为细致。《岭南丛述》称:“花边钱以银镕为钱样,面有水草、烛台诸纹,间有作人马形者。边轮有花,俗称花边钱,其大小递分减为五等,轻重皆有度,便于鬻物,市中间用之。”[12]花边钱即为西班牙银元,其有五种不同的形制,皆有广泛使用。而梁绍壬在《两般秋雨盦随笔》中介绍广东市面流通的洋银时称:“粤中所用之银不一种,曰连、曰双鹰、曰十字、曰双柱,此四种来自外洋。其后外洋钱有花边之名,来自米时哥;又有鬼头之名,来自红毛,亦谓之公头。民间呼为番面钱,以画像如佛,故又号佛番。南、韶、连、肇多用番面,潮、雷、嘉、琼多用花边。”[13]是著介绍了本洋的多种称谓,并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同时总结了不同形制的西班牙银元在广东各府的使用情形,相较此前的介绍更为深入。与此同时,亦有对各国银元的铸造情形的详细介绍。《铸银钱说》记载江、浙行用佛头洋银,铸自大西洋之西班牙国,……乾、嘉之时,其国在广东省贸易繁盛,故其银流入中国最广,中国因习用之[14]。佛头洋银即为西班牙银元,但其并非在西班牙本土铸造,而是在其殖民地墨西哥铸造。咸、同之后,舆论对于洋银有了更深入的认知。同治十年(1871),有学者在《中国教会新报》上发表《洋钱考》一文,对当时流通的洋银进行细致介绍:“今之洋钱有一种面作人像,边作回文,中国人称为本洋者,始于西班牙国。有一种面作鹰鸟,边作棱文,中国人称为英洋者,始于麦西哥国。”并介绍了鹰洋的铸造年份和具体数量,“自一千五百二十一年至一千八百有三年,所铸洋钱十七万六千七百九十五万有奇……迨至一千八百二十一年立国后至一千八百五十六年,计铸洋钱四万七千八百三十九万有奇”[15]。与此前较为简略的介绍相比,该文不仅对西班牙侵占墨西哥的历史及本洋、鹰洋的铸造做了详细介绍,更细致统计了本洋和鹰洋的铸造数量。虽然此数量并不一定精确,但从空间和数量两个维度的介绍,说明此时对洋银的认知较之此前更为全面。而有关“鹰洋”、“英洋”之谓,邹弢给予了合理的解释:“英法两国所用之洋,各有款式,彼此不能通用。今中国所用之洋,面上有鹰,遂误鹰洋为英洋,谓洋自英吉利所铸,而不知非也。此洋皆铸自墨西哥,运来中国,实与英吉利无关,此洋亦不能用于英国。”[16]此前鹰洋多被误作为“英洋”,使国人误以为此币为英吉利所铸,邹弢则给出了准确的解释,起到了勘误的作用。
洋银在中国大规模流通后,各地伪造的银元层出不穷。《明斋小识》云:“乾隆初年市上咸用银,二十年后银少而钱多,偶有洋钱,不为交易用也。嗣后洋钱盛行,每个重七钱三分五厘,……下此红铜为质,外粘白金,或镕银时掺杂铜屑,或雕空洋板,中以铅灌,种种作伪可乱真。”[2]此处反映的是上海一带的情形,乾隆初年上海市场上的洋银还较少见,此后开始盛行,并逐渐出现仿铸的银元,作者甚至提到了仿铸之法,可见当时仿铸已司空见惯。为此,部分著作从观法、听法等方面,强调真、伪洋银之间的差别。道光十四年(1834),盛大士在《泉史》提及沿海商民伪铸洋银之法,洋钱盛行之后,内地仿铸者不断涌现。但外洋所铸本非足色好银,仿铸者银色更低,掺杂了大量的铜和锡。洋银以七钱二分之数,易千余文制钱。于是沿海奸民,视为利薮,将足色好银掺入铅铜,以铸洋钱[17]。银元含银量低于纹银,但兑换制钱数却要高于纹银,因此造成伪铸盛行。光绪戊子(1888)年的《新增银论》称:“目下所用之番银倾镕断无十足,惟贸易者,彼此通行。若除通行银与勾钱银除外皆称为杂钱,所呼名目,因形而唤,其样繁多不能尽列。”并提到辨识新、旧番银的管法,旧银鬼字管法曰:“阿掩原来万字多,新旧花边并掩阿。竹节有分中大小,的噫时管不差讹。中粗舂砍皆衣掩,单掩钱绳鬼字疏。更有凸粗无伪效,阿噫时管贵观摩。”对于1872年铸造的新式鹰洋辨识管法则谓:“鱼骨边栏管法多,的司丕字及知阿。掩阿意则常多见,衣掩单阿有几何。尚有知司连两字,单知唉字勿差讹。磨牙边样间中有,噎治双唉也亦疏。”[18]作者用琅琅上口的诗词编写新旧洋银辨识之法,均是为了帮助民众识别正版洋银。
除了对洋银形制、价格等方面的介绍外,魏源、徐继畲还从地理角度对洋银的铸造、输入路线进行了介绍。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称:“凡中国所用番银,俱吕宋所铸,各国用之。”[19]1565年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建立据点,成为大帆船贸易的重要中站点,因此菲律宾有“吕宋”之称。但菲律宾只是银钱流动的中转站,并不铸造银元。相较于魏源的介绍,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中的叙述更为详细:“各国行用番银,出于墨西哥者盖三分之二。……每岁得番银一千数百万圆,西班牙以此骤富。”[20]徐继畲关于西班牙殖民地墨西哥及其铸造银元情况的介绍,对于时人正确认知洋银有重要作用。
二、揭露层面——对洋银暗耗国人财富的抨击
前文论及,洋银与银锭、制钱汇兑,因其节约了交易成本,有一定程度的升水,因此时人对于洋银升水的认知以及与纹银的兑换亦值得关注。成书于乾隆年间的《石渠余记》云:“闽广近海之地,多行洋钱,来自西南二洋。……质不及银而价视银为高下。始番舶捆载而来,岁数百万,与东南货币相流通。顾昔以洋钱易货而来,今以货易银而去。其流入内地,堑凿消耗,亦渐以难得矣。”[21]洋银最初是以结算货币的身份进入,但与纹银进行兑换时,有一定的价格升水,暗地消耗国人财富。《病榻梦痕录》明确记载了嘉庆元年(1796)杭州一带的银钱汇兑情形,“每番银一圆,直制钱一千七八九十文”[22]。市肆交易,更有高达一千一百三四十至七八十文,银价因之日减。当时,一两纹银不过兑换制钱一千零二十文左右,而银元含银量不如纹银,兑换的制钱却要高于纹银,这说明银元更受市场偏好,因而具有更高的升水。这在《谈浙》中得到了印证,浙江喜用洋银,外洋银饼一块重止七钱,且银色低潮,“咸丰七年来抵银一两,其轩轾已不可解。十年、十一年奸商借轩轾生波澜,于往日光板、烂板、轻板、锈板之外,另生大糙、小糙、净光之名,以轻重相同之货贝,而贸易相悬殊。旦夕之间,亦有涨落,把持盘剥,民甚病之”[23]。洋银在浙江深受欢迎,但伪造也因此盛行,且洋银价格不断波动,加之奸商操纵,百姓深受其害。包世臣对此揶揄道:“又江、浙各省市易,皆以洋钱起算,至压宝银加水。凡物之精好贵重者,皆加洋称。”[24]江苏、浙江一带的市场,洋钱充斥。又因“洋”之称谓,价格昂贵。
汤震在《危言》中论述鹰洋流通与纹银外流的关系,自海禁大开,东南各行省不知有银,仅知鹰洋。鹰洋每元作银七钱三分,其中掺杂铜质五六分,而以铜易我五六分之银,“吾民沾涂所得之银,流出外洋,殆不可訾算矣”[25]。汤震认为,洋银中含有五六分的铜,而以铜易银,造成白银外流,且其确数难以估量。林则徐则称,“即如洋钱一项,江苏商贾辐辏,行使最多,民间每洋钱一枚大概可作漕平纹银七钱三分,当价昂之时,并有作至七钱六七分以上者。夫以色低平短之洋钱,而其价浮于足纹之上,诚为轻重倒置”[26]。林则徐同样看到了洋银较高的价格升水,使得中国商民常受“暗耗”之亏。《论通商之益》亦持同一观点:“通商五十余年,银钱之流溢于外者,不可胜数。”[27]亦在强调白银外流,漏卮无底,使中国蒙受巨大损失。
洋银与纹银、制钱兑换常有升水,加之金银免税,因此美、日等国将大量的银元、小银元运入中国,从中赚取利润。比如美国专门贩售鹰洋,在美仅为八角五分,在华则作十角,此中暗耗亦可想见。银色既低,而进口免税,以彼之洋易我之钱,虽不准出洋,而金银则在免税之列,以其劣银之洋,易我足色金银。日本亦仿效此法,以五角、两角、一角等小洋通行于中国,通商地方受此暗耗,亦复不少[28]。光绪十六年(1890)十二月,《申报》上有文章谈及洋银暗耗纹银,漏卮之危害远甚于洋药、洋货、洋炮与洋船,原因在于每纹银八钱五分换洋钱一枚,每圆浮占纹银一钱三分,如各省均以此交易,每岁何止四五千万枚?即已浮估四五百万两[29]。而洋银每元浮价一钱三分,造成每年外流的纹银达四五百万两。其余各国银元含银量均在九成左右,又有一定的价格升水,漏卮更甚。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及洋银畅行带来的三害:其一、洋钱皆非足色,与银兑换,并不实核分两,只照市价长落,此中无形之折耗甚巨。其二、银色既低,又免进口之税,以此钱购我货物不下千百万,而其换得宝银,旋即铸造洋钱,仍售于我,从中取利,往复无穷。其三、洋银每元或抬价一二分、三四分,甚至六七分,暗中剥削,为数无底[30]。总体而言,郑观应所述三害均是强调洋银以低成银色,暗中侵夺中国财富。另一方面,洋厘的涨落,易造成物价剧烈波动,且洋银含有铜质,含银量不如纹银,但洋厘不时涨落,消耗国人财富。但鹰洋式样精美,取携方便,深受小民欢迎,常“喜用之而不自觉也”[31]。
汤成烈指出洋银来自外番,奸商牙侩从中渔利,导致银价高涨,而百姓需用钱换银,以用之纳税。银价奇昂,奸商从中盘剥百姓[32]。魏源在《钱漕更弊议》就曾提到,江苏漕费原本用钱,而当时洋银兑换铜钱价格较低,因此州县喜用洋银,但洋银价格的上涨,造成暗加等费用的增加,反而使百姓的负担更为沉重[33]。郭嵩焘曾就江浙喜用洋钱发表评论,“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价,漠然无知其非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曾颉刚以家讳乘坐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吾之脂膏,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34]!郭嵩焘指出江浙偏好使用洋银,对于洋银暗耗国人财富茫然无知,而对铁路、电报,则深恶痛绝,加以阻难,郭对此种现象无法理解。在此情形下,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呼吁铸造银元,以图抵制洋银,而杜暗耗之弊。
而清廷内部对此问题亦有关注,嘉庆四年(1799)十月,御史奏称洋商用低潮洋银暗耗中国足色纹银,为此皇帝要求两广总督吉庆留心观察洋商在粤贸易,“不使内地银两被夷人巧赚”[35]。嘉庆十九年(1814)正月,户部左侍郎苏楞额奏称“夷商贿连洋行商人,将内地银两络绎偷运,每年约计竟至百数十万之多”,“夷商以为奇货可居,高抬价值,除不补色外,每个转加算银七八分不等”[35]。 而皇帝也要求广东督抚设法禁止纹银外流。道光年间,关于洋银升水高昂,暗耗中国纹银的奏章屡见不鲜,皇帝多次要求沿海督抚酌定章程加以应对。但是洋银在沿海省份的对外贸易中使用广泛,禁止使用势必影响几省利益,因而粤、闽、江、浙等几省均敷衍了事,洋银升水的现象并未得到改观。
三、应对层面——自铸银元、改革币制的呼吁
洋银盛行于通商口岸及工商城镇,具有较高的升水,造成国人财富流失,部分学者呼吁清政府铸造银元,同时建议在银元上铸上年号、标记,以宣示货币及国家主权。
早在嘉庆年间,学者丁履恒即建议政府铸造金币、银元,他认为此举既可阻止商人任意确定银钱比价,又可抵制外国银元[36]。而道光之际江苏巡抚林则徐也称一些商人相信官方铸造银元是抵制外国银元的唯一办法,且费用远低于铸造铜钱的开销[37]。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申报》上有文章评论道,中国既欲使用银洋,曷不自行铸造,何必购于外洋?而且自行铸造,即可铸写中国年号于其上,如日本新铸之银洋,更为妥当?购于外洋每圆加银多则七八分,少亦三四分,利润尽为外商所获[38]。因此作者主张仿照日本龙洋铸造银元,不仅免受鹰洋升水之盘剥,还可铸上本国年号,宣示国家主权。光绪二年(1876)十一月初七日,《论自铸银钱之便》一文称西人精于计算但重诚信,而华人贪利而又寡信,也是难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基于此,作者建议由户部统一铸银,形制采用一两定式[39]。户部单独设局铸造,不准各省和民间私自铸造,即可免于诈伪烂铸,保证新铸银元的信誉。《中国富强策》则提到了铸币利益,其称铸洋钱之利,每洋钱一枚计重七钱二分,汇兑铜钱有较高升水。南美国运洋钱出口,每千元纳税银四钱,如此重税,仍可获利[40]。虽然金银运入中国各口免税,但运出该国则需缴纳一定的出口税。鹰洋自墨西哥阿卡普尔科运出,“每千元纳税银四钱,如此重税,尚可获利”,则表明铸币有着巨大的利益。同时使自铸银元子母相行,利于收归货币主权。
在朝野取得一致意见(自铸银元)后,广东率先设置银元局,自光绪十六年(1890)开始铸造银元,成效较为显著,“张香帅总制两粤时设局鼓铸大小银圆五种,小者现已通行,而日本、香港之洋已日见其少,惟大者曾不数见,总由鼓铸不敷之故。苟能数浮于市,当市如本洋之见夺于鹰洋,而鹰洋亦自日见其少矣。”因此舆论纷纷建议各省铸造银元,如此“外来之洋不绝而自绝矣,此亦收回外洋利权之一急务也。通行之后不特钱筹钱票自无倒闭遗失之虞,并现在市上现钱到处缺少,小洋一多更可以补钱之不足,不亦一举而三善备哉”[41]。到了清末,不同的意见开始涌现,陈炽在《铸银条陈》中指出中国自道光年间以来,外国银钱行销于中国海疆、内地,并无多少弊端。因天下之钱,本供天下人之用。……今自铸金、银钱,而外国之金银钱与中国分两成色相同,均准通用,则彼钱皆我钱,为我振兴商务,以货易之而已[42]。陈炽声称洋银流入中国“行所无事,亦竟无弊端”,“天下之钱,本供天下人之用”,与洋银暗耗国人财富的认知相比,可谓截然不同,同时主张自铸银钱以振兴贸易。
除此之外,有学者作《推广龙圆说》,文内称本洋、鹰洋流入中国,其重约合中国库平银七钱二分,但其获利犹属不资,因银元中均含有少量铜质。同时指出中国部分官员为了改变这一情形,纷纷设局铸银,但龙洋与鹰洋同一分两而价值不同,各省铸造的银元也价值不一,因此建议凡是上解京饷及各省关税厘金一概收用龙洋,不必有仅搭三成之限制[43]。《自造银币利弊论》一文同样认为洋银流通甚广,造成漏卮无穷,需铸造本国银元以取代之,且在形制、式样,甚至名称均加以改革,以示与洋银的区别[44]。《通商论》中提出鼓铸银元以收回利权,其称美国专贩鹰洋,在美国仅售八角五分,在华用作十角,此中暗耗何可悉数。故应添局铸造,以图收复利权[45]。
朱云表在《商务议》中称,欲兴商务,则需鼓铸银钱,“金银铜钱出数太少,而外洋之小洋、鹰洋遂得畅行于内地。须购买机器,各省设局鼓铸,则外洋之销行自滞。如前年盛行日本小洋,自广东设局铸造,而明治小洋遂日少,此其验也。推而行之,设官银行于省会,以运行钞币,是又赖世之执政者矣”[46]。作者以广东小洋成功取代日本小洋为例,指出铸造银元、设官银行、发行钞票对振兴商务有重要影响。洋银大量流入,加之制钱日渐稀少,造成银贱钱贵。《论银贱钱贵之可骇异》中指出,本洋、鹰洋先后盛行于中国,攫取了巨额利润,但中国“不自铸造银钱,死守成规,专铸极笨极重之元宝,既不便随时分拆,又累于平正高低”[47],造成利源外流,而国家难获其利。不过此前广东等省仿照西法铸造的七钱二分银元,行用以来获利不菲,因此建议户部明定章程,永除宝银、锭银之旧制,一律改铸库平一两之大洋元,五钱、三钱、二钱、一钱之小洋元。通饬各直省照此征收钱粮、关税,支发军饷、俸薪以及厘金、盐课等。
针对铸造银元所费不赀,糜费国帑等说法,《铸银币得失说》进行了驳斥,其称英、美、德、法所铸银元皆系九成银色,每百两中含铜十两,且以紫铜浇入,音愈响亮,质亦圆匀。而用之于市肆,每圆皆抬价一二分,赢余显而易见。并以鹰洋为例,指出洋银充斥市场,利权外流,希望国家收归货币铸造权。“今如由官经理,严其禁令,善其章程,铸之日精,行之日广,则洋钱皆可不用,由是国家既利权独握,民亦受益无穷,不数年必能多西人之利权,而使漏卮顿塞。”[48]李鼎颐在《通行银元八议》中指出通商以来,洋银行用渐广,不仅利权为外洋所握,而且伪币盛行,市面益形败坏。若再不自铸银钱,恐利源外溢日多,伪币日甚一日[49]。另一方面,自铸银元亦需通行无弊,防止伪币。
实际上,早在道光年间,林则徐与陶澍奏称“欲抑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50]。然而道光帝以不能改变祖宗成法为由,驳斥了二人的奏议[注]《清宣宗实录》卷235,道光十三年四月初六日。,不过冯桂芬、郑观应均认为林则徐在江苏已有铸银饼之举,只是未能成功。《校邠庐抗议》称“侯官林文忠公造银饼,初亦使用,未几即质杂,市中析之为另银,银饼遂废”[51]。《铸银钱说》亦云“林文忠公造银饼,其制渺少,全无法度,后又无法以行之,宜其不行也”[14]。虽然林则徐究竟是否在江苏铸造此种银币尚有疑问,然而其未能广泛流通却是毋庸置疑的。咸丰时期,黄寿臣在浙江仿造洋银铸造银元数万元,但市侩从中作难,每元须贴银水,亦未能成功。
林则徐、黄寿臣等人铸造银币的实践虽未成功,但自铸银元已成为朝野共识。光绪十年(1884)十一月二十四日,吉林将军希元奏请设立机器局,铸造一两、五钱、三钱、一钱几种形制的银钱[注]《为制钱过少不敷支用变通钱法试铸银钱事》,档号:03-6683-06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清廷并未立即应允,也未以祖宗成法不能改变为由加以驳斥。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二十四日,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设局铸造银元,得到清廷同意,并于光绪十六年(1890)正式铸造银元。此后,湖北、江苏、山东等十余省份纷纷走上铸造银元的道路。随着各省银元的流通,逐渐改变了洋银充斥的局面。
四、革新层面——整顿圜法的建言
除了介绍洋银、呼吁自铸银元外,还有部分有识之士建议整顿圜法,从根本上改革货币制度。康有为曾多次上书光绪帝,力陈变法之必要。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其上皇帝第二书中,直陈改革币制的重要性。他从货币名称及内在价值两部分直斥洋银对中国社会的危害,请求皇帝饬令“户部预筹巨款,并令各直省皆开铸银局,其花纹年号式样成色皆照广东铸造。增置大圆,由督抚选精明廉吏专司此局,厚其薪水,严其罚刑,督抚以时月抽提,户部以化学核验。他日矿产既盛,增铸金钱扺禁洋圆,改铸钱两,令严而民信,可以塞漏卮,而存正朔矣”[52]。康有为的改革之法亦从“保利”“争权”两个方面考虑,此奏是否得到皇帝的重视不得而知,然而晚清“新政”中设局铸银确系重要内容,成为地方督抚热衷之事。光绪二十三年(1897),《论中国亟宜整顿圜法》一文指出,本洋、鹰洋在中国的广泛流通引发广东、湖北等省铸造银元的实践,但各省铸造的银元仅在东南七省流通,且“商民因墨西哥洋圆有定值,较中国龙圆为可恃,故至今仍喜用墨西哥之洋圆而避用龙圆”。因此欲杜此弊,有待中央政府约束各省督抚,使之一心一德、通力合作,毋相挤轧,以善其用。如此则可“使分两成色归于划一,则虽铸自各省而皆成为一国之银圆,无论中外商务,均可畅行而无滞矣”[53]。
汪康年在《论今日中国当以知懼知耻为本》中呼吁,墨银通行各埠,中国银钱不能一律行使,“而我失制币之权,西法税轻,重其入而轻其出,我则反是,则失税权”。各省铸造银元,且不能互相通用,使得鹰洋畅通无阻,导致中国丧失税收。当务之急在于统一币制,收回货币铸造权[54]。晚清金石学家、文献学家叶昌炽曾于1903年在兰州求古书院出了三道试题,其中一题为:“问欧洲各国皆用金镑,中国用银,金贵银贱,公私漏卮甚巨。即以银币论,西人曰先令,每一先令重二钱二分。易中国银,浮于所之重数悬绝,是同一银币,中西贵贱不相敌,不变圜法,匮可立待,何策以维持之?”[55]叶昌炽作为晚清知名的学者,深知当时中国货币体系的缺陷,认为需要从货币制度上加以改革。以此为题,也是希望学子关注中国的货币问题。光绪三十四年(1908),历史学家孟森在《东方杂志》发表《上度支部论铸银币书》,开篇提到,中国的商业经营有素,然而国无币政,创巨痛深。今闻大部议改用金,议改铸银,暗自庆幸,以为国币有望。然而又听闻封疆各大臣持议不一,又不能无忧。作者深知清廷内部意见纷纭,只会造成圜法改革的延宕,并针对国币单位之争评论道,部议改铸新币,主张以七钱二分为国币,符合人民生活需求。直隶总督袁世凯斥为非计,以主权二字立论。商人则称主权之行于货币,在有不用外币之实力,不在故意排斥外币之重量,从而扰乱国内物价[56]。
实际上,晚清各省自铸银元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弥补制钱不足。因制钱的缺乏导致通货紧缩,商业停滞。因此当时亦有学者认为应采用钱票,以补制钱之不足。王瑬建议改革圜法须先发行纸币,政府一方面可以用发行的纸币从民众手中购买铜料以铸造铜钱,另一方面又可以轻便的纸币取代外国银元[57]。另有文章提到上海自通商以后,制钱之外兼用银元,一曰本洋,一曰鹰洋。初行之时,本洋每元可换钱一千二三百文,鹰洋亦可换一千百余文。近年以来,本洋不复见,鹰洋仅值一千零数十文,至今日则止值钱九百数十文。“食力之人,咸有忧色,论者皆以为奸商市侩垄断居奇,以致洋价日跌,制钱日缺。”作者主张推行钱票,以弥补制钱不足,“长江一带多有用此者,惟各分地界,彼此不能相通,究不若现钱之便”。“推广此法,可以照中西各银行规例,或由殷实商务承办,自百文以至前文票式,可与近日所行之钞票同,取其纸张坚厚,不易破坏。”[58]
《论行钞票以济钱之不足》也指出钱法日坏,而制钱日缺,“民间日用铜器繁多,奸民贪利以钱镕铜,并私铸沙钱入市行使,致钱法败坏而不可收拾。”而银两则因各地砝码不一难以通用,“至银币或锭、或锞、或零星,不过成色有高低,平砝有大小,而各省通行,并无缺乏。乃自日斯巴尼亚银圆进口,华人以其便利争相行用,于是中国银币之权为外人所侵矣。继复有墨西哥银圆进口行用更广于日银,近来日银几不一见,民间所用惟墨银,于是银币之利几尽为外人所夺。”而金本位之论,显然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形,因中国产金有限,仍摆脱不了列强的控制。因此作者认为应行用钞票,以弥补制钱不足,同时阻塞白银外流[59]。
《纵论时事》称圜法之坏,始于今日。广东、湖北、天津、福建四省铸造大小银元,难以在全国流通。中国自铸大小银元,尚不能畅行,而让英洋、香港、日本银元满布中华,而民皆乐用,原因何在?是因为中国自铸大小银元银色不及外洋银元?还是轻重不及外洋银元?主要在于使用习惯的问题[60]。并提及其友自天津到上海,携带天津局铸造银元二十枚,但上海关官员称此等银元,上海不能通用,每元须贴水五十文。因此感叹到,官员尚不肯收用本国银元,遑论小民,故而认为民众对洋银产生强烈的偏好,自铸银元于事无补。
关于改革币制和国币单位的选择,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应以两为国币单位,理由在于两为记账单位,而七钱二分银元虽在通商口岸广泛使用,但“元”并不能作为标准单位使用[61]。实际上,“两元之争”也成为清廷内部围绕国币单位形成激烈论争的焦点。宣统二年(1910)四月十六日,清廷颁布《币制条例》,规定“中国国币单位,着即定名曰圆,暂就银为本位。以一元为主币,重库平七钱二分”[62]。清廷规定的国币单位和重量,实际与流通广泛的洋银几无二致。换言之,币制改革仍以洋银的形制为蓝本。
五、结语
洋银自明末流入广东、福建沿海一带以来,逐渐取代原有的银锭和制钱,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此后逐步用于缴纳赋税。这一趋势不仅体现在沿海商埠的中外贸易往来之中,在广东、福建的农村交易市场亦可发见。与此同时,洋银逐步从粤、闽北上,流通至江、浙等省份。有别于庙堂之上各级官员或禁或放的意见,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见此情形,纷纷通过著书、日记等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
不过在康熙年间,清政府为击败郑成功集团,一度实施海禁政策,洋银流入锐减。雍正二年(1724),蓝鼎元呼吁解除海禁,理由在于海外贸易能够带来收益和中国所需的银钱。“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工针黹,皆于洋船行销,岁收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人我中土,所关为不细矣。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既禁以后,百货不同,民生日蹙。”开海贸易之时,岁入“银钱货物百十万”,沿海商民深受其利[63]。其后不久,清政府解除海禁,对外贸易再次兴盛,洋银再度大量流入。
结合前文内容来看,民间舆论对洋银流入有着不同的认知,主流看法认为洋银成色低于银锭,暗耗国人财富,造成白银外流。少部分人对洋银持正面评价,认为其适应了当时中国的贸易情形,但其声音却显得微弱。民间舆论的激烈反应说明社会层面对洋银流入导致利源外流的忧心忡忡,并多次呼吁地方政府和清廷中央积极应对,借仿铸洋银以抵制之,且从根本上改革圜法币制,以实现金融和经济上的自主。从成效来看,虽受当时认知条件的限制,但清末各省自铸银元的实践以及清政府的币制改革受到此种舆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中美贸易摩擦的缘起与对策
——一个文献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