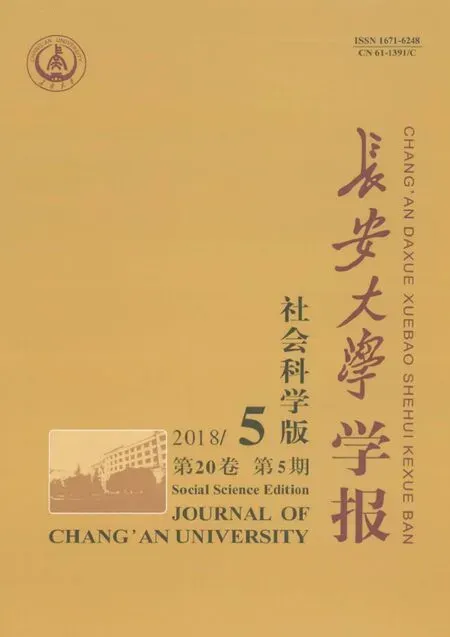中美贸易摩擦的缘起与对策
——一个文献综述
余淼杰,金洋,刘亚琳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了针对中国的大规模贸易加税。2018年7月6日,特朗普政府正式对来自中国内地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 %的关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纠纷影响着全球经济形势[1]。在这一背景下,许多研究对全球化中的中美贸易关系从诸多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尝试对这些最近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以厘清这种贸易纠纷背后的深刻经济影响因素,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期提供依据。
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缘起
此次贸易摩擦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时已经埋下伏笔。特朗普以反全球化的姿态赢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同一年,英国全民公投,决定脱欧,同样是反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这两件标志性的事件,背后是西方国家普遍的民粹主义抵制思想的高涨。
针对这一思潮的兴起,Pastor等结合全球收入不平等趋势的上涨,提出了一个增长经济体中民粹主义抵制内生出现的模型,试图从经济角度解释这一政治思想的变化趋势[2]。在该模型中,西方国家的选民有厌恶不平等的偏好,特别是厌恶高消费的所谓精英阶层。在给定的假设下,均衡时的消费是一个向右扭曲的收入分布状态。也就是说,是富人的高消费而非穷人的低消费驱动了收入的不平等,对不平等的反感反映的是对精英阶层的嫉妒,而非对穷人的同情。因此,选民致力于减少精英阶层的消费,将之视作降低不平等的最有效的方式。在一个增长经济体中,由于不同收入水平的选民风险偏好的异质性,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增长在客观上加剧了选民之间经济上的不平等。选民面对着消费水平和平等程度之间的权衡取舍。产出水平较高时,降低消费带来的损失较低,因此随着产出增加选民更加愿意牺牲消费来换取平等。也就是说,高收入国家的选民面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倾向于投票选举那些承诺终结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者。最终的结果是,民粹主义者上台,全球化走向自我毁灭。如何避免这一结局?作者分析了一系列的再分配政策,发现财富的再分配政策只能延缓民粹主义者上台的时间,但是改变不了其最终的发生。文章还根据模型推测,不平等程度越高、金融越发达、经常账户赤字越大的国家容易对民粹主义产生更强的支持。作者随后用29个发达国家的实证数据支持了这一推测。模型还预期,教育程度较低、更贫穷、更反精英的群体更有可能投票支持民粹主义。而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上台的事实正是给了这一模型较为直接的支持。他们发现,不论是在英国脱欧的投票中,还是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投票中,教育程度较低和低收入的选民都更有可能投票支持退欧和特朗普上台。
因此,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反全球化主义上升不是偶然的。无独有偶,Autor等对美国选举的实证研究发现了更直接的贸易对政治态度影响的证据。他们利用2002和2010年的国会选举以及2000、2008和2016年的总统选举,发现初始白人人口或者共和党支持者占多数的贸易冲击地区变得明显更有可能支持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人,而初始少数族裔或者民主党支持者占多数的贸易冲击地区变得更有可能支持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也就是说,贸易冲击使得美国选民政治倾向的两极分化加剧了。而在总统选举中,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越强烈的地区,在总统选举中更有可能在选举中转向更加保守的共和党人[3]。这说明,此次特朗普政府的上台和相关措施的制定,确实有其深刻的经济基础。
自由贸易对经济与福利的提升作用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上都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美国8 %的消费来自进口。根据Costinot等从需求面出发的最新估计,美国从贸易中的福利获益占到美国GDP的2 %~8 %[4]。正如Feenstra所言,贸易主要可以通过增加产品多样性、推进破坏性创造以及竞争效应降低成本加成等途径增加总体福利[5]。但其中推进企业的破坏性创造过程中,确实会涉及到新旧产业企业工人的调整问题。与贸易的总体福利作用相比,学术界和政策界争论更为激烈的正是贸易在分配上的作用,特别是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作用。特朗普总统此次发起贸易争端的经济依据主要是中美贸易冲击减少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岗位数量。但是最新的深入研究表明,这方面的依据都站不住脚。
二、中美贸易对两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针对中国加入WTO之后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影响力最大的当属Autor等研究。他们分析了1990到2007年之间中国进口竞争的上升对美国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以通勤区为单位,他们利用不同地区之间产业面临中国进口竞争的不同,识别了进口冲击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他们认为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增加造成了美国劳动力市场更高的失业率、更低的劳动力参与率以及更低的工资。根据他们的估计,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有四分之一可以被中国的进口增加所解释[6]。Pierce等也将美国2000年以后制造业就业的下降归咎于关税下降带来的中国进口的增加。基于地区间的简约式识别方法,他们的结果显示面临关税下降越多的行业经历了更多的岗位减少、更多的中国进口、更多美国进口商和中国外资出口商的进入[7]。这两个研究都将2000年以后美国制造业就业的下降与中国加入WTO之后对美国贸易的大幅增长联系起来,并引起了学术界与政策界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但是Wang等最新的研究挑战了这些结论。他们认为,这些研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中间品贸易的重要性。从2000年以来,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中间品的份额是在不断上升的。即便是制造业企业,也有大量从中国进口中间品,从而相应地实现规模的扩大。而这些中间投入品进口的增加会促进进口企业雇佣工人数量的增加,从而促进就业。因此,考虑了供应链的机制后,来自中国的进口对美国就业的影响有三种渠道:第一种是直接的竞争效应,这会降低制造业企业的就业;第二种是通过供应链作用对美国上游企业的影响,那些不直接与中国进口竞争,但是为其他美国企业提供中间品的企业被挤出,其提供的就业会相应减少;第三种则是美国的下游企业,这些企业因为来自中国的进口中间品而实现了扩张,增加了就业。其中直接的竞争效应只会影响到较少一部分行业,而下游渠道影响到的企业几乎是美国整个经济体,包括服务业。因此,尽管下游渠道是间接作用的,但是其对总就业的影响仍然可能很大。而实证数据检验发现,第三种机制确实是占主导地位的。根据他们的估计,综合三种效应,与中国的贸易使得美国各地的就业平均增加了1.27 %,并且平均有75 %的美国工人因为与中国的贸易而实现了工资的增长。也就是说,与中国的贸易增加不但没有恶化美国劳动力市场整体的就业量和工资水平,反而是促进了就业,提升了劳动力的报酬[8]。因此,与之前的研究结论截然相反,该文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贸易对美国就业,包括制造业就业的正面作用。因此,特朗普以增加美国制造业岗位为名义发起的贸易保护主义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Fort等研究同样对Autor等[6]研究提出了质疑。他们发现,从宏观趋势上看,美国制造业就业的下降从1970年代末期已经开始了,但2000年以后下降的速度确实有所加快。与此同时,美国制造业的实际增加值却几乎与非制造业GDP以相似的速率增长。也就是说,1970年代末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在稳步提升。作者随后利用美国的微观数据检验了美国制造业就业如何在不同行业、企业、地区之间流动。他们发现,企业的净退出能够解释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的四分之一,而美国制造业就业的下降是贸易与技术共同驱动的,而目前很难鉴别出每一种机制的作用大小。同时,不同制造业部门在就业下降的同时,产出水平却有升有降。整体而言,2000到2012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了25 %的同时,美国制造业的总产出却是上升的,这意味着美国制造业部门劳动力生产率相比于其他部门有着更快的上升[9]。因此,将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完全归咎于中国的贸易冲击是不严谨和有失偏颇的。
同样,针对中国贸易对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的冲击,Lee等则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出发,批评了中国贸易导致美国劳动力市场恶化的结论。在这篇研究中,他们评估了全球价值链在全球化对贸易和收入分配冲击中的传导作用。该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多国一般均衡模型,其中生产是多阶段的,不同生产阶段对应不同的生产率和不同的要素密度。模型中,异质性的工人内生选择他们工作的部门和职业,国家和工人层面的比较优势互相作用。贸易成本的下降导致了国家在其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和生产阶段进行专业化生产,从而改变了劳动力需求,导致了工人更多转移到符合他们比较优势的部门和职业中。该文将这一模型运用到2000年的美国、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模拟了中国加入WTO后中美贸易成本下降的冲击。模拟结果显示,中美两国劳动力的技能溢价都有所上升,而全球价值产业链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0]。因此,中国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对于不同技能的劳动力是有差别。美国政府更应着眼于通过再分配机制缓解内在的不平等。
除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中美贸易增长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同样发生了重要的影响。Rodriguezlopez等研究了中国加入WTO之后全方面的贸易自由化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通过构建企业层面的税收下降水平,仔细区分了国外关税、最终品中国关税以及中间品中国关税三种关税,并区分了加工贸易企业、非进口的纯出口企业、同时进行进口的出口企业以及进行进口的非出口企业。利用2000到2006年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生产率的企业岗位数量有着不同的变化。最终品关税下降会带来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下降,而对于高生产率企业,则会创造出新的岗位。而中间品中国关税下降的净效应则是低生产率出口企业的岗位流失。三种关税变化中,最终品中国关税的变化是三种关税变化中带来最多新岗位的,而外国关税的变化是造成最多岗位流失的。整体而言,最终品中国关税下降是新岗位增加的主要驱动力。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非进口和进口的高生产率出口企业是新岗位创造的主要来源[11]。与之前着眼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不同,Rodriguezlopez等首次将研究目光聚焦到中国劳动力市场,揭示了中国加入WTO以来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对劳动力市场的丰富影响。
三、贸易保护主义是一个好的应对策略吗?
虽然目前不同研究对劳动力市场整体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仍然存在争议,但是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贸易自由化进程导致了不同收入阶层的重新分配。问题在于,面对这种重新分配的结果,特朗普政府选择的反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一个好的应对策略吗?
针对贸易开放导致的不同阶层收入重新分配问题,理论上存在一种帕累托改进,使得每个个体的福利得到提升。但是这对于政策实践的意义并不显然。Lyon等试图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选择问题,他们研究了一个经济体在面对贸易自由化时应该采取的最优混合政策。他们发现,最优混合政策不是像特朗普政府目前所做的那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增加关税,而是在保持低关税的同时采用一个更加激进的累进税收系统。在这一项研究中,他们建立了一个存在摩擦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在此模型中,贸易具有基于动态的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模型发现,一个更加激进的税收体系能够有效提升整体的经济福利。最优的累进税收系统是在权衡提供社会保险的利益和降低劳动力供给与移民的成本。在模型中,累进税收制度为贸易相关的劳动力收入风险的不完全保险提供了代替品。根据模型的参数模拟结果,最优的税收体系应该是贸易开放程度每增加10 %,对最高收入群体的边际税率就应该增加5 %。而提升进口关税则不会带来任何的福利提升[12]。因此,特朗普政府采用增加关税而不更改税收制度的政策,对于改善收入分配问题并不是一个好的策略。
Barattieri等则从经济周期的角度对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提出了质疑。利用高频的贸易政策数据,他们分析了这些暂时性贸易壁垒的动态作用。国家层面的面板VAR分析结果显示,贸易保护主义扮演了负面的供给冲击角色,导致了短期的产出下降与通胀的上升。对于缩减贸易赤字,保护主义的作用非常小。同时,他们还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探索贸易保护主义的作用。模型的基本结论是,即使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能够轻微改善贸易赤字,其代价也将是经济的衰退。其作用机制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的更高进口价格将成为推动通胀上升的主导力量,而关税导致支出转向国内的可贸易品,国内市场份额更多偏向低效率的国内生产商,从而降低了整体生产率。更高的国内价格降低了总的实际收入、更低的固定资产投资与生产创造[13]。此外,央行对于上升通胀的政策反应也会加剧对经济衰退的刺激。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几乎在所有情形下都不是刺激宏观经济的有效工具。
给定美国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应对策略决定了此次贸易摩擦对各国的福利影响。Guo等基于Eaton-Kortum的多国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表明,如果美国政府兑现特朗普竞选总统时宣称的对中国进口采取45 %的关税增加政策,那么国际贸易将会遭受巨大的负面影响。文章研究了中国或世界其他国家采取相应加税措施和不采取加税措施四种情形下的影响,发现无论哪种情形,美国都会遭受巨大的福利损失,而中国的损失相比于美国则小得多[14]。因此,中国在面对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时,有更大的政策空间。
四、结语
综合这些前沿研究的结论,我们可以理解特朗普政府诸多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产生的民意基础,也从理论和实证上说明了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上半年针对中国提出的大规模加税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缺乏科学基础的。全球化从客观上加剧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但是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应对这一问题无异于因噎废食。治本之策仍然在于建立更有效的再分配机制,使全球化带来的整体福利提升惠及到低收入阶层。而不论美国特朗普政府此次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前景如何,中国将遭受的整体福利影响都会有限,我们因此有理由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开放形势抱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