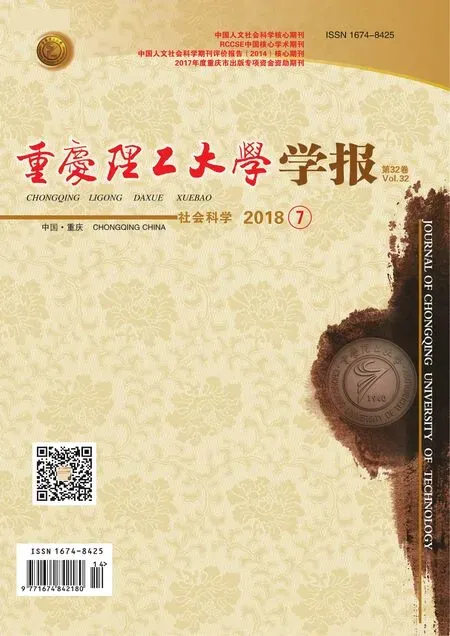文学新奇性的认知进化阐释
——以埃德加·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为例
杜 坤,李健宁
(1.四川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 重庆 400031; 2.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湖南 韶山 411301)
文体、形式和内容的创新一直以来是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看重的问题。20世纪初,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因强调文学艺术的新奇性、呼吁作者让作品新奇化而成为现代主义的传奇人物。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维克托·鲍里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和读者接受理论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 同样强调文学新奇性的重要性。诗人、小说家、评论家爱伦·坡(Edgar Allan Poe)早在100多年前也发表了类似观点。但是,单单是爱伦·坡、什克洛夫斯基、庞德、姚斯的观点并不足以证明对文学新奇性的推崇是现代化进程产生的文化现象,文化因素与认知进化因素的共同作用才是促进文学创新的持久动力。
一、文学新奇性的认知阐释
人类为新为奇所吸引的特性具有进化方面的证据。认知心理学家斯蒂芬·卡普兰(Stephen Kaplan)指出从进化论角度看,所有物种中只有人类是以知识为导向,并且找寻它、利用它。人类作为广泛的信息采集的物种,与其说占据地理上限定的栖息地为人类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受限的信息形式,不如说人类进化为寻路人(wayfinder),带着一种特殊需要在环境中仔细辨认符号,尤其是辨识出已知的,察觉出异常的和稀有的[1]581。所以,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不断对新环境中不熟悉的方面进行评估。同时,以知识为基础对领地予以评估将人类从本能的、自动的反应和受到地理严格限制的栖息地中解放出来,这不可避免地使他们接触新的环境,而原有的知识就显得很有限。然而新环境不仅蕴含着很多未知的机会,也存在很多潜在的危险,所以人类怀有一种矛盾心理:既寻求新东西又回避新东西、回避难以理解的东西[1]585。
但是与其他物种不同,作为一种独特的寻路(wayfinding)物种,人类通过一种松散的、持续进行的思维-行为模式去组织经验,这种模式从根本上说是叙事[2]621。叙事结构有内在复杂性,有内在的人类对环境的认知关系。在这种抽象情境模式中,人类有能力认识到在因果框架中运作的人物。这些人物虽然并不与自身相符,但是可以识别出他们作为施事的动力,评估和预测他们的相关行为。所以,我们人类对叙事有认知偏好,例如偏好连续的、因果关联的事件,偏好机制相似的人物心理观念,若打破或者颠覆叙事结构,也就意味着挑战人类的认知习惯和偏好。
作为认知产品的文学作品是人类体验新奇事物的媒介,由于人类偏好新事物但又回避陌生环境,因此阅读文学作品既可以接触新颖事物,又可以避免直接的威胁。书面文学的出现和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中的文化发展促使新奇事物抢占先机,而且书面文学具有的复杂叙事结构,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这与我们进化的认知有着独特的关系。书面文学作品测试我们对叙事组织的偏好、对既定主体地位的偏爱、对社会关系的既定理解、加工熟悉的环境现象所需的几近无意识的能力和我们对已经建立的社会关系的感知[3]152。所以,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解释性认知模式,可以通过新奇性来表达其真实的独特性。文学阅读的认知进化模式,以解读寻路的人类(wayfinding humans)的心智过程为基础[2]615,为文学新奇性提供了解释[4]。
文学新奇性的中心地位在文学批评和心理学中也有广泛的基础。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到20世纪中叶,心理学家在动物和人类行为研究中发现习惯化(habituation)在很多物种中都随处可见,在一系列的感知、认知模式上也随处可见。心理学家理查德·汤普森(Richard F.Thompson)和丹尼斯(Dennis L.Glanzman)指出,如果适度刺激一个有机体,最初的反应会重复,之后就不会再有回应。这可能是最简单的学习形式,学习不回应[5]49。也就是说,如果习惯化使每天的刺激过程短路,注意力就集中在不可预知的、异常的和稀有的事物上。所以说,习惯化把认知活动集中起来以应对新奇事物。那些看惯了的、看多了的事物就变得平淡无奇了,这就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谓的“无意识化”。心理学家还认为感知习惯化导致感知自动化,什克洛夫斯基对此表示赞同,并认为“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使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6]11。虽然习惯化提高了对日常事物的加工效率,但是又会导致自动化、半意识化,只有新奇才能将其打破。这也就是陌生化一直强调的,文学艺术的宗旨是让熟悉的变得奇特,让日常的变得陌生,换言之,即不断更新人们对于审美对象的陈旧感觉,摆脱习以为常的机械化、自动化的控制和制约,使人们即便是面对熟视无睹的对象也能有新的感受和体验,从而感受到对象的非同寻常,产生审美愉悦。
什克洛夫斯基的观点与美国新批评学派的观点一致,认为语言的特殊使用将文学话语和日常话语区分开来,20世纪70年代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什克洛夫斯基的观点逐渐被边缘化。然而文学新奇性以及其产生的审美效果却从未过时。正如心理学家科林·马丁代尔(Colin Martindale)认为,“新奇性是一种有活力的、内置的艺术规律”[7],皮尔(Willi van Peer)进一步强调,“文学作品经典化不单单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基于语言、形式、观念新颖性的持久过程”[8]。姚斯同样强调新奇是真文学的特征。他认为:“一部作品在诞生的历史时刻,以某种方式满足、超越、辜负或驳斥它最初的读者,这种方式显然为确定其审美价值提供了一种标准。”[9]31每一部作品都会激起读者一定的期待,这种期待可能与作品的艺术水平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在姚斯看来,通俗或娱乐性艺术作品对读者来说不需要视野变化,因为它们根据大众流行的标准实现了人们的期待,这样的作品的审美价值就比较低。相反,优秀的文学作品超出了读者的期待,打破了人们认识事物的原有方式,因而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尽管什克洛夫斯基强调个人感知的变化,姚斯强调艺术变化的社会历史维度,但二人都侧重于读者的角色和文学新奇性的重要性。文学作品是一个认知对象,只能在阅读过程中完全实例化,因而关注读者的认知变化和阐释文本的新奇性是文学理论不可或缺的。文学阅读的认知进化视角,将文学感知的基础定在寻路人类的心理程序上,为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概念和姚斯的视野期待理论提供了解释。
二、爱伦·坡短篇小说的新奇性特征
爱伦·坡的文论《创作哲学》中有这样一段话深刻表明了他创作的目的性:“由于始终把故事的独创性放在心上,我总是在动笔前就问自己:于此时此刻,在无数易打动读者心扉、心智或心灵的效果中,我该选择哪一种呢?首先选好一个故事,然后选定一种强烈的效果。”[10]662大多数评论家关注的是爱伦·坡调动一切可利用的素材和想法去达到他预设的作品应该表达出的效果,即“效果统一论”。其实,过多地关注作品产生的效果,往往忽视了效果来源于作品的创新。与其说爱伦·坡的创作原则是追求效果统一,不如说其创作初衷是凸显“故事的独创性”,因为他在《创作哲学》中同样强调“我的首要目的是创新”[10]664。爱伦·坡注重的是“打动读者心扉、心智或心灵的效果”。也就是说,爱伦·坡认为读者才是作品创新性和新奇性的裁判者,作家对作品任何形式的创新都需要读者的认可。爱伦·坡的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历久弥新,原因在于他心目中的创新不是一味地编织、虚构离奇故事,而是打破人类的认知、心理和思维规律,所以任何时代的读者都会被其作品的新奇性所吸引。笔者将从哥特文化、叙事方式、语言形式三个方面探讨爱伦·坡短篇小说的新奇性特征。
(一)哥特文化的创新
从整个文学史的演进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民族的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文学样式,而且后来的文学样式既是对前面传统文学样式的继承,也是对传统文学样式的超越。一些通俗的、民间的、边缘的非主流文学逐渐向时代的主流文学趋近,最终在特定时期成为人们接受的主流文学。诞生于18世纪的哥特小说由英国传到美国,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化历史等因素发生了诸多变化,在美国浪漫主义时期得到迅速发展,素有“黑色浪漫主义”之称,可以说是美国浪漫主义的一个偏离,并在一次次的偏离中得以生存和发展:感伤型哥特小说、恐怖型哥特小说、恐怖小说、现实恐怖小说、侦探小说、黑色悬念小说、哥特言情小说等。正是这种文学史上的大偏离,与当时美国文学浪漫主义鼎盛时期的文学创作风格格格不入,使得哥特小说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次革新,打破了读者对传统浪漫主义时期作品的普遍认识,并由于其新奇特色得到大众的广泛接受。
而在从事哥特小说创作的美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家中,爱伦·坡被公认为“心理哥特的鼻祖”。爱伦·坡曾说:“在我的众多作品中恐怖是不变的主题……它来自心灵,也就是说,我的恐怖来自于正当的源头,并用其完成正当的目的。”[11]1所以他的短篇小说探索人类的心灵世界,善于表现人的思想病态。爱伦·坡认为,按照人类最普遍的理解,在所有忧郁的题材中最忧郁的题材是死亡。所以在他的恐怖小说中,有《黑猫》(TheBlackCat)和《泄密的心》(TheTell-TaleHeart)中的心灵变态、虐待致死,《陷坑与钟摆》(ThePitandthePendulum) 与《厄舍府的倒塌》(TheFalloftheHouseofUsher)中的监禁和活埋,也有《丽吉亚》(Ligeia)中的美女死后复生,还有《红死魔的面具》(TheMasqueoftheRedDeath)中的逃不过的咒语和宿命。死亡在传统的哥特小说中是常见的,但是爱伦·坡笔下的非正常的痛苦和死亡,利用人类原本对死亡恐惧的特殊心理,进入到人的潜意识领域,从而揭示人类最隐秘的内心世界,展现人类最原始的认知本能。爱伦·坡对哥特小说的创新使得读者对传统哥特小说的认知受到了强烈冲击,读者真正体会到了追逐心灵恐怖的震撼和新奇。
(二)叙事方式的创新
打破读者对叙事方式的认知偏好也是爱伦·坡所追求的不同寻常的效果。对叙事者的选择、对叙事结构的安排和对叙事时空的设定,都是他努力探索震撼心灵效果的各种方法,为的就是使读者对故事的叙事产生新奇的感觉,紧紧扣住读者的心弦。
1.“否定”叙事者
爱伦·坡在短篇小说创作中多运用第一人称叙述,由“我”来讲故事,从而拉近了叙述者与故事的距离,更能给读者一种真实感。但是在其中一些作品中,比如《黑猫》《泄密的心》和《一桶白葡萄酒》(The Cask of Amontillado)中,在故事还没有开始时,叙述者就自行否定了故事的真实性。历来的小说家都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强调故事的真实性,或强调故事在生活中曾经发生过,而读者也往往把是否真实作为一种评价标准。爱伦·坡的大胆而冒险的行为,究其原因是他希望通过对“真实性”的“否定”而获得读者的好奇。这样,读者与有缺陷的叙事之间对抗产生的新奇感觉就会相当强烈。在阅读过程中,叙述者或者小说人物是读者的代理,为读者对故事世界的感觉建构和意义建构提供一个基本点,从叙事一开始读者的代理自我就能建立起来,换句话说,读者需要叙述者和人物的指引,这样他们建立的代理自我才能在文学环境中定位。爱伦·坡笔下的“我”作为作品的叙述者和人物,其真实性问题在本质上阻碍了叙事。虽然不可靠叙述让读者对叙述者作为向导和事件的解说者感到矛盾,但是读者仍可以开发一个可疑叙述者角度,在追踪故事的同时判断故事。若读者相信故事的真实性,就会感受到叙述者或小说人物变态的心理;若读者不相信,就会认为是一个神经病的疯语。但是,无论读者相信与否,作品留给读者去识解的信息与作者拒绝给读者提供方向指导阅读的这种分离,最终挫败读者阅读的习惯反应,从而引发额外的意义,但也让读者慢慢领悟到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为了使作品产生新奇效果而做的尝试与努力。
2.打破叙事结构
打破原有叙事结构,延缓叙事进程,阻碍读者叙事结构建构,从而使读者丧失一个连贯的定位角度,也是爱伦·坡叙事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嵌入一段独立的诗歌、故事或新闻报道,把直接叙事模式和其他模式结合起来,模式间的自由切换消解了统一意义上的叙述者。叙事进入偏离,读者若依据认知偏好,可能会期望重新回到原来的叙事中,因为原来的叙事作为情境支持能继续建构读者的叙事模仿;也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在插曲上,重新进行认知加工,建构新的叙事模仿,但是无论读者偏向何种方式,嵌入的部分都会破坏读者形成有序叙事解释的能力。尽管这样,读者仍会被这种新奇的叙事模式吸引,不断挑战自我的阅读思维习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爱伦·坡对自己的诗歌十分看重,小说中时常插入诗歌。比如:在《厄舍府的倒塌》中插入了一首厄舍即兴演唱的《闹鬼的宫殿》(TheHauntedPalace),暗示读者“邪恶”已经侵入了他的思想;在《丽姬娅》中插入《征服者爬虫》(TheConquerorWorm),把丽姬娅在临死时的绝望和恐惧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此外,《幽会》(TheAssignation)中引用了奇切斯特主教的诗句,《绝境》(APredicament)中引用了塞万提斯、阿里奥斯托和席勒的诗句。虽然诗歌的嵌入影响读者的叙事模仿进程,但是读者也会认为这种形式很新奇,并从侧面解读主人公的情感和心理状态。
除了嵌入诗歌,另一种比较常见的就是蕴含故事。《椭圆形画像》(TheOvalPortrait)在“我”的故事中又包含了一个风格迥异的故事:一个故事从容冷静,体现军官的理智;另一个则杂乱疯狂,体现艺术家对艺术的狂热。如《莫斯肯漩涡沉浮记》(ADescentintotheMaelstrom)中“我”和老人的故事中插入了一段老人回忆当年和兄弟经历莫斯肯大漩涡的故事。作者用引号将插入的故事标注出来,以便吸引读者的目光,也便于读者识别。而且在篇幅上,插入的故事与“我”的故事平分秋色,并沿着叙事进程迅速推入高潮,所以也能更加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关注。
在侦探推理小说中爱伦·坡喜欢插入新闻报道。在《莫格街谋杀案》(TheMurdersintheRueMorgue)中插入了两条关于案件的新闻报道,《玛丽·罗热疑案》(TheMysteryofMarieRoget)中插入了12条新闻报道用来提供案件的信息。这两篇侦探小说都取材于当时的社会新闻,由新闻报道和杜宾的推理分析支撑起小说,其中杜宾的推理又建立在新闻报道的基础之上,这种近似于记事的新闻叙事中嵌套新闻的形式,有助于增强故事的真实性。一方面满足同时代读者对案件真相窥探的欲望,在紧张与期待、探索与满足中获得审美体验;另一方面也使读者看到爱伦·坡注重的不是现场侦查和捉拿凶手,而是推理过程,他开创的侦探推理之风也是其创新的一大亮点。
3.颠覆叙事时空
由于人类的认知偏好,处理文学作品和一切事物一样,在基本的意义构建过程中优先将信息合并入因果模式,并依赖于因果关系的推理过程把信息同化入叙事模式。因为按时间顺序安排的叙事功能强大,不可或缺,所以这种时序若被打破,再习惯它就非常困难。在爱伦·坡的创作中,不仅要求文学作品的篇幅不能太长,重视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对时间的体验,而且在文本中巧妙地处理了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打破读者的认知习惯,让读者在错综复杂的时间关系中对故事产生多重猜想,丰富了读者的心理空间。
爱伦·坡的大部分小说都采用事前叙事手法。首先把事件结果展现出来,引起读者对神秘事件的好奇,再把读者放在迷宫般的情节中,最后再揭晓事件的来龙去脉。其中一类是叙述者“我”或故事中人物回忆自己的过去,比如《威廉·威尔逊》(WilliamWilson)、《莫斯肯漩涡沉浮记》《厄舍府的倒塌》《泄密的心》《黑猫》《一桶白葡萄酒》等。另一类是侦探小说,如《莫格街谋杀案》《玛丽·罗热疑案》《窃信案》(ThePurloinedLetter)、《金甲虫》(TheGold-Bug)、《就是你》(ThouArttheMan)。爱伦·坡的创作意图使得他早已经设计好故事的每个环节,因此故事中每个步骤的描写必然不是毫无来头的赘述。而他却在叙事过程中暂时让某段叙事时间出现关键性的缺口,那么面对结局而对过程一无所知读者就具有了阅读动力。虽然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认知偏好,以便应对时间顺序和因果顺序的错乱,但是为了满足对作品的好奇,也会在后续的阅读中不断填补空缺的时间,从而将叙事模仿中的各个事件井然有序地串联起来,小说叙事时间逐渐变得封闭、完整。
叙事文本中空间和时间有着同等重要的价值。对于生活在城镇中的普通读者来说,传统的哥特式建筑在日常生活中是极少接触到的,所以在爱伦·坡的小说中,传统哥特罗曼司的巨大性消失了,巨大的城堡、教堂或大古宅被压缩成贵族宅第,或更小、更压抑的卧房、书房或地窖,正如冗长的哥特罗曼司被爱伦·坡短小精悍的故事所代替了一样[12]。对于读者来说,古宅的荒凉和阴郁、地牢的黑暗和阴森再熟悉不过,爱伦·坡的古宅和地窖就会让读者产生无限的遐想。爱伦·坡的“房间”窄小封闭,诡异奇幻。《丽吉亚》中的丈夫在房间中陪伴着一具尸体,不断产生幻觉;《斯蒂芬克》(TheSphinx)中“我”因为躲避霍乱来到一个朋友的别墅,却喜欢整日坐在书房里;《红死魔的面具》《泄密的心》和《窃信案》的杀戮也都发生在房间里,而且《莫格街谋杀案》首创了“密室谋杀”模式,大侦探杜宾却偏爱在黑暗的卧房内思考问题,对案件进行分析。在读者看来,卧室、书房作为私密性场所,承载着个人生活的绝大部分,通常意义上给人们带来安全感。尤其是卧室,是人们休息的地方,主人公在房间内发生各种各样的恐怖事件,使得书房、卧室既变成了恐怖事件的案发现场也成为了案件侦破的场所,在读者看来,叙述者的故事犹如噩梦缠绕着主人公。同时,爱伦·坡在这样安静舒适的空间内创造出几乎令人窒息的气氛,并利用人的心理误区和错觉诱导读者产生恐惧心理,也极大地颠覆了读者的思维习惯和接受极限。
(三)语言形式的创新
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作家的语言作为一种渠道,能够让读者在阅读时接收足够多的信息,引导读者改造文本中的意象,排除不恰当的解读,寻求更适合的阐释途径;同时,读者用自身的经验去填充、丰富文本中的语言信息,激发想象力,唤起读者对生活的思考。所以说,语言所激发出的联想意义要比读者原先所接收的信息量要大。
在爱伦·坡的作品中,首先,大量色彩黯淡、表现心理刺激和情绪不安反应的形容词被用来渲染阴森气氛和恐怖效果,例如《泄密的心》中hideous heart、 dreadful silence、 terror、 horror等; 《红死魔的面具》中scarlet horror、 Courage of despair、 delirious、 countenance of stiffened corpse等;《厄舍府的倒塌》中dark、 dreary、 vacant、 rank、 bleak、 decayed、 shadowy、 black、 lurid、gray、ghastly、dull等。这些形容词使恐怖的意象变得清晰,成功地将阴郁的色调投射到客观物体上,使读者的心理情感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进而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其次,爱伦·坡大量使用具有否定意义的词。例如,《红死魔的面具》中直接否定词(no、not、nor、none以及带有un-、-less等否定词缀的词)的运用达到35处。《厄舍府的倒塌》中同样运用了大量的否定词,以 un-为否定词缀的词共出现43次,以-less为否定词缀的词共出现4次,以 dis-为否定词缀的词共出现21次,以 in-为否定词缀的词共出现90次。这些否定词消极、反面的意义色彩投射给读者一种灰暗的心理暗示。再次,爱伦·坡还用了很多拟声词。例如《一桶白葡萄酒》中的Ugh! ugh!…Ha! Ha!…He! He!…等等,有时甚至是一长串的拟声词,这些声音让读者感受到歇斯底里的人发出的垂死挣扎,也可能使读者自己产生一种被人扼喉的心理错觉,恐怖的氛围不言而喻。最后,爱伦·坡频繁使用一些标点符号,在现代短篇小说中也是罕见的,例如在《泄密的心》中使用了68个破折号,是他的其他恐怖小说所没有的。不仅如此,破折号与感叹号连用多达10 处,而且破折号还分别与逗号、分号和双引号连用。所以仅从文本形式上看,破折号使用密度之大使整个文本趋向碎片化,而且愈近结尾,破折号、感叹号出现得愈加频繁,文本愈显破碎。
除此之外,爱伦·坡还善于使用谐音、借代、隐喻等修辞手法美化语言。所以说,爱伦·坡通过高度凝练的语言形式,体现他对小说情感的集中把握,而且通过细致入微的描写,把主人公精神自我崩溃的痛苦过程、人头脑中的下意识状态以及正常生活下的人的非正常心理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大大扩大了读者的想象空间,其笔锋所指之处往往是他人难以触及的人类心灵的幽暗与隐秘之地。
三、 结语
爱伦·坡在美国浪漫主义时期的大文化背景下对哥特文学进行大胆革新,使哥特小说的恐怖内向化,使恐怖有了质的变化,从意象的感官刺激变为心灵式的恐怖。所以说,爱伦·坡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是第一个开掘人类意识最深处幽暗领域的人。他创新的目的是为了向读者演绎恐怖的合理源头在于人的心智,深入开掘人类潜意识领域中最幽暗之处,并营造出一种震撼人心的恐怖效果。爱伦·坡正是抓住了人类共同的心理特征和认知偏好,所以在创作中才能把握住合适的机会不断地挑战不同时代读者的心理,从而使读者从他的作品中体会到人性中恶的恐怖和对虚无、死亡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