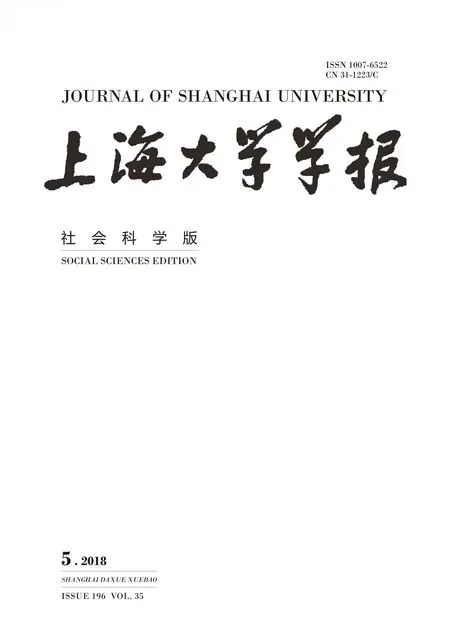文本的衍变:《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辨证
徐建委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872)
从知识史的连续性角度来看,东汉中后期至西晋末年的经史注释,多是后来此类著作的渊薮。以汉末魏晋时代的注释为主要资源的经史注本,也是唐以前经史主流传本的主体。西汉经学的辉煌,从注本当中是很难得见其大概的。反而汉末魏晋大儒的成就,多可从《五经正义》一类的著作中窥其仿佛。《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这一时期比较特别的一部,原书已佚①《四库提要》曰:“原本已佚,此本不知何人所辑,大抵从《诗正义》中录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295页。)今传本二卷,《隋志》、新旧《唐志》载为二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均载录,亦为二卷,马端临《文献通考》亦载二卷,明清书目亦多载录,故不知何时亡佚。。《毛诗正义》《齐民要术》《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尔雅疏》等书有数量可观的引用,或题“陆机《疏》”,或题“《毛诗义疏》”,或题“《诗义疏》”,或题“陆机《毛诗疏义》”,异文颇多。但其内容基本相同,都是对《毛诗》草木、鸟兽、虫鱼一类的训诂。虽然不能确定这些典籍是否直接征引了《草木疏》,但可以确定,这些引文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此,因此可以将诸书所引笼统的称为陆《疏》。关于陆《疏》的研究,其实不多。毛晋《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焦循《陆玑疏考证》、丁晏《校正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等大概是比较仔细勘对引文或详加考证的著作,若再寻专门研究,则相对少见。①名物学著作亦以《草木疏》为基础,而一般性的研究论文可以比较容易查阅,此处不作赘述。
这部分散在各书之中的陆《疏》,前人多径直称其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记其作者为陆玑。但是,问题至此并不明晰,其作者、书名、体例样式、文本衍变等疑问,略略翻检诸文献就可发现。这些疑难,自然不能轻易放过,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毛诗》研究的诸多方面。它们甚至可以帮助我们熟悉魏晋学术的某些相对具体的问题,比如知识风格、文本结构、流传特点等。鉴于此,本文以《毛诗正义》《齐民要术》《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著作的陆《疏》引文为主,对此书的诸多疑问试做简略之考释。
一、《毛诗义疏》还是《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有关《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第一个大的疑问是:《齐民要术》《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引用的陆机《毛诗义疏》,是否就是《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齐民要术》《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经典释文》《毛诗正义》等典籍引用的陆机《疏》,内容基本一致,有三种不同的征引类型或方式:
其一,《齐民要术》、《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书引用条目、文字内容非常一致,以《御览》最近全面,其他诸书所引几乎都可与《御览》所引对勘。题曰“诗义疏”“毛诗义疏”“毛诗疏义”“义疏”或“疏”。《齐民要术》不署作者,《类聚》《御览》题为“毛诗疏义”者,多署陆机。
其二,《经典释文》所引文字极简,题曰“草木疏”,《序录》称作者为陆玑。
其三,《毛诗正义》引文如第一种情形,比较详细,但与第一种相对勘,发现异文较多,题曰“疏”;或不题,径作“陆机云”。
前人多以上述类书、农书所引《诗义疏》即陆机《草木疏》。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逐条对比《要术》与类书、《正义》引文的异同,认为《诗义疏》并非《草木疏》。其依据主要在异文上。如《要术》卷四《种栗第三十八》引《诗义疏》曰:
蓁,栗属。或从木。有两种:其一种,大小枝叶皆如栗,其子形似杼子,味亦如栗,所谓‘树之榛栗’者。其一种,枝茎如木蓼,叶如牛李色,生高丈余;其核中悉如李,生作胡桃味,膏烛又美,亦可食噉。渔阳、辽、代、上党皆饶。其枝茎生樵、爇烛,明而无烟。(a)[1]296
《太平御览》卷九百七十三“榛”条曰:
《毛诗·邶柏舟·简兮》曰:山有榛,隰有苓。
陆机《毛诗疏义》曰:山有榛,枝叶似栗树,子似橡子,味似栗。枝茎可以为烛。(b)
《毛诗·墉柏舟·定之方中》曰:树之榛栗,椅桐梓漆。
《诗义疏》曰:榛,栗属,有两种。其一种大小皮叶皆如栗,其子小,形似杼子,味亦如栗,所谓“树之榛栗”者也;其一种枝茎如木蓼,生高丈余,作胡桃味,辽代上党皆饶。(c)[2]4313-4314
《毛诗正义》亦引此条:
陆机云:“栗属,其子小,似柿子,表皮黑,味如栗。”(d)[3]101
我对相关的四条引文标上记号,以便论述。不难看出,a、c基本一致,二者属同源文献,b和d应是对a、c的简化版本,很可能也是同源文献。d描述的“表皮黑”,a和c是没有的,显得不同。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默认d是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故b也应该是此书。b、d和a、c差异大,a、c有题曰《诗义疏》,故他判断《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和《毛诗义疏》不是同一部著作。但是,从写、抄本时代的书籍书写流传情况分析,同一源头的文献形成上述四个不同写本的可能性还是最大的。依据后世抄录中的异文判断源头文献样态的做法并不可取。
不过,《太平御览》同一条目下接连征引陆机《毛诗疏义》和《诗义疏》,且文字大异,确可说明以陆机名物解释为基础的疏,不只一部。《太平御览》是以《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为基础的类书,这一条目很可能是抄录自不同的两部类书而成。两部类书对同一源头文献的处理不同,故出现了两种引文方式。但《御览》所引b与《正义》所引d的简化方式一致,《正义》所引陆机《疏》与类书是没有关系的,这说明唐以前在“榛”字的解释上,确实存在一种简化版本的陆机疏。明确而言,《要术》、《御览》所引《诗义疏》很可能与《正义》所引陆机《疏》不同。
这种痕迹还有很多,又如《齐民要术》卷五《种竹第五十一》“笋”条引《诗义疏》曰:
笋皆四月生。唯巴竹笋,八月生,尽九月,成都有之。篃,冬夏生。始数寸,可煮,以苦酒浸之,可就酒及食。又可米藏及干,以待冬月也。[1]361
《毛诗正义》于《大雅·韩奕》之《正义》引陆机疏云:
笋,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笋,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长数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3]682
《正义》所引虽与《要术》所引同源,但少了“篃”的部分,意思就不一样了。《要术》条介绍了两种竹笋,但《正义》合并了两种解释,实际是弄错了。《正义》与《要术》、《御览》之间的这种文本差异的几乎是整体性的,只不过各条目差异的程度有大小不同罢了。这种文本差异若仅数条,则可能是传抄之误,但整体上都如此之大,则说明《要术》与唐宋类书所引的《毛诗义疏》与《毛诗正义》所引的陆机《疏》不是同一文献。
再者,若二书对同一植物的解释有不同,则更不可能是同书异名了,《齐民要术校释》正好举出了这样的例子。《要术》卷十《藄九一》:
《诗疏》曰:“藄菜也。叶狭,长二尺,食之微苦,即今英菜也。《诗》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英。’”(一本作“莫”)①案缪启愉考证,此处“英”应作“莫”。详见《齐民要术校释》卷十,第829页。
缪启愉《校释》曰:
“藄菜”,是《诗义疏》就《诗经》的“莫”作解说,莫就是藄菜。但《汾沮洳》孔颖达疏引陆机《疏》解释有不同:“莫,茎大如箸,赤节;节一叶,似柳叶,厚而长,有毛刺。今人缫以取茧绪。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为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谓之‘酸迷’,冀州人谓之‘干绛’,河汾之间谓之‘莫’。”则是指蓼科的酸模(Rumexacetosa)。[1]829-830
即《毛诗义疏》释“莫”为“藄菜”,而《正义》引陆《疏》则以为是“酸模”。如此,至少这一条批注显示《齐民要术》所引《诗义疏》与《毛诗正义》所引陆机《疏》并非同一文献。
以上是从文本差异上做出的判断。更为重要的是,《毛诗义疏》中有许多只有晋以后才会出现的表述,这显示作者至早是晋人,而非吴人。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在著录《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之时,就提到了此书引用郭璞《尔雅注》的问题:“其名从玉,固非晋之士衡。而其书引郭璞注《尔雅》,则当在郭之后,亦未必为吴时人也。”[4]于是径题曰“唐陆玑”。《四库提要》云:“夫唐代之书,《隋志》乌能著录?且书中所引《尔雅注》,仅及汉犍为文学、樊光,实无一字涉郭璞,不知陈氏何以云然。”[5]因有了电子文献,故检索方便,陈振孙所谓陆《疏》引郭璞之说,确可检索到。但不在传世辑本之中,而是在类书中。《太平御览》卷九七九引陆机《毛诗疏义》曰:
菜葑①疑误“葑菜”为“菜葑”也。,芜菁也,郭云今崧菜也。可食,少味。[2]4339
陆德明《经典释文》之《毛诗·谷风释文》曰:
《草木疏》云芜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3]89
《御览》明显作为一条,而《释文》则不确定。陈振孙所见文本,当如《御览》,故有《草木疏》引郭璞《尔雅注》之论。《毛诗正义》亦引此条,并无郭璞注:
陆机云:“葑,芜菁,幽州人或谓之芥。”[3]90
其实,今本《尔雅·释草》无“葑”字,只有“须,葑苁”一条,亦无郭璞此条注释。《毛诗正义》于《谷风正义》对“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及《毛传》“葑,须也。菲,芴也。下体,根茎也”有详细的名物考释,繁引如下:
《释草》云:“须,葑苁。”孙炎曰:“须,一名葑苁。”《坊记》注云:“葑,蔓菁也,陈、宋之间谓之葑。”陆机云:“葑,芜菁,幽州人或谓之芥。”《方言》云:“蘴荛,芜菁也,陈、楚谓之蘴,齐、鲁谓之荛,关西谓之芜菁,赵魏之郊谓之大芥。”蘴与葑字虽异,音实同,即葑也,须也,芜菁也,蔓菁也,葑苁也,荛也,芥也,七者一物也。
《释草》又云:“菲,芴也。”郭璞曰:“土瓜也。”孙炎曰:“葍类也。”
《释草》又云:“菲,蒠菜。”郭璞曰:“菲草,生下湿地,似芜菁,华紫赤色,可食。”陆机云……[3]90
《正义》引《尔雅》名物考释的通例是在《尔雅》文字后,再引郭璞注,如引文第二、三两段。但在《释草》“须,葑苁”后并没有引郭璞的注,说明《正义》或《正义》所据刘炫《毛诗述义》所见《尔雅注》已经出现脱文。今本《尔雅》及《尔雅注》的祖本乃是唐《开成石经》,因此其源流至迟可以追溯到唐代。鉴于《正义》的性质,可以认为隋唐之际的主要《尔雅注》传本中,此条文字的郭璞注已经亡佚。那么,《太平御览》所引陆机《毛诗义疏》中的郭注,就不可能是宋以后补入,也不会是源出《艺文类聚》和《文思博要》的部分,应是承袭自《修文殿御览》。《修文殿御览》又多据梁《华林遍略》而来。
这样看来,《御览》中的这条陆《疏》,的确可能是梁代文献的原始样貌。故南朝的某部主流《毛诗义疏》中确实征引了郭璞的《尔雅注》。隋唐之际的《经典释文》因与《御览》所引文字几乎全同,恐怕也不是巧合。
又,《齐民要术》卷十“土瓜”条所引《诗义疏》亦有郭璞注:
《卫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毛云:“菲,芴也。”《义疏》云:“菲,似葍,茎麤,叶厚而长,有毛。三月中,蒸为茹,滑美,亦可作羹。《尔雅》谓之‘蒠菜’。郭璞注云:‘菲草,生下湿地,似芜菁,华紫赤色,可食。’今河南谓之‘宿菜’。”[1]803
《毛诗正义》于《谷风正义》亦有此条:
《释草》又云:“菲,蒠菜。”郭璞曰:“菲草,生下湿地,似芜菁,华紫赤色,可食。”陆机云:“菲似葍,茎麤,叶厚而长,有毛。三月中,烝鬻为茹,滑美可作羹。幽州人谓之芴,《尔雅》谓之蒠菜,今河内人谓之宿菜。”[3]90
《太平御览》卷九九八所引与《正义》基本一致,都没有郭璞注,故缪启愉校释怀疑《齐民要术》“土瓜”条所引郭璞注是后人插进去的。这个判断应该是对的。
至此,能够初步判断《毛诗义疏》征引郭璞《尔雅注》的材料也就仅有一条而已。不过陈振孙言之凿凿,似其所见之《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确有引录郭注之处。
另外,一些《诗义疏》的文字也从侧面佐证这些具体条目确有后代书写或抄录的痕迹。我们看《太平御览》所引的如下诸条《毛诗义疏》:
《毛诗义疏》曰:蒲,周礼以为菹。……今吴人以为菹。[2]3890
《诗义疏》曰:鹤,大如鹅,……今吴人园中及士大夫家皆养之,鶏鸣时亦鸣。[2]4060
《毛诗义疏》曰:鹭,水鸟。好白而洁,故谓之白鸟。……今吴人亦养之,好群飞行。[2]4109
陆机《毛诗疏义》曰:“椒聊”,聊,语助也。椒树似茱萸,有针刺,叶坚而滑泽。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煮其叶,以为香。[2]4253
吴人的称呼,是一种外在视角,也可以说是全局视角,这至少暗示作者不是一个以吴国为其“想象世界”中心的人。或者说,至少不是吴国时期的陆机(或陆玑)。上引第三条见于《太平御览》卷九二五,其后文又曰:“楚成王时,有朱鹭,合沓飞舞,则复有赤色。旧《鼓吹曲》 有《朱鹭》是也。”[2]4109据《宋书·乐志》,《朱鹭》为汉鼓吹之第一曲,魏、吴、晋均新造鼓吹,且模仿汉曲。[6]此条《毛诗义疏》云旧鼓吹,作者确为魏晋时人。因其语气非吴人,作者又传为陆机,更不可能是魏人,故当为晋人。
又《御览》卷九六一:
陆机《毛诗疏义》曰:梅楠,其树及叶似豫章。叶大如牛耳,一头尖。其华赤黄,子不可食。楠木理细于豫章,无子。赤者材坚,白者脆。荆州人曰:“梅多江南。”及魏兴、新城、上庸、蜀 ,皆多樟、楠。[2]4267
《晋书·地理志》曰:
魏文帝以汉中遗黎立魏兴、新城二郡,明帝分新城立上庸郡。[7]454
称“魏兴、新城、上庸、蜀 ,皆多樟、楠”者,必魏明帝以后人,也不太可能是东南吴人,最大的可能还是西晋人。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御览》所引《毛诗义疏》有草木、鸟兽、虫鱼之外的名物训诂。如《御览》卷一四五:
《毛诗义疏》曰:女史彤管,法如国史,主记后夫人之过。人君有柱下史,后有女史,外内各有官也。[2]709-710
卷八〇七:
《义疏》曰:内鼊之属。又有紫贝,其白质如玉,而紫点为文,皆行列相当。大者有径一尺六寸,今九真、交趾以为杯盘宝物也。[2]3588
卷八一六:
《毛诗义疏》曰:《杨之水》“素衣朱绣”,绣当为绡。绡,绮也。[2]3630
这三条均非《草木鸟兽虫鱼疏》所能涵盖。故《毛诗义疏》绝非《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总之,目前类书等文献所引陆《疏》,有的条目不可能是吴人陆机所作,其时代可能晚至西晋。有的条目甚至引用到了郭璞《尔雅注》,其时代就要到东晋以后了。《毛诗义疏》的涵盖范围也大于《草木疏》。那么,吴陆机之《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与诸文献所引陆《疏》,并非同一文本。
二、陆《疏》的衍变
接下来的问题是,即便我们确定诸书所引及今传本作者为陆机(或陆玑),也不能说明诸书所引陆《疏》出自同一文献,这是写抄本时代文献的基本特征之一。上文已初步证实《齐民要术》、《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所引《诗义疏》或《毛诗义疏》并非《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但《太平御览》当中所引用的“《诗义疏》”(又作“《毛诗义疏》”、“《义疏》”)和“陆机《毛诗疏义》”也未必是同一文献。原因为:
1.《御览》引用“《诗义疏》”往往在所引《毛诗》及《毛传》原文之后,有时会以双行小字附在《毛诗》之后。但引“陆机《毛诗疏义》”却是独立征引,并不附在《毛诗》之后。
2.除一条可能的抄写讹误外,《诗义疏》或《毛诗义疏》均不署名,但《毛诗疏义》绝大多数署名“陆机”。
3.“《诗义疏》”和“陆机《毛诗疏义》”尚有一条之内重复征引,但文字大异者。如上文所引卷九七三“榛”条。又如《御览》卷九五八“柞”条:
《毛诗·车舝》曰:陟彼高岗,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叶湑兮。
又曰:维柞之枝,其叶蓬蓬。《疏》曰:栩,今柞。壳为斗,可以染皂。今俗及河内云杼斗,或豫斗。
陆机《毛诗疏义》曰:“芃芃棫朴”,《尔雅》曰:“棫,白桵(注音蕤)。”《三仓说》“棫即柞也。其柞理纯白,无赤心,为白桵。直理易破,故可为犊车轴。又可为矛戟铩。”①《正义》引陆《疏》云:“今柞栎也,徐州人谓栎为杼,或谓之为栩。其子为皂,或言皂斗,其壳为斗,可以染皂,今京洛及河内多言杼斗。谓栎为杼,五方通语也。”(《太平御览》卷九五八,第4251页)
前《疏》与《毛诗》原文相接,有的条目即刻作双行小字。
4.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诗义疏》和《毛诗疏义》的书写体例也大不相同。这从上述“柞”条即可看出:《诗义疏》是附在《毛诗》、《毛传》之后的疏文,属于注疏合钞的样式。陆机《毛诗疏义》则多附有所释具体诗句或词语,类似于今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属于独立的义疏。又如卷九七三“木瓜”条曰:
《毛诗·卫·淇澳·木瓜》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毛云:楙也。《诗义疏》曰:楙,叶似榛,实如小扁瓜,上黄着中,令蚡香欲嘬者,蜜封,藏百日,食之也。[2]4312
这一条《诗义疏》甚至不是对《毛诗》名物的训诂,而是对《毛传》语词的解释。而卷九五八“梓”条引《疏义》曰:
陆机《毛诗疏义》曰:北山有楰,《尔雅》曰:“楰,鼠梓。”其树叶木理如楸,山楸之异也,今人谓之昔楸。湿时脆,燥时坚。今永昌人谓鼠梓,汉人谓之楰。[2]4252
《御览》所引绝大多数的陆机《毛诗疏义》,均有类似体例,即将每条冠以所释之语辞或诗句。
与上述书写体例相关的是,“《诗义疏》”或“《毛诗义疏》”除了“硕鼠”一则引《尔雅》外,整体上不引《尔雅》,但“陆机《毛诗疏义》”却比较经常的引《尔雅》。这一形式也暗示,“《诗义疏》”可能在前面的疏文中已经引过《尔雅》,而不需再引,但“《毛诗疏义》”是完全独立的名物著作,故引《尔雅》以明古义。《御览》还引用了八条《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也是完全独立的征引,甚至放在了子书之后。因此《御览》所引陆《疏》整体上是有三个来源的:一部经、传、笺、疏合钞本;一部陆机《毛诗疏义》;一部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后两部形式接近,很可能是同一著作的不同时期的传本。而《御览》所引的第一种陆《疏》中——因为这是一部经传疏合钞的书,出现有“女史”、“紫贝”、“绣”这种超出草木、鸟兽、虫鱼范围名物训诂,也就不奇怪了。
那么,能否依据《隋志》等目录来考证《毛诗义疏》的作者呢?因《毛诗郑笺》本是二十卷本,故若存在一部注疏合钞本,其卷帙应在二十卷以上。《齐民要术》、《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诗义疏》同源,故只能将此源头追溯到梁。①其间流传较广的类书是刘孝标《类苑》和梁武帝命徐勉等编纂的《华林遍略》。《隋志》载录晋以后、梁以前卷数在二十以上的注或疏有:
晋谢沈注《毛诗》二十卷
晋江熙注《毛诗》二十卷
梁崔灵恩《集注毛诗》二十四卷②《梁书》、《南史》崔灵恩传称二十二卷。
舒援《毛诗义疏》二十卷
沉重《毛诗义疏》二十八卷
《毛诗义疏》二十卷,未署名,不知时代
《毛诗义疏》二十九卷,未署名,不知时代
《毛诗义疏》二十八卷,未署名,不知时代[8]916-917
其中,可以确定的经注合钞本是崔灵恩《集注毛诗》。《毛诗正义》对经、传、笺的异文有所校定,主要的校定对象就是崔灵恩《集注》、颜师古《定本》以及唐俗本。那么,《集注毛诗》一定是经、传、笺、注合钞本。除此之外,其他著作很难依据卷数来判断其是否为经注合钞,即便四十卷的刘炫《毛诗述义》,也非经注合钞,而是单疏本。
不过,《隋书·经籍志》(《五代史志·经籍志》)时唐人所见南北朝书目,或同郡人陆德明《经典释文》的记录,均没有提到陆机著有《毛诗义疏》。因此,除了《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陆元恪应该没有其他传世的《毛诗》义疏。同时《要术》、《御览》等所引《诗义疏》或《毛诗义疏》除了少数几条外,绝大多数均为草木、鸟兽、虫鱼之疏,因此这些引文的源头还是《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只不过梁或北齐类书在抄录这些条目时,参据了一部集注性质的《毛诗》注本,这个注本汇录了大部分陆《疏》。
这个注本类似于蔡谟的《汉书注》,目的是撰作一部方便于阅读的《毛诗》注本,省去分别翻看经传原文及音义单注本的麻烦。因为《要术》、《御览》等所引《诗义疏》显现出晋人所作的时代特点,所以若非找到《诗义疏》的直接出处,谢沈和江熙所著两部《毛诗义疏》是最有可能的选择。如果考虑到《御览》所引《毛诗义疏》引及郭璞注的问题,那么就只剩东晋江熙所著《毛诗义疏》了。①《释文序录》:“江熙,字太和,济阳人,东晋兖州别驾。”《经典释文序录疏证》,第91页。
当然,鉴于唐及唐以前五经义疏以单疏形式为主,且考虑流传因素,《要术》、《御览》所引《诗义疏》也有可能出自崔灵恩《集注毛诗》。但崔灵恩天监十三年(514)南归梁,《华林遍略》的编纂始于天监十五年(516),至普通五年(524)乃成。②《南史·何思澄传》曰:“天监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勉举思澄、顾协、刘杳、王子云、钟屿等五人以应选。八年乃书成,合七百卷。”(《南史》卷七十二,第1782-1783页)《梁书·钟嵘传附钟屿传》:“天监十五年,敕学士撰《遍略》,屿亦预焉。”(《梁书》卷四九,第697页)《梁书·何思澄传》:“天监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勉举思澄等五人以应选。”(《梁书》卷五十,第714页)因《集注毛诗》作于何时不可考知,故只能推测这部唐以前最为通行的《毛诗》注本之一,汇集了包括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在内的诸多注释,或出于简省考虑,将此书名为《毛诗义疏》。
上述两个推测,没有文献依据,不能服人。事实上,很难知道《御览》等所引《诗义疏》出自上述哪部《毛诗义疏》,同时因《毛诗正义》也仅仅称“陆《疏》”,我们也不能确定《正义》所引是出于原本,还是某部《毛诗义疏》。
但有一点是可以做出肯定判断的,即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在两晋时代已经被编入了集注性质的《毛诗》义疏类著作,并被著者随手增加或删减了部分内容。原本的流传、不同的义疏辗转相抄、类书的采引、后人从类书中的引用,以及这些不同的流传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造就了不同系统的陆《疏》文本。这样一来,陆《疏》的原始文本就已经不可见了。以陆《疏》原始样貌为追求的“考证期待”,是无法实现的,这也是钞本时代的特点之一吧。
三、“陆机”还是“陆玑”?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作者,南北朝隋唐间,已多异文。《隋书·经籍志》载曰“乌程令吴郡陆机撰”[8]917,《齐民要术》、《毛诗正义》、《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旧唐书·经籍志》、《日本国见在书目》亦作“陆机”。而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曰:“陆玑,字符恪,吴太子中庶子。”[9]《新唐书·艺文志》等后来书目除《通志》外,亦多作“陆玑”③《册府元龟》卷六百五曰:“陆机,字符恪,吴郡人,为太子中庶子、乌程令,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264页。。李匡文《资暇集》“绿竹猗猗”条辨之曰:“陆玑字从玉旁,非士衡也。愚宗人大著作祝尝有显论,今秘阁西南廊新碑,古人姓名,若此参误多矣。”[10]《崇文总目》谓陆机为晋人,本不治《诗》,故以为当以“玑”字为是,此说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承:“《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右吴陆玑撰。或题曰陆机,非也。玑仕至乌程令。”[11]至此,《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作者为吴人陆玑,几无疑议。
不过,陆机字士衡,陆玑字符恪,名与字的对应关系初看起来是交错的。《尚书·尧典》有所谓“璇玑玉衡”之文,故陆玑似应字士衡也。然古书“机”、“玑”有混用,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二十七《跋尔雅疏单行本》曰:
此书引陆氏《草木疏》,其名皆从木旁,与今本异,考古书“机”与“玑”通,马、郑《尚书》“璇玑”字皆作“机”。《隋书·经籍志》“乌程令吴郡陆机”,本从木旁。元恪与士衡同时,又同姓名,古人不以为嫌也。自李济翁强作解事,谓元恪名当从玉旁,晁氏《读书志》承其说,以或题陆机者为非,自后经史刊本遇元恪名辄改从玉旁。予谓考古者但当定《草木疏》为元恪作,非士衡作,若其名则皆从木旁,而士衡名字尤与《尚书》相应;果欲示别,何不改士衡名耶?[12]
钱氏之说佳,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即用其说。自此,元恪、士衡似同名,均为陆机。实则早期书目、文献或以过录早期文献为主的唐宋类书,如前举《隋志》、《旧唐志》、《毛诗正义》、《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均作陆机。唐以前只有《经典释文》的宋刻本作“陆玑”,故《草木疏》作者写作“陆机”似更为恰当。
元恪、士衡本为同时代人,亦为同郡人。据《隋志》、《释文》,元恪曾为太子中庶子、乌程令。陆德明亦吴人,他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此二职衔,亦非泛泛之徒可任者。太子中庶子乃太子近臣,多由文士充任,《三国志·吴书·孙登传》曰:
孙登,字子高,权长子也。魏黄初二年,以权为吴王,拜登东中郎将,封万户侯。登辞疾不受。是岁,立登为太子。选置师傅,铨简秀士,以为宾友。于是,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以选入,侍讲诗书,出从骑射。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登待接寮属,略用布衣之礼,与恪、休、谭等或同舆而载,或共帐而寐。太傅张温言于权曰:“夫中庶子官最亲密,切问近对,宜用俊德。”于是乃用表等中庶子。后又以庶子礼拘,复令整巾侍坐。黄龙元年,权称尊号,立为皇太子。以恪为左辅,休右弼,谭为辅正,表为翼正都尉,是为四友。[13]1363
太子中庶子最亲密,负责太子之切问近对,实掌太子文翰之事,又有议政参谋之助,《晋书·职官志》载晋太子属官曰:
中庶子四人,职如侍中。中舍人四人,咸宁四年置,以舍人才学美者为之,与中庶子共掌文翰,职如黄门侍郎。[7] 742-743
《礼志》曰:
惠帝、明帝之为太子,及愍怀太子讲经竟,并亲释奠于太学,太子进爵于先师,中庶子进爵于颜回。[7] 670
陆元恪所任之太子中庶子,按理来说应为其最终职衔,但此官往往存在于士人仕途的早期阶段,属于为太子铨选的秀士,角色是太子之友。与太子太傅和少傅不同,太子中庶子很像是未来天子的人才储备。《三国志·吴书》所载曾任太子中庶子之人,如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韦昭和陆祎①陆凯之子,凯陆逊族子也。故陆祎乃陆机从兄弟也。诸人,太子中庶子均为其仕途早期之职。《魏书》、《蜀书》、《晋书》所载亦同,任此职者多为青年才俊,且以文翰之事为长。被征召的地方名士的起步官往往也是太子中庶子。同时,上述诸葛恪诸人多为吴之重要文臣,以望族士人为主。
乌程为东吴重镇,汉封孙坚为乌程侯,孙策袭爵,孙皓亦封乌程侯。皓即位后新立吴兴郡,治所在乌程。《三国志·吴书三》裴松之注引其宝鼎元年八月诏曰:
古者分土建国,所以褒赏贤能,广树藩屏。秦毁五等,为三十六郡。汉室初兴,闿立乃至百五,因事制宜,盖无常数也。今吴郡阳羡、永安、余杭、临水,及丹杨故鄣、安吉、原乡、于潜诸县,地势水流之便,悉注乌程。既宜立郡,以镇山越,且以藩卫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分此九县,为吴兴郡,治乌程。[13]1166
据此知,乌程令应是一个相对重要的千石官。
总之,虽无太多信息可供钩沉,但仅就元恪所任之太子中庶子和乌程令两官来看,他似应出身吴郡甲族。由此,笔者猜测陆元恪或出自陆逊一族。同时,这两个官也很可能是他的早期任职,故他或曾入晋朝。如果此种猜测成立,则两陆机同属一门,同一时代,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四、今本是否为辑本
《四库提要》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原书已佚,今本不知何人所辑。若假定吴人陆机确为此书作者,因《隋志》、《释文》均如此记载,这个假定几乎是可以确定的,目前也只能以此为基础来推演。况且,《太平御览》所引陆《疏》中,还有一条保留了注释者的按语,在卷九三七:
《毛诗·鱼丽》曰:鱼丽于罶,鲂、鳢。鳢,鲖鱼也。
陆机《毛诗疏义》曰:鲂、鳢,《尔雅》曰:“鳢,鲖也。”许以为鲤鱼,机以为鲤,狭而厚。[2]4164
作者自称“机”。在无反证材料的前提下,我们只能判断《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确为陆机所作。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此书引用了郭璞注,吴之陆疏如何引及东晋郭注,说明陈氏所见已非原书。况且,《太平御览》所引《毛诗义疏》也引及郭璞注,那么陈振孙所见就很可能已经是辑本了。①见下文。但今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不见郭璞注,与宋辑本又有不同。
那么,今本从何处辑来?《四库提要》以为辑自《毛诗正义》。但《小雅·南山有台正义》曰:
陆机《疏》云:“枸树高大似白杨,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长数寸,噉之甘美如饴。八月熟。今官园种之,谓之木蜜。”[2]347
《齐民要术》卷十《枳柜》条曰:
《诗》曰:“南山有枸。”毛云:“柜也。”《义疏》曰:“树高大似白杨,在山中。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长数寸,噉之甘美如饴。八九月熟。江南者特美。今官园种之,谓之‘木蜜’;本从江南来。其木令酒薄;若以为屋柱,则一屋酒皆薄。”[1]860
类书所引大体与《要术》相同。但今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曰:
枸树,山木。其状如栌,一名枸骨。高大如白杨,所在山中皆有,理白,可为圉板。枝柯不直,子著枝端,大如指,长数寸,噉之甘美如饴,八九月熟。江南特美。今官园种之,谓之木密。古语云:枳枸来巢。言其味甘,故飞鸟慕而巢之。本从南方来,能令酒味薄。若以为屋柱,则一屋酒皆薄。[14]16
今本《草木疏》文字两倍于《正义》、《要术》、《御览》所引,绝非宋以后可以辑得。故丁晏《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叙》曰:
今所传二卷,即玑之原书,后人疑为掇拾之本,非也。《尔雅》邢疏引陆玑《义疏》,《齐民要术》、《太平御览》并称“义疏”,今以陆《疏》之文证之诸书所引,仍以此书为详。《疏》引刘歆、张奂诸说,皆古义之仅存者,故知其为原本也。间有遗文,后人传写佚脱尔。[14]1
此说虽未必准确,但今本不是能从《毛诗正义》、《太平御览》等书辑出者。因此,今传《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若为辑本,也当是宋以前辑本。
五、余 话
若以唐代视点回看经史注疏传统,会发现汉末魏晋时期是注疏学的黄金时代。郑玄、王肃、王弼、韩康伯、陆机、何休、范宁、杜预、何晏、郭璞等五经注释,应劭、服虔、苏林、文颖、李奇、孟康等十数家的《汉书》音义,都是唐代经史注疏的主要学术资源。《五经正义》、颜师古《汉书注》、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李贤《后汉书注》、李善《文选注》等影响到今天的大书,乃是以上述诸人的著作为底本,或以之为主要素材来源。这样看来,似乎汉末魏晋时代是学术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经史之学在这一时期尤为兴盛。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依据传世文献和史志书目来判断学术的历史,还应考虑到哪些因素会使得某一阶段的著述能够更好地流传于后世。如果我们以《汉书注》为例来看的话,西晋开始,出现了汇集众家的集注这一著述类型,如晋灼《汉书集注》、臣瓒《汉书集解音义》,东晋时蔡谟又散《汉书集解音义》入《汉书》原文,纂成了一部《汉书》的注本,这是直到唐代都最为通行的《汉书》传本。两晋的集注和散集注入原文的注本,是留存汉末魏晋时期学术与思想的最重要的因素。《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就是依赖《毛诗义疏》一类的著作,得以流传后世的。
影响于今的许多著名注本,如《史记》三家注、颜师古《汉书注》、李善《文选注》又以引书宏富而著称。如李善《文选注》即以详于释事,征引博赡而闻名,“文选学”亦因其而生。据清代学者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考证,李善注引书竟多达1607种。今人程金造先生《史记索隐引书考实》逐条考释司马贞之引书,其数量亦颇为惊人。然以当时物质文本之流传状况,很难想象李善可以正好备齐这一千多种他需要的古书,况且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有相当多李善征引的文献在唐代已经失传。《五经正义》、《史记》三家注、《汉书注》所征引的古书中,也有大量文献不见于《隋》、《唐》三《志》及《日本国见在书目》。那么,这些著名的注疏如何做到宏富的“佚书”征引?自然是通过参据前代之注疏,尤其是那些容量可观的集注、集解。这是唐以前制作集注的便捷之途,这说明古人著作多借力而为,但作者与著作对应的书目著录方式,却掩盖了某些知识史、学术史的累积性过程,让我们无意中夸大了裴骃、孔颖达、颜师古、司马贞、李善等人的贡献。此虽近乎常识的问题,多为学者所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