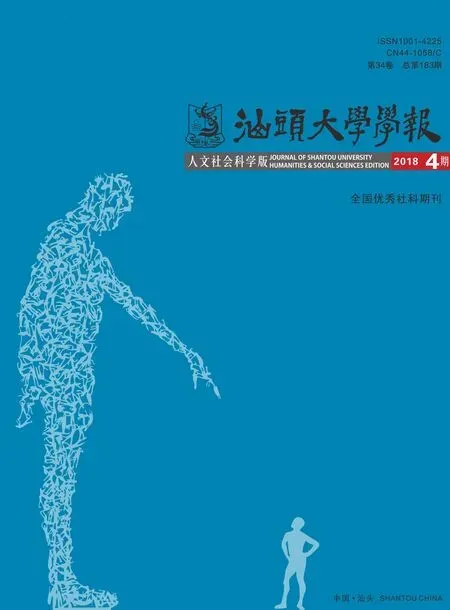新文学观念的一种图像性表达:张爱玲的画境小说《传奇》
周翔华
(莆田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福建 莆田 351100)
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上海文坛,张爱玲横空出世。这位天才女子以她艺术上大气、自由、汪洋恣肆且富有力度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给艺术上开始呈衰败迹象的新文学第三个十年这一历史时期注入新的生机。现代文学史上,在以鲁迅为源头,经由废名、沈从文等人推进和发展的画境小说这一支,到了张爱玲手里已呈现出明显的“变调”。张爱玲的画境小说艺术试图超出中国传统的审美趣味,向西方现代绘画艺术趣尚靠拢和借鉴,但不可否认,传统绘画艺术的因素仍在张爱玲小说中起作用,因此,张爱玲的小说画境中呈现出中西并举、传统与现代交相融合的混杂之美来。《传奇》中的“画”既有中国古典的工笔重彩的韵致,又有西方现代艺术后印象派油画的效果,还含有点儿夸张和怪诞,而且是嵌在镜框里的那种后印象派的油画。张爱玲在为画境小说艺术的丰富和发展做出自己努力的同时,也成为新文学史上画境小说的总结者。
一、“生命自有它的图案”
《传奇》结集出版的时候,张爱玲才刚刚20岁出头,第一版十万册的《传奇》4天内销售一空。当时文坛上许多前辈大家都对这颗冉冉升起的璀璨之星给予相当的关注,人们探究《传奇》小说世界的同时,才女传奇的身世也成为另一个版本的“传奇”。“身上流着贵族的血”的她在很小的时候就接受传统的和西式的教育以及多种艺术熏陶。张爱玲8岁时,留法学画归国的母亲教她画图配色,让她了解到色彩沉丽的西方绘画艺术,接触到了印象派绘画。长大以后,张爱玲在油画、水彩、漫画、插图等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堪称为美术家。她为自己的小说绘插图,文章署名“张爱玲作并图”;为许多杂志刊物绘的扉页画,也很有现代派的气息。她对西方现代绘画艺术倾注了别样的热情,像 Gauguin,Van Gogh,Matisse,以至后来的Picasso,都是她喜爱的画家。她还留下了《谈画》《忘不了的画》等经典名篇。品读画作,张爱玲总能读到现代画家的灵魂深处。她注意到塞尚静物画中“块”的发现,肖像画中“不安”的意味;在高庚的画作中,她读到了“最原始的悲怆”;观梵高的画作,她感受到他油画创作上的雕塑,强烈的光影效果所产生的“浮雕感”。
后印象主义是在19世纪末出现的艺术思潮,以塞尚、高庚、梵高为首的画家不满足于印象派仅凭视觉描绘自然和对光色单纯客观的表现,而认为绘画是表达感觉的一种手段,应主观表现自我的情感和个性。东西方两种不同绘画艺术在后印象主义的绘画里凸显了契合点,高庚和梵高是后印象主义画家中受东方艺术风格影响较大的两位。从小对颜色敏感,喜欢浓厚色彩的字眼,长大后仍爱看《聊斋志异》和俗气的巴黎时装广告的张爱玲喜爱后印象主义绘画并不是奇怪的事。
而在中国的洋画家中,张爱玲只喜欢一个林风眠。她认为,他那些穿着宝兰衫子的人像,有着极圆熟的图案美。林风眠致力于中国画的革新,呼吁尽量吸收西洋绘画的新方法,主张中国绘画从传统、摹仿和抄袭中走出来。而张爱玲也认为中国画应该求变,中外的画家应多交流,主张把中国画介绍到美国去。绘画观念上“求变”的一致性,这也许是张爱玲认同林风眠的又一个原因吧。作家身上具备的种种艺术素养,都成为她在文学创作时获取个性化艺术表现中极为难得的元素,这种种元素成就了张爱玲。
二、《传奇》的世界:传统与现代的混合体
作为20世纪40年代现代文坛上一位文学与绘画皆通的女作家,张爱玲对西方后印象主义绘画的钟爱,明显地影响到她感受世界和艺术地再现世界的基本方式。后印象主义画家在艺术表现上强调画家的主观感受,注重瞬间的感觉印象、时间流的绵延,凸显绘画内在精神的自觉表现和内心情感的有意识传递,用隐喻和暗示来渲染气氛,引发观者情绪上的共鸣与联想。为了表达绘画观念的需要,后印象主义的作品大多以离奇怪诞的表现手法对物象进行有意识的形变、表现和组合,创造了某些新的艺术手段和形式。这种艺术上的综合表现与形变等特点,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到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小说集《传奇》正是她向西方现代绘画艺术取法,借语言来作“画”,融中国古典的笔墨于现代的运思之中的一幅幅复杂华糜的画。《传奇》的封面,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①张爱玲:《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张爱玲文集》(第四卷),金宏达、于青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259页。文中出现的张爱玲作品原文,皆引自此版本。。这一画面构图可谓奇崛和矛盾的组合:画面上一道栏杆划出了内外即古代和现代两个不同的世界,给人一种超越时空的感觉。同一画面之中将中国古典仕女图和人体比例异常的现代绘画两种风格迥然不同的艺术混杂并置。仕女图给人一种幽幽情韵,而比例异常的现代人好奇地窥视,这一情景“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文明的恐怖”,这幅画真有点使人“不安”。张爱玲借此令现代人与传统人物构图展开对话,可见其艺术匠心。古典的、现代的、民族的、西洋的,各种艺术观念、技巧手法、情调氛围在极具功力的艺术手腕的调配下进行新的组合。相克相悖的艺术元素经过精心地特殊调置而融为一体,杂糅于同一作品之中,这正是张爱玲对艺术的理解与个性化的发挥,也使她迥然有别于鲁迅、废名等作家。
(一)古典的笔墨,现代的运思
张爱玲俨然是一位调制“鸡尾酒”的高手,一方面醉心于在古典的传奇性的氛围中筑造她的形象世界,她的画境小说具有地道的中国式的古典味,另一方面又潜心于对物象、对人性作非常“现代”的感悟和破译。
首先,张爱玲借鉴传统的小说戏曲艺术中的“讲故事和图画相结合”的方式来表现小说艺术。在传统的小说艺术中,故事和画图往往被并置在一块儿,故事中穿插图画。在页的上方附有文字讲述故事的内容,同时在页的下方配有图画,这种“上文下图”的形式,在宋人小说中常常出现,称为“出相”。明清小说中有只绘书中人物的,称“绣像”,又有在一个故事之后配以一幅与故事相关的图画,画每回故事的,称“全图”,也称“回回图”。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后记》中提到的元郭居敬编的《二十四孝图》,就是24个孝子故事文字配上图画的图本。[1]而张爱玲对这一传统艺术的借鉴含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小说文字之外,配有画作,如写这一小说时配有“王娇蕊”和“孟烟鹂”不同的人物线描肖像等,《传奇》中这种“图文”形式比比皆是,形成鲜明的“张爱玲作并图”的特点;二是借鉴传统说书艺术中讲故事的叙事特点“开场”和“结尾”来作小说,但张爱玲又打破传统故事通篇线性时间叙述的形式,而在小说的“开场”和“结尾”之间的主体部分,采用空间化的显示,营造画境来表现时间性的故事,形成说书的“叙述”与绘画的“显示”相结合的独特的小说文体面貌。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开场就是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展开故事的叙述。说书人的角色在道出“引子”之后,就隐匿起来了。接下来的故事就自行上演。小说的结尾说书人又回来了,“这一段香港的故事,就在这儿结束,……薇龙的一炉香也快烧完了”。作者在小说开头和结尾处,时不时充当“民间说书人”的角色,而在小说中间主体部分又全然换了另一种身份,从说书人转变到“画者”的身份上,让画笔下的世相物态自行“显示”或“呈现”。又比如《金锁记》和《红玫瑰和白玫瑰》的开头和结尾,或隐或现的议论,对人物的品评等,仍然是说书的语调,都属传统的笔墨。但故事以空间化的状态“显示”又属于现代的运思。
其次,人物形象的描写塑造借鉴传统的工笔仕女画技法和传统小说中的人物描写手法的同时,又超越了这一古典的对客体“静观”描绘的特点,而注重瞬间的感觉印象,借用了现代艺术中隐喻、暗示和联想的方法,实现对客体作“动态”的现代意识的审美。《金锁记》中,曹七巧这一人物的第一次出场是安排在她嫁到姜家之后,与姜家这一封建大家庭中大大小小的主子以及仆人会面的场景中。对这一场景的描写,作者显然采用传统绘画中工笔细描的笔法,把姜家大奶奶、三奶奶、二小姐等众女子穿着打扮、言谈举止、说笑行乐诸细节描绘得十分生动、明晰、流畅,这一场景俨然像一幅出自唐代画家周昉笔下的工笔仕女图。且看文中对曹七巧的描写:
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了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四下里一看,笑道:“人都齐了。今儿想必我又晚了……”[2]89
在偏于静观的一丝不苟的描写中透出工笔重彩的明丽精细,对曹七巧这一外在形象的描写,不由让人想到《红楼梦》中王熙凤等的人物描写笔法,让人想起唐代张萱、周昉笔下工整浓密,用笔流畅的仕女画。可见,张爱玲对传统的古典艺术的传承与接纳。但小说中的人物描写又不纯然是古典的,即便是对同一个曹七巧,也有十足“现代”意味的令人惊惧的笔致。没有比一个被黄金枷锁套住一辈子生命灵魂的人,临死前流下的一滴清醒的眼泪这一描写更令人惊惧和悲哀的。小说结尾对曹七巧的描写也就超越了外在的静态描绘的处理方法,而是注重内心感觉,捕捉“七巧推镯子至腋下”这一瞬间动作的感觉印象,经由象征、隐喻、暗示等触发,读者可自行展开对所绘人物一生的精神生命、生存状况一番动态的回想。又如新娘子芝寿,“行的是半新式的婚礼,红色盖头是蠲免了,新娘戴着蓝眼镜,粉红喜纱,穿着粉红彩绣裙袄。”[2]110这中西杂糅的“半新式婚礼”的一幕,着实给人以奇特怪诞的艺术感受,张爱玲在用小说家的眼光来审视这一场景和人物命运的同时,也用现代画家的眼光来观照芝寿这位在命运里无谓挣扎的女人。婚礼上,只在七巧对新娘子“看了一看”瞬间印象之后,等待新娘子的命运竟是无言的悲剧!
《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张爱玲把葛薇龙比作《聊斋志异》里的书生,巧妙地传达出葛薇龙惘然的感觉。用小型慈禧太后喻她的姑母在小天地里是一位能操控全局的能人,这也是寓现代人的思想于传统的人物形象之中的一种写法。当然,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形象也有纯然西方现代绘画感的:
棠倩是活泼的,活泼了这些年还没有嫁掉,使她丧失了自尊心。她的圆圆的小灵魂破裂了,补上了白瓷,眼白是白瓷,白牙也是白瓷,微微凸出,硬冷,雪白,无情,但仍然笑着,而且更活泼了。[3]222(《鸿鸾禧》)
她穿着的一件曳地的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她略略移动了一步,仿佛她刚才所占有的空气上便留着个绿迹子。[2]136(《红玫瑰和白玫瑰》)
再者,景与物的描写既来自传统又超越传统,在寻常的“物象”或“境”中组合出超常的“意”。在张爱玲的小说里,美丽的仙人掌吐着蛇信子,恶毒地窥视四周;皎洁的月光有蓝阴阴的火,暗示着心理的邪恶欲念;灿烂的太阳是昏黄的,象征着心灵的暗淡;那满山轰轰烈烈地开着的红色的野杜鹃花,那么美丽,却成为欲望的火焰,把上海来的女学生灼灼燃烧掉了;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宝石装饰梁太太身上,却象泪珠,象青痣,又透出蜘蛛的毒气。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张爱玲经营意象的方式:写实基础上的描述性,加上自我感觉的解释性,加上一点点比喻、夸张变形,得出超出寻常的“意”,有时还加上自省性的剖析。探索张爱玲小说中的意象,不禁让人想起梵高笔下那炽热的火焰般象征生命激情的《向日葵》和最富幻想力的《星月夜》,以及塞尚和高庚笔下那些真实而又略带夸张的人像(头大身小),或是被放大缩小的物象。张爱玲在《谈画》一文中说:“对现代画中夸张扭曲的线条感兴趣的人,可以特别注意那只放大了的,去子圭角的手。”[4]200而张爱玲在自己的小说中也曾画过类似的变了形、质的手臂:乔琪见到薇龙,“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2]22。后印象主义绘画在现代性美学、审美的影响下走向表现,画中的物象都是表现过后的对象,但并没有夸张得离谱,属于真实地抓住特征的变形。张爱玲的意象经营也是在真实之中抓住对象的某些特征,进行主观的形变和想象,呈现出特殊的美感——神秘,超自然。一切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总能给人新奇、独特的感觉。
(二)桃红与葱绿参差对照的浓郁之象
张爱玲对色彩有天生的敏锐感知和体会,“颜色这样东西,只有没颜落色的时候是凄惨的;但凡让人注意到,总是可喜的,使这世界显得更真实。”[4]163。为了让自己笔下的颜色真实可触、不落窠臼,又能够调动起读者的诸多感觉,张爱玲主动地在作品中赋予色彩审美的个性表达,且有自己的配色原则。“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刺激性。可是太直率的对照,大红大绿,就像圣诞树似的,缺少回味。……参差的对照,譬如说: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4]89。她在《自己的文章》中表明了自己的美学追求:之所以更喜欢苍凉,是因为苍凉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这一“参差的对照”的创作观,也许一般人很难理解,而一旦用配色作喻,葱绿配桃红却是人人明白的。
色彩是张爱玲“艺术”“生命”表达的符号,在她的小说中广泛运用。小说中的景物描绘、人物的勾勒、活动场面的再现,多与设色同步进行。有人曾“取《传奇》集子中全部16篇作品,随便各拣出一段描写景物或描写女人的文字来统计,16段共91处用了带色调的词汇”。[5]单就女性的奇装异服的颜色,就令读者目不暇接。《传奇》中女性的服饰颜色中,“红”就有银红、深粉红、石榴红、橙红、枣红;“绿”有淡绿、水绿、苔绿、橘绿、果绿、海绿。《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对梁太太的花园内外景色的描绘可谓极尽张爱玲的“敷彩染绘”之能事:金漆托盘、长青树、艳丽的英国玫瑰、墙里的杜鹃花开着,花朵儿粉红里略带些黄是鲜亮的虾子红。墙外的野杜鹃灼灼的红色,杜鹃花外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殖民地都市的光怪陆离、诡丽斑斓,各种不调和的奇幻镜像,全都搀糅在张爱玲的笔下,“处处都是对照”。又如《金锁记》中,曹七巧等人也是生活在末世华糜的环境色里,但外在的金碧辉煌无不映衬对照出人物内心的空虚、变态或恐惧、妥协、堕落。张爱玲画境小说中的色彩运用不仅交待了背景,体现了人物的处境,有时还暗示了人物的结局。《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色彩描写淋漓尽致,但五颜六色的背后无不透露葛薇龙对未来的无边的恐怖。外在的、琐碎的、花花绿绿的世界再怎么丰富,也不能填补她内心的空虚。小说中色彩的描绘暗示了她一步一步地迈进她姑妈和丈夫设置的世俗情欲的陷阱里,深深地沉溺于其中,又时常感到荒凉的虚无。
如果说鲁迅的画境小说中鲜明的黑白带有批判的锋芒,废名的《桥》营造的清清白白的世界濡染了逃遁的意味,那么,张爱玲则是在葱绿配桃红参差对照的浓郁的色彩里直接地诉说。这种浓妆艳抹本来就是现实的俗界的色彩,但张爱玲却不避俗。她要“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和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4]51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艺术作品的产生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6]张爱玲处在一个颓败、畸形的乱世,华糜是她熟悉的周遭实际生活底色,她把这种苍凉、离乱之感寄托在她的笔下,灵活地运用现代色彩语汇,在力求表现的真实中,使华糜的生活内容与形式紧密结合。大量绘画色彩语言的频繁使用,同时赋予她的作品以整体上的浓郁的抒情性,“加强了抒情化、散文化和对于趣味的追求乃至偏嗜。”[7]
(三)嵌在画框里的油画
张爱玲画境小说的空间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封闭式的结构,借用作者在《倾城之恋》中的一句话就是:“那整个的房间像暗黄的画框,镶着窗子里一幅大画。”[2]61我感到张爱玲的画境小说的空间构图上总有一种有形的无形的“框框”存在,它框住了一个个发生在特定的时期寻常男女身上的传奇性的故事,但却框不住作家创作的精神自由向度。
首先,这种感觉的获得来自于小说故事发生在相对封闭、狭小的自然与人事场景空间之上。《传奇》中的故事多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香港和孤岛时期的上海。租界使上海变成为中国最特殊的地方。没落的官僚、旧家庭因为生活在租界上而延长了他们所尊奉的封建制度,也借过去的剩余苟延残喘,“他们忘却了时代,也被时代忘却,整个地封闭在旧的生活方式中,始终背向着时代盲目地挣扎。”[8]他们的家就是一个小小的“清朝”。香港在长期“存而不在”的殖民地和平下成为一个被遗忘的窒息的“老”社会,吸引了不少“外省”来的遗老遗少。像从上海来的葛微龙的姑母,在此关起门就可以做小型慈禧太后。整个社会正如傅雷指出的,就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青春,幻想,热情,希望,都没有存身的地方。川嫦的卧房,姚先生的家,封锁期的电车车厢,扩大起来便是整个社会。一切之上,还有一双瞧不及的巨手张开着,不知从哪儿重重地压下来,压痛每个人的心房。”[9]所以,诸如房间、家、卧房、封锁期的电车车厢等这些封闭的空间也就是张爱玲《传奇》的“世界”。虽然,作为直接诉诸画面的具体的场景空间呈现,但已不是单纯的自然空间,而是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二合一”。显见,张爱玲小说的自然、社会时空领域较为封闭且狭窄。但这并不影响到张爱玲艺术创作的大气、自由、汪洋恣肆。其实,相对于自然空间与人事场景空间,还有一个心理空间,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心理空间的展现可以不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任凭作家创作时在其内在心理活动中天马行空、自由想象展开自由的空间。《传奇》中已逝去的那个繁华的旧世界与现代世界的自由杂糅,显然就是一种精神意识空间的展现。栏杆外的那个鬼魂现形似的现代人孜孜的窥视那个古代的世界,这是一幅现代绘画艺术中穿梭时空的幻景,是否可以称其为梦幻空间呢?
其次,小说结构的“开头”与“结尾”以重复的文字形成首尾和谐照应,增强小说画面的装饰效果,同时也拉开了画面与现实读者的距离。张爱玲总喜欢把自己绘制的这一“现代画”嵌在一个既不突兀又不碍眼的“画框”里。无疑,这是不以自然的美为满足,而要求比自然更理想化些,因而,作者在意匠上下功夫,在作品上上下下、前前后后营造一种氛围,衬托主体,使主体画面艺术效果更为突出。《倾城之恋》的开头提到“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2]48结尾又提到了“胡琴咿咿哑哑拉着……”[2]84故事的讲述与琴声联系在一起,小说在首尾呼应中获得了某种奇妙的韵律感,读者阅读起来兴味无穷。又如《金锁记》开篇是“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2]85,结尾“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了,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2]124,这一近乎重复文字的结构安排,形成一种装饰效果,令读者有意无意地感受到作品是一个独立自足的艺术整体。这种对称重复的文字组织的结构具有装饰图案美,吸引观者的注意力,使观者似参与其中,又同日常生活经验区别开来。画面的节奏深缓、悠远,使小说作品产生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三、苍凉之寒与“那一抹走向无光的蓝”
张爱玲的小说以丰富、鲜明、强烈的具有色彩感和绘画感的视境呈示于读者面前,华丽与苍凉二元对立、桃红配葱绿参差对照的浓郁意象经营,是她绘制画境小说时走不脱的模式,她的画境小说世界中既有中国古典的工笔重彩的繁丽精湛,又有西方现代绘画那种夸张的感觉。但“她是刻意要用金碧辉煌来叙说一个衰败的世界”,她告诉我们当繁华消逝之后生活只留有一个苍凉的底子。苍凉之寒是张爱玲画境小说中哲思审美境层的“道”。
张爱玲画境小说中的“苍凉之寒”是有迹可循的,有凭依的,并非《红楼梦》中“白茫茫落得大地一片真干净的”虚无主义,而由“人性的苍凉”和整个“文明的苍凉”构成画境小说《传奇》的“苍凉”的意蕴内涵。西方“现代绘画之父”的塞尚常常在画作中借比例完全不对的人体和矛盾的不调和的画面来表现一种奇异的,不安于现实的感觉,“一种微妙的文明的恐怖”。而张爱玲作品中也常常借笔下的一个个人物来寄托自己的一份苍凉之感,“姜家的二少奶奶也罢,麻油店的曹七巧也罢,依靠残存的最后一缕青春去抓住一个依靠的白流苏也罢,自甘堕落的葛薇龙也罢,最终回归家庭、又变成一个好人的佟振保也罢,只不过是张爱玲叙说苍凉的身世之感的载体”[10]。张爱玲以自己独立的眼光俯视着众生世相,俯视人类和文明,并且悲哀着人类的愚昧,感受着人生的苍凉。对人类的恒常中的一面即人性中世俗的小奸小坏充满生存的挣扎或丑恶,张爱玲是以极其宽厚的心胸给予包容理解的,她是有“哀矜”的,“我写到的那些人,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够原谅,有时候还有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4]227,但恒常中的另一面即“就近求得自己平安”,没有任何“生长力”的生存则是令她十分惊惧震动而且感到无比悲凉的。“看着他,好像这个世界的尘埃真是越积越深了,非但灰了心,无论什么东西都是一捏就粉粉碎,成了灰。我很觉得震动”[4]244。进而上升到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苍凉感的体悟。
张爱玲十分敏感于不幸的存在,特别是她深切地感受到那个她所熟悉的洋场贵族社会的崩裂:“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传奇再版·序》)。时代的没落感及随处可见的畸型、窒息、腐烂与恐怖,在《传奇》小说画境中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张爱玲清醒地意识到,一个时代走到文明的末梢生长不了真正的“悲壮”的事物,“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不是反映“周围的现实”的。惟有人类的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恒常事物才是“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而历史进展到她所处的时代,繁华已成为过去,只有苍凉是恒常,就像时间在加速,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一连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传奇》画境中处处流露出张爱玲面对文明的整个崩溃却无处着力的悲哀。“这里是什么都完了。剩下点断墙颓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是什么都完了。”[2]82。这是张爱玲在作品中传达出来的彻骨的感觉,在记忆中的雕梁画栋匆匆崩溃的废墟之上,人类的心灵恐慌而茫然,张爱玲悲悯着乱世中人类的不幸,但又对人类的愚昧深深地感到悲哀。
笔者认为,张爱玲是出现在40年代上空现代的一个幽灵,《传奇》的扉页上那幅“现代画”中幽灵似的现代人那窥视的神情,太多地“混杂了反讽与哀悯之复杂情感的张爱玲的眼神。”[11]她把感觉到的生命与艺术中矛盾纠葛的诸元素荟萃起来,杂糅在《传奇》复杂诡秘繁丽的小说画境之中,可谓“苍凉之音却以华贵出之”。她与她笔下的人物一起带着神秘的目光从我们面前跫然走过,把盏品味着“我们的日子短促的苦味”,笑看着人生的无奈与苍凉。[12]
四、结 语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小说与绘画精神相通性联系的画境小说在艺术探索和实践的道路上业已汇聚了众多小说家的履痕,应该说,不止鲁迅、废名、张爱玲等人,但他们是三个典型的个案。“以图入世”,无论是新文学的封面、插图,还是这批现代小说家创作的小说内部“画境”的建构,都可以说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成为新文学观念的一种图像性表达。即便将现代的画作和传统的古典的中国画直接呈现置于同一篇幅之中,也仍能构成耐人寻味的互文关系。作者的用意也很明显:其一,古典的、现代的图画,在此自行展开对话。图文结合,现代作家的小说创作与美术的关系,一直自觉地接通历史的根脉,诗画互通在他们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传统与现代奇妙的拼接,使历史感与现代感在他们的画境小说中获得某种沟通。其二,鲁迅、废名、张爱玲之外还有沈从文、凌叔华、师陀、萧红等,他们小说的图画叙事断断续续,形成了一支时隐时现的艺术流脉,呈现出一种传承与超越相交织的关系。对这支画境小说流脉进行梳理,是富有新意地解读中国现代小说的一条途径。这一批小说家承继中国诗画互通美学传统,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融入现代的画理画趣营造画境,推进小说艺术的空间化,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形式的小说。画境小说因之常常在作品中营造深具魅力的艺术之境,而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熠熠生辉。
[1]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66.
[2]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二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3]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一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4]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5]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248.
[6]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2.
[7]范智红.在“古老的记忆”与现代体验之间[J].文学评论,1993(6).
[8]余斌.张爱玲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22.
[9]于青,金宏达.张爱玲研究资料[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124.
[10]岳晓英.蝉遁与沉浮——张爱玲、萧红对于生命的两种解读[J].理论学刊,2004(7).
[11]艾晓明.混杂之美[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3).
[12]张洪.无奈与悲哀——张爱玲的小说基调[J].当代文学评论,19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