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烬里的光亮灼伤野蛮的焰火
王雪茜
二〇一〇年,克莱尔·吉根的小说《寄养》获得戴维·伯恩爱尔兰写作奖时,美国著名作家理查德·福特在颁奖词中赞扬吉根“对词语的直觉令人毛骨悚然。她对生命的重要过程和结局持有耐心的关注”。词语尚属表象,归根结底,吉根对转瞬即逝的隐秘情感的洞察非用“毛骨悚然”不能形容,那些没有解药的沉默、孤独与爱,被她冰锥似的笔刺穿血脉汩汩流淌出来,触目惊心。
“吉根用简洁的词语写出简洁的句子,然后组合在一起绵延出简洁的场景。”如果单凭村上春树的此类评价,你可能连翻动书页的愿望都不会有。没有温度和内涵的句子再简洁也索然无味。读吉根后你却会惊奇地发现,她的作品绝不是那种伪抒情的、诚挚得令人颤抖的文学。“我认为短篇小说可以很好地探索人与人之间的沉默,孤独以及爱。”《寄养》就是对吉根这句话的完整诠释。
当然,无论是任何伟大人物的任何精妙评论,无论是再多引文再多内容介绍,都无法给予吉根小说以公正的对待,公正对待它的最正确方式就是去读它。如果你不想漏掉那些可以敲开生活外壳一窥内核的微小可能性,那么我只能发出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请求:读吉根!读吉根!
“如果你想要写出好的小说,你就要等待这一刻的出现。其实你知道你可以强迫它出现,但如果你过于用力,你就得不到你想要写的那一个故事或者说你想要的那个感觉。你的故事或许就会沦于庸俗之中。对于我来说,我一直在尝试去找到一种清新的语言去描述我们每天的生活的意义。一部好的小说,其实是我们感情的一部分,是有关转瞬即逝的情感,是感动人心的。不好的小说只有单调的陈述。”吉根的这种“顿悟”的获得不仅仅源于她静得下心来写得很慢,足够耐心,足够淡定,更源于她对素材的熟悉度和敏感度。吉根所说的“一种清新的语言”并非说吉根擅长使用自创的新鲜生造词,肤浅地以阅读上的陌生化来吸引读者。恰恰相反,吉根总是试图用最常见的语言表达出更多层次不落窠臼的新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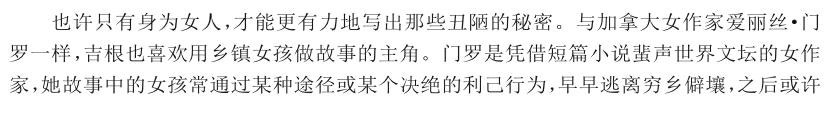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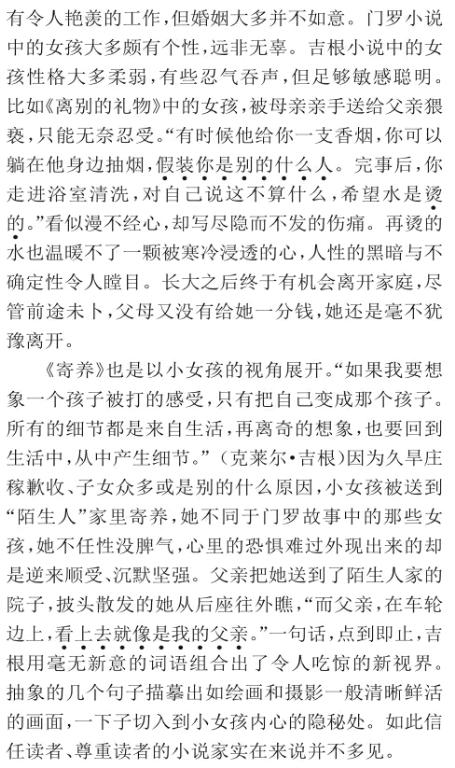
好语言就像幸福的童年。我常常会回忆被誉为“作家们的作家”的博尔赫斯小说中那些精彩的句子。《汤姆·卡斯特罗: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骗局》中蒂克波尼夫人在巴黎一家旅馆收到汤姆·卡斯特罗(他假冒她在沉船中遇难的儿子)的信。骗子提到了两个确凿的证据:他在左奶头旁的两颗痣和童年时发生的那件他永远也忘怀不了的不幸往事——他遭到了一群蜜蜂的围攻(证据当然是虚构的,这场骗局的导演波格雷认为突出事物之间的某些不可避免的差异反倒能求得它们之间的相似)。极度悲伤和孤独的蒂克波尼夫人“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便记起了她儿子请她回忆的那些往事”。时隔多年,我仍能清晰地记起初读这句话时的震撼、感动与手足无措。没错,手足无措。读到好句子时的快感真会让人一刹那间无所适从。读博尔赫斯的小说我常会情不自禁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围着桌子走几圈,又下意识坐下,仿佛这样做就能把那些好句子完全融汇在血液里似的。读吉根的小说也是如此。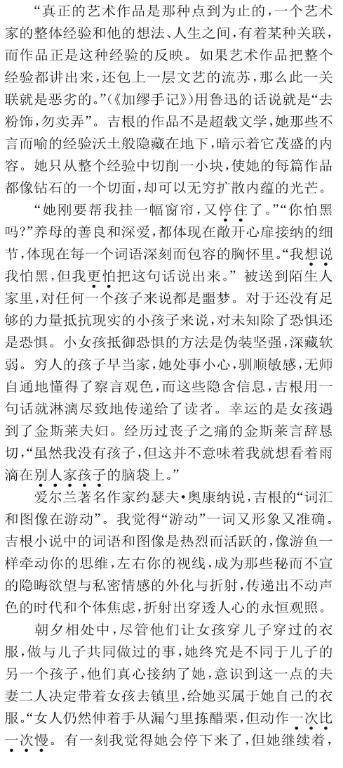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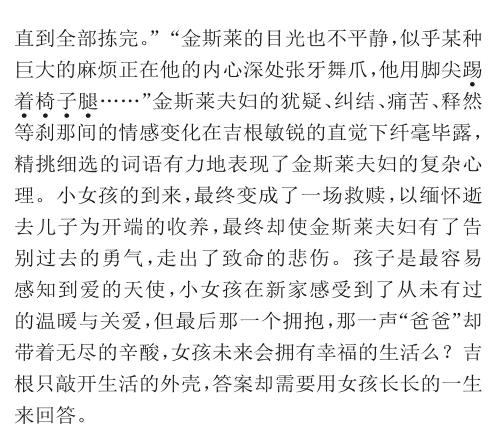
這只是吉根的一篇故事。她的短篇集《南极》和《走在蓝色的田野上》有很多篇故事比这一篇更好看——更残酷,比如《南极》《护照汤》;更深刻,比如《姐妹》《烧伤》;更智慧,比如《跳舞课》《水最深的地方》。不过,还是先读读《寄养》吧,如果收养小女孩的人家不善良,她遇到的不是金斯莱夫妇,结果会如何呢?再好的小说也无法拯救世界,甚至无法拯救一个国家,一个家庭,但它却很有希望拯救一个人的灵魂。吉根的小说虽未必能拯救灵魂,但至少让我们有勇气正视灵魂中的暗影,正视那些羞于见人、耻于开口的秘密。
加缪说,人生想要过得更快乐,就必须尽量去见证其中的悲剧。真正具有悲剧性的艺术作品,应该都是幸福的人创作出来的。吉根恰巧是“应该”中的一个,她是一个幸运儿。
吉根生于爱尔兰东部海岸上的威克洛郡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家庭。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她的童年在威克洛的一个农场度过。她熟悉农场里的每一件工具,她观察乡间的云、牛、马和鸭子,在乡间瞎逛,她还有匹小马,“我叫它花斑马,棕色与白色混合,我没马鞍,它很棒,夏天我常骑着它跑。”唯一不同于乡间野女孩的是,她很小就学会了阅读,“我还记得自己是怎样学会读书的,就像学会自行车的时候一样感觉很自由。你会意识到自己可以去任何地方,有了开始就不会结束,你随时可以上路。所以,学会读书就有了自由。”十七岁时,自由的吉根离开家乡赴美求学。沉潜于深沉而诡异的美国南方文学的吉根受到了威廉·福克纳、弗兰纳里·奥康纳、尤朵拉·韦尔蒂等文学先师的深刻影响,但吉根并不喜欢都市的喧嚣。一九九二年,克莱尔回到爱尔兰,相继在威尔士加迪夫大学和都柏林三一学院攻读创意写作硕士课程,并于一九九四年尝试创作小说。初学写作的吉根很快发现了自己超凡的写作天赋,随即参加全国性的写作比赛,作品相继获得了两个爱尔兰短篇小说奖——弗朗西斯·麦克马努斯奖和威廉·特雷弗奖。在弗朗西斯·麦克马努斯奖的颁奖仪式上,她认识了爱尔兰有影响的作家、编辑戴维·马库斯。马库斯对吉根颇为欣赏,他把吉根的小说寄给了伦敦的书商,一九九九年,吉根的第一部小说集《南极》顺利出版。第二年,她便获得了鲁尼爱尔兰文学奖以及《洛杉矶时报》年度图书奖。
吉根获得“戴维·伯恩爱尔兰写作奖”的过程更为幸运,她在截稿当日才想起寄稿子,而当天雪下得很大,大到吉根根本没有办法开车去邮局,她只能徒步穿过积雪覆盖的田野,把稿投进了邮箱。好在邮递员并未因糟糕的天气耽误工作,吉根如愿以偿地获了奖。她自豪地表示,她估计自己是整个爱尔兰唯一一个能靠写作养活自己的短篇小说家。endprint
吉根常住在乡间放满了书的小房子里,窗边放一张小桌子,“我喜欢喂鸟,喜欢写作的时候知道它们在外面,我在窗台下面放了喂鸟的容器。”
自由的鸟儿会带来新鲜的空气、灵动的喜悦以及未知的感动。吉根尝试带给读者新的视界、新的阅读可能和阅读快感。阅读吉根的作品鲜有断代感和国别感,反会有恍若他乡是故乡,恍若他人是故人的强烈同化感。她的笔刺入到人心深处,探测到人类共通的情感永恒的特质并确立一种真正自我的原创表达,那就是简单呈现,而这其实并不简单。她不负责修复心灵黑洞,她的词汇与图像具有的张力就在词汇和图像表面,以致我们谈论“隐喻”之类的修辞都显得多余。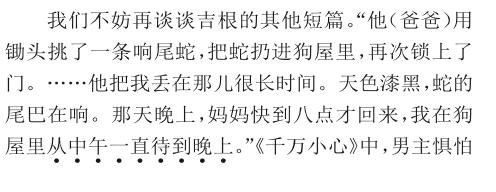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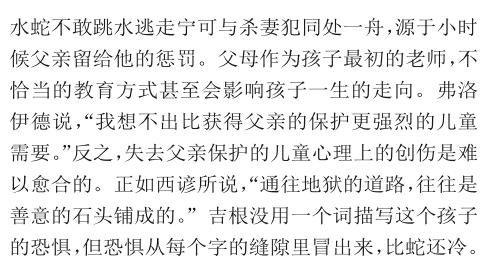
“阿拉伯的大地是忧伤的,她的忧伤是语言额头的皱纹”,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这句诗可以作为吉根小说语言特点的一个注解。爱尔兰的大地也有无尽的忧伤,吉根“语言额头”的皱纹正是忧伤。吉根不给她作品中的人物情感下定义,你很难在她的作品中找到诸如“痛苦”“绝望”“嫉妒”“愤怒”之类直抒胸臆的词语,但忧伤无处不在,她的担忧无孔不入,如空气一般弥漫在小说的每一个空隙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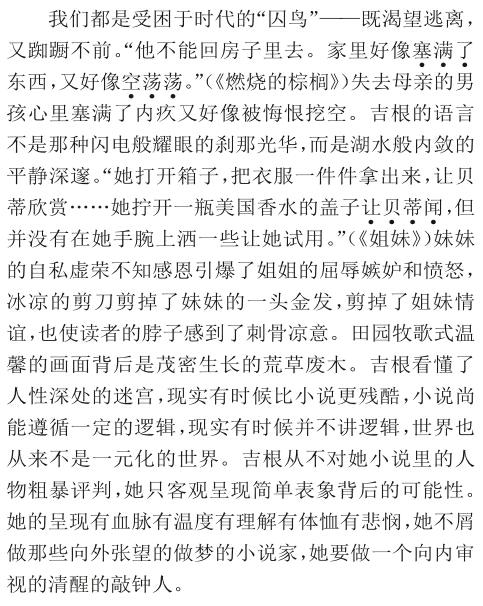
瑞士心理学家,分析心理学首创人卡尔·荣格在他的名著《红书》的自序《来者之路》中说,“人类就像植物那样生长,有些在明,有些在暗。有很多依赖的是黑暗,而不是光明。上帝的形象有阴影,阴影如它本身那样大。”曾支持荣格创办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后与荣格决裂的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下过一个更极端的定义:人类世界就是一個悲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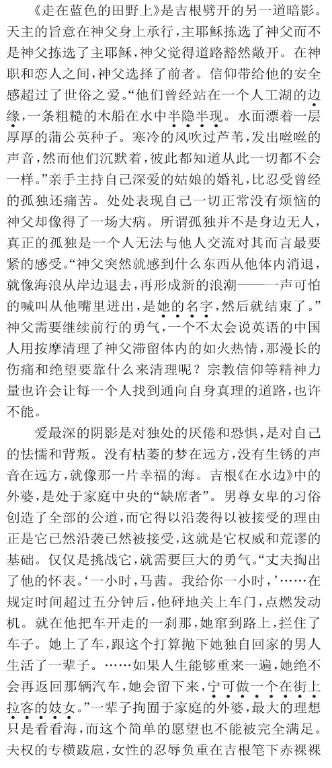

德国作家妮娜·乔治写过一本治愈系小说《小小巴黎书店》,书中男主人公佩尔杜经营一家叫“水上文学药房”的船屋书店,他自称“文学药剂师”,能辨别出每一个灵魂所欠缺的东西,再把自己视为“解药”的书卖给对方,而以书为药,相信唯有文学才能治愈人心的他却深陷隐痛,被围困其中。文学不是万能解药,想在吉根的书中找到现成的灵丹妙药,寻求捷径避开生活荆棘的读者可以原路返回了。人性中难免会有暗处,灰烬中也总会有光亮,正是这一点点光亮让勇敢的人跨过黑暗的河流,找到人生的方向。吉根的小说更多是给身在暗处的人开一扇门,让那些受困者凭借聪慧直觉自己走出来。
我们读过很多患了多语症的小说,不诚实的文字僵死呆板,被动变成作者的单向传声筒,它们毁坏了读者的智慧,失去了跟读者交流的功能,语言应该具备的基本的“信号”功能丧失殆尽。吉根从不制造文字垃圾,她的每一个字都有自己必须存在的价值,她的语言不会使读者丧失阅读中思维在场的乐趣。
希望总是最后死去的东西,在黑暗中摸索并不是羞耻的事情。挣扎、紧张、平静,在平静中体认白昼和黑夜的秘密。最后,我发现读完吉根的故事用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的诗句来收尾也毫无违和感:“我不愿把你称作爱/也不愿把你称作喜悦/它们对我来说已被取代/代之以奇异而陌生的血。”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