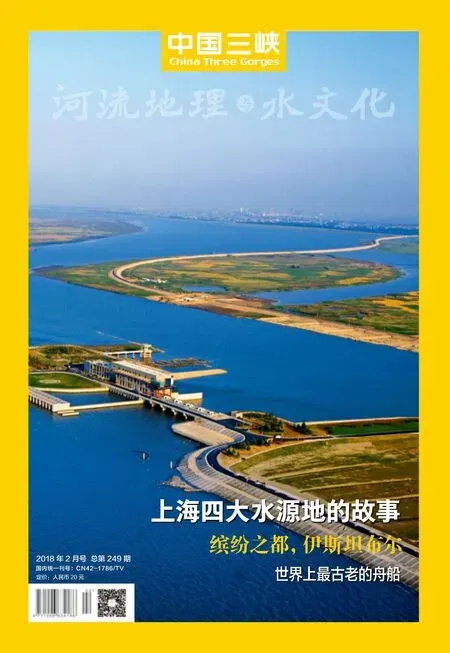缤纷之都之一深海的往事
◎ 文 | 吴荞 编辑 | 田宗伟

博斯普鲁斯大桥 摄影/ 视觉中国

加拉太大桥 摄影/视觉中国
“如果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国家的话,伊斯坦布尔将是这个国家的首都。”—— 拿破仑
一个夏夜的凌晨两点钟,我真实地嗅到了金角湾海风的气息。
当第一句祷告的歌声划破伊斯坦布尔寂静的长空,如平地一声惊雷,响彻在我耳边,这不同凡响的叫醒方式,令我迅速地从混沌中清醒过来,意识到我的所在正是有着2700多年历史的伊斯坦布尔城。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这座城市的名字叫作君士坦丁堡。
我看了一下表,伊斯坦布尔时间清晨4∶35,初来乍到的好奇心令我一个翻身跳下床,走上阳台。目之所及,非惊叫不足以表达那种震撼。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晨光下的伊斯坦布尔:一片片的红屋顶、灰蓝色圆穹的清真寺顶和高耸的宣礼塔构成了它的天际线,博斯普鲁斯深蓝的海水、海峡上翻飞的海鸥、宁静的泊船的港湾以及海面上无声无息匀速航行的各色船只,这场景正如许多描摹这座古城中世纪古画里的样子。
万城之城,万都之都,与其说我现在身处的国度是土耳其,不如说我是到达了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城邦拜占庭,又或者说我是站在了1000多年前的东罗马帝国之都君士坦丁堡,再或者,也可以说我正凝视于500多年前奥斯曼帝国的都城伊斯坦布尔。这是一个融汇了东方与西方文明的古老存在,一个在地理、历史、宗教、艺术、建筑各个领域都为人类刻下不凡印记的独特都市,从某些意义来说,她值得这样至高无尚的荣誉——世界上只有两种城市,一种是伊斯坦布尔,一种不是。
清晨的伊斯坦布尔城尚未从沉睡中醒来,整座城市的街巷、楼房、山丘和海洋,全都笼罩在仿似从天而降的沧桑、肃穆的晨礼祷歌中。
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人开始在这里的金角湾依山筑城,取名拜占庭。
公元324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扩建拜占庭城区,移都拜占庭,并将拜占庭更名为新罗马,也称君士坦丁堡。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后,君士坦丁堡成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此后千年间,君士坦丁堡以欧洲最大的城市著称于世,成为基督教世界财富和权力的象征,东罗马帝国也因建都于原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而被后人称作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
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军队攻破,最后一任东罗马皇帝战死,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国灭亡。君士坦丁堡为奥斯曼帝国占领,并成为奥斯曼帝国首都,更名为伊斯坦布尔。

鲁梅利城堡 摄影/视觉中国
1922年,奥斯曼帝国灭亡。土耳其民族领袖凯末尔带领军民战斗,使土耳其共和国获得独立,并进行世俗改革,相继废除了苏丹和哈里发制度,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土耳其。
我们通常所说的土耳其包括1453年之后的奥斯曼帝国和1922年之后的现代土耳其。
我下塌的酒店位于苏丹艾哈迈德的老城区,正在金角湾上,从这个阳台可以看见的海,是马尔马拉海与博斯普鲁斯海峡南口的相接处。金角湾在古代的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时期,是重要的港口和商业据点,海军和海洋运输活动均集中于此。而现在的金角湾,已是保存良好的伊斯坦布尔城的古都观光区,这里云集着旷世之作蓝色清真寺、圣索菲亚大教堂、托普卡帕老皇宫,建筑风格独特,历史遗存丰富,异域风情浓郁。从我住的地方出发,穿过土耳其老城常见的卵石坡道街巷,这些重磅级景点可步行到达。
博斯普鲁斯海峡
“博斯普鲁斯海峡用一把钥匙开启和封闭两个世界、两片大海。”
—— 皮埃尔·吉勒,16世纪法国学者
我们从老皇宫外的码头登上游船,四面开敞的游船载我们驶离金角湾,穿过连接欧洲新区和老城区的加拉太大桥,由此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
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长度,似乎和它在历史地理上的名气并不匹配,全世界任何一个学过地理的人都会知道它的大名,可它全长不过30公里,最宽处仅3700米,最深处120米,其最窄处不过700米,最浅处只有27.5米。如果坐轮渡,只需几分钟就可以从欧洲到达对面的亚洲,伊斯坦布尔有不少年轻人会选择在亚洲区买房或租房居住,因为那边房价便宜,他们每天坐轮渡或乘车经跨海大桥去欧洲区上班。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记载,君士坦丁扩建拜占庭城时仿照罗马的格局和风格,连城市都是建在仿罗马的“七座山丘”之上。我们乘船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北上,沿岸蓝天碧海、绿树山丘,两岸低密度的建筑恰到好处的依山而筑,各有风情,左手亚洲,右手欧洲,这世上真有这么美丽的地方,难怪无数的画家、作家,都在这里发现惊奇,找到灵感。在这里,我看到了帕慕克所描写的沿岸房屋窗户的景象:“面朝博斯普鲁斯的客厅,会让椅子、沙发和餐桌面向海景,如果从马尔马拉海搭船进来,你会看见沿海峡两岸的几百万扇贪婪的窗子挡住彼此的视线,毫不留情地挤开彼此,只为了能看见你搭的船和船通过的海面。”
应该感谢土耳其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是他的许多作品让我对这个城市有了更加立体和深入的了解,仿佛一个浮光掠影的观光者,有幸遇到了一位特别有学识有见地的当地人,可以从容地听他娓娓道来关于伊斯坦布尔的那些事儿,以及生于斯长于斯的伊斯坦布尔人的想法。帕慕克笔下对于伊斯坦布尔的回忆和描述,那种细致和亲密,叫你完全可以相信,他已经刻画到伊斯坦布尔的细胞了。他描写博斯普鲁斯的笔墨尤其多,也许是因为他从小就习惯了去博斯普鲁斯划船度周末,习惯了从自己住的公寓阳台眺望博斯普鲁斯海峡上航行的各种船只——“罗马尼亚邮轮、苏维埃战舰、从特拉布宗进来的渔船、保加利亚客轮、驶入黑海的土耳其海上客轮、苏联气象观测船、高雅的意大利海轮、运煤船、巡防舰,以及生锈、斑驳、失修、在瓦尔纳注册的货运船和借黑夜掩护国旗与国籍的老船。”他的笔是神奇的,单是罗列这些船只,就足以给我们展示出这条扼欧亚大陆咽喉的海峡是何等的繁忙,何等的举足轻重,我们甚至还能从形形色色的船只名称上,看出世态万象、时局形势。人与人的区别是多么大啊,我小时候只能对着家门外的重重群山傻傻地发呆,而帕慕克从小望向窗外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看到的都是万国之船、世界局势。
与我们的船擦肩而过的,大抵都是从黑海穿海峡而来。我站在船舱后部的护栏边,看船尾的尖头如一把利剑,劈波斩浪,将深蓝色的海洋划出白刃般的海浪,浪花飞溅,离开海水腾空起来,就变成了雪白。这就是博斯普鲁斯的海水,我痴痴地盯着那深不可测的海面,这迷人摄魄的深海,这越看越让人心悸的深海,它的海面之下,到底淹没了多少往事,大到载入史册的战争,小到一个司机开车落入海峡,海水也会不动声色地先拥着小车轻转几圈华尔兹,再悄无声息地将它全部吞入。万顷碧波只是海水浮浅的美色,深蓝的下面,才是大海的咆哮,和大海的忧伤。
鲁梅利城堡
游船渐渐航行到整条海峡最狭窄的位置,鲁梅利城堡扑面而来,这个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军事建筑,以前只在电影《征服1453》里见过,现在真实版城堡就威严地矗立眼前,令人如置梦境。
这个城堡还有一个名字,叫割喉堡。
修建这个割喉堡的人,是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相当于中国的皇帝)穆罕默德二世。修建的时间,是1452年。
回溯到1451年,穆罕默德二世成为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时,年仅21岁。茨威格曾在《拜占庭的悲剧》一文中这样描述这位年轻苏丹的双重秉性:“一方面他虔诚热情,另一方面他又残忍阴险;一方面他是个学识渊博、爱好艺术、能用拉丁文阅读恺撒大帝和其他罗马伟人传记的人,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杀人不眨眼、歹毒的人。”他在成为奥斯曼帝国最高统治者之后,第一件政治行动就是派人把自己未成年的亲弟弟淹死在浴池里,以此排除自己皇权上的嫡血竞争对手。第二件事就是干掉了这位被他派去杀他弟弟的人。
那么年轻,能干出这么冷血的事情,而且计划周密,城府极深,不得不说他天生就是当帝王的料。不过,杀嫡亲这事,也是有传统的,穆罕默德二世他爹、还有他爷爷都是这样干的,所以轮到他,这种行动也不足为怪了。要说帝王这种职位,万众景仰,但真不是谁都干得了的,也不是谁都愿意干的,工作压力大、技术难度高不说,人身危险还不小,有的即便继位当了皇帝,也是勉为其难,所谓“术业有专功”“人各有志”,拿中国的皇帝来说,南唐后主李煜就不适合当皇帝,他更适合去写写诗词,小情小调。又比如明朝的明熹宗朱由校,他更适合去做木匠,在木器设计与制作的专业领域发挥特长。与此相反,这世上又总有另一些人,果敢决绝,情感稀薄,政治目标明确,谁要不幸遇上这样的政敌,那就只有自求多福了。
不幸的东罗马帝王君士坦丁十一就遇上了这么一位狠人。新上任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有着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野心勃勃,他身上具备了各种危险的力量,而且这些力量都对准了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攻取拜占庭城,也就是东罗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在他冷静而沉默的外表下,深不可测地藏着一颗腾腾燃烧的心,他要摘下与小亚细亚隔海相望的那朵欧洲最艳绝的花。
经过他祖辈和父辈几代人的开疆拓土,奥斯曼土耳其人那时已经占领了君士坦丁堡除城墙之外的全部土地,就差最后攻城决战。然而君士坦丁堡拥有中世纪最好的防御体系,东、南、北三面环海,而西面陆线修筑的城墙又无比坚实,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被这坚挺的城墙弄折了手中的弯刀。
对于14和15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东罗马拜占庭城的存在,就是“卡 在真主喉咙里的骨头”。
作为这一地区的地理中心和政治、经济中心的君士坦丁堡,仍然是拜占廷帝国的首都,如果奥斯曼人不能征服它,并从那里发号施令,他们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雄霸世界的帝国。更令奥斯曼人担心的是,不彻底拿下君士坦丁堡,万一哪天皇帝又玩出新高度,去联合某个欧洲海军强国把达达尼尔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起封锁,切断奥斯曼人由小亚细亚通往欧洲大陆的便利交通线,那才真是追悔莫及,每每想到未来可能发生的这种扼腕之痛,就会像一记警钟猛敲到穆罕默德二世的头上,令他攻打此城的决心更加坚定。
这固若金汤的城池,对苏丹的雄心仿似一种嘲讽,他曾无数次遥望着城墙之内高高耸起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巨大穹顶,看那高贵而华丽的灯光铺洒海面,看那教堂顶上凌空展开双臂拥抱世人的十字架,心里却在呼唤着他至高无上的真主,他无法平息内心熊熊燃烧的征服的欲火,他的第一步计划就是在欧洲这边修筑战事要塞,也就是眼前这个割喉堡——后来和平时期改名为鲁梅利城堡。
我们乘坐的游船在经过鲁梅利城堡时速度减了下来,大概是让我们可以仔细地瞧上几眼。紧靠鲁梅利城堡北边的,是1973年建成通车的连结欧亚大陆的吊桥——博斯普鲁斯大桥。这个城堡和这座桥,二者的建造时间前后差了六百年,但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海峡最窄处。
1453年前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属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只有亚细亚一岸,拜占庭的航船是可以畅行无碍地穿过海峡驶进黑海,驶往自己的粮仓的。现在,苏丹计划要阻断这条通道,割断拜占庭城伸向黑海的咽喉。在对面的亚洲岸,已经有苏丹巴耶济德一世早年修成的阿纳多鲁城堡,届时两岸城堡遥相配合,可以完美配合在海峡咽喉最窄处形成一道交通封锁钱,先行阻断君士坦丁堡赖以生存的海上补给线。苏丹征募了擅长建筑军事要塞的工匠世家,雇用了1000名监工、2000名苦力和众多运输工人,开始在东罗马的眼皮子底下动工修建这座要塞。

鲁梅利城堡 摄影/吴荞
君士坦丁十一也只能眼巴巴地干看着,他能做的,只能是等待欧洲各基督教国的救援。要知道,那时仅存于高大城墙之内的拜占庭帝国已经十分孱弱,在经历了十字军的劫掠和破坏,兵灾、瘟疫造成的人口锐减,以及常年不断的游牧民族的侵犯后,如今的拜占庭帝国,只剩下一个首都,连国土面积都没有了,就像一个人只剩了脑袋,并没有身子。确切的说,它只剩下金角湾那一圈被城墙包围起来的拜占庭城了,里面是教堂、宫殿和一些民居。金角湾对面的加拉太,那时也已落入热那亚人的手中。曾经横跨欧亚非三洲的拜占庭大帝国,全盛时期骑着马走上几个月也走不到边的疆域,如今只要迈开双腿,一个下午就能轻松的逛遍全国,还包括串门吃饭加唠嗑。
仅仅四个月,这座坚固的鲁梅利城堡就筑好了,两岸城堡遥遥相对,横锁海峡,封锁交通,成功切断了外界援助拜占庭帝国的海上通道。这使得原本就只剩城墙之内弹丸之地的拜占庭,越来越接近于一座孤城。
我们的航船继续前行,曾经的割喉堡,现在的鲁梅利城堡离我们的视线越来越远。
当年的割喉堡建成之后,意味着攻城大战一触即发,血与火的洗礼像宿命一样,等待着城里的每一个人。
而现在这里的夏夜,经常会举办音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