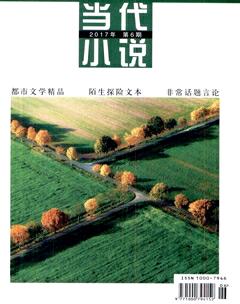谁在深夜里和我说话
柏祥伟
大雨来临之际,那个神色疲惫的中年男人,随着漫天翻滚的黄风进入了我所住的这座院子里。窗外电闪雷鸣,厚重的乌云伸手可及。气势凶猛的黄风在院子里涡旋,暴躁的呼啸声从窗户外钻进房间,飞溅的石子敲击着窗户上的玻璃,长驱直入的狂风让房间里陷入了一片昏暗里。
当时我刚用煤气灶炖熟了一锅白菜豆腐,又撕开了一袋盐椒花生,撬开一瓶白酒,等待大雨来临,把酒听雨。我起身走到窗台的墙壁上,摸到电灯开关的时候,听到喤喤的雨声已经响彻在院子里,阵阵潮湿的土腥味儿扑面撩心。我探头朝院子里看了一眼,一个黑色的人影从大门口窜进来,他恍惚不定的身影,在雨声里就像被打湿的落叶一样摇摆不定。我瞪大了眼,想再次确定他是什么人时,飘忽不定的人影像是被狂风卷走了,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我正愣怔是不是看错了的片刻,听到了几声短暂却急促的敲门声。
我对着门板喊:“谁啊?”
门缝里传来一声模糊的回答:“是我。”
他的声音潮湿无力,很快就被雨声淹没了。
我犹豫了一下,伸手拉开了铁制的门栓。嘈杂的雨声瞬间涌入我的耳朵,一阵凉风劈头打在我脸上。我不由抬手抹了一把脸,然后我看到立在门口的那个中年男人。他穿着白衫黑裤,头发乱如野草。瘦削的脸庞,糙黑的脸色,紧绷的嘴唇,深陷的眼珠儿滚动了两下,僵直的眼神戳在我脸上。
又一阵狂风从他的后背涌进来,他摇摆了一下。抬腿迈上屋门前的台阶。我闻到了一股发霉的气息,就像半个月以前,我刚入住这间屋里的味道一样,是那种干涩的、浓重的、陈旧的、有些刺鼻的霉气。
“你们爷俩长得真像。”他走进屋里,打量了几眼屋子.然后用略带嘶哑的嗓门说出了我父亲的名字:“三十年以前.我跟你父亲就是老朋友了。”
“你认识我父亲?您叫什么名字?”我边说边让他在靠墙的木椅子上坐下:“您怎么知道我来这里了?”
“我姓陈,叫陈松原,家在这个村子南边的踅庄村。三十年以前,你父亲在这个村子里插队,知识青年下乡,那个时候我和你父亲就是老相识了。”这个叫陈松原的男人揉了一把鼻子,提高了嗓门说:“听说县里派来个包村扶贫的工作人员.我一打听,居然是宋宏图的儿子。”
他再次直言不讳地叫出了我父亲的名字。他坐在木椅上.双手撑在膝盖上,偏头看着我。虽然他的神色倦怠,肤色粗糙,可是他坐在木椅上的姿势骨骼挺直,胳膊和大腿上的肌肉饱满,闪动的眼珠灵动自如,如果他跟我父亲是老朋友的话,应该像我父亲一样有七十多岁了,可他的样子却看不出一点暮气。
“我比你父亲小几岁,嗯,快四十年没见过他了。”他冲我摆了摆手,像是要对我解释,又像是自言自语:“我就是来看看你,没想到刚进门就下雨了。”
我叫了他一声陈叔。问他吃晚饭了吗?没吃的话。我俩可以坐下来喝一杯酒。
没想到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起身坐在我身旁的饭桌上。顺手摸起一双筷子在饭桌上顿了顿。我把塑料袋子里的盐椒花生倒进盘子里,摸起勺子从锅里舀出白菜炖豆腐,把酒杯放在他面前,给他倒满了酒。
我说:“早知道您来,我提前多准备几个菜呢。”
他嘿嘿地笑了两声:“这样就挺好啊,喝酒吃菜不重要.目的就是咱们爷俩一起说说话。”
陈叔的直爽让我的心情也变得轻松起来。这是我按照单位的派遣,来到这个村子半个月,开展包村扶贫工作以后,第一次有人在这间屋子里陪我吃饭。平日里跟村里的干部们一起聚餐,都是在十几里路以外的镇上的饭店里。
窗外的风小了很多,哗啦啦的雨声反而让整个天地变得安静。天气却越来越暗,我看了一眼表,已经是傍晚七点多。下雨的天气总是让人找不准时间,不过这倒是一个适合喝酒说话的空闲。虽然这是一位不请自来的客人,因为他是我父亲当年的好朋友,我觉得和他之间平添了几分亲近。我也想顺便听他聊一聊当下村子里的真实现状,跟我了解的到底有多少差距。
我坐在他对面的位置上,跟他聊起了附近村子里的一些事,现在一亩地的收入到底有多少,外出打工的年轻男女一年的收入有多少,留守妇女儿童的具体现状。大多时候,是我问,陈叔回答,不过他好像对当下农村这些事不是很清楚,也并不太感兴趣,他只是简单地用嗯或是啊等字眼,根据我的问话态度回答我。两杯酒下肚之后,陈叔的脸色变得红润了一些,他的话开始多起来,声音也显得欢快了一些。
“我给你说说我年轻时候的事吧,你愿意听吗?”没待我回答,他咂巴了一把嘴唇,像是对我倾诉,又像是自言自语:“你父亲知道我家的事,那时候他跟四五个知识青年来我们大队插队。那时候村子叫大队,乡镇叫人民公社,我们村就改了名字,叫红旗大队。我和你父亲那时候都是二十岁左右,年龄相仿,自然容易接触。不过我家是地主成分,我爹是个守财奴,政府要把俺家的土地分给老百姓,俺爹舍不得。
“俺爹死的时候很惨,却也让人憎恨,他居然把俺家的地契吞进了肚子里,然后上吊死了。他聪明了一辈子,却糊涂了一时,俺家没保住,他的命也没了。俺爹死后,我姐嫁给了我们村里最穷的一户男人。越穷越光荣,俺姐就是奔着这份光荣跟我们断绝了亲情。我跟俺娘被赶出家门,住在村口的一间用来看护庄稼的破屋里。
“我二十岁那年,又一场运动开始了。那次运动又把俺娘给拽出来了,有人举报俺家还藏匿着金银财宝。让俺娘彻底交代。那时候俺娘俩吃住都没有保障,哪里还有金银财宝呢。俺娘被拉到主席台上批斗,很多人朝她脸上吐痰。用石子砸她。她的头发被人薅掉了,头发带着头皮撕下来,冒着血珠儿,疼得她浑身冒汗。很多以前看不惯我家的人,趁机整治俺娘,给当官的头头添油加醋,惩罚她扫大街,掏大粪。那时候我还不到二十岁,觉得俺娘这个地主婆真是可恶,干嘛那么嘴硬呢,我看见她的样子就觉得厌恶。
“有一次她挨斗完回家,躺在床上哭。我真是忍无可忍了,朝她脸上啐了一口痰。俺娘当时就不哭了,她瞪着被打得青紫的眼皮看我。她问我,儿啊,你也觉得我该死吗?我说,我恨你,我也跟你划清界限,你以后不是我的娘!俺娘閉上眼没吱声。我没想到,当天晚上,俺娘也上吊自杀了。她死的时候,穿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梳了头发。
“这个人见人恨的地主婆畏罪自杀了。我拿着勒死俺娘的那根绳子去给红卫兵汇报这事。造反派的头头表扬了我,说我终于脱胎换骨了,奖励给我一枚毛主席像章。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啊。我还背会了毛主席语录,学会了跳忠字舞,歌颂伟大领袖的样板戏。我以为我的表现可以让红卫兵承认我了。可是,事情还是出现了意外,有一次我上厕所的时候,挂在胸膛上的毛主席像章不知怎么掉了下来,落在了便池里。当时被人看见了,说我侮辱伟大领袖,说我是黑五类兔崽子,心里还有反党反国家的贼心。我真是害怕了。我把像章从便池里捞出来,为了表示我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我对造反派的头头发誓,情急之下,我把像章吞进了肚子了。”
陈叔说到这里,忽然停止话头不说了,他伸直着脖子,上身抖了一下,猛地打出一个饱嗝来。我等着他再说下去,陈叔却不再说了,他抓起酒杯,仰脖喝了一口酒,像是被呛着了似的,剧烈地咳嗽起来。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惊悚的事,陈叔的讲述让我目瞪口呆。过了老大会儿,我才小声问:“后来呢?”
陈叔擦了一把眼,咽了一口唾沫说:“当时那造反派的头头吓坏了,他说你疯了吗?他用手指头抠着我的嗓眼说,你这个疯了的地主羔子你活腻了吗?我疼得浑身冒汗,满地打滚。后来很多人用地板车将我拉到镇上医院里,再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该再问他什么,正疑惑着,忽然一道闪电从窗外掠进来,一声炸雷在我头顶上响起来,吓得我浑身猛地一哆嗦,屋子里的电灯泡也跟着熄灭了。房间里陷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我正愣怔着,想起身去桌子抽屉里找蜡烛的时候,听到陈叔发出了一声叹息。
“你听说过鬼的故事吗?”陈叔在黑暗里缓慢地飘起来,就像缓缓流动的水一样,凉飕飕的,却又粘稠地贴在我的皮肤上。
“其实,我来看你没什么事,就想找人说说话,我不说觉得憋得慌。看来雨还要下一阵子。我一时半会儿走不了,我再给你讲一个鬼的故事吧。”
陈叔的潮湿的声音在黑暗里慢慢涨起来,潮水一样缓慢地却不依不饶地包围了我,我觉得我的整个身子都要在这种真实的潮水里漂浮起来了,浮萍一样随波摇摆。“古时候,一个叫宋定伯的男人赶路去集市,遇到另一个人,他问男人是谁,那人回答说,他是鬼。宋定伯回答.他也是鬼。那鬼便很高兴与宋定伯同行赶路。走了一段路,那鬼说,路途遥远,不如你我相互背着走,也节省些力气。宋定伯答应,让那鬼先背着他走了几里路。鬼说:你太重了,难道你不是鬼吗?宋定伯说:我是新鬼,所以身体重罢了。宋定伯于是又背鬼,鬼一点重量都没有。他们像这样轮着背了好几次。宋定伯又说:我是新鬼,不知道鬼害怕什么?鬼回答说:只是不喜欢人的唾沫。又走了一段路,遇到一条河,宋定伯让鬼先渡过去,听鬼过河,完全没有声音。宋定伯过河的时候,水哗啦啦地发出声响。鬼又说:你为什么有声音?宋定伯说:我刚刚死不久,不熟悉鬼怎么渡水,不要对我感到奇怪。快要走到宛县的集市了,宋定伯就把鬼背在肩上,迅速捉住他。鬼大声呼叫,要求放开让他下来,宋定伯不再听他的话。一直把鬼背到集市中,才将鬼放下在地上,鬼变成了一只羊,宋定伯就把它卖掉。又担心它变化成鬼,就朝他的脸上吐唾沫。卖掉得到一千五百文钱。”
陈叔说到这里的时候,房间里的灯骤然又亮了。从黑暗里一下子回到光亮里,刺目的光线让我眯了一下眼。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看到陈叔失神似的盯着我,他的脸上油光光的,像是冒出了一层汗。我起身给他倒了一杯水,把杯子端到他面前。他冲我摆摆手,吭哧了一声说:“你应该听说过这个故事吧?”
我点点头。
“你是怎么理解这个故事的呢?”
“有意思啊,宋定伯利用机智捉到了那个鬼。”
陈叔抽动了一下嘴角:“还有呢?你不觉得宋定伯利用了那个鬼的善良吗?”
我想了想,才对陈叔噢了一声。
“那个鬼对宋定伯善良啊,他完全信任了宋定伯,所以才被宋定伯利用了,把他的鬼命都搭进去了。”
陈叔的理解真是和我不一样,我有些羞愧地对他笑了笑。这时候,窗外的雨居然停了。似乎还有风在刮,隐约能看到云层后面的月亮散发着迷蒙的光。我甚至听到了院子里响起了蛐蛐和虫子呜叫的声音,吱吱呀呀的,打着哈欠似的,带着惺忪的睡意。雨后清新的空气钻进了房间里。我离开饭桌,走到门口,拉开了屋门。空气里带着浓郁的植物的清爽,月光也跟着淌进了屋子,空气和月光一下子联接了屋里和屋外,让人有了想出去走一走的冲动。陈叔也站起来了,他走到门口,对着院子里的月光说:“好,雨停了,你也该休息了,我也该回去了。”
我抬起手腕看看表,已经快九点了。时间过得真快,三个小时的时间,在陈叔不停的讲述中过去了。我挽留陈叔住下,明天一早再回去,他摇头拒绝,没待我再次挽留,他已经走出了院子,朝大门口的方向走去。我折身从饭桌旁拿了一把雨伞,朝陈叔追了出去,我想让他带上雨伞,再送他一段路。
我追出大门的时候,才发现这一场大雨让脚下的土路变得泥泞不堪。我迈动步子几次险些滑倒。陈叔似乎走得很快,他像是不在意脚底下的泥泞.他的身影轻飘飘的,蜻蜓点水一样行走在月光里。
我所住的这个院落在村子的最东边,是村委主任特意给我安排的一座空闲院子。白天去村里很方便,只有一条土路连接村街,通往村外的田野。我紧追了几步,前边的陈叔却越走越快,他的步履轻盈,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离我越来越远,我只得冲他喊:“陈叔。你等等我。”
我的喊声穿过潮湿的空气和朦胧的月光,追赶着陈叔的身影。话音未落,我看到陈叔的身影摇摆了一下,就像被一块飞起的石子打在后背上一样,他一个趔趄歪倒在地上。我赶紧朝他追过去,奔到他跟前。
“你没事吧?陈叔,我只是想让你慢点走,我想让你带上一把雨伞。”
我边说边弯腰去扶他。在我的搀扶下,陈叔挣扎着站起来,月亮落在他的脸上,我看到他是一副痛苦的神情。
“你嚇到我了。”陈叔试探着弯曲着左腿,哎哟了两声:“坏了,我的脚脖子崴了。”
他说着推开我的搀扶,试探着再次朝前走,他瘸着腿走了两步,又停下来,扭头无助地看着我。
万籁俱寂的深夜里,村民们早已经休息了,我不好意思再叨扰他们借用他们的车辆。我犹豫了一下,只得把雨伞递给他,然后弯腰蹲下身子。
“陈叔,我背你走吧。”
“那怎么好意思呢。”陈叔的声音落在我的后背上。他叹了口气,只是迟疑了一下,一阵窸窸窣窣的碎响,我听到陈叔说:“好吧,那就累你了,大侄子,真是不好意思。”
我说:“别客气,您趴在我后背上吧。”
“我已经趴在你身上了,你起身走吧。”陈叔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来。我很奇怪,我只是听到了陈叔的声音,却感受不到他趴在我身上的重量。我犹豫着直起腰.朝前走了两步,还是没有感觉到一点重量。陈叔趴在我身上,就像一片落叶打在我身上一样,让我没有任何感觉。
“陈叔,您的身子真轻啊,我没觉得一点重量。”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像宋定伯背的那个鬼一样轻呢?”
陈叔的话像一阵凉风灌进我的嘴巴。陈叔怎么会这样比喻呢,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陈叔也没吱声,他轻微的喘息声在我耳边回荡。我朝前走着,鞋子在泥泞里发出嘶嘶的摩擦声。路边庄稼的气息香甜清新,蛐蛐的呜叫愈发密集起来。月亮完全从云层里挣脱出来了。这一场大雨冲刷得天地一派通透,整个天地明目清心。我迈动的脚步踢得脚下的野花碎草窸窣作响。拐过一片杨树林,四周空旷。路边的杨树林被夜风刮得哗啦作响,好像是一大群鸟儿在树冠里窜动。这样的响声却显得四周更加寂静,我甚至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这个陈叔真是有些奇怪,他自我介绍说,他和我父亲是老相识了,这个晚上却没问我关于我父亲的一句话.他对我父亲的现状没表示一点的关心。此时想起他说把毛主席像章吞进肚子的情节,我的肚子也莫名其妙地疼起来:“陈叔,我想知道,当年你吞下毛主席像章,被拉到医院以后的事,你能说说吗?”
我听到陈叔吭了一声,他呼吸的气息扑打着我的耳朵:“我也不记得我被拉到医院的事了。我来就是想问问你,你父亲有没有对你说起过我以后的事。”
“您怎么会不记得呢?”我说:“我父亲没有对我说过你的事。”
陈叔噢了一声,我听出他的语气有些失望,他叹了一口气:“我记得是你父亲和另外几个知青把我拉到医院里。当时医院里的外科大夫们,都被红卫兵拉着开批斗会去了,你父亲跑着到处联系医生,他急得满头大汗,呼喊医生的声音在医院的走廊里回荡……”
“后来呢?”我忍不住停下脚步,扭头问陈叔。
“后来,后来我就死了,就什么都不记得了。”陈叔低声说:“我就是想问问你父亲,我死了以后,我肚子里那一枚毛主席像章弄哪里去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像章,可是不能随我的身子一起火化呀。”
“死了?”我说:“可是,可是你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不,我死很多年了,我知道,我早就死了。”陈叔的声音忽然变得轻飘飘的:“你不觉得我的身子很轻吗?就像宋定伯背着那个鬼一样轻呢?”
我忽然想哭。陈叔的话让我突然就想哭了。
“陈叔,您没死,你活得好好的啊。”我带着哭声说:“您没死,您看,现在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我的确是死了。在活着的人们心里,我早就死了。活着的人早就把我忘了。”陈叔在我背后挣脱了一下,他的声音越来越轻,丝丝袅袅的烟雾一样缠绕在我耳边:“侄子,你别哭,其实,鬼最怕的不是人的唾沫,最怕的是人的眼泪。”
陈叔的身子在我身后挣扎着,他让我把他放下来。
“你放我下来吧,我想起来了,前边就是我爹和我娘的坟地。我想过去看看他们,我很久很久没来看我的爹娘了。”
我弯腰蹲下身子,觉得陈叔从我后背上挪动下来。陈叔单薄的身影在月光里晃动着,就像一棵在风中摇摆的树。他跷着瘸了的左腿,抬手指着远处的一片空地说:“那地方就是我爹娘的坟地,我过去看看他们,我想我的爹娘了。”
我盯着月光里的陈叔,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怀疑是在梦里。可是我悄悄掐了一把大腿,却感觉到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下雨的傍晚,这个朦胧的月夜,我到底遇见了什么,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不敢确定眼前看到的和耳朵听到的一切,是真实还是虚幻。我不知道自己是处在恐惧之中,还是坦然的状态里。我只是看到陈叔挪动着瘸腿,朝远处那片空地走过去,他走了几步,又扭头对我说:“侄子,我没吓着你吧?”
我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还会说什么。只想跟着陈叔去他父母的坟地上看看。
陈叔说:“你回去吧,我自己过去看看就行了。”
我说:“我陪着你。”
陈叔迟疑了一下:“好吧,不过你要答应我,你别掉眼泪,我真的害怕眼泪。”
我答应了陈叔。我攙扶着陈叔从水泥路上迈下路边的浅沟里,歪斜着朝远处走去。田地里泥泞不堪,泥水灌进了我的鞋子里,有些滑溜溜的凉意,我的脚下发出嘶嘶的响声。我们歪斜着走了一段路,果然看见两座土包出现在一片长满荒草的空地里。陈叔在土包前站下了,他愣怔着打量土包,好大会儿,才自言自语似的说:“爹,娘,我来看你们了。”
“爹,娘,是我不孝顺,是我把你们气死了。”
陈叔的声音里带着哭声。他的身子哆嗦着,触电一样抽搐,他的双腿一弯,跪在了土包面前的泥水里。他只是哭着说话,我却看不到他眼窝里涌出泪水来。他跪着的膝盖朝土包前挪过去,双手摸在土包的枯草上,密密麻麻的枯草发出干涩的瑟瑟声。
“爹,娘,您的头发全白了。”
陈叔的哭声更大了,他的身子随着突然爆发的哭声扑在坟包上。陈叔的哭声是干涩的,抽搐的,就像一团结实的绳子绞在这个潮湿的月夜里。没错,他的哭没有眼泪,干硬,没有一点水分,却又不依不饶地钻入我耳朵里,让我心生疼痛。
我说:“陈叔,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呢?”
陈叔压低了哭声,他没回头,是冲着坟头说:“你不用帮我,我心里憋得慌,我哭出来就好多了。”
陈叔的悲伤让我不知所措。我正要劝他起身时。忽然看远处的水泥路上,一道刺目的车灯照射过来。就像一把剪刀刺在光滑的布上一样,车灯的光亮刺破了月光。车灯越来越近,我听到了汽车马达的哒哒声。几道手电筒的光柱在夜色里挥舞了几下,不约而同地落在了我和陈叔的身上。我听到光柱里传出几声喊叫:“那里有人!”
“是,在那边呢,赶紧过去看看!”
月色里传出砰砰的关车门、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几条光柱交叉着朝我这边晃过来。他们急促的喘息声在光柱里窜动。我扭身朝奔过来的那几条人影看。一个细长的身影冲我喊:“你是谁?在这里干什么?”
刺目的光柱让我看不清对方的面目,我只得眯着眼回答:“我送我的一个叔叔回家,怎么啦?”
“送你叔?”细长的身影迟疑着走过来,他身后的几个人影簇拥着他,几条光柱瞬间包围了我。光柱在土包上跳跃了几下.然后又落在我脸上:“哪里还有别人?你叔呢?”
我扭头朝身后看,在刺目的光柱里,我身后只是两座沉默的土包。一阵风刮过来,土包上的枯草瑟瑟作响,远处的杨树林里,传出了喑哑的鸟鸣。
陈叔不见了。
只是在我转身和这几条陌生的人影对话的瞬间,陈叔就像一滴水一样消失了。
“怎么……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转动着身子,四处打量着土包周围,我不知道我是在问这几条人影,还是在问自己:“就在刚才,陈叔还趴在这里哭呢。”
“你干什么的陈叔?”细长的人影晃了晃手电筒:“你不会是遇见鬼了吧?”
话音未落,人影里爆发出嘿嘿的笑声。
“你们是什么人?”
我有些恼怒他们对我的调侃,我靠近了他们,想质问他们的身份。那个细长人影把手电筒折到自己身上,我看到了这几个人影是穿着警服的警察,细长人影的手递过来,我顺着手电筒的光柱看,他手里是一本黑皮的工作证。
“我们是镇上派出所的警察,刚接到报案,踅庄村的一个男人突然死了。我们赶过去看看现场,路过这里。听到有人哭,就停下来看看了。”细高个的警察偏头打量着我:“你是谁?刚才是你在这里哭吗?”
我说出了我的名字和工作单位,并说出了村里村委会主任的名字。那个细高个将信将疑地点点头,他索要我的手机号,并用他的手机拨通了,听到我衣兜里的手机响起来。他才放心似的倒退了一步:
“刚才不是你在哭吗?”
“不是。”
“那你刚才没听到哭声?”
“没有。”
“哦,真是见鬼了,莫非我们几个都听错了?”细高个警察招呼那几个人影折身朝水泥路上走,又扭身对我说:“天太晚了,赶紧回去吧。”
这几个警察橐橐的脚步声朝水泥路上走过去。我愣怔地看着面前的土包,还是没怎么反应过来。水泥路上的警察钻进了车子,车灯又照亮了前方的路面,呼啸着朝踅庄村的方向走过去。四周又恢复了平静,月光流水一样缓缓地荡漾在静谧的田野里,蛐蛐的叫声越来越弱,像是快要睡着了似的打着哈欠。我抬手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已经是深夜十点半了。
我想对着空荡荡的月光喊一声陈叔,我张了张嘴巴,终于还是没有喊出声来。
那天晚上,我用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就从田野里回到了我所住的院子里。房间里的灯光还亮着,饭桌上的杯筷菜盘,散发着一股热烘烘的油腻气息。一只苍蝇在菜盘上腾展扫挪,显出了曲终人散的落寞。那个叫陈叔的男人,他的声音已经从这个房间里消失了。我能体会到的只有深夜的空虚和寂寥,犹如浓重的烟雾包裹了我,让我陷入了恍惚的感觉里。我趴在床上,顿时觉得一阵浓重的睡意涌遍了我的全身。窗外好像又开始下雨了,哗啦啦的雨声灌满了我的耳朵。翻卷的雨水从我身下飘过,我的身子像一片落叶一样在水面上随波漂浮。一阵波浪翻滚过来,像是撞在了一棵枯死的老树上,哗啦一声响,我睁开眼的同时,看到有人在拍我的胳膊。
站在我床前的是村委会主任,这个面相憨实的男人用友好的眼神看着我。他和我年龄相仿,我来村里这半个月里,在工作之余,我和他找到了共同的爱好,我俩经常在夜里坐在院子里仰望星空。面对密密麻麻的繁星,让我们只是在仰望的时候沉默不语。
“你怎么一夜没关门,也没关灯?”村主任的嗓音在白天里总是带着没来由的喜悦。夹杂着唢呐般的欢快。他瞄了一眼饭桌,指着饭桌上的筷子说:“昨天晚上谁来陪你喝酒呢?你也不让我一起来。”
他好像不在乎得到我的回答,兀自又说,他今天要去踅庄村吊唁,他一个表叔突然自杀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嗓门依然是高亢欢快的,大段大段的句子从他胡子拉碴的嘴里吐出来,让我想起流淌在山涧里的小溪,哗啦哗啦,清澈明亮。
“我这个表叔,七十多岁了。年轻时失踪了好几十年,后来突然又回来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回来这些年里,孤身一人在敬老院里住着。整天叫喊着肚子疼,一直不愿意去医院检查。后来疼得厉害了,去医院做了B超,果然检查出肚子里有阴影,摁着还很结实。外科医生把他的肚子豁开了,翻遍了五脏六腑,也没找到什么,只得又缝上了。表叔对别人说,他肚子疼是心病,医生治不了。却整天叫喊着他要死了,可是就是死不了。別人都被他叫喊得烦透了,背地里都说,要死就死,真是叫唤的猫不逮老鼠。可是谁也没想到,昨天上午,表叔却用剪刀豁开了自己的肚子,悄无声息地死掉了。你说,我这表叔是不是神经有毛病?”
村主任戛然而止的话头,像一根大棒砸在我头上,我猛地一激灵。
“你表叔叫什么名字?”
“他叫陈松原,一辈子爱看书,满肚子都是鬼啊神啊的故事。”村主任揉了一把鼻子说:“我小时候,听他讲过一个宋定伯背鬼的故事,很吓人,嗯,现在农村跟他这么有学问的老头不多了。”
村主任正说着,兜里的手机响起来,他掏出手机,对着手机说话,显出匆忙离去的神色,边打手机边一溜小跑奔出了院子。我怔怔地看着村主任的身影消失在大门口,一直到他的脚步声完全消失了,我才回过神来。我走到饭桌旁,坐在木椅上,对着饭桌上昨晚的残羹剩菜,掏出手机拨通了我父亲的电话:
“爸,您以前在村里插队的时候,认识一个叫陈松原的人吗?”
手机里传出呜呜的声音,像是有陈年的风在一直刮。半晌之后,我终于听到父亲迟缓又苍老的嘶哑声:“你说什么?大声点,我听不见。”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