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保姆故事的《温柔之歌》
毛亚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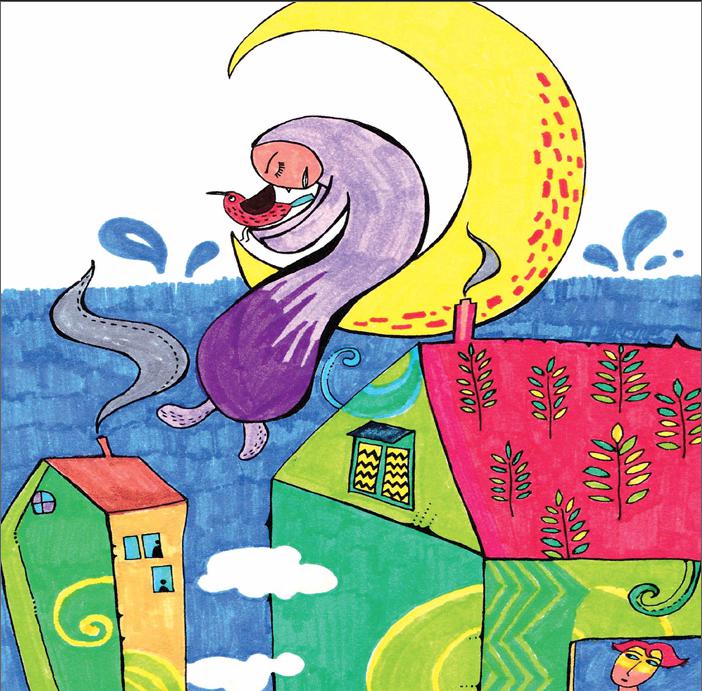
这对夫妇并不了解保姆的生活,也不知道保姆怎样对待他们的孩子,而读者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2018年还没过几天,“金牌月嫂”又上了热搜。原因是山东青岛的傅先生在调试家中监控时看到了令他“毛骨悚然”的一幕:高薪聘请的月嫂正对着自己40天大的女儿做出摇身、打脸、颠头等一系列激烈的动作!
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里,“保姆”一直是一个居高不下的“热词”。如果说6月的“杭州保姆纵火惨案”使此话题推至舆论的峰顶,那各地频繁曝出的保姆虐童事件便是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它们威胁和刺激到的是这个社会绝对的主力人群——中产父母们脆弱的神经。
保姆与雇主,彼此需要又关系微妙,二者虽分属链条的两端,却共享着一种脆弱性。我们该如何看待,又该如何去讨论它?法国女作家蕾拉·斯利玛尼的小说《温柔之歌》给出了一种解答。
女性地位的复杂现状
仅仅出版了两部小说,“80后”作家蕾拉·斯利玛尼就跻身法国文坛。2014年,她出版关于女性性瘾者的小说处女作《食人魔花园》,使其在法语文学界崭露头角。两年后,她的《温柔之歌》又让她一举拿下龚古尔文学奖,成为了龚古尔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曾经是职业记者的经历使得蕾拉擅长从现实事件中获取文学写作的灵感,她的《食人魔花园》就是取材于新闻报道的“DSK事件”。“DSK”是法国经济学家、律师、政治家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名字的缩写。2011年5月,他涉嫌在纽约市的一家饭店侵害一名女性服务员,美国警方以性侵害、非法监禁、强暴未遂等罪名起诉他。同年7月,事件出现逆转,检方发现该女服务生在性侵犯指控和个人经历的细节上有许多漏洞和不实之处。受到此案件的启发,蕾拉决定写一个关于女性“性瘾”的故事,她用亦真亦假的笔触展现出女性在两性关系这一话题所引发的争论,与当下一味讴歌女性性解放的潮流有所不同。
然而在大多数读者看来,与《食人魔花园》相比,蕾拉的第二部小说《温柔之歌》更胜一筹。故事同样取材于社会新闻。2012年10月,纽约的一位波多黎各裔的保姆杀死了她看护的孩子,并且对杀人动机讳莫如深。此事震惊到了蕾拉,她记得在报道中看到那个保姆和那对夫妇在书房的合影,那对夫妇还说,“她(保姆)是我们家的一份子”。
“婴儿已经死了。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小姑娘倒还活着……她的喉咙口全是血。肺部被刺穿,脑袋曾经遭到激烈的撞击,就撞在蓝色的衣柜上。”杀人者是时常被雇主夸赞“是个仙女”的保姆路易斯。小说一开篇,故事就已成定局。而书写保姆为何杀人,才是此书的重点。
蕾拉在接受ELLE杂志采访时表示,之所以采用“闪回”式倒叙处理,是为了打破小说主角米莉亚姆夫妇和读者之间的疆界,“这对夫妇并不了解保姆的生活,也不知道保姆怎样对待他们的孩子,而读者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读者可以全程目睹保姆抑郁得快要发疯了,而那对夫妇却因为不在场,对白天发生的一切全然不知”。
蕾拉表示,“小说中保姆的名字路易斯来源于路易斯·伍德沃事件,这个年轻的英国女孩儿在一个美国医生家庭做保姆,她猛烈地摇晃婴儿导致其死亡。对她的审判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辩护律师坚持说是由于母亲忙于工作而没对孩子尽到责任,她不应该对此有什么抱怨。此事在美国引起争论:父母可以推卸责任吗?可以确定的是,雇用夫妇确实不知不觉地冷落、忽略了孩子的保姆”。
就像读者揣测蕾拉本人是否像《食人魔花园》中的女主那样拥有双面人格一样,人们认为《温柔之歌》中的米莉亚姆身上同样有着蕾拉的影子。小说中,生了两个孩子的米莉亚姆再也无法忍受平庸而琐碎的家庭主妇生活,她决定雇用一个保姆帮她照看孩子和家务,以便自己能回归到律师的行列。“但一个女人因为忙于其他事情而找人帮忙照顾孩子,她就是自私的”,米莉亚姆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摆脱这种罪恶感。而同样是孩子母亲的蕾拉,也曾有过是做一个母亲还是做一个作家的纠结。“别人总对我说,你在家里写作,正好可以照顾你儿子啊!但实际并不是这样的,正是因为我写作才不能照顾孩子。我在怀孕的同时要写作、要正常生活,并且要为新生命的到来做准备。在我看来,这是个值得一试的挑战。”蕾拉说。
蕾拉承认自己呼吁女权主义。《温柔之歌》试图写出每位女性都会面临的烦恼,“在面对社会和找工作时,在处理和老板的关系以及照顾孩子时,女性地位的复杂现状就一点一点构建起来了”。
路易斯的心理质变
蕾拉表示,写作这部小说,唤起了她很多小时候的回忆。她从小在摩洛哥长大,家里有请保姆的习惯。她时常会想起小时候保姆说过的那些让她不舒服的话,“我很难过,我们和这些女人之间永远存在着这样的鸿沟”,蕾拉说。
阶层的分化,源于各阶层的自我认知,其他阶层则属于“他者”。这点在男主人保罗挑选保姆时已经显露无遗,“不能是黑户,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吧……我可不想找一个随时会出现问题,可能招来警察或者需要去医院的人。至于其他方面,不要太老,不要抽烟的。最重要的是要灵活点,能专心带孩子”。
即便那个新闻原型中的雇主称那个杀了人的保姆曾经是家里的一份子,但事实上,雇主和保姆的关系是微妙的,也是界限分明的。小说里,虽然米莉亚姆尽自己所能,不伤害路易斯,不想让她感到嫉妒或者痛苦。比如她会经常送东西给路易斯,会在地铁口一家便宜的小店里买耳环、橘子蛋糕给她,把自己不穿的衣服给她,同時也顾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侮辱她。甚至逛商店替自己和孩子买东西时,她总把新衣服放在一个旧布包里,只有路易斯走了之后才拿出来。家庭晚宴上也邀请路易斯入座,向朋友介绍她,就像介绍自己一个熟悉的朋友。但事实证明,这些努力是徒劳的。
和米莉亚姆一家的那次希腊之行也许是悲剧的开端。路易斯在那次度假中发现了阶层的差异,认为自己的生活存在改变的可能性。蕾拉这样写道:当路易斯漂浮于幽蓝美丽的海水之中,回想起孩提时代,班里有个同学掉进了村口的池塘。那是一片泥泞的水塘,在夏天里散发出一股恶心的气味。她想到那片黑暗的、腐朽的水面,还有在烂泥中找回的那个孩子的脸。童年肮脏的池塘与现在清澈明净的大海成了两种世界的比照。endprint
路易斯的这种心理质变,在小说中有迹可循。在蕾拉笔下,路易斯表面上看来,是那种“非常沉着”,目光中透露“是一个什么都明白、什么都能原谅的女人”,也正是凭借这种平静稳重的气质,加上她近乎完美的业务水平,路易斯才会轻易得到米莉亚姆一家人的信服。但婴儿的父母不清楚的是,这其实是一个拥有很多“残忍的故事”的保姆:路易斯的睡前故事像魔法一样驯服了孩子们,孩子从来没听过这样的故事,故事里都是同一类人物,孤儿、迷路的小姑娘、被囚禁的公主、吃人妖魔丢弃的城堡。而这些意象的背后,指向的是保姆身后不堪的现实处境——死去丈夫留下的难以偿还的巨额债务、拖欠的房租以及痛苦而灰暗的精神折磨。
于是,希腊之行后,困境中的路易斯开始寄希望于雇主能够有求于她,让她更深入地介入到这个家庭,从而过上另一种世界的生活。蕾拉这样写道,“她现在有了一种私下里产生的信念,灼热的、令她感到痛苦的信念,那就是她的幸福取决于他们。她属于他们,他们属于她。”
蕾拉最高明的地方在于,面对保姆与雇主的共处,读者无从替残忍的凶案寻到一个真正可靠的逻辑线索。因为在她的笔下,保姆路易斯并不是一个心机深重的罪犯,而是一个痛苦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可怜人,而雇主米莉亚姆,亦不是个富有而挑剔的女主人,相反,她温和而友善,家庭生活拮据克制。
无法跨越的鸿沟
随着路易斯对这个家庭越来越深的介入,米莉亚姆和保罗开始警觉,原有的和谐开始坍塌。小說提到保罗看到路易斯在他家待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会感到焦虑,“我可不希望有一天,他指控我们剥削她”。随着关系的越来越紧张,平衡被慢慢打破,斗争和悲剧也就开始了。
有一天,回到家的米莉亚姆发现保姆和孩子用餐的餐桌上摆放着油光铮亮的,光秃秃的,一丝肉都不剩的鸡架——那是她早晨扔进垃圾袋里的。路易丝显然是将女主人扔进垃圾袋里的鸡架捡回了,并让孩子们将鸡上剩余的肉啃得干干净净,之后再用洗涤液将鸡架洗净,再摆放在厨房显眼处,以此来报复女主人的“浪费”。这使得米莉亚姆觉得那鸡架“就像某种恶意的图腾”。以至于她预感到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那动物没准儿会活过来,跳到她的脸上,站在她的头发上,将她逼到墙边”。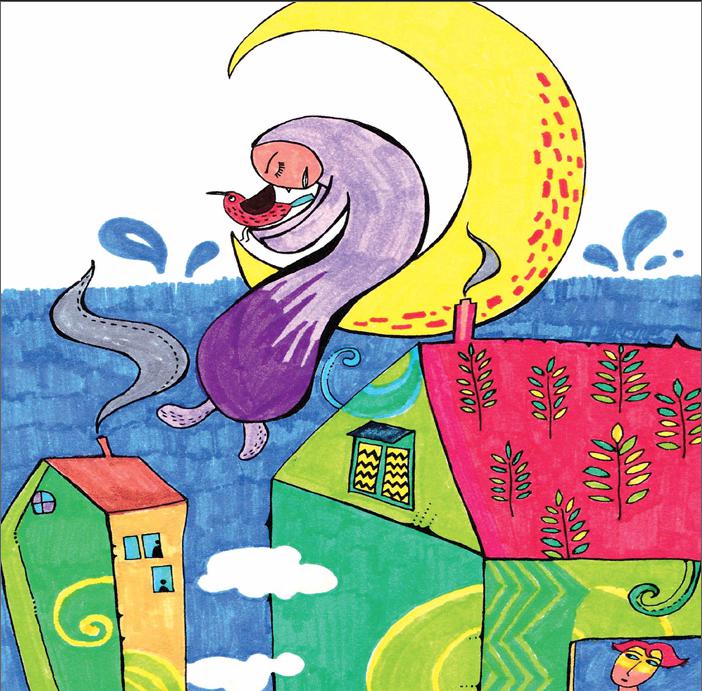
米莉亚姆认为是时候做个了结了——“人们只有在不彼此需要的时候,才会是幸福的,只过自己的生活,完全属于自己的、和别人无关的生活。”但她同时还担忧起来,“路易斯有他们家的钥匙,她什么都知道,她已经深深嵌入这个家,所以现在似乎根本不可能迁往别处。他们把她推出去,可她会再回来的。他们和她说再见,可是她会贴在门上,还是会回来,就像一个受伤的情人,极其危险”。
路易斯注定是米莉亚姆一家的外来者,雇主们甚至并不了解这个保姆在家庭之外的状况,也不会关心她的心理状态。书中最绝妙的一个细节,在小说后半段,当米莉亚姆夫妇从朋友家开车回来的路上,无意中在人群中看见了他们的保姆——她正走在马路上。这激起了女主人强烈的好奇心,第一次,米莉亚姆在家庭生活之外的地方看到了路易斯,“一副不合时宜的样子,娃娃领、裙子很长,就像是走错了故事的人物,身处一个陌生的世界,注定要永远流浪”。那一瞬间米莉亚姆觉得,路易斯对他们而言如此陌生。
虽是“他者”,他们却相互需要,这是悲剧真正的源头。面对保姆与雇主的共处,读者无从替残忍的凶案寻到一个真正可靠的逻辑线索。但却在蕾拉步步推进环环相扣的无数个细节中走到了凶案发生的那刻。这不得不让人意识到,有些事情即使复盘,也无从避免。当路易斯的存在满足了米莉亚姆所需的同时,不要忘了,路易斯也需要走进这个家庭,获得收入,实现自我价值。因此当无法说服夫妻生第三个孩子时,她滋生了杀掉孩子的念头。
寄希望于幸运?
“人们只有在不彼此需要的时候,才会是幸福的”,《温柔之歌》中米莉亚姆的这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法国著名剧作家、哲学家萨特在情景剧《禁闭》中揭示的主题,“他人即地狱”。《禁闭》的场景设在地狱的密室之中,且禁闭室里没有镜子,三个有罪的人进入到那里面,只能把他人当作镜子,只能通过他人的眼光认识自己:这三个人中,加尔散是胆小鬼,艾丝黛尔是色情狂和溺婴犯,伊内丝是同性恋和力图支配他人的心理变态者。加尔散想证明自己不是懦夫,但艾丝黛尔找不到需要的回答,他试图通过说服伊内丝来完成。艾丝黛尔作为色情狂只能从唯一的男士加尔散那里证明自己的魅力,伊内丝总想以自己的目光来支配别人,她要求艾丝黛尔把她当成镜子,又冷酷地揭示加尔散的真面目,要挟他不让艾丝黛尔获得安宁。这样,“他人的目光”让他们互相折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折磨他们的最大武器。
路易斯想通过自己的保姆身份参与、控制雇主的生活,无法避免地成为彼此的地狱。
《温柔之歌》的中文译者袁筱一在新书分享会中表示,《温柔之歌》最终推导出的是整个社会的无解。“米莉亚姆夫妇并不是真正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很窘迫,住着最小的套间,女主人做律师的收入实质是和请保姆的费用相差无几,与中国所谓的中产阶级家庭同样脆弱。
小说中,当路易斯前雇主家的小男孩艾克托在得知路易斯杀人后,“他的第一反应不是震惊或惊恐,而是终于松了口气。就好像他长期以来都深受威胁,一种纯洁的威胁,模糊的,难以表述的。这种威胁只有他、他的眼睛和他那颗孩子的心能够看到、感受到。命运希望这威胁能够在另外的地方找到出口”。由此可见,保姆路易斯争夺社会空间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她时常被不被需要的焦虑和恐慌所困扰,同时她又无法打破阶层的壁垒,所以在她的内心,日益滋长着对社会、对雇主的仇恨,最终导致米莉亚姆的孩子成为了牺牲者。
小男孩艾克托的反应实在是意味深长,这其实也反映了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时的一种普遍心态,“寄希望于幸运”。
而袁筱一则把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人的理性,“我感到可怕的地方不在于我们可能遇到什么可怕的人,而是我们的内心深处,就从来没有产生过邪恶或者挑战道德的念头吗?但拯救我们的是我们的理性,这就跟文学相关。如果路易斯有能力进行理性思考,她是不会杀人的。”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