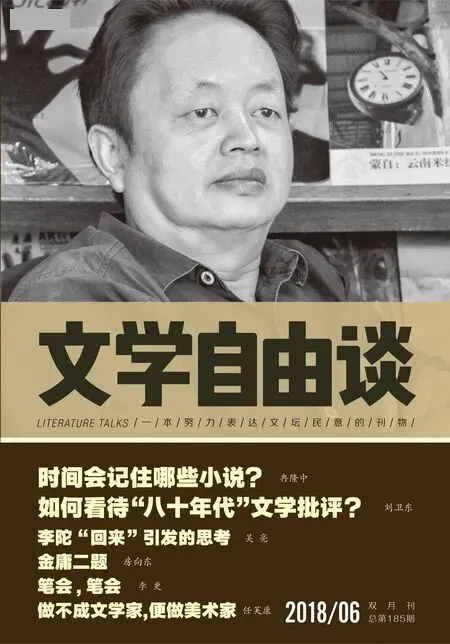“打工文学”的更名与危机
周思明
近期,有一个现象值得玩味:文学版图上为我们所熟悉的“打工文学”这个命名,被冠冕堂皇的“劳动者文学”所取代,称其为“打工文学”在新时代的延伸;而且,有学者还有意将其范畴扩大至城市白领、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在为打工文学更名者,乃至有的打工文学作者看来,“打工文学”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很不雅观的名字,就像过去穷人家的孩子叫个阿猫阿狗一样;而“劳动者文学”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官名”。其实,在我看来,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对那些急于想给“打工文学”更名的人,我倒很想问一嘴:打工者卑贱吗?打工文学下作吗?既然打工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诸多新生事物的一种,为什么就不能允许“打工文学”这一名称继续沿用下去?退一万步说,命名光鲜了,文学就高雅了吗?
其实,叫“打工文学”比叫“劳动者文学”更有本真的意义和真实的价值。这是因为,“打工文学”是诞生于改革开放以来大城市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数以亿计的进城打工者白天在流水线上从事简单机械的劳作,晚上下班后常怀 “机器人与木头人”的感叹。现实的残酷与文化饥渴激发了打工者拿起笔进行文学创作的欲望与激情,早期被学者命名的“打工文学”即由此而生。“打工文学”乃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共名”的新生事物。打工文学已然形成一个绕不开的文学现象,在新世纪文学的画廊里,已经有了“打工者”的艺术形象,中国现代文学馆里,也已经有了专为“打工文学”设立的展示专柜,成为我们这个变迁时代民族心灵史的一部分,而且,当代生活中打工者形象特殊的历史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也有目共睹。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的打工文学,经过40年的发展,的的确确已积聚了一定的人气。打工文学的活跃与打工群体的痛苦体验,让打工作家们在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省、转型社会中的矛盾冲突与复杂现实的博弈与对撞中,激发了不可遏止的创作冲动与文学灵感,真实反映了成千上万打工一族,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的独特心路历程和酸甜苦辣。
应该承认,相比于其他题材的文学板块,“打工文学”在文化积淀上先天不足,气场也显得孱弱。打工文学作家群很难获得自己的话语权,甚至在打工文学队伍中,也不乏急于甩掉认为“打工文学作家”这顶帽子不光彩,甚至丢人现眼的写作者。但中外文学发展史证明,小发展为大,弱者变成强者,不是不可能的,只是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气候,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是也。打工文学作家群体有一个共性,即他们有着“不得不说”的共同情感,苦难的底层生活遭遇,沉痛的务工生活体验,这些元素一经与新的思想相遇,就将催生新的文学创造。在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新世纪以来,打工文学继承现实主义传统,融合其他创作方法、思潮,在拓展自己的审美视野、突出作品的文学性和现实性上,有了比较突出的特色。
无论承认与否,打工文学乃是一种野生的、野性的、江湖的、体制外的、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文学物种,是现代社会转型期特有的新生事物。其基本元素是城市与乡村、上中层与底层、知识分子与农民工这三对矛盾的二元冲突。打工文学集中地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伦理、道德、人权、性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其情绪基调是农村人、小地方人在努力适应大城市生存环境的过程中心理的紧张感、异化感和断裂感。打工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是独特且重要的,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人文矛盾色彩。即使在“文化媚雅”潮流的冲击下,严肃的打工文学仍然会存在并顽强成长。当然,也要看到,由于“打工文学”整体上仍属于一种平民化、粗粝化的文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从发展的角度讲,打工文学与其他纯文学相比较,还要在美学的、历史的、艺术的、人民的范畴内做更加艰苦的努力和提升。
打工文学作家们笔下人物的痛苦,与其说来自物质的贫困,毋宁说是来自精神的、文化的、体制的压抑,诸如自我身份的被歧视、城市霸权的胁迫、文化权利的缺失等等。他们从现实中提炼出的题材,颇具象征意味,隐喻着底层的精神诉求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基层打工者在城市用血汗浇铸的对自我未来的希望,承受着生命之轻与劳作之重,生存环境的恶劣与逐步改善,生存空间的狭窄与不断拓宽,心理生理受损与不断修复,是这个群体挥之不去的梦魇与梦想。笔者欣喜地看到,打工作家群里已有王十月、郑小琼、柳冬妩、周崇贤、陈再见等作家进入主流文学视野,一批打工文学作家通过写作改变了命运。目前中国各大城市聚积着多达一亿多的农民工,且会有更多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农村城镇化的趋势也是不可逆转的。打工文学的生存与发展绝无问题:它有着学历越来越高、越来越有文化的“打工文学作家”们自我实现欲望和素质能力基础,也有着外部因素的支持,即政府、文学界、社会和读者的热诚扶助。打工文学作家及其作品应百尺竿头更上台阶,于现有基准上再接再厉,总结经验,向着更高水准发起新的冲刺。这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唤,更是打工文学的前途所在。
应该指出的是,现在评论界对“打工文学”虽然有了认同,但怀疑者、不信任者大有人在。不能说此类文学没有好作品,其中的一些佼佼者已然上升到较高审美层次,跻身国家主流文学行列。这是打工文学成功的一面。与此同时,打工文学颓败的一面也依然存在。读此类文本,感觉仍停留在诉说底层故事的层面,就像苦兮兮的鱼儿挣扎浮游在泥浆水塘而非碧蓝海洋之中,它们张开自己的嘴巴倾吐一肚子的苦水。无论是写城市农民工还是写家乡人事,还习惯于从概念出发,去演绎一个个可以引来悲悯泪水或叹息的凄惨故事;以“苦难”作为某种“论据”,图解一种底层经验;还有的作者往往依从理论界的某种说教与诱导,将笔下的人物拔高、雅化或者矮化、污名化。至于如何从打工故事里抽取、升华,使之具有审美性、思想性、可读性的艺术作品,还是一个让我们很难看到有所突破的旧格局。
目前,就全国而言,打工文学写作者已然颇具规模。他们中的一些有志者,因坚持阅读与写作而从工厂流水线上脱颖而出,成为有了名气的打工作家。务工的苦涩经历逼迫着他们成长,在收获文学创作果实的同时,也让他们的人生轨迹得以改写。这也正是打工文学能在大城市里扎根生长的客观条件和内在原因。与“打工”同步的“文学”,正在悄然改写着打工文学作者们的生活乃至命运。然而与此同时,一个巨大的悖论也浮出水面:那些苦熬出来的打工文学作家,告别了忙碌辛苦的流水线生活,告别了务工的苦闷压力及由此而生的写作冲动,其文学写作的 “后劲”也就荡然无存——这正是打工文学的危机所在。诚如有的打工文学作家指出,有些打工文学作者有了名气进入作家行列之后,内心就会排斥打工文学,觉得这种下里巴人式的文学写作类似识字班作文——层次太低。有的打工文学作者随着地位的改变和名气的提升,也不再愿意书写打工题材的作品了。打工文学曾有的粗粝、蛮野、不羁、呼喊、抗争等等,就像森林中的珍稀物种一样神秘消失,这才是打工文学真正的悲哀与危机所在,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