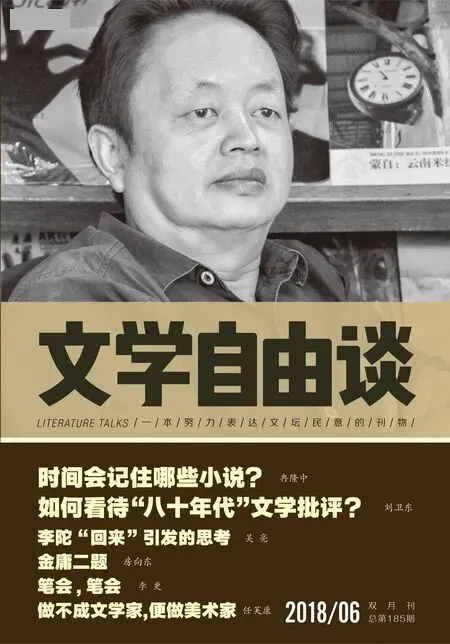批评的冬天到了,更凛冽的寒冬还会远吗?
翟业军
今年8月17日,许子东、李陀携各自的新书参加上海书展,顺道做客凤凰网,做了一个题为《文坛要有争论,当代文学批评非常软弱》的对谈。有理由、有底气指责当下的文学批评“非常软弱”,是因为他们心中矗立着一个永远回不去的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八十年代”。以“八十年代”为参照,朝向没有具体所指因而空洞成“虚指”的当下批评开炮,原本就不是一次真实、有效的批评行动,而是这两位“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风云人物所完成的又一次的自我“祝圣”仪式。他们“骂”得越狠,他们心中的神圣感就越强。他们在强烈的成圣幻觉中,误以为自己就是当下批评的救世主,忘了自己也是“非常软弱”的批评界之一员的事实。你看,李陀援引别林斯基对于果戈理的毁灭性批评,他也真的毁灭性地批评阎连科“越写越差”;但他和许子东都巧妙地回避了对彼此新作的评价,理由都是:昨天刚拿到,没看完——毫不软弱的批评必须从对面这个亲近的人开始,“没看完”只不过是他们所批判的人情社会里一个司空见惯的借口。他们对人情社会批判得越凌厉,他们的脚其实就越扎扎实实地站在人情社会之中。
“八十年代”的文学界是否流淌着牛奶和蜜,我没有发言权,不过,他们对当下批评的恶评,我基本接受;我甚至觉得,他们的抨击还是太温和了,有时还瞄不准靶心。本文就是一次瞄得更准一点、说得更透一些的努力。
我认为,我们的批评生态起码在两个方面出了严重的问题。
首先是作家和评论家关系的畸变。写作意味着把自己抛出去,与绝对的“他异性”相遇,此时的“我”不再是“我”,甚至不再是活人,而是一个幽灵,一个亟待在作品之中显影的幽灵。这样的写作者当然是孤独的,就像每一个“在死者”都是孤独的,因为他的死亡只有他自己来独自承受。批评则是在浩瀚的文本之海中,打捞与自己、进而与人类有同一种天性,从而能让自己和人类暂时性地“摆脱时间的独裁”的对象。每一次打捞都是一次别无依傍的指认,都是对于自身天性的再一次确认。这样的过程不得不是孤独的,因为唯有孤独能让批评者看到大海上一束幽暗的火,听到心灵深处一缕微弱的回声。孤独的作家与孤独的批评家之间,只能保持莫里斯·布朗肖所说的“始终维持一种无限的距离”的友谊:“我们必须以一种陌生人的关系迎接他们,他们也以这种关系迎接我们,我们之间相互形同路人。”但是,当下中国的作家和批评家都是群居动物,他们害怕寒冷,恐惧孤独,他们必须不断地聚会、研讨、对谈,相互确认,彼此输诚,慷慨激昂地宣示着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崇高立场,喋喋不休地重复着已经重复了无数次还要一再重复下去的正确的废话,却丝毫闻不到拥塞的会场里的体臭。他们哪里是路人?他们是超越了血缘关系的一家人,就像《红灯记》里“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的祖孙三代,只是《红灯记》把非亲非故的人们粘连到一处的黏合剂是阶级立场,他们则是赤裸裸的一个“利”字。对此反常现象,余华早有观察:“在中国,作家和批评家都成了‘统一战线’了,而在国外就像几十年前国共间的关系似的。”
置身于同一个统一战线、神圣同盟之中,批评家就只能一个劲地说一些搔痒不着的好话,否则会被视为挑衅、中伤,随时有可能被驱逐出统一战线。被宠坏了的作家偶尔遇到入木三分的“恶评”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你说了什么,说的对不对,而是你有没有说,为什么说。2011年,我发表《复制的写作——迟子建创作局限论》,迟子建从来没有用文字的方式回应过我对她的任一点批评,而是请江苏某位作家出面,三番五次地找我的领导向我施压;她还找当时的中国作协领导,要求组织文章批判我。以权力阻击批评,用大批判遏制学术争鸣,这是作家、批评家结成统一战线以后必然会发生的小小喜剧,因为这个统一战线只是一个分配文学的象征资源的权力场,与文学本身并无太多关联。
其次是圈子的单一化和固化。李陀说,当下批评乱象丛生的根子在于商业化。他真是抬举当下作家的写作和他们的吹鼓手们的聒噪了。要知道,文学早已退出公共视域,是电影而不是文学周期性地引爆舆论,并由此模塑着公众的精神生活。想想《芳华》所引发的集体怀旧和《我不是药神》这种“疼痛现实主义”所刺激出的汹涌的泪水吧,它们确实有点怯懦、粗糙、错乱,但就是这些怯懦、粗糙、错乱的精神制品,调节着公众情感喷发的方向、速度和流量,并最终把他们塑造成心平气和的观众。电影操控了公众的情感,当然随之收获巨大的商业利益。自说自话、自我循环的文学根本扣不住公众的情感脉搏,哪有什么商业价值,遑论什么商业化,它更无力作为流行文化的反对者,把心平气和的观众搅动成心猿意马的读者——心猿意马起来正是看穿时代之痛的前提。
当然,这是一个视觉文化的时代,文学的式微是无可挽回的事情,没必要大惊小怪。不过,中国文学式微得实在过于迅速和不堪了,究其根源,大概在于文学圈子的急遽枯萎,枯萎到只剩下一个超级圈子。只有无数个圈子之间相互竞争、彼此攻击,文学才是活的,虎虎有生机的,因为每一个势力都渴望发声,每一种审美都有机会绽放,每一样偏嗜都在誓死地捍卫自身,这不就是一幅万花缭乱的文学胜景了?在唯一的超级圈子内里,没有阴阳两极的排斥与吸引,没有否定之幽灵切开一道道本体论的裂口,从而根本性地推动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它注定是僵死的,不可能有未来。它之所以还能维持着死而不僵的现状,只是因为只有它的周期性地拿出来当作酬庸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能够被纳入文学GDP(许子东语)。只要GDP的折算方式没有发生重大改革,GDP至上主义的迷信未被打破,它就会一直活着,活在一种卸掉了过去和未来的向度的绝对的现在之中。当一切文学活动只有被折算进GDP才有意义时,文学批评家要么自己去争鲁奖,要么参与茅奖和鲁奖的“操作”,否则就近乎隐身和失语,不管他们说什么,说多少,都没什么人听见,更没什么人在意——现在,真实的批评只能是自言自语。
有人会问:不是还有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一系列奖项?可是,这些奖项哪有挣出超级圈子,构建属于自己的圈子的决心和勇气?它们不过是茅奖、鲁奖的粗陋的仿品和可有可无的补充。它们最大的梦想无非是哪一天也能够获得被折算进文学GDP的资格,哪怕被打上一个再大的折扣。
当文学批评家只能漫无边际地说一些好话,再想方设法地把这些好话编织进超级圈子的意义系统时,批评的冬天就真的到了。当超级圈子近乎疯狂地加速度运转剪灭了任何其他圈子滋长的可能,文学就像高尔夫球场一样既奢华又贫瘠时,我看不到批评的春天到来的一丁点迹象。我甚至担心,更凛冽的寒冬想必也不会远了。
2018年10月28日,玉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