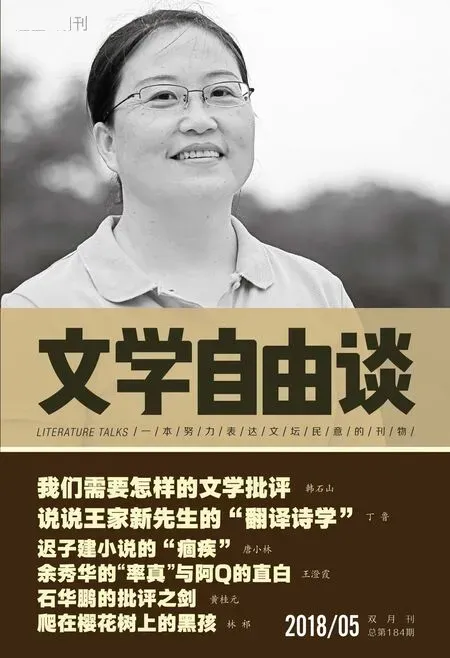当前宁夏文学题材透视
牛学智
文化现代性思想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文化自觉。“自觉”云者,按照通常的论述,好像讲的是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以及凡主体选择的便是有道理的这样一种所谓的“多元化”。其实不尽然,无论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泰勒的 《原始文化》,法国哲学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抑或法国哲学家乔治·巴塔耶的《内在性体验》等经典论著所反复指出,“主客互渗”“主客不分”仅仅是较低层次意义上主体人对客观外界的感知与体验,特别是人对客观外物产生神秘感表明的是人作为主体性的不自觉,并非人的主动选择、人的文化自觉,它们均属于人类认知局限所导致的混蒙状态。文化现代性思想所希冀的是,人从混蒙状态分离出来,成为人本身。因此,在现如今重提文化现代性思想,其首要的针对性就在于照射现代社会、现代文化完善这个大势下,人们对自身认识的暧昧与不觉醒情况,或者人们对自身认识的自为与觉醒程度。这样的一个关注点,文学题材的选择显然成了重点。在文化传统主义者看来,模拟现实及由模拟而得的传统农耕文化与价值,就是人的终极归宿,一切精神文化问题亦由此迎刃而解;在文化现代性看来,亲近现实为的是超越现实——像鲁迅0世纪20年代对浙东乡土的叙事那样,正因他获得了高于浙东乡土现实的眼光,或者正因他对人的现代化的接受、认同,使他的文学叙事思想针对了不限于具体个体人性的问题意识,因而从整体上推进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叙事的社会启蒙水平,文学的文化现代性思想才被众多知识分子所接受、所发展,终至于构成现代社会、现代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种思想资源。
今天在这里以文化现代性思想透视宁夏文学题材问题,不是为了简单回应鲁迅,也不是为了重走鲁迅路子,是为着在不可逆转的文化城镇化大势下,审视“多元化”中谁最适合人的现代化的问题。相信一些以各种变异面目存在的文化传统主义文学和以经济市场主义为圭臬的反现代性文学,会裸露其偏狭本质的。
一
就文体界限较明确的诗歌和小说看,在创作方法上,当前宁夏叙事文学基本属于现实主义写作;诗歌话语则普遍趋向于细小化、片断化和小情绪化,主要表达个体体验的平静、谦和、慵懒和向民间知识靠拢的趋势。也就是说,农耕型人物性格已经被后工业型社会结构冲击、打破,但人物还没有从他置身的文化中反过来审视这个文化,是贴近现实了,但没有反观现实、反思现实。换句话说,完成了此岸现实主义,但没有到彼岸现实主义。文学视野普遍比较狭窄,除了用真实性、客观性、逼真性等经典现实主义批评话语来论评以外,要启用新理论来分析还比较困难。
小说方面,追求题材变化比较明显的是石舒清和郭文斌。石舒清新近的短篇表现出了后现代特征,现实人和事开始自由地进入小说叙事流程,人物不像现代主义小说那样去实现因果取向的期望,拒不以开头、中间和结尾这样的成规来创作小说,打破读者的期待,不去提供整一化的世界经验。用偶然的世界来取代现代主义、现实主义所谓高级话语的世界经验,叙事比较自由,主人公不再时时处处适应作者的主观性。这样的一个明显变化,是与他以前形成并显得比较稳定的题材完全不同的。包括1998年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 《清水里的刀子》在内,以前长达20年的创作磨砺,他的小说题材基本可以清晰地分为“死亡故事”与“日常生活故事”两类。前者的典型代表是《红花绿叶》《清水里的刀子》,后者是《农事诗》《果院》等。这个变化,基本以顺序时间为经,先是死的故事,接着是平常流水日子,后来是后现代尝试。每个阶段大概都不超过10年。若按全国小说思潮和趣味来对照,石舒清似乎也是有所跟进的。20世纪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之交的一段时间,时兴“终极关怀”,这明显是创作界对批评界关于“人文精神”堕落的回应;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批评界照样率先掀起了“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化日常生活”的大讨论,这是为了论证“宏大叙事”被解构之后,何为日常”的问题,创作界在此时的一个微调是“底层叙事”变成了伪浪漫主义,即幸福故事、安逸生活。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至今,文坛差不多是70后为中锋、80后为冲锋陷阵的急先锋、60后为后卫的格局。70后的身份危机、身份揭秘,80后的青春青涩、初涉社会的忧伤难言,的确更像一盘后现代的残局。虽然60后尾巴上的石舒清的年龄与70后打头的属同代人,但他起步显然早得多。当一般的70后好不容易在《人民文学》上发一篇东西而欢呼雀跃时,石舒清小说的风格其实早已形成。文学上的不同步,阅读同龄人的作品就产生了审美上的错觉。也即是说,最近石舒清小说中的后现代特征,从接受影响的角度解释,一定程度上来自于他对某些刊物小说文本的感知,这也基本符合他的个人特点。在他的创作流程中,仔细分析,他是很少触及当前社会现实的(《低保》等不多的几篇除外),尤其是社会现实中巨变撕裂的大命题,他几乎未曾审视过。他倾心的仍是有把握自我感知自我领悟自我理解的题材,人生的小小挫败、人性的微微波动,他处理之后精致而成功。比如他见证的各种 “死”及旁观者对死”的态度,比如劳动的细微过程及背后的微妙心思,等等,这是批评界总乐意把他小说中“静”的境界看作“神性”“宗教性”“仪式化”的一个原因。
由此看来,石舒清小说的后现代特征,实际上是一种有着拼贴、穿越、欲想突变的心态下的不成熟尝试。这些小说甚至可以与他2011至2012年在《黄河文学》所开系列随笔专栏《读书记》一样去读,有点文人小趣味、小知识、小经历,但并无叙事上的什么思想张力,更不会关涉人如何不觉醒一类现代性命题。事实也如此,截止我修改此稿时间为止,再也没见过他发过类似小说。
石舒清的例子在宁夏确有典型性,不同只是在略感不适后他能很快停止,其他作家却不然。“死亡叙事”“流水般的日常日子”作为文学的永恒题材,当然怎么写都是有其意义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类在恒常中透视精神文化状态的写作,它所赋予的“神性”“仪式感”必然是相对静止的文化价值观所赐。只要相对静止、稳定的外部环境与条件支持,平凡人生中的意义感方被发掘、放大,一旦“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来源于外部,人生的恒常、人性中的确信被打破,这类题材就无法应对了。这是石舒清遭遇后现代性时显得惊悸与退缩的本质所在。其他在这类题材惯性中写作的作家,致命局限则是相信自我确认带来的激情,他们甚至连挑战题材惯性、挑战情感惯性的想法都没有,一味沉陷在“过去”的轻车熟路中而不自知,也就不会主动选择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从外面袭击时,用怎样的情感方式与形象思维来结构故事的思想能量。而新型城镇化恰好是一种从外面打破稳定、确定价值秩序的社会生活,封闭在个体内在性的人性叙事和删除社会生活只顾自然状态下人生流程的叙事,根本上就不能算是现代文化叙事,也就很难说是自觉的文化现代性故事。
石舒清所擅长的小说,其实是模拟现实的心理分析小说,适合怀旧、安妥人的漂泊感,也适合给经验共同体的人提供自我确认的喜悦、抒情、感伤、安慰,所以研究石舒清的论文,大多数都属于“审美批评”或个体道德修为的“道德批评”。说到底,石舒清小说世界所营造的,古代社会也有,现代甚至当下社会也有,区别只在里面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人的观念。这不同于现代主义小说大师卡夫卡对个体现代心理变形的分析、伍尔夫充分现代化了的集体无意识。他们关注的是个体心理如何变得不正常乃至完全异化的外部原因,叙事目的直指不正常的社会现实和不正常的现代社会机制。只有在不完善不成熟的现代社会机制中,已经有着觉醒意识的个体,才会充分感受到非人、假人、丑人,而混沌状态中的个体,即使在不成熟的现代文化中,感受到的也仍然与人的异化无关。这是石舒清有过后现代的一些尝试后马上终止的本质原因,因为后现代性毕竟是现代性里面的一种反思现代性的品质。石舒清的观念表明他并没有充分感受、体验过现代性,他也就不可能在所谓后现代性小说中植入反思现代性本身的情感与形象。
当然他在题材上的求变,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也进一步表明宁夏大多数中青年小说家普遍缺乏自觉的文化现代性意识,所以呈现为小说文本,他们的悲悯、忧伤、悲情、痛苦等,其实只是亘古以来中国文人受儒家道家文化影响的笼统的感时忧国情绪,并不具体而明确地指向一个完整意义的思想蓝图,这便是李泽厚所说的缺乏彻底转换的“旧”。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的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一章,李泽厚挨个点评完至今我们在文学学科规定性中都认为很有批判锋芒、很有个性、很有良知、很有道德感的近现代英豪、作家、知识分子的古体诗词、长篇小说、学术等后,他写到:“但在心态、情感上却并没有真正的新东西。他们没有新的世界观和新的人生——宇宙理想,来作为基础进入情感和形象思维,而旧的儒家道家等等又已经失去灵光。因此,尽管他们揭露、谴责、嘲骂,却并不能给人以新的情感和动力。这就是晚清小说之所以失败的重要原因。”
郭文斌的《农历》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全球化以后,当代中国到底有没有自己整全的价值系统?在文学叙事的层面,这种整全系统究竟有无可能内化到当代人破碎的精神生活中去?叙事充满了建构和修复的努力,最起码在叙事修辞层面是令人信服的,他的努力也就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学经验。但郭文斌的所谓新经验,也可能仅是自己的一种信仰或趣味,很难普遍化。因为有至少两个致命局限摆在那里悬而未决:一个是以始终长不大的儿童来执行并实践传统孝悌文化,这表明郭文斌倾心的传统文化中所谓的“安详主义”“祝福性”“纯洁性”,只限于人类的幼年阶段,或只适应于理想状态下的社会;另一个是狭义的或原始朴素的传统道德伦理秩序,始终是其用以安妥人们心灵世界的良药,他参照的其他文献文本必然是 《了凡四训》《弟子规》《三字经》一类古代社会童蒙启蒙读物。这说明在郭文斌的观念中,人根本是不用经济生活的,要么纷繁纠结的经济生活一旦照面,传统文化中具体的道德伦理方式方法会自动终止欲望,马上换成另一面孔来迎接摇头晃脑的礼仪生活,大家迅速集合,举止如仪。这种观念不但简化了古代社会的复杂性,更是浪漫化了现代文化和现代生活。
理想一点来展望,如果他能解决好以上两个瓶颈问题,那么,纯洁无瑕、天真烂漫、人人和谐的文化氛围、价值秩序就会建立。可是,目前来说,仅凭他个人似是而非的信仰理念与看似虔诚敬畏的态度,恐怕难以有说服力。毕竟信仰也罢,敬畏也罢,乃个人选择,无法像现代文化那样,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
二
宁夏中青年诗人诗作近年来在题材上朝向整体的、阔大的和历史纵深感的变化,颇值得肯定。如杨梓的《西夏史诗》、邱新荣的“大风歌”系列、马占祥的《半个城》、王怀凌的《风吹西海固》等等。杨梓和邱新荣的追求是,把“史诗”的经典诗歌话语方式转化成日常诗歌话语,从而提升一直以来只写琐屑生活片段这一路诗歌的品位,想要从重启象征的蓝图中,给平庸的现实赋予一种意义感,而这种意义感通过与身边细枝末节的生活兑换,达到生成价值生活的目的。从这一点说,邱新荣从上古一直到先秦他的规划一直要写到建国初期),以历史、稗史、坊间话语为轴心的诗学追求,也许还有更大的雄心。这是一种旨在建构民族主体性的诗歌表达,不止是重启了中国当代诗歌的象征系统,还要注入诗歌的历史批判维度,在历史与人文交织处,转化琐碎的日常话语,形成新的诗歌表达方向。马占祥、王怀凌把当前纳入视野,企图建构一种以地方历史、风物、人物为中心的诗学,诗中充满了社会学的辩驳。诗歌当然不是新闻写作,会迅速集结一批新词热词,零距离照应新现实。他们对诗歌经典经验的迂回观照,说明他们的确充分感知到了当下文化碎片对价值生活的毁坏,这种诗歌写作的当下意义就非常有针对性了。
然而,近年来涌现的一些年轻诗作者的“探索”,则完全相反。一是热衷于写“截句”,一首诗三言两语,甚至于一半句话就结束了。也许是追求语言写人而不是人写语言,或者短而不嫌其短、长而不厌其长之故,这类称之为“截句”的语言组合体,的确有那么点灵光一闪的所谓哲理、感悟、情绪,但总的感受是草率、粗鄙、庸俗,甚至还充满着反知识、反修辞、反结构、反思想的气息。受此类趣味的蛊惑,宁夏一批年轻诗作者沉陷于此,成天制造一些无关痛痒的词语晾晒于微信平台,相互点赞相互鼓吹。这种短与少,并不是思想精华的凝练与升华,而是表明诗作者内心的空洞与无聊,追根溯源,恐怕是“小时代”被命名以来,城市小青年对鸽子窝似的个体单元生活的一种高度认同,里面既无智慧反讽,也无批判张力,有的只是随着四时季节的轮回而生的人生俯仰,移花接木、落雨飘雪、花开花谢、绿肥红瘦看起来皆可入诗,也似乎显得相当天人合一。其实不然,这仅仅说明诗已经与脚底下真实的社会生活无关了,写诗只是某种强势流行文化趣味的二道贩子。这就谈不上创作,更遑论创新。二是对大题材、大主题、大问题无限分解,一直到“单子化”自己为主,这一情况与“截句”这个形式倒是极其相称的。如果勉强把更年轻一批诗作者看作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到了他们这一代,诗变成了另一种娱乐手段,自我的存在感重于一切,无力也不愿结构重要社会现实问题,也就暂时看不出他们这一代诗作者通过写作言说时代前沿问题的能力和技术支撑。反复无常的题材变化,表明他们正好对真正的变与不变的迟钝。这也符合无论本雅明还是麦克卢汉对机械复制时代或消费主义艺术的判断,即他们无意中把媚俗、轻逸、跟风、复制当作了创作,而严肃的创作往往被冠以臭名,或者被视为该颠覆、挖苦的对象。
到此为止,就其题材变化来说,宁夏地域诗歌发展到这个阶段,恐怕连它曾经因对西部地域文化的深度挖掘、铭记而铸造的一种优秀地域经验书写传统,都要面临严峻的挑战了。
不能不说,与以上两位小说家题材求变的不怎么成功相比较,幸好,宁夏地域诗歌还算有这批中坚力量的诗人诗作垫底,扭转了宁夏诗歌在题材上滑向偏小、偏碎、偏小情小绪的局面,证明了中青年诗人讲求规模并处理重大题材的诗歌写作能力,从某种意义上,也拯救了宁夏诗歌。
在以上所提炼的关于题材问题的典型个案以外,对照目前大多数宁夏文学(包括众多散文创作在内)所存在的共同不足,如果我们把文化现代性理解成一种内在于人的现代化的文化视野、一种文化方法、一种文化价值参照,那么,文化现代性作为一种当然语境,宁夏文学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乡土优于新型城镇、城市、都市的惯性题材决定论,就需要思想上的调整,否则,文学不单会流失大量读者,可能还会导致因文学日渐与基本的社会生活脱节而失去言说时代的契机,进而堕落为纯粹的机械码字。
第一,作家的文学思维其实是因袭多于断裂。个人事件是被迫“纯化”处理后的一种公共事务性叙事,里面的复杂社会学信息已经变得不可靠,失去了个人命运的寄存能量。一段时间,我们批判过福柯的“知识—权力”阐释模式,也认同性地转译过这个理论模式所希望的解构性叙事方式。但总的来说,从当前比较有影响的叙事文学来看,因为对“断裂”的肤浅理解,文学叙事方式只限于在文学文本——可能还是所谓“纯文学”文本的“双重否定”式循环,思维上没有进行彻底的革命,所得的现实主义不过是以个人有限的了解、观察、想象,再加上对意识形态构造的简单拼贴为基础的虚构,远没有一般性社会学著作对现实的了解,文学谁还信服?最近,伊格尔顿出版了一本书,叫《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里面有一个观点很精彩,这观点转换到文学,是说作家对经济竞争的邪恶性进行了批判,但对社会秩序的批判很少发展到财产制度的程度。他还说,现代办公室中亲善的随意着装,以及老式的等级结构或许已经让位于去中心化、网络化、团队导向、信息充足、直呼其名和开口衫为特征的组织形式。那么,等级形式,贫富差距,以及精神领域的一切不安,还是否存在?这正是正面注视成熟城市生活与文化的一个结果,不再是城与乡旷日持久对峙而产生的乡土优于城市的简单思维所能完整打捞,这都需要作家以新的理论眼光和新的社会学视野来打量这个世界。
二十多年前,一些严肃而带有普遍性的精神文化问题,比如底层”“弱势”,基本由地方基层作家率先发现,再慢慢渗透到全国一线的创作思潮;三十多年前,同样一些重要思想文化命题,比如“人文精神”“崇高”或“躲避崇高”,也基本由人生经历坎坷、生活磨难沉痛的前辈人文知识分子所首先叙事,尔后不断扩大,渐渐变成全国人性讨论的前沿热点。可是现如今情况完全变了、颠倒过来了,往往是“北上广深”、南京等一线城市作家、批评家、学者讨论西部及云集于西部的社会问题,比如社会保障体系缺失、现代性程度不高、底层社会不公等,而西部作家、批评家、学者却率先起而证伪这些问题,所谓“诗意乡村”“苦难美学”等等即是。宁夏文学在这个颠倒过来的文化思潮中,就扮演着如此审美的重要角色。不消说,其中他们的题材就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虽不能贸然断定“底层叙事”转变成伪浪漫主义就是宁夏文学所为,但当一篇篇充满祥和、幸福、安逸的底层叙事,以审美经验的名义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纷纷选载时,对于学科化的文学研究或理论批评而言,便是另一求之不得的“中国经验”。
第二,是新“国学论”——一种旨在通过拯救传统文化来获得文化自觉、自信的论述方式、话语方式,已经深入地介入到了作家的文学价值观和世界观。文学创作完全按照文化产业的思维运作,导致的主要后果是,发现了许多边缘的、偏僻的、地方性的知识、性格、故事和审美符号,但是被发现的这些东西因缺乏当代世界前沿的价值观支撑,很快变成了一大堆谁也不认识的文化信息、文化垃圾,要么一味地回到历史,讲述一些隔山打虎的陈腐故事;要么沉迷于自为性的民间,反复地打捞一幕幕在当代人看来完全属于“传奇”的传统文化仪式。当代中国人的困惑以及困惑的根源,当代中国底层群体的生存问题以及造成这些底层问题的体制性原因,基本上都在所谓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视野之外。真实性就是人们觉得的确是那么回事的感知印象。你很难说文学提供的比网络信息、手机段子和酒桌上的笑话高明多少。与其说这是人们对现实的隔膜,不如说是狭隘的文化传统主义话语给文学叙事带来的巨大灾难。对于到狭隘文化传统叙事为止,和只反映当前流行文化现象的作家来说,都是应该引起反思的。
目前的宁夏文学,其低迷根源,一定程度上,不能说与以上两种强劲思潮无关。不仅如此,细加分析还会发现,之所以如此,对于宁夏作家来说,其实还存在一个盲目追赶因而丢掉优秀传统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宁夏文学滥觞期,现实主义成就了一批作家,张贤亮、张武、戈悟觉、南台、查舜等便是典型代表。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之交,日常生活写作,以及城与乡的交织视角,也使得一批作家因发现了别人未曾发现的尖锐现实问题和精神文化问题而引起文坛普遍关注,陈继明、石舒清、火会亮、李方、漠月、季栋梁、邱新荣、杨梓、牛撇捺、朱世忠、王怀陵、薛青峰、赵炳鑫等即是。到了现如今,的确新晋了很多作家、诗人、散文家,但写作半径似乎越来越小了。一言以蔽之,就其根源,实际是过分依赖全国流行文化思潮所致,结果往往是,自己的问题被中东部作家所青睐,而自己又吃力地奔波在别人身后,勉为其难地撰写已经被时髦小说家、诗人、散文家玩腻了的题材。
三
回到文化现代性思想的角度,宁夏文学错位现象的普遍发生,似乎与没有使用好文化现代性的视角、方法、眼界等,有直接关系。文化现代性是为了更好更深入地叙事自我,而不是用以讨好杂志、选刊的花拳秀腿。不巧的是,目前的宁夏小说家、诗人、散文家,特别是新晋的大多数文学从业者,好像还沉陷在如此思维误区中,只把文化现代性当作了某种形式花样和点缀元素来利用,并没有以这一思想视野来整体打量所写对象,因此很容易以传统农耕社会形成的道德伦理具体方式方法来评价一切,很少自觉考虑水涨船高的经济社会影响、制约人们合理欲求、诉求的背后究竟缺失什么等一类根本性问题,这是值得引起宁夏作家集体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