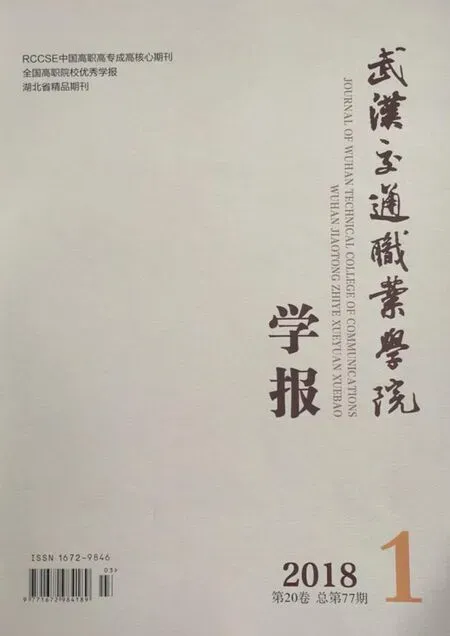特殊预防视角下的终身监禁价值评析*
李莎莎
(西南科技大学,四川 绵阳 621010)
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且致国家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死缓犯开始适用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到目前为止,已有3名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被判处终身监禁。从反腐斗争的层面来看,终身监禁不失为一把锋利的“反腐利剑”;从限制死刑适用的层面来讲,终身监禁的适用也为实现我国刑罚体系从死刑向生刑的过渡提供了一条途径。但从刑罚的目的层面来看,终身监禁更侧重于报应的实现,忽视了对罪犯的教育、矫正目的,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刑罚结构性完善。
一、终身监禁的产生背景
(一)慎用死刑刑事政策萌发终身监禁
在国际上死刑的发展开始走向消亡的背景下,我国开始了对死刑正当性与合理性以及人道性的价值评判。在我国,有的死刑废除论者认为刑罚对正义的实现并不必然要求“同态复仇”式的等量报应,而是旨在达到罪责刑相适应的价值均衡,因而死刑并非正义的要求;也有论者从一般预防论的角度指出死刑并不具有应有的威慑力,而从特殊预防论的角度来看,死刑直接消灭了犯罪人的肉体,剥夺了其获得教育、矫正的权利,违背了人能被矫正的理念;还有论者认为死刑作为最残酷的刑罚直接剥夺了人最为宝贵的权利——生命权,不再留给犯罪人改过、悔罪的机会,同时也相当于对其亲人处以极刑,死刑附随的多层负效应充分体现出其不人道,因而死刑必须予以废除[1]。而死刑保留论者则主要从死刑的报应特性以及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层面论述死刑保留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然而,理论与实践总是存在出入,国际潮流的发展方向不能直接决定我国死刑的存废大局,死刑的存废必须立足于我国国情。完全废除死刑在我国尚不适时,各种严重暴力性犯罪、贪污腐败犯罪等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尤其是现在贪污腐败犯罪呈高发态势,直接废除其死刑将会违背民意要求,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也会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灵魂,它对于一个国家的刑事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2]。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刑罚裁量过程中为法官合理量刑提供了指导思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首先意味着应当形成一种合理的刑罚结构,这是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础[2]。我国的刑罚体系由主刑与附加刑构成,其中涵括自由刑、财产刑与资格刑,这一刑罚体系看似完善,但根据我国长期的刑罚执行情况来看实际上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即“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结构性缺陷,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虽同为死刑体系,但实际执行存在天壤之别,犯罪嫌疑人获得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即表明其丧失了生的希望,而获得死刑缓期执行则表明其获得了“免死金牌”,只要没有严重的故意犯罪,通过减刑、假释终将出狱,且实际服刑时间通常与无期徒刑相当,无法体现出死刑缓期执行的严厉性。在此背景下,由于受到死刑制度发展潮流的影响,我国遂采取了“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坚持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并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刑法修正案(九)》缩减了22个死刑罪名,其中大部分属于经济型、非暴力型犯罪。贪污贿赂犯罪虽然同为经济犯罪,但我国目前正处于强力反腐的时期,直接废除该类罪名的死刑不仅会削弱死刑对贪腐犯罪所具有的功利效果,同时也会破坏民意对死刑作用的依赖。因而在慎用死刑政策的引导下,《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规定了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这也是终身监禁得以设立的政策基础。
(二)贪腐犯罪严峻形势催生终身监禁
在《刑法修正案(九)》审议的过程中,对终身监禁这一“特别死缓”应规定在刑法总则中还是仅对个罪予以适用进行过讨论,由于规定在刑法总则中涉及罪名众多,实务中不易把握,最终只增加在重特大贪污贿赂犯罪中。贪污贿赂犯罪中终身监禁的设立不仅是慎用死刑政策的体现,也是刑法针对贪污贿赂犯罪严峻形势进行的及时调整。贪污贿赂在我国同死刑制度一样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壤与制度土壤,在封建时期权力就是财富的象征,权力越大能够获得的财富也就越多,而作为当时没有权力与权利意识的平民并不会对达官贵人获取财富的方式有所异议,甚至忍气吞声的成为达官贵人财富的提供者。王朝的更迭与意识形态的发展并未将这一现象铲除,即便现在的群众对贪污受贿之人深恶痛绝,可大家却又在不同场合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维系着贪污受贿现象。贪污腐败并不仅仅是公权力腐败,就其社会成因而言,“腐败”并非某个特定社会群体的独特现象,毋宁说它是社会整体生活方式的产物[3]。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反腐败工作的坚决态度。当下我国贪污腐败呈现出“一把手腐败突出、苍蝇式腐败多发”的现象。2013年以来,全国法院已审判的中管干部职务犯罪案件达250余件;2013年到2014年期间,全国各地公开“村官”违纪违法案件171起。其中,涉案金额超过千万的案件有12起,涉案总金额高达22亿[4]。各地贿选案件及“塌方式腐败”都在挑战着刑法的底线,贪腐犯罪的严峻程度迫切需要刑法对该类犯罪案件采取强硬措施以遏制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在此基础上,《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受贿犯罪设立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将断绝其通过减刑假释提早出狱的后路,极大地威慑了贪污腐败分子,从而形成不敢腐的防范机制。
(三)减刑假释权力滥用助产终身监禁
减刑、假释是我国对被判处自由刑的罪犯通过缩减实际刑罚执行时间或提前予以释放的刑罚执行制度。对犯罪人而言,减刑假释能够缩短他们的在监执行时间从而得以早日回归社会;对监狱而言,减刑假释能够维护监管秩序的稳定,节约国家行刑资源,因而减刑假释制度在监狱的刑罚执行过程中得以经常运用。但减刑假释都存在适用前提,适用减刑要求罪犯在执行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有立功表现;适用假释则要求更为严格,除了服刑年限必须达到要求,还要在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基础上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上述适用前提看似全面,在实务中确因为缺乏可操作的量化标准而存在滥用的情形,这在贪污贿赂犯罪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监狱刑罚执行是司法的最后环节,同时也是整个司法过程中最不透明的环节。公正的司法审判建立在确实充分的证据基础之上,而刑罚的严格执行是对公正审判权威的实现。完全依照审判结果执行刑罚满足了司法权威与刑罚报应目的,确忽视了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改变。事实上审判并不只是对犯罪行为已造成的危害结果的价值评判,同时也是对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评价,法官作出的判决是结合犯罪行为的危害性这一定量与犯罪人的人生危险性这一变量的相对确定的结果,因而在刑罚执行过程中,也应当将上述定量与变量纳入刑罚执行的范畴,也就是说,对犯罪人的监禁不仅要实现对其实施犯罪行为的报应,还要考察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否降低,当行为人已经接受了足够的报应,同时人身危险性在改造过程中得以降低,那么就应当给予其减刑或假释的奖励。而我国监狱系统并无完善的人身危险性监测系统,只能通过平时罪犯的改造情况对其适用减刑假释,加之监狱系统的刑罚执行情况几乎不对外公开,一些“有权人”“有钱人”便通过自身权力地位、金钱优势所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自己的减刑、假释之路铲除荆棘,获得其不应有的提前出狱的机会。司法腐败问题同样也伤害了群众对司法制度的信任。为了填补制度上的漏洞,杜绝刑罚执行过程中的司法腐败现象,《刑法修正案(九)》对具有权力背景的贪污受贿犯罪规定了终身监禁,断绝其通过权钱交易的方式逃避刑罚措施之路,以实现对贪污贿赂犯罪的严厉打击。
二、特殊预防论视角下终身监禁的价值评析
(一)特殊预防论的要义
特别预防论是实证学派在对犯罪学的研究中逐步发展壮大并与报应论、一般预防论鼎足而立的重要刑罚目的理论。古典学派的报应刑论认为刑罚之所以实施是为了实现对犯罪行为的报应,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是基于其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一旦行为人实施犯罪,那么就应当接受刑罚的惩罚以恢复被其损害的正义。针对报应刑论缺少对犯罪人的矫正,缺乏弹性而易导致刑罚僵化的问题,一般预防论者则认为刑罚的实施主要是为了威慑社会上的潜在犯罪人使之不去犯罪,从而达到消除潜在犯罪的可能性。一般预防论实际上都是从人趋乐避苦的本能出发,认为潜在犯罪人会基于趋乐避苦的本性理性计算犯罪带来的快乐和刑罚带来的苦果,在二者之间权衡后回避犯罪行为,因此,从一般预防的威慑对象看来,刑罚的威慑效果主要是针对潜在犯罪人。特殊预防论产生于19世纪后半期犯罪激增而古典学派刑法理论却无能为力的时代。主张特殊预防论的新派学者更关注犯罪人,并致力于对犯罪原因的研究,挖掘犯罪现象背后的根源,指出同样的犯罪行为体现出的人身危险性是千差万别的,刑罚适用的根据不是犯罪行为而是犯罪人,针对不同人身危险性的犯罪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措施对其予以矫正教育或是排除出社会圈[5]。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已经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在罪与罚的选择过程中并未遵从“理性人”趋利避害的本能,这就意味着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对犯罪人已经失灵。如若此时仅以绝对的报应作为刑罚适用的根据,虽能实现对犯罪人的道义责难和对正义的恢复,却难以逃离机械惩罚的批评。实际上,犯罪人与犯罪行为多种多样,即便同犯盗窃罪,却并不一定都是为满足个人对金钱的贪婪欲望,有的行为人或许是迫于无奈而实施盗窃,如若对他们施以同样的刑罚,无疑损害了社会民众的正义情感。
通常在谈论到特殊预防论时,学者大多更为重视教育矫正理论,但实际上特殊预防论包含了许多不同观点。特殊预防论又称为个别预防论,包含了特别威慑、隔离和教育矫正等理念。其基本观点是刑罚的目的应该包括预防已经犯罪的罪犯将来不再实施犯罪行为[6]。预防罪犯未来犯罪行为需要由外及内的进行,这意味着特殊预防首先要实现对犯罪人外在消极地威慑与隔离,并在这一前提下积极对其开展教育矫正工作以实现复归社会。在大陆法系中,特别威慑论并非特别预防论者关注的重点,这是因为以威慑机制作为预防犯罪手段的一般预防对犯罪人已然失去效用,那么同一机制下的特别威慑的效果也被普遍质疑。但与一般预防论不同的是,特别威慑的理论基础是一种心理学的自我体验观:“一个人自身经验所造成的心理影响要比他人经验(即从理性上吸取教训)所造成的影响深刻地多。所以,刑罚个别威慑作用比普通威慑作用更为明显[7]。”罪犯对刑罚之恶的体验最为直接,这种亲身经历带来的体悟远比单纯想象的刑罚之苦深刻得多,而这种更为深刻的感触能够更有力地遏制犯罪人未来再次犯罪的冲动。
隔离论又称剥夺犯罪能力论,该理论认为刑罚的目的就是通过将犯罪人与社会强制隔离从而剥夺犯罪人危害社会的能力以保护社会。隔离随着自由刑的勃兴产生,并逐渐具备独立的地位。对需要长期技巧训练的罪犯和发泄性罪犯,隔离是最有效的方法。龙勃罗梭是隔离论的代表人物,他指出遗传基因塑造的“天生犯罪人”只能通过隔离才能保护社会。加罗法洛同样认为对由生物原因决定的自然犯无法教育矫正,因而只能将之隔离,“排斥出社会圈”,剥夺其再犯能力。李斯特也提出,对犯罪人应当采取“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不能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的对策,对不能矫正的罪犯,除了将其从社会中剔除,任何手段都已失效了。
教育矫正论是特别预防论中最为主要的内容,该理论认为,罪犯是由人格、社会及自然等多重原因造就的病态人格,其中社会原因又是最为主要的导火索,所以社会有义务采取各种措施治疗矫正罪犯的病态人格,教育矫正论否定了自由意志的存在,从根本上否定了报应论的立论根基,并将刑罚目的从强硬的报应导向温和的教育矫正。教育刑论的代表人物李斯特十分重视在自由刑执行中融入教育矫正的思想,他认为在刑罚执行过程中,要给予他们高质量的矫正治疗,使罪犯在执行机构内学会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法律,并将社会规范内化于心,改掉恶习,练就生活技能,达到再社会化的目的[6]。
(二)终身监禁的价值评析
我国对贪污受贿罪终身监禁的设立有其特定背景,它不仅体现出浓厚的报应气息,同时也是特殊预防论个别理论的彰显。从其法律定位看来,终身监禁作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似乎是最为合理正当的,而从刑罚目的的层面看来,终身监禁则更趋向于实现对重特大贪污犯罪分子的报应。不难看出,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虽然排除了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实现了对罪犯的隔离效果,却同样排除了刑罚的教育矫正目的。
1.终身监禁与特殊预防论的秩序价值
特别预防论将保护社会作为刑罚的出发点和归宿,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是其首要价值目标[8]。犯罪是最严重的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制裁、控制犯罪是维护自由,保障社会秩序的关键。为更有利地实现对社会秩序的维护,特殊预防论者提出应当运用多种方式矫正犯罪人或剥夺其犯罪能力,就剥夺犯罪能力而言,最有效的莫过于将犯罪人隔离,使其不能为害。但是,剥夺犯罪人再犯能力是有前提的,那就是犯罪人所体现出的高人身危险性与再犯可能性且已经无可矫正,任何刑罚措施都已归于无效,从这一前提来看,贪污受贿犯罪人是否已经无法矫正了呢?人类具有极强的可塑性,这给人的未来增添了无限可能性,不同的生存环境与社会环境使人发展各异,这表明人是可以改变的。能够实施贪污贿赂犯罪的人都是手握权力的人,他们本就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对外来事物与知识的学习理解能力很强,况且,实施贪污等经济犯罪的人同杀人犯不同,他们并非激情犯罪,会理性计算罪与罚带来的利益与痛苦,这也意味着一旦他们被抓获同样会理性衡量接受矫正与否的利益,虽不免功利,却有力地表明了贪污犯罪人是具有可矫正性的,因此不能直接将其划归为无法矫正之人。且针对贪污贿赂类犯罪,剥夺犯罪能力的方式并不止隔离这一种,作为纯正的身份犯,贪污受贿类犯罪明确要求必须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因贪污贿赂犯罪被褫夺公职的犯罪人已不可能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即便出狱后也不可能再犯。
2.终身监禁与特殊预防论的自由价值
立法者制定法律是为了构建相对和谐的社会秩序,使人与人能够共存,从而更好的保障自由[9]。自由是没有任何他人违背本人意愿下的对各种需求的满足。人需要自由,这是自然法则,是人与生俱来的最重要的价值。人对各种需求的满足是本性需要,本身没有对错之分,但满足需求的方式多种多样,除了人们内心的道德围栏,仍然需要法律对满足需求的方式予以规制。犯罪作为突破道德及法律底线的行为是最不容社会接受的,有必要以刑罚处罚。因而从维护秩序的角度讲,刑罚也是对自由的限制。严重的贪污贿赂犯罪既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破坏了民众对公务人员的信任感,同时也侵犯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给人民财产带来极大损失,刑罚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终身监禁适用范围。
特别预防论在决定论的基础上指出犯罪行为是人格、社会、自然等多种因素促成的,是无可避免的社会现象,正是因此,刑罚不可能完全消灭犯罪,只能通过社会改革来改善诱发犯罪的环境,这必然导致对个人自由的最小剥夺[8]。贪污腐败现象不仅是官员一方造成的局面,民众一方面在痛恨谴责贪污腐败的同时,又无法革除通过金钱寻求权力帮助的陋习,因此要想彻底解决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仅靠严刑峻罚无法拔出贪腐现象根深蒂固的病根,有效的社会体制改革、权力体系改革才是更好的“治疗方式”。当然,当下最为有效的处理方式自然是对贪污腐败分子的刑罚惩罚,适当的自由刑与罚金刑的结合实际上完全可以实现对贪污贿赂犯罪人的惩戒。法国监狱学家卢卡斯曾指出:“过长地监禁一个不再有危险性的人是错的”[10],我国的贪污贿赂犯罪人基本都是年过半百之人,经过长时间的关押和金额巨大的罚金刑之后,都成为鹤发鸡皮的老年人,此时多数已不具备人身危险性,且不仅丧失了生产能力,还需要监禁机构提供更多医疗保障和资源,刑罚执行的成本大幅增加甚至超过其效益。
3.终身监禁与特殊预防论的正义价值
特殊预防论虽因强调防卫社会而易走入重刑主义的窠臼,但因其对犯罪原因的研究而又富含正义的观念。特殊预防论对犯罪原因的研究促进了人们对犯罪现象与刑法功能、目的的科学认识。犯罪行为的发生并非犯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而是各种原因诱发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将罪责完全归于犯罪人,还应当考虑何种社会因素、环境因素塑造了这样一个犯罪人或者说是“病人”,对这样的“病人”,不能直接以报应之刑罚草草处理,而要在刑罚过程中矫正其不良行为,实现犯罪人再社会化。对犯罪原因的研究不仅让人们认识到刑罚存在的局限性,消除人们对刑罚惩罚功能的迷信,同时缓和了人们对犯罪人的憎恶感,促进了刑罚的轻缓化与宽容性,提升了刑罚的人道主义蕴含[8]。贝卡利亚指出:“我们的精神往往更能抵御暴力和短暂的痛苦,却经受不住时间的消磨,忍耐不住缠绵的烦恼[11]。”终身监禁摧残的不是人的肉体,而是人的精神,是在用时间慢慢消磨、葬送一个身体活着的犯人。被作为死刑立即执行替代刑的终身监禁看似缓和了我国“死刑过重”的结构性障碍,却永远地剥夺了犯罪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和塑造自由生活的希望,很难说终身监禁是更为轻缓,更具人道主义的刑罚。与此同时,终身监禁在量刑的阶段就堵死了犯罪人减刑假释的道路,忽视了人的可改造性,同样无法体现人道主义关怀。
三、余论
重特大贪污贿赂犯罪人的终身监禁制度本是为了替代死刑的适用而设置的刑罚执行措施,在当前严打贪污犯罪的情境下暂时能迎合社会民众的正义情感,但长远看来,终身监禁或许无法成为解决刑罚结构性缺陷的有效措施。因此,攻克我国刑罚结构性缺陷的难题不在于寻找死刑替代措施,而在于改革完善我国刑罚执行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当然,改革内容纷繁复杂,对刑罚制度的完善不仅关涉到刑罚执行机关的管理,也牵涉到犯罪人的权益保障,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1]何显兵.死刑的适用及其价值取向[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29-51.
[2]陈兴良,主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13.
[3]王志远,杨遇豪.反腐败的根本路径及策略保障[J].净月学刊,2015(4):13-20.
[4]陈延庆.腐败“新印象”——也谈当下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EB/OL].(2014-12-26)[2017-06-01].http://theory.rmlt.com.cn/2014/1226/364993.shtml.
[5]赵亮.中国减刑制度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2.
[6]李川.刑罚目的理论的反思与重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2,13-17.
[7]储槐植.美国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303.
[8]何显兵.个别预防论的立场及其价值分析[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5(2):24-29.
[9]曾粤兴.刑罚伦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98.
[10]张明楷.死刑的废止不需要终身刑替代[J].法学研究,2008(2):79-94.
[11]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