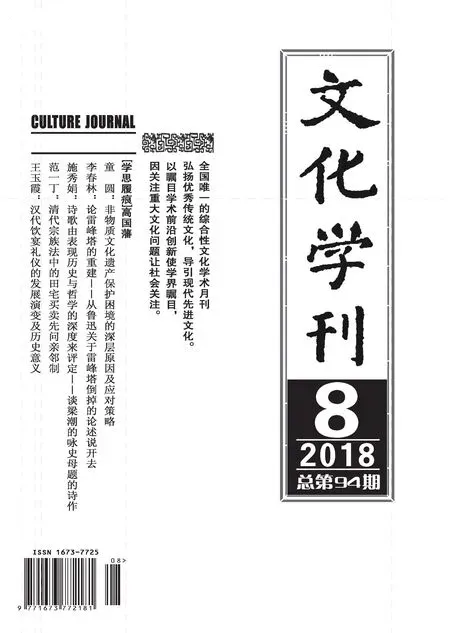论宋代科举的理学化特色
张 静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由于宋朝“佑文抑武”政策的影响,读书人将科举取仕作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崇文的时代氛围促进了理学的发展。“学而优则仕”成为读书人一生的追求,显然,科举考试的推动使宋朝成为一个有浓厚书卷气的朝代。在崇文的时代风气影响下,理学家极力主张“读书穷理”,如朱熹强调“格物致知”,“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1],穷理的途径就是读书,通过学习“四书”“五经”来参加科举考试,以求进入仕途。同样,理学也是如此,宋代的理学兼融儒释道思想于一体,形成新儒学体系,为儒学注入了理性,富有思辨性。侯外庐、邱汉生等在《宋明理学史》中论述道:“理学的实质,是用一个非人格化、精神性的‘天理’来论证封建等级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合理性与永恒性。”[2]并将这种强化统治的方式逐渐渗透在科举考试中,所以,理学与科举二者有共同的结合点,决定了其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渗透与融合。
一、科举内容及形式的理学化
理学对科举制度的影响在北宋甚微,到南宋时,理学日益受到推崇,成为南宋时期的主流思潮,理学的发展影响着士人的思想,所以也必然影响科举的选拔。这一时期,伴随着理学的兴起,科举在形式和内容等各个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设置上基本沿袭唐代,进士科最受重视,考试科目设置诗赋、帖经、墨义、策问等。宋代科举考试内容时常有所变动,时考诗赋,时考经义。在科举考试中,考试内容增加了“理”的概念,以“理”作为创作的指南和批评的标尺。理学家认为万事万物皆有理,因此,在理学家的作品中,阐释义理的作品占了很大部分。理学蓬勃发展并在南宋后期逐渐成为官学,其相关著作也成为科举考试规定的教科书,这一趋势必然影响到文人的思想。
理学家在儒家经典的外衣下阐释义理,多以注疏的形式重新解读儒家经典,《宋明理学史》中说道:“理学家注释儒家经典,把它纳入理学轨辙。他们的办法是用理学观点进行注释,用理学家的言论进行注释。”[3]如张载通过注疏经典阐发自己的观点,并写出了《易说》。此外,还出现了周敦颐的《太极图·易说》,程颐的《伊川易传》《春秋传》《诗解》,朱熹的《诗集传》等众多著作。理学家依据程朱义理对《四书》类著作的重新解释对文人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其次,宋代科举考试内容在理学的新体系下阐释儒家义理、程朱义理,其论理形式相应地以议论为主。宋代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催生了自由个性的滋长,理性精神高扬,在文学领域表现为多用议论的笔法行文。诗赋在科举考试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理学化的特点在宋代理学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不论是对待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还是国家大事,诗人自觉地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呈现出鲜明的议论特色,并在议论中表现哲理。理学家真德秀认为,诗乃“以诗人比兴之体,发圣人义理之秘”,理学家用议论的笔法论理,或表达理学思想,或表现理学风味,在吟咏性情的咏物诗中也有情与理的交融,达到了诗意与哲理的融合。
最后,内容与形式的理学化特色,使宋代科举考试在衡文评判上确立了以“理”为最高标准,“学识优良、词理精绝为第一,才思该通、文理周密为第二,文理俱通为第三,文理中平为第四,文理疏浅为第五。”(《宋史》卷一百五十五)科举考试中以涉理、论理的程度决定文章水平的优劣,科举与理学的联系更为紧密,理学的发展影响着科举的变革,科举的发展也伴随着理学而革新。
二、科举幻灭后理学家隐逸思想的发展
北宋时期,宋代科举制度不论是从内容、形式、还是制度方面,都日趋成熟,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也成为时代风气,读书人都将科举作为获取官职的“敲门砖”,但也有一批理学家独树一帜,走上了一条与科举不同的道路。经历了“五代战乱”以后,统治者强调重文轻武,崇文风气盛行,且对隐逸人士格外推崇,隐逸文学蓬勃发展。此后,变法、党争不断,大批文人卷入政治的旋涡,这一时期的科举制度也显露出一些弊端,恩荫制度造成了科举考试严重不公,阻塞了寒门士子入仕的道路,使他们心生不平。经历了宦海沉浮与不公的科举选拔后,文人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与无奈使他们将注意力转向山林自然的美景与自由,以此获得心灵的休憩。
少年时期的邵雍也曾“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4],他以读书为乐,早年也曾参加科举考试,希望通过科举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但在精通性理之学后,邵雍毅然归隐于山林,《宋史·道学传》中记载宋神宗曾连下三道诏书要求邵雍任职,他都一一回绝,从此在“安乐窝”中开始了自己的闲居生活,并创作了一系列以“乐”为主题的诗作,成为终身不仕的理学家。
同样,北宋的著名理学家张载,少年时研读儒家经典,立志博取功名,并在嘉佑二年登进士第,从此开始步入仕途,后因对王安石变法持反对态度遭到贬黜,遂辞职回乡,隐居横渠,著有《理窟》《易说》《语录》等著作,并形成了以其为中心的理学史上最大的四个学派之一——关学学派,张载也成为理学的奠基者。这些文人最初也是推崇科举考试的,希望借此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但在经历了官场的争斗后,毅然放弃科举,归隐山林。究其原因,在权利集团的斗争下,科举制度已不再是选拔人才的方式,而是政党争权的附属品或牺牲品,这一现象在南宋时更为明显。
在南宋时期,朝政上党争不断,一个突出的表现便是理学与反理学的斗争,伴随着理学发展的沉浮,理学和理学家们的处境和地位也随之变化,双方的政治主张也影响着在科举中选拔人才的方式。所以,在“学而优则仕”的愿望破灭时,一部分理学家选择了出世的人生态度。“庆元党禁”时期,道学被斥为伪学,《宋史·选举志二》记载:“是举,语涉道学者,皆不预选。”[5]“四书”也被列为禁书。这次伪学清洗运动,其目的便是将理学从科举考试中彻底清除,理学遭到沉重打击。在对现实及科举制度失望过后,理学家开始寻求新的寄托,其结果便是转向山林开始隐逸生活,这种转变一方面是畏祸心理作用,以及科举制度被政敌控制后的无奈使然,另一方面也是理学家在参透了心性之学、性理之学后,祈求到大自然寻求心灵的平静。宋代理学家注重修养,追求的最终总目的是“穷理正心”,以求得“修己治人之道”(朱熹《大学章句·序》)。理学家张载主张“虚心”,即消除利欲之心,做到清心寡欲,以此才能知理、顺理,他认为可以通过读书的方式达到博学的效果,此外,也要加强自身道德的修养。由此可见,理学家的这种心性修养影响着他们进入仕途的选择。
三、南宋以后科举的程式化
每个时代的文学思潮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要求下产生的,理学的发展顺应了宋代统治的需要,在经历了几次沉浮之后终于大放异彩,在南宋后期蓬勃发展,并成为官学,理学著作更成为科举应试的教科书,与科举考试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理学思想与科举的相互渗透也影响了文人的选择,催生了理学家隐逸思想的发展,为文学的发展增添了活力,促进了文学形式的多样性。理学发展对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具有深远意义,但在科举与理学交融的过程中,也不可忽略其产生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宋代科举考试为身居下层的读书人进入官场提供了一条相对公平的途径,但科举的程式化阻碍了文人自由个性的发展,其以论理标准来评判文章的优劣,过度追求义理的阐释,忽略了文章文采、字句的表达及思想才情的发挥,导致科举与文学审美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另一方面,科举与理学的沉浮密切相关,科举考试演变为政治斗争的场所,其政治化趋势明显,科举及文学的工具性增强,文学性减弱。科举程式化在南宋时期逐渐完备,也标志着这一制度的活力逐渐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