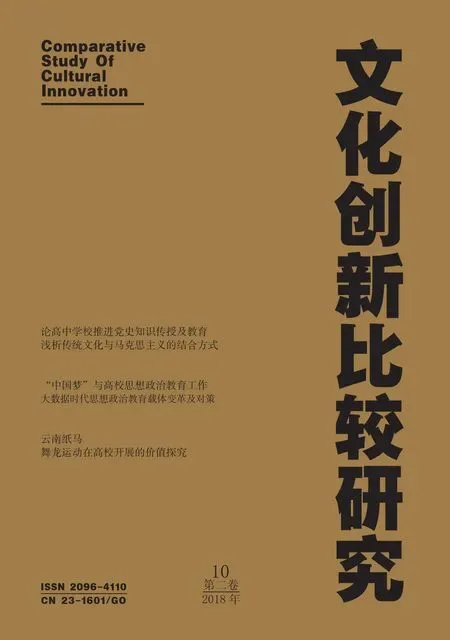从红绿之争到红绿联盟
——论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观
祝玲玲,艾志强
(辽宁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锦州 121001)
佩珀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第三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其《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一书中,清晰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生态思想对于应对当代生态运动中环境议题的政治相关性的重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绿色分子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揭露了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反人本主义和乌托邦色彩,从而建议绿色分子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现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即红色分子的联盟,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1 解决红绿之争的思想基础
随着传统工业化与城市化生产生活模式的反生态本质和不可持续性特征的暴露,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生态运动已经成为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主流,但是随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西方生态政治思潮出现了“红绿之争”。 “所谓的‘红绿之争’指的主要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在关于实现生态社会方面的纷争[1]。”在佩珀看来,“红色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充分利用了马克思主义,而绿色的生态主义者则更多地受惠于无政府主义,以至变成了生态无政府主义者[2]。”并且佩珀认为,绿色分子主张建立的生态无政府主义社会是一种反人本主义,其将自然神秘化的论调与做法最终将导致生态无政府主义沦为无法实现的生态乌托邦社会。因此,佩珀主张实现 “红绿联盟”,即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作为红绿联盟的思想基础,从而实现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绿色无政府主义积极因素的结合。
佩珀明确肯定马克思主义蕴含了丰富的生态学思想,并着重分析了马克思生态思想中两个对红绿联盟具有启示意义的理论视角。
第一个视角涉及到物质生产和集体斗争对于实现社会变革的重要性。其一,社会变革依赖于生产力的状态。马克思反对仅仅作为观念进步的历史观,他强调“物质生活中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生活进程的一般特征”[3]。因此物质生产是马克思主义历史概念的起点,物质生产构成了所有社会的基础。佩珀认为这一理论对于生态运动是重要的,因为它表明生产方式构成了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方式。因此,我们若想改变目前人与自然异化的关系,不仅要寻求人们思想意识的改变,而且更加重要地是要看到思想意识的改变对于物质生产和经济生活的依赖关系。只有如此,方能克服西方绿色分子的“意识决定论”,即人们在自然界中的实践活动将随着个人意识的变化而变化,把社会变革寄希望于个人价值观变化的思想。其二,针对绿色分子将个人作用“神圣化”的做法,佩珀更加重视马克思的社会变革集体观。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任何人想要变革社会,就必须清楚意识到社会变革如何与集体的政治斗争相关[3]。”佩珀认同马克思以阶级观点审视环境主义兴起的思想理路,因此,他认为,如果我们想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异化的状态,创建一个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少关注个人态度和价值观的变革,更多地关注全世界无产者的集体的政治斗争”[2]。这有利于克服西方绿色分子主张的“个体决定论”,即“个体在社会变革中处于关键地位,相信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否认群体运动,认为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群体,不能掌握资本生产的组织和劳动制度的观点”[4]。
第二个视角涉及到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分析。在马克思看来19世纪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由城市化、资本主义工业化以及农业化相关的经济剥削产生。因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遭受生态破坏的主要场所是工厂和产业工人的居住地,大规模农村和乡村贫民窟[5]。”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环境的破坏性时,佩珀主要选取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农业技术对环境的破坏这个视域。佩珀表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出于对农业利润的追逐,发动了通过技术来提高生产力的农业革命,然而在资本主义农业革命中,“所有的进步是在技艺上的进步,它不仅掠夺了劳动力,而且掠夺了土壤,所有在既定时间内提高土壤肥力的方法,都是一种毁灭那种肥力的持久源泉的进步”[6]。由此佩珀认为,真正引起环境破坏的是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而并非绿色分子倡导的将自然系统的破坏归咎于技术发展的技术原罪论。
2 构建红绿联盟的社会模式
在探索解决红绿之争思想的基础上,佩珀又积极探究了实现“红绿联盟”的社会模式——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并且为了切实实现红绿联盟的社会形态,佩珀在比较分析红绿双方观点差异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论述了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特点。
首先,关于红绿双方主张的差异。佩珀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第一,在环境退化根本原因的断定上。红色分子主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罪魁祸首,他们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干预自然的方式造成了土地退化和生态掠夺”[7]。但是绿色分子则认为,引起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人们之间的权力关系——等级制和支配关系,正如默里·布克金强调:“在人类社会等级制发展的同时,带来了一种统治意识,这种统治意识主要表现为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和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因此最终结局是生态危机”[8]。第二,在实现生态社会的战略上。绿色分子主张非暴力运动,在政治中对个人的崇拜取代了集体的意识,并且鄙视“工人崇拜”。对此,绿色无政府主义者布金早在1936年就不再把无产阶级说成一个革命的力量,而是把他们看成“不了解自身,缺少阶级意识和才智,屈服于偏见的群体”。与之相反,红色分子则支持暴力革命和有组织的革命先锋队。佩珀指出:“即使无产阶级在夺取权力时不想发动暴力,资方将在试图平息起义中使用暴力,因此工人阶级必须准备斗争来保卫他们的生命和事业[2]。”第三,在对待国家的态度上。绿色分子拥有简单化的国家观点,主张废除国家。他们赞同巴枯宁的主张,即“资本家仅仅因为国家的恩惠拥有他的资本,因此国家是主要的罪恶,一旦国家废除了,资本主义将会自行消亡”[9]。但是红色分子奥康纳则认为,应努力使国家民主化,而不是去尝试取消国家的生态学计划,他指出:“大多数经济,社会和生态难题不可能在地方水平上得到恰当处理,区域的,国家的和国际的计划是必要的”[11]。
其次,在比较红绿双方观点差异的基础上,佩珀又进一步描述了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特点。第一,针对绿色分子将自然神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反人本主义性质,“自然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模型,是人类的第一任伦理教师,人类必须完全顺从自然”[11]。佩珀明确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论的,他强调:“自然的权力如果没有人类的权力是没有意义的”[2]。但与资本主义短期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反,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长期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它主张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劳动来合理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第二,针对绿色分子把生态社会的经济模式设计成“自然社会”的模式,即亨特主张的“自然社会是猎人采集者的社会,是懒散的和‘经济零增长’的社会”[12]。佩珀明确表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生产,也需要发展经济,但和追逐利润和交换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建立在以人为本和使用价值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在艺术上更加丰富的社会,人们享受更加巧妙精致的食物,接受更好的教育……[14]。”第三,对于绿色分子主张的生态社会中技术必须是小规模的观点。佩珀坚决认为,这是一种技术上的非历史主义,它忽视了技术难题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联系。佩珀主张,“伴随着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旧的机器将会被更快捷,更智能化的机器所取代,并且这是一种适应自然而非异化的技术[13]。”
3 实现红绿联盟的实践策略
为了促成红绿联盟,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佩珀认为红色分子——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应该要选择性地吸收绿色无政府主义者的积极因素。因此佩珀选取了绿色分子的一些环境行动模式,虽然这些行动没有一个事例是完全让人满意的,但它们都值得红色分子的支持和仿效。
第一,采用以工会为核心的政治经济互动战略。佩珀认为,工会和劳工运动在环境运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值得提倡的,正如英格兰伯明翰老邮政大楼因为建筑工人和环境主义者的联盟而最终免于破坏等事件一样。但是针对工会运动在环境运动中的消极作用,正如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悉尼的绿色禁令由于工人团结一致的抵制而被迫取消的现象,佩珀又进一步强调,“工人”计划必须采取集体的方式,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不可能离开阶级斗争,因为“阶级斗争是将人性从资本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核心,如果没有一个意识成熟的多数社会主义者,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14]。”
第二,构建城市自治主义和国家扶持并重的治理模式。为了阻止资本主义控制国家,绿色分子曾经提出要把主要权利交给地方和基层组织,使地方共同体可以自我管理和改善他们的城市环境,比如城市自治社会主义。对此,佩珀指出:“虽然城市自治社会主义不是革命性的,但是它确实接受了一些重要的社会主义原则[15]。”例如它倡导用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来规范、控制、补充或消除市场的原则,以及对于环境的界定集中于人们的生活场所而并非原始自然的原则等。但是针对早期城市自治社会主义无法实现,以及改善城市自治社会主义的问题,佩珀强调国家扶持的重要性。在这里佩珀比较支持弗兰克尔的国家观,即“在社会主义发展中,一个有能力的国家对于计划的实现是重要的,如果没有复杂的管理和国家来确保民主参与,民权和经济的协调是不可行的”[16]。
第三,实行地方货币制度。为了克服资本在权利意识的支配下只追逐利润而无视生态危机的缺陷,绿色分子主张取消货币。但是佩珀认为,倡导一种无货币的经济在现实性上注定是一种空想。为此,他提出可以通过货币制度改革来保留货币,从而弥补绿色分子的空想性缺陷。对此,佩珀指出:“在当今社会中,权利已经不存于任何一个阶级之中,而是存在于以货币为媒介的制度本身,改革货币制度是使制度摆脱资本控制的关键[17]。”佩珀在此主要提倡的是地方货币,对于地方货币的特征,佩珀比较赞成巴顿的观点,即“成员账户起于零点;没有货币被存蓄或发行;……从没有任何贸易的义务;一个成员知道另一个成员的余额和周转;总的来说,没有余额利息被索要或支付”[18]。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佩珀所谓的地方货币仅仅是一种劳动符号,通过此种符号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凭借货币进行空间复制,预防在区域内的剥削和积累现象,规避剩余价值的区域间占有,而后者恰好是诸多环境问题的根基。在佩珀看来,具备了上述特征的地方货币一定是与生态社会主义相一致的。但是佩珀并没有真实地领悟到马克思对货币的批判,即“货币体现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货币的不同形式可能更好地适应不同阶段的社会生产,但是只要他们依旧是货币形式,那么任何货币形式都不能根除货币关系固有的矛盾,而只能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代表这些矛盾”[19]。所以,佩珀所提倡的地方货币并不能真正解决资本的控制问题。
参考文献
[1]王雨辰.论戴维·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J].汉江论坛,2008(12):27-32.
[2](英)戴维·佩珀,著.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2,4,59,259.
[3]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基本著作.伦敦:封塔纳出版社,1859:40, 50.
[4]罗斯扎克.创造一种反文化[M].伦敦:法伯出版社,1970.
[5]帕森斯·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生态学[M].伦敦:格林伍德出版社,1977.
[6]费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著作[M].伦敦:封塔纳出版社,1859.
[7]约翰斯顿.环境难题:自然、经济和国家[M].伦敦:贝尔哈温出版社,1989.
[8]默里·布克金.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9]巴枯宁,著.上帝和国家[M].朴英,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0]奥康纳.生产的“外部自然的”条件、国家和生态运动的政治战略[M].桑塔克鲁兹生态社会主义研究中心,1991.
[11]塞尔.土地居住者:一个生物区域视角[M].圣弗兰西斯科希拉俱乐部出版社,1985.
[12]亨特.自然的社会:绿色无政府主义的基础[M].牛津EOA图书出版社,1974.
[13]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14]詹姆斯·奥康纳.社会主义和生态学[J].绿色政治思想,1991(1).
[15]戴维·佩珀.公社与绿色观点:反文化、生活风格和新时代[M].巴辛托克绿色图书出版社,1991.
[16]弗兰克尔.后工业乌托邦[M].剑桥政体出版社,1987.
[17]李旦.绿色政治的红色渗透-试论戴维.佩珀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构建[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24-27.
[18]巴顿.绿色思想词典[M].伦敦:罗特里奇出版社,1988.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