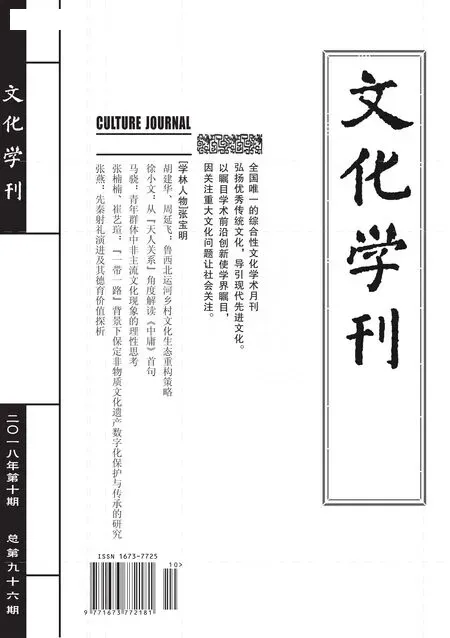解读沈从文《萧萧》对中国传统童养婚习俗的诠释
黎晓华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广东 茂名 525200)
《萧萧》创作于1929年,主要叙述湘西女子萧萧在含苞欲放的年纪被卖给一户人家给只有三岁的男孩子做童养媳,后来在情窦初开的年纪被长工花狗诱奸导致怀孕,事情败露之后婆家没有怪罪于她,依然平静地生活,后来萧萧生下了一个小男孩,在小男孩几岁时萧萧又为他取了一个童养媳。
该小说分为三条线索,一是萧萧给三岁男孩做童养媳,二是萧萧情窦初开被花狗诱奸,三是萧萧怀孕之后的生活。最后,萧萧给自己的儿子又娶了一门媳妇的结局意味深长,预示着童养婚的悲剧在不断地循环。
童养婚,也叫童养媳,是中国传统社会自家有了子嗣之后,利用强制的形式买进或者抱养别人家的子女养大成人,之后与自己的子嗣成婚的一种形式。童养婚还有一个别名叫等郎婚,这种形式是自己还没有子嗣,先把别家的女儿抱来抚养,等自己诞下子嗣之后再让两人结合。[1]童养婚是中国传统社会所特有的婚姻形式,其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所特有的根深蒂固的文化行为习惯:一是婚姻实质的买卖关系,二是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孝亲”礼制[2],三是内容与形式的挣扎,四是人性与民俗的博弈。
一、婚姻实质的买卖关系
所谓婚姻,即是结两姓之好,把两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男女双方结合在一起,肩负起繁育后代的责任,婚姻形式是人的一生中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形式,也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婚姻的实质除了繁衍后代之外,更多的一种买卖关系。沈从文的《萧萧》对婚姻买卖关系最明显的形式——童养婚进行了悲而不哀的诠释。
所谓买卖,是双方通过实物或者货币进行交换以换取自己所需物品和服务。在童养婚的习俗下,婚姻已经失去了结两姓之好的意义,更多体现为商品的买卖关系。商品是为了交易而产生的,其最大的特征是价值,价值又可分类为本质价值和使用价值,商品的本质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使用价值是商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这也就说明了商品的附属性。
在母系社会里,女性担任着生育及抚养孩子维持生存的责任,女性是社会的主人,这是女权主义时代。但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社会成为男人的天下,女性的地位一落千丈,从物质到精神都依附于男人,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更是把女性沦为男性的附属品,于是女性具备了本质价值和使用价值,成为了男性社会精神层面上的“商品”。失去了独立的人格,一直到民国初期,虽然女性不断地抗争,但似乎没有带来太大的改观。
在童养婚的形式里,一般是女大男小,男方家里一般是为了多一个劳力而寻找媳妇,女方家里则是为了少一张嘴巴吃饭及买卖关系带来的收益。在沈从文的《萧萧》中,萧萧做媳妇时年纪十二岁,有一个小丈夫,年纪还不到三岁,丈夫比她年少十来岁,断奶还不多久。其实这是一种商品的买卖关系,因为萧萧具备价值的本质属性和使用价值的基本属性。萧萧价值的本质属性是萧萧可以作为子嗣的媳妇,在小丈夫长大之后可以结婚,完成人最基本的繁衍后代责任。而萧萧使用价值是其进入公公婆婆家之后,除了完成繁衍后代的责任,还可以帮忙照顾自己的小丈夫。“她每天应做的事是抱弟弟到村前柳树下去玩,到溪边去玩,饿了,喂东西吃,哭了,就哄他,摘南爪花或狗尾草戴到小丈夫头上,或者连连亲嘴,一面说:‘弟弟,哪,啵。再来,啵。’在那满是肮脏的小脸上亲了又亲,孩子于是便笑了。孩子一欢喜兴奋,行动粗野起来,会用短短的小手乱抓萧萧的头发,那是平时不大能收拾蓬蓬松松在头上的黄发。”“每日抱抱丈夫,也帮同家中作点杂事,能动手的就动手。”[3]可见,萧萧除了带小丈夫之外,还要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这是萧萧的使用价值,萧萧的公公婆婆把萧萧娶过来,就是通过货币的交换而获得服务,所以说,童养婚的实质是一种商品买卖关系。
二、“孝亲”礼制的控诉
传统的婚姻形式一般都要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没有任何的婚姻自由,完全由父母决定,这种礼俗对中国人的影响根深蒂固。在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封建礼教影响下,这种婚姻制度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这种制度不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也酿成了不少爱情悲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源于西周的“孝亲”礼制。西周孝道有三种内涵:一为“孝亲”,主要体现为奉养、顺从在世父母;二是“享孝”,即人世“祭献”冥世祖考;三是“追孝”,追溯、缅怀祖宗之德与业,以承其志、继其业。[4]西周时期,“享孝”“追孝”能强有力地增强宗族的凝聚力,并维护天子、诸侯、大夫、士及国人的宗族等级秩序,从而占据西周孝观念的主体。而与我国婚姻礼制能够结合在一起的是第一种内涵——“孝亲”,其形成一种大家长式的封建统治单位,“百善孝为先”,这是我国传统社会最基本的伦理观念。
萧萧是典型的封建妇女,她的婚姻不能自己做主,完全由父母决定,包括萧萧长大之后有了情欲和花狗在一起导致怀孕之后,她还不能顺从自己的心意和花狗在一起,最后依旧留在公公婆婆家与丈夫成亲。这种婚姻礼俗包含着最基本的人性,但在形式上遵从着传统礼制的束缚,看似是一种对风俗的描写,揭示的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礼制。
三、内容与形式的相悖
小说的内容是小说的思想本质,但小说的思想本质又需要载体形式进行支撑,在这里把“内容”与“形式”定义为文学概念。语言是小说的载体,小说的内容需要语言形式表达出来,好的语言形式可以让小说内容更形象逼真。在《萧萧》中,随处可见乡言俗语,更添作品的形式美。无论是对湘西地理环境的描述,还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作者作为一个农民之子,最擅长的就是方言,其给作品增添了湘西之美。“唢呐后面一顶花轿,两个夫子平平稳稳的抬着,轿中人被铜锁锁在里面,虽穿了平时不上过身的体面红绿衣裳,也仍然得荷荷大哭。”[5]这是对湘西结婚风俗的描写,“不上过身”是从来没有穿过的意思,用湘西特有的口语化形式,使整个民俗更具湘西味道。
在童养婚形式上,内容和形式没有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而是作为一种悖论相结合。人的欲望是内在的东西,这叫人的潜意识,萧萧和花狗在身体生长发育到一定程度都有了情欲的需求,自然而然地发生了男女关系,萧萧因此还怀孕了,这是人的本质,但在童养婚形式之下,是违背内容而表现出来的。童养婚习俗下,媳妇的年纪一般都比丈夫大五到十岁,女人身体已经发育成长,而男人的身体还没有发育,甚至还没有存在这个男人,而等到这个男人已经长大成人具备性能力时,女人在生理上已经慢慢衰退,所以说这种夫妻结合的童养婚形式很明显是违背内容而存在的。
按照传统伦理,女人出轨是大罪,要承受浸猪笼、活活烧死等酷刑,而《萧萧》里却没有出现这样的结局,萧萧甚至连最基本的惩罚都没有受到,而生出儿子之后还可以继续和小丈夫在公公婆婆家平静地生活下去。小说平和的叙述语气透露出淡淡的悲哀,看似和谐的布局也包含了作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
四、人性与伦理的博弈
在文本的叙述中看不出作者对童养婚的态度,实质上却透露出作者的矛盾与焦虑。一方面,萧萧是自然生长发育,“几次降霜落雪,几次清明谷雨,一家人都说萧萧是大人了。天保佑,喝冷水,吃粗粝饭,四季无疾病,倒发育的这样快。”萧萧情窦初开被花狗诱奸并怀孕都是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作者并没有将这种自然的生长放到一个道德制高点去进行批判。但大伯却忽略了萧萧的自然生长发育而把她嫁给一个三岁的丈夫,这是作者对人伦不合理的平和控诉,最后还创造了一个美好却不符合现实的结局:“这一天,萧萧抱着自己新生的月毛毛,却在屋前榆腊树看热闹,如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这是人性的胜利,人伦的考验,在“五四”各类锋芒毕露的小说中,大部分的矛头都指向了封建传统礼制,更多的是倡导人性的大解放,沈从文的温情小说在“五四”潮流下似乎格格不入,但仔细研读就会发现,作者温情敦厚的笔触下暗含时代的洪流。很多关于沈从文的评论作品沉浸在作者笔下的一幅幅唯美的民俗风情画中不可自拔,而忽略了作品中人性解放的意义。传统礼俗的一夫多妻制限制着人性,但在沈从文的《萧萧》里,萧萧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还在婆家的帮助下养起了私生子,这样的结局在当时是反社会的,也是反人伦的,但其实际上与“五四”时期倡导人性的解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正是《萧萧》的时代意义所在。